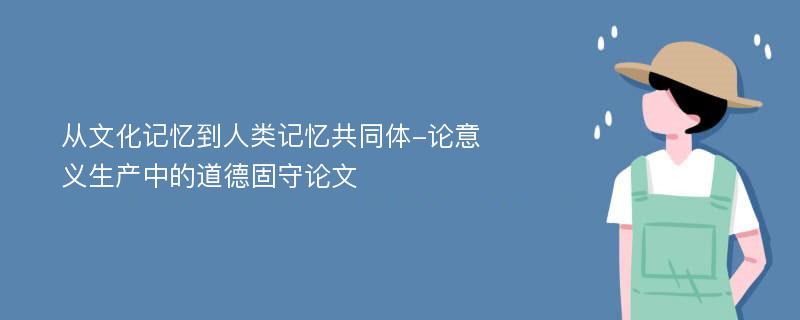
从文化记忆到人类记忆共同体
——论意义生产中的道德固守*
李 昕
[摘 要] 文化记忆深植于人类的文化结构,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相比,文化记忆更能体现人的文化存在。以文化记忆为基础构建人类记忆共同体是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前提。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再到人类记忆共同体,是意义生产从个人层面、集体层面到文化层面深度共享的过程。道德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人类记忆共同体的道德性体现在以文化记忆构建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中,受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制约而形成的一系列记忆选择、遗忘和再阐释的道德标准。这套道德标准对于维护特定群体的记忆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构建人类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局限性。正确认识文化记忆及记忆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意义生产的独特属性,勇于承担人类记忆共同体构建中的道德责任,对于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人类记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化记忆 人类记忆共同体 意义生产 道德共同体
人是文化的存在。人们习惯于将对过去事物的回忆称为记忆,大到人类的文化遗产和民族、国家的历史,小到一幢老旧建筑、儿时的玩具,都是人类“文化创造”和“文化存在”的有力证据。这些记忆碎片在今天所呈现出的色彩斑斓的文化图景不仅定义了今天的“我们”,也形塑着明天的“我们”和我们的“明天”。人类的“文化存在”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轴上以文化记忆① 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记忆”由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首先提出,主要是指文化主体为构建其身份并获取身份认同所构建的一系列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文化记忆的相关研究打破了以往记忆研究在时间、空间上的局限,以更加广阔的视角研究社会、文化和心理间的互动。 的形式呈现出来。记忆最初发生时的目的是“记住”,一旦记忆主体从单数变为复数,无论对于目的还是过程,“共享”都成为记忆延续与传承最本质的社会属性。但是,人类记忆的共享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一蹴而就的。人类如何共享记忆,共享怎样的记忆,应该以怎样的标准作为记忆选择与遗忘的底线,这些都是构建人类记忆共同体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国内外学者多有探讨,如以色列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的伦理》、著名学者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② 美国犹太裔哲学家阿维夏伊·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曾是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他的《记忆的伦理》出版后反响强烈,受到广泛好评。徐贲曾以此书为基础写了《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并作为“序”收入其同名著作,本文中的相关引文主要以徐贲的译文为准。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等均探讨了记忆中的伦理或道德问题,但这些研究多以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为对象,鲜少探讨文化记忆与构建人类记忆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从文化记忆到人类记忆共同体,是意义生产从个人层面、集体层面到文化层面的深度共享。道德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人类记忆共同体的道德性体现在以文化记忆构建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中,受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的制约,而形成的一系列记忆选择、遗忘和再阐释的道德标准。这套道德标准对于维护特定群体的记忆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构建人类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局限性。正确认识文化记忆及记忆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意义生产的独特属性,勇于承担人类记忆共同体构建中的道德责任,对于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人类记忆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从文化记忆到记忆共同体:文化层面意义生产的深度共享
共同体(Community)有狭义、广义之分,既可指有形的,也可指无形的。狭义的共同体可指社群、社区。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基于主观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如经历、身份、价值取向等方面的相似性)而形成的各种层次的有形、无形的群体统称为共同体,可以是民族的、国家的共同体,也可以是想象的共同体、记忆的共同体。共同体产生的基础是基于相似性的共同特征,共同体的延续依赖其共同特征的长久保持。
记忆共同体以相似的文化记忆为基础,通过记忆共享,形成相似的价值取向并获取身份认同,从而与其他群体相区别。文化记忆的共享不仅在于记忆内容的共享,更重要的是意义生产过程中的价值重塑。文化记忆由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发展而来,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是文化记忆意义生产的初级阶段,记忆共同体的构建本质上是意义生产结果的共享。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到文化记忆,再到记忆的共同体,是意义生产从个人层面、集体层面到文化层面深度共享的过程。文化记忆作为人类文化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其在记忆的媒介及承载方式等方面所表现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令记忆共享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这些都是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无法比拟的,因此,以文化记忆构建记忆共同体可以有效维护共同体的同一性和延续性,也最能体现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类记忆的社会性是不言而喻的。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① 莫里斯·哈布瓦赫是法国涂尔干学派第二代成员中的代表人物,早年受柏格森的个体主义思想的影响,后在涂尔干学派的影响下转向集体主义,开始社会学研究。1925年,哈布瓦赫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记忆的社会框架》(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首先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曾经指出,“不具有社会性的记忆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也只有在社会中,人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纯粹的、不受任何因素影响和约束的个体记忆是不存在的。个体记忆产生的基础是社会交往,只有在其所属的集体中与其他成员发生关联,与其他成员的记忆融合后,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记忆,并在不断回忆中获得认同,所以哈布瓦赫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②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集体记忆形成的过程就是共享个体记忆的过程,个体记忆帮助集体重构对过去的记忆,并以重构后的集体记忆决定唤起个体记忆的途径与方式。集体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传达与实现的。集体通过社会交往决定其成员的记忆,反之,如果集体不能为人们重建记忆提供帮助,或者本来拥有相同经历的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唤起共同记忆的诉求,那么集体记忆也就失去了存续的可能。因此,哈布瓦赫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③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335页。
集体记忆中的“共享”是除“记住”之外最为重要的价值指向。这种共享绝非简单的复制和分享,而是在社会框架形塑过程中的融合与渗透,是比个体记忆更加复杂和深入的意义生产。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曾经对集体记忆中的“共同记忆”和“共享记忆”进行区分,他认为共同记忆是个体记忆数量上的聚合,即“所有亲身经历着的记忆聚合起来就成为共同记忆”,而共享记忆则不仅仅是个体记忆的聚合,而且是“融合和标定事件记忆者的不同角度”。④ 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1. 转引自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第8-9页。也就是说,共享记忆来源于自由的公共交流,即使不是亲历者,也可以分享他们的记忆。集体记忆是建立在社会交往基础上的共享。哈布瓦赫曾明确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①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93页。 集体记忆构建的过程要受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的制约。这就是记忆的社会框架,也是记忆共享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记忆的社会框架不仅形塑了个体记忆,也成为集体记忆无法摆脱的窠臼。在构建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个体记忆不是被客观地保留下来,而是集体在现实语境中,按照当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要求,为巩固自身主体同一性,通过选择和借用而进行的重新阐释和建构,这个过程就是集体记忆意义生产的过程。在社会框架中的意义生产通过记忆在内容、形式和理念上的共享,形成相互交织、互为过程与因果的个体记忆及集体记忆。正是在这种相互形塑的过程中,意义生产成为记忆共享的实现方式,也成为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自身发展和演变基本的存在形态。
记忆能否被更多的人共享,能否进行更深层次的意义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记忆媒介的选择。简单来说,表现形式、传播方式不仅是区别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的重要指标,也是决定记忆共享的程度以及意义生产的广度和深度的重要因素。文化记忆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记忆的媒介。文化记忆中所蕴含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是高度符号化的产物,记忆正是借助文本、意象和仪式等记忆媒介,经过高度符号化的过程才实现了从交际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转化。在文化记忆的意义生产中,文字、图像、身体和地点都是重要的记忆媒介,其中文字的地位最为重要。文字被认为是思想的载体,能够抵御时间的侵袭,所以作为记忆的媒介一直备受推崇。这一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埃及时期,那时的文字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记忆媒介。文字的应用不但使记忆摆脱了人的寿命限制,也是“抵御社会性的第二次死亡(即遗忘)的更有效的武器”。④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2页。 但是,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正是文字的这种颇具稳定性的记录记忆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记忆的冷漠,形成遗忘。因此,对于记忆而言,仅有文字一种意义生产方式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文字也从来都不是唯一的记忆媒介。近代以来,随着文本的思想承载能力遭到质疑,图像在记忆呈现中的不可言说性和开放性及其在个体记忆保有中的特殊作用逐渐得到重视。对图像的认知离不开身体的主观感受。身体在面对图像或经历特殊事件时所产生的强烈情感是回忆重要的催化剂和稳定剂。强烈情感不仅是增强记忆的重要手段,也是回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在意义生产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成为抵御文本记忆政治书写的重要力量。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特定情况下图像和身体往往被认为是更加真实和纯粹的文化记忆的载体。此外,地点也是重要的记忆媒介。地点本身并不包含内在的记忆,作为记忆的媒介,地点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回忆空间构建中的不可或缺性。这种不可或缺性不仅表现在地点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某种记忆得到固化和证实的重要条件,更表现在,在特定历史时期地点比任何其他文化记忆的媒介更具持久性。扬·阿斯曼通过研究发现,古埃及刻满文字和图腾的神庙不仅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也是古埃及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古埃及文明曾经的辉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这些记忆的地点。
与集体记忆相比,文化记忆的意义生产体现的是更加广泛、深入和立体的共享。对于文化记忆而言,意义生产不仅是自身构建的过程,也是构建记忆共同体的过程。如前所述,“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建构”,② 这是法国学者刘易斯·科瑟在《论集体记忆》一书的序言中对集体记忆的论断。 这种建构以现实意义上的“社会交往”为基础,所以集体记忆的共享不得不依靠人类的生物学存在,这也是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称以社会交往为基础的集体记忆为交际记忆或交往记忆的原因。扬·阿斯曼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交际性的短时记忆”,指涉的是“新近的过去”,是一种与同代人或最多不超过三四代人共享的记忆,这种记忆产生于日常生活的人际交往中,以口头传承为主,并随着传承人的逝去而消亡。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不同,文化记忆是一种“文化性的长时记忆”,与绝对的过去有关,如有关人类起源之类的神话传说,是一种被高度固化的、符号化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包括语言、文字、仪式、建筑物等等。文化记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③ [德]扬·阿斯曼:《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文化研究》2011年第11辑。
“合法化”与“去合法化”是推动文化记忆意义生产的重要动力。选择与遗忘、隐瞒相伴而生。根据相应的目的和标准作出选择后所剩下的“无用的、变化冗余的、中性的、对身份认同抽象的专门知识,还有所有错过的可能性、其他可能的行动、没有利用的机会”,④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151页。 被德国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称为存储记忆。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不同,是未来文化记忆演化的前提和基础,其主要作用是为未来的文化记忆提供资源保障。这些被遗忘和被隐瞒的记忆,不但不会因为没有被“现在”选择而就此消逝,反而会成为反抗力量的集聚地,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这股巨大的力量就会通过各种渠道,以反抗者的姿态质疑、颠覆现有秩序的现实合法性,从而激发新一轮“去合法化”与“合法化”的较量。无论是以“合法化”“去合法化”还是以“区分”为目的的意义构建,都不是单个记忆主体单项记忆所能实现的,而是多个记忆主体根据不同的记忆目的在记忆共享的过程中,依照记忆选择的标准在共同的意义生产过程中实现的。正是在这种“合法化”与“去合法化”的角逐中,文化记忆不断地被形塑、重组和更新,不断派生出新的形式和内容,并在意义共享的过程中实现文化记忆的演化和社会文化的变迁。文化记忆包含的不仅仅是构建的力量,还有潜在的、巨大的破坏与重构的、反抗的力量,正是这两种力量的角逐实现了文化记忆的发展与演化。
管理工作的另一方面,是教务指导、培训,以及法制教育与宣传。每年祝国寺都会举办法制教育方面的培训班,2018年6月17至18日,祝国寺召集了全区除祝国寺外20所寺庙的教务和管理人员培训,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宗教政策,重点是学习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和相关文件,说明下一步宗教活动场所该往什么方向管理。
二、从记忆共同体到人类记忆共同体:意义生产中道德问题的凸显
人类记忆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拥有共同的记忆、共同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的群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共享记忆是获取身份认同、提升凝聚力的重要途径,构建人类记忆共同体是维护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
每隔24 h取30 mL污泥,将污泥置于1 200 r/min的离心机中离心6 min,取过滤后的水样来测定其氨氮、磷酸盐和COD的浓度,同时做荧光光谱的扫描。将收集的污泥经冷冻干燥12 h后用于中红外光谱分析。
以文化记忆的内容选择为例,记忆“经过选择、连缀、意义建构的过程——或者用哈布瓦赫的话说,是经过框架建立的过程”,②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第151页。 造就了文化记忆中的功能记忆。文化记忆中的功能记忆根据所选择的内容主要具有“合法化”“去合法化”和“区分”三种功能。“合法化”是指统治者以获取身份认同为目的进行记忆内容的选择,并通过意义构建和意义共享以获取自身合法性的行为。“去合法化”与“合法化”相对,是“合法化”的派生物,以颠覆前者的现实合法性为目的。“区分”是前两者的终极目标,意在建立集体的身份认同,构建自身区别于“他者”的身份,从而与其他群体相区别。控制社会记忆是当权者维护自身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的等级”。③ [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页。 社会记忆为维护当下社会秩序的合法性而存在,所有社会记忆内容的选择与借用都要以此为前提。现有的社会秩序决定社会记忆的内容和传递的方式。对于那些过去发生的可能不利于维护现存秩序的内容则以一种遗忘的形式将其从社会记忆中抹去。遗忘是权力角逐中最残酷的打击方式,也是权力支配共享内容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无论是被记忆还是被遗忘,都是社会权力角逐过程中意义生产和意义共享的结果。
注2 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C2与ε有关,当ε→0可能会爆破(blowing-up), 但在β>0时,利用(3)式可以推出s>5,再利用(4)式可知奇点的阶数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有限的,而且常数C2和C3都与ε无关.
本工作对不同NaCl浓度下的GMZ07膨润土及其掺砂混合物进行了直剪试验,研究掺砂率及NaCl浓度对膨润土及其掺砂混合物强度特性的影响;在掺砂混合物中引入膨润土有效干密度概念,并结合扫描电镜试验结果,从微观机理上分析了NaCl浓度对膨润土及其掺砂混合物强度的影响.
如果说文化记忆在内容层面上的意义生产和意义共享多依赖于功能记忆的内容选择,那么,文化记忆以媒介选择为基础的意义生产则主要表现为符号化过程中的聚变反应。也就是说,即使是被选择和共享的记忆,也并不意味着可以始终保持其最初的模样。文化记忆与追求客观、真实的历史书写不同,今天的文化记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与最初的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文化记忆构建的过程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稳定性与变异性并存。扬·阿斯曼曾经指出,“我们回忆的根本特征是它们的‘不精确’和‘变化’”。事实上,真实性从来都不是文化记忆构建的标准,因为“人类的记忆……在本质上是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不是精确的存储”。① [德]扬·阿斯曼:《回忆的真实性》,冯亚琳、 [德]阿斯特里特·埃尔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余传玲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3页。 文化记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极为复杂,从文化内容的选择,到社会框架内的形构,再到借助媒介形成符号,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众多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都使文化记忆的形态丰富多样。在记忆媒介相对单一的情况下,内容选择是记忆共同体构建中意义生产的重要场域,然而,随着记忆媒介的不断丰富,基于媒介选择的意义生产过程也逐渐成为记忆共享的重要内容。同时,媒介自身的发展也增加了文化记忆选择的偶然性,继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记忆形态。以记忆的文本化为例,记忆主体为使记忆的内容被当下所理解和接受,势必会根据现实的需求做出相应的修改、调整和补充,并按照语言文字的编码规律进行编码,从而形成文本。作为阐释记忆的媒介,文本距离真实的过去“隔了三层”(柏拉图语),而且文本自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主体囿于确立自身文化身份的诉求而对文本进行重新建构、重新阐释,致使文本的衍生物越来越多。正如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所说:“第一,记忆文本不等于原始记忆;第二,记忆文本也不是对原始记忆的原封不动的复制;第三,记忆文本作为一种理解,已经构成对原始记忆的改变;第四,正是原始的本真记忆,记忆文本,以及对记忆的每一次表述或理解,一起构成了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历史。”② 转引自赵静蓉:《文化记忆与符号叙事——从符号学的视角看记忆的真实性》,《暨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各种不同的文本相互关联、相互印证,甚至相互矛盾,却共同构成了“对记忆的记忆”。
总之,文化记忆依托记忆媒介,通过符号化的过程,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获得了永生。正是文化记忆这种高度稳定和持久的意义生产方式使记忆在文化层面的深度共享成为可能。这种记忆在文化层面意义生产的深度共享,实际上就是记忆共同体构建的过程。
(3)哈拉湖四周河谷平原区域。Na+与K+,Ca2+,Mg2+呈显著性相关,Cl-与K+,Na+,Ca2+呈显著性相关,主要原因是盐滤作用增强,Ca2+与显著性相关,主要是对石膏的溶解,矿化度与所有离子都有较高的相关性,见表4。
事实上,对于文化记忆而言,其符号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意义不断衍生的过程。记忆通过媒介,在经历了符号化的过程后形成一系列的符号系统,转化成文化记忆。为了获取身份认同,文化记忆对记忆的内容进行不断地选择、替换、重组,并进行详尽的编码,这个过程令记忆符号的意义成几何倍数增长。同时,符号本身的建构性也赋予了文化记忆以更加广阔的阐释和理解空间。在意义生产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无法判断离真实的过去究竟是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种互文性在令记忆变得模糊和不确定的同时,也令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文化记忆构建过程中意义生产的纷繁复杂与不可控。尤其是20世纪文化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之后,语言自身具有建构性的观念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接受,语言文本的独立性和自我言说功能日益凸显,更加剧了文化记忆意义生产的繁复性。在构建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中, 与其说共享的是文化记忆的内容,不如说共享的是文化记忆从内容到过程全方位的意义生产。文化记忆的构建过程本质上是意义生产的过程,这种意义生产不仅包涵记忆内容的无限衍生,也包涵记忆形式多方位、多层次的演变。记忆内容与记忆形式的交叉结合产生的“聚变反应”令文化记忆的意义生产更加繁复。但是,无论这种意义生产如何复杂,终究都无法摆脱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的制约,这对于某一群体的记忆共同体而言是记忆选择唯一“合法”的标准。
世界上不存在完全自然的记忆共同体,无论对于家庭、种族、宗教群体还是民族而言,记忆共同体都是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通过社会构建形成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性是共享记忆的目的,也是构建记忆共同体的终极目标。因此,无论文化记忆还是记忆的共同体,只要是属于民族、国家的文化记忆和记忆共同体,都是以符合本民族、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进行选择,然后通过共享达成共识,形成不同层面的记忆的共同体。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不同的记忆共同体即使共享的是关于同一问题的记忆,其所秉持的观点、立场,甚至价值取向却是完全相反的。从记忆共同体到人类记忆共同体,不仅意味着记忆主体已经从特定群体扩展到全人类,也预示着以往特定群体的文化记忆、记忆共同体构建时所遵循的文化选择标准及道德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无法体现全人类共同利益了。这种隐含于文化记忆内部的意义生产方式在构建人类记忆共同体中所表现出的道德失范告诉我们,与特定群体的文化记忆、记忆共同体不同,人类记忆共同体中记忆的选择不应只关心人们“愿意”记住的,更重要的是要记住那些人类“应该”记住的。只有这样才更符合人类共同体成员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构建人类记忆共同体的最终目标。
三、从人类记忆共同体到人类道德共同体:意义生产中的道德固守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曾经指出:“作为一种文化,其特性取决于……某些节段的选择。各地人类社会在其文化习俗制度中,都作了这种选择。”① [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选择是文化发展最重要的内部机制。记忆的内容由谁,依照何种标准进行选择,又通过何种记忆方式和手段对其进行固化,形成符合权力所有者所需求的文化记忆,这些都决定着文化记忆的意义生产。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记忆。在构建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中,任何一种文化选择都意味着通过共享某种或某些记忆达成某种共识,形成为共同体成员所认同的记忆选择的框架,或者说,某种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根据自身的需求决定了记忆选择的标准,并通过共享使其成为记忆共同体成员的共同选择。这是推动文化记忆意义生产和记忆共同体形成的核心动力。
德国哲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曾经指出,与以选择意志为基础的社会不同,共同体是建立在本质意志基础上的。以地缘、亲缘、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中所包含的“一体性和同质性决定了它可以获得习俗和道德的规范,可以在习俗和道德的基础上形成权力治理体系”。① 转引自张康之、张乾友:《共同体的进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3页。 道德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共同体的道德以一体性和同质性为基础,具有排他性,任何共同体所遵循的道德标准都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宗旨,在此我们无意就千百年来存在于哲学领域的道德普遍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之争做出判断,但是,某一共同体所推崇的道德有时对于其他共同体而言却是不道德的,如在战争中,一方所认为的英勇在另一方看来却是残暴,原因就在于文化选择所遵循的道德标准不同。
构建记忆共同体与构建道德共同体是同步的。记忆共同体以相似性为基础,关注的是那些具有共同特征、属于同一意识的事物,是具有相同旨趣的群体连续的日常生活。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人们具有相似的社会生活,相近的生活记忆和价值取向,能够在群体面对外部威胁时产生团结一致的道德意识,以维护群体利益不受侵犯。因此,记忆共同体与道德共同体是共生的、相辅相成的。在某种层面上,记忆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政治诉求的集中体现。记忆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为获取其现实合法性而构建起的文化存在形式,其蕴含的社会秩序、价值取向及道德准则势必以维护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为目标,任何与此目的相悖的事物都会被屏蔽在记忆共同体之外。因此,记忆共同体中所蕴含的道德属性必定以保障共同体主体的存在和发展为旨归。如果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共同体中各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就会失去控制,从而损害共同体的利益,利益共同体、记忆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本文以某铸造企业生产中型压缩机为研究对象[24],对其实际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对其中核心铸造过程进行任务分解,构建出该企业的制造能力,在此基础上应用所提出的制造能力度量模型进行分析评价。如图6所示为该企业的铸造生产过程。其中,过程1~9为造型过程,过程10~27为铁水熔炼过程,两条制造路线于下端汇聚在一起,进行熔炼、浇铸、铸件处理等。
记忆共同体可以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属于某个集体、某个民族,也可以以整个人类为基础,属于全人类。人类记忆共同体的道德性是毋庸置疑的。阿维夏伊·玛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通过区分“伦理”和“道德”,揭示了道德对于人类记忆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伦理”关乎的是对那些与我们具有亲缘、血缘等特殊关系,拥有共同记忆的相关者的责任,而“道德”关乎的则是我们对陌生人、普通人或人类的责任,“伦理关乎忠诚和背叛”,“道德关乎尊重和羞辱”。② 转引自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第2页。 因此,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记忆共同体选择记忆的标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忠诚和背叛,而以人类为基础的记忆共同体则代表了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类的责任,也就是徐贲所说的,“人类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因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③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第12页。 同样,人类记忆共同体的构建与人类道德共同体的构建也是不可分割的。作为人类记忆共同体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性道德的记忆不仅决定了人类记忆共同体构建中的道德性,也为人类文明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人性道德的记忆不仅包含了人类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美好回忆,还包括那些违反人性、违背道德的人类恶行。构建人类记忆共同体,不应该遵循我们“愿意”记住什么,而应该遵循记住什么是我们的道德责任,也就阿维夏伊·玛格利特所说的,我们应该记住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① 转引自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第13页。 的邪恶事件。
在人类历史上,“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反人类、反人道事件并不鲜见。从16世纪以来欧洲殖民者为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和资源而对印第安人实行的长达三个世纪的奴役和屠杀,到二战期间纳粹运用现代化手段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等等,仅近几个世纪发生的这些“毁灭人性”的灾难就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非命,无数人无家可归。许多人类暴行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深刻的反思,甚至有的被刻意排除在人类记忆之外。尽管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却依然被日本右翼诋毁为“虚构”。人们不禁要问,如此缺乏道德自省的人类记忆共同体究竟能否固守道德的底线?
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大规模的暴行从来都不是一两个人独立完成的。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2017年1月27日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的致辞中说:“如果将大屠杀仅仅视为一群纳粹罪犯精神错乱的结果,那将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大屠杀恰恰是数千年来以犹太人为替罪羊的仇恨和针对犹太人的歧视,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反犹太主义的巅峰之举。”② 2017年秘书长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致辞,https://www.un.org/zh/holocaustremembrance/2017/sg.shtml。 因此,纳粹屠犹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基督教世界千百年来集体恐犹幻觉的历史延续,这种将犹太人妖魔化的群体行为在纳粹统治时期达到了顶点。相似的还有侵华日军攻陷南京时,当时日本民众“提灯游行”“普天同庆”,日本媒体也是以歌颂“英雄”的立场报道南京大屠杀中的杀人比赛。人们或许可以辩称自己受到当权者的蒙蔽和利用,被裹挟为求自保不得已才会沦为暴行的帮凶,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推脱说那是祖辈的恶行,与今天的“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无论是否与暴行有直接关系,无论是今天的“我们”还是我们的后代,只要是人类的一份子,就必须承担记忆这段历史,对人类暴行进行反思、忏悔并引以为戒的道德责任。
人类记忆共同体是人类道德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文化记忆的内容浩如烟海,意义生产的过程也无法摆脱各种权力的制约,但是,只要每个共同体成员承担起记忆的道德责任,固守人类记忆共同体的道德底线,由此形成的道德共同体就会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有力的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才能最终实现。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10-0170-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世界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对话研究”(13CGJ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昕,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江苏 南京,210004)。
责任编辑:王法敏
标签:文化记忆论文; 人类记忆共同体论文; 意义生产论文; 道德共同体论文;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