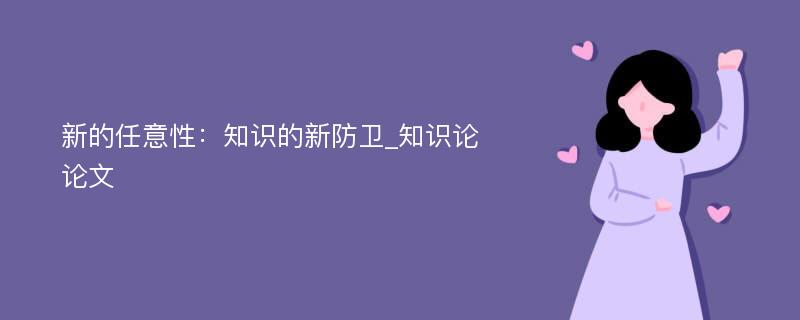
新独断论:一种新的知识辩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10-0053-09
“新独断论”(new dogmatism)是一种知识论①。它认为,知觉经验对知觉知识的获得来说是充分的。其中,知觉知识指基于知觉经验的知识。例如,通过看,我知道草席上有一只猫。如果我们不反对经验论的基本信条(关于世界的知识最终来源于经验),那么就必须承认,知觉知识是最基本的知识,对其他知识的完整理解只有了解它后才有可能。新独断论试图对知觉知识给出说明。这是一项需要付出努力的基层工作,但并不是所有努力都是成功的。我将表明,普赖尔(James Pryor)的新独断论(以下简称PND)是有问题的。不过,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在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的“析取论”(disjunctivism)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独断论(以下简称MND)可以解决PND的问题。MND蕴涵了两组分知识论(知识是得到辩护的信念,而不是传统上所说的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两组分知识论为解决知识论的难问题带来了新希望,是一个有前途的理论。
一、经验辩护问题
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论点是,单纯的相信构不成知识,因为它的真得不到任何保证。信念只有在满足了某种认知标准后才有资格称得上知识。所以,知识论关注满足了标准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我们说它是得到了“辩护”(justified)的信念。按照这样的理解,辩护是知识的必要条件。知识论的重要任务就是弄清楚信念是如何得到辩护的。
很显然,信念可以从其他信念那里获得辩护。例如,我相信我妻子在家里了,是因为我相信家里的灯亮着。可问题是,我们不能一直这样追溯下去,因为那样会产生无穷倒退。实际上,我们根本不会无限追溯,因为当辩护被追溯到信念的基本来源时,我们将不再援引信念。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相信家里的灯亮着,我会直截了当地说,我看见家里的灯亮着。这种情况下,至少从字面上看,我是在用知觉经验辩护知觉信念。很多知识论者认为,知识论应该容纳这样的日常会话,也就是说,知识论应该承认,有些信念可以从经验那里获得辩护。此种辩护被称为经验辩护,得到经验辩护的信念被称为基础信念。引入基础信念的好处是双重的:既符合常识,又可以中止信念辩护的无穷倒退。由于经验不是信念,它本身无需辩护,所以辩护到了经验这里就自然停止了。
可问题并未因经验辩护的引入而消失。一个重要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是,非信念状态的知觉经验如何能向知觉信念传达一个它所不具有的东西(即辩护)?一些人,例如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和戴维森(Donald Davidson),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强行坚持的话,就会陷入“所予的神话”。②另一些人,例如普赖尔和麦克道尔,认为知觉经验与知觉信念一样具有命题内容,因而可以辩护知觉信念。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只是在于,知觉经验对知觉信念的辩护是不是充分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某个知觉信念是否可以单独地从某个知觉经验那里获得辩护?在20世纪前,几乎没有人给予肯定回答。理由似乎很明显:经验是可错的,我们不能在没有事先确定知觉经验是否可靠的情况下,就用它来辩护知觉信念。
但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承认经验辩护是不充分的,那么,信念辩护的问题就仍然没有得到说明,除非我们能说明,我们何以能够事先确定知觉经验的可靠性。可如何说明这一点呢?洛克的回答是,虽然单个的经验不能提供充分的知识辩护,但多个经验可以。例如,虽然我不能仅凭当下的视觉经验确定一个物体是球形的,但我还可以去触摸它。多个经验的相互印证,特别是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与有序性,可以有力地说明经验总体上是可靠的。③不过,洛克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既然所有经验都是有待确认的,那么诉诸另外的经验来确认经验的可靠性就是一个坏循环。休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无奈地承认,经验论是不完备的。康德试图用先验论来拯救经验论。先验论将经验如何给信念传达来自世界的合理性限制的问题,转化成世界如何按主体的认知结构显现出来的问题。这等于取消了经验辩护。显然,这样做的正当性取决于先验论本身的正当性。而先验论的正当性恰恰是非常可疑的。由于经验的领域也就是科学的领域,所以,断言有一个超越经验的先验领域也就相当于断言存在一个超出科学之外的领域。这让人很难接受。
鉴于传统知识论的问题,当代知识论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外在主义”(externalism)进路。外在主义认为,一些外在于认知者视角的要素也可以辩护信念。“可靠主义”(reliabilism)是典型的外在主义。根据可靠主义,一个信念是否得到辩护,在于它是否由可靠过程产生。过程的可靠性是客观的,即使认知者不知道某个认知过程是可靠的,他也可借由它获得知识。这为经验辩护问题提供了一个外在主义的解决方案:经验在辩护信念时其可靠性需要得到确认,不过,确认是外在的,无需认知者知晓。通过取消意识层面的确认,经验辩护的循环问题也随之取消。但问题没这么简单。外在主义甚至无法真正兑现经验的可靠性在意识层面的确认是可取消的承诺,因为认知者完全可以反过来根据他所获得的知觉知识确定知觉过程的可靠性。说明如下:假设我具有可靠的颜色视力,但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根据可靠主义,我可以运用视力获得这张桌子是红色的知识。另外,假设我知道这张桌子是红色的信念是由我的视力产生的。有了这两点,我就可以推知,我此次的颜色经验是准确的。重复这样的推理,我就可以知道,我的颜色经验在多数情况下是准确的,因而我的颜色视力是可靠的。沃格尔(Jonathan Vogel)形象地将这种证明方式称为“自举”(bootstrap)。④承认经验可以自举是难以接受的,因为知觉知识是知觉过程的结果,用它反过来证明知觉过程的可靠性是循环的。通过自举的方式获得的知识,正如柯恩(Stewart Cohen)所说,来得太简单了,它表明我们的知识论出了问题(柯恩称其为简易知识问题)。⑤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经验辩护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难以缓解的张力。一方面,知觉知识的直接性以及信念辩护的可能性要求经验辩护的充分性。但另一方面,经验的可错性又让我们对经验辩护的充分性产生怀疑:经验至少需要得到某种程度的确认后才能辩护信念。这让我们很是困惑:知觉经验到底能不能单独地辩护知觉信念?
二、普赖尔的新独断论
新独断论对经验辩护问题给出了一个直截了当但相当惊人的回答:知觉经验可以单独地辩护知觉信念。迄今为止,最为精致的版本是普赖尔提出的,即前面所说的PND。PND有三个核心论点⑥:
(1)经验辩护的直接性原则:“当你的知觉向你呈现出情况像是p时,你对相信p具有一种不预设或不依赖于你对其他任何事情的辩护的辩护,你可以在论证中(即使是扩充性论证)引用它。具有这种对于相信p的辩护,你只需具有表征情况像是p的经验就可以了,而无需进一步的觉知(awareness)、反思(reflection)或背景信念。”
(2)经验辩护的可击败性原则:“我们对自己的关于环境的信念的辩护是可击败的(defeasible)——我们的认知状态总有可能得到提高,以至于不再支持那些信念。”
(3)经验辩护的充分性原则:“你通过仅仅具有情况像是p的经验而获得的辩护有时足以给你情况是p的知识。”
先看直接性原则。普赖尔承认,直接性原则隐含了一个预设。这个预设便是“意向论”(intentionalism)。概括地说,意向论是这样一种观点:知觉经验是意向状态,它指向世界,将世界表征成某种样子。知觉经验将世界表征得所是的样子就是它的表征内容。表征内容具有语义特征,因而是命题的。⑦因此,在意向论看来,知觉经验是有命题内容的。这与传统观点大相径庭。传统观点,包括英国经验论与感觉材料理论,认为知觉经验是原初的所予,并不具有命题内容。在当代,意向论获得了大量支持。⑧意向论解释了知觉经验何以能够辩护知觉信念:知觉经验通过向知觉信念移交命题内容的方式发挥辩护作用。
在意向论的基础上,直接性原则进一步断言,知觉经验可以不依赖于任何进一步的辩护而辩护知觉信念。普赖尔称这样的辩护为“直接辩护”。⑨相反,假如我们对某个信念的辩护依赖于对其他东西的辩护,那它就是间接辩护。直接辩护不同于认知上的独立性。一个信念,如果认知者无需持有任何其他信念就可以持有它,那么它就是认知上独立的。得到直接辩护的信念不必具有这样的独立性。认知者对信念p的持有也许依赖于一系列背景信念,但这并不表示他对信念p的辩护就依赖于他对那些背景信念的辩护。毕竟,持有与辩护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个区分很重要,它可让新独断论免于“观察渗透理论”论题的反驳。⑩
再看可击败性原则。可击败性原则告诉我们,知觉经验所提供的辩护是初步的(prima facie),它有可能被新的证据击败。起击败作用的证据有许多,例如支持非p的证据,能够将看起来情况是p“解释掉”(explains away)的证据。然而,在没有击败者的情况下,知觉经验却具有默认的辩护效力。可击败性原则为在知识论上区分像真实知觉那样的好情形与缸中脑(11)那样的坏情形提供了可能:虽然两种情形中经验都可以提供初步辩护,但坏情形中的辩护是可击败的。
充分性原则断言,知觉经验有时足以让我们获得知觉知识。这当然是合乎常识的。比如说,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草席上有一只猫?”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看见的。”当我给出这样的回答后,对方一般会满意,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回答足够了。
普赖尔认为,上述三个原则都是易于接受的,因而并未给出严格的论证。(12)不过,普赖尔论证了,由上述三个原则组成的新独断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温和的反怀疑论方案”。(13)这个方案虽然不能像“雄心勃勃的反怀疑论方案”那样,在怀疑论者允许我们使用的前提范围内,证明我们可以得到辩护地相信外部世界的一些事情,但它却向我们表明了,我们何以能够知道怀疑论假设的否命题(如我不是缸中脑)。(14)这足以保证知觉知识的可能性。普赖尔争论说,像PND这样一个既成功又符合直觉的理论,如果我们找不到要求我们弃之不顾的反对意见,那么就应该接受它。这可以看作是普赖尔对PND所做的间接辩护。
问题是,我们真的找不到有效的反对意见吗?并非如此。正如普赖尔所承认的,PND蕴涵了可错主义。可错主义认为,我们可以在可击败的辩护的基础上获得知识。普赖尔认为这是可接受的。的确,很多当代知识论者都承认可错主义。(15)但是,PND所蕴涵的可错主义会给它带来麻烦,它会导致内塔(Ram Neta)所说的“可击败性悖论”。(16)这个悖论表现为,四个单个地看都是可接受的陈述合起来却是不相容的:
(1)在时刻t1,我知道p。
(2)在将来的某个时刻t2,我有可能获得好的证据,表明我在t1时刻不知道p。
(3)假如我在t2时刻获得了那样的证据,那么我在t2时刻就不知道我在t1时刻所知道的那个p。
(4)如果S知道p,并且S继续拥有关于p的全部证据,继续在那些证据的基础上相信p,那么S就不会仅仅因为获得新证据而失去知识p。获得新证据本身不可能让你变得更无知。
上述陈述中,(1)和(2)分别为充分性原则和可击败性原则所蕴涵。(3)是(1)和(2)的推论。(4)的可接受性没那么明显。然而,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否认(4)会导致矛盾。S知道p意味着,S所拥有的关于p的全部证据对他知道p而言是充分的。否认(4)意味着,S可以在继续拥有关于p的全部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获得新证据就失去了知识p,而这恰恰表明,S先前所拥有的关于p的全部证据是不充分的。因此,(4)是难以否定的。可是,(4)和(3)却是矛盾的,把它们放在一起就会产生悖论。(17)
三、析取论与新独断论
可击败性悖论表明,PND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PND既要坚持可击败性原则以容许经验的可错性,又要坚持充分性原则以保持新独断论的身份。前一个原则要求经验辩护与知觉知识保持一定的距离,后一个原则又要求它们之间能够无缝接合,这实在难以两全。除非放弃一方要求,否则冲突难免。对新独断论来说,充分性原则是不能放弃的,因为那样也就不成其为新独断论了。因此,出路只有一条,修改可击败性原则。
可击败性原则承认,只要没有击败者,所有经验都可以辩护信念。即使我只是幻觉到草席上有一只猫,只要我的幻觉是如此地栩栩如生,以至于我不能发现它是幻觉,那么,我的幻觉经验就辩护了草席上有一只猫的知觉信念。由于经验被认为是通过转交内容的方式辩护信念的,因此,幻觉经验能够像真实知觉一样为知觉信念提供初步辩护,也就意味着它具有像真实知觉一样的内容。这初看起来似乎是不成问题的。毕竟,幻觉与真实知觉都向认知者呈现出了“情况像是p”。所以,它们传达给信念的就是“情况像是p”。普赖尔就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如果知觉经验的内容一旦被限定为“情况像是p”,它何以能够辩护知觉信念也就不得而知了。“情况像是p”并不等于“情况就是p”,它总是相容于“情况像是p,但实际上非p”。因此,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经验辩护同样适用于缸中脑。这样一来,我们的认识论地位就岌岌可危,怀疑论者随时都可以向我们施压。于是PND遇到了传统知识论同样的问题,情况未有任何改善。
以上分析表明,PND的可击败性原则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它默认了在好情形与坏情形中,知觉经验都只有向知觉信念传达“情况像是p”。“情况像是p”构成了真实知觉与幻觉的共同要素,使得它们成为同种类型的经验。它们的不同仅仅是外在的,即它们与外部事物的联系方式的不同。马丁(Michael Martin)称此想法为“共同种类假设”。相应地,那些预设了该假设的理论就为“共同种类理论”。(18)PND与传统知识论都属于共同种类理论。共同种类理论存在共同的问题,它们无法说明经验的有效性,因而注定不能解释知识何以是可能的。因为一旦我们承认,在好情形与坏情形中认知者享有的是同种类型的经验,那么自然而然地,我们就无法知道自己拥有的到底是哪种经验。毕竟,我们不能越过自己的经验去看它与外部事物的联系。如此一来,经验在何时传达了“情况就是p”也就不得而知了,从而,经验辩护的有效性也就不得而知了。
哲学理论的问题往往出现在预设上。共同种类理论也是如此。它们所承诺的共同种类假设并非不证自明的先天命题,也不是得到证明的后验命题,而只不过是未加审视的直觉。这种直觉来自好情形与坏情形中经验现象上的不可分辨性。但是,现象上相同并不代表本体上就相同。比如,一张老虎的全息照片看起来与真老虎一模一样,它们现象上相同,但本体截然不同。这告诉我们,不能仅从经验现象上的相同推断出它们种类的相同。这正是析取论所想说的。析取论认为,尽管坏情形的经验与好情形的经验在现象上是不可分辨的,但它们在本性上却是不同的。在好情形中,我们感知到了世界中的事物,它构成了经验的一部分。如果没了那个事物,我们就不说那个经验是真实的。因此,好情形的经验是依赖外部事物的。坏情形的经验则不同,它恰恰是在没有外部事物时发生的,因而不是依赖外部事物的。析取论吸收了这样的前理论直觉,认为好坏情形中经验的不同是本性的不同。因此,知觉经验并不是一个种类:它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析取论由此得名。
我们还可以从内容的角度来理解析取论。对意向论者来说,真实知觉是依赖外部事物的,也就是说,知觉经验的内容是由事物及其性质本身而不是用以指示那些事物或性质的概念组成的。这样的内容,称其为罗素式内容。之所以冠以罗素的名号,是因为罗素曾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单称词项只对它所在的句子所表达的命题贡献它的指称。(19)这意味着,包含单称词项的命题是由单称词项的指称和谓词所表达的性质组成的。例如,“济南很干燥”这句话所表达的命题是由济南这个地方和干燥这一性质组成的。罗素式内容是世界中的事实。如果一个心理状态具有罗素式内容,那就肯定存在那个心理状态所表征的那个事实。这样的状态,我们说它是“事实性状态”(factive state)。(20)麦克道尔式析取论认为,好情形中的知觉经验是事实性状态。(21)“在我们未被误导的那个经验中,我们接受的是‘事物如此这般’。‘事物如此这般’既是那个经验的内容……也是一个可感的事实,即可感世界的一个方面……[它们]之间没有本体论上的间隙。”(22)相反,在坏情形中,知觉经验是纯粹显相(mere appearance),并不具有罗素式内容。因此,好情形与坏情形中知觉经验的内容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决定了它们传达给信念的东西是不同的。在好情形中,知觉经验传达给信念的是“情况就是p”。在坏情形中,知觉经验传达给信念是“情况像是p,但实际上并非p”。所以,好坏两种知觉经验并非像共同种类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相同的辩护效力,相反,它们的知识论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麦克道尔式析取论蕴涵了新独断论。根据麦克道尔式析取论,好坏两种情形中,知觉经验所传达给知觉信念的内容是不同的。假设认知者S在坏的知觉经验E(B)的基础上形成了知觉信念p。这种情况下,E(B)传达给信念p的是“情况像是p,但实际上并非p”,信念p并没有从E(B)那里获得辩护,从而S也没有从E(B)那里获得知觉知识。在好情形中,S的知觉经验E(G)传达给信念p的是“情况就是p”。“情况就是p”排除了~p,所以信念p肯定为真。在此意义上,我们说E(G)构成了对信念p的“排除了错误(falsehood-excluding)的辩护”(23)。“排除了错误的辩护”足以保证认知者所获得的是知觉知识。因此,在好情形中,经验辩护是充分的。而这正好是新独断论的独特标志。所以,麦克道尔式析取论就是新独断论,可称其为MND。麦克道尔本人也承认,可以将他的观点称为独断论。在一篇与布兰顿(Robert Brandom)商榷的文章中,他明确地说:“独断论,布兰顿说我拒斥的四个论点中的一个,正是我所捍卫的。”(24)
仿照PND的刻画方式,我们可以把MND概括为如下三个论题:
(1)经验辩护的直接性原则:当你的知觉向你呈现出情况是p时,你对相信p具有一种不预设或不依赖于你对其他任何事情的辩护的辩护,你可以在论证中(即使是扩充性论证)引用它。具有这种对于相信p的辩护,你只需具有呈现出情况是p的经验就可以了,而无需进一步的觉知、反思或背景信念。
(2)经验辩护的不可击败原则:如果一个知觉信念p得到了E(G)的辩护,那么它就是不可击败的——它不可能被新获得的证据击败。
(3)经验辩护的充分性原则:你通过仅仅具有情况是p的经验而获得的辩护足以给你情况是p的知识。与PND的表述相比,可击败原则被换成了不可击败原则,直接性原则与充分性原则中的“情况像是p”被换成了“情况是p”。这种替换是拒斥共同种类假设的结果。新的直接性原则与充分性原则同样可体现新独断论。
不可击败原则使得MND可以避开困扰PND的可击败性悖论。根据不可击败原则,“S知道p”蕴涵了“S相信p”得到了“排除了错误的辩护”,它不可能被新证据击败。因此,可击败性悖论中的(4)是对的。(1)和(2)单独地看都是可能的,但合在一起不可能都对。假设(1)是对的,鉴于知道蕴涵了“排除了错误的辩护”,它不可能被击败,所以(2)实际上是不可能的。S在t2时刻所获得的证据其实是不好的证据,它让S觉得(2)是对的,但实际上并不对。假设(2)是对的,然则t1时刻的证据就未能给予不可击败的辩护。按照MND,S实际上并未获得知识,所以(1)不成立。在t1时刻,S只是觉得自己知道p,实则不然。所以,在MND看来,可击败性悖论根本就不成立。
四、两组分知识论
我已经说明了MND是一种新独断论。下面我将论证,可以在MND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型的两组分知识论。我将说明,两组分知识论为解决“盖梯尔问题”(Gettier problem)带来了新的希望。此外,我还会对一些可能的重要批评进行回应,以保卫所取得的成果。
我所说的两组分知识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即知觉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知觉信念。我认为,可以这样从MND推导出两组分知识论:
(1S)认知者S的知觉经验E(G)为他的知觉信念提供了“排除了错误的辩护”,这足以让他获得知觉知识。
(2N)只有当知觉经验为知觉信念提供了“排除了错误的辩护”,认知者才具有知觉知识。因此,(3C)S具有知觉知识p,当且仅当其知觉信念p得到了E(G)的辩护。
其中,(1S)是MND的主张,给定MND自然就有(1S)。(2N)是需要说明的。说明如下:首先,由新独断论可知,只有知觉经验才能辩护知觉信念。如果承认可靠性、“安全性”(safety)这样的非经验要素可以起辩护作用,那就等于否定了经验辩护的充分性原则,从而也就否定了新独断论。所以,新独断论已经将辩护的候选者限定在经验之中。其次,新独断论将知觉经验理解为意向状态,将经验辩护理解为内容的转交,这意味着,辩护的候选者只能是经验内容。而按MND,只有罗素式内容才能起辩护作用。罗素式内容就是事实p,有它就有事实p,所以,它所提供的辩护必定是“排除了错误的辩护”。因此,由MND可推出(2N)。(2N)结合(1S)就可推出(3C)。
我已经从MND中推导出了两组分知识论。下面我将说明,两组分知识论为解决盖梯尔问题带来了新希望。让我们设想如下情形:假设S走进一个光线条件良好的房间,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只杯子,于是他相信这个房间有一只杯子。实际上,S所看到的杯子只不过是一台计算机产生的全息照片。这台计算机通过性能可靠的传感器与一只藏在完全不透光的帘子后面的杯子相连,产生它的全息照片。但S并不知道这些情况。直觉告诉我们,S在这种情形中并不具有知觉知识。然而,S的信念是真的,并且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据支持,那么,为什么说他不具有知识呢?传统的三组分知识论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即使是后盖梯尔知识论也好不到哪里去。以可靠主义为例。在这个例子中,从传感器到计算机再到S的知觉,整个过程都是可靠的。因此,可靠主义并不能排除这类盖梯尔情形。但两组分知识论处理起来却很轻松。两组分知识论认为,上述情形中,S的信念并未得到了辩护。由于实际存在的那个杯子不在S的视线之中,S并未看到它,因此,S的经验并不具备罗素式内容,它并不能辩护信念。
两组分知识论的去盖梯尔化解释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就拿上面那个例子来说,很多人,当然包括普赖尔,认为S的信念得到了辩护,因为S的知觉经验给了他证据支持。看一下所谓“新缸中脑假设”,问题就更清楚了。设想有一个神通广大的精灵,他能制造出某个认知者S的缸中脑复制品S′,假设S在t时刻基于他的事实性经验相信p,那么,S相信p得到辩护的程度与最新复制出的S′相信p得到辩护的程度相同吗?(25)大部分哲学都回答说是。例如,德雷斯克(Fred Dretske)就认为,由于S′的信念和我们的一样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基于与S用以确认他的信念的证据相同的证据去相信p的,所以,S′和我们一样有权去相信p。(26)不得不承认,S′拥有信念p的确有合理之处。例如,S和S′尽到了同样的认知义务,也负起了同样的认知责任。两组分知识论并不反对这些看法,但它认为那些因素与经验辩护无关。对经验辩护来说,唯一相关的是知觉经验的内容。如果认为S和S′的知觉经验具有相同的内容,那么,他们的信念得到辩护的程度就是相同的。可是S和S′的知觉经验的内容并不相同:前者是罗素式内容,后者却是纯粹显相。由于S和S′所拥有的证据基础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的知识论境况是不同的。
对于一般化的盖梯尔情形,两组分知识论同样可以处理。以盖梯尔的例子为例(27)。史密斯为什么并不知道那个得到工作的人口袋有十个硬币?两组分知识论的回答是,史密斯的信念或者为假,或者没有得到辩护。史密斯所拥有的证据,如果是事实性的话,那它的内容必定涉及了琼斯(因为罗素式命题由事物及其性质本身构成)。假如史密斯在事实性证据的基础上形成了信念“那个得到工作的人口袋有十个硬币”,那么,“那个得到工作的人”指的就是琼斯。现在琼斯并未获得工作,所以史密斯的信念是假的。另一方面,假如史密斯所拥有的证据并不是事实性的,那么,在他的信念中“那个得到工作的人”就可以指那个事实上得到工作的人,即史密斯他自己。但这样一来,他的信念就没有得到辩护,因为他没有事实性的证据。由此可见,两组分知识论可以很好地处理一般化的盖梯尔问题。
两组分知识论拥有与众不同的去盖梯尔化效能,这得益于它对辩护的独特理解。在传统知识论中,辩护与真分别代表了两股不同的力量:其中一股是来自心灵的内生力量,另一股是来自世界的外生力量。当这两股力量完全融合时知识就产生了。可是,假如我们认知者的知觉经验即使没有向知觉信念传达事实性的内容也仍然能够辩护信念的话,就等于承认了辩护与真有可能会错开。由此就产生了盖梯尔问题。后来的知识论以解决盖梯尔问题为己任,它们想尽了各种方法想把辩护与真重新对接上。但这注定是项希望渺茫的工作。既然已经错开,又如何能够对接上呢?两组分知识论拒绝做徒劳的工作,它从一开始就坚持真与辩护是不可分离的。在“排除了错误的辩护”中,真与辩护已经融为一体了,因此不存在分离的问题。
至此,我阐明了MND的三大好处。第一,解决了经验辩护问题;第二,避开PND的问题;第三,它所蕴涵的两组分知识论为解决盖梯尔问题带来了新希望。问题是,这些好处真能兑现吗?MND会不会和PND一样,只是做了一些虚假的承诺?这个担心并非多余。因为MND的所有好处都依赖于析取的经验概念,依赖于它对E(G)与E(B)作出的本体论上的区分。但是,如果本体论上的区分不能在知识论层面得到确认的话,那么好处将无法兑现。于是就有这样的质疑:在E(G)与E(B)主观上不可分辨的情况下,认知者又如何知道他当下的经验是E(G)而不是E(B)呢?(28)如果认知者做不到这一点,那么E(G)与E(B)的区分对他来说就是无意义的,从而“排除了错误的辩护”说法也就是无意义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层面给予回答。首先,在内容层面上,答案是肯定的。知觉当然能够把它所表征的东西呈现出来。感知动词后面的东西,例如,我看到……,我听到……,是知觉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也是一个有知觉意识的人所觉知到的东西。鉴于认知者对他所处知觉状态的内容是有觉知的,所以,当认知者实际上处于E(G)状态时,它就可以觉知到E(G)的内容,即E(G)所表征的世界中的事实;而当认知者处于E(G)状态时,它就觉知了E(B)的内容,即作为显相的“看起来情况像是p”。因此,在内容层面上,认知的确可以感知到E(G)与E(B)的不同。问题就出在状态层面上。认知者又如何知道他所处的是E(G)状态而不是E(B)状态?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发现休谟的自然主义是很有帮助的。(29)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对E(G)采取默认态度。在没有相反的证据时,我们自然就会相信自己的经验是真实的。不过与休谟不同,我认为,我们的这种态度并非习惯使然,而是进化的结果。进化将我们塑造成依靠知觉来和世界打交道,因此我们不得不相信它。假如我们一开始就对知觉经验持怀疑的态度,从而拒绝采取行动甚或采取相反的行动,我们就不会存活到今天。给定知觉经验的认知价值,我们对它采取默认真的态度是合理的。以默认真为起点,结合经验之间以及经验与信念之间是否融贯的考虑,总的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所处的是E(G)状态还是E(B)状态。
当然,认知者默认自己的经验是E(G),并不意味着它就是E(G)。E(G)与E(B)的不可分辨性有时会引诱认知者犯错。实际情形是E(B),认知者却将它默认成E(G)。在这个时候,认知者认为自己的信念得到了辩护,但实际上却没有。不过,并不能因为认知者会犯错就否认他的认知表现,这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有时会做坏事就否认他做过好事一样。当然,犯错会给认知者对自己的认知结果的判断带来问题。究竟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宣称自己具有某项知识?我们好像很难作出这样的宣称。然而,一个真正理性的认知者不会对他这样的认知境地感到不安,因为他并不奢望一劳永逸地完成对世界的认知。相反,他总是在不断地审查自己的信念,看看是不是在某个地方出错了。这是苏格拉底的精神。在当代,塞拉斯最好地把握了这种精神。塞拉斯说:“经验知识是理性的……这不是因为它有一个基础,而是因为它是自我纠正的事业,能够把任何主张置于危险之中,尽管不是一下子全部。”(30)一个像塞拉斯那样看待知识的人是不会担心状态层面的问题的。另外,我还想指出,状态层面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由于“知道”并不蕴涵“知道自己知道”(31),所以,即使认知者不能确定地知道自己处在何种心理状态,他一样可以拥有知识。这样看来,区分E(G)与E(B)的问题并没有原先认为的那样迫切。
除了上面那个反对意见,还有一个容易想到的质疑。MND会不会有自举问题?说一个知识论有自举问题,也就是说,那个知识论允许认知者在不知道自己知觉过程是否可靠的情况下,依靠它获得知觉知识,然后又用这些知识来辩护知觉过程的可靠性,从而生产出简单知识。但MND不允许认知者以这种方式生产简单知识。原因就在于,按照MND,辩护必须是排除了错误的,而简单知识并不满足这一条件。正如在房中杯子的例子中,认知者的整个认知过程都是可靠的,然而他却不具有知觉知识。在MND看来,可靠性根本就不是知识的充分条件,因而也就不能用它来生产知识。因此,MND不存在自举问题。
我已经对MND的两个主要反对意见进行了反驳。我的结论是,MND没有那样的问题,是个强健的知识理论。最后,我想借用普赖尔的话,像MND这样一个既成功又符合直觉的理论,如果我们找不到要求我们弃之不顾的反对意见,那么就应该接受它。
综上所述,每个领域都有它自己的难问题。如果说“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的自然化是心灵哲学的难问题,那么经验辩护问题就是知识论的难问题。这个问题近来引起了大量讨论。讨论方案虽然众多,但基本观点不外乎两种:一是承认经验辩护的充分性,二是否认经验辩护的充分性。西林斯(Nico Silins)称它们分别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保守主义”(conservatism)。(32)新独断论属于自由主义。我认为自由主义是对的。如果不承认经验辩护的充分性,循环就很难被打破。当然,坚持经验辩护的充分性免不了会遇到经验的可错性问题。新独断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普赖尔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不过并不成功。我论证了,在麦克道尔的析取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独断论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由于析取论对幻觉实施了有效隔离,所以我们可以无碍地坚持经验辩护的充分性。我还论证了,在麦克道尔的新独断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两组分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将真融进了辩护,从而避免了传统知识论所遇到的真与辩护分离的问题。虽然我的论证针对的是知觉知识,但却可以将它推广到一般知识的情形。当然,推广工作是复杂的。首先,会遇到内容为特殊性命题的知觉经验如何为内容为普遍性命题的信念提供辩护的问题。其次,还会遇到理论命题是否可以具有罗素式内容的问题。这些问题很有趣也很重要,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在哲学中,独断论通常指人们可以拥有某些知识的断言。这种用法可追溯到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根据恩披里克,那些宣称已经发现了真理的人,例如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他们的哲学便是独断论[Sextus Empiricus:Sextus Empiricus,Vol.1,R.G.Bury(tra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p.3]。其后,康德用独断论来指以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为代表的、认为人类能够通过理性的单纯运用就可以获得关于经验实在或非经验实在的知识的思想。新独断论断言存在知觉知识,这是对独断论的继承;它还断言知觉经验对知觉知识的获得来说是充分的,这是对独断论的发展。
②Wilfrid Sellars,Richard Rorty & Robert Brandom: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33.
③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London: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2006,pp.483—484.
④Jonathan Vogel:"Reliabilism Leveled",Journal of Philosophy,2000,97:p.614.
⑤Stewart Cohen:"Basic Knowledge and the Problem of Easy Knowledge",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2,65(2):pp.309—329.
⑥⑨James Pryor:"The Skeptic and the Dogmatist",Nous,2000,34(4):p.519,p.517,p.520,p.532.
⑦⑧Tim Crane:"Intentionalism",in A.Beckermann and B.McLaughlin(eds.),The Oxford Handbook to the Philosophy of Mi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474—493.
⑩Norwood Hanson:Patterns of Discove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观察渗透理论”这个论题在20世纪中叶非常流行。它是反基础主义的重要论据之一。普赖尔的区分让我们看到,这种论证其实是无效的,至少,它不像当初所认为的那么有说服力。
(11)缸中脑是这样一个假设:我们的大脑并不是长在身上,而是泡在一个营养缸中。再假设有一台超级计算机,它通过连接到我们大脑神经末梢的信号线给予我们丰富的信号刺激,从而让我们具有种种经验。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种集体幻觉,我们“看到”了“天空”、“听到”他人的“叫喊”、“触摸到”自己的“手”,情况如同我们现在发生的一切,然而实际上并未真正发生[H.Putnam,"Brains in a Vat",In B.Wray(ed.),Knowledge and Inquity:Readings in Epistemology,Broadview Press,2002,p.190]。
(12)在另外的地方,普赖尔对直接辩护原则做了论证,概括起来有两个:无穷后退论证和举例论证。不过我认为这两个论证都没有说服力。对于无穷后退论证,普赖尔自己也承认:“它并非最好的论证。”举例论证的问题在于,普赖尔所举的例子涉及的都是自我知识而不是知觉知识,例如我知道我疼痛,我知道我正在想我外婆[James Pryor:"There Is Immediate Justification",in E.Sosa and M Steup(eds.),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Oxford:Blackwell,pp.181—202]。
(13)James Pryor:"The Skeptic and the Dogmatist",Nous,2000,34(4):pp.517—532.
(14)推理如下:(1)我知道草席上有一只猫。(2)如果我知道草席上有一只猫,那么我就知道我不是缸中脑。所以,(3)我知道我不是缸中脑。
(15)例如,柯恩(Stewart Cohen)就说:“在知识论中,承认可错主义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Stewart,Cohen:"How to Be a Fallibilist",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1998,2:p.91)
(16)Ram Neta:"Perceptual Evidence and the New Dogmatism",Philosophical Studies,2004,119:pp.199—200.
(17)Harman和Ginet讨论过这个悖论,分别参见Gilbert Harman:Though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Carl Ginet:"Knowing Less by Knowing More",in P.French et al.,(eds.),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V:Epistemolog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0,pp.151—161.
(18)Michael Martin:"The Limits of Self-Awareness",Philosophical Studies,2004,120:p.40.
(19)Bertrand Russell:"On Denoting",Mind,1905,14(56):pp.479—493.
(20)Timothy Williamson:Knowledge and its Limi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5—8.
(21)析取论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例如形而上学的、知识论的和现象的。这里所说的麦克道尔式析取论属于知识论的析取论(Adrian Haddock & Fiona Macpherson:"Introduction:Varieties of Disjunctivism",in Disjunctivism:Perception,Action,Knowled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24)。
(22)John 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7.
(23)(24)John McDowell:"Knowledge and the Internal Revisited",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2,64:p.97,p.98.
(25)Keith Lehrer & Stewart Cohen,"Justification,Truth,and Coherence",Synthese,1983,55:pp.191—192.
(26)Fred Dretske:"Entitlement:Epistemic Rights without Epistemic Dutie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0,60(3):pp.591—606.
(27)Edmund Gettier:"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1963,23:pp.121—123.
(28)Crispin Wright表达了这样的质疑[Crispin Wright:"(Anti-)Sceptics Simple and Subtle",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2002,65(2):pp.342—343]。
(29)休谟的自然主义大致上是这样一种观点,人类心灵受其认知方式的限制,并不能理性地认识世界,所以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哲学上是没有答案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反,在日常生活中,哲学问题自动消失了(David Hume: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Oxford:Clarendon Press,1946)。
(30)Wilfrid Sellars: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79.
(31)此即著名的KK原则。这个原则曾经一度得到广泛支持,例如Roderick Chisholm、Laurence BonJour等。但Timothy Williamson对KK原则给予了有力反驳(Timothy Williamson:Knowledge and its Limi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15—119)。
(32)Nico Silins:"Basic Justification and the Moorean Response to the Skeptic",in T.Gendler and J.Hawthorne(ed.),Oxford Studies in Epistemology,Vol.Ⅱ,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08—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