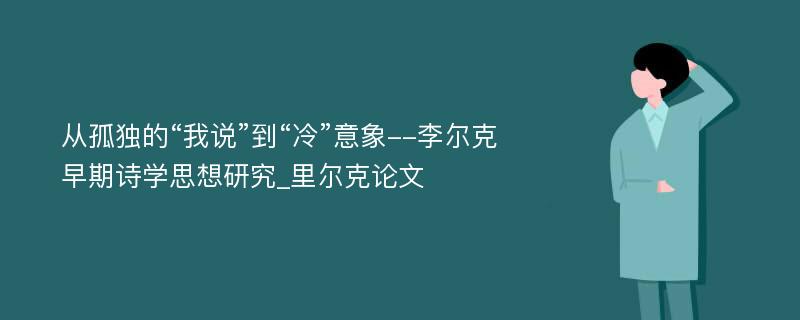
从孤独的“我言”到冷硬的“图像”——里尔克的早期诗学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图像论文,冷硬论文,孤独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诚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言,申述存在的焦虑经验及索问其意义乃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经典文本的一个核心主题。①虽然里尔克早在20岁左右就已因其申述与索问的独特性而享有了一定的声誉,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诗人早期的作品中平庸之作居多,整体运思水平甚至不及随笔,因此他后来再也未重印满溢着“幼稚的感伤”的第一部诗集《生活与歌曲》。学界一般认为里氏诗艺的真正开端之作乃是《时辰书》(1899-1903年)与《图像书》(1900-1902年),而这两部诗集之所以杰出是因为诗人在创作上述两部诗集前,便对贫困时代的抒情诗人究竟何为已然有了一种十分清醒的自觉。这种自觉可以从里尔克于1898年3月5日夜间在布拉格所作的名为《现代抒情诗》讲座中看出端倪。在该讲座中,他对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及抒情诗人的责任问题给出了清晰的判定。里尔克认为现时代的抒情诗人惟有以意大利诗人但丁为榜样,方能“深入到自我里面去倾听,一直深入到那自他存在便亦存在的、一直被言说的崭新的内容里面,都肯定能成为开天辟地第一人。只有当个人穿过所有教育习俗并超越一切肤浅的感受,深入到他的最底部的音色当中时,他才能与艺术建立一种亲密的内在关系:成为艺术家。这是衡量艺术家的惟一尺度”。② 简言之,抵达自我深处,寻获惟一属于自己的“崭新”语词来言说“存在”,是艺术家的真正职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当宗教与形而上学等其它归家之途俱被理性巨石堵死之际,“艺术”或许是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归家的惟一道路,而真正的艺术家则是任何想望此种归家的引路人。里尔克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即使对“最缄默的事物都要缠住发问,并永不知足,一直问个不休”,因缄默之物乃是“一切生命幽秘的发源地”,③其中有“存在”之价值的深意伏焉。作为引路人的求真艺术家,承担着清道之责,这便决定了他们必然是孤独的先锋,所以任何旁人都不能将这些“尚未有家乡的伟人邀至家中,因为,他们也不在自己家中,他们是等待者,是寂寞的未来之人”。④ 问题是为何惟有抒情诗,而非其他体裁方能曲尽时代之状,迫近存在之思呢?这是由抒情诗的体裁独特性与现时代精神氛围所决定的。首先,抒情诗“让艺术家能够不受束缚地表白自我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⑤其次,现时代具备诞生伟大抒情诗的氛围。里尔克认为与以往作家相较,现代诗人在技艺方面已日臻成熟,他们“在历史知识方面却受到极好的训练,前几世纪的客观的现实主义令他接触了自然与生活,训练他用眼睛度量事物的尺度”。⑥换言之,已然练就屠龙之术的新时代抒情诗人,只需沉潜谛听内心深处对新时代律动的应和之声,词语鳞爪自会成就腾跃飞龙。无疑,在此过程中他们需要的是“耐心倾听”和“安于寂寞”。这就决定了新时代抒情诗人必然是以常人难以估量的辛劳,来从事一项令常人难以忍受的严肃事业。里尔克认定自己堪此重任。 一生的目的与归途既已明确,那么接下来就只有去探求:作为一个前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⑦究竟如何以“孤独的我言”来道说“存在”源域,以及能以何种方式呈现“事”与“物”中所显现的“存在”影像?里尔克明言应创作一件关于时间以及时间洪流中的人之声音的艺术品,来“反映更深沉的生命、反映超越现今而适于任何时代经历的”⑧图像/影像,其运思结果便是《时辰书》与《图像书》。 一、时间:我言与“存在”——在时间湍流中铭刻“我言”之痕(论《时辰书》) 《时辰书》(Das Studen-Buch,又译《定时祈祷书》或《时间之书》)分为三部:修士生活之书、朝圣之书、贫与死之书。在1911年的一封信中,里尔克曾如是解说该诗集的源始:“清晨醒来,或在夜晚当你能听见寂静的时候,在我心内即升起——过去有时亦如此——从我自身出来的字语,似乎就是‘祈祷’,倘若你愿意如此相称的话——就是祈祷——至少我认为它们是祈祷。”⑨由此,便需弄清这种孤独的“静祷”或曰喃喃的“我言”,究竟朝向谁?意义何在?笔者认为,诗人的先“倾听”后“言述”的“静祷”行为究其本质而言,是他想在时间湍流中铭刻“我言”之痕,在“听”与“言”中确证“存在”的意义与指向。 1.时间:定时祷入“弥赛亚瞬间” 里尔克的定时澄心静祷,意味着他想脱逸历史主义那变动不居的普遍逻辑带给人的无物可依之感,意味着他希望进入时间的“本真瞬间”,让“时间”本身触击“自我”: 这一刻时辰垂下,触动我 以清澈的金属的敲击: 我的感觉在颤栗。我觉得:我能—— 我抓住这可塑的日子。 一切尚未完成,在我直观之前, 每一个形成默默停止。 我的目光已成熟,谁想拥有物, 物便像新娘委身于谁。 (1899年,林克译)⑩ 时间的这种本真的“瞬间”不是均质的流变时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此种“瞬间”里,时间是静止而停顿的;只有在此种“瞬间”中,“现在”才能免于流向“过去”和涌向“将来”,即能独立于流逝的时间之外而获得永恒性。因此,此处的“瞬间”实在地说不是“时间的原子,而是永恒的原子。它是永恒在时间中的第一个反射与第一个尝试,仿佛要停止时间”。(11)也惟有此种瞬间里,诗人才会感到“每一个形成默默停止”(或译“每个进程都静静凝伫”)。无疑,这是一种“弥赛亚式的瞬间”(Messianic now),它的任务是将历史整体主义那均质化的时间中断,其本质是一种断裂的当下。永不在场的历史意义与整体意义必须从碎片中去撷取;也惟有在此种“瞬间”中,时间方能如其所是地绽开。“过去”、“当下”与“未来”都是时间之花生长出的破碎花瓣,时间永远不会结出带有目的性的异化之果,这样的时间也就有了涌现不息的内在活力和可言说的无限可能性。此时,存在的本真性便会骤然现身——诗人“想拥有的物”便会如“新娘”般委身自己,“给出”自身。然而,这种“形象化的现身”却只能被领会,而难将其捕捉并呈现于“我言”,因为这是一种先于语言的“晦暝之境”: 我爱存在的晦冥时刻, 它们使我的知觉更加深沉; 像批阅旧日的信札,我发现 我那平庸的生活已然逝去, 已如传说一样久远,无形。 我从中得到省悟,有了新的 空间,去实践第二次永恒的 (1899年,杨武能译) 在生命的晦暝时刻,个体的“我言”默然无声之际,居于语言之先的“知觉”却能更强烈地触知那尚未道出与不能道出的东西。里尔克认为,“一切事物都不是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可理解而又说得出的;大多数的事件是不可言传的,它们完全在一个语言从未达到过的空间;可是比一切更不可言传的是艺术品,它们是神秘的生存,它们的生命在我们无常的生命之外赓续着。”(12)因此,惟有在生命的某些晦暝时刻,一个更加本质的耀动着永恒之光的辽阔的“内在宇宙空间”才得以敞现自身。由此,肉与灵的冲突被凸显出来——外在的沉重肉身生命易坏,而内隐轻逸的魂灵生命却可永驻并能迫向无限领域。诗人体认到这个不能为语言之光所照亮的黑暗之境,才是一切能被语言道出之物的真正本原——“显与亮”本自“幽与晦”: 黑暗啊,我的本原, 我爱你胜过爱火焰, 火焰在一个圈子里, 发光,因此给世界加上了 界限,出了圈子 谁还知道有火焰。 然而,黑暗包罗万象: 我信仰黑暗。 (1899年,杨武能译) 光与火焰等“可见”的有“界限”之物是“有封、有畛的”,而不可见的“黑暗”却是“未封、未畛”之物,后者才是前者的本原,所以本诗结语道“我信仰黑暗”。为言说方便计,诗人将居于静祷朝向域那黑暗之心的“存在”真宰强名之为“上帝”。因此,《祈祷书》中的“上帝”虽保有《圣经》所载的诸多神迹,却是一种为言说方便之故而为“存在”起的一个假名,此种“上帝”观念其实源自一种能使艺术家超越自身(免于陷入人类中心论)与时代(免除囿于独尊性的一神论)之双重局限的“泛神论”。 与基督教上帝相比,这个品物流行的“存在”上帝更显神秘、无限,更能超越时空限制而显现自身;而作为有限者的人,对他的爱也就愈加无尽、强烈,因而在朝向他的静祷中,人终能以艰难却虔敬的“心言”照亮自身的存在。接下来,诗人给出了这个能在时间湍流中任意西东、自在永在的“存在”上帝之真容。 2.存在:圣言·谛听·期待 里尔克笔下的这个“存在”上帝,自在、永在于时间湍流之中,首先是在“过去”中——时间因一个象征纯粹沉思的“光”字而“开始”,所谓太初有“言”: 你曾喊出的第一个字是:光。 从此,时间诞生。你随即沉默了很久。 人是你说出的第二个字,它令人惊恐, (它的话音依然将我们遮蔽在夜色深处) 接着又是沉默。你再次酝酿要说出的东西。 但我就是那个从未听你说到过的第三个字。 我经常在夜晚祈祷:只用手语 而不用言语,祈祷会悄然生长 (1899年,臧棣译) 据《圣经·创世记》载,“光”是上帝所言的第一字,这第一个字分出两个世界:一为“光”(言)所照亮的“有限世界”,或曰能被言说的世界;二为“光”亮所不及的“无限世界”,或曰语言不可言说的前语言的世界。显然,“言”在创世中意义可谓非凡: 有个人说“光”,我们仿佛听到“一万个太阳”。他说白天,你听到的是“永恒”。你突然明白了:他的灵魂在说话,不是出自于他,不是通过那些你第二天就会忘记的渺小的话语,也许是通过光,通过声音,通过风景。因为,如果一个灵魂说话,它便在万物当中。它将一切唤醒,赋予它们声音,它让我们听到的总是一支完整的歌。(13) 因此,诗人深知晚祷时“只用手语,而不用言语”,免遭那“不可言说的奥秘的嘲笑”。那么,这个“以言创世”后,却不“再言”的“存在”上帝居于何处呢?里尔克认为,只要“谛听”就会识察出他就“比邻”在我们左右,因为“在邻近之中寻找一种与‘无限’的关系,是一种把无限性留给‘无限’的见证方式……只有在邻近与上帝的靠近中,人们才能谈到一个非本体论的上帝”。(14)一个真正的诗人就本质而言,就是圣言的谛听者,即使在看似最徒劳无益的日常生活中,亦应时刻儆醒谨守,因为“圣言”犹如不速之客的邻人,总会不期而至地叩门: 主啊,你是邻居。如果在夜晚 我用震耳的敲门声把你吵醒,这样做 仅只意味着我听不到你喘息 我明白:你是孤独的。 你应该喝点什么,难道那里没有人 在黑暗中摸索着,把饮物递给你。 我一直在谛听。虽然传来的气息微弱 我知道自己在接近。 在我们中间横竖着一堵窄墙 从你的或我的唇中呼出的召唤 凭借纯粹的机缘 那一切全无声息 这堵墙由你的影像筑成。 (1899年,臧棣译) 当然,识察到“存在”上帝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就能谛听到“圣言”(“我听不到你喘息”)。若想成功,只有持“一直在谛听”或喃喃“我言”的这种“在期待之中”的状态,来迫近存在(“我知道自己在接近”)。惟其如此,在某个“纯粹的机缘”成熟时刻,“我”与“你”之间“横竖”的“窄墙”才会被“负重的我言”或“神恩的圣言”(“你的或我的唇中呼出的召唤”)所“推倒”。无疑,“我言”能否使存在源域最终敞开,全赖某种“机缘”的降临;而在此之前,诗人能做的便惟有忍耐与期待,而忍耐与期待的力量之源无疑出自一种对“未来”的“信与望”: 你是未来。盛大的日出染红 永恒那一望无垠的平原 你是黎明,当时间的暗夜逃走 你是露水,是早晨的鸡鸣,是处女 陌生人兼母亲,你是死亡。 你出身于命运的变幻的形象 耸立在漫长的孤寂中, 既没有受到哀悼,也没有受到欢呼, 像一片原始森林,你远离修辞。 你是万物深刻的缩影 紧闭的唇中含着生存的奥秘, 你以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展示自己: 对于船,你是港湾——对于陆地,你是船。 (1901年,臧棣译) 显然,这个“存在”上帝无处不在,“它寓于万有中,便在于万有中,并且由此可以推断说,它既不会开始‘是’,也不会终止‘是’(esse);它总是曾是(fuit)、正是(est)、将是(erit)”。(15)在这个自在永在,在一切之中的时间“上帝”面前,诗人能做的是满怀“期待”(未来)地谛听(现在)圣言(过去),以便在机缘莅降时,书写“我言”。因此,作为一个求真诗人便意味着“在一种持续不断地向着绝对者的自我伸展中,在对上帝的开放状态中度过他的一生……人之所以为人仅仅由于总走在通向上帝之路上,不管他是否明确知道这一点,不管他是否愿意,因为他对于上帝永远保持着一个有限者之无限的开放状态。”(16)换言之,作诗就是走上朝向“存在”上帝之途,它是作为终有一死的人(此在,Dasein)所负有的一项道出不可或缺之“我言”的使命。 3.此在:终有一死但不可或缺 与自在永在的不朽“存在”上帝相比,“此在”无疑是终有一死的易朽者,但这绝非意味着悲观,因为人若想肯定有一种存在的照亮状态,就首先需要将自身肯定为一种偶然性的有限者,即人是终有一死者: 因为我们只是树皮和叶片。 那巨大的死,人人包含, 乃是果实,万物围绕它旋转。 (1903年,林克译) 人惟有体认到死是一切生命要素的重要成分,并伴随着整个生命,才能真正了悟存在的意义:“主啊,让每个人有他自己的死吧!/在这来自生命的去死中,/他才有爱、意义和苦难。”(1903年,孙周兴译)同样,与“存在”上帝创生万物的“大能”相比,“此在”充其量只是一个匠人: 我们全都是匠人:要么是学徒,师傅, 要么是大师。是我们建造你这巍峨的教堂。 偶尔,会有一位神色严峻的旅人 走向我们,像一束耀眼的光 让众多匠人的心灵惊悚不已, 它向我们传授了一种新的记忆。 (1899年,臧棣译) 但人这种有限的存在者却因其能追问“存在”与“必然性”,而会以一种精神自由的状态伫立在“存在”上帝前,因为归根结底人乃是一种综合——“无限性”和“有限性”、“那现世的”和“那永恒的”以及“自由”和“必然”的综合。(17)要之,这种综合的特性,使“人”(尤其是艺术家)成为这一“存在”上帝的见证者与言说者。因此,没有“人”,“存在”上帝便顿失其存在的意义: 你该怎么办,上帝,若我死去? 我是你的水罐(若我破裂)? 我是你的饮水(若我枯竭)? 我是你遮体的衣,谋生的手艺, 失去我你就失去你的意义。 没有我你就没有家,听不见 问候你的话语,亲近而温暖。 丢掉天鹅绒凉鞋,这就是我, 你疲乏的双脚又穿什么。 你的大氅正从你身上滑落。 你的目光——我用我的脸颊, 像一个枕头,温暖地承受它, 一定会投来,久久搜寻我, 并在太阳落山之时, 投入陌生岩石的怀里。 你该怎么办,上帝?我发愁。 (1899年,林克译) 这个“存在”上帝的存在乃是因人的存在而具有了意义,他所创造的万物因艺术家的勤勉劬劳而能进入可被言说的无蔽状态。如果我们将万物喻作一个舞台的话,“在人没有登台用他身体上快乐或悲哀的动作充实这场面的时候,它是空虚的。”(18)因此,成就一件艺术品就是去切近“存在”上帝,就是去“寻找他、认识他,在自己内心深处创造他,在作坊里面找到他”。(19)总之,艺术家完成艺术品的辛勤劳作,便是荣耀着“存在”上帝,而亲近艺术其实是迈向终极完美,迈向“存在”上帝。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于圣言的谛听,不可须臾休止;对于万物渴求其表达自身的愿望,不可稍有倦怠,即使 扑灭我的双眼:我能看见你, 堵塞我的双耳:我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能走向你, 没有嘴我也能召唤你。 折断我的双臂我抓住你, 用我的心像用一只手, 止住我的心,我的大脑会跳动, 纵然在我脑子里放一把火, 我用我的鲜血驮负你。 (1901年,林克译) 诸神退隐的衰颓世界终会因“艺术家”的“我言”,而变得再次宏大:“一切将再次变得宏大而强盛:/大海涌起波纹,陆地平展开阔。”(1901年,臧棣译)当此之时,真正传播美的严肃使者便会以崭新的艺术语言称道上帝之义。那么,缘何艺术家有此种大能呢?这与里尔克此时所持的上帝观念有关,他认为,就本质而言,“存在”之假名的“上帝”不过是一件“最古老的艺术品”。(20)“古老”意指时间之初的“本原性”,一切由其创生的万物自然都会被置入只向艺术家“显现”的艺术品性,因此,“艺术乃是万物的朦胧愿望。它们想要成为我们的所有秘密的图像。它们很乐意抛却其业已凋敝的意识,以承载某种我们的沉重的渴求……它们乐于带着艺术家所赠予的新名称而感激不尽,千依百顺……事物的愿望是想成为他(艺术家)的语言。”(21) 那么,居有“物”的“艺术方式”与“庸常方式”有何不同呢?我们知道,在现代性所确立的一般主体面前,物的“存在状态等于是通过自我主体并且对自我主体而言的被表象状态”,(22)即物只能被把握为“对象式的存在者”,物的存在本身被遗忘了。此时的人们将“自身建立为一切尺度的尺度,即人们据以测度和测量(计算)什么能被看作确定的——也即真实的或存在着的——东西的那一切尺度的尺度”。(23)这就使“物”陷入了诸种沉重的意义关系中,它们沦为被表象与被算计的对象了。总之,物“本质的巨大联系”(24)灾难性地消失殆尽了。里尔克认为惟有当真正的艺术家捕捉到“事”与“物”中的“存在”(艺术)显现之际,艺术品方能诞生,而“物”也会随即被提升到其“本质的巨大联系”中。因此,里尔克说必须在“一切统一为‘一’之处,艺术才得以实现”。(25) 二、空间:我言与“图像”——将“存在”显现的“影像”素描为“图像”(析《图像书》) 1.存在显现:“影像”与“图像” 既然“事”与“物”中显现着“存在”的影像,它们渴求着自身能被诗人的“我言”道说,那么究竟以何种方式将这种“显现”呈示于“我言”呢?里尔克突然意识到,《时辰书》中那种直面“存在”本原时所采取的充溢着强烈情感色彩的“我言”方式,显然不适用于描述“存在”在事物与人中所显现的“影像”。里氏认为这种“显现”是真实且客观的,因此主体就应尽量抽身而出,以一种精准客观的方式对其把握,“人们必须把万物从自己身边推开,以便后来善于取用较为正确而平静的方式,以稀少的亲切和敬畏的隔离来同它们接近。”(26)也就是说,面对万物的主体将自身的激情逐步摒除后,就能以一种更简洁的方式捕捉到一个伟大的现存的真实。这种寻求“客观表达”(sachliches Sagen)的尝试结果就是将“存在”显现的真实“影像”描绘成《图像书》(Das Buch der Bilder)中那一帧帧冷硬坚实的“图像”。里尔克拈取了德文Bilder这个兼有“影像”(image)与“图像”(picture)两义之词可谓煞费苦心,挑明他自信捕捉到了“事”与“物”中所显现着的“存在”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图像书》中修辞策略的转变引发了一种抒情诗写作传统的革新,它使“从济慈发轫的那种奇异的、那喀索斯式自恋的抒情诗终结”了。(27) 那么,这种新的诗学观念缘何发生?笔者认为,除却诗人长期不休的探求外,1899年与1900年的两次俄罗斯之旅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小觑。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的俄罗斯,在里尔克心里始终都居于一个能连接诸神与大地的纽带性地位,它让诗人对神、物和艺术的三者关系有了一个清醒的体认。当里尔克置身伏尔加河畔时,他觉得自己好象“目击了创造本身”,万物中充盈着几近涨溢而出的“存在”,“我在那里体会到一种伟大的、神秘的安全感,我的生命因此而存在。”(28)此时,诗人觉得自己“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发现“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29)他能切近“存在”的根基,而不需像《时辰书》中那样以艰难的喃喃絮语来剖白、亲近隐匿的“存在”。要之,时间湍流里那阔大坚实的万物中有“存在”显焉,只待有心之“眼”观而道之于恰切“我言”。 2.存在·此在·物 《图像书》分为两部,分别侧重描述“存在”在“事物”与“人”中的显现影像。此时,里尔克的修辞策略与表现对象都已明确——只需一个“开端”来“进入”对存在之显现影像的描绘:“你造就了世界。世界巨大/如一个字,尚在沉默中成熟。”(《开篇》,1900年,陈宁译)当然,作为一种新的运思经验的“开篇”之作,本诗仍残留些许《时辰书》中向作为“存在/本原”的“存在”上帝的剖白。从词源意义上看是“本原”造就了世界,“本原”(arche),在其古希腊文词源中有两义:一是开始、开端,二是政治上的权力、统治。它是事物追求的“最终目的”,引发事物运动的“动力”,成为引起并统治事物运动的“原则”和“根据”。形而上学即是追寻事物存在的最终根据的“本原”的学说。在传统形而上学中,“本原”完满至善,超时间性、永恒在场,独一无二,如上帝、绝对理念以及第一因等观念。那“本原”/“存在”究竟如何显现自身呢?诗人说“世界巨大/如一个字”,无疑“字”即西方思想史上那本惯有的“原始之书”,即世界是一本由上帝所书写的“大书”(“自然之书/世界之书/真理文本”),各种人写的“普通文本”都是对这一“大书”踪迹的某种追寻、接近但又不可能抵达之的一种尝试。在“原始之书”中隐含着一种所谓的“原始书写”(arche-writing),它是言语(语言的语音形式)和文字(语言的文字形式)得以进行的动力和基础,它履行的乃是揭示世界意义的功能。 因为“原始书写”并不现身,只在“普通文本”中留下“踪迹”,所以“世界巨大/如一个字,尚在沉默中成熟”,“世界”只是“原始之书”/“存在”的显现影像。因此,世界必不成熟完善,而艺术家的职责就是通过自己的艺术语言使之走向成熟完善:“由于我们,他形成着,由于我们的快乐,他成长着”。(30)但无可否认的一点是,对其进行把握是异常艰难的,因此,“艺术家似乎尚在智者之上。后者努力解谜的地方,艺术家却面临着远为伟大得多的任务,或者人们也可以说,更伟大的权利。艺术家的权利是爱谜。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爱,倾注在谜上的爱。而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如此:谜,用爱来拥抱、美化、浇灌的谜。”(31)换言之,艺术家是必须表达“某种非常个人的、孤独的东西的人,表达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的人,他总是设法表达最陌生的东西”。(32) 因为“存在”在世界中的显现域,只有人(此在)与非人(非此在)的存在者两种,所以《图像书》中对存在之显现的申述也分为两类。首先,让我们以《严重的时刻》一诗为例,来看“存在”究竟如何在“此在”中显现: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夜间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1900年,陈敬容译) 本诗的主题乃是“存在”在“此在”中的显现被遮蔽或被遗忘了。严重(Ernste,或译“危急”、“急迫”)时刻之所以“严重/急迫”,皆因诗人已然识透——能识得自身之“存在”本真性以及自己乃是与他人共同存在着(共在)的人甚少。因此,他在四节诗中反复用了四次“此刻”(时间)与“某处”(空间)与“有谁”(他人),来反问究竟有多少“他人”能在同一时间与空间中,领会到自身的本真性存在以及与“我”共同存在的他人之存在。 需要关注的是四节诗中的“无缘无故”一词,因为若是有因由地“哭、笑、走、死”以及有因由地“哭、笑、走向、望”着我,都是出于一种世俗性功利目的,而非因领会到“存在”的关联所致。里尔克并未选取那些大家碌碌其中的庸常状态来切近“存在”,因庸常状态之中的人不可否认地是遗忘了存在。“紧迫”之处乃在于,就是当人置身“哭与笑”等非同寻常的情感体验时,行走于人生的存在之途而倍感“孤独”之时,乃至经验此在的终结——“死”之时,都遗忘着“存在”(自身的“存在”以及与他人的共在)。因为在日常状态中,当遭遇他人之死时,此在大抵会自语“人终有一死,自己却是尚未”,以便“继续遮蔽死,削弱死,减轻被抛入死亡状态”。(33)这样,“死”便被“敉平为一种摆到眼前的事件,它虽然碰上此在,但并不本己地归属于任何人”。(34)当“死”都不能使人领会到“存在”,这个“时刻”就是存在被遗忘的“急迫与严重”程度的峰顶。在这帧存在被遗忘的图像面前,我们感到触目窘迫乃至羞愧惊心。 人容易遗忘存在,那“物”的存在如何呢?当里尔克以诗人眼光谛视周遭万物时,发现万物显现着存在:“万物似乎都没有年龄:/眼前景物像《圣经》的诗句,/肃穆,庄严。永恒。”(《观看者》,1901年,杨武能译)然而,若想将这种“我观”以“我言”恰切地呈现出来却又是一件十分艰难之事,因为,“我们与之搏斗的,何等渺小。/与我们搏斗的,大而无形;/要是我们像万物一样/屈服于伟大的风暴脚下——/我们也将变得宽广、无名。”(《观看者》,1901年,杨武能译)显然,“艰难”是因为“存在”的不对等,即诗人作为终有一死者,想要言说沉默无形的隐幽存在,他只有通过辛苦工作、搏击,才能进入伟大的存在风暴,才能真正地赢获存在。(35)这种安于“忍耐”而最终会被裹挟进“存在风暴”的激荡状态,被言述在其名诗《预感》中: 我像一面旗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 我觉得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 下面一切还没有动静: 门依然轻轻关闭,烟囱里还没有声音; 窗子都还没颤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 (1902-1904年,陈敬容译) 在本诗前半首中,诗人通过移情树立了一面将要突进“物化”状态的“旗”。在裹挟着本真性“存在”的大风袭来并注入世界之前,置身辽阔空间中的旗、居有终有一死之人的屋(门、窗)、朝向“天空”的烟囱以及散落在“大地”之上的尘土,这世界中的四者之间尚未进入里尔克所说的那种“本质的巨大联系”中。因此,“旗”与其他三者之间仍是相互分离的对象物,里尔克居入的那面“旗”就未成其为真正的“旗”。这样,前后节之间的那一行空白便不可或缺,因为它是一个本真性“存在”显现前的信盼与本真性“存在”显现着的激动之间的伟大静息域,此时: 人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他感到,它们的存在是怎样在规律中消隐,没有期待,没有急躁。并且在它们中间有动物静默地行走,同它们一样负担着日夜的轮替,都合乎规律。后来有人走入这个环境,作为牧童,作为农夫,或单纯作为一个形体从画的深处显现:那时一切矜夸都离开了他,而我们观看他,他要成为“物”。(36) 静息过后,裹挟着本真性“存在”的大风袭来并将“旗”卷进其中,“旗”物化着(或曰旗“旗着”),“旗”便回返到它“本质的巨大联系”中。当这种关联展开之时,“旗”的存在才显现而出,“旗”方成其为一面真正的“旗”,因为“旗”聚集着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旗作为“物居留大地和天空,诸神和终有一死者;居留之际,物使疏远的四方相互趋近”。(37)“认出”(或译“知道”)了“存在”,就是“知道”了“存在”——已经知“道”。“我/旗”因本真性“存在”的充盈而激动如大海,“我/旗”在本真性“存在”的风暴中猎猎卷舒,其状如大海波浪起伏,“我/旗”最终被“独自”抛入向来我属的本真性“存在”之中,分化支离的世界最终转换成一个具有“本质的巨大联系”的世界。里尔克认为,诗人的最重要职责就是促使世界实现此种转换,即将“‘物之精华’从一切转变、混乱和过渡当中挽救出来;它应将每样物都从偶然的联系中隔绝出来,然后把它们置于更庞大的关联当中去,真正的重大事件顺着这些关联展开”。(38) 换言之,诗人的职责就是通过居于“物”(或“成为物”)中,来与“物”之旋律相应和,进而“我观”到本真性“存在”的现身,最终才能以精妙的“我言”将其画为“图像”,以便使更多的人知道究竟何为一个具有“本质的巨大联系”的世界。当然,在里尔克成功捕捉“存在”在人与物中的显现影像的诗集《图像书》中,最为汉语学界所熟知的诗作乃是《秋日》一诗: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晷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1902年,冯至译) 前两节诗中,本真性“存在”(“主”/神)的“无形”(阴影、秋风)与强力(落、刮、让、给、迫)先是显现于天地间的诸种“物”(日晷、田野、果实)中,尔后又聚集着天地之气,显现在人的劳作物(“酿入浓酒”)中,原本各行其是的天、地和人最终因本真性“存在”的驱策收束而汇拢到一起,分化支离的世界再次转换成一个具有本质的巨大联系的世界。当然,能领悟并呈现“本质的巨大联系”的世界的诗人注定是一个异于常人的孤独者,因此第三节诗中端呈出的乃是一个真正以艺术为家的求真诗人——他注定要永远孤独地行进在归其真家之途上。 总之,里尔克在其早期代表诗集《时辰书》与《图像书》中,先是经由在时间的湍流中铭刻自己观照“存在”时所得出的“我言”之痕,而后又借助将“存在”显现的“影像”素描为“图像”,淋漓尽致地道出了现代社会带给每一孤独个体的那种难言的存在焦虑感。笔者认为,解读里尔克的早期诗学思想对于我们把握其中期和晚期诗作的意义十分重大,因为里氏早期诗作中所展示出的上述诗学思想在其中期和晚期的诗作中只不过是被继续深化了而已。 ①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289页。 ②R.M.里尔克:《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集》,史行果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44,45页。 ③R.M.里尔克:《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集》,47页。 ④R.M.里尔克:《里尔克精选集》,李永平编选,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90页。 ⑤R.M.里尔克:《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集》,49,50页。 ⑥R.M.里尔克:《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集》,50页。 ⑦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一书中认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笔者认为,我们可以称里尔克为发达资本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对应文化样态为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抒情诗人,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论争参见以下两书:Fredric Janeson,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London & New York:Verso Books,1991);Ernest Mandel,Late Capitalism,translated by Joris De Bres(London:NLB,1976)。 ⑧R.M.里尔克:《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集》,77-78页。 ⑨R.M.里尔克:《时间之书》,方思译,台北现代诗社1958年版,4页。 ⑩本文采用的里尔克诗作中译文均出自《里尔克精选集》(李永平编选,燕山出版社2005年版)、《里尔克诗选》(臧棣编,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杜伊诺哀歌——里尔克诗选》(林克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三书,文中只注明译者。 (11)Howard V.Hong & Edna H.Hong eds.The Essential Kierkegaar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51. (12)R.M.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冯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5页。 (13)R.M.里尔克:《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集》,99页。此处对不可见物的等待,显然受到了《圣经》的影响,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圣经·罗马书》和合本8:24-25)。 (14)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238页。 (15)安瑟伦:《信仰寻求理解——安瑟伦著作选集》,溥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64页。 (16)K.拉纳:《圣言的倾听者》,朱雁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72页。 (17)基尔克郭尔:《畏惧与颤栗·恐惧的概念·致死的疾病》,京不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419页。 (18)R.M.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86页。 (19)R.M.里尔克:《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集》,99页。 (20)霍尔特胡森:《里尔克》,魏育青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90页。 (21)R.M.里尔克:《里尔克散文》,叶廷芳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111页。 (22)马丁·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821页。 (23)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113页。 (24)R.M.里尔克:《里尔克散文》,111页。 (25)R.M.里尔克:《里尔克精选集》,628页。 (26)R.M.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90页。 (27)霍尔特胡森:《里尔克》,279页。 (28)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莱纳·玛丽亚·里尔克与里尔克一起游俄罗斯》,王绪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3页。 (29)R.M.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91页。 (30)霍尔特胡森:《里尔克》,91页。 (31)R.M.里尔克:《艺术家画像》,张黎译,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21页。 (32)R.M.里尔克:《艺术家画像》,52页。 (33)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293页。 (34)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291页。 (35)据考,本诗中人与存在的艰难“搏斗”,可能典出于《圣经》中的雅各与神摔跤,“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圣经·创世记》和合本32:24-28)。显然,雅各因与神摔跤的胜利而赢得以色列国,诗人则因与存在上帝之搏斗的胜利而赢得了语词。 (36)R.M.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90,91页。 (37)Martin Heidegger,Poetry,Language,Language,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Harper & Row,1975),177页。德文wissen(know)直译应为“知晓”或“知道”,陈敬容将其引申译为“认出”,便与和合本《圣经》中译文形成了互文,因为“认出”一词曾在《圣经》中多次出现,如属神之人可以认出“神的灵、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圣经·约翰一书》和合本4:2-6),当然诗人此处“认出”的乃是本真性“存在”的显现。 (38)R.M.里尔克:《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集》,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