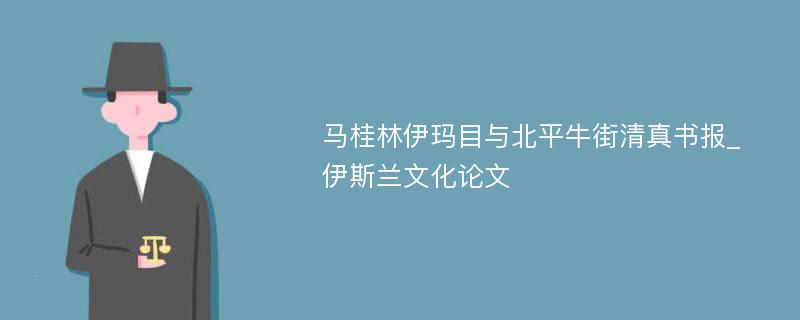
马魁麟阿訇与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平论文,真书论文,阿訇论文,报社论文,牛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4)06-0041-04 哈佛大学阿瑟·萨克勒博物馆至今保存着几十张弥足珍贵的中国伊斯兰招贴画及海报,它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毕敬士在临终前捐赠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后转交阿瑟·萨克勒博物馆保存。这些招贴画和海报大多数是民国时期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下文简称书报社)印制的。书报社是北平地区创社最早、规模最大的清真出版社,由北京阿訇马魁麟及其子创办并经营,其宗旨是“传播伊斯兰文化,扩大穆斯林知识视野”[1]。其书刊远销海内外,颇具影响,为回族穆斯林攻读伊斯兰知识、传播伊斯兰文化、促进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 马魁麟,字星泉,北京牛街世居回民,生于1878年,卒于1940年[2],享年63岁。台湾回族学者贾福康称,马魁麟的“先祖传为明太祖原配皇后马娘娘(又称大脚马皇后)之族人,任明朝皇宫禁卫军指挥,在北京城内以‘侍卫马家’著称,奉钦命其后裔得在清真寺任教化之职,其祖先甚多任职牛街清真寺阿訇”[3](68),由此可知马魁麟出生于宗教世家。 马魁麟家族原居南京,祖上曾在明朝宫廷里担任过大内侍卫武官,故得名“侍卫马”。清末民初时,牛街有过一位教义精深、品格端正的大阿訇马善亭,就是“侍卫马”的后裔。“侍卫马”的另一支后裔就是马魁麟家族。马魁麟及其父都因从事宗教职业,其家族又被称为“师傅马”。民国初年至抗战期间,马魁麟家办了“清真书报社”,故在牛街又被称作“书铺马”[4]。马魁麟之父名叫马旺,字玉山,是一名精通伊斯兰教法的阿訇。马魁麟自幼秉承庭训,耳濡目染,对伊斯兰教造诣很深。早年在家设立私塾,召集周围的学龄儿童,教授穆斯林必备的宗教基础知识,“循序诱导,桃李盈门”[2]。马魁麟追随父亲的职业做阿訇。他除了教街坊里的教民有关伊斯兰教知识以外,还认真地要求自己子女学习伊斯兰教义和伊斯兰教典籍。 在现代印刷术流行于中国经堂教育体系以前,中国穆斯林师生们都习惯于用竹笔和绵纸抄经。手抄的典籍时间一长就容易被磨损、虫蛀或发生残缺。为了将残破书籍修复成新,马魁麟在担任教职的同时还自行研制了一套整旧如新的技术,无论怎样破旧的经书典籍,一经修补,便可如新。“友好之藏经破碎者,多请阿訇为之修补。”为了给求学者提供方便,他经常带着儿子奔走于北京各清真寺,收集各种破旧经书,回到家后予以修补,再送到每个学员手中,博得众人的好评。因此在北京他以“粘经阿訇”著称[5](92)。 马魁麟的三子马明道在回忆中如此描述父亲早期“粘经”的情形:“先父在世时,将北平城郊的四十一座清真寺(除去女寺五座不计外),区分成若干路线,每有整妥之经卷数卷,或十数卷时,辄循一条路线前进,走遍沿线各清真寺,一条路线复一条路线,一年岁月复一年岁月,周而复始,直至年老衰竭时,始行放弃此项周而复始之循行活动。每到一座清真寺时,先行拜访阿衡,次访诸经生——海里凡,展示整新作品,然后以新品换旧品,视新旧品大小厚薄之差别,然后贴出或贴入若干铜板,以作教材费,将换得之旧品,携回舍间,利用闲暇时间予以修整,修整妥善后,再循行另一条路线,沿线访问各清真寺并交换新旧品。”[6]在长期的修补宗教典籍的工作中,加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马魁麟萌发了办一个有关回族教义书籍的印刷机构,以解广大经学生及回回民众缺乏知识读物之困[7]。 对于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成立的具体时间,尽管几则资料认为是1920年至1922年前后时期,也有人认为是清朝末年,还有具体确定在1905年的。但总体而言,清真书报社的经营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为它的鼎盛时期。当时书报社的印刷地点设在牛街西北,即广安门大街以北的“中华禅林寺”。书报社租用了该寺临街三间屋子西头一间,约有12平方米,作了印刷“车间”[8](631)。当时,书报社印了不少经堂教育所用的教材和穆斯林学者的著述。一般较畅销的是经堂教育专用教材,一年能售出上千册,而一些古籍、哲学方面的书籍,因销量不大,一年只印几十本[7]。 书报社所售书不用一般的明码标价的办法,而是不定期地将售书价格印制成价目表,根据情况随时调整。经堂教育的初级教材一般是2至10个铜板一本,古籍价钱昂贵些,一般为1至2个现大洋。门市由马魁麟主持,视情况或优惠或赠送,故书报社的早期经营具有义务传播伊斯兰教文化的性质。书报社的销售范围除北京地区外,还远及大西北,尤以兰州、宁夏为主。同时还向出国人员经销,把国内印刷的经本作为礼品带到国外交流,亦将留学人员从国外带回的原版经本翻译后出版印刷,在国内销售。据说,大约在1922年书报社销售门市部才打出了蓝布横幅“北平清真书报社”,字是当时的宁夏督统马福祥所题,它既做招牌又做广告[7]。至于书报社印刷书籍的装帧,就古籍和精品书而言,一般采用木板线装代布函套,单册书及教材一般用石印线装的装订形式。 由于书报社是民间创办的私营企业,其经费基本上靠自养。回族上层人士马福祥曾资助印了一些伊斯兰教书籍让书报社代售外,也对它很少关注。因此,书报社初期经费十分紧张。马魁麟便采取多种措施筹集资金,一是募捐,即到各清真寺讲经,或被人宴请到家中念经,以此挣些报酬,书报社还经常得到牛街回民的微薄捐助。二是以书养书,靠代售书籍。三是销售宗教用品,以出售香饼、礼拜帽和芭兰香等来积累资金。当书报社购置了石印机后,印刷出版和销售业务有所扩大,经费逐渐好转,事业遂兴旺一段时间[7]。 有人描述那时书报社的情况:(它)坐落在牛街寿刘胡同,其规模很小,就是两间平房绿色门面,又印刷出版,又销售书刊的一个小书店,别看它小,却名扬海内外。叙述者在西北学校读书时几乎每天路过此店进去看书,室内四围图书柜架布满了中、阿、波各类书刊,墙壁上方贴满很多绘画、挂图,题材有:克尔白图、阿里宝剑图、奴海船图(即诺亚方舟)、至圣避难洞图、五十代传光图以及阿拉伯国家纪念邮票等。伊斯兰文化气氛很浓[9]。书报社出书种类也较繁多,其印刷、出版和经销的经书包括《古兰经》及圣训选译本和有关伊斯兰教义、教法、哲学、历史、文学、伦理、常识及语言、修辞等各类经书刊物,尤以明清以来著名的汉文译著所占比重较大[10](93)。 马魁麟生前经理书报社时,曾得到其几个儿子的辅助。长子马宏道跟随王静斋阿訇学经,他与马魁麟1921年初创办《清真周刊》杂志,马魁麟任经理,马宏道任发行人及编辑部主任,从事伊斯兰教义与教理的宣传。后来,马宏道又随王静斋到麦加朝觐,途中到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后又转到土耳其留学,获得伊斯兰哲学硕士学位后返归故里,他协助父亲继续经营书报社。他还参与了《正道》杂志的出版和发行工作。马宏道那时在书店中为出版和经销伊斯兰经书勤奋工作,颇有成绩[11](37)。 三子马明道离开成达师范学校之后,返回家中协助父亲经营书报社。他小时曾陪同父亲经常到北京各清真寺去回收破旧残缺的经书带回家修补粘贴。他还到牛街清真寺教大家念经,并创办过一所临时性小学,专教牛街穷苦人家的男女儿童念初级教材连三本,在学校门口放一个笸箩,凡是来念连三本的孩子就扔一个铜板进笸箩,以资书报社[11](37)。马明道凭借自己坚实的经汉两通的知识,为出版和发行伊斯兰经书,传播伊斯兰文化尽心工作。后来他到土耳其留学军事,学成回国后投入抗战。再后来在民国政府中从事外交工作。1949年后旅居台湾,任台湾政治大学的土耳其语教授,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成果颇丰[12]。 马魁麟的次子马光道也经常帮助父亲经营书报社。马魁麟去世后,他又帮助弟弟马中道经营管理清真书报社,付出了不少心血。抗战期间及国共内战时期书报社一度萧条。日本侵略者蹂躏中国半壁江山的痛心局势对马魁麟的身体状况有很大影响。1940年12月马魁麟无常归真,书报社经理由四子马中道继任。马中道在二哥马光道的配合下,继续经营着书报社。此时的书报社已是“落日余晖”,不再大量印刷书籍,只是守着原来的老家底,勉力支撑着局面。1949年新中国成立,次年,马中道向人民政府申请了营业执照和出版执照,但情景不看好,书报社陷于困境,甚至濒临破产,后来出版了马崇义的《穆罕默德的生平》而稍有转机。1956年公私合营,书报社加入宣武新华书店,马中道本人成为新华书店职员,遂将书报社积存的全部版本交给宣武新华书店,由政府给他支付一笔报酬。历时半个世纪的“北平清真书报社”经营至此结束。然而,交给宣武书店的书籍版本至今下落不明。1966年“文革”开始,马中道本人收藏的书报社印刷的书籍孤本也被迫交出,又被强令烧毁[7]。由此马魁麟开创的中国民间伊斯兰出版机构的典型代表——北京牛街清真书报社正式落下了历史帷幕,这真是件令人十分痛惜的事。 据不完全统计,书报社数十年刊印的书籍大概有近百种。最早以书报社名义刊印(或代销)的书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四篇要道》(张中)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刊印的《归真总义》(张中)以及宣统三年(1911年)出版的《清真释疑》(金天柱)。1913年已出现了以书报社的名义出版的书籍,出版了中国穆斯林先贤的很多著述,如刘智的《天方三字经》《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孙可庵的《清真教考》,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归真总义》,马德新的《四典要会》《四典要会·大化总归》,蓝子羲的《天方正学》等。 1930年至1931年间书报社出版追求学会丛书:《穆斯林的祈祷》《和平的宗教》《穆罕默德》(前三本书系穆罕默德·阿里著,追求学会的会员翻译)、《问答》(曼祖勒·义洛赫著,追求学会会员译)、《追求中的真宰》(傅统先)、《追求中的伊斯兰教》(作者也许是追求学会会员)、《至圣先知言行录》(嘉玛鲁丁著,周沛华、汤伟烈译)。出版了汉译的伊斯兰经典,如铁铮译的《汉译古兰经》,陈克礼编译的《圣训经》,王静斋译著的《真境花园》等。此外,书报社还代销国外进口的精装阿文《古兰经》。 值得注意的是,书报社还影印了一些伊斯兰教招贴画、经字画、海报、日历等,比如“小历”“封、开斋节时刻表”“五时定刻表”“开尔白图”“阿里巴巴仙剑图”“奴海船图”“避难洞”“炉瓶三设”“海水赞圣”“清真书目一览表”等,还有独具特色的阿文经字书法中堂和对联等。 以上各种书籍在改革开放后为民间翻印和影印,而北平清真书报社刊印的老版本书册今天在一些旧书店的网上被列为稀有资料,出售标价高达数千元。 自明末清初到民国时期,先后相继涌现出很多回族穆斯林学者,他们将有关伊斯兰文化的古籍进行了整理和编译,流传至今,成就极大,在保存宗教文化方面功不可没。他们著作译述的问世得益于一些出版者、刻印社或清真寺支持和赞助。这些出版团体中的佼佼者如江苏镇江山巷清真寺长年刻经印书、余昭文(字海亭)在成都创办的宝真堂及其子余泽洲后来与人合办的爱伯书局、马魁麟创办的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唐柯三和马松亭创办的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买俊三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回教书局、达静轩在上海创办的穆民经书社、云南昆明南城清真寺教长沙平安成立的天方书局,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的清真寺也参与翻印和出版活动。它们印制和出版了不少中阿文的经堂教育课本和伊斯兰教典籍、学术著作、译著、学术刊物等。 在以上民间的中国穆斯林出版社中,北平清真书报社是历史最长、影响最深、规模堪称最大的一家,北平清真书报社在印刷复制和整理中国伊斯兰古籍、译著中起到的继承和传播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尹伯清评价书报社总经理马魁麟时说:“自印暨转贩之书,岁以万卷计,行销遍于各地。因之而明晓教义者,又不知若干人也。阿衡弘扬圣教,霈溉后学之功之效,可不谓大且溥耶?”[2]运子薇则认为,清真书报社的出现“是回回民众自发的民间出版机构,它带着淳朴、务实的大众本色登上历史舞台,是回回民族时代觉悟的具体体现,也是回回民族追求文明自强的精神代表……它是早期回族文化出版事业的一颗耀眼明珠”[7]。 回首历史,“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政治大浩劫将历史文物尤其是宗教文化出版物包括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印刷的许多典籍、招贴画、经字画、阿文对联等资料在中华大地上摧毁殆尽,要想寻找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真是艰难啊!未曾想到的是,毕敬士,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却将书报社在民国时期出版刊印的伊斯兰教资料中的许多保存了下来。它们被珍藏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有十函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的中阿典籍)和阿瑟·萨克勒博物馆里(有数十张牛街清真书报社印制的经字画、招贴画等)。如果已故的马魁麟及其后人得知他们创立的书报社所印刷和出版的许多书籍和经字画等被完好地保留下来的话,他们一定感到无比欣慰。 我们现在将这一段令人垂泪的历史故事挖掘出来,不仅重温中国伊斯兰文化自觉运动的历史,而且亦是见证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对话和交流。马魁麟和毕敬士也许从未谋面(可能通过书信,因为毕敬士收集这些书籍、经字画和招贴画等肯定要写信并汇寄邮资和定单到北京,而马魁麟及马中道、马光道也不时将目录和书籍资料寄给在汉口的毕敬士),但坚贞的信仰却将这两个素不相识的宗教教职人员的心灵联结起来,他们虽然远隔大洋、相隔半世纪,却在保存文化精品这个愿望方面是心心相印的。这些典籍、彩色经字画、阿文对联和海报的问世及重新介绍表明了马魁麟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实践者、引领者、弘扬者、宣传者和捍卫者;而这些回族文化精品能够历经七八十年而在世界另一个角落里幸存下来,也间接证明毕敬士是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忠实采集者、观察者、记录者、保存者和研究者。优秀文化具有跨越种族、跨越地域、跨越信仰、跨越思想藩篱和政治界限的生生不息之力量。它见之于中国社会及其培育的中国文化具有包容不同宗教文化的宽广胸怀和博大精神。就是凭着这股坚韧精神,我们祖国历经沧桑和艰辛而在七八十年之后建设了一个文明和谐社会,并将国力提高到世界前列。无数代中国穆斯林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把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融会贯通而形成的传统中国伊斯兰文化是抵御宗教极端思潮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