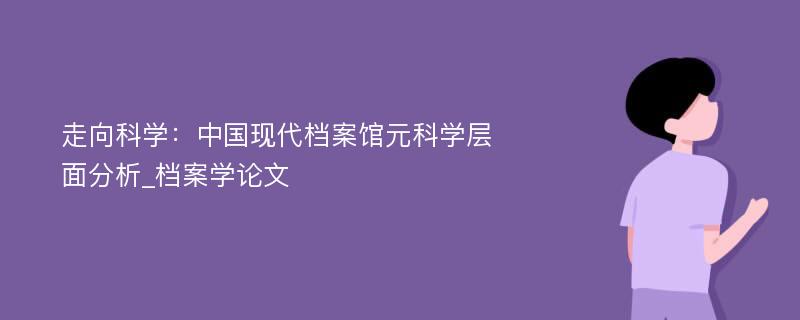
走向科学——中国现代档案学元科学层面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中国论文,层面论文,走向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科学学的观点,任何一门学科的演化要经过四大阶段,即准科学——前科学——常规科学——后科学。如果说准科学和前科学是科学的胚胎和幼年,那么,常规科学和后科学是科学的成年和老年。
中国档案学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就档案学自身研究而言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前十几年可以说是一个空白,直至80年代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共识才达成。
然而,随着信息社会的出现,档案学仍处于前科学时期。因为在前科学时期,种种“理论”的争论谁也不能取代谁,科学呈“多重态”形式。只有待“多重态”式消失,达成统一认识,或达到只有两家共处的局面,前科学时期才结束。“相对统一的认识,就意味着科学规范的形成,而科学规范的形成乃是常规科学的标志。”目前,档案学对本学科的学科对象、逻辑起点、研究领域、体系结构、学科性质、类型、归属、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也未达成共识,不过它正日益“临近向常规科学转化的界点。”因此,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展望:在21世纪,档案学将由前科学阶段迈向常规科学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出现,档案专业领域受到了冲击,档案学理论研究也受到了挑战。因此,要使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档案学由前科学阶段顺利迈向常规科学阶段,加强档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提高其理论学术水平,显得极为重要。笔者以为加强其元科学层面的研究,是从整体上提高的有效途径。
元科学简介
元科学(metascince)是“广义上的‘科学的科学’”。科学的科学,如同历史的历史一样,是一门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二次科学,它以科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从整体上对科学自身进行全面研究的一种科学理论,其“研究所包括的范围,大大超出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局限,它要包括从历史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研究科学的内容”。
由于“科学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知识体系,研究科学的进步必然要研究理论发展的机制,它的产生和消亡、结构和方法,这就是理论的理论——‘元理论’”。对某一具体科学的元理论研究,首先是从西方国家兴起的,并形成了一个相对于各具体学科研究的特殊的元理论(元科学理论)家族。它们对原学科进行鸟瞰式的整体审视和批判,推动原学科的前进。
档案学原科学层面研究情况的回顾和分析
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档案学,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可划分两大时期,三个不同的阶段。从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全面进步的新时期,促成了中国档案学前所未有的繁荣,开创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新时期——发展期,这个时期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繁荣阶段(1978.12--1992.10)和转型阶段(或纵深阶段,1992.10以后)。纵观档案学的兴起、发展和深入的各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
在档案学的创建阶段,学科研究刚刚起步,但就档案学自身问题的研究而言,1949年10月共和国成立以前可以说是空白。那时的档案学研究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与行政效率和历史研究的需要密切相关的档案实际工作问题上,而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体系、研究方法、学科历史似乎被排除在研究之外,如吴宝康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档案学问题》一文中,对档案学自身的研究对象作过阐述,其表述是不全面的,仍将档案学排除在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之外。因此,这一时期对档案学元科学层面的分析几乎处于空白。
在档案学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共识已最终达成。高校档案教育也获得了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学工作者开始加入档案学深层次理论研究的队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电子档案的出现,使档案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促进研究者们重新审视档案学。这一时期,档案学教材大量涌现,档案杂志数量也猛增。档案学研究的全面铺开,使不少学者开始对档案学自身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如吴宝康先生1986年出版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和后来出版的几个版本的《档案学概论》都大大增加了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再把档案学简单地等同于档案工作的经验总结,从而开始了从元科学的高度把档案学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加以整体系统地考察研究。总的来说,新中国的档案学在其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研究具体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较多,但对自身问题的思虑极少。
近几年来,档案学的研究向纵深推进,进入深入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即有关学者认定的临近常规科学界点的阶段。此时研究者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加强学科自身的理论研究,才能突破档案学的前科学阶段,从而跻身常规科学之列。人们开始把档案学置身于科学演进的大文化背景下,对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历史的、哲学的和具有社会意义的综合阐述。与前一时期相比,这种研究显得更为自觉和深入。如吴宝康先生在1986年出版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档案学自身理论和历史问题的专著;寒江的《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湖北档案1988年第6期》)、任遵圣的《试论档案学的科学性质》(《档案与建设》1988年第1期)、吴宝康的《关于我国档案学科学体系的基本思考》、王李苏、周毅的《回顾与展望》等文章,都开始从更高的视点对档案学进行定位,但也不无局限性。
档案学元科学层面分析研究的意义
在对档案学元科学层面的研究作了简单回顾和分析之后,笔者认为,要推动档案学进一步快速发展和步入常规科学阶段,用元科学理论全面系统地对档案学进行自身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1.它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点。长期以来,不少档案学研究者因自身的研究兴趣、学识水平、所处环境、资料条件以及能利用的时间、精力因素的制约,往往将研究的视野局限在档案学的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应用理论上),陷身其中不能自拔(当然,这种研究也是需要的),从而影响了档案学的整体理论建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元科学理论则可以使我们摆脱“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能够从更高的高度去鸟瞰整个档案学,可以帮助我们开拓视野,发现档案学研究中原被忽视的许多问题,如档案学在整个学科之林中的地位与功能、与社会诸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关系,档案学的整体发展(迁移)的步向,档案学科学研究的组织管理及研究队伍的智力结构等。
2.它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元科学理论对档案学的研究者来说,不仅开拓了研究视野,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从整体系统的角度去研究档案学自身。这种整体系统的分析与综合,不仅仅大大拓展了研究者思维能力的状态空间,有效地深化了思维方式变革程度,而且有助于反整体上对档案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探索整个档案学的发展规律。如研究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把档案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考察,着重研究整个学科体系内外联系,并注意联系的等级和层次,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分支学科的内在关系,找出档案学发展的规律,从而指导人们制定发展档案学的战略和策略。当然,元科学理论也能促使档案学与许多相关学科的相互渗透,有利于对各学科研究方法的沟通和借鉴,扩大档案学的开放度,使其触角纵横延伸。
3.它有助于培养形成一支高素质的档案学研究队伍。由于要对档案学进行元科学层面的研究,牵涉到许多学科的知识(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逻辑学、文化学、科学学、系统学、心理学、经济学乃至数学等),因此要求档案学研究者具有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开创性的思维,从而有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高品位的研究队伍,为深入研究档案学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
总之,元科学理论为我们从高层次的战略意义上探索档案学的整体理论、发展规律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这一点已从元科学理论在其它学科中的推广应用中得到证实)。尽管我们现在用元科学理论来构建一门“元档案学”还为时过早,但元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反思”科学活动,对档案学自身进行整体上的探索研究,实现档案学自我认识系统化、理论化还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现在已到了有意识地、更为自觉主动地、系统完整地研究档案学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