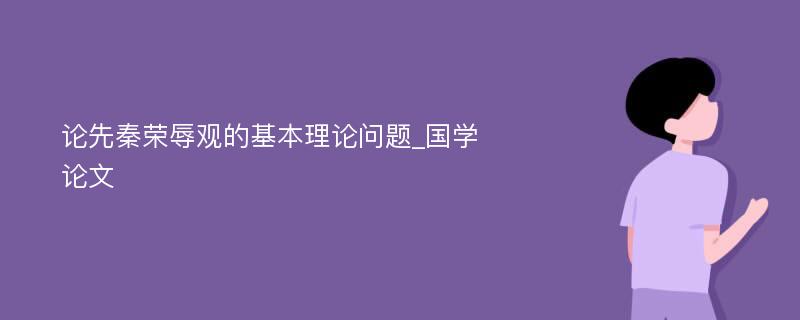
论先秦荣辱观念的基本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荣辱论文,基本理论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1)03-0072-06
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于荣辱观念的诸多基本理论问题做了深刻的、多方位的伦理思考,主要包括荣辱的人性根源、荣辱与德性的关系、荣辱与经济的关系、荣辱与教育的关系、荣与辱的关系等。主导的、带有倾向性的观念主要有,“好荣恶辱”是人内在的自然性情,德性是荣辱评价的内在基础,言行是荣辱评价的外在根据,教育是“衣食足”与“知荣辱”的必要中介,同时还要注重探讨荣与辱的内在关联,以求“辩乎荣辱之竟”。
一、荣辱与人性:“好荣恶辱”是人的自然性情
追求荣誉、避免耻辱是人的自然性情,是人之常情。在权力、财富、才智、道德、声誉等方面达到理想的高度,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赞许,是人生追求的重要目;同时,人们又在尽力避免被否定、被责备、被羞辱的境地。
儒家对于人的“好荣恶辱”本性表示高度的认同。一方面,关于对荣誉的追求,《左传》里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衰,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人们希望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追求不朽的声誉。孔子认为人都希望有好的名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关于避免耻辱,儒家强调“愧耻”、“有耻”、“羞恶之心”,重在通过发掘、培育人的知耻之心,以达到良好社会秩序的实现。《尚书》里讲,“其心愧耻,若挞于市”(《尚书·说命下》)孟子认为,人都有“羞恶之心”,这是一种人性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外部力量强加于人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追求荣誉、避免耻辱是人的自然性情在荀子那里被表述为“好荣恶辱”,荀子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荀子·荣辱》)他认为:“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小人则日徼其所恶。”(《荀子·儒效》)
法家深谙人的“求荣避辱”的本性,强调把明确的、严格的赏罚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和统御人才的工具。“求荣避辱”的本性来自人的自利本能,如造车的人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人盼望人夭亡,父母“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韩非子·六反》),无不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算计。李泽厚对此评论说,韩非主张的是一种极端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韩非把一切都浸入冷冰冰的利害关系的计量中,把社会的一切秩序、价值、关系,人们的一切行为、思想、观念以至情感本身,都还原为归结为冷酷的个人利害。它成了衡量、考察、估计一切的尺度标准。”①关于人的“求荣避辱”的本性,商鞅作这样的描述:“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商君书·算也》)。商鞅还说:“民之生,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也》)。商鞅主张,“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商君书·君臣》)韩非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韩非子·八经》)
道家并不完全否认人具有“好荣恶辱”的本性,也在讲避辱,如“知足不辱”(《道德经·四十四章》)。但是,总体上说,道家并不看重、不强调这种本性。根据张岱年的观点,道家的人性论是一种“无善无恶论”,或者说是一种“性超善恶论”,“道家只教人顺性自然,无知无识的生活下去。”②道家认为儒家的荣辱观念已经走上邪路,是舍本求末。人应该顺应“道”的要求,自然无为,守辱处下,不慕虚荣,不争虚名,超越世俗的荣辱观念,保全生命才是人生的根本。
《吕氏春秋》认为“欲荣而恶辱”是人的性情。“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吕氏春秋·适音》)。“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吕氏春秋·适音》)
二、荣辱与德性:仁义是荣辱评价的德性基础
“好荣恶辱”的人性只是人的自然倾向,是一种可能性。在儒家看来,实现这一可能性的基础是德性,德性是荣辱评价的基础,而人的最基本的德性就是仁义。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孟子说,“仁者荣,不仁者辱。”(《孟子·公孙丑上》)
荣辱评价既包括来自外部的组织、他人的评价,也包括来自个人内心的自省式的道德评价,二者之中,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是荣辱评价的根本和主导。荀子认为荣辱有“两端”,即荣辱可以分为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内在的荣辱即“义荣”、“义辱”,外在的荣辱即“势荣”、“势辱”。他说:“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志意惰,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孰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荣。流淫污侵,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藉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辱”(《荀子·正论》)荀子主张做君子就要追求“义荣”,注重自身内在的意志、品德和智慧;同时不能有“义辱”,不能贪婪、淫邪、无礼、傲慢。“势荣”是指来自外部的功名利禄,“势辱”是指外在力量对于个人的身心打击。“义荣”、“义辱”完全可以由个人的修养和意志所能把握和决定,而“势荣”、“势辱”不是完全由个人的修养和意志所能把握和决定的。君子应当以“义荣”为荣,以“义辱”为耻;而不必以“势荣”为荣,以“势辱”为耻。正因为此,“义荣”、“义辱”应当作为个人进行自我荣辱评价的德性基础。对人的荣辱评价不能根据外在的“势荣”、“势辱”,而应根据内在的“义荣”、“义辱”。
《论语》中孔子对身陷囹圄的公冶长的评价正是暗合了荀子“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荀子·正论》)的观点。孔子谈到公冶长时说:“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论语·公冶长》)朱熹解释说:“长之为人无所考,而夫子称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虽尝陷于缧绁之中,而非其罪,则固无害于可妻也。夫有罪无罪,在我而已,岂以自外至者为荣辱哉?”(《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三》)也就是说,孔子主张荣辱感从根本上是取决于个人品质的,公冶长虽在牢狱之中,但他是无罪的,自己不必感到耻辱,他人也不应做对他耻辱评价。用荀子的观点来评价的话,公冶长有“势辱”但无“义辱”。
荀子关于“义荣”、“势荣”的区分,明显是受到了孟子区分“天爵”与“人爵”的启示。“爵”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荣誉、一种奖赏、一种高度。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天爵”是“仁义忠信”的产物,与“义荣”相对应;“人爵”是政治权位的象征,与“势荣”相对应。冯友兰说:“天爵都是在价值世界里才能够达到的境界,至于人爵都是人类世界里纯属世俗的概念。”③孟子强调不能舍本求末,不能舍“天爵”而求“人爵”,应当通过修“天爵”来得到“人爵”,更不能得了“人爵”而抛弃“天爵”。
管子认为内在修养与外在名誉是“里”与“表”的关系,内在修养是外在名誉的基础,外在名誉是内在修养的自然表征。“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修行谨敬,则尊显附矣。中无情实,则名声恶矣。修行慢易,则污辱生矣。故曰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④
儒家把仁义作为荣辱评价的德性基础,这一主张并不是被普遍接受的,它受到主要挑战来自道家的自然主义和法家的利己主义。在道家看来,儒家讲的仁义、孝慈、礼仪等是虚伪的,是“大道废弃”、“六亲不和”的产物。“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三十八章》)”仁义因而不能作为荣辱评价的依据。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主张赤裸裸的、极端的利己主义,认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利益而不是道德,不能根据仁义来做荣辱评价,“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韩非子·五蠹》)。依照韩非的国家主义或君主专制主义,荣辱评价的根据在于是否符合君主的政治统治意志,即君主依照人的求荣避辱的本性,把荣辱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对于能够给君主和国家带来利益的行为就大力奖赏,反之就严惩不贷。
三、荣辱与言行:言行是荣辱评价的外在根据
人的内在品质必然会通过自己的言语、举止、作为等表现出来,个人言行的方式、言行的结果便成为荣辱评价的外在依据。“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韩非子·大体》)。“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孟子·离娄上》)
荀子认为君子与小人在“材、性、知、能”方面没有什么差别,都“好荣恶辱”,都“好利恶害”,其差别在于求荣、求利的行为方式,君子的荣誉是行善而得到的奖赏,小人的恶名是作恶的自然报应。他主张:“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小人则日徼其所恶”(《荀子·儒效》)。他还说:“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是故穷则不隐,通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荀子·荣辱》)
人们既然非常在意社会自己的荣辱评价,那就要时刻注重自己的言行,要慎言慎行,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实”(《论语·宪问》),“古者言之不出,耻躬行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周易》里说:“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周易·系辞上》)。这就是说,人是通过言行来“参天地之化育”的,言语能够招来祸患,行动能够引来耻辱,君子的言行因而不能是轻率的和随意的;言行对君子来说就如“枢机”,言语一旦讲出,行动一旦做出,必然导致荣或辱的结果。
墨家认为荣辱的获得依靠洁身修行,“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墨子·修身》)“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也”(《墨子·修身》)。墨家“尚力”而“非命”,主张“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贵,不强必贱”(《墨子·非命下》),把荣辱建立于实现国富民强、长治久安的积极作为和现实功利之上。
管子强调“荣辱在为”,要致力于“为善”,而不要“为不善”,行恶是不可能求到美名的。他说:“先王重荣辱,荣辱在为,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故先王重为”(《管子·枢言》)。他还说:“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管子·大体》)
四、荣辱与社会:财富的充裕与教育的介入
荣辱感不仅与人性有关,也不仅与个人的修养和言行有关,还需要适当的社会外在环境。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财富的充裕和教育的介入。
个人尊严与荣辱感的建立需要以较为充裕的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作为基础。管子认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管子·牧民》)。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上讲,“衣食足则知荣辱”是有其经验上的合理性的。“衣食足”为“知荣辱”创造了充裕的财富基础。如果物质财富极度匮乏,饥寒交迫,就会陷于野蛮的、无序的“丛林社会”境地,无暇顾及荣辱。俗语讲“人穷志短”、“笑贫不笑娼”、“穷山恶水出刁民”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孟子讲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也说明这个道理。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论证的逻辑是,国家治理要“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财富充裕之后,民众就不必担心“养生丧死”的担忧,理想的“王道”治理秩序就有望实现。相反,“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
但是,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讲,尤其是从个人德性修养的意义上讲,“衣食足”、“有恒产”并不是“知荣辱”、“有恒心”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衣食足”不一定会产生“知荣辱”的结果,如“为富不仁”、“饱暖思淫欲”就是证明。同时,“衣食不足”不一定会导致“不知荣辱”的局面,如孔子称赞学生颜回能够超越贫穷的困扰,一心向学,致力求仁。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就属于孟子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孟子·梁惠王上》),这样的知识分子具有超越精神,不以“恶衣恶食”(《论语·里仁》)为耻,虽然“仓廪不实”、“衣食不足”,但也能够做到“知礼节”和“知荣辱”。
在孔子的思想中,“衣食足”不会自然导致“知荣辱”,“衣食足”与“知荣辱”应该有个中介,此中介就是教育。《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正因为教育的重要性,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才兴办私学,有教无类,广收门徒,并且因材施教,一直诲人不倦。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观点与孔子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主张在“制民之产”的同时,还要有“庠序之教”的跟进,使民众懂得“孝悌之义”。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五、“辩乎荣辱之竟”:荣辱相因与对荣辱的超越
相对于儒家、法家等学派而言,在荣辱观念上最为特殊、在行动上最为特立独行的是道家。道家以道为贵,拒绝虚荣,崇尚自然、无为,主张处下、“守辱”,不以功名为荣。道家深刻地洞察到荣与辱的相互依存于相互转换,并努力实现对于荣辱的超越。
道家荣辱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方面:第一,从核心观念而言,与儒家“以仁为荣”的主张不同,道家的主张是“以道为贵”,遵“道”而行。在老子看来,“道”为本原,为“万物之奥”(《道德经·六十二章》),“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德经·五十一章》)。第二,根据“道”的原则,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老子说:“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第三,知荣而守辱,以贱为本。“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道德经·二十八章》)。即深知荣宠,却甘守其辱,做到虚怀若谷,常德不离。老子说,王侯之所以自称“孤”、“寡”,是因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道德经·三十九章》)。“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详,是谓天下王。”(《道德经·七十八章》)第四,以贪婪为耻,主张知足以避辱。老子讲“知足不辱”(《道德经·四十四章》)、“知足者富”(《道德经·三十三章》)、“祸莫大于不知足”(《道德经·四十六章》),都是在强调节欲、戒贪。庄子说:“为欲富就利,故满若堵耳而不知避,且冯而不舍,可谓辱矣”(《庄子·盗跖》)。第五,戒除虚荣,不以功名为荣。老子认为“至誉不誉”(《道德经·三十九章》),即最高的荣誉是不需要夸耀的。人应该像大道那样,有功而不居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五十一章》)。杨朱认为,人生苦短,难得百年,应该从心而动,从性而游,而不要为虚名所动,“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列子卷第七·杨朱》)。
道家荣辱观念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洞悉荣与辱的辩证法。荣辱相对,二者相比较而存在,为对立的双方。“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道德经·十三章》)。同时,荣辱相因,即荣与辱相互依存,互为对方存在的根据,并且会相互转换。关于荣辱相因,根据老子的朴素辩证思维,矛盾双方相生相成,互为因果,互相转化。老子认为荣辱、福祸、善恶变幻无常,捉摸不定,难以知道其究竟,发出了“大白若辱”(《道德经·四十一章》)、“孰知其极”的感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五十八章》)更是荣辱相因、福祸转换的经典表达。
道家荣辱观念的另一基本特征是,在洞察荣辱相因、荣辱转换的辩证法的基础上,道家致力于实现对于荣辱的超越。道家与儒家都讲荣辱之别,二者“同途”而“殊归”,有着根本不同的旨趣。儒家讲荣辱是为了做到荣辱分明、求荣避辱,而道家则意在淡化差别、超越荣辱,追求超越亲疏、利害、贵贱的“玄同”境界。超越荣辱,就是视荣辱为身外之物,通过知足、无为、不争、处下等方式,做到宠辱不惊,以保全人的自然性命。张岱年认为,“道家教人不以得失祸福毁誉穷达扰心,即教人脱除名利的思想;如依此修养,可得到一种精神的解脱。”⑤老子认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道德经·十三章》)。无论受宠还是受辱,都会让人们感到惊慌失措。未得宠的时候希望得宠,得宠之后担心失宠,如此既患得又患失,结果是会伤害身体的。庄子的主张是混同是非荣辱,“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庄子·秋水》),“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这都是对于世俗荣辱的否定、混同与超越。《列子》记载了一位自称“有疾”的龙叔,他把自己的“症状”描述为“吾乡誉不以为荣,国毁不以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视人如豕;视吾如人。处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观吾之乡,如戎蛮之国。凡此众疾,爵赏不能劝,刑罚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乐不能移。固不可事国君,交亲友,御妻子,制仆隶。(《列子·仲尼》)”医者文挚“诊断”后的结论是“以圣智为疾”,不是有病,而是有“圣智”,只有具备这种“圣智”的人才能达到超越荣辱、喜忧、生死、贫富、他我、盛衰、利害的境界。
注释: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7页。
②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6页。
③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6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0页。
④《管子·形势解第六十四》。
⑤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