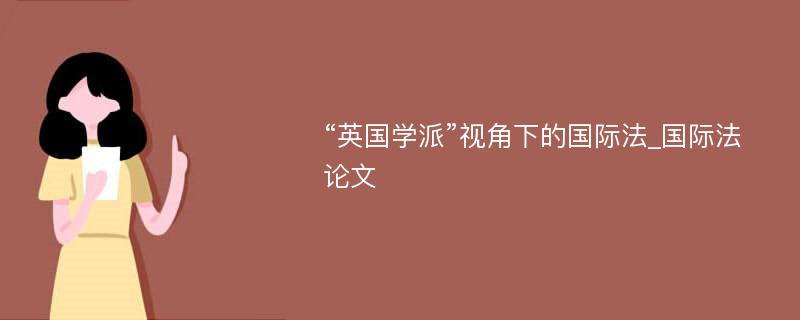
“英国学派”视野下的国际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英国论文,学派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英国学派”的崛起: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的有限联结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紧密,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相辅相成,这些特性决定了两个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结。一方面,描述、解释、研究、估价和预测国际关系的现状与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同时代的国际法之盛衰具有重要的影响或解释功能。另一方面,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国际法的研究比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更为久远与成熟。实际上,将近三百多年来,通过国际法的视角审视国际现象是学者们的普遍做法,即使是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仍被普遍使用。①早期的国际关系著作充斥着对国际法理论研究成果与方法的借鉴,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从法学研究中脱胎而出。②
直至二战后,现实主义理论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国际关系的研究突然变得与国际法学疏远。③与理想主义者崇尚法律与道德的作用不同的是,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是一切政治的基础,追求权力是每个国家参与国际关系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没有实力的国际关系是空想的国际关系,靠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来实现的国际和平只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客观上讲,由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强势以及在二战后得到实务界的重视,其对国际法作用与独立性的贬低或否认立场,不仅严重影响到国际法在二战后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地位,而且导致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法研究的普遍忽视。“现实主义者有关国家在关键的国家利益领域不受法律所限制以及国际法不属于政治现实的一部分的观点,使国际关系学者缺乏研究国际法的动力。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研究国际法的国际关系学者非常少。”④不过,有关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研究脱钩现象主要描述的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状况。这一时期,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甚至掀起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即行为主义革命。但同一时期“英国学派”的研究命题与方法却是独树一帜的。这个二战后在英国逐渐衍生发展起来的一支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仍然维系着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的紧密关系。
实际上,无论是英国学派在研究命题上以“国际社会”为核心,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对法律等传统方法的青睐,都决定了该学派的研究脉络与国际法的紧密关系。一方面,在研究命题上,英国学派把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劳秀斯(Hugo Grotius)作为自己的思想先驱,并根据国家关系的发展对格劳秀斯的国际社会概念与国际法思想做出了发展性的诠释。格劳秀斯认为虽然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的政府,但可以存在秩序,即这是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并且,国际法是维持这个国际社会秩序的重要条件。英国学派的学者也像格劳秀斯一样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征,并将这个特征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主要出发点,致力于研究国际社会形成的条件和克服无政府状态、建立国际秩序的机制。同时,英国学派在讨论建立有序国际社会的时候,十分强调的一点是国际法在维护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国家通过国际法实现国际社会的可能。虽然他们也认为共同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条件。但是他们首先认为国际法、国际惯例、国际制度是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⑤当然,英国学派并非格劳秀斯主义的“正统派”或“原教旨派”,而是其“修正派”。它倚重的是经过重新解读、局部改造和重要补充的格劳秀斯理性主义传统,将“国际社会”以及国际法命题的研究推至更高境地。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英国学派的学者广泛使用了被称为“起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具有明显依靠运用判断的特征”⑥的传统方法,国际法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经常被他们娴熟运用。而且,英国学派的学者并不仅限于把国际法当成他们论述国际关系命题时的论证材料,而是经常开展对国际法的直接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国际法学向前发展,有许多论述对国际法学者是具有启发性意义的。
无疑,在当时美国同行普遍忽视国际法的研究并热衷于“科学行为主义”提倡的方法论之情境下,英国学派的这种做法以及研究成果对于这时被现实主义忽视或贬低的国际法,其蕴含意义是深远的,直至今日仍然发挥出重大影响。而从英国学派的学者有关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的研究中寻找到某种启示与帮助,也是国际法研究中的一个有用的途径。考虑到英国学派队伍庞大、著述丰厚、思想深邃,在有限的篇幅与能力的情况下,我们有选择其代表人物的相关研究作为切入点的必要性。鉴于此,本文围绕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与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研究而展开论述。
二 英国学派对国际法的“法律地位”与性质的分析
既不满于国际法的“虚无主义”之立场,也不满于卡尔、摩根索等现实主义者将国际法看成是一种存在重大缺陷与原始类型的法律之观点,英国学派的学者重新解释了国际法的法律地位、性质、作用,以及发展趋势等。
(一)英国学派对国际法的“法律地位”的分析
国际法的法律地位与性质是一个休戚相关的问题,只有在肯定国际法是“法”的地位后,具有“法律地位”的国际法才涉及到判定其法律性质的问题。
从学术发展史上看,有关国际法的法律地位的观点颇多,既包括类似于奥斯汀(John Austin)的“国际法只是一种具有积极作用的国际道德”的观点,也包括诸如凯尔森(Hans Kelsen)提出的有关“国际法实际上是一种依赖于非集中制裁的‘强制性命令’”的观点,以及有从哈特(H.L.A.Hart)把基本规则与次要规则相结合的法学思想出发,将国际法与制裁分开从而肯定国际法的法律地位的做法。⑦对于这些观点,以怀特与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学者做出了各种分析,并最后得出肯定国际法具有法律地位的结论。例如,怀特认为,国际法是确确实实存在于国际体系中的法律,其也是国际社会存在的最基本证据,即:“国际社会存在的最基本证据是国际法的存在。每一个社会都有法律,这是规定其成员权利与义务的法规体系。因此,那些否认国际社会存在的人往往从否认国际法的现实开始。他们说国际法不是‘真正的’法律(因为他们界定‘法律’的方式排除国际法),要不然则认为国际法是在实践中一直被国家置若罔闻的抽象的东西。另一方面,那些认为国际社会正在稳步发展为类似国内社会的人将国际法看做一种‘原始’法律,正逐步变得像国家内部的法律一样。但在这个问题上,前者还是忽视了证据,后者也还是夸大了证据以迎合各自的主观臆想。国际法是一种特殊的法律,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划分为许多主权国家的社会的法律。”⑧
同时,布尔也经过对历史上有关国际法的法律地位的各位观点进行详细的分析后,得出了国际法具有法律地位的结论。对此,他写到:“那些否认国际法具有法律地位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法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它同国内法的区别(类似于原始社会的法律)。然而,把国际法视为‘法律’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有关该问题的争论并非是无用的或者无意义的。国际法作为行为惯例,事实上同国内法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的语言和程序是很相似的。现代法律既包括国际法,也包括国内法。那些关注国际公法以及国际私法的行为体,即政治家及其幕僚、国内和国际法庭以及国际会议,都承认国际法规则就是法律规则,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基础。假如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仅仅具有道义或礼仪的地位,那么这些行为体的所有行为都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国际法规则具有法律地位(尽管这在理论上可能还有问题),才使国际行为的主体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⑨布尔进一步指出,无论理论上的证明有多大障碍,确信国际法律规则的法律身份的事实,使得在国际社会的运行中各种国际法律制度扮演着不同的重要角色。⑩换句话说,国际行为体不仅称呼这种规则为法律,也把它们当成一种法律而行动。因此,虽然国际法律规则由一种与国内法完全不同的方式创造,但它们仍然是被国际系统中的权威决策者当作法律而构建的,即“法律的存在并不是依靠强制力,也不是依靠物质力量的使用,虽然在理解人们根据法律规则而行动时,权力与制裁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11)
显然,以怀特、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学者肯定了国际法的法律地位,并肯定作为“法律”的国际法是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以及被广泛的应用的,即使将其与国内法相比,也能找到很多共同的“法律”特征。这种立场不管是与国际法是否为“法”的怀疑论者相比,还是与摩根索所论证的国际法只是一种“初级”或“原始”的法律观相比,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更为可贵的是,当理性主义国际法学者拘泥于国际法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制裁等强制力量来论证国际法是否为“法”的问题时,布尔已经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国际法为什么是“法”的答案,即因为在观念上国际行为体认同它是“法”,以及国际法的强制力量不在于制裁而是其本身的“合法性”这种观点,这实际上已经超越国际法是否为“法”以及强制力来源问题的论辩,对于国际法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启示。
(二)英国学派对国际法性质的分析
英国学派对格劳秀斯主义的“重新解读、局部改造及重要补充”,也体现在格劳秀斯主义的国际法性质方面。虽然格劳秀斯主义也承认实在法构成国际法的渊源之一,但更强调自然法渊源,即认为自然法是国际法的最基本的渊源。也被其称作为“万国法”的自然法是什么?就是最普遍、最基本的人类道德原则,是人类理性的结晶,是最基本权利概念的具体表现。无论是国际社会的和平,还是秩序或正义,都有赖于这种法则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同时,无论是格劳秀斯主义还是新格劳秀斯主义(Neo-Grotianism),它们根深蒂固的偏好是试图规避主权同意这种必要条件而寻求国际法的新的渊源,试图将国际法的主题往超越国家以及促进正义的方面延展。(12)相反,英国学派的学者,包括怀特、布尔、文森特(John Vincent),在国际法性质的认定上,既保留了诸如“正义”、“公平”、“秩序”等格劳秀斯主义的自然法学说的各种“要素”,同时也吸收了为实证主义国际法学所界定的国际法“现实形状”。
例如,怀特在《权力政治》一书中指出,国际法是一种特殊的法律,是一个在政治上被划分为许多主权国家的社会的法律。它的主体是国家,不是个人;它是国家通过条约、默认的惯例和习俗,来界定交往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体系;除国家外,它没有实施法律的代理机构,也没有行使强制管辖权的司法机构。(13)可见,怀特所描述的国际法的“外在形状”基本上与实证主义国际法学的描述是一致的。如果说怀特在解释“国际条约为什么能够得到遵守”的问题方面尚赞成除功利主义的解释角度外,还存在着一个古老与抽象的答案,即与正义标准相一致的伦理规范,那布尔甚至连这一点自然法渊源都已是不保留。(14)即对于格劳秀斯有关国际法的基本渊源为自然法的界定以及将法律与道德看成具有同等意义的核心规范的观点,布尔是持否定态度的。
一方面,布尔完全赞同实证主义的界定,认为国际法渊源主要是实证法,其效力基础来自国家的明示或默示的同意,其只能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用他的话讲,即“国际法可以被看做是对涉及政治中的国家及其他行为体在它们彼此交往中具有约束力和法律地位的一组规则。……从国际法规则事实上影响着世界政治行为这个意义说,国际法规则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15)另一方面,布尔接受了奥本海有关国际法学者可以归类为自然法学者、实证法学者以及主要关注自然法并稍微兼顾实证法的“格劳秀斯学派”的三分法。正如奥本海做出这种划分是期待实证主义走向繁荣的寓意,布尔也接受了实证主义的大量观点,尤其是吸收了哈特的基本思想,包括法律与道德必须分离的核心观点。虽然布尔自身没有去论证法律与道德为什么必须分离的观点,但他主张必须把法律与政治主张,以及法律事实与社会价值相分离,即法律必须与其他非法律因素相分离,法律与道德有着界限分明的分野。国际法学者的主要工作应该是解释现存法律规则,如果他们把时间与精力大把的花在伦理、社会学等问题上,结果只能是国际法的角色在国际关系中日益走向衰微。(16)
英国学派对自然法传统的继承更多地表现为布尔所说的某种“经验性翻版”,“他们继承了格劳秀斯作品中的核心思想,但又与格劳秀斯传统以及新格劳秀斯主义保持距离,因为他们的真正兴趣在于面对现实的国际关系”。(17)从国际社会的实践看,英国学派这种结合实证主义的观点对格劳秀斯主义自然法倾向的基点进行修正,从而得出他们自己的对现代国际法性质的判断,更加符合当代国际社会的实践。究其原因,“布尔等人看到的国际体系现状是广阔与多元的国际社会,已经是远离格劳秀斯当年所能理解的世界。面对道德怀疑论者的质疑,他们已经无法全然接受格劳秀斯的自然法观点以及道德的作用”。(18)当然,他们仍然吸收了格劳秀斯主义有关自然法的关键要素,即给国际法赋予了自然主义特有的“正义”、“公平”、“秩序”等人文精神,从而使得国际法摆脱纯粹实证主义所给予它的机械性的规则定义。通过此,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的国际法思想与哈特的“自然法的最小内容”的思想已是非常接近,而这种思想实际上成为布尔在《无政府社会》中所阐述的世界政治理论的基础。
三 英国学派对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诠释
一旦认定国际法是一种原始的、软弱无力以及依附权力的法律,那自然它们在国际政治中的存在并不一定是必要的,外交事务依赖“法制主义——道德主义途径”(Legalistic-Moralistic Approach)以及安全事务方面的集体安全机制完全不可行——这就是现实主义者的立场。(19)不过,既然英国学派学者已经否定了现实主义有关国际法性质的观点,那从理论逻辑上他们肯定会对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有不同的看法。
事实正是如此,英国学派学者重新肯定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的存在以及存在的必要性。例如,马丁·怀特在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分析中写道:“无政府状态这一特点将国际政治区别于其他政治。国际政治的研究预先假定不存在政府制度,就像国内政治的研究预先假定存在政府制度一样,限定条件是必要的:存在着一个国际法体系以及国际制度,用以缓解权力政治的运作或使其复杂化。但实际情况大体是这样:在国内政治中,权力斗争受到法律和制度的支配与制约;而在国际政治中,法律和制度则受到权力斗争的支配和制约。”(20)实际上,在怀特看来,政治理论与政治现实相联系;国际政治理论,尤其是以法律术语表达的国际政治理论,要求改变而非只是理解国际政治的现实。因此,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不是无能为力或者一味屈服,而是试图或已经影响国际政治的现实。用他的话讲,即是“国际法似乎与国际政治背道而驰,如果外交领域充斥着暴力与无耻,那么国际法就会上升到自然法的领域之内;如果外交领域需要一定的合作习惯,那么国际法就在法律实证主义的泥潭中缓慢前进”。(21)
与怀特一样,布尔也将国际法存在与作用作为国际社会存在的证明。不过,在布尔的意识中,国际法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而是认为国际法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其对国际秩序的维持所起的作用。布尔认为,在建立与维护理想的国际秩序乃至更深远的世界秩序的进程中,传统外交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国际法虽然有着本身的局限性,但也发挥出很大的作用。具体包括:(22)第一,国际法的最重要的作用是把主权国家社会的观念视为人类政治组织的最高规范性文件,或者说,把这种观念成功实现法制化;第二,国际法阐述了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相互共处的基本规则,主要包括:有关限制国家和其他行为体之间暴力行为的规则;有关这些行为体之间协议的规则;有关主权和独立的规则;第三,国际法促使国际社会行为体遵守国际社会的各种规则,既包括基本的共处规则,也包括具体的合作规则,以及其他的规则。虽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国际法基本上得到了国家的遵守,但是,并不是国际法本身的限制性要求构成国家遵守国际法的主要动力,而是包括其他一些重要因素,比如有关当事方接受协议所基于的目标或价值观念,受到一个强国的惩罚,以及互惠利益等等,促使国际社会的行为体遵守国际法。同时,立足于整体主义方法论,布尔强调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不仅是对国际行为体具有约束性作用,也在于对角色的建构作用,即“包括国际法与势力均衡在内的国际制度的首要角色就是认同和维护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合法行为体,并强调国际社会作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层次的规范性原则”。(23)无疑,布尔对于国际法的建构作用之强调对于以后的建构主义观点的提出起到良好的启发意义。
更为可贵的是,布尔在肯定了国际法在创建与维持国际秩序或者说在国际社会的存在的作用与意义的同时,却没有像理想主义者一样脱离政治现实而盲目拔高国际法,而是舍弃了理想主义者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抱有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更为理性的看待国际法的作用。布尔指出,虽然国际法对于国际秩序的维持能够发挥出很大的作用,但也必需注意到国际法作用的有限性:(24)一方面,国际法并非是创建与维持国际秩序的一个必要的,或者关键的条件。从理论上讲,国际法的地位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所具有的这种功能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国际法本身并不足以产生国际秩序,除非在其他条件也是具备的情况下,国际法才能发挥作用。例如,只有国际社会本身已现买存在的前提下,国际法才能把国际社会的观念确定为最高的规范性原则并使之获得承认。因此,立足于相应的现实基础是国际法发挥作用的前提。否则,国际法本身是不能够像“以法律实现世界和平”或者“通过世界法律走向世界和平”的构想所阐明那样,成为维持秩序或者和平的工具。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英国学派学者对国际法作用的认识仍然界定在权力政治范围之内,即并不是国际法律支配或制约国际政治,而是国际政治支配或制约国际法,但他们至少是肯定了国际法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或“缓解”的作用。与现实主义相比,这无疑是对国际法作用的认识的提高。事实上,在崇尚权力政治、漠视国际法的作用的现实主义与强调理性对话,重视均势与国际法作用的格劳秀斯主义,以及反对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的看法,认定国际法可以向超国家法方向发展,并可建立国际政府与达到国际社会永久和平的康德主义之间,英国学派学者对国际法作用的认识更接近格劳秀斯主义的观点。如怀特指出,格劳秀斯主义是欧洲传统思想的最重要的主流。他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成为一个格劳秀斯主义者,同时又吸收摈弃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和不带狂热和盲信的康德主义。(25)无疑,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尤其是英国学派学者所处的超级大国紧张对峙的冷战现实看,英国学派学者对国际法作用的这种态度与期望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不仅肯定了国际法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而且指出了国际法在二战后的新的发展趋势。在对二战后国际法在包括主体、适用范围、法律制定过程以及国际法学家的作用等方面的最新发展也做出了详细分析,布尔得出如下结论:“……国际法不仅发生了变化,也有所进步:从约束国家的法律演变成了世界共同体的法律;从仅仅关注国家间共处的法律演变成为关注世界共同体中人类经济、社会和环境合作的法律;从一种无法阻止某些无法无天的国家蔑视世界共同体的法律,演变成一种使这种共识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从一种被静止地和机械地加以解释、与世界共同体观念的变化不相干的法律,演变成一种被动态地和创造性地加以解释、与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法律。”(26)同时,布尔对国际法的研究已经突破偏重国际公法领域的传统局限而向国际经济法延伸,从而实现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经济法的“间接影响”到“直接影响”的转变。(27)事实上,布尔不仅仅描述了国际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这个事实,他还总结了这种适用范围扩大的原因与意义,即“国际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经济、社会、通讯以及环境问题领域,表明国际法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增大了,因为它提供了应对国际秩序所面临的新威胁之手段。在这些领域中,一国政策对他国影响力的增大,是国家之间冲突和无序的一个根源,国际法律规则无法遏制这样的冲突。如果国际法不扩大自己的适用范围以应对这些事态的发展,那么国际秩序所面临的因经济、社会、通讯以及环境领域内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而产生的威胁就会更加严重。”(28)
四 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命题的研究与国际法学的互动
在英国学派的各种研究命题中,对“国际社会”的研究最为引人注明。国际社会的研究渊源于格劳秀斯的思想,而在英国学派中,曼宁、怀特、布尔、文森特等人都对“国际社会”进行了全面与深入的研究,并建构了一整套的有关国际社会的理论以及观点。而在对“国际社会”的研究中,英国学派学者广泛的运用了国际法的知识。同时,有关“国际社会”研究开展也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有关“国际社会”命题的研究与国际法学的作用是互动的。
(一)国际法的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存在证明
重视从传统的历史、哲学、法学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的学者在研究“国际社会”的概念时,把目光投向了国际法,并试图用现代国际法的发展来论证国际社会的存在。例如,怀特写道:“国际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的证据是国际法的存在。”(29)
虽然布尔放弃了怀特关于国际社会必须拥有共同文化纽带的论断,把它更换成共同的利益观和归属感纽带,但他仍然借鉴了从国际法的发展中寻找国际社会的存在证据的做法。布尔认为,国际社会的存在有其要素能以证明,这些要素包括: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国家遵循的共同规则以及国家所创立的共同制度之观念。按照布尔的阐释,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第一步是,国家之间必须形成一个追求社会生活基本目标的共同利益观或共同价值观念。不管这些国家所追求的具体目标是否大不相同或者互相冲突,但它们都很看重这些基本目标。不过,旨在追求社会生活基本目标的共同利益观念本身并不能明确地告诉我们,哪些行为符合这些基本目标,这必须依赖于规则。这些规则可能是国际法、道义准则、习惯或先例,也可能只是不是通过正式的协定而产生的操作规则或“游戏规则”。规则的形成往往历经这样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是操作规则,然后成为先例,接下来又变成道义规则,最后被纳入法律文件中。在国际社会中,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主权国家发挥着使规则具有效力的作样,国家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中的主要制度。它们通过认定规则、解释规则、改变规则、保护规则、使规则合法化等等推动规则的发展。国家在发挥这些作样的时候,会在不同程度上根据国际社会的制度相互进行合作。这些制度包括:均势、国际法、外交机制、大国管理体系以及战争。这些制度象征着国际社会的存在,表明国际社会不只是所有成员的总和,也说明成员之间在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时所进行的相互合作具有实质性和持久性,并且有助于成员避免忽视共同利益。(30)无疑,布尔所指的国际社会或国际秩序的三要素并不是与国际法完全等同,它们的范围比国际法要大得多。不过,它们与国际法的关系是紧密相关的。例如,共同利益可以用国际法得以发展来证明;共同规则与国际法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核心部分;制度与国际法的发展紧密相关,或者可以通过国际法的制定、修改、维持以及解释等现象反过来证明这种制度的存在。
因此,在布尔眼中,也是在整个英国学派的意识中,国际法并不能解释国际社会存在的具体原因,但它却是证明国际社会的存在的一个核心要素。(31)对于布尔的这种逻辑中,就如他的学生文森特的描述:“在布尔看来,与国际秩序紧密联系的国际法的功能并不是其本身(就像某些进步主义思想所论述的一样)能导致国际秩序的建立,而是它首先能界定出人类的政治组织即国家社会里存在的建构性原则,而后它又能推断出这些国家社会共存的基本规则,并提供一种使其正式关系得以发展的语言……对国际法的兴趣并不是体现在国际法本身为何物,而是国际法代表了什么。它为社会的存在提供了证据,但并没有提供解释社会存在的原因。对于布尔来说正是在这方面国际法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使其能像矿工使用矿灯那样挖掘出社会的方方面面:凡是存在着社会的地方就存在着法律。”(32)
客观上讲,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国际社会存在的最好证明,因为国际法的存在确实意味着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之间存在某种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规则以及共同的制度。
首先,国际法是在各国之间与各国人们之间的交往中不断形成与发展,是对它们或他们的关系的法制化,“无论是在对外交往、海洋资源的开发领域,还是在环境保护、国家管辖权的限制、外层空间的利用方面,国际规则能够不断演进皆是因为各国在这些领域存在着某种的共同利益”。(33)
其次,即使在缺乏中央政府以及强制力的情况下,国际法的共同制定并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共同遵守,本身就是在证明国家之间与各国人们之间遵循着一定的价值观念或心理特征。而在国际法的不同发展阶段,诸如人类良知、人类理性、共同法律意识以及公平、正义等观念,都成为国际法的各种理论学派论证国际法效力来源或根据的重要基础。事实上,也正因为此,强制力欠缺的国际法在大部分阶段,其基本原则与义务都得到绝大部分国家的遵守。(34)
再次,几百年来,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其效力范围从西欧旧基督教国家构成的“原始国际社会”发展到二战后的全世界。实际上,20世纪后半叶,国际法的普遍性趋向更为明显。(35)
最后,国际法的普遍性不仅表明国际法是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表明世界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新现实主义主张的纯粹物质结构状态,而是存在着“国际法律机制”或“国际法律制度”。反过来,这种国际法律机制或制度的存在表明,虽然国际社会尚处于不完善状态,但它确实是存在。(36)
(二)“国际社会”的研究为国际法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无疑,国际法是国际社会存在的证据之一,它们在维持国际社会的秩序中具有积极的功能或者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实际上,“这些规则和制度是国际社会的秩序直接产生结果的原因的一部分,它们是国际秩序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与充足条件之一”。(37)简单地讲,规则和制度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发展,使得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但有序”状态。同时,反过来讲,国际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对包括国际法在内各种规则与制度有着“需求”的必要,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的规则与制度的“供给”。因此,国际社会从原始状态走向逐渐成熟,将为国际法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国际社会与国际法之间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成正比例的曲线增长。我们通过考察当前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就可以看出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空间。
由不同国内社会之间的人们直接的连接或通过国家等工具为代理的间接连接而形成的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组成的“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相比,紧密程度存在明显差别。不过,晚近国际法与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正使这个松散的国际社会日益紧密。例如,从国际经济的视角看,晚近蓬勃兴起的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化实际上正在把原先被传统主权制度分割的国内经济的彼此联系变得日益紧密。第一,经济全球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日益使世界经济连接为一体,这不仅使“国际经济一体化”日益成型,也为广泛意义的“国际社会”的存在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这时,国家之间已不仅仅是由简单地彼此经济联系而形成国际经济体系,而且是通过不同层次的经济对话和谈判,及数目繁多,具备系统性、层次性及多元化的国际经济制度体系,建立了引导相互关系及个体与集体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共同行动准则或标准。所有成员都认识到,维持与发展这些安排是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第二,虽然世界政府或某种中央集权目前是不存在,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有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也没能得到良好实践,但是相互依赖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国际道德体系与人权理论的发展等等,在思想或价值方面,构成与国内政治中所不同的、推动全球秩序良性发展的某种权威保证。同时,随着晚近跨越国界的“新社会运动”(38)的开展,日益凸显的“跨国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也标志着国内政治经济活动与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联系日益紧密,并预示主权原则与国界划分所造成的、人为的对人类社会条块分割的鸿沟逐步走向淡化。
因此,晚近经济全球化、自由化以及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国际社会的宏观主体即国家之间以及国际社会的微观主体即私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同时,在诸如国内政治中的中央集权尚不存在的情况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正在分担政府的某些职能,这种分担使得持着相同信仰或价值观的个人跨越国界走向全球范围内的联合。实际上,“国际关系的发展,客观上来说,就是一个‘社会化’不断提高的过程,所有的国家都无法避免的卷入这一过程。”(39)无疑,国际社会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是晚近国际法以及其他因素发展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又为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强烈的“需求”,即为其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即由于国际社会缺乏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为了满足国际社会的“社会化”程度提高所产生的对国际法的需求的加剧,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的主权国家必须负起这种“供给”国际法律制度的重任。
首先,各国必须通过谈判协商,制定满足国际社会的发展的国际法律制度。在国际社会“社会化”程度不高时,各国合作所给国际社会提供的法律是“共处法”,主要包括限制世界政治中暴力的使用,有关巩固各国对其民众和领土的控制权或管辖权的行为规则以及规定国家合理的行为方式的共处规则等,但在国际社会的“社会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各国的谈判协商的重心向“发展法”转移,加强各国在经济、社会、人权、环境等方面的合作的法律将被大规模的“供给”。
其次,国际社会的“社会化”发展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这种加速度的特点意味着国际法的供给必须成规模的增长。因此,与过去相比,各国谈判协商的频率以及效率都必须得到提高,通过大量的国际会议以及国际组织使得国际社会中原已存在的各种非法律规则法制化。这样,与过去的相比,国际立法的数量以及精细程度将大大提升。而且,相应修改与更新程序也必须同时提供,从而满足国际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
再次,由于缺少一个执行机构,一直以来的国际法的执行责任落到国家自助上,包括使用武力,根据习惯规则、道义规则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力。由于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少的共识,或者它们较难做到团结一致,所以国家自己所采取的自助行为或者强制执行规则的行为,经常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何况,国家之间的实力严重不对等,小国与弱国在根据国际法维护自身权利方面亦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这种自助行为将难以满足国际社会的“社会化”提高后的需要,国际法的执行方式不得不面临着质的突变,即由自助行为转向集体的方式,例如早年由国际联盟所创造并由联合国所继承,但没能得到很好实践的集体安全模式将更有用武之地。同时,国际法的管辖也将从“自愿管辖”向“强制管辖”的模式转变,例如,WTO与GATT相比的一个最大特色在于前者的争端解决程序不仅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司法机制,而且在于取得了专家组审案的“强制管辖权”,这是对传统国际法里有关不得强迫任何国家违反其本身意志来进行诉讼的原则的重大突破,(40)也反映了国际法的适用从自愿模式到强制模式转变的趋势。
最后,国家也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承担起“保护”国际法规则得到尊重与执行的责任。国际法是国际秩序有序化与法制化的重要方式,国际法能否得到尊重与执行,实际上这种由国际法所建立与规范的国际秩序能否有效运行的证据。如果在一个法治程度相当高的国内社会里,法律的自助自足可能就能够协调自身秩序运行。在“社会化”程度远不能够与国内社会相比的国际社会中,权力政治与武力外交仍然占据相当重要,或者说最为重要的角色,国际法所维护的国际秩序远达不到自助自足的状态。但在国际社会的“社会化”的提高需要国际法所维护的国际秩序得到良性发展的背景下,需要各国加强法律以外的其他方式,如外交、斡旋、均势,甚至战争等手段维护国际法所代表的国际秩序的发展。海湾战争是冷战后第一次依靠各国军事力量对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的应用与维护。再如,近一段时期,困扰国际社会的核问题成为外交谈判与大国斡旋的焦点。2003年10月,在与英、法、德三国外长进行会谈后,伊朗宣布将中止铀浓缩项目,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框架也得到国际社会肯定,迄今已经进行多轮会谈。虽然这些行动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例举这些现象只是为了说明:在国际社会的“社会化”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主权国家提供包括外交、均势、武力等手段对国际法秩序的维护行动将进一步加强。
总之,国际法的发展是国际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证明以及必要条件,而国际社会的“社会化”提高又将为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将使国际社会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而这种提高所产生的对国际法的供给需求将使国际法的发展获取更广阔的空间。
五 余论
在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主流思想与流派的压抑下,长期以来英国学派并没有赢得相称的国际影响力。不过,是金子终究要闪光。无论是英国学派学者对国际社会的研究,还是他们的国际法思想,在历经数十年的埋没后,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受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重视。这和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形势是分不开的。一些敏锐的学者发现,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的思想不仅可以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综合提供有力的支持,其整体主义方法论以及与国际法学紧密联系的研究思路也为建构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借鉴,可以被用来抨击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因此也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热点课题之一。(41)
注释:
①Robert J.Beck,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Vander Lugt eds.,International Rules:Approaches fi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96,"Preface",p.vi.
②See J.Craig Barke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Continuum,2000,p.70.
③Robert J.Beck,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Vander Lugt eds.,International Rules: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vi.
④Ibid..
⑤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1页。
⑥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in John A.Vasuez ed.,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90,pp.83-88.
⑦Robert J.Beck,"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Prospects for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in Robert J.Beck,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Vander Lugt eds.,International Rules: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9-10.
⑧[英]马丁·怀特著,[英]赫德利·布尔、[英]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9页。
⑨[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二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⑩Hedl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p.136,Quoted from Anthony Clark Arend,"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Legal Rules",in Robert J.Beck,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Vander Lugt eds.,International Rules: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96,p.293.
(11)Jutta Brunnee and Stephen J.Teope,"Internation Law and Constructivism:Elements of an Interaction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Vol.39,2000,p.65.
(12)Benedict Kingsbury,"A Grotian Tradi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Grotius,Law,and Moral Skepticism in the Thought of Hedley Bull",Bridgeport law Review,Vol.17,Spring 1997,p.19.
(13)[英]马丁·怀特著,〔英〕赫德利·布尔、〔英〕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第68页。
(14)Benedict Kingsbury," A Grotian Tradi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Grotius,Law,and Moral Skepticism in the Thought of Hedley Bull",p.20.
(15)[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101-102页。
(16)Benedict Kingsbury,"A Grotian Tradi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Grotius,Law,and Moral Skepticism in the Thought of Hedley Bull",pp.18-19.
(17)Ibid.,p.3.
(18)Ibid..
(19)George F.Kennan,"Diplomacy in the Modem World",in Robert J.Beck,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Vander Lugt eds.,International Rules: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03-106.
(20)[英]马丁·怀特著,〔英〕赫德利·布尔、〔英〕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第63-64页。
(21)[英]马丁·怀特:“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22)[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111-112页。
(23)Kai Alderson and Andrew Hurrell eds.,Hedley Bull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37.
(24)[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113-114页。
(25)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26)[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120页。
(27)[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116页。
(28)同上书,第122页。
(29)[英]马丁·怀特著,〔英〕赫德利·布尔、〔英〕卡斯滕·霍尔布莱德编:《权力政治》,第67页。
(30)[英]赫德利·布尔著:《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53-59页。
(31)J.Craig Barke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tations,p.83.
(32)R.J.Vincent,Ord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Order and Violence :Hedley Bul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dited by J.D.B.Miller & R.J.Vincent,eds.,1990,p.54.
(33)Anthony Clark Arend,Legal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p.192.
(34)Anne-Marie Slaughter,Andrew S.Tulumello and Stepan Wood,"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 New Gene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hip",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2,1998,p.371.
(35)[英]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0页。
(36)Anthony Clark Arend,Legal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93.
(37)[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59-60页。
(38)有关“新社会运动”的详细论述,参见〔美〕约瑟夫·A·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李东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290页。
(39)朱锋:《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40)赵维田:《世贸组织(WTO)的法律制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41)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奥勒·韦弗尔:“国际思想形象:介绍人物而非范式”,〔挪威〕伊弗·B.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锋、石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9页。
标签:国际法论文; 自然法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