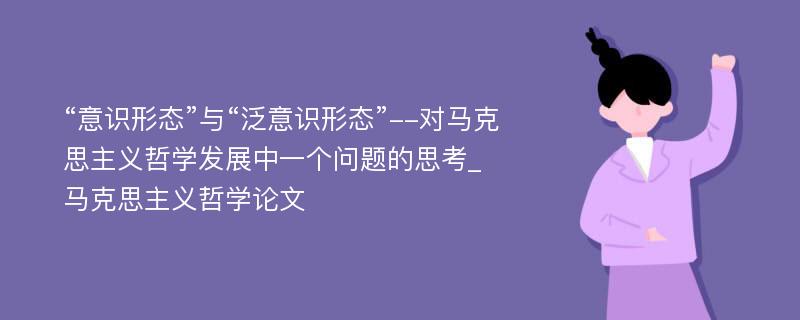
“意识形态化”与“泛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问题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一个问题论文,沉思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3)03-0004-06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过去作为非意识形态的哲学到现代作 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的重大转变,至少在共产党领导并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 义哲学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指南和支柱。
什么是“意识形态”(ideology)?尽管学术界和思想界中有许多分歧和广泛争论,但是 根据对于“意识形态”一词的最普遍的也是最流行的看法,我认为,“意识形态”是指 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或者具有统治作用的思想学说。换言之,意识形态不只是停 留在社会意识或社会思想的主观层面,它更主要的是体现为社会形态中的思想制度,正 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所指出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是在社会经济、政治、精神 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或统治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意识形态 ”的众多论述,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还只是众多非意识形态性的哲学中的一种,而到了20世纪, 它已成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变革社会生活的重大意识形态的哲学之一,成为社会主义 国家乃至社会主义世界的精神依据。这不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及其命运的巨大变 化,也不能不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出前所未有的问题、困难、挑战和机遇。所以 ,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无法回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的,无法回避由于 这种意识形态问题而映射出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价值、取向、评价、意 义和转型等重要问题以及相关的衍生问题。
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作为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某种政治、法律、哲学、经济 学等独特的内涵和功能,即这些部分作为统治阶级及统治集团的统治学说,必然使它们 自身带有强烈的政党性、突出的排他性和严格的自律性,以及从表面形式上自视为代表 全社会的功利性。意识形态性在凸现了某种社会形态的重大思想学说的特定地位和特定 功能的同时,也使这类思想学说显示出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画面的某种精神“底色” 或者某种思想文化特质。因而,意识形态问题同样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历程和轨迹的“标杆”之一。
那么,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言,“意识形态化”意味着什么呢?
在我看来,“意识形态化”主要是指作为某种社会形态的精神指南或者理论依据的思 想学说的制度化,简称为“思想制度化”。这种制度化最主要的功能不仅是保证作为意 识形态的思想学说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占统治地位,而且还保障这类思想学说获得与之相 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维护,特别是使这类思想学说落实到物化的设施、专门的媒 体和特有的科层体制(bureaucracy)机构等方面上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化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1.意识形态化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过去的非主流社会意识形式之一的哲学变成了现 今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普及带来了极大方便,也为马 克思主义哲学占据社会精神领域的主导地位提供了必要条件。
2.意识形态化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规教学和普通教育提供了可靠而又有力的保障。 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高等院校所指定的必修课程之一,这使得全社会尤其 是知识者阶层初步学习和初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数空前增多,甚至达到了社会中 的多数成员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定了解或有所感知的状况。
3.意识形态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经典著作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著作和一般读物的出版和发行带来了方便,出现了 职业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及研究刊物。
4.意识形态化形成了一大批以宣传和解说并执行相关职能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干 部队伍和宣传部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终于在相应的社会结构及社会组织 中得到了直接实现和运作。
5.意识形态化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各项工作的哲学学说,指引 这些国家社会意识活动的进行,并且在国际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成为跨国家、 跨地区和跨民族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哲学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 纪中叶的盛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6.意识形态化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某种特定的国家哲学的同时,还意味着马克 思主义哲学同若干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某些历史传统文化及某些历史传统哲学相结合、 融会、贯通,并且在同这些文化及这些哲学的互动关系中产生出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民族形态,或者使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富有了民族特色。
7.意识形态化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世界历史上成为一个理论斗争和思想交锋 的精神“制高点”,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哲学领域所具有的典型风范和独到内 涵。与此同时,也正是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或沟通,令人瞩目地产生了一批带有 马克思主义哲学烙印的新型的理论,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乃至意 识形态化的影响力。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化的作用和影响不仅在整个哲学史上 是无出其右的,而且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 化的历程中,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执政 党的意识形态是“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化的取向、职能、 地位和影响等等在人类已有的全部意识形态的历史中都是为数极少的。
然而,在看到上述方面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 许多相关问题,而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我把它们加以概括,称之为“泛意识形态化”问 题。
什么是“泛意识形态化”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对于作为社会精神指南或支柱的意识形 态所作出的泛化或过度化,亦即致使作为思想制度的意识形态化本身出现了某种夸大、 膨胀和绝对化的特征和倾向,出现了由意识形态过渡到或者混同于非意识形态的现象和 事实,甚至出现了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在同一种意识形态内进行的分化、裂解、变型 和在同一意识形态下实施的论战、冲突、挞伐等。
下面将对“泛意识形态化”的诸多现象作一列举,以便于稍后的分析和评论。
1.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构成(或组成)。马克思主义究竟由哪几部分构成?马克思 主义哲学究竟由哪几部分构成?当人们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外,超出了由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 ,而寻求或建构什么诸如“马克思主义生物学”、“马克思主义系统工程论”、“马克 思主义现象学”直至“马克思主义某某论(或某某学)”时,无疑是一种“泛意识形态化 ”的做法。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当成黑格尔哲学那样的“绝对理念”的大全体系 的企图,实质上是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经过了“泛意识形态化”的作用而有可能导致 僵化,尤其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可能丧失其哲学的性质和功能而陷于某种非哲学性的 教条或教义的境地。
2.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或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某些时期,“泛意识 形态化”的做法制约了上述关系,甚至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出现过由于“ 泛意识形态化”而使上述关系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或社会意识形式之 间每一方的局面。“泛意识形态化”的一个显著之处是用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或包 罗有关的社会科学或社会意识形式,甚至简单地取消或处置某些社会科学及社会意识形 式,例如,社会学、法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经历 和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泛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往往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 某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例和结果。
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所谓人类最高哲学的问题。在过去某个时期,“泛意识形态 化”的某种做法往往是有意或无意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人类哲学的巅峰,当成全部 哲学的终极。这种做法不仅是对于哲学知识和哲学精神的一种荒唐而又可笑的无知,而 且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种亵渎。“泛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常常是表面上抬高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实际上却是贬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贻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人们必须警惕:在“泛意识形态化”轰轰烈烈之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很有 可能是处在滋生了难以解决的矛盾甚至危机之时。“泛意识形态化”的背后往往隐蔽着 大搞“泛意识形态化”的某些人的偏见、狭隘和私利。有一点可以肯定,当马克思主义 哲学被“泛意识形态化”为哲学的顶峰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及生命力也就无从谈 起。
4.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等同于政治及政策、时事策略和宣传方针的问题。回答当 然是否定的。“泛意识形态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而又简单地 当作上述几个方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还是一种哲学的话,它必定同上述几 个方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保持着对它们的反思和审视,保持着不同于它们的独立地位 。若是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上述这几个方面,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这种“泛意 识形态化”所造成的随意性、暂时性和短效性以及某种程度的实用功利性,不但会使马 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独特价值、独特取向和独特功能有所损失甚至丧失,而且会使马克 思主义哲学存在的必要性消失殆尽。
5.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与作为学术思想体系的哲学之间的内 在张力问题。“泛意识形态化”的另一个特征是过多地甚至是惟一地注重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例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视为某种政策、宣传和教学大纲及教 科书,而忽略甚至摈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学术思想研究和学术思想建设的功能 。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于斯大林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 唯物主义”一尊之后的若干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思想价值与功能大为降低,这 一点直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下半叶曾一度落后于当时高速发展的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水平,其严重的后果即使在今天依然有着影响。对此,需要指 出的是,上述内在张力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言,决不是牺牲一方而实现 另一方的“畸型”。
6.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用性和时效性问题。在“泛意识形态化”那里 ,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和有机性,看到的常常是根据一时一地的实用之目的 和功利之需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任意妄为地加以抽取、分割、剥离,然后对这一哲学 的某一方面加以夸大或绝对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肢解为其各个方面没有或失去内在联 系的单面体,进而把这种单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拼凑为一幅只是适应目前形势和当下 利益的“图画”,追求某种眼前的、一时的轰动效应,而牺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谨 和严肃。甚至还有这种情况,即上述做法所带来的片面的深刻性和肤浅的全面性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方方面面(包括其意识形态方面在内)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7.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内部的论辩、斗争、冲突和异化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 “泛意识形态化”所带来的最严重也是最残酷的后果就是它一旦达到极端,往往造成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分歧和论争转向了人际关系和现实生活的冲突甚至迫害,甚至这 种冲突和迫害的惨烈在众所周知的特定年代和众所周知的少数国度里超过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其敌对哲学的矛盾和交锋,在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 冤假错案。这些问题即使在得以纠正之后,依然没有得到深刻有力的反思和批判的总结 。“泛意识形态化”最终所导致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常而健康的发展,更谈不上 什么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繁荣和昌盛的局面,而有的往往是难堪回首但需要我们刻骨 铭心地记取和大力奋进地改革的诸多方面。
8.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化的政党关系与“泛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关系问 题。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执政党由于对共同信 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歧和论战,导致了中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关系的对峙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这两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关系的破裂,这不 但造成了这两个国家及政党几乎走向大动干戈的战争边缘,而且致使世界性的社会主义 阵营土崩瓦解。回首往事,我们所要反思的是:什么是造成同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 形态内部的分歧和社会主义国家间、执政党间的对立和隔阂的原因之一呢?进而,为什 么相同的意识形态内部斗争和冲突的严重和剧烈远远超过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 和交往呢?为什么正是意识形态在那时成为了调整和制约马克思主义的党与党之间、社 会主义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尺度呢?
9.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功能的泛化、滥用问题。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 ,“泛意识形态化”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了超出了哲学之外的某种非哲学的 东西来加以夸大和绝对化。如果说哲学超出其自身还是一种必然的倾向和趋势的话,那 么这种超出并不意味着哲学失去自己的性质和特征。而“泛意识形态化”的要害恰恰在 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其哲学特性和哲学内涵,不成为哲学,而沦为一种非哲学的 甚至是反哲学的东西。因而,“泛意识形态”的做法还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功 能当成惟一的、全部的和绝对化的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泛政治的、泛政策的直 观和映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观点加政策或者原理加事例的“组合”。在此意义 上,我个人认为,“泛意识形态化”也是一种反意识形态化,因为它最终背离了意识形 态及意识形态化的初衷。
这里,随即提出的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化与“泛意识形态化”的关系具体来说是什么 呢?
表面上看来,先有意识形态化,后有“泛意识形态化”。这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泛意 识形态化”是由意识形态化而来的印象或心理。更有甚者,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化一定会 造成“泛意识形态化”。是否造成“泛意识形态化”,不是仅仅取决于一定的意识形态 本身和一定的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而更主要的是在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运用者和传播者的 主体因素,以及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因素和思想文化因素。所以,十分明显,意识 形态化并不是“泛意识形态化”成立的全部充足而又必然的前提之一。
然而,当一定的“泛意识形态化”发生或出现时,人们会更多地面对和反思的是与此 相对应的意识形态化本身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化由之而来的意识形态本身。虽然我们会从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化二者之间的互动中探寻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方方面面,但是 ,应该看到,在意识形态化演变为“泛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还有下列因素:
1.特定的意识形态属性。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当中,在意识形态化的不同时期,有可能 导致“泛意识形态化”的时机和状况是大不相同的。当某种意识形态强烈地、一味地力 图充当全民、全社会的惟一的精神代表和精神形式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论述过的思想可以确定,这种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虚假性,不是在有或无、 存在或不存在的意义上的虚假性,而是那种浮夸、扩充、膨胀乃至以偏概全、以一代万 的虚假性,并正是由于这后一种虚假性有可能为“泛意识形态化”的形成带来契机。
2.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功能。特定的意识形态力图寻求、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精神统治, 力图获得社会日常文化最高的话语权力和阐释权力,它就会把自己的种种功能外化为具 有切实作用的思维、语言、心理、风俗、道德、传统等直至相关媒体传播的各个层面和 各个渠道之中,就会竭力把整个社会意识活动及相关方式纳入到它自己所制约、所规范 的轨道和目的中来进行。因而,这种功能距“泛意识形态化”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了。
3.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其敌对的意识形态之关系这一点,决定了前者为了战胜和警惕昔 日强大而雄厚的敌对意识形态势力,必须通过或多或少的“泛意识形态化”来加以进行 ,来对自己内部加以有形的或无形的整肃。更有可能的是,基于历史上以往所有意识形 态及所有意识形态化的兴衰成败之经验,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为了防范与己不同的意识 形态而趋近于“泛意识形态化”。这里,“泛意识形态化”因为上述的意识形态与敌对 意识形态的关系而同这种关系有着深厚而久远的历史渊源联系。
4.意识形态化导致“泛意识形态化”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及思想文化条件。例如,某 种意识形态化的时期正处于国内战争时期,或者正处于大规模的政治整肃和政治清洗时 期,或者正处于该意识形态内部各种歧见、各种势力进行决战性的斗争时期,等等。这 些都有可能导致“泛意识形态化”的产生或出现。这种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泛意识 形态化”,不仅表明了外部的大敌在旁,境域对外的战争在即,而且显示出全社会的精 神生活如临大敌,往往伴随着思想的高度压抑和精神的高度紧张,而此种“泛意识形态 化”就很有可能为了凝聚全民心理、团结全民上下、统一全民步伐、增强全民意识而显 示出非凡而独特的作用。
紧接着,我要提出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泛意识形态化”到底起 了什么作用呢?“泛意识形态化”究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的“正品”还是其 意识形态化的“负品”?“泛意识形态化”在20世纪中叶之后尤其是在90年代初苏联、 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解体或消失之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对此应有什么 样的反思呢?意识形态化通向“泛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失去了什么和获得了什么呢?马 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泛意识形态化”能否和怎样重新回到意识形态化呢?“泛意识 形态化”的衰退、减小或消失就一定意味着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化的裂变、蜕化或解构 吗?等等。在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加以认真而深刻的思考。
无论如何,“泛意识形态化”都是给予我们反思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处难 得的“基点”,因为,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化时期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正常发展时期,都不会有也不可能向我们提出在“泛意识形态化时期”关于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众多尖锐、复杂、深刻、敏感、痛切甚至攸关我们的学术生命和思想生机的问 题或诘难、矛盾或挑战。与其看到“泛意识形态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带来的众多 负面因素,不如揭示并抓住它们有可能从反面所蕴含、所激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 切入点和突破点。在某些情况下,“泛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或出路已潜在地包含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与过去不同的异质因素、异质原创和异质形态。这种“泛意识形 态化”在有可能回归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失去的是意识形态旧有的局限和不足,更有 可能获得的是与以往意识形态特性不同的新质乃至新意识形态化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的 扬弃。因此,我们不是简单地摈弃或否弃“泛意识形态化”问题,而是把这些问题当成 与意识形态化问题息息相关并且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性和历史性的问题。 总之,在对“泛意识形态化”进行扬弃和变革之际,“泛意识形态化”实现了什么呢? 我只强调一点,它更加促使人们去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而 不是自我畸变和自我异化。
必须补充的是,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及“泛意识形态化”问题并不涉及我 国现实政治生活中所讲的那种“非意识形态化”及“反意识形态化”问题。因为,即使 是“泛意识形态化”问题也不可能与“非意识形态化”或“反意识形态化”问题同日而 语,它们不是同一个层次或同一种属性的问题。就“泛意识形态化”而言,它是在传播 、解说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事实或后果,亦如从某种带有 评价色彩的观点所言,是一种所谓失误或偏差。而“非意识形态化”与“反意识形态化 ”大都是从根本上反对或否定这里所言及的充当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在狭 义上所说的反对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本身。“泛意识形态化”则与“非意识 形态化”和“反意识形态化”大相径庭,因为它本身毕竟是对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化的 接受、认可和肯定。
不过,另一方面,“泛意识形态化”与“非意识形态化”和“反意识形态化”有所不 同甚至有所对峙,但我个人提出的问题在于:这三者之间在某些地处具有这样或那样的 联系。首先,“泛意识形态化”是否有可能导致一种特定的“非意识形态化”呢?其次 ,“泛意识形态化”是否就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一种颠倒了的“再现”呢?再则,“ 泛意识形态化”为什么与“非意识形态化”有着最直接的历史渊源关系和最切近的逻辑 派生关系呢?最后,“泛意识形态化”与“非意识形态化”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事 实或结局说明了什么呢?我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但我还是希望有 心并有志致力于此问题探讨的读者给予我启迪和帮助。
总之,“意识形态化”与“泛意识形态化”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解决和把握这一关系问题不仅促动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中诸多方面的鉴别、评价、运行和变革等,而且直接作用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