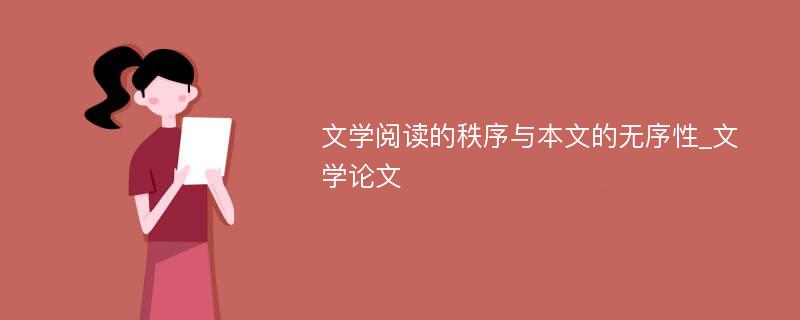
文学阅读的序次性与本文的非序次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文论文,文学论文,序次性论文,非序次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阅读活动有着人们习见而不察的序次性,这种序次性建立在文学作为动态过程的根本性质之上。以这种序次性为前提,文学本文展开了非序次或反序次的一系列艺术形式技法。序次性与反序次性的矛盾运动召唤产生了贯穿文学微观阅读全过程的读者游移视点。通过游移视点的运作,阅读序次性与本文反序次性相互作用,相反相成,终而达到完美交融,臻于艺术形式创造与审美感受的崭新境界。
一、文学阅读的序次性及内化过程性
文学作为动态的历时性的过程,既包括宏观的整体历史发展中意义的不断集合(即文学的历史性),又包括微观的每一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动态运作(即文学的过程性)。在微观的具体阅读活动中,这种动态特点表现为阅读的序次性和主体的内化过程性。
文学作品的阅读不同于对具有外在形体的现实物体的观察,也不同于建筑、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种类的艺术鉴赏,可以具有一目了然、顿见整体、浑然于心的对全局的瞬间体察和直观把握,从而由整体达于部分,再由部分返归整体。文学以语词为媒介,在感知方式上它具有语言艺术独特的间接性特征。作为符号,它必须俟诸读者想象的再度转换。所以,在文学阅读中,读者的内在主体结构对本文的解读一般都有一个在时间上前后相续的过程,都必须经历由词而句而段而章达于全体的由部分到整体的阅读运作程序。
现象学美学家、批评家罗曼·英伽登认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发生而且必须发生在一系列连续的时间阶段中,这些时间阶段是互相综合地联系的。”〔1 〕接受美学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吸取了英伽登的这一思想,他指出,在文学阅读中“整体本文的各个部分绝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短暂的瞬间被同时感知……只能通过对不同序次的段落依次逐一阅读的方式来进行想象。”〔2〕在阅读中, 即使极通俗的武打小说,引你不忍释手,你也只能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读下去。根据感觉心理学家在印刷页的阅读方面所做的深入研究(诸如李乔多、佐特勒、孙思等人的研究),〔3〕在连续阅读中,眼睛注意的焦点每行不得超过2到3个, 而且阅读中眼睛停留或专注于每一个个别字母的情形且在物理上也是不可能的,读者只能处在一种阅读的思想流中,依据读到的不同序次的段落去逐一展开想象。美国批评家斯坦利·费史也注意到了读者在阅读的时间顺序中反应的“特别重要”性,他说:“阅读经验是时间上的流动,因而,读者是按照这种时间的流动作出反应,而非针对整个句子作出反应。这也就是说,不论话语长短如何,读者总是在某一时点上读到第一个词,然后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如此下去。记录读者身上发生的事即记录在该点上发生的事。”〔4 〕这就构成了文学阅读的第一个基本事实:我称之为阅读的序次性。
如果说对有形物体或造型艺术的感知,是要主体站在对象的外面去观看、掌握、把握,那么对文学本文的阅读,读者只能身处其中,入乎其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象学批评家乔治·普莱曾生动地描述过这种区别:“买个花瓶带回家,放在你的桌上或壁炉台上,过了一会,它就使自己成为你家庭陈设的一部分。但它并不因此有所变化,还是个花瓶。可是,带回本书,你会发现它在提供、打开自身。……一本书不是关闭在它的外形内,不是幽禁在城堡里,它只要求存在于自身之中。总之,在和一本书的遭遇中,那最不同一般的事实就是你和它之间障碍的消除。你处于它之中;它处于你之中;不再有外在或内在。”〔5 〕普莱强调了读者深入本文里层,在相互包含、溶浸中进行阅读感受的特点。伊瑟尔也反对那种以外在的主体——客体感知方式来框定文学中“读者——本文”的交流。他认为文学阅读“有别于那种一般可以直接观察得到,或者至少能够设想得出其整体的既定客体……因此,本文与读者的关系是截然不同于那种既定客体与观察者之间的关系的。”〔6 〕伊瑟尔认为,文学阅读中本文与读者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体——主体”之间的结构。而阅读作为一种事件要求读者亲身参与其中。这就构成了文学阅读中的第二个基本事实,我称之为文学的“内化过程性”。这不同于读者面对可以确指的实存对象(如瓷瓶之类艺术品或真实物体)所展开的艺术鉴赏而是指读者主体思维在阅读中一直处在亲身参与创造的生成和转化中。
试读李贺游仙诗《天上谣》:
天河夜转漂四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缨。
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
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7〕
我们读到:一个睛朗的夜晚,诗人游目天河,被璀璨的群星所眩迷,于是游心呈意,飞展想象之神,游历绚丽的天上世界,先是漫步月宫看见桂花纷披,仙女采花,装进香囊垂挂;继而,我们看到嫁给萧史的弄玉正卷起窗帘,观赏晨景,窗前梧桐上立着引他们飞升天堂的神鸟;放眼远观,只见仙人王子晋正吹着细长的笙管,驱使神龙翻耕烟云,播种瑶草;回头再望,一群艳服仙女,漫步青洲正在寻芳拾翠……在这里,我们看到,读诗不同于观画,它只能一句句地读,在阅读中通过想象将文字再度转换为艺术情景。那种一目十行、一瞥之间了然于心的说法只是文学中的夸张。读者只有一句句依次进入诗中,才可能把握和理解诗的语义;只有一个情景一个情景地转换,才能逐次呈现诗中的一个个意象,最终建构出该诗的审美对象(意境),体验出该诗更为深远的意味:天上人间、沧海桑田的人世感喟。
实际上在叙事作品的阅读中这种审美感受发生的序次性和内化过程情更为充分。在长篇小说的阅读中,读者只有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渐次感受,一个视点一个视点的逐步体验,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情节,体会人物,品味意蕴。这就是说,文学阅读是一个事件,是一个主体意识渐次运作的过程。作为过程,它在阅读中形成了不同的阶段,这包括不同的时段与不同的视域。从全过程来看,每一阅读阶段都只是在本文的此一部分形象基础上建构审美意象(格式塔),所以必然具有不完整性和未完成性。而正是这种不完整性与未完成性提供了艺术和形式技法展开的广阔天地,使之在阅读序次性与本文非序次性的矛盾运动中形成一整套创作——接受的叙事形式法则。
二、本文结构的非序次性与反序次性
文学的阅读总要逐章逐节逐行地沿时间顺序延伸,而文学本文则不能完全照搬生活中的时间序列来“记流水帐”,也不能按一般的空间序列去“数门牌号”。作家艺术家们总要绞尽脑汁打破事件发生的自然序列和日常言谈的叙述顺序,他要召唤读者,吸引读者,激发乃至挑逗读者。所以他总是“卖关子”、设“悬念”、包“包狱”,总是欲扬先抑或欲擒故纵,这就是在阅读序次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非序次或反序次的艺术形式技法系统。它利用阅读过程各阶段自身所具有的不完整性和未完成性,来吊起读者的胃口,引起读者探照究竟的心理动力,形成强烈的希望了解“结局如何”的读下去的愿望。
其实在原始艺术中,文学“故事”的顺序总是与事件发展的历时顺序相一致,而阅读(倾听)故事的序次也总是与叙事和事件的顺序相一致的。在漫长的艺术发展史上,它逐渐成为一种作者与读者共同接受的叙事程式。但这种长期的程式化的常规惯例越来越造成人的感觉的钝化、迟滞,使读者无法激起新鲜、生动、奇异的艺术感受。为了打破程式化惯例带来的平庸、无聊、乏味,磨砺钝化的感觉,寻求新奇特异的表达方式,艺术家们一直在进行着艰苦的探索。他们打破了原始艺术中的叙述序次,发展出多种叙述视角(视点),创造出穿插、倒叙、转接、“叠映”等叙事手法,不断变换叙事观点,交叉运用各种叙事方式,展开对比、照应、映衬、铺垫,特别是设置“悬念”等一系列艺术技巧,形成了反常规惯例下自然序次的非序次叙述:空间上非自然排列的顺序,时间上非自然流动的时序与节奏,情节上非常态展开的程序安排,情感情绪上非常态发生的“意外”之趣,这样,艺术创作就打破了现实的拘执,进入了无限广阔的自由想象的时空领域。天上人间,古往今来,奇景仙境,无不自由驰骋想象之骏;而艺术形式则在这种不断的创新中日益获得丰富、变化和发展。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曾深入研究小说中的这种叙事文学的形式特征。 他们认为, 从形式方面看, 小说的一个根本特点是“法布拉”(fabula)与“休热特”(sjuzet)之间的对立与变化。〔8 〕所谓“法布拉”,即“本事”或“故事”,它是指按时序发生的事件的简单罗列;而“休热特”,即情节,则是指艺术家一反本事发生和叙述的一般程序,采用种种手段,将本事的各构成因素通过变形或切割、突出或隐去、扩张或凝缩、调换与转换所作出的艺术性安排。在本事与情节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它们分别遵循“本事时间”和“叙事时间”,“本事空间”与“叙事空间”。作为事物自然发展原态的本事时(空)间经过艺术形式手法的陌生化处理,转换为叙事时(空)间,转换为艺术情节。这样就造成了间离和疏远的效果,读者注意力被引向叙述的手段和方式本身,从而打破了先前因习以为常而变得“代数化”、“自动化”、“程式化”的感受方式,大大延长了阅读和感知长度,加强了感知难度。
当代叙事学的基本兴趣也在于探讨“故事”(本事)与“情节”之间的转化。在叙事学看来,故事是依据时间顺序排列的一系列事件,而叙述就是要精心地设计、筹划,巧妙地安排处理这一系列事件。要把这一系列事件切分成不同的视点(视角),打乱原有的层次和形态,分别镶嵌于不同的空间与时间序列上,最终组成统一的情节结构。法国叙述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综合了让·普莱和茨维坦·托多洛夫的观点,从叙述学角度将本文观点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全知视点,指叙述者>人物的情形,热奈特称之为“非聚焦或零聚焦叙事。”第二类是“有限视野”,指叙述者=人物的情形,热奈特称之为“内聚焦叙事。”第三类是叙述者<人物的视点,热奈特称之为“外聚焦叙事。”热奈特认为本文叙述中的视点变化可以作为聚焦的变化来分析,三种情形都存在着“增叙”或“省叙”的变体〔9〕。同时, 他认为每一本文中的叙述视点都不是单一的,总是同时存在着多种语式,存在着“双重的聚焦”。热奈特发现的多种观察角度,多种叙事视点的交叉和共在,打破了“从一而终”的本事叙述惯例,而“增叙”和“省叙”的艺术处理正是安排情节发展曲线的必要手段。
德国接受美学则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研究本文视点。伊瑟尔将本文的内部视点概括为四个方面:“本文内组合的是整套视点体系,因为文学作品不仅是作者个人视点的显现,它本身就是各种不同视点的汇集。只有通过各种不同视点的组合,才能建立审美对象非既定的现实性。一般来说,保留剧目模式中首先会出现四个视点:叙述者视点、人物视点、情节视点和为读者虚设的视点。通常叙述本文中并不要求各个视点俱在。”〔10〕伊瑟尔发展了罗曼·英伽登的“未定之处”观点,认为在本文的各视点之间存在着“空白之域”,它打破了常规叙述的联结性,造成了各视点各层面间的联系的中断,也造成了人们使用的日常语言期待的“中断”。也就是说,现代叙事不再是简单的“说故事”,它增加并利用各视点间的差异,增加并利用本文各语义段落间由于阅读的未完成性形成的不完整特点所造成的距离,增加并利用“说”与“不说”(空白、悬念)的辩证表现的艺术技法,等待着读者的“阅读行为”来自己“联缀”故事,填补空缺,消除悬念。显然,接受美学所描述的这个建立在视点间相互作用基础上的本文结构是非序次的当代叙述技术法的产物。
当打破叙述序次的非序次叙事方式在长期运用中成为一种创作表态的形式技巧或法则时,这种非序次就成为一种套路、一种惯例、一种新的序次,这种非序次成为序次的过程,一方面有待于打破原有序次惯例的形式美的创新所达到的当代水平和新异程度,另一方面则依据于人类感觉在审美接受中基于当下实践所能达到的审美理解的水平。比如“倒叙”这种艺术叙事技法,在小说发生史上就曾有过相当强烈的创新意义,打破了“顺叙”的常规叙述方式,并为当时的审美感觉的发展程度容纳、认可并接受,并逐步成为一种基本的叙事序次,为妇孺所共知。而80年代中期我国文坛曾经出现的那种简单模仿西方当代潮流的文学创作,虽然也达到了很高程度的反序次创新,但终因其超离于当时现实语境的审美理解水平而颇难为人所接受,因而也难以成为艺术形式积淀中的技巧原则,从而成为一种无序次的序次。只有二者间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达成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才能在双向交流中不断完成“序次——非序次——序次”的循环演进。而当这种非序次的序次又凝定化、程式化为一种陈规惯例时,即完全沦为一种套路(如我国章回体小说对倒叙等方法的运用)时,它就引起了阅读感觉的钝化、“代数化”、自动化,失去当初新创时新鲜、生动、特异的形式冲击力。在这种时候,新一轮的非序次创新与陌生化变革就开始了。在文学发展史上,这种序次与非序次的矛盾运动所引发的形式技法的积淀与创新,和审美感觉体验的钝化与陌生,一方面构成了文学艺术的形式发展史,另一方面构成了人类艺术感受的审美经验史,而正是这两条有着自身发展轨迹的链环之间的相互拒斥、对立、斗争而又相互溶侵、容纳和融合,才推动了人类艺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历史上长期动作的“序次——非序次”演进方式,在当代以剧烈变革的反序次方式呈现出来。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文学本文中的非序次性被推到极致,它完全打破了古典的传统的叙事方式乃至静穆优美的审美标准,无视一切原有的叙事规则,创造出荒诞、倒错、中断、魔幻、戏仿、意识流等极端变形的、断裂的、扭曲的、畸趣的新叙事话语,将非序发展为反序乃至无序。处在审美理想变革关头的波兰批评家罗曼、英伽登曾从其传统审美观和叙事观出发,对这种“无序”深表不然:
我们曾进入思想流,在已完成一个句子的思想之后,我们便准备在另一个句子特别是与第一句子有关的句子形式中思考其“延伸”,这样阅读便轻而易举地前进了。但是当第二个句子与第一个句子没有可供感觉的关联时,思想流便被抑制了。随着抑制导致的思想流的中断,便或多或少地引起读者强烈的惊讶或烦恼的联想,如果我们想重开我们的阅读流,便须首先打开这一障碍之处。〔11〕
英伽登从古典主义传统的优美和谐观来判定当代阅读活动,在他看来,“中断”对于阅读思想流是一种缺憾,它会引起读者的“烦恼”。但在文学本文及其阅读范式的当代发展中,“中断”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功能,在当代阅读中,如果阐释完全按照传统叙述程式展开延伸与记忆间的对称性相互作用,那么本文肯定因其平淡、雷同、重复而使读者失去继续阅读的内在动力。当代的众多艺术本文总是在阅读之链中制造“中断”、“突变”,在阅读的恰当时机制造“障碍”、“含混”,有意延长语词、话语、观点的感知长度,以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而“震惊”、“新奇”、“刺激”等早已进入当代文学的阅读视野,从20世纪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荒诞派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派、黑色幽默等无不将反时空序列的中断、障碍、变形、倒错等作为本文叙述技法。它的确在阅读中引导出众多完全相反的意义阐释,从而大大拓宽了意义的联想域,使作品产生更为丰厚的意味。但其反艺术的极端品格在失去相应的历史语境后,必然引发新一轮的否定与回归。
三、在游移视点中相互作用
阅读的序次性要求本文结构保持一定程度的非序次性乃至反序次性来提高阅读的情节性、趣味性与刺激性。任何一部毫无波澜的“流水帐”都不可能获得读者的青睐。但同时,本文结构的非序次性与反序次性又必得以阅读的序次性为前提。如作家在本文中苦心经营的“悬念”,就是作者依据读者阅读中的序次性预先设置的情节或情感的心理“陷阱”,守候着读者的“陷落”。但如果一位读者因急于知道故事的结局,匆匆越过这些充满陷阱的曲折之途,不顾文学的铺垫、映衬、误导或“包袱”,而经直去翻找结果,那么当他翻到答案,抖开“包袱”时,也就到了结束阅读的时候。即使再读下去,也必然兴味索然。这是为一般读者的审美经验所证实的常识。
实际上本文结构的非序次性与反序次性仍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序次,只不过这一序次在外显形态上可能表现为颠倒、错落、杂陈或空白等无序状态。正是这样一个潜在的非对称结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追求平衡与对称的势能,因之它呼唤、要求读者复现并调节由本文提供(或可能提供)的全部要素,吁传读者进行积极的审美综合,参与创造和建构具有新的序次的作品的意义世界。
那么,阅读的序次性究竟如何展现呢?本文结构的“无序”状态如何转换为统一而有序的作品世界呢?读者阅读的序次性如何与本文结构的非序次反序次性交相作用相反相成呢?
回答是:这只能诉者阅读中的读者游移视点。
游移视点是伊瑟尔在英伽登审美阅读现象学基础上提出的阅读活动的重要概念。它是指读者在阅读中依先后序次进入本文结构中既定的各视角去逐次体验对象的审美活动的轨迹,是阅读中读者与本文相互交融的方式。伊瑟尔认为:“本文与读者间的关系是截然不同于那种既定客体与观察者之间的关系的。与哪种主体——客体关系不同,文学阅读中存在着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解的游移视点在其内部不断运动,这种掌握客体的方式是文学独具的。”〔12〕本文视点的相关性召唤一种读者视点,而阅读的渐次运作形式又决定读者不能固着于某一视点,也不可能同时经历多处视点,因而正是文学独具的这种主体亲身参与的内化过程性,才产生了阅读中不断变换视角,沟通联贯本文结构的游移视点。它克服了外在的和凝固的读者——本文关系,也克服了读者完全认同的本文绝对论的偏颇,探索出一条由读者从本文内部展开双向交互作用的生成艺术意味的审美体验途径。
游移视点的首要特点是其“游移”的特殊性,在本文结构中,一个个句段构成了不同的叙述视角(视点),这些视角从各自独特的人物、情节、叙述方式、叙述语境以及先设的预期读者位置等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叙述同一个“故事”。由艺术形式技巧中积淀的非序次(反序次)方式往往将一个期待中的七宝楼台拆散成各种玲珑器物,它暗示了其间的种种联系,又充满了空白与不确定性,等待着读者的重建。而游移视点就是将之联缀、组合、重建的再造过程和运作方式。在现实文学阅读中,读者游移视点在某一瞬间总是处在本文中的某个视角中,但它又绝不固着于这一视点,而是不断地在本文视角间行进、转换,从此一视点转到下一视点。在这一不断转换中,前一视点的阅读成果不断累积,成为后续阅读的背景,而当下阅读视点则构成了突前的阅读前景,形成在阅读时间流中不断游移的阅读焦点。在阅读流程中,旧的阅读瞬间作为背景制约、影响着作为前景的新的阅读瞬间,而作为此一焦点的前景也影响并改变着过去阅读过的部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又不断地融为一体。
游移视点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内含着读者在动态过程中对各视点相关意象的综合或生产。文学的阅读并不是对字词的表面含义和视点表层叙述的被动接纳或单向的信息收取。作为文学,它一定要从文学意义走向艺术意味,从视点的表层含义引出深层蕴涵或韵味。这就产生了相关审美意念或相关审美意象。也即中国古代文论所说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严格地说,游移视点并不是象一个走进展览馆的游客,随意地“穿行于”各视点,而是如同一条生产线,在每一视点都增加、吸取并减少些什么。当读者驻留于每一本文视点时,读者并不可能将所有阅读过的字符铭记于心,而只能有所删削并由此及彼,在相互作用中生成该视点的相关审美意象。它是读者视点与本文视点进行视野间融合的成果。同时,在阅读行进的方向和维度上,又不断展开各相关审美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修正、相互否定、相互溶浸,最终指向作品整体审美意味世界的生成。
游移视点的第三重意义在于对本文信号的再加工与再综合。同本文的非序次性中包含着潜在的序次性相反,阅读中读者视点的序次性中实际上也包含着潜在的非序次性。这种序次性并不是绝对地只相关于相邻前一视点的相关审美意象,前一视点只能作为后续视点的背景,而是由于不同语境和不同读者的组合、选择,先前视点往往可能在后续阅读中,因新的语境的建立和新的契机的刺激,再次成为阅读中的突前视野,并在对本文的整体反思性阅读中参与构成本文的核心视野或整体意境。也就是说,读者绝不是一次性地加工本文信号(尽管第一次加工十分重要),由于读者记忆材料不断进入新语境,便必然不断引起再综合与再加工,这样,过去某一被“淹没”的光点,便因当下视点而被激活,并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意义,从而使作品的意味世界不断丰富。
文学阅读的实践证实了游移视点的这些特点,从本文方面看,文学作品总是若隐若现地存有一个“预示结构”,似断似续地埋下“草蛇灰线”,常常伏脉千里,一朝洞明。如我国古代长篇小说,就常常用“伏笔”之法引起阅读中的再综合。毛宗岗评《三国演义》时说:“《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善圃者投种于地,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13〕这种传统的伏笔,与其后来的应验,就存有很长的间隔,只有读者在后来的阅读中悟到了,它才展示出其深蕴之意。《红楼梦》中的伏笔则具有另一种“草蛇灰线”的技法。哈斯宝称“伏脉千里,绵连不断。”〔14〕就是说,从伏到应,其中有条暗藏的脉胳,若隐若现,读者在游移视点穿行中,已无意中接受了这条线索的信息,后来应验时,先前“伏”设的机关,全部被激活,便形成了豁然洞明的阅读感受。比如《红楼梦》中安排了众多的人物视角,这些视角常在谜语、诗词、戏言中埋下伏笔,看似无意,自然地融于叙事之中,其后则在读者的整体综合中,蓦然显出深意。如第二十二回探春的谜语:“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汝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远别离。”这便与她后来的远嫁成为呼应。又如宝钗的谜语:“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别,恩受夫妻不到冬。”读者在阅读到宝钗日后守寡的语义段落时,先前的这一对照符号就不仅合理地嵌于谜语,而且被激活,成为探春和宝钗的人生“谜语的谜底。只是这一谜底只能在游移视点行进的某一阶段上方始亮出。再如宝黛各自的命运。宝玉平时不止一次说自己以后要当和尚去。三十回写宝玉与黛玉拌嘴,有一段这样的对话:黛玉道:‘我回家去。’宝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这在先前的语义段落中是天真无邪的玩笑戏言,合情合理,而当游移视点行进到黛玉死去,宝玉果真回归天国,随一僧一道走时,先前只有情景意味的戏言玩笑,便在读者的整体综合中再度呈现出极为深刻的“空”观展示,先前语义段落中十分合理的戏言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同样,黛玉在《葬花吟》、《桃花行》中写花的诗句,也以预“伏”而被激活融进黛玉整个命运的“花开花落”的隐喻,在读者的最终综合中呈现其“韵外之致”。
这样,本文信号和读者意识便在一种生产活动中融合一致,而生产活动则只能是二者共同运作的结果,在后续阅读的再综合中,由于对先前某一视点的记忆是作为相关审美意象综合体来回忆的,所以它唤起的记忆便连带着过去的语境及当时阅读的状况。比如宝黛爱情,游移视点进入黛玉焚诗稿这一语义段落时,先前各视点的综合体便作为已获理解的东西再度得到深化和表现。先前十九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中,宝黛二人聪明机智的打趣寻情,亲密无间的嬉笑逗闹,就连带着先前阅读时的语境及读者当时的情感意象一起浮现,并在黛玉濒临死亡的境况刺激下,特别发挥出与当初巧合无垠的美乐气氛完全不同的令人极度悲伤、凄楚以及人生险恶无常的反面语义潜能。
综而观之,文学本文结构的非序次乃至反序次性中暗含着潜在的序次性,而读者阅读的序次性中又包含着主体综合的非序次性和反序次性,二者通过游移视点展开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吸纳、相互补充,终而达到本文形式创造与读者审美感受视野间的完美融合,建构出丰富多样、无限展开的艺术意味世界。
注释:
〔1〕罗曼·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第96页。
〔2〕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 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版129页
〔3〕参见亚伯拉罕·A·莫勒斯:《信息理论与审美感知》(英文本)论述的有关内容。莫勒斯指出:“当我们阅读某一印刷页时,我们的注意力并未聚集于纸上的印迹,即使它们下处于我们的视域之内也罢。实际上我们只看见运用字母形式表述的潜在思想。在更高的观察层面上,我们从感知心理学家在印刷页的阅读方面所做的广泛工作中得知,在连续阅读中,眼睛注意的焦点每行不得超过两到三个,而且眼睛掌握每一个别字母的形式在物理上也是不可能的。存在着无数印刷幻觉的例子。所有这些发展都引导心理学家接受格式塔理论,以反对单方面的细读概念。”这一论述对我们理解文学阅读的过程颇有启发。
〔4〕斯坦利·费史:《文学在读者中:感受文体学》, 见《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第56页。
〔5〕乔治·普莱:《阅读现象学》, 见《最新西方文学论选》第4页。
〔6〕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第116页。
〔7〕《李贺特选》
〔8〕《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 见其中鲍·艾享鲍姆《“形式方法”的理论》一文,见该书第38页前后。
〔9〕热拉尔·热奈特:《论小说创作的视点》, 见《文艺理论研究》1985年第4期第120页以后,并见《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第126页以后。
〔10〕乔治·普莱:《阅读现象学》,见《最新西方文学论选》第4页。
〔11〕罗曼·英伽登:《论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第八节,见中译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33页译文有所修改。
〔12〕伊瑟尔:《阅读活动》中译本第130页。
〔13〕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14〕哈斯宝:《译译〈红楼梦〉回批》第34回批语,内蒙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