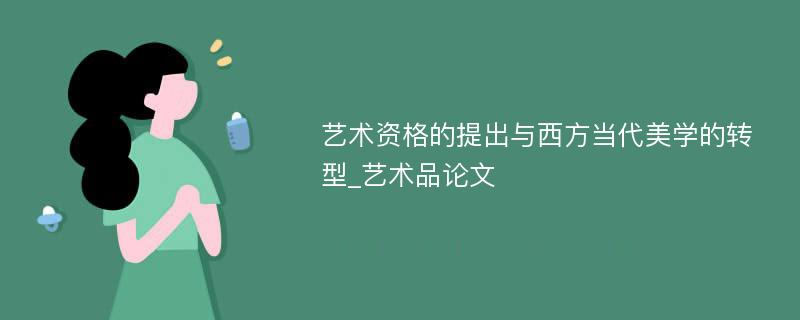
艺术品资格的提出及西方当代美学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艺术品论文,当代论文,资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9)10-0029-06
当以凯奇、沃霍尔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震撼着西方社会时,美学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来自于新的艺术实践的压力。后现代艺术中所呈现出的艺术与非艺术界线、雅俗界线消弭的趋势,令人们对艺术品本身的性质再一次产生了疑问。后分析美学的代表人物诺埃尔·卡罗尔在其《艺术哲学》一书中就已指出,20世纪是近代西方艺术变革不断发生的时代,新的艺术范例不仅在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的美学惯例,它们甚至抛弃了艺术创作所基于的那些媒介。而当新的艺术范例冲击着既定美学传统时,非西方(如东方)艺术也陆续地被发现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① 在此语境下,界定“艺术”的传统艺术哲学路径业已成为愈来愈突显、但又愈来愈成问题的一个讨论主题。
在20世纪下半叶所出现的种种美学理论中,阿瑟·丹托的艺术界理论与乔治·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都对当代艺术哲学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最直接地应对了后现代艺术实践,为达达主义、波普艺术等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而且也是因为他们继维特根斯坦及韦茨的语言学转向与艺术不可界定说之后,为艺术哲学的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路。自丹托1964年在《英国美学杂志》发表了他影响深远的《艺术界》一文以来,众多艺术哲学家开始重新思考艺术和美学理论与历史、文化、社会语境的关系,而不再局限于对艺术品本身的分析,或是相对单向地来理解艺术品及与其相关的各要素之意的关系,例如艺术品如何摹仿、再现了现实物质,或是它如何表现了创作者的情感,等等。相较而言,“艺术界”路径开启了艺术品及其各要素之间的更为复杂而动态的联系,尤其是突出了“艺术”作为一种资格(或者说是一种身份)是如何在此关系中被建构而成的。它进一步也涉及“过去”的艺术品是如何参与了对“当下”艺术品的建构,以及在这种建构与被建构之间所可能存在哪些张力。1969年,T·J·迪菲的《艺术界》(“The Republic of Art”)与乔治·迪基的《艺术是什么?》两篇文章相继出现,它们不仅积极回应并推进了丹托的观点,而且也在英美美学界掀起了新一轮的轩然大波,围绕着这一话题而展开的争论直至数十年后的今天也依然长盛不衰。在这一场争论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美学视角上的转型,即从“艺术是什么”向“某物为何是艺术品”的转型,换而言之,也就是从“艺术品本体”向“艺术品资格”的转向。这一新的美学视角进一步打破了以“美”的范畴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旧有美学格局,并引导美学发展向新的方向发展。
一、“艺术是什么”与现代美学体系的形成
其实,从史的角度来看,正如“美学”体系的确立是一个现代现象,所谓“艺术是什么”的问题也是随着这一体系的发展而出现,并作为艺术哲学的核心问题逐渐具有了本体论上的重要意义。尽管提到艺术的定义,我们通常会联想到摹仿说、再现说、表现说等等,似乎这种界定艺术的形式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已出现,从而有了某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② 但实际上,所谓的艺术定义,以及以下定义的形式来回答“艺术是什么”的问题,甚至于“艺术哲学”本身都是现代美学体系确立及其发展的伴生现象。
对“艺术”概念的理解可以说建构着与艺术相关的各种实践:它不仅意味着艺术实践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人们从中了解到他们正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同时它也在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设置了界线,使艺术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领域。克利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在他著名的《现代艺术体系》一文中,通过对从古希腊到19世纪以来西方艺术观念的梳理,先后分析了狄德罗、夏夫兹伯里、鲍姆嘉通、康德等人的理论。他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美学家们是如何一步步把艺术与技艺、科学相区别,并赋予审美愉悦以无利害特性,进而把“艺术”与“美的艺术”概念合而为一。最终,在鲍姆嘉通与康德那里,一种有意识的有关于“美”的艺术体系得以形成。③ 而在这一有关“美”的艺术观念的传播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便是这种特定的艺术观念何以在18、19世纪演化为一种“理所当然”普遍的艺术原则,并为德国古典美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在对“美的理论”史的梳理下,克利斯特勒向我们给出了他有关现代艺术体系的三大判断:其一,直到18世纪,趣味、情感、天才、独创性、创造性的想象等这些概念才获得其明确的现代意义;其二,直至那个特定的时代,不同的艺术才得以被相互比较,并依据其各自所遵循的技巧原则而分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但与此同时,这些彼此迥异的艺术却可以在某些普遍的艺术原则下加以讨论;其三,在现代艺术体系中,大写的“艺术”总是与“美的艺术”相联系。④ 当然,直至德国古典美学那里,“美”都不只是一种专属于“艺术”特性,反而言之,艺术只是康德等人在谈论“美”时所涉及的其中一个对象,按照卡罗尔所言,在那一阶段,美的理论并不等同于艺术理论。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在现代艺术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一个最为有意味的事件便是:随着美学领域的自主化,艺术史学家与艺术哲学家都有意识地强化了将艺术与非艺术相区别的要求,同时也产生了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对某种普遍适用于“艺术”之原则的需要。这种需求的出现无疑是“艺术是什么”出现的基础。当然,在现代艺术体系形成的初期,对艺术自主性的意识尚未演化为艺术哲学对某种艺术本质的明确追求。
然而,尽管严格意义上,美学并不等同于艺术哲学,但在19世纪到20世纪期间,美学却逐渐被赋予了艺术哲学的含义,18、19世纪美学家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美”的概念也因而成为有关艺术本质讨论得以展开的基础。卡罗尔与普雷本·莫滕森(Preben Mortensen)都相当重视克莱夫·贝尔在这种本质主义界定路径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卡罗尔便认为,在贝尔那里,美被视为了艺术的一种独有功能,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被用来建立了艺术概念,⑤ 卡罗尔把这一方法描述为“美的理论变质成艺术理论的可疑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重要的是对美的检验——无利害——转变成艺术品的全部要点或目的。”⑥ 这也就是说,传统美学家实际上是把美学理论中的某些概念挪用为辨别一个对象是否是艺术品的充分必要条件。罗伯特·斯特克(Robert Stecker)指出,在那一阶段,理论家们普遍认为艺术是审美价值最为重要的载体,艺术是为了实现审美价值而创作出东西,从而,美学中的某些概念也就成为了衡量艺术本质的关键词。正是这种观念推动了美学向艺术哲学的演化。⑦ 这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称的传统/本质主义艺术哲学的兴起。
18、19世纪所逐渐形成的对艺术区别于它物的观念的信仰终于演化为一种界定“艺术”的野心,即为“艺术”找到某种本质属性的野心。这种本质主义界定路径在罗宾·乔治·科林伍德、克莱夫·贝尔等人那里都表现得相当自觉。贝尔曾言道:“当人们说道‘艺术’时,总要以心理上的分类来区分‘艺术品’于其他物品。那么这种分类法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呢?同一类别的艺术品,其余共同的而又是独特的兴趣又是什么呢?不论这种性质是什么,无疑它常常是与艺术品的其它性质相关的,而其它性质都是偶然存在的,唯独这个性质才是艺术品最基本的性质。艺术品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特性:离开它,艺术品就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⑧ 从贝尔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界定“艺术”的路径是随着严格区分艺术与非艺术的心理需要的强化而日益明确的。也就是说,艺术哲学家们关注的目标日益汇聚到一个问题上——“艺术是什么”。尽管艺术实践千变万化、各有不同,但在这些差异背后,总有一个普遍适用于各类艺术的原则或属性,足以将之与其它文化现象或是物质严格地区别。这一观念在现代美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应运而生,并在艺术哲学这里凝聚为一个精炼的问句。它最终是要将各种无穷无尽的事物和现象凝聚到一个独一无二的名称之上,而所谓的艺术的永恒不变的“本质属性”就是“艺术”这一名称存在得以可能的保证。
所谓“艺术是什么”问题在美学界影响颇为深远,翻开任何一本艺术概论或文学概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其理论阐述的基础及核心之一。它甚至“超越”了其自身的现代意义,具有了穿越时空、整合各种观念的能力。艾布拉姆斯对于文学四要素结构的总结,及其对于摹仿说、表现说、形式说等艺术理论的定位无疑便得益于“艺术是什么”所预先赋予的合法性。然而,这种追问方式的合法性在20世纪中叶却受到了质疑。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为艺术界定方式提供基础的那些“概念”有效性本身首先成为了必须反思的对象。
二、对“本质”的颠覆
如果说对“艺术是什么”的追问是源自于区分艺术与非艺术的需要。但随着先锋派艺术实验的愈演愈烈,想要在根本上回答“艺术是什么”却越来越让人感到困惑。当马歇尔·杜尚的现成物(自行车轮胎、或是便器)、当奥兰的整容等被称为“艺术”时,并且,当公众被要求接受这些事物是“艺术”时,艺术家们的所为不仅只是打破了传统的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杜尚的《泉》之所以会给当时的艺术界掀起轩然大波,是在于从未有一位艺术家能够如此彻底地摆脱“视网膜艺术”⑨ 传统,从未有一位艺术家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建立起艺术与现实的联系,也从未有一位艺术家能够如此彻底地打破美学家或批评家对传统艺术观念的信赖。“美学是难的”,这是杜尚之后,所有关注艺术的人共同陷入的困境。杜尚为美学家提出的问题已经超越了“艺术是什么”的疑问。
“当某一声称自身为艺术的对象或事件表面看来并不同于艺术范例时,‘艺术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出现是很正常的。”⑩ 如果说,以往“艺术是什么”是一个让人普遍认同却又被遮蔽住的问题,那么在“是艺术”或“非艺术”之间,它则彰显为一个令人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它引发了理论家们的以下疑问:以往区分艺术与非艺术的标准是否正确;“艺术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是否合法,是否确实存在着诸如此类的标准;理论家们为何对回答这一问题怀有如此之高的热情?20世纪下半叶以来,这种对“艺术是什么”有效性的质疑及抨击已经愈来愈深入。
在《社会秩序中的艺术》一书中,莫滕森尖锐地指出,相对于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艺术是什么”作为一个单一的提问形式,通常诱导许多艺术哲学家们仅追求着一个单一的答案(11);而与他的观点相得益彰的是,卡罗尔在《超越美学》中也言道,“艺术是什么”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哲学的核心问题“在不同的时候可以表示对不同信息的需要”,同时他也赞同T·J·迪菲的看法,认为“这些信息可能不会像大多数当代哲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合乎逻辑地联系起来”。(12) 也就是说,艺术哲学家们所执着的“艺术是什么”问题虽然看似是在孜孜不倦地求索着一个“真实”、“客观”而又“唯一”的原则,但是在各个迥异的答案的背后却暗藏着各位学者们对于艺术的自身视域与主观期待,而这些期待彼此之间的联系却可能相当松散。在此语境下,对于曾经一统“艺术哲学”天下的“本质主义”思路,它的种种谬误在我们看来都不再会感到吃惊。诸如此类的质疑不仅去蔽了我们所习以惯之的那种美学研究思路,更彰显了一种传统美学范式的合法性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削弱甚至失效。
而以维特根斯坦、韦兹等人为代表的新维特根斯坦学说无疑是最早对这种本质主义思路做出批判的一派学说。他们的工作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即对传统的界定艺术思路的批判与否定,主张“艺术”不可界定;并提倡用“家族相似”来实现对“艺术”的描述、解释,从而取代传统的艺术定义。
作为维特根斯坦学说在分析美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韦茨对于传统艺术哲学的反本质主义批判可谓大刀阔斧。在他看来,传统理论家们对“艺术是什么”问题的重视暗含着一种单纯的信仰,即界定艺术是理论家们辨识出艺术、进而能够着手品评艺术价值高低的唯一途径。换而言之,只有在此前提下,我们才有理由承认艺术品具有更高的价值,更特殊的意义、并且值得我们去收藏,或是做出其它一系列回应。确如卡罗尔所言,如果缺乏对哪些对象或行为可以被归类为艺术品的认识,现代艺术博物馆无法实现其收藏,艺术拍卖行无法确定其拍卖品的价格,同样政府或个人对艺术的经济赞助亦无法展开。(13) 这种弥漫于传统艺术哲学家心中的信念导致他们相信一种正确的理论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但是这其实是在根本上曲解了艺术概念的逻辑,误以为“艺术”理应服从某种真正的定义。
韦兹指出,上述这种理论上的冲动使得理论家们无法看到,界定艺术的企图与艺术实践永不停歇的变革冲动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方面,找出艺术的某种本质属性,从而确定“艺术”概念的一系列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这使得“艺术”概念总是呈现为封闭的形态。但是另一方面,艺术实践总是走向革新,相对于艺术实践,艺术概念明显地显示出它的滞后性。因而,艺术不可能具有稳定的本质,它不能被定义,“艺术”其实是个开放概念。“如果我们实际地来看我们称之为‘艺术’的是什么?我们同样将发现没有共同的属性——只存在着一系列的类似之处。知道艺术是什么,这不是理解某些宣言或是潜在的本质,而是借助这些相似之处,我们能够认识、描述、并解释那些我们称之‘艺术’的东西。”(14)
在提出艺术不可界定的同时,新维特根斯坦学说主张对“艺术”、“美”等这些概念进行语言学上的革命,强调“美”、“艺术”这类词语并不永恒地或天然地包含有某种意义,我们对其意义的把握有赖于该词语所使用的特定语境。即所谓“意义即用法”,认为“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15)。通过对“艺术”概念的重新认识,韦茨等人不再是沿着“艺术是什么”的思考模式纠正对“艺术”意义的理解,而是质疑了艺术哲学中界定“艺术”概念的那一既定思路。在此基础上,新维特根斯坦学说试图通过“家族相似”理论来重构对“艺术”的理解。韦兹所谓的“相似”(即“家族相似”),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描述来看,是指“相似点重叠交叉的复杂网络:有时是总体的相似,有时是细节的相似。”(16) 具体到“艺术”上,即是指某一对象之所以能够获得“艺术品”的资格,是由于它在某种程度上与早先的艺术范例存有相似之处。新维特根斯坦学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它对传统艺术界定思路的质疑,及其“家族相似”理论对“艺术”的重构,为我们重新理解美学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思路。
三、复兴还是重构?
新维特根斯坦学说对当代艺术哲学的影响可谓深远,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切艺术哲学的讨论都离不开维特根斯坦所提供的理论语境。维特根斯坦之后的分析美学家们的一个重要规划就是重新回答“艺术是什么”的问题。但饶有趣味的是,作为在这一规划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家,丹托、迪基的理论中却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艺术是什么”已被逐渐地转化为对“某物为何是艺术品”的解答,而在此过程中,对“艺术品本体”的关注正渐渐地转向对“艺术品资格”的兴趣。这种转化的轨迹在丹托与迪基那里恰恰也体现得相当明显。
作为对维特根斯坦理论的一种回应,丹托的艺术界理论与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他们都体现了“回归”界定路径的意图。与同时期的许多其他分析美学家一样,丹托和迪基仍然是在讨论艺术品的某种本质属性,思考怎样的一种艺术定义才能将以往历史中的和新出现的艺术形式同时包容在内。这从他们的以下定义中便可见一斑:“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界。”(丹托(17))“因此说明艺术的本质,几乎没有比提出以下这两个条件作为某物拥有艺术资格的必要条件更为合适。成为一件艺术品就是(i)有关于某物,以及(ii)表达它的意义。”(18) (丹托)“类别意义上的艺术品是:(1)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制度(即艺术世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迪基(19))
与上一点相比,他们之间的第二个共同点则显得更为重要。无论是丹托还是迪基,都相当关注后现代艺术对“视觉”的颠覆,这一变化使得人们很难依据外观、或是某种独特的创作技法识别出“真正的”艺术品。这一困惑促使他们转向了对“艺术品资格”的探寻。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他们二人都选择从艺术品及其所处语境的关系来解释一件事物是何以成为艺术品的,这其实就涉及到了对艺术品资格(the status of art)问题的讨论。
首先,丹托和迪基对艺术品与其所处语境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是艺术界理论与艺术体制理论最令人关注的成果之一。尽管新维特根斯坦学说主张将对“艺术”的理解语境化,但是由于维特根斯坦将艺术问题语境化的讨论是建立他的语言批判基础之上的,因此维特根斯坦主要探讨的是“美”或是“艺术”等作为一个词语是在什么场合下被使用、以及是如何被使用的。但是,丹托和迪基对“语境”的讨论却并不仅限于“艺术”一词的使用,而更为强调艺术品及其“语境”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丹托反复强调的某物成为艺术品所不可缺少的“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或是迪基所说的艺术品与其周围更为复杂的网络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 Davies)等美学家会把他们归为“语境论”的原因。(20)
关于这一“语境”或是框架具体所指为何,丹托和迪基对艺术品的理解无疑有着较大的差异,丹托强调的是艺术品的有关性,即它的语义学意义,他关心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是如何赋予了普通物品以“艺术品”的意义。而迪基则强调了社会机制在艺术品获得其资格时的作用,从而其“语境”携带了更鲜明的社会学色彩。可以看出,这一思路更多地涉及一种社会批评以及历史分析的视角,是对某个事物如何获得其“艺术品资格”的追问。这一新视角的发现对于当代美学的变革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它使美学有可能从更广阔的时空来思考艺术品所处的复杂语境。从这一层面上来说,艺术界理论已经超越了新维特根斯坦学说。
其二,丹托和迪基对艺术品及其“语境”之间关系的兴趣,其实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即某物、尤其是与日常物品外观上毫无差别的物品,它的艺术品资格是如何获得的。在此意义上,而关注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艺术界中,作品被特定共同体认可拥有艺术品的身份,即所谓的“艺术品资格”。用迪基的话来说,这就是“尽管艺术品类有‘大杂烩的一面’(其成员缺乏传统理论所刻求的‘关键类似’),这个类仍旧由这一事实——其成员通过在艺术世界的一个系统占有的位置而作为其成员——组合在一起。”(21)
丹托和迪基对“艺术品资格”的重视使他们的理论呈现了不同于传统路径的特征。就我而言,虽然他们仍是在回答“艺术是什么”的形式下阐释其理论,但却以“某物为何是艺术品”转换了这一追问,“在我看来,艺术确实地或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与之相对照的是表面上的、或是非本质上是什么——对于哲学问题而言是一个错误的形式,在各种问题中,我最先考虑的应该是。如我所认为的,当一件艺术品与一件非艺术品之间并不存在使人注意的感知上的差异时,是什么造成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我已经指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有那种形式:两个表面上难以识别的事物会属于不同的、实际上是属于极为不同的哲学类别中。”(22)
上文中丹托对于“是什么造成了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的差异”的提问,实际上就是对艺术的“为什么”式的发问,而这恰恰也是深深触动迪基的一个问题。他们对此问题的关注超越了对艺术品本身的兴趣,而涉及使艺术品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品的那些现实语境,涉及艺术品的历史特殊性,甚至涉及了构建出艺术品的那一过程。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下去,当艺术品资格是得自于艺术界代理人的授予时(正如迪基所言),那么,这其中必然还要牵涉到种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和使某物具备艺术品资格的那些特定的社会结构。
尽管丹托主要还是从语义学角度探讨了艺术与现实之间区分问题,但是,他对“是什么造成了艺术品与非艺术品之间的差异”的追问,却使艺术界理论抛弃了以往美学对“美”的固恋。这是美学追问从“是什么”向“为什么”转变的开始,也是美学摆脱以艺术品为中心的习惯思维,关注于艺术品资格问题的开始。在一种新的对“为什么”的提问中,我们必然会涉及到艺术品出现的语境,以及这一语境对某物被视为艺术品所提供的种种条件,即艺术品资格如何获得的问题。正如我们在丹托和迪基那里所看到的那样,通过将讨论放置在“艺术界”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中,丹托和迪基的理论使美学不再是与艺术实践、与现实相对分离的抽象思辨,美学思考开始落实到更具体而复杂的社会语境中。
由此可见,从“艺术是什么”向“某物为何是艺术品”的转型,或者说“艺术品本体”向“艺术品资格”的转向。这是艺术界理论跨出传统分析美学视域,建构自身理论框架的起点。从提出“艺术品资格”的问题开始,艺术界理论为当代美学向更开放的视野发展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基于上述这些转变,“艺术界理论”也突显出了它的巨大意义。如果从对象何以获得它的艺术品资格这一角度来追问,它就不再是依据某种视网膜的反应(或诸如此类的其他反应),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某种“看的方式”。在美学发展中,丹托和迪基是率先主张从艺术品与其具体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来考察艺术品的理论家。艺术界理论的独特意义正在于,它在揭示出美学中一直潜藏着的“看的方式”的同时,改变着美学的观看方式。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虽然卡罗尔、莫滕森、斯特克,以及丹托和迪基都认为艺术界理论和艺术体制理论是对传统界定路径的创新性复兴,但就这一转向而言,他们理论中对美学所做出的重构却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由艺术界话题所引发的这一美学转向已成为当代美学中最为醒目的现象之一。
注释:
①(13) See Noel Carroll,Philosophy of Ar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p.206-208,p.6.
② 这种“不言自明性”在艺术哲学家那里也影响颇深,譬如在迪基的体制理论就是从批判摹仿论、表现论艺术概念的不完备性开始的。
③④ See Paul Oskar Kristeller,“The Modem System of the Art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12,Issue 4,1951,496 - 527 & Vol.13,Issue 1,1952,pp.17-46.
⑤ 参见卡罗尔《超越美学》,李嫒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8页。
⑥ 卡罗尔:《超越美学》,第61页。
⑦ See Robert Seeker,Aesthe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Art,Rowman & Littlefield,2005,pp.1 - 2.
⑧ 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⑨ 尽管这种艺术上的变化只是发生在绘画/雕塑领域,但这一绘画艺术上的新变化无疑可以作为我们思考艺术领域发展的方向标。而20世纪60年代凯奇的音乐创作也佐证了这一新的发展趋势。
⑩ Annette Barnes,“Definition of Art”,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ed.Michael Kell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vol.1,p.511.
(11) See Preben Mortensen,Art in the social order: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Ar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7,p.2.
(12) 卡罗尔:《超越美学》,第120页。Also see Joseph Margolis,Philosophy Looks at the Arts: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Aesthetics,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7,part three.
(14) Weitz,“The Role of Theory in Aesthetics”,Reflecting on Art,ed.,John A.Fisher,Mountain View: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1993,pp.14 - 15.
(15)(16)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1、46页。
(17) Arthur C.Danto,“The Artworld”,Aesthetics :The Big Questions,ed.Carolyn Korsmeyer Cambridge:Blackwell,1998,p.40.
(18) Arthur C.Danto,After the End of Ar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195.
(19) 迪基:《艺术是什么?》(II),载李普曼编《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
(20) See Jerrold Levinson,The Oxford Handbook of Aesthe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73- 174.
(21) 迪基:《艺术界》,载朱立元总主编、李钧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三卷,《结构与解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8页。
(22) Arthur C.Danto,After the End of Art,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