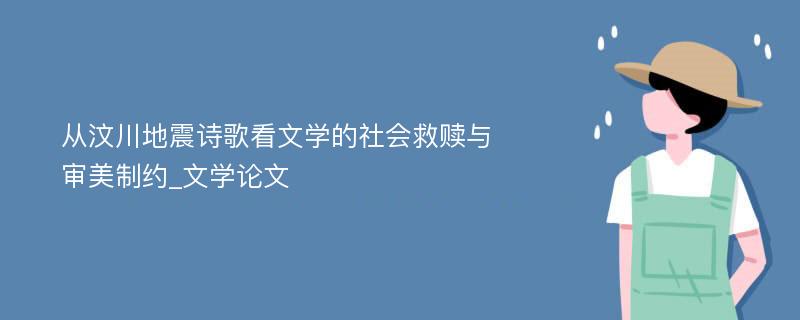
从“汶川地震诗歌”谈文学的社会救赎和审美限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汶川论文,诗歌论文,社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底层写作”、“打工文学”、“草根写作”、“地震诗歌”、“灾难文学”这样的文学名词逐渐从社会现实(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关注层面引渡至文学表现的层面而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学话题和批评热点。这些话题及其所引起的争论,确实强化了近十几年来在政治情结淡出、商业大潮渗透之下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作家的时代使命,使“文章合为时/为事而著”的经典命题被重新加载进当代文学的写作中,其中,尤以“汶川地震诗歌”最为典型,在这场诗人集体“以笔为旗”进行文学的抗震救灾中,地震诗歌写作在激活诗人对社会关注的现实感、道义感之时,其社会救赎和审美限制之间的复杂性也再一次引起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深思。
叙述社会史的文学史:审美的表现与限制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几乎贯穿始终,虽说各个时期反映社会生活的重心不同,改朝换代的革命风云、疗救人心的文化运动与民族救亡的时代话语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叙述内容,但艺术审美却在“间歇性”的表现和限制中跌宕起落。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断纠结的一个话题,功利的还是审美的?有用的还是美的?类似的矛盾困惑历史性地纠缠着一代代的文学创作者和文学批评者。
“五四”之初就高扬起“为人生”的文学命题,直面血与泪的现实,写平民的文学,关注社会时代构成了现代文学的重要基调之一。如果按照今日“底层写作”的批评话语划分,那么鲁迅似乎就是比较早的底层写作者了,他笔下的“阿Q”不正是一位标准的底层弱势群体吗?而鲁迅的“底层”却常常在“被同情”的时候也充当了“被启蒙”的对象。其后如夏衍的《包身工》、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也写底层,其底层更是社会万相和人性百态的言说,启蒙的批判与同情的吁求共同拉近了这一时代文学与社会的联系。
正如很多人把地震诗歌跟抗战诗歌相比,灾难历史往往成为文学的母题,痛苦会进发某种书写的激情一样,这种时效性极强的文学激情几乎天然地带有某种搁置审美的道德化倾向和大众自觉响应的社会意义。抗战使诗人在急迫的社会使命中大多放弃了审美的自律而投向直接的社会目的,诗歌在街头、枪口上成就了自己的荣誉,战火的废墟也使诗美沦落为简单的非诗口号。同样的例证还有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诗歌写作与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现实政治同声呼应,其在迅速反映切近现实而无暇顾及艺术审美的应激式、及时性写作中几乎沦为道德写作和本能写作的摹本,文学本身诉说复杂历史语境和人性的深厚内涵也因此被窄化和表面化。尤其是世易时移之后,这种始于社会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诗歌写作是否会在社会关注度减弱之后成为速朽过时的写作?而文学创作本身仍然需要某种恒久有效的经典写作?正如“汶川地震诗歌”一样,诗人写下了面对废墟的血泪与悲情,也写下了生命的道义和人性的救赎,更写下了对现实腐败致灾的拷问鞭挞,这些诗歌彰显了地震中诗人的社会担当,也使处于同样现实境遇的亿万读者感同身受,所以更易引起大众的共鸣和反响。但是,共鸣之后的重读却使很多作品难以卒读,其原因耐人寻味。
实际上,自共和国建立后,当代文学的社会使命就被强调到至高地位,反映社会生活几乎变成了对“政治生活”和“时代主旋律”的礼赞,自我与审美都受到规训和压抑。工厂、农村、军队对应着工农兵的火热生活,重大事件的密集出现使得文学写作成了一个道德天平,写社会生活成了诗歌的天职。这种论调在汶川地震诗歌写作中也不乏其声,写地震题材的诗人对另外一些不写地震题材的诗人进行道德指责——面对这么大的民族灾难,你能无动于衷吗?你良心良知何在?至此,诗歌表现社会生活和重大事件时的盲目、切近和机械已见端倪。如是,面对社会重大问题(如灾难),“言与不言”之间,首先是个道德问题,其次可能才是审美问题。这就像建国初期何其芳、穆旦他们被指责一样,面对火热的社会主义生活和新中国人民,你们为什么不唱出你们对这个时代、这些人民的赞歌?而何其芳的回答是:
如果我的杯子里不是满满地
盛着纯粹的酒,我怎么能够
用它的名字来献给你呵,
我怎么能够把一滴说为一斗?
——何其芳《回答》①
与此同时,穆旦由于“对新事物向往不深,对旧的憎恶不多”而产生“新生活”的书写焦虑:
这时代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
而我呢,这贫穷的心!只有自己的葬歌。
——穆旦《葬歌》②
曾经在抗战中投笔从戎,用切身行动书写了诗人自我与社会时代的圆满契合,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投身报国后却在如何表现政治这一诗歌创作的时代问题上发生了困惑。何其芳与穆旦的诗歌回答显然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自然成为当时的“另类”和“毒草”,但这样的例证说明的正是文学与社会关系被“泛意识形态化”和“泛道德化”之后的可悲结局。当时代要求诗歌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简单明确为完成政治任务时,政治第一、审美居次,诗人自我退隐,个体膨胀为集体,言说自己成为禁忌,为工农兵代言成为通行证。于是,诗人的创作个性和审美追求在被政治限制的痛苦中埋葬。
可以说何其芳与穆旦的写作痛苦恰恰是诗人自我思想、审美个性与时代表现之间的挣扎困惑,这样的例证在汶川地震诗歌中亦不乏条件反射式的“泛政治化”抒情或叙事。比如由中国诗歌学会在地震第六天即火速编辑出版的第一本抗震救灾诗集《感天动地的心灵交响》、“皇家”刊物《诗刊》的抗震救灾专题诗页以及蜂拥出版的各种地震诗集诗选,其过度主旋律的政治抒情诗模式给人一种“历史性雷同”的乏味之感,而真挚切肤的个体感受和陌生化的美学意境却付诸阙如。以《诗刊》2008年第7期上半月刊为例,黄亚洲的《重建:信心与希望》之《映秀开始清理废墟》、谭仲池的《特殊党费》、张玉太的《党在岗位上》、李永新的《党啊,永远是人民的依靠》等大量诗中充斥着轻车熟路就改头换面的假大空套话和旧瓶装新酒后万事可诗的“万能”革命语言,可以说暴露了一些诗人其实与灾难无关痛痒的浅薄乐观甚至是戏说痛苦的轻浮。期间,最庸俗化的例子当属王兆山那首著名的“鬼诗”《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③,当人们震惊并谴责王兆山漠视死难者生命和献媚政治的同时,更应该深思的是,类似的把政治庸俗化的歌颂模式和“有事就有诗”、“坏事变好事”的表达思维其实并不鲜见,它是一种政治抒情体式的媚俗变体,是对“多难兴邦”精神的歪曲误读,是把文学表达的社会激情道义演变成解读、解说当下政策的敏感嗅觉,这在文学史上的统制其实经久不绝。当代诗人的典型如郭沫若,他自觉放弃了诗歌的自我和审美个性,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事件中亦步亦趋紧跟政治形势,极为自觉地充当了以诗歌图解时代政治政策的文学急先锋。因此,本应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文学史似乎本末倒置地充当了社会史和生活百科全书的看客。
而在诗情过剩、文字高产的地震诗潮写作中,王家新的一首短诗《哀歌》(2008.5.15)颇能说明某种存在于诗人内心的诗歌精神,在短短6行的日常语态叙述中最后出场的诗人身份“我”显得格外突出,其言犹未尽中深藏的是无法言说的悲痛和节制滥情的自我儆醒,在铺天盖地高呼地震诗歌已由“个人化”写作回归“社会化”写作之际,这是真正的艺术自律,它或许昭示着诗歌的尊严和人性的尊严。当重大社会事件突袭,“言与不言”之间,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亦是一个审美问题。
父亲失去了儿子
孩子失去了母亲
失去,还在失去
失去,还在冒烟
而我失去了你——语言
你已被悲痛烧成了灰烬④
语言作为言说的武器是诗人介入社会的标志,但面对如此毁灭性的灾难,语言又是如此无力、轻浮。王家新诗中“而我失去了你——语言/你已被悲痛烧成了灰烬”与朵渔诗中“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或许同样指向了在大灾难大悲痛面前,诗人为何写作,诗人怎样写作的深思。显然,“诗人何为”的自我拷问在不同诗人的笔下体现了不同的表达。正是在此文学史意义上审视汶川地震诗歌写作,阿多诺所说的那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抒情诗是可耻的”⑤才更有效也更具警世意义。诗歌与社会的关系首先应建立在诗人直面自己人性恶时的弃绝轻佻和自觉反省,这样才能使关乎灵魂的文学在面对普遍性的社会苦难时重新审视、书写人类自身的灵魂苦难,这才是当代文学弥足珍贵的道德品质。在“诗歌合为时而著”的历史语境中既不因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而为文学授予道德褒奖,也不因以关注社会现实为名义写作媚俗政治诗而放纵道德缺失,换句话说,在诗歌与社会的关系衡量中,审美和道德缺一不可,但二者如何无害相遇而不两相抵消则是考验诗人创作技艺与精神人格的重要尺度。
地震诗歌:个人化写作与社会化写作的相遇
无论是地震诗歌还是底层写作,文学反映自己的时代现状,介入重大社会事件,从伦理道德的审判迈向艺术审美的检验。如果说一个诗人对现实生活中具有社会性、公共性的苦痛、喜悦有所感知和承担,那么如何艺术化地、富有审美个性地表现时代万象和世道人心就成为这类写作的焦点。
“个人化写作”是近二十年风靡诗坛的关键词,自“朦胧诗”几乎被盖棺定论为“社会化写作”之后,曾被他们重新发现的“个性”、“个人”、“自我”却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路诗人们审美救赎的法宝。许多当代诗人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挤兑之下变得“自我”、“小气”,他们一度拒绝时代话语和社会担当,甚至以“社会性题材”、“重大历史事件”等公共话语入诗为耻,“背对生活”被奉为创作潮流。而当汶川地震这样举世震惊的灾难发生后,生命的脆弱与绝望、死亡的恐怖与残酷、人性的守望与坚韧作为公共事件被淋漓逼真地呈现,成为比任何文学作品和任何艺术想像都更具真实震撼力的社会现场,诗人的目光和心灵在共同关注中凝聚文学的力量,没有比用鲜血和泪水洗涤的灵魂更为洁净。诗人们释放了久已压抑的社会性,各种叙述或抒情方式也被激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精神和审美方式一一呈现。每个诗人都成为公共记忆的亲历者、在场者,每首诗都成为灾难现场的记录和内心疼痛的倾诉。
可是,地震诗歌的社会化写作虽使诗歌具有与社会大众亲近的历史现场感,苦难虽使诗歌绽放出一种沉甸甸的悲壮美,但这并不代表选取重大社会题材或灾难题材就先天具有审美的优越性。不可否认的是,地震诗歌在道德伦理上实现了某种同悲共喜鼓舞人心的社会救赎功能之后,一方面由于普通大众广泛参与导致写作者身份和诗艺水准的鱼龙混杂,许多诗作充满即兴随意的草拟痕迹,不少是过于迫切的应时之作,缺乏诗艺的打磨和审美的自律。即使是专业诗人也有不少迷失在地震诗歌写作大潮中社会救赎的“入场口”,所以地震诗歌中充斥直抒胸臆的同情堆砌与悲伤泛滥的过度抒情,还有依托口号简单急就的口语诗、朗诵诗、街头诗,如“汶川挺住”、“生死不离”以及在地震诗歌中人气最高获得大众最多共鸣的那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从当时的情境来看,这类“短平快”的诗作很有感染力,但从社会历史消逝后的文学价值来看,其魅力和深度却打上了先天不足的烙印。而当领袖的政治良知和普通百姓的社会良知被放大成时代精神的核心,众志成城的抢险救灾和英雄主义的“人定胜天”重新结合成一种时代传奇,灾难叙述中又被肤浅空洞功利地重新消费。当同一社会题材带来严重的雷同化、程式化倾向时,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地震诗歌写作恰恰不同程度地限制、损伤了诗歌的审美品质。
甚至更为普遍性的是“个人化写作”让位于社会化写作后重新彰显个性的艰难,艺术永远不排斥技艺,不能以社会承担的重任遮蔽掉审美的位置。文学不是止痛药或速效救心丸,而是关于国家和民族伤痛的公共记忆。在地震诗歌写作中,也有文学与社会结合的极端主张,比如“写诗不如去汶川现场救援更有意义”,“不去地震现场就不配写作”,“地震不能成为文学资源或风景”。在我看来,“题材无禁区”仍然应是诗歌创作中的法则,关键看如何把握所涉题材,地震这一灾难性的公共事件也当然可以成为写作资源或文学风景,但绝不是廉价浅薄的猎奇游记,即如血腥的赤壁还会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吊古怀古的资源背景一样。既然灾难已经发生,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肉体心灵和文学艺术去直面历史,表现苦难?忘却或遮蔽都是对灾难历史更大的不敬,正如我们曾经直面政治地震意义上的文革灾难一样。甚至在我看来,题材无禁区,文学的渊源则取之不尽,大者如国家社会事件(战争、下岗、矿难、地震等)、小者如自己的身体状况(疾病、生育、亲人的死亡等),写自己其实也是写社会,写社会并不排斥写个体。
其实,诗人作家未必要深入震灾一线以求所谓的“现场感”,我以为,现场感不是你的脚去不去汶川的问题,而是你的心为那里跳动没有?现实生活的叙述终必转化为历史叙事,所以,即使不从传世魅力来苛求,仅从超越社会性层面的审美性来讲,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在这样的大灾难面前,关键是要写出“丰富”和“丰富的痛苦”⑥,写出具有文学独创意义的“这一个”、“这一首”,而不是说出“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轻浮可耻之语。仅以抗战诗歌为例,在战火和死亡面前很多诗人拿枪拿笔,有现实体验亦有痛苦激情,但审美之伤却比比皆是,而投笔从戎后从野人山尸堆里九死一生的穆旦却在社会救赎和审美限制之间找到爆发点,如《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一诗中那动人心魄的祭歌: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在祭奠抗战死难者的诗歌中,穆旦这首诗点石成金的语言与化腐朽为神奇的想像独具一种过目不忘的审美效果。而在汶川地震灾难中亦有令人震撼的诗情,在此,我想说说灰娃这位80岁高龄的女诗人,地震后她在北京阜外心脑血管医院病房中写下了《国旗为谁而降》、《用柔软坚硬的笔触》等爱恨交织的诗歌,哀悼、愤怒与悲悯的社会关注漫溢纸端,她能“透过深藏的泪水”体恤“整世纪的伤恸”:
你竟这样离开人世,不辞而去
昏昧天气尚未隐退,原本你
能等到吉祥之光,而那个时辰
你的心,正被日子一些细微光彩
激活?还是儿子的学费、居住款项
折磨着你?或许,你用残损的
肢体撑起劣质水泥,回想起与
父母官们的那次争执?
——灰娃《用柔软坚硬的笔触——为5·12四川大地震作》⑦
灰娃以日常形象和世俗现象入诗,直接拷问天灾中的人祸,充满直观画面感的“残损的肢体”显示了人性善恶的触目惊心,与穆旦哀悼死难者的诗歌具有同样的审美魅力。此外,一些作家诗人能在一片直白哀哭的地震诗中烛照理性和人性的光芒,不滥情不矫情,不发空言不喊口号,这样的作品可谓兼具思想深度和审美感受。小说家方方的诗歌《到那个时候》已经遥遥望穿了此刻抗震救灾的喧嚣而预见到了灾后平凡而残酷的生活:“日子比过去更加漫长甚至残酷/可是生活除了继续,别无选择”,感情的真实平凡与细节的真实平常使其诗歌在抒情中带有一点小说叙事甚至聊家常的亲切感,脱弃了一般地震诗书写灾民时的空洞失真。
当喧嚣声潮水般退去
当周围的人越来越少
当生活变得庸常
当日子成为自己的
……
当中秋
当空空的秋千无节奏地摇晃
当另一个枕头永远失去温度
当病卧在床茶杯里没有热水
当早上醒来习惯地喊着的一个名字
当年关
当人们去关注无数与你无关的事
当你再次进入茫茫人海不再是焦点
当最艰难的时候沸腾地过去
与方方以低沉低调的家常语言直接体恤、对话灾难群体不同,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写于持续震撼中的5·12大地震》接续的则是阿多诺的反思精神,显然是对所有灾难目击者和地震写作者甚至写作本身的深刻怀疑,其折射的正是诗人普遍的内心彷徨和诗歌在社会救赎与审美救赎中的悖论境地。
今夜,我必定也是
轻浮的,当我写下
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
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
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
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
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
轻浮如刽子手,
轻浮如刀笔吏。⑧
在灾难面前,诗歌更应该挖掘复杂深沉的“丰富的痛苦”。一首优秀的诗歌在社会救赎之后应该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审美张力。时代灾难往往使所有诗人面临共同语境,经历共同历史,但如何表现这种共同的社会痛苦和历史悲剧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时的激情,还应有对历史的深刻儆醒与体悟,正如王家新在1990年末写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
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照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剧⑨
经过历史遽变的中国人如何幸存,如何面对过往的苦难和未来的新生活,显然,共同的灾难亲历者还必须直面可能不断会重演的共同悲剧,而诗歌在更为沉痛的社会救赎之后还将担负起必要的审美限制,即激情泛滥后的反思,悲沉背后的情理兼备。就像抗战时艾青在他的诗歌名篇《土地》(1938年)中所写: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或许这不算我的偏见:越是在充满遽变的大灾难大痛苦之时的文学,其应急的社会时效和恒久的审美力量常常发生错位。我以为,流着泪写的诗未必是好诗,好诗却一定需要有泪,和着爱与恨的泪;而流到心里的泪比流到脸上的泪更具有文学震撼力,更具有社会深广度,正如少陵野老杜甫《哀江头》中“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一样沉郁,亦如陶渊明《挽歌诗》中“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自悼一样。流泪是人面对苦难的本能反应,但诗人的眼泪更应是一种深沉丰富的“吞声哭”——凝结着对人类社会深沉大爱和丰富痛苦的文字结晶。
在汶川地震第一时间集中爆发的地震诗歌写作已经退潮,深刻深广的灾难现实也将逐渐成为灾难历史,但是,那些灾难中逝去或幸存的生命,那些人性的闪光和丑陋,或许就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被文学记忆。当“现场写作”转换为“历史写作”之际,诗歌的社会救赎不再搁置审美救赎,直面现实也直指灵魂的文学既可以是“有用的”也应是“美的”。那些因灾难历史而使人心沉重、痛苦丰富的诗歌或许正是社会所值得期待的文学书写。
注释:
①何其芳:《何其芳诗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②穆旦:《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王兆山《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发表于《齐鲁晚报》2007年6月6日A26版,原诗为“一位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发出如是感慨:‘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④引自黄礼孩主编《5·12汶川地震诗歌专号》,《诗歌与人》总第19期,2008年5月刊印。
⑤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⑥此处借用穆旦诗歌《出发》中的诗句“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⑦灰娃:《灰娃的诗》,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⑧朵渔:《今夜写诗是轻浮的》,《诗歌与人》2008年5月刊印。
⑨王家新:《王家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标签:文学论文; 诗歌论文; 穆旦论文; 汶川地震论文; 地震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何其芳论文; 灾难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