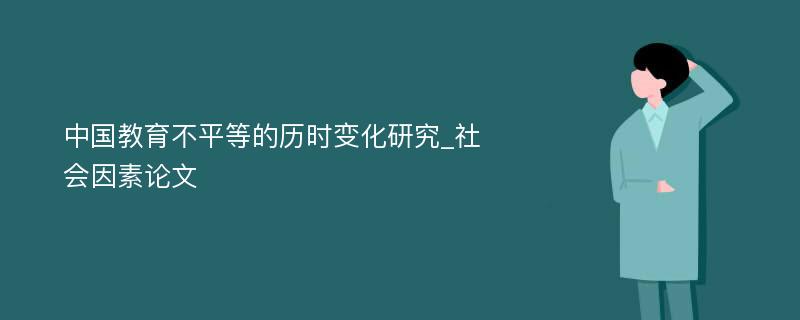
我国教育不平等的历时性变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发展,具有三个最为基本的共同特性:在剥夺旧有统治阶级的教育特权的同时,迅速扩大广大民众接受教育的权利,使教育成为推进社会主义平等的一个重要工具;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力;在学校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使学校承担对学生进行政治社会化的功能。这三个基本功能的实现,使我们很少意识到要去探讨教育发展过程中,社会个体在教育获得方面存在的差异。而事实上,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了解这种差异性及其变化,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教育和促进教育发展。
一、文献回顾
教育不平等问题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大约在60年代以前,人们的理想是消除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但是较少讨论教育过程本身的平等问题,并且一致认为平等的教育必然推动社会平等的实现。帕森斯关于教育平等的理论是此类平等观念在社会学中的重要体现(Parsons,1961(注:本文中,作者倾向于将“不平等”概念当作一个中性词,用来指称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当然,帕森斯的观点一直受到多方面的批评。
最早提出对教育不平等概念加以区分的是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他在1966年发表的著名报告中提出,要将社会环境的影响与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区分开来(注:Parsons,T.,1961:‘The school as a Social System:Some of Its Functions in American Society.),完全的教育机会均等“只能消除所有校外的差异性才能实现”,而这是永远不可能的(Coleman,1966)。后来他在1975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必须拒绝两种关于教育平等的一般认识,一种是教育结果上的平等,另一种是教育资源投入的平等。他认为前一种教育平等的观点没有考虑环境对不同孩子的不同影响,而后一种观点只能导致谁也得不到教育。因此教育的真正目的应该是通过教育过程来降低环境因素对不同学生的不平等影响,从而减少这些因素对孩子将来的成年生活的影响( Coleman,1975)。对科尔曼来说,教育均等, 就应该是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均等,即学业成绩的均等。这当然是科尔曼的一种教育理想。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要达到这样一种结果的均等,必须满足几个至关重要的条件:(1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了能够满足所有人所有阶段学习要求的时候;(2 )所有的学生具有相同程度的求学欲望和相同程度的学习兴趣;(3)为了不使学生受到来自家庭、 社区等的环境的影响,学生必须生活在只有教师和同学的纯粹的学校环境中,否则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不可能随时削减外界环境的影响。
然而当这些条件不能满足时,我们就有理由来研究这些社会环境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教育获得的。事实上,这也一直是从布劳—邓肯开辟现代社会分层研究以来的研究主题之一。
布劳—邓肯对教育获得的研究,是通过建立教育获得的因果模型来进行的:个人教育水平作为结果,来自父母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作为原因。许多从经验研究中分析教育获得的学者,沿袭的大体是这种研究范式,并得出了大体相似的结论:人们的教育获得,与其父辈的社会阶层特征和教育水平有着极为显著的相关关联。直接袭承布劳—邓肯研究的威斯康星学派(Stratification School of Wisconsin,Madison)在研究过程中引进了一些中介变量,如个人智能、努力程度、父母学校鼓励等,由此生长出教育获得与社会分层之经验研究间的两个重要分叉。可以说布劳—邓肯模型注重于地位结构、先赋性因素对教育获得的社会传承意义,而威斯康星学派则更注重于人际之间、代际之间影响的个人心理机制在教育获得和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影响。比较这两种研究思路,前者可以适用于研究社会地位获得的一般状态,后者更适用于研究影响整体社会中特殊亚群体之教育、地位获得的特殊因素。
来自欧洲的社会分层理论传统非常明显地支持了教育获得的社会传承观。具有代表性的是布迪厄的社会、文化再生产理论,他与帕塞荣合作的《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一书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许多人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看成是可以客观描述出来的人们在社会生活空间中的位置结构。与此类观点相比,布迪厄更倾向于将之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Bourdieu,1987), 教育正是这个动态建构过程的关键环节。他认为教学活动(padagogic action)是一种运用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进行教学沟通的过程,孩子的学业成绩如何,主要看这个沟通过程的效果如何,而决定沟通效果的主要是受业者与沟通过程相关联的社会特征和学业特征(文化资本)。所有教育过程的特殊产品是造成与孩子在家庭中获得的文化习念(habitus)相区隔的、由主文化之任意专横(cultural arbitrary)所支配的新习念。因此,布迪厄与帕塞荣提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由于不同阶级的孩子在家庭中习得的文化习念与主文化要求之间的差别,使得孩子在学业成绩上存在差别。以语言资本为例,布迪厄认为具有上中层阶级背景的子弟由于从父母那里就接受了学校所规定和奉行的中产阶级文化形态,从而在各种与语言有关的、需要广泛的文化知识背景的考试中,就能较容易地取得好成绩,而来自下层、工人阶级的子弟,即使付去了更大的努力也很难取得相应的好成绩,这与波恩斯坦的研究结论相似。
另一方面,教育制度也体现了阶级利益关系和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关系。教育系统中的不同学校类型(这在一个国家中往往决定孩子的地位流动),决定着对不同阶级的子弟的教育选择,在后来出版的《国家贵族》一书中,布迪厄用统计事实表明,具有不同地位流动倾向的学校类型(尤指大学)的分布,与孩子在进入该类学校之前的社会空间分布是平行一致的(Bourdieu,1996)。
由此不难看出,布迪厄的思想对社会传承观的支持:家庭社会背景和文化资本的阶级差异影响着孩子在专业选择、学业成绩、升学机会、地位升迁上的区隔,从而在孩子中间再生产出一个相应的社会、文化的地位等级。
二、教育获得的先赋性差异及其历时性变化
教育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它与整体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教育发展和教育获得过程中的不平等情形,一方面直接源于教育制度的演变,另一方面也受到整体社会变迁的影响。因此,在不同的教育制度变迁时期,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状况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在开始对我国教育发展与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之前,我们首先来对下面用到的几个关键概念作进行操作化定义:
学龄群体:以“出生年+14岁”作为学龄年,相同学龄年的个体则为同一学龄群体,几个相近的学龄年群体称为学龄组。这个“学龄年”概念是大多数教育社会学学者所认可和采用的。
教育发展程度:不同学龄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教育不平等:(1)不同学龄群体中的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差, 我在这里称之为结果上的不平等;(2)父亲教育程度对教育获得的影响;(3)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我在这里称(2)、(3 )两种不平等为机制性不平等。这里社会经济地位是根据我国标准职业分类、参照国际职业地位指数(ISEI)所确定的,分值在10 ~90 之间(Treiman & Ganzeboom,1988,1996)。(4)性别不平等;(5 )城乡身份带来的不平等,由于户籍身份制度是1958年才开始确定的,因此对于58年以前的学龄组,其身份以14岁时居住地为农村还是城市为判定依据。(2)~(5)四种不平等同时可称为先赋性不平等,因为这些因素是由人们的出身、生理遗传差异以及个人所不能左右的身份制度所限定的。
为了分析影响教育获得的先赋性因素,我们首先设计了一个一般微观方程,这个方程的基础是Blau—Duncan地位获得模型中的关于教育获得的先赋因素方程,我们在其中添加了另外两个变量:性别和城乡身份差异:
E=β[,0]+β[,1](FE)+β[,2](FS)+β[,3](M)+β[,4](C)+δ (Ⅰ)
表:先赋因素随学龄的推移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之变化
自变量
截距
父亲教育
父亲社会
性别(男性)
学龄组
经济地位
49以前
-0.504*
0.61967
0.072072
2.86635
50~55
1.35967
0.31959
0.024680
2.77058
56~60
3.21187
0.28956
0.013676
2.22312
61~65
2.19445
0.16234
0.044189
2.76332
66~70
3.40398
0.18758
0.038915
2.52347
71~76
5.26909
0.12231
0.032378
2.00293
77~80
5.83532
0.18070
0.016231
1.57618
81~85
4.77356
0.22885
0.031832
1.23569
86~90
5.77136
0.23420
0.021870
0.25076*
自变量
14岁时的身 Adj-R[2]
因变量
样本量
学龄组
份(城市) 均值
49以前
0.78515*
0.36 3.14
685
50~55
3.37939
0.41 4.43
493
56~60
1.78442
0.26 5.46
478
61~65
2.66569
0.32 5.30
607
66~70
2.30236
0.28 6.16
928
71~76
2.36128
0.242 7.70
872
77~80
1.87977
0.25 8.00
762
81~85
1.83930
0.346 7.93
742
86~90
1.99932
0.30 8.11
519
带‘*’的参数表示在0.05水平下不显著。
这里,方程左边(因变量)E为本人的教育程度(年数), 方程右侧FE为父亲的教育程度,FS为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M 为性别的虚拟变量(男性=1),C为城乡虚拟变量(城市身份=1),β[,0] 为截距,β[,1]、β[,2]、β[,3]、β[,4]分别为变量FE、FS、M、C的回归系数,δ为误差项。对于此方程,我们只是选取了49年以后的各学龄组进行分析,其结果如下:
E=3.95+0.28(FE)+0.028(FS)+1.8M+2.11C
(R[2]=0.26,F=432)
(37.6)
(18.6)
(7.2)
(18.3)
(14.1)
(本行为检验上行变量和截距项之显著性的T值)
从上面的方程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讲,1950年以来的各学龄组,其个人教育水平,26%的原因是来自于先赋性因素的影响(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2]=0.26)。 这个方程的回归系数可以解释为: 在分别控制方程中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父亲的教育水平每高出一年,父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提高10分,其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均可大约提高3/10 年(对于父亲职业地位,3/10≈0.28=10*0.028); 在分别控制方程中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教育水平比女性平均要高1.8年左右, 而有城市身份的人比农村人教育水平大约平均高2年。
那么,这些先赋性因素是如何随着学龄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呢?我们大体按相距5个学龄来将全部样本分为九个学龄组, 然后分别运用上面方程来分析不同学龄群体的教育获得受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这九个学龄组的划分是:49年以前、50~55、56~60、61~65、66~70、71~76、77~80、81~85、86~90。由于我们主要想考察解放以后的情况,所以49年以前的学龄组没有再细划分,并且,样本中年龄最小者为76年出生(调查时20岁),所以最后一个学龄年为90年(76+14岁=90)。于是我们就有下面的方程组:
E[,i]=β[,i0]+β[,i1](FE)+β[,i2](FS)+β[,i3](M)+β[,i4](C)+δ[,i] (Ⅱ)
这里i=1,2,……9,对应于9个学龄组的划分, 其余各变量的解释同方程(1)。其结果如下表:
上表中,除49年以前学龄组的两个系数、86~90学龄组的性别差异系数不显著外,其余都具有很高的显著度。九个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均在25%以上,其中高于30%的有四个,低于30%的也有四个,与方程(Ⅰ)的测算结果大致相仿,因而可以说个体的教育获得大致有30%是由先赋因素所决定的,其中较低的是71~76,77~80学龄群体,大致相当于“文革”后期和改革的最初几年学龄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这两个时期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在此考察一些当时更为重要的政治背景因素,诸如父亲是否是党员、家庭出身等。当我们对这九个回归方程分别加入父亲是否是党员这个政治背景因素来分析其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时,这个变量在66~70、71~76两个学龄组中是非常显著的(P<0.01,回归方程及详细结果从略), 在控制其他背景因素的影响后,父亲是党员的子女,其受教育年限要比非党员子弟高出1年以上。但是, 这个变量对其他七个学龄组的影响没有通过置信度为90%的显著性检验。
下面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上表中各因素随学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情况。截距项可以看作是在控制各背景因素的影响后,各学龄组可以受到的平均教育年数。随着学龄的推移,平均受教育年限是逐渐增加的,这表明教育扩展的程度。这其中也有三个例外,一个是49年前学龄组,其截距不具有显著性,而56~60学龄组的截距项大于后面一个学龄组。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认为,50~60年是我国教育体制形成时期,有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在影响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这个时期,对于教育扩展的政策经常是变动的,在对待大众教育的问题上,由于在经济发展和义理性要求之间存在过度的紧张,导致对如何普及大众教育,决策层存在意见分歧,因而使得教育扩展政策也时紧时松。这种情况自然会直接影响在这一阶段人们的教育获得水平。第三个例外是,77~80学龄组的截距项高于后面两个学龄组,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仍可以从教育政策方面来加以解释。77~80年学龄组基本上仍然受文革时期的教育制度的影响,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的分流功能尚未恢复(职业高中是80年以后才开始正式恢复的),教育指导思想仍然是从66年以前教育制度中抽离出来的、不合实际的意识形态与义理性要求,因此在这一时期学龄群体普遍受到了时间较长的学校教育。而随后所出现的教育政策实际上是在逐步转向精英教育,并对大众教育的步伐作出了相应的调整。当然,有一个事实也不能不引起注意,那就是改革最初几年中的经济刺激难免不会影响到人们对于接受教育的态度。同时,在86~90年学龄组中,有部分人(占该学龄组的2%)被调查时仍在学习, 并且根据生命历程的理论,他们接受后续教育的机会也要比前面各群体多,因此对于上述例外,我们尚不可作出后面两个学龄组的平均教育水平低于改革最初几年学龄组的判断。
与教育发展相类似的是,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城乡身份差异是随着学龄的推移而迅速下降的,并且一直保持着非常明显的连贯性。这无疑与整体的教育扩展政策密切相关。唯一的例外是56~60学龄组中的身份差异比其他学龄组都要小,其原因不难从58年大跃进时期大批农民进城来加以解释。
从父亲教育的影响系数来看,整体上,这个背景因素对教育获得影响无论是对哪个学龄组,都是十分显著的。不过比较而言,相对49年前的学龄组来说,父亲教育对50~76年各学龄组的影响依次渐降,而对77年以后各学龄群体,其影响又显著上升。
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都也是十分显著的。与父亲教育的影响不同的是,相对50~55学龄组,父亲职业地位对61~65学龄组的影响是显著提高的,ISEI值同样提高10分,对61~65学龄组的教育获得的意义,可望高于50~55学龄组1/5年[0.19=(0.044-0.025)*10]。而相对应的是,父亲教育水平提高1年,对61~65学龄组的来说, 平均要比50~55学龄组少受0.16年教育(-0.16=0.16-0.32)。接着我们对66~70、71~76、77~80几个学龄组进行比较,发现受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变化,与父亲教育的影响相比,大约要向后推移5 年的学龄时间。这种差异表明,当教育制度在59年左右趋于定型的时候,父亲教育的影响随后开始减弱,而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却依然明显地维持下来,直到在经历过“文革”初期的那几个学龄年组里,这种影响才有明显的降低,但是文革后期的学龄组与之相比,变化又很微弱。
从这种比较中,我们还发现,1950年以来,父亲教育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尽管也曾随教育制度的变化而出现过下降或上升的波动,但是其重要性意义一直是延续的。而父亲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不同,建国后,出现了两次较大跌宕,而这种跌宕又并不像大多数人所估计的那样,出现在解放初期或“文革”动乱之中,而是发生在战乱以及动乱结束后、制度基本定型时的学龄群体身上(56~60,77~80),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对此提出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首先,父亲教育和职业地位是子女可资利用但性质不同的两种先赋性资源。父亲教育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它可以通过家庭教育的形式(更精确地说,是家庭社会化的形式)对子女教育产生影响,所以外在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阻碍这种文化资本的影响意义还需要透过家庭这层屏障,这可能是父亲教育的影响能在政治运动频乃的社会中一直明显存在、延续的主要原因(注:在科尔曼报告提出之前,美国社会一直存在关于教育资源投入不平等的观点,认为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异是由于不同学校之间在师资、经费、设备以及课程设置等学校质量因素所造成的。科尔曼的研究本意想证明这一点,并为决策提供建议。但是科尔曼的分析却发现学校质量对学校之间的成绩差异并无多大影响,而家庭背景因素与学校内部学生成绩差异具有更高的相关,从而改变由此改变了人们对教育不平等的看法。后来著名的英国曼彻斯特调查(Manchester Survey )也得出了与科尔曼相同的结论,证明影响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在家庭环境,家庭因素的重要性二倍于社区和学校两项因素的总和。)。而社会经济地位这种因素不同,它作为一种职业地位,主要是通过运用职业所掌握的社会资源来对子女入学升学产生影响,从而最终影响到子女的教育获得。而职业地位及某种职业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职业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它所受到的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强烈,因此当制度出现重大的重新安排的时候,不同职业所掌握的权力、资源的分配也会随之出现重大调整,从而职业地位(抑或社会经济地位)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出现紊乱(注:当然,有人会用相反的证据来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事实上,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家庭内部,但是,以家庭为单位来组织个体生活的方式,从来没有中断过,只不过是部分的家庭功能被单位制度所替代了而已。),直到新的制度大体确定下来,职业地位的影响也会重新稳定下来。其次,在出现第一次跌宕时期,旧体制中的教育精英仍然作为一种潜流在新体制中延续了下来(注:这里所说的紊乱,是指在新制度定型初期,固定的SEI值对个体生活的意义会出现交接对错, 这也是一些人怀疑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分析变动社会的价值的原因所在。不过,只要一种新制度大体定型了,职业的声望地位在一个社会中仍然会回复原来的意义,并与从前职业地位之间保持一种高度的相关性。比较有关我国职业声望的一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不同时期的职业声望测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93以上,并且它们与国际职业声望地位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均在0.87以上。这表明职业地位的相似性在我国是基本存在的。正因如此,我们坚持使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分析问题。),他们所受的教育作为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尽管受到了波及,但并未完全中断。而就职业地位而言就不同了。在建国初期,职业地位的社会性评定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职业结构本身是稳定的。而在随后的一个时期中,一个突出的历史性事件是“大跃进”,在这个时期,大约有5000多万农民进城寻找职业,大致也是在同一个时期,这些人又被劝退回到农村,职业地位变化的幅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短暂时期内,职业地位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相对于发生职业变化的个人来讲,通过职业地位升迁所获得的资源还未及对个体生活产生影响,就又重新恢复到了原有的状态,这自然导致了职业地位与子女教育之间的相关联系变弱。第三,就第二次跌宕来讲,当时也是职业地位重新调整的重大时期。一方面,有很大一批在“文革”时期占据较好职业地位的人,在这个时期作为“第三种人”被清退,与职业相应的资源、权力也同时消失。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肇始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明显地触及了职业地位的相对变化。农村改革明显地增进了农民的利益,农民这种职业所掌握的各种资源与城市工人之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这样,对一个固定的职业地位指数而言,其所代表的职业资源的意义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因而变化过程中职业地位指数对个体生活的影响之间的相关联系会变弱甚或消失。然而当这种变化又因不可逆转的改革潮流而被加以制度化和定型的时候,它对个体生活的影响又会重新显现出来。
三、基本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建国以来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一直随着学龄的推移而稳步提高,并且随着教育的扩展,城市中个体教育获得结果上的不平等也逐步下降,而农村中学龄内部教育获得的不平等则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然而就是在这个教育发展和教育获得结果不平等下降的过程中,影响教育获得的先赋性因素,其影响作用依然很强烈,这可以从各回归方程的判定系数中可以看出。教育发展除了对性别、身份两个先赋性不平等因素具有较为明显的缓解作用外,对来自父亲教育、职业地位等家庭背景因素的不平等影响,并不具有我们预期那样的消解作用。相反,此类不平等因素的影响更多地与社会变迁、教育制度的演变相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