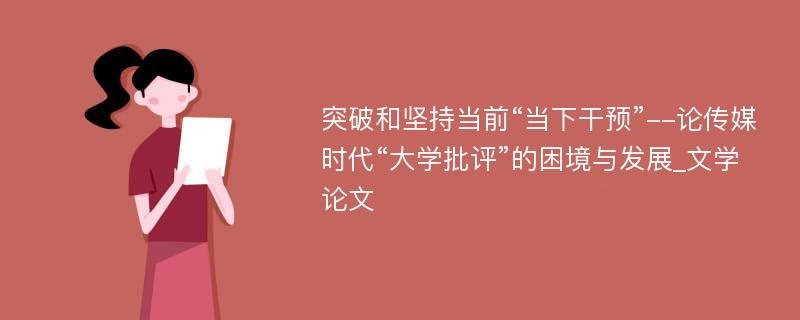
“介入当下”的突围与坚守——试论传媒时代“学院批评”的困境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困境论文,批评论文,传媒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院批评,依照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Albert Thibaudet)在《六说文学批评》中对文学批评模式的分类,属于以大学教授为批评主体的“专家批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院批评都是文学批评的主体,作为批评者的教授专家们不仅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而且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开阔的历史视野,从而在文学—批评中占有明显的优势甚至一度“称雄评坛”。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以及文学传播与接受机制的变化,囿于“自己的园地”的学院批评,日益与社会脱节而变得孤芳自赏不合时宜,甚至成为了僵化、学究气的代名词。“批评家尤其喜欢借用不同学术领域的理论来解释小说,甚至简单的叙述性的话都能解释的东西,偏偏用非常抽象的术语或者套话,挟学院所谓的权威优势来宰割作品。”①作家张大春在《小说稗类》中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很多作家对学院派批评的看法。而读者对于学院批评的不满更是比比皆是:“搬弄西方学术名词、话语呆板、枯燥、乏味、行文程式化、规整化、学究气浓厚、堆砌时髦的学术名词,却未击中要害,没有思想深度、没有锐气、没有鲜明的立场、没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没有对作品文本的针对性、行文空洞、沉闷。”②甚至很多学者也敏锐地指出其弊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③学院派批评一度四面楚歌,更为严峻的是,学院批评逐渐丧失了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与纷纭的文学现象的能力。文学批评的当下价值体现在对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的介入上,而恰恰在这方面,学院批评失去了“介入当下”的力量,对当下的作品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学院批评在文学批评中的失语使其不再具有曾经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而被日益边缘化。
与此同时,随着书籍、报纸、杂志、网络等信息传播渠道和载体的多元化,媒体全方位地介入了文学领域,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也使媒体批评应运而生。2000年3月18日,《文汇报》刊载了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和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两篇论文,“媒体批评”(“传媒批评”)首次作为学术专有名词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作为迥异于学院派批评的新型批评话语,媒体批评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日益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首先,媒体批评强调感受性。媒体批评中出现了批评主体泛化的情况,记者、编辑、作家、普通读者都成为了批评的主体。因此,媒体批评往往显得较为感性,多直感式、印象式的批评方式,没有引经据典却往往言之有物,为大众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和方式;没有晦涩的理论与繁琐的注解,却生动细腻从而更加贴近大众。其次是趣味性。媒体批评的接受对象大多是非专家的普通读者,因此较之纯学术阐释式的文学批评要求具有更强的可读性。因此,媒体批评在语言运用上往往机智幽默,生动活泼,作者写来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读者的阅读也是轻松惬意、酣畅淋漓。再次,媒体批评具有即时性的特点,这使得它对当下的作品能做出快速反应,不仅以其鲜活、灵敏的姿态与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借助大众传媒的优势得以广泛传播,而这些正是学院批评所欠缺或忽略的。
不过,媒体批评的弊端与不足也逐渐显现:一方面,文学批评要求批评者有一定的阅读储备与人文素养,而媒体批评主体的泛化,使撰写者往往缺乏专业的文学知识和人文素养而显得后劲不足;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产业化、市场化特征,使其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追求“眼球”效应,一些哗众取宠、变骇为习、强调娱乐至上的“酷评”、“恶评”堂而皇之地成为批评的主角。以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十作家批判书》(朱大可等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为例,其从撰写到出版、发行都打上了鲜明的商业炒作与市场运作的烙印。封面上赫然印着“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书中的标题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失禁的道德激情中作秀”、“道德的自慰与失禁”、“纵万般风情,肾亏依然”……如此“酷评”虽然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却因此丧失了文学批评的道德标准与理性批判的科学尺度,使得原本不乏真知灼见的文学批评湮没于刻薄恶俗、哗众取宠式的矫情浮夸中。这些都使文学批评溢出了正常轨道,偏离了对审美性、艺术性等文学价值的追求,而走进了媚俗的误区。
正是基于这样的批评现状,学院批评的突围显得尤为重要而呼之欲出。众声喧哗的批评环境尤其需要学院派以其深厚的学术积累和人文素养来树立标尺,以合格的“把关人”身份重塑批评的公信力与审美指向,自觉地承担起提升大众审美品位的责任,为文学批评的健康、有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反之,学院批评如果还固守于自己的园地,拒绝与时代、社会对话,终将失去与大众对话的能力和文化建设的引领功能。如今,文学批评的传媒化趋势已愈演愈烈,学院批评应与媒体批评互相激发和补充,从媒体批评的得失中借鉴反思,同时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当下文学批评的建设,共建健康有序的文学批评环境,如陈思和教授所指出的尽可能地把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转为社会文化的精神,从而使媒体、学术与文学批评共同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象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吉林出版集团最近推出的由刘中树、张学昕教授主编的“学院批评文库”显示出重要价值,嘈杂的时代并没有湮没批评者的声音,文库中所选二十位批评家既身处学院又活跃于文学现场,并以自身愈益坚实的批评实绩预示了具有本土经验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广阔前景,“重新寻找自己的姿态、批评立场、精神方位和话语方式,以重新确立批评的合法性”④。那么,从学院批评的长远发展来看,如何凭借其学院优势展开有效的文学批评,从而在杂沓纷呈的媒体批评中突围,这是摆在文学批评界与文艺理论界面前的重要问题。
就在我对“学院批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我看到媒体上关于赵本山“舌战”教授的相关报道,感慨良多。前不久,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赵本山携主创人员与二十多名来自文化界和影视界的专家学者见面。在研讨会进行过程中,原本声称要听批评和提醒、“抵抗力很强,非常能接受批评”的赵本山,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直言不讳地展开批评时,却大动肝火恶语相向,甚至将前者的发言视为“吃了就会死”的“毒药”,使研讨会一度陷入僵局。赵本山与曾庆瑞教授之间的冲突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一次激烈交锋,其背后凸现的正是学院派批评在“介入当下”的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三大障碍。
首先是学院批评如何与大众实现有效对话的问题。赵本山希望在研讨会上倾听学者教授的批评,以提升喜剧创作的态度和出发点应该说都是好的;而曾教授以学者的身份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本山喜剧的批评质疑以及对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期望,同样有理有据无可厚非。但是,二者之间却遗憾地无法形成有效的对话。令赵本山震怒的实际上是曾教授对《乡村爱情故事》的这段批评:“电视剧绕开真正的现实生活走,其实是一种伪现实主义。……本山应该抓住更广博、更深层的东西,敢于揭示现实生活矛盾、冲突,这样的作品才能流传下来,长留艺术史。……本山先生要追求更高尚的境界和更博大的情怀。当以追求高雅、崇高为目标和境界。”不难看出,曾教授的批评使用的是学术术语,而且由于会议发言的限制无法将立论完全展开,落到实处。可能正是“伪现实主义”、“高雅”、“崇高”这些标签化字眼,以及“应该怎样”的说教方式,让赵本山无法接受。他在随后的发言中强调“我想听一点善意的话,别玩深刻”。当然,深刻的并非就是不善意的,但对于赵本山这样的非学者来说,曾教授稍显“深刻”的形而上的学院批评话语显然是“曲高和寡”。从赵本山随后的回应来看,他并没有听懂曾教授使用的学术术语,把“生活的真实”理解成对农民实际生活的熟悉,从而重申自己立足农村题材的创作理念,将对话引向雅俗孰优孰劣的无谓之争。两人的发言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实际上没有形成有效的对话与交锋,这也是造成此次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展开“有效”的文学批评,这是当代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文学批评与大众的融合,当然不是降低批评的尺度以俯就大众的鉴赏水平,批评者追求的应是如何“提高”大众的鉴赏水平,而不是如何“适应”读者的鉴赏水平。但是在学理辨析的同时,也需要摒弃言不及物、自说自话的陋习,注意语言沟通的层次和逻辑。如批评家谢有顺所指出的:“就一种批评品质而言,以学院为基础的重视学理的话语方式,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但重学理,并非就拒绝读者,以堆砌术语为乐——这不过是学院批评中最没有创造性的一部分。”⑤批评者只有尝试使用普通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才能有效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出去。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文学批评为吸引读者眼球而刻意媚俗,跟风甚至炒作。
其次是学院批评如何坚守批评的独立品格问题。当学院派批评家从自己的园地中突围并积极地介入当下时,还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理性、自由的批评姿态,一个批评家应当诚实于自己的恭维,也要诚实于自己的揭露,“介入的批评”应当是一种生气勃勃、坚持理想、勇于承担,决不放弃批评的基本责任的姿态⑥。无论何时,作为批评者都要坚守其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破除“权威崇拜”与“市场崇拜”,不因外界的干扰而改变评论的尺度。
身处“爱面子”的社会氛围,在一片叫好声中发出“恶声”,既是批评者的真诚流露,更表现出其捍卫学术独立品格的勇气。正因如此,曾庆瑞教授虽然在研讨会中遭遇“批评发难者”的尴尬处境,但其切中肯綮的批评意见与仗义执言的批评风骨却收获了众多赞同。不少学者在随后的发言中就呼应了曾教授的观点,而根据凤凰网的民意调查,有66%的网友认同曾教授的批评。曾教授的批评建议不仅是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把脉开方,其“坚持自己的原则,看到不好的就要提出批评”的批评立场也提示广大批评者坚守文学批评的准则。以之反观当前的某些作品研讨会,往往开到最后就开成了“捧场会”,充斥其中的那些立足于吹捧的随声附和,以及不痛不痒敷衍塞责的批评,不仅使严肃的文学讨论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过场,也恶化了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
这就涉及本文要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即如何提升文学批评的公信力。批评者诚然有批评的权利,被批评者自然也有拒绝批评的权利,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赵本山在反驳中流露出的对专家教授们的轻蔑与不屑:“我也最恨那些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有文化的,而实际在误人子弟的一批所谓教授”,“有些专家和教授就是靠质疑和批评别人吃饭的,如果叫他们不批评别人,可能他们就没饭吃了”;那“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霸道:“农村到底什么样?您去没去过?您体验过吗?假如没有发言权的话,那考虑好再说”;以及对批评者充满挑衅羞辱的质疑:“不如您自己写个剧本,自己拍一个,假如您拍的那个收视率比这个高,我当时就给您跪下”。赵本山居高临下舌战教授,反映出的决不仅仅是被批评者要有胸襟和气度的问题,更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无情地暴露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
外在的诟病昭示的是内在的病灶,不得不承认,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影响力日益衰退,昔日担当着发掘作家的“伯乐”与人文精神的“守夜人”的双重身份的评论家们,在新时期却被庸俗化、功利化的文学批评败坏了声誉。一方面,随着学术的体制化发展,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岗位制度的完善,使学院派知识分子日益沦为学术的奴隶。知识分子们为了各种量化的指标而疲于应付,落入了为批评而批评的怪圈。研究者既无暇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认真研读,又无力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出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其批评往往隔靴搔痒,空洞无物,只剩下学术名词的堆砌,炮制出了大量没有创造力的学术垃圾。加上社会上流行的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等现象,文学批评变成没有风骨的附庸,甚至这都使得批评家们逐渐失去了大众对他们的期待与尊重。另一方面,从主观的角度看,学院知识分子在世俗的压力下主动放弃了对文学与文化的担当,自甘平庸地按照世俗的标准进行自我塑造。学术研究从精神世界的退场,精英意识的逐渐消退,实际上也是整个人文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尴尬处境。因此,文学批评公信力的提升与重塑,需要文学批评环境的净化以及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而文学批评者只是其中的一元,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而一味要求批评者如何如何,肩负其无法承受的重负,无疑是一种苛责。作为人文精英知识分子参与言说的重要方式之一,学院批评所面临的困境与发展说到底体现的是知识分子何为的深层命题,而一个健康的学术批评场的建构则需要几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张大春:《说稗》,《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陈竞、金莹:《学院批评:如何批评,怎么说话?》,载《文学报》2010年1月12日。
③刘中树、张学昕:《总序》,张学昕:《话语生活中的真相》,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页。
④朱自奋:《“学院批评”始终是中坚力量——访“学院批评文库”主编张学昕》,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1-26。
⑤⑥谢有顺:《如何批评,怎样说话?——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