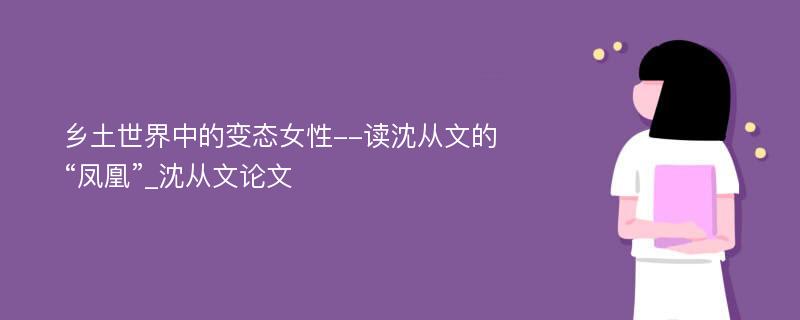
乡土世界中的变态女性——读沈从文《凤凰》所想到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凤凰论文,乡土论文,从文论文,女性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习惯沿着沈从文有意设定的抒情视角去领略其作品中湘西世界的“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冷不丁冒出《凤凰》这样一部提到湘西蛊婆、仙娘、落洞女子的与其他作品叙述内容不太谐调的事象的作品,也常不以为意,轻轻掠过和绕开,继续在叙事者散漫、优美、舒缓、从容的文字中感受湘西的“纯朴人性”,高唱对湘西世界“健康、优美、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的赞歌。
作为著名的“文体家”,沈从文的叙事态度可谓十分温和节制,其叙事语言也十分婉约隽永。然而正是这样的文字,掩盖了多少真实的东西!人们往往被作者叙事姿态中有意突出的平淡从容气度所打动、迷惑,而忘了深究作者内心中所包含的许多苦涩、辛酸、悲凉和沉痛!作者自己也曾说,伟大作品不定都有一滩血和一把泪。对于湘西的复杂深沉情感,使沈从文选取了这样一种叙事姿态和叙事方式:把深沉的思想、情感、爱憎和疼痛掩盖在夕阳的淡淡的余晖中。美,单从文字和叙事情感上看,没有人会觉得不美——湘西带着她特有的沉静和美展现在你的面前。然而,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美,总是愁人的”,在解读沈从文湘西世界的作品时,能否从作者的感叹中获取一些作者的真实意图呢?
一
按照人们通常的认识,原始民族或落后民族中是难以发生精神病和变态人格的。弗洛伊德关于“变态人格”的产生其前提是文化的高度发展,伴随文明的进步而出现了文化的负面影响:理性的高度发展抽空了人的感性欲望,压抑束缚了人的自然本性,致使人的自然本性在理性的千层重压下艰难地扭曲、萎缩。换句话说,是文化的发展把人置于文化的对立面,从而导致人的紧张与变态。弗洛依德的“人格构成”学说关于“变态人格”的理论对于现代文明环境下出现的神经症或精神疾病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说。
如此,人们也就很自然地推导出,在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地区或原始社会里,人的自然本性要比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更为舒展、自然,因为,理性尚未获得较高程度的充分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抽空人的感性,从而造成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抑。一个著名的观点是:“野蛮人很幸福。他们笑啊跳啊,一眨眼工夫就把烦恼忘到九霄云外。”(注:(美)托玛斯大林·A·巴斯之语。)他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们中不会产生精神病,不会产生变态人格,他们不需要精神病院。我们也常常以类似的观点来看待民族地区的文化与人群。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非洲大陆第一位精神病专家托马斯·阿迪奥耶·兰姆到他的祖国尼日利亚的农村进行了为期数十年的调查,以探索“幸福的野蛮人”的奥秘。他发现了许多精神病患者和患精神分裂症的人。事实上,他认为“非洲精神病患者的发病率和纽约相同。但是非洲人对精神失常的人司空见惯,这种对反常行为极强的忍受力,使得西方人对‘野蛮人’的不幸视而不见”(注:(美)托玛斯大林·A·巴斯之语。)。这就是说,在非洲这样一些原始落后民族中不是没有精神病和变态人格,而是人们对这些病症的确认存在问题。
同样,在民族地区(仅以湘西为例),蛊婆、仙娘、落洞女子这样一些非常态的人格形式流传了千余年,而且至今在社会中(主要在农村)仍见有大量这样的人的存在。她们的行为方式、家庭背景、精神情状及心理都表明她们不是简单的个别的某种特殊精神现象,相反,这是传统文化中带有普遍性的复杂的社会事实。
理论是抽象的,逻辑是无情的,但如果二者与事实发生矛盾,则二者都必然要回到事实。这是因为,其一,传统社会内部其文化也无时无刻不发生变动,只不过我们往往没有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之中,便往往以为这样的文化是贫乏的、静止的、缺少发展的,甚至以为这些地区“没有文化”。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这些地区不但有文化,而且非常丰富,并不断地发生变动。其二,我们认为,在民族地区(包括原始社会),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人同样可能被置于文化的对立面,“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摆脱神经机能症的困扰”(注:(美)托玛斯大林·A·巴斯之语。)。其三,不管在哪个地区、何种文化进程里,总可能会有些人被抛到文化的轨道之外,成为局外人、边缘人、异己人甚或“非人”一类的东西。在湘西,蛊婆、仙娘、落洞女子正是这种被抛到主流文化之外的“另类人”。
二
通常认为沈从文所描写的人的本能欲望受到压抑的那些人,往往为现代城市中有知识、有身份、受过文明熏陶的“文化人”,如《八骏图》、《如蕤》、《绅士的太太》等都有对这类人物的描写。而与此相对比,人们认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儿女的情欲人生,却都是“自然的”、“充满活力的”,认为沈从文通过湘西儿女的情欲人生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初初读到沈从文的作品往往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但随着阅读的深入,尤其对于作品中人物身份和性别的考察与总结以及对于湘西社会背景的了解与实地调查,这些印象便大大打了折扣。
其一,在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生命形式中,存在着人的主体意识的严重缺席,尤其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严重缺席。女性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处于受动状态的片面人。
人性的健全一方面包括人的自然属性的健全,体现为身体的健康和生命力的强旺(这点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完全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本质的方面,“人的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主体意识的高扬、独立个性的形成、创造性的自由而充分的展开是人之为人的最醒目的标志,也是优美健全人性的最显著的表现。而湘西地域的封闭性与地域文化的因袭保守使民众无法获得独立人格的建立和主体性的高扬。诸如丈夫(《丈夫》)、牛伯(《牛伯》)、藤老顺、老水手(《长河》)、萧萧(《萧萧》)、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桂枝(《小砦》)等,从他(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普通的湘西人满含顽愚和麻木的因袭和忍从,以及对自己命运表现出的异常的无能为力……应当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儿女的生命多停留在自然属性的层面上,而为许多人欣赏不已、赞叹不绝的“人性”也全体现在人的自然属性的展露上。如此情形,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是因为湘西社会环境无法为本能的升华提供多样的途径,无法为心理能量的移植提供足够的替代对象从而使得大部分心理能量被性欲等本能欲望消耗,无从上升到自我和超我那里,因而导致主体性的缺失。如此“人性”,又何谈“健全”呢?
作为众人津津乐道的湘西优美健康人性的经典代表翠翠,纵然对傩佑的爱情强烈到如痴如醉,梦里且为他的歌牵引“到对崖上折了一大把虎耳草”,也仍然如湘西众多其他女子一样,让这份炽热的爱情翻腾于内心而绝口不向心爱的人吐露一个字。小说的结局令人悲伤,一切都被置于一种不甚明了的期待之中。我们不能不为翠翠担心,如此无望的等待,主动权全在他人,如那个人向她表白,则情形对翠翠尚好,但如那个人永不表白,则翠翠将永远被置于一种无望的等待之中。再若那个人同哥哥天保一样因偶然事件而送了命,则翠翠的热情与悲伤必将同时汇聚于心,辗转反复,无从诉说而致情绪的积压。再设想翠翠的人生更苦一点,遭遇心中的爱却又屡屡失去,皆因不敢表达而失去(这样的人生在湘西并不鲜见),谁又能保证美丽聪明、敏感而多情的翠翠不至于因情感压力而致精神上的变态呢?
一个男子其心理能量尚可能主动地通过转移到情欲生活中而得到舒通缓和,而一个女子则是从社会到私生活中都发生了全面的根本性的退却。这大致可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在湘西,女性变态的人数要比男性多且普遍的原因。
其二,在所谓“两性开化的湘西性世界”中,性自由通常只是男人的性自由。这是因为在近代社会环境下的湘西,一方面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习俗中女子峦爱自由(婚前)的风尚被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中有关女子贞洁观念冲击、取代而失却,这固然是近代社会变革的成绩;另一方面,近代湘西时局动荡,武力干戈间或不断,军人成为地方整个的统治者。军人因职务关系,时常离开家庭外出,在外面取得对于妇女的经验,使女子贞洁道德观念增强,以维持他的性的独占情绪与事实。
所以,在湘西,“本地认为最丑的事无过于女子不贞,男子听妇女有外遇。否则的话,纵然是毫无关系的旁人亦可将这女子捉来光身游街,表示与众共弃”(《凤凰》),严重一点的,还可由族人按古老规矩将这女子“沉潭”(《巧秀与冬生》)。
女子中有自主追求性爱自由,大胆表白,说出自己的感受的,但这些女子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往往是以妓女的身份出现(如《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桃源与沅州》、《鸭窠围的夜》),她们是妓女,也只能是妓女了,要么就是女匪(如《女难》、《一个大王》),而一个“良家女子”是不应当主动表达自己的,更不应主动追求“性爱自由”。在这方面,沈从文自己也承认“地方习惯是女子在性行为方面的极端压制,成为最高的道德”(《凤凰)》。
所以,人们从妓女、水手、土匪(如弁目)等人的性爱生活中看到生命的“自然”与“力量”、“美”与“善”,但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湘西性爱生活吗?能代表湘西真实的大众人生吗?在近代湘西,倒是充满了女子如牛羊、猪狗而被掳、被掠、被奸污的事实。如“弁目”(《一个大王》)当山大王时,“烧房子、杀人……”是常事,在原版作品中,“……”省略部分赫然还有一句“奸淫妇女”;《上城里来的人》中,尽管作品的背景有所虚化,但仍可见到一支或军或匪的部队在(湘西)乡下奸淫掳掠的情形:“他们有刀,枪,小手枪,小手榴弹,他们是这样多,衣服一色。”他们抢掠了牛、羊、财物以后就轮到妇人们了,妇人也“如牛羊一样,被另外编成一队”,他们指着谁“说声‘来!’我们就过去一个”,无论大表嫂、“我”还是未出嫁的大表妹子,都无一幸免。《凤凰》中举到一个例子,旅长刘俊卿,夫人为一女子学校毕业,平时感情极好,但因夫人在校时一个女同学与她通信时说了一句语近男子的话,“嫁了人你就把我忘了”,遂引起刘怀疑,且在不问清事实的基础上就了结了夫人一条性命。这类悲剧在湘西常有。而“多数人只觉得死者可怜,因误会得到这样结果,可并不觉得军官行为成为问题。倘若女人当真过去一时还有一个情人,那这种处置,在当地人看来,简直是英雄所为了”。《凤凰》中还举有一例,某女子因对其小叔“有心”不遂,违背了古老法规,结果在一个特别仪式上引颈受戮,而众人“默然”,皆以为这种处罚是天经地义之行为。
如此森严和残暴地对于女子的掳取和控制,以至于沈从文自己也不能不感叹:“类乎这种事情还很多,都是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交缚不可分。”(《凤凰》)
女子所受压制既是如此严酷,则势必造成女子的精神压力,这压力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缓解办法的话,则容易转为病态。加上地方宗教、万物有灵,个人在性方面的压抑情绪与宗教情绪交缚混同,便容易产生人神错综的一种变态形式——落洞。“凡属落洞的女子,必眼睛光亮,性情纯和,聪明而美丽。平时贞静自处,情感热烈而不外露,转多幻想。间或出门,即以为某一时无意中从某处洞穴旁经过,为洞神一瞥见到,欢喜了她。因此更加爱独处,爱静坐,爱清洁,有时且会自言自语,常以为那个洞神之驾云乘虹前来看她。……等到家中人注意到这件事深为忧虑时,或正是病人在变态情绪中恋爱最为满足时。”(《凤凰》)
蛊婆的产生,也无不与社会中对女子的压力有关。放蛊多与仇怨有关,仇怨又多与男女事有关。换言之,在新欢旧爱得失之际,蛊可以应用作争夺工具或报复工具。蛊婆多“年老而穷,怨愤郁结,取报复形式方能排泄感情,故蛊婆所为,即近于报复”(《凤凰》)。年老而穷,失宠于男子,故怨愤郁结,取报复手段。报复的对象亦多为男子,典籍或民间传说中蛊婆多为丧夫之妇。如果深究蛊妇之现象何以能留传千年,或应与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的历史事实有关。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结束了女性盘踞社会要职的历史,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对妇女的“一夫”而对男人的“多妻”,男人们可以妻妾成群。虽然湘西由于生存条件险恶,须“男女并作”方可维系最简单生活,但并不妨碍婚姻之主动权在男子手中,男尊女卑的观念仍十分明显。如此不可更改的社会事实,女人惟一能做的只是“勉力巩固自己在家庭中的合法地位,承认男子的领导,小心翼翼地取悦于男子,避免‘始乱终弃’的潜在危机的随时发生,于是包括药物在内的媚术(巫术)应运而生,这便是‘蛊妇’存在的主要原因”,而一旦“媚术”不成,或因年老,或因为穷,最终失宠于男子,便转“媚术”为“报复”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三
既然变态人格是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异常或病态表现,那么就应当在弄清变态心理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和机理的基础上对其实施疗治。在西方社会,出现了许多有关变态人格治疗的尝试,如弗洛伊德的“分析疗治法”和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的“患者中心疗法”。前者意在通过自由联想,梦的分析、转移和移情、阐释和自我了解使病人自己意识到其无意识的症结所在,产生意识层次的领悟(insight),使病人了解症状的真实含义,便可使症状消失;后者则依靠患者进行自我探索、内省,发现和判断自我价值,调动自己的潜能,认识自己的问题,改变自己的症状。咨询者和治疗者只需为患者提供适宜的环境和创设良好的心理气氛,给病人以无条件关怀,对病人的病情表示理解,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治疗成功的关键不在治疗技巧而在于治疗者对患者的态度。不管这些方法是否得当和奏效,但都显示了西方学者及社会对病态人格的一种基本态度以及缓解和减少这种病症的努力。
作为沈从文,在表现变态人格的怪异荒诞之余,不可能不在内心产生对这种事象的反思、自省和追问,并在其作品中包蕴严肃、庄重的人生思考。
变态心理主体大多为弱势人群,在主流文化和历史规律面前,个体心理的“硬伤”往往会使之陷于尴尬境地。如蛊婆,往往为村人回避、厌恶,人们敬而远之,唾而骂之,严重一点的则驱而赶之。如沈从文述:“但某一时若迫不得已使同街孩子致死,或城中孩子因受蛊死去,好事者激起公愤,必把这个妇人捉去,放在大六月天酷日下晒太阳,名为‘晒草蛊’(生死概由天论)。或用别的更残忍方法惩治。这事官方从不过问。即或这妇人在私刑中死去,也不过问。”(《凤凰》)
可以见出,在湘西民族地区,社会缺乏对变态人格的疗治,相反,按传统习俗,社会倒加重了这种变态心理的发展,致使这类人的病症进一步加深,终不能自拔。她们到后来真的相信自己有致人于死的魔力,并以放蛊作为矫正心理、导泄郁情的良方。故一些蛊婆在遭到“晒草蛊”的惩处时,在烈日炙射下,面对围观者,反以为获得了一种“表现自我”的机遇和弥合心灵隐痛、排遣郁情的类似于受虐狂的心理上的快感,有板有眼地“招供出有多少魔力,施行过多少次,某时在某处蛊死谁,某地方某大树自焚也是她做的。在招供中且俨然得到了一种满足的快乐”(《凤凰》)。
再如人们对落洞女子的态度。一个女子之会把恋爱对象转移到神,是因为她在人间得不到爱,而如果人们想法让她感受到人间的爱,她又怎么会死死执迷于神之爱呢?因而沈从文尝试提出了他的办法即让这女子结婚,过一种正常的婚姻生活,则必然可以把女子从这可怜生活中救出。“可是照习惯这种为神所眷顾的女子,是无人愿意接回家中作媳妇的。家中人更想不到结婚是一种最好的法术和药物。因此末了终是一死”(《凤凰》)。
沈从文以其惯有的散淡的文字叙述了湘西三类同源异流的女性变态人格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境遇,文章没有严密的结构,也没有巧设的情节,不惊艳,不跌宕,与其说这是一部“艺术创作”,倒不如说这是一部真实的对于湘西社会的“历史的记录”。它提出了许多我们生活中存在却未曾被我们认识和认真反思的东西,诸如变态人格的历史文化致因问题、变态人格之于人性的摧残问题、变态人格命运的多重性问题、对变态人格的态度与疗治问题,以及文学作品应如何承载文化反思和生命自由的道德问题……一部《凤凰》,透过作者散淡的文字,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沉重和痼疾,也看到了一颗鲜活跳动的充满人文精神和人类关怀的“人类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