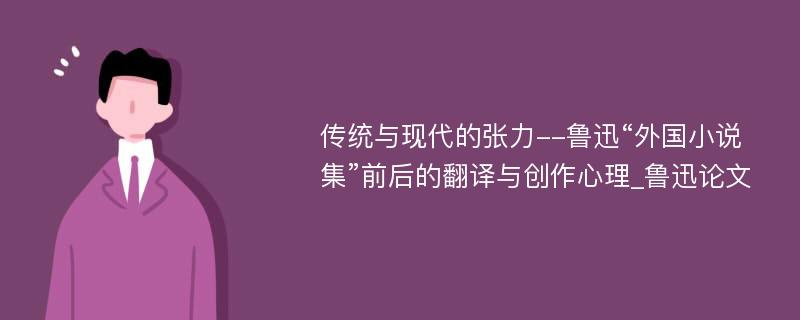
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域外小说集》前后鲁迅的翻译与创作心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域外论文,小说集论文,紧张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终其一生都是为了实现“改造社会”这个目标而不遗余力,其文学指向乃至终极追求,无一不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为目的。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和他的作家形象一起,交织成了鲁迅一生文学活动的两条主线。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丸山昇对于鲁迅翻译的价值曾有这样的评价:“对于留下的翻译数量堪比包括小说、杂感在内的创作的鲁迅来说,翻译恐怕和创造一样,在他内面的作用巨大。”① 在这其中,1909年出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集的单行本,从文本选择、翻译方法到思想内容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是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然而,作为在当时上下两本各只卖出了20多册的书来说,又不能不说是一座“失败”的界碑。时隔近一个世纪,《域外小说集》方才显现出它的读者群之众,影响面之广,对它的研究论述也充盈于各类学术书籍当中。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进一步发掘翻译与鲁迅创作心理的深层次关联。《域外小说集》本身,将作为本文论述的中心:由此向前,勾勒出鲁迅古奥与欧化相结合的翻译思想形成路径;由此推后,探寻鲁迅最终转向白话文创作以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原因。鲁迅身上体现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古代文人”与“现代斗士”两种身份的犹疑、转化和结合,则是贯穿全文的讨论重点和意旨所在。
一、引言
和大多数人一样,鲁迅早年东渡日本,试图学习先进的技术与思想,拯救摇摇欲坠的国家社稷。他此时的小说观,是科学救国、开启民智、寓教于乐等思想的杂糅,既有提升小说地位的成分,又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痕迹。鲁迅期望通过外国文学,实现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借他山之石以更新国人性格的愿望:“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谷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候,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海之微沤欤,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②。可以说,《域外小说集》初版和新版序是鲁迅吹起的借白话文小说进行启蒙的号角。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小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开拓、引导作用,“是件大事是一块里程碑,标志着新一代译才与新一代小说家的出现,……可以看作新一代翻译家的艺术宣言”③。
如果说林译小说使国人知道了外国也有小说,《域外小说集》则为中国小说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新形式,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及其与世界文学相融合开辟了门径。鲁迅在翻译国外小说时,把自己前所未有的文学体验忠实不二地转换成母语,创造了独特的翻译文体——使用古字古意翻译中国传统小说里完全没有的西方象征主义与心理描写,这是十分大胆的尝试。而这里的古,已经和林纾、严复的古不一样了,这是一种对先秦古汉语近乎偏执的使用,又是逐字逐句地对应外文的内容甚至是语法。这无疑是对文言文表达能力的一种极限试验。这包含了两个意思,一方面是《域外小说集》以先秦古汉语为基础工具,以欧化句法为路径忠实翻译,使得译本诘屈聱牙,甚或到了一种不可读的地步。正如鲁迅的弟子徐梵澄所说:“那译笔古奥的很,似乎是拟《庄子》或《列子》。以原著的思想及文采而论,实有类乎我国古代的‘子书’。宋五‘子’尚不在其列”④;另一方面,则是其内容站在时代的前列,力图开启新的文学风气,于是,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和新的审美趣味的“弱小民族”的小说进入了鲁迅的视野。
可以说《域外小说集》是融极古与极新于一炉,合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然而这两种元素却南辕北辙,甚至水火不容,使整个《域外小说集》从表达方式到内容主旨无不表现出此时的鲁迅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紧张感的最高点上。这里所谓的紧张感是鲁迅进入文学领域初始的一种状态。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则是出国之后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所带来的现代理念。处于思维两端的这两种思想在鲁迅期望以文学经世济国的追求中不断交织,对于两者都充分认同又使鲁迅对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忍卒失,努力对其对抗进行平衡。这种紧张感始终贯穿于鲁迅自留日至新文化运动之间,他既绝对坚信要用传统中国文言的表达方式,并且这种古与桐城派的严复、林纾不同,一定要做到极古;另一方面,他又引入西方的句法与思想,绝对秉持自己的“直译”原则,忠实于域外原文,甚至在译文中有意识的、有系统的输入欧化的标点符号,使翻译文体毫无疑问具有话语形态的现代性。学界一般认为,这一时期的鲁迅还是偏向传统的,作为受传统文化熏染的青年学者,他内在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并没有特别大的变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倘若将现代性理解为对传统与生俱来的怀疑、排斥和反叛,那么鲁迅一生都强烈体现了这种反叛,他坚信要吸收弱小民族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用来启迪国民。孙郁曾说:“在鲁迅选择的译本中,大多是反平庸的、具有冒险的与刺激的因素。他和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里挑选的作品,在根本点上是反中国传统的。有一点内倾和苦涩,内中压抑的激流,在默默地淌着。”⑤
“现代性是对‘它性’与变化的承诺,它的整个策略由以差异观念为基础的‘反传统的传统’所塑造。”⑥ 在《域外小说集》里,可以明显感觉到此时显现在鲁迅身上的传统与现代的剧烈摩擦。对于鲁迅来说,这两者都是他所最为认同的文学工具,他不能放弃任何一边,试图强硬地将两者捆绑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域外小说集》紧张感的顶峰。正如李欧梵所言:“他将全盘性偶然破坏主义看作一种思想义务,同时他对中国传统中某些特殊积极的因素有着具体确实的了解,这使得他意识中产生了痛苦的知识的矛盾和精神的紧张。”⑦
二、形成:传统文言的习得与现代思想的获取
对鲁迅1903年至1906年回国结婚之前的翻译语体进行一下梳理,会很明显地发现文白相杂的语言达到了可观的规模。《中国地质略论》采用文言,《月界旅行》以旧白话为主,《地底旅行》是文白杂糅,到《造人术》又回归到文言。可见,在翻译《域外小说集》之前,鲁迅已经尝试了多种翻译语体。科技论文因为具有学术性质,选择文言进行翻译,自然可以理解。而对于科幻小说,鲁迅似乎放下了这个原则,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科学小说的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关注点并非作为表达方式的文字本身,因而就翻译策略而言,必然是尽量迁就读者的阅读能力。
这个时候鲁迅身上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还并不强烈。虽然他已经开始尝试用现代的方法来作文,但发现并不容易之后又很随意地继续用起了古文。尤其是,他所译介的作品不管是何种题材,西方进步思想总是能通过附言或是改写而融入译文中。《月界旅行》本为科学幻想小说,但青年鲁迅在《辨言》中却赋予其鲜明的实用意义,将这种创作行为解释为“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如伊藤虎丸指出的,鲁迅的文章体现了“民族主义和自然科学的结合”的特征⑧。
但我们若由此就得出结论,说鲁迅在传统文体问题上是一个随便的人,那就错解鲁迅了。再看他这一时期的重要翻译作品《哀尘》,先秦典籍中的经典语汇语句被径直引用,与早期严复的翻译方法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时鲁迅的翻译态度,与之后《域外小说集》的直译风格,已经非常相近了。可见古雅直译的翻译方法并不是以《域外小说集》为肇始的,而是始终存在于鲁迅的传统翻译观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字学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锤炼以传统文言为工具的翻译手法,自然成了鲁迅下一步的努力方向。1908年,鲁迅在东京师从章太炎,学习训诂学知识。从1908年3月22日至10月31日,章太炎的授课内容涵盖了《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义疏》和《广雅疏证》,使“小学”成为鲁迅掌握古奥汉语的敲门砖。凭借它,鲁迅真正认识并找到了心目中的纯净语体道路。
章太炎对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最大影响主要在于先秦语体的采用和朴讷风格的确立。这也能够在鲁迅之后的多次回忆中得以坐实:他一再提到进行《域外小说集》等传统汉语翻译是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文章很“生涩”。⑨“此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但这集子里却一篇也没有。”⑩ 木山英雄认为:“从听讲《说文》到第二年出版‘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一、二集,更可以看到鲁迅和章炳麟的关系。”(11)章太炎在日讲学的1908-1909年与小说集的翻译完全吻合,可以想见在《域外小说集》翻译的方式方法上,章太炎很可能对周氏兄弟做过指导,这自然包括了先秦语体的采用。文体的古奥艰涩是章太炎行文的最大特色之一,鲁迅跟从其师行此文风,也可说是题中之义了。
除却独特的个性风格和博大精进的治学风范之外,章太炎对鲁迅的最大影响在于“依自不依他”的思维方式。鲁迅提倡复古和“别立新宗”,显然是受此影响。木山英雄称:“周氏兄弟在章氏的直接熏陶之下,与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一无与伦比的体验,为即将到来的新文学准备了不可替代的基础。”(12) 但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问题上,鲁迅的认识比章太炎还要早。在个人主义方面,章太炎提出“依自不依他”,推崇自尊自信,这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的核心论点“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13) 有着异曲同工的意味。就其活动来看,章太炎也可称是发扬个性于极致的国学大师,章氏《民报》的言论,颇具文化批判、“重估一切价值”的气概,这无疑对鲁迅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他们“个人主义”的共同思想来源便是尼采。
鲁迅初次“遇见”尼采,大概是赴日后在弘文学院学习时期,通过日文的介绍性书籍接触到了尼采的思想。周作人也佐证了鲁迅对尼采的关注:“鲁迅学了德文,可是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这里尼采可以算是一个例外,《察拉图斯忒拉如是说》一册多年保存在他书橱里,到了1920年左右,他还把那第一篇译出,发表在《新潮》杂志上面。”(14)
鲁迅直接读尼采的原著,应是他离开仙台到东京之后,阅读了《察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部分。1918年,在创作《狂人日记》的同时,他用文言文翻译了《察罗堵斯德罗绪言》10节中的前3节。1920年以白话译全,并作译者附记,这是唯一一部鲁迅用古文和白话文翻译两遍的书,可见鲁迅对于它的重视实非一般。可以说他此后创作《狂人日记》,与在日本期间对尼采的阅读不无关系。鲁迅立人的目的是为了立国,而尼采思想恰好可以用于对鲁迅的“立人”思想的建构,关于“精神界之战士”的思考则成为“立人”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层面。尼采希望人们反对“千人一面”、被社会奴役的虚假自我,而成为不受外力支配、不受群体约束的“超我”,这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共鸣。当时鲁迅的文艺思想就是希望用个人的生命意识和艺术精神向传统的旧的思维方式发出挑战。他认为,文学的自觉必须根源于和符合于人心的内在欲求,才能打动人心,不同凡响。也就是说,独创必须以人心为基本,才能触动人的生命意识。
然而,鲁迅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积极准备造就“精神界之战士”,另一方面,又绝望地发现,自己并不是理想中的精神界战士:“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15) 现代的先锋性与传统文化的因袭滞后水火不容,而旧有的文化体系具有强大的惰性,它总是试图消除、同化、磨灭异己的文化成分,这就使得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必然会有激烈的对峙、碰撞,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由此进一步强化。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代表,鲁迅与传统文化进行的搏斗是充满绝望悲观情绪的,他摆脱不了身上的传统性,摆脱不了“中间物”的状态,于是抗争成为“无地彷徨”,昭示了内心传统与现代的紧张。鲁迅虽然严厉地批判封建礼教对于民众的迫害,但“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依然潜藏于他的翻译和创作之中。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在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中达到了顶峰。
三、顶峰:先秦语体与“弱小民族文学”的结合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中体现了对于古文字的偏好,他的翻译以先秦语体为主,古奥程度甚至超过了“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严复。同时,《域外小说集》一反林纾等人的“归化”策略,而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把“弱小民族”的文学译介到中国,并系统的、有意识的采用了西式标点符号,音译了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至此,鲁迅的翻译文体生成方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而他的翻译文本面貌,文字语法却都比较古奥难懂,远未走出传统的藩篱。鲁迅处于传统和现代的交界处,使得《域外小说集》呈现出空前绝后的异质性。
在某种意义上,鲁迅不是个反传统主义者,更不是复古主义者,鲁迅的现代性正如汪晖所言,是“反传统的传统”。鲁迅对于传统的态度与桐城派的复古不可同日而语,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反传统。鲁迅的紧张感恰恰在于他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矛盾时的微妙态度。他始终想把现代因子以一种自然融合的方式融入传统的血液,但由于质素的极大差异,最终极难在短时间内杂糅而成。鲁迅的一切努力正是试图完成这样一项至难之业,而二者间始终不可调和的差异,直接导致了鲁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的紧张感。《域外小说集》是他这种尝试的顶峰,拒绝了简单的“传统”或是“反传统”,而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即“反传统的传统”,如黑格尔的“正反合”一样,鲁迅完成了他精神的敞开。
佐藤春夫曾这样描述鲁迅:“鲁迅是一个吸取了西方因素而又保持着东方特质的作家”。(16) 鲁迅在“精神”和“个性”方面,可以说是把握住了现代西方的本质。他彻底的批判精神是西方的,可他批判的对象则是深入骨髓的传统文化。我们明显感受到鲁迅作为个人对于传统的又恨又爱,而作为启蒙者,他必须压抑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古老和新潮在他内心缠绕纠结着,《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强烈地体现了这种矛盾和焦虑感。对于鲁迅而言,传统是他喜欢反复打量和批判的对象,然而又是永远割舍不掉的“十字架”。他的激愤,来源于对传统文化强烈失望和强烈希望的并存。《域外小说集》是在集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极度紧张之下而产生的文本,作为翻译著作,应该让大多数人读懂它,才能达到传播效果。然而鲁迅使用的古奥文字则拒斥了这种可能性。带着传统文人优越感的鲁迅和深感国家落后而寻求外部思想支援的鲁迅,二者混合成为一个巨大的矛盾共同体。
对于这极端古奥的文字,鲁迅在《域外小说集》1920年版序中也曾说道,“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屈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但这却是十年前的鲁迅极为看重的表达工具。这是一个旧的价值体系行将就木,新的价值尚未形成,核心价值真空的时代,又是一个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百家争鸣的时代。鲁迅所提倡的丰富中国文法的办法,不仅仅是输入外国的思想,还要装进“古”的句法中去。因而,如果说林译是明清古文的“欧化”改造,鲁迅的翻译则是对先秦文言的“欧化”改造。这一时期鲁迅翻译所使用的语言是中西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体系剧烈摩擦下的产物。另外这也是为了迎合目标读者群的偏好,当时士大夫阶层是中国的实际控制者,鲁迅看到改变中国的现状需要引进西学,提高民智,而其中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士大夫阶层对于世界的认识,技术上采用文言文的字词句法可以给他们的阅读带来亲近感,能比较容易地接受翻译话语所传达的思想。
以上所分析的鲁迅为何采用先秦语体的因素,都是结合时代背景给出的答案,未能冲破后来鲁迅在人们心中“文学战士”的形象。但抽离出种种外在因素,当回归到鲁迅自身来看这个问题时,答案的另一面则是,作为一个具有极端自我个性的翻译家,此时的鲁迅译本与其说是为普天之下的愚昧国民所译,不如说是为自己而译。对于早已熟习几载的先秦文体,鲁迅有着独特的认同感,促使他不断地用这样一种难以理解的语体进行翻译,而忘却了其本身用于传播先进思想的功利性。他偏执地认为只有这样一种经典的形式才能得以万世流传,也可见他对此译本的期待之高。同时,他也一厢情愿地把读者群设定为“卓特之士”,但最后的发行结果却无言地道出了真相:这毕竟只是一个太小众的译本,既无法让大多数国民读懂,也让那些对传统叶公好龙之士退避三舍。而真正能和鲁迅心灵相通的,便只剩却寥寥可数的几位。这确然说明了在《域外小说集》中先秦语体是作为鲁迅极度个人化的翻译方式而存在的。
鲁迅要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启蒙、个体与社会等等二难的选择中做出抉择,理性告诉他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传统文化的好坏不是泾渭分明,而是深刻勾连在一起的,这使他无处下手。出于传统文化殿军章太炎之门的鲁迅有他情感上割舍不掉的传统情怀。对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使鲁迅的创作具有出类拔萃的深刻性;而现代人文精神的学习和涵养,丰富了鲁迅个体生命的体验和反省。鲁迅文学创作所触及的现代人文精神和现代性的文学追求是深刻的、丰富的,但是作为历史存在的鲁迅是矛盾的、痛苦的。鲁迅善于解剖自己,然而,这种解剖带来的自我否定的痛苦又深深折磨着他。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面对势如水火的两方,鲁迅试图两全其美,于是产生了一个矛盾重重的文本。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文学道路上难以避免的失败,是一个伟大的失败,历史否弃了试图让极新潮和极古奥并存于一个文本当中,并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可能性,这从反面促成了鲁迅思想的现代转型。《域外小说集》是传统与现代双重文化语境剧烈交锋下的产物,它身上有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影子,是新的白话文出现的前奏。
在1930年代,鲁迅依然坚持“直译”,以推进语言改革为目标,主张通过直译“输入新的表现法”,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努力,现代汉语才得以丰富和发展。20年前鲁迅在《域外小说集》中播下的种子,终于得到了丰厚的收获。《域外小说集》成为鲁迅现代汉语文学语言、中国现代汉语文学语言乃至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
四、发展与消解:为何走上白话文之路
1909年,鲁迅由日本归国回到了家乡,一直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这段时期被称为是鲁迅的沉寂期,鲁迅自己也说是“沉入国民中”。不可否认,鲁迅这段时间确实有些颓废。寄予厚望的《域外小说集》在发行上惨遭滑铁卢,而更让他忧虑的则是,传统文言与现代白话这两种在他看来最为优秀的工具都未能被接受,那么到底使用何种手段才能让这个古老而落后的民族得以开启民智,更新思维呢?这成为困扰了鲁迅将近十年的问题。
蛰伏,正因为鲁迅深信选择的正确,还无法放弃其中任何一端。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依然焦灼着他,但是,比之译介《域外小说集》时期,两者的冲突已然减小。究其原因,传统文化作为表象成为鲁迅这一时期工作、研究包括生活方式的主线;而西方现代思想,则随他的创作一起“沉潜”了。需要格外注意的是,这种“沉潜”,不是消匿,不是出离,更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退让。而是,战斗已经不复为鲁迅的文学姿态,他也无必要将冲突的两个极端依然放在尖锐对立的同一体中。鲁迅对现代思想的理解已不单单是表面上的宣传和绍介。“沉潜”的状态,给了他更加平静而超脱的心境,去思考西方现代思想的真正用意,寻找其与中国现实的最佳融合点。可以说,青年时代过于激动的革命热火已经开始退却,转而变为更加成熟的对文化内质的思考。在这里,现代思考涌流在传统文体之下,依然困惑着鲁迅,但一显一隐的方式显然已经使对立所带来的紧张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对于传统文言,尽管有了《域外小说集》失败的例子,鲁迅依然矢志不移,这是他辛苦五六载才得以习得的利器,他并不会因此失败而放弃其合理性,相反,之后的近十年,这已完全成为他的写作语言。1914年他翻译的《海涅的诗》采用的是先秦骚体。鲁迅还鼓励周作人继续用朴讷的文言翻译近世小品,并四处张罗出版。《域外小说集》出版近10年,鲁迅的翻译文体没有“进化”。这一实验的巅峰见于鲁迅于1918年翻译的尼采名作《察罗堵斯德罗绪言》,译文愈发古奥,甚至连《域外小说集》中的西式标点符号都不见了踪影。他回归了传统的做法,每句用圈断句。在现代视域之下,他依然并不否定这种译介方式的恰当性。在当时白话文已经风起云涌的情况下,鲁迅依然抱着古文不放,看起来落伍得很。其实,鲁迅的文体选择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倘若说留日前期,鲁迅更多的是为他人翻译,那么此时此刻他是为自己而写,为将来的人而作。孙郁曾说:“我在读这些译著时有一个闪念,那时就想,与其说是译给中国读者的,不如说也是译给译者自己的吧。这些作品都带着沉郁、灰色而又不甘沉沦的悸动,有汩汩的流血,能一下子冲击到心灵深处。而这些译文里的思想也转化到先生同期的随笔、小说中”(17)。同尼采一样,鲁迅因超越这个时代太多而被世人误解,他索性古奥到底,达到了古奥与新潮的极致融合,这种尝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鲁迅这时的生活,是十年前甚至五年前所不可想象的。亲身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动荡,朝代更替,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景,称不上是绝望,也是惘顿与不知所终了。埋首故纸堆,按照他所倾心的嵇康式的传统隐士生活方式来麻醉自己,使传统既是聊以凭依的生活原料,又是超脱现实之外关注现实的思考方向。他骨子里淌着的仍是传统文人的血,不肯趋炎附势,干脆躲进小楼。但又和传统文人有所不同,以现代思想来改良除弊的想法在他心中依然鼓动着脉搏。
以传统文人生活为主线,而辅以对现代性问题内心思考的鲁迅,以一种看似平和的姿态调整着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表面上看似乎就此沉寂,从二十九到三十六岁,转眼间人生最为激越的几年已经过去,而这个“血荐轩辕”的革命战士却在故纸堆中沉默着。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轰轰烈烈,没有白话文学的如火如荼,他是不是就会一直这样沉寂下去,抄抄古籍,读读佛经了呢?好在历史没能给我们这样一个假设的机会,而是给了鲁迅真正拿笔做匕首的十八年。从1918年5月第一次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开始,直到逝世前的病榻上,这支如椽大笔再也没有停过。
令人好奇的是,一直以来如此坚定地把持着传统文言写作方式的鲁迅,为何就这样突然地、毫无征兆地转向了白话文,并且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便再无可出其右者了?笔者认为,鲁迅并不是无准备的。沉寂多年,心中的革命火焰积蓄了太多能量,只等着一个出口。而他也不是一开始便知道这就是自己最终会一直走下去的路,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依然彼此对抗,而鲁迅,则在这种紧张感的平衡中,最终确立了他的文学道路。
其实,鲁迅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认同白话文运动的。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文化启蒙思想刺激着古旧的社会,鲁迅却似乎一直不为所动。1917年正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即便是在1918年,给许寿裳的信中仍说:“当枯坐牙门中时,怀想弥苦”(18)。鲁迅最终接受了钱玄同的建议,开始了白话文小说的创作,其推动力正在于一直盘桓于内心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这一时期,他虽然以辑录校勘古籍佛经为主,但对于现代性的思考并未停止。尤其是,他的视域已从传统文化精英的“卓特之士”,逐渐转向了年轻的一代:从儿童,到青年,关注他们的心理、教育。也许是这一段的工作让他真正看见了作为同僚的中年以后的“精英”们到底是受毒害太久,太冥顽不化,鲁迅也有些失却信心了。而从青年身上,年界三十七的中年鲁迅则看见了十年前自己期望思想革命的强大愿望。传统文体,对于孤守古籍近十年,却依然未能被大众所接受,甚至读者越来越少的鲁迅来说,尽管是其秉持的信念,却也是给自己设立的一道藩篱,即使他自己未必认同。多年的古文阅读,带给鲁迅的并不是传统士大夫的封建礼义,而是由于比旁人更深刻地了解“吃人礼教”所产生的极度痛恨。封建痼疾如鲠在喉,不得不拔,现代思想已然成熟,即将喷涌而出。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在这时又一次凸现出来,但在鲁迅已经为它蛰伏近十年之久的1918年,传统还未能压倒现代。面对《新青年》的邀请,他愿意,哪怕只是试一试,用浅白的语言告诉人们一些自己经历过的世态炎凉,以及饱览了古籍经书之后的肺腑之声。由此,由文言转向白话,也是一件瓜熟蒂落的事了。
由文言转向白话,确实不能说是鲁迅有预谋的处心积虑之举,我更愿意把它称为是一次“意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鲁迅为什么偏偏选择“狂人”这个形象作为他开山之作的主角?又为什么要用日记这种叙述角度?我认为这恰恰是鲁迅当时并未想要积极投入白话文运动的例证。首先,“狂人”作为一名精神病患者,他的思维是片段式的,疯狂的,这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现代性的思维,他始终与当下抽离、断裂,同时却能旁观者清地指出这个满嘴仁德礼义的社会吃人的本质。在这样一种疯狂与清醒只差一步之遥的状态中,他的喊叫能给沉睡已久的人们带来醍醐灌顶的效果。同时,从文体上说,《狂人日记》这样的形式能给作者一个理由:为什么他要使用白话文的理由。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的人的内心独白,断然是不会用传统教育精英人士才会使用的文言的。这本来就是一个俗人给其他俗人所讲的俗白的故事,但其中包含的,却是几千年无人敢发的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抨击——鲁迅用这种文体,将他的读者对象转移了,从“卓特之士”转移为真正生活在底层的大众。鲁迅没有用议论文,或其他正式的文体来揭露这种吃人的礼教,而借狂人之口用白话文来揭示他深沉的用意,这其实是鲁迅给自己的一个用白话文进行创作的理由。
另一方面,自回国后,政治上的受挫使他转向古籍佛经,而心境也由这条路走向更寂寞和悲哀。时日渐逝,在寂寞与悲哀的啃啮中,鲁迅为自己营造出一个压抑的狭暗空间。这是鲁迅一己的生命体验,其中更大的成分是隐喻着鲁迅对自我生命被压迫的绝望总结。他用铁屋子做比,对这个社会那些沉睡的人,也对自己,都抱着怀疑乃至绝望。但鲁迅之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对于这种怀疑本身也进行了怀疑:“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19) 反抗绝望,成为了鲁迅确立自我存在感的一种形式。鲁迅决定身手一试,他应该很难料想到能取得成功,所以仍有所保留。正如上文中不断提到的一样,这种文体是鲁迅给自己的一个理由,一旦未能成功,他大可以把白话创作仅仅作为“狂人”的“日记”这样一种多重限定下的语体特例,而非他的完全转向。而为什么一定要找这样一个理由,则正是因为鲁迅极强的个性,“依自不依他”的精神,一切社会的旁人的因素都不能阻挡他,唯一能阻挡他的就是自己。在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之下,鲁迅给自己设定了文学发展模式,而这也恰恰成为了他尝试各种文体的限制。这次鲁迅给自己找的理由成为一个通孔,疏导了内心深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使之变得富有弹性,同时也形成了安全的创作心理。它的大获成功,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使鲁迅看到了希望。紧张感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减弱,鲁迅给自己设定的枷锁渐次打开,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白话小说写作。虽然一开始的作品,包括《孔乙己》、《阿Q正传》依然选取底层人物作为叙述主体,但一当这一创作渐渐成熟(20),鲁迅便很快开始了其他文体的尝试——从1918年9月第五卷第三号的《随感录二十五》开始,鲁迅已经在《新青年》不定期发表短评了。
但决不能说传统与现代的紧张感就此消失了。事实上,这已经构成了鲁迅创作心理运行机制的一部分。只是在这次的减弱之后,紧张感的内部发生了倒置。与此前十年不同的是,现代思想在鲁迅意识中深藏多年之后,终于以一种更成熟的姿态浮出了水面,并成为之后鲁迅成长为一名文学战士时手握的犀利武器。而传统思想所起的作用,则是指导这个武器指向何处的指针——鲁迅的大家风范便在这里,他后来虽然反对他人读古书,怕受了里面仁义礼教的迫害,但自己却浸淫其中多年,早已进得来出得去,游刃有余。他像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封建传统中那些落后的虚妄的死脉,当他以笔为刃之时,便能干净利落地直捣利害之处,让其瞬间土崩瓦解。而另一方面,魏晋名士的奔逸绝尘,侠骨柔情,却早已深入骨髓,成为了他的生活状态。这也就是鲁迅的高人之处,他不像胡适等人把白话新文学仅仅建立在一个基础不牢的语体转变之上,他除旧的同时又能以最精当的方式保留传统的精髓,使之化入现代于无形。
注释:
① 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②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③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8页。
④ 徐梵澄:《苏鲁支语录·缀言》,[德]尼采著,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页。
⑤(17) 孙郁:《译介之魂》,《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4期,第14页。
⑥ 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见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⑦ 乐黛云主编:《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⑧ 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4页。
⑨ 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⑩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1)(12) 木山英雄著,赵京华编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209页。
(13)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14)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页。
(15)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440页。
(16) 郭光:《我所见到的鲁迅——在中央大学文学研究会鲁迅悼念会报告》,见《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第224页。
(18) 鲁迅:《180104 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7页。
(19)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8页。
(20) 其实鲁迅的白话文从第一篇《狂人日记》就已达到了前人无人能企及的成熟高峰,但这里的成熟更多是指鲁迅自身对这一文体创作的内心接纳。
标签:鲁迅论文; 文学论文; 章太炎论文; 域外小说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周氏兄弟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白话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