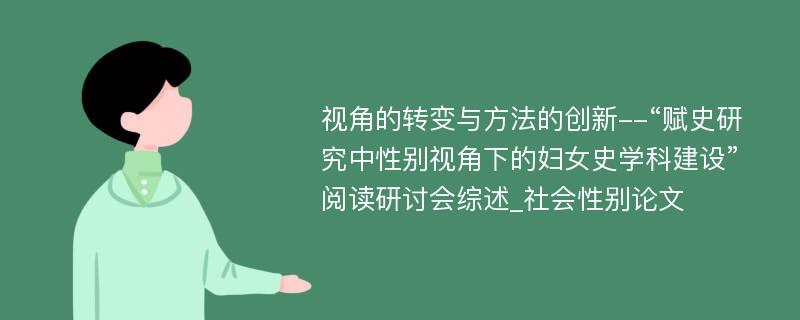
视角转换和方法革新: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妇女史学科建设读书研讨班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讨班论文,史学论文,视角论文,妇女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妇女学学科建设:意义·概念·运作
当今的妇女史研究,如果脱离国际妇女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单纯把它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甚至仅把妇女史视为社会史的一支),无疑是一种视野和方法上的缺憾。所以,这次读书研讨班在讨论妇女史学科建设之前,首先讨论了妇女学学科的建设问题。
1.意义
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教育和学科体系对其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延续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妇女研究到目前为止仍多属于“妇女问题”为主的课题、项目研究,这类研究的关注点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解释或改变妇女的具体现实处境上,从而忽略了在各个学科领域内与传统知识结构进行对话和挑战这一更有战略意义的知识重构工作。于是,国内妇女研究领域出现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妇女问题研究和发展项目如火如荼,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的妇女学学科建设冷冷清清,妇女学的学科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与我们教育学术体制、妇女研究者自身对妇女学学科建设意义的认识、概念的理解和具体运作缺乏认真探讨有关。
在读书研讨中,通过总结国内外妇女学科建设的经验,大家认识到:妇女学学科建设,就是要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体制内建立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学术研究体制,系统地开设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课程,培养从事这一领域研究、教学和全社会需要的人才,而这也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发展开辟新的局面:(1 )为现实的妇女问题和发展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理论和学科背景框架;(2 )有计划有系统地培养妇女研究、教育、工作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3 )通过在各个学科领域内的学术对话和批判去改造传统的知识体系,从而建立起新的性别文化。
2.概念与运作
在与妇女学科建设有关的概念和如何运作方面,与会者围绕如下问题展开讨论:
(1)妇女研究和妇女学·女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
80年代中期从国外传来的Women's Studies 被汉译为“妇女研究”,而准确的译法应是“妇女学”。国外“妇女学中心”的任务是开设课程从事研究,而另设有为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妇女研究中心”机构。有的学者认为要发展中国的妇女学,当务之急应把“妇女学”从作为问题和课题的“妇女研究”中相对分离出来,使之进入科学领域,走上课堂。有人认为“妇女”这个词政治色彩太强,建议不用“妇女学”而用“女性学”;但同时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说“女性”一词易将妇女“生物学化”,掉进本质主义陷阱;有的学者提出还是称作“妇女与社会性别学”(Women & Gender's Studies)较好,其理由是现在“社会性别”逐渐成为一个分析范畴,适用于所有学科,“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这一称谓可以避免淹没妇女主体。在国外,一些大学纷纷以“妇女与社会性别中心(所、系)”命名,就反映了这种趋势。
(2)多学科与跨学科
与会者就美国学者玛丽莲·鲍克塞的新著《当妇女提出问题的时候》(1998)和她的文章《不守规矩的知识:妇女学与学科问题》(1999)、《重新规划大学蓝图:培养妇女研究博士的前景》(1998)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她提出的妇女学追求的两个目标:“同时参与学科和跨越界限”深表认同;但目前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还没有更多的积累。许多学者认为分学科地用社会性别理论清理、挑战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打通既有学科分割,改变既有的认知模式,建立一种以社会性别视角联系多种范畴视角的新的认知方式,既是紧迫的任务,又是可以同步进行的(郑新蓉)。在具体的运作上,有学者提出,在原有学科中设置专门的分支学科或专业方向是符合国情的做法。比如,可以在历史学科中建立妇女史分支,或在传统的断代史和专门史中招收妇女史方向的研究生;在理论框架和方法上引进新视角新方法,挑战原来的学科,从边缘进入主流(郑永福、邓小南)。有的学者还认为,挑战本身就是革新、颠覆和改造,经过一个个学科加入社会性别视角的反思,注入新的活力,就会发现原有的知识缺陷,就会进行多种整合和综合,实现知识的交融和知识与人生的融合(周华山、郑新蓉)。
二、妇女史研究回顾:历程·理论·方法·范例
在明确了妇女学概念范畴的基础上,读书研讨班集中探讨了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先是对国内外以往研究的发展历程、主要理论贡献和论争、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范例进行研讨。
1.历程:妇女史——社会性别史——差异的历史
从70年代美国妇女史学家勒纳在《妇女史的挑战》中,将妇女史定义为“剥离出被传统史学掩蔽的部分”, “重建女性历史的努力”(1976),到80年代末斯科特提出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的范畴”(1988),以及鲍克在《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争论的多个方面》中正式提出“要用包含社会性别的方法去做通史,……妇女史就是出色的社会性别史”的目标(1989),直到90年代斯科特主编《女性主义与历史》提出“差异”(difference)的重要性,指出社会性别不是唯一的分析范畴,除了性别以外,还要注意因为种族、族裔、阶级、年龄等身份形成的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权力差异同样是重要的(1996)……可以看出国外妇女史理论的发展和变化。这一发展和变化反映了妇女史研究理论的深化和研究实践的深入。苏珊·维特妮的《透过社会性别的棱镜看历史》一文评介的四部妇女史著作,给大家提供了将社会性别与其它范畴(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信仰、文化等)结合以及将“差异”(种族、阶级、国家、性别等)范畴运用于妇女史研究的新范本。
2.理论焦点:社会性别与生物学·社会性别中立话语·实证研究与实证主义
围绕妇女史发展过程中的几个核心理论问题,与会者在讨论中的辩诘争论十分激烈。将“社会性别”的概念引进历史研究的时候,人们不自觉地受到“生物学”观点的影响。生物学观点认为,无论从社会性方面提出何等激进的“男女平等”的口号,生物性上的男女自然差异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妇女的自然性就是生育、抚养孩子、管理家务;另外,还有“男人味”和“女人味”——这不但赋予是一种“天职”和“天性”,也暗含了一种“价值判断”,成为像种族歧视一样的性别歧视的理论根据。正如鲍克指出的:将“社会性别”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性别”的分离及“生物决定论”都妨害用社会性别视角去研究历史,应该“用一种综合的方法使用社会性别,而不是生物学”的眼光来了解被文化构建的女人和男人的生活及这些生活以外的东西。鲍克的论述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示。有学者指出,生物学的性别观点是从本世纪初引进的,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如建构“女人是柔弱的”、心理特点如何如何的理论,宣扬女性的天性是母性,而且作为科学来宣教,这对妇女史研究也难免有所影响——人们关注的不是贤妻良母,就是后妃美女名妓(王政等)。鉴于生物学观点在我国的巨大市场和顽强定势,在今后妇女史研究中,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将此清理、克服。
与此相关,不少人担心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是否会偏离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在读书研讨中,大家发现大量事例、研究范例证明没有“纯客观”和绝对超然、中立的价值存在:即使所谓“纯科学”的生物学,在19世纪时也曾以“女人的子宫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如果用脑过度,子宫就衰竭了,就不能生育了”的理论阻止妇女接受高等教育。至于历史学和其它门类的人文社会科学,从来就更不是客观和中立的。这是因为:其一,历史现象和史实不是“透明性(transparency)”的。所谓“透明性”,即,过去的历史研究者认为历史事实、现象是可见的,通过挖掘史料可使其凸现。后结构主义史学家就提出:历史现象和史实不是“透明”的、人人看来都是一样清晰的物体;看到的史料也不一定是真实的记录,所有记载的文本都是一种“再表现(representation)”,都是经过过滤和加工的。其二,即使是个人经验的真实,在复述的时候,也有主体的影响。所谓“经验”,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就是一个主体被建构的过程”,所以经验也不是空白、客观和中性的。其三,即使发掘了某件历史事实,对它的阐释可能会因史学家的不同立场和观点而异。所以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学者不承认绝对客观、中立,他们总是首先把自己的身份、学术立场、使用的方法、要达到的目的告诉大家,而不以真理、客观、公正自命自居。有的学者指出,国外妇女史学者很早就警惕在社会性别逐渐作为史学界普遍使用的分析范畴时,有人会用一种“社会性别中立话语”来“软化妇女史的挑战”(鲍克,1989)。因为这种“中立话语”容易导致妇女的淹没。当我们担心用“女性视角”看历史容易走极端时,这里既有误区,也有焦虑:比如有人混淆“女性视角”与“社会性别视角”的区别,以为的“女性视角”不过是以女性的利益、情绪发声,这是缺乏对社会性别理论了解所致;一些女性学者的焦虑乃是缘于学界中男性霸权的压力,担心自己得不到学界认同;另外,混淆实证研究与实证主义的界限也是担心原因之一。周华山指出,在方法论方面,国内社科界对西方19世纪兴起的实证主义依然非常崇拜和流行。实证主义有两个理论基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即相信理性是绝对的,经验是客观的,具有理性的人能“发现”“客观”的“真理”。其实“发现”也是在建构,“经验”也是主体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实证主义在国外已受到很大的挑战。当然,反对实证主义并不是不要实证研究,而是不但要尽量挖掘已有的材料,更要挖掘过去不曾注意的、被掩蔽了的下属群体的声音,比如口述史的运用。
3.方法:口述——如何听声音
读书研讨班重点阅读和讨论了关于口述史在妇女史方面的运用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外妇女史学者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读书班的讨论集中在如何听到叙述者的声音和怎样对待声音——前者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权力关系问题,后者是怎样分析和处理材料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识到访谈者和叙述者建立真正尊重平等互动关系的重要性;访谈者要学会“倾听”,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控制访谈对象。在对待声音方面,正如美国妇女口述史两位资深学者所说:“采访者作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的解释加到她所听到的内容中,必须忠实于叙述者对她们自己生活的阐释,竭尽全力做到从她们的角度来理解。”(苏珊·阿密提支和舍纳·格拉克,1998)妇女口述史不仅要做到由妇女来做研究、做有关妇女的研究和为妇女而研究(to do researchby,about and for women),而且要与妇女一起研究(with women)。 旅美学者鲍晓兰为这次研讨活动专门撰写了文章,谈她在写《美国纽约华裔制衣女工》博士论文时进行口述访谈的经验体会。她从传统认为纽约华人社区家庭稳定、而她又从人口统计中看出妇女自杀率高的矛盾中开始了跨国界的口述访谈和资料找寻,特别是在广东侨乡的访问,使她弄清了事情真相:由于美国早期移民法中的阶级性——排斥华人劳工不许他们的妻子移民,所以当年留在侨乡的妇女不但要经受“寡居”的寂寞、父权制性别制度的压迫,还得在家庭中撑着“整个天”;而70年代的女性新移民也“继承”了前辈女性的“遗产”,在华人家庭社区中,一些妇女因处于男权压抑并无处求助而寻短见。这项研究不但填补了史料,改变了观念,而且也改写了历史。(《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意义、方法和思考》)王政、王金玲、杜芳琴、臧健、韩嘉玲等还分别介绍了关于访谈“五四”新女性、当代女性性工作者、农村妇女和西北女童及海峡两岸流动婚姻中的女性并进行口述研究的经验体会。
4.范例:中国妇女史研究成果简介
这次读书研讨班精心选择了海外发表的最新研究成果,以读书报告的形式介绍其内容和背景,然后集体分析讨论;有关中文的专著和文章,在研讨期间也做了推荐、引介和较充分的交流,收到很好的效果。苏珊·曼的《珍贵的记录:漫长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妇女》、王政的新作《中国启蒙时期的妇女——口述和文本的历史》、贺萧的《危险的愉悦——二十世纪上海的卖淫业和现代性》和夏洛特的《旺盛的“阴”——中国医学史中的社会性别:960—1685》等四本书被重点介绍和讨论。 这四本书共同的特点是:运用了社会性别理论切入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妇女生活;运用了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挑战“东方主义”的学术话语,力图表现中国性别文化的正面价值和妇女的能动性。苏珊·曼的书改变了以往汉学家在前近代史研究中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中心的视角,而是以社会性别关系和妇女活动为中心,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下,重新解读传统的史料——以大量的妇女的文本(尤其创作的诗词)为主,还有男人的写作(为妇女作的传记、诔文、地方志以及政府文告、表章奏议等),描绘出盛清时期江南地区妇女在文艺写作、娱乐行业、劳动工作和宗教活动等方面多彩的生活画卷,表现了妇女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王政的书的最大创新是把文本的和口述的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现了“五四”前后中国早期的女权主义的兴起和第一代知识女性参与女权运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作者用文本材料重构男性知识精英建构起来的女权主义话语,用“五四”新女性的口述展现新的女性主体。本书的意义正如美国的妇女史专家高彦颐的评论所指出的:“不仅仅局限在它发现了妇女的历史,而且在于它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重新改写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历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贺萧的著作是其十年潜心研究的力作,这既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性别史,又是社会史和思想史,也是用后结构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来研究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关系的开创性著作。该书最重要的成就是在理论和方法上的贡献:作者考察、剖析了关于妓女的包括游乐指南、传闻佚事、肖像、诗歌、小报流言、官方管理文件、警察审讯记录、对拐卖妇女的报道、中外改革者对卖淫问题的讨论、医生对性病的调查报告……各种材料,进而在分析这些历史的“杂音”中揭示各种社会力量在不同时期对卖淫的不同界定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复杂的意义。夏洛特的新作为中国读者揭开了崭新的妇女史研究领域:她将医学这一看似纯科学、纯生物学的领域与社会性别联系起来,具有开拓意义。作者检视宋明时代七百年间丰富的妇科学传统,利用医学典籍、通俗手册、历史个案等材料,揭示了有关妇女生育、月经、妊娠、临产、性和妇科学话语的演进。书中还论述了“阴阳”概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认为不能简单地将古代两性关系理解为男尊女卑,至少在妇科学中看不出来这种单一的倾向。这是妇女研究一个崭新的领域,也启发我们去进行开拓。
三、接轨·本土化·创新
经过读书与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中引入社会性别的概念,打破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和方法的单一性,尽快推出更多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推进妇女史学科建设。事实上,我国的妇女史研究历程并不短,最近十几年也出版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著作。郑永福专门撰文并在会上宣讲的《50年来的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就指出,近代妇女史的研究成果累累,据统计近20年就出版专著和教材上百种,论文逾千篇。吕美颐、郑永福合撰的《中国妇女运动1848—1919》、《中国近代妇女生活》、罗苏文的《妇女与近代中国社会》以及妇联系统集体编写的《中国妇女运动史》等就是重要的代表作。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由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制作的《中国二十世纪女性史》系列电视片。该片将资料与研究、学术与传媒结合起来,代表近现代妇女史研究和普及的最新成果,在会上受到一致好评。在民族妇女史的研究方面,定宜庄在会上介绍了自己最新研究成果《满族妇女的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和《最后的记忆》。这两本书将传统的文献考辨和口述的方法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和重写历史上都有很大的突破,特别是后者,是专门采访满族老年妇女的经历和历史记忆的记录,具有“填补”和“抢救”历史的双重意义。古代妇女史的研究一直延续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虽然出版了像《唐代妇女》、《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等著作,但还是以描述为主,缺少理论框架体系的支撑。可喜的是最近有了从社会性别角度探讨妇女史理论的开端,如杜芳琴等人的《中国妇女史学科化建设的理论思考》,对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形成、构造及妇女在其中身份地位的复杂性做了揭示,该文也在会上做了交流。当然,真正将中国妇女史赋予社会性别,还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并且,妇女史的研究也应是兼容的,多种理论方法应该各逞千秋。
在会上,对如何“接轨”,即在继承我国优良的妇女史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的理论和方法并进一步创新,展开热烈讨论。有学者提出应该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史学”,“以我为主”;有学者提出老一辈史学家潜心到国外学习历史学理论方法,回到中国消化后创立了中国历史学,今天也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创建中国的妇女史学(齐文颍)。还有学者说,“本土化”的提法是多余的,因为人在中国或是中国人在用国外有用的理论方法做研究时,本身就是在“本土化”了,过度地强调本土的东西实际就是拒绝纳入世界学术潮流。但无论如何,大家还是对社会性别理论、口述史方法形成了共识,不少人当时就被引发了许多新的思路,如中国家族制度、宋明理学、徽商和晋商、女工、医学和妇女等诸多议题,都找到了社会性别视角审视的切入点。还有的学者建议尽快进行有关妇女史基础性工作。大家坚信,在扎实工作和研究的基础上,勾勒中国妇女史、重写中国通史将不是渺远的理想。
这次读书研讨班是由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办,来自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妇女史学者王政、鲍晓兰博士主持、出席或给予了各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