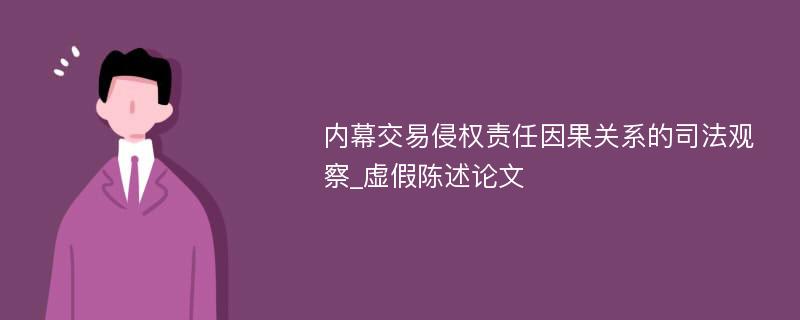
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司法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果关系论文,内幕论文,司法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10月,被称为我国首起正式判决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陈祖灵诉潘海深案①——以原告的败诉而告终。该判决指出:被告潘海深与原告陈祖灵在本案诉讼前并不相识,更没有对后者进行与内幕信息有关大唐电信股票的交易作过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指导或提示、建议;同时,被告内幕交易行为并未对股价产生影响,因此,原告买入大唐电信股票并非受到被告的引导,其投资损失与被告的内幕交易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②2012年12月,轰动一时的投资者诉黄光裕内幕交易③民事赔偿案,在历经两年三次开庭之后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原告吴屹峰、李岩的投资损失与被告内幕交易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此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④2014年8月5日,备受关注的投资者诉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光大证券)内幕交易⑤民事赔偿案正式开庭审理,其中因果关系问题仍然是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原告主张,光大证券的内幕交易与大盘下跌具有直接因果关系,所有的投资者都有权起诉。而光大证券认为,造成大盘下跌的原因是其他投资者的跟风追涨,与光大证券没有关系。⑥ 由此可见,在我国法院审理的为数不多的几起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中,因果关系均是决定投资者能否追偿成功的关键因素。根据我国民商法学界通说,内幕交易属于证券侵权行为,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即属于侵权责任,⑦所以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因果关系即指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那么,何谓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为何其能够决定投资者能否获得损害赔偿?究竟内幕交易与投资者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又应当如何予以具体证明?对于这些涉及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根本性问题,我国《证券法》均未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导致学理观点的严重分歧甚至完全对立:有学者提出内幕交易与投资者损失之间通常没有因果关系,后者系由市场风险所致;⑧但多数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是证明困难,对此可以通过法律推定方式解决。⑨两派观点相持不下势必会对内幕交易司法实践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妨碍投资者成功索赔。 因果关系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内幕交易侵权司法实践所面临的主要难题,而既有的理论学说,无论肯定论抑或否定论,均不具有充分说服力,因为其皆建立在对内幕交易行为错误定性的基础之上。对此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不公平交易行为——来对内幕交易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进而深入剖析其与投资者损失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应当如何具体认定这种因果关系。为确保建议方案的切实可行,本文将详细考察资本市场法制先进法域对此的问题的解决思路及措施,全面比较其逻辑与实效的优劣,最终构建契合内幕交易侵权行为本质的因果关系司法认定规则。 除引言和结论外,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因果关系的内涵切入,详细介绍其在内幕交易侵权责任领域的认定困难,并具体分析一般欺诈侵权和证券欺诈侵权相关规则难以适用的原因。第二部分深入剖析既有肯定论未能提供有效解释的根源所在,并从不公平交易行为的视角论证内幕交易与投资者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进而从根本上反驳了否定论。第三部分阐述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具体认定,提出理论与实践并重、投资者与内幕人利益兼顾的内幕交易侵权诉讼适格原告界定规则。 一、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困境 侵权责任因果关系是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前因后果的联系(causal connection),它是确定侵权责任归属与责任范围的必要条件。⑩广义上,侵权责任因果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事实因果关系(factual causation),或称责任成立因果关系;以及法律因果关系(legal causation),或称责任范围因果关系。(11)前者是指被告侵权行为在事实上是否对原告权益被侵害的发生具有原因力,后者解决的是被告应当对原告因权益受侵害而遭受的损失中的哪些负赔偿责任的问题。上述分类方式同样适用于证券侵权领域,只不过被美国法赋予了新的称谓:交易因果关系(transaction causation)和损失因果关系(loss causation)。以内幕交易侵权责任为例,前者要求证明被告的内幕交易行为导致了原告进行相关证券交易而遭受损失;后者则要求证明原告的投资损失是被告的内幕交易行为直接的、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结果。(12)交易因果关系解决的是肇因问题,即在与原告进行亏损证券交易相关的诸多事实中,确定内幕交易行为是否与其存在客观上的联系。因此,交易因果关系决定着内幕交易侵权责任是否成立,属于责任的构成要件。而损失因果关系则是在责任成立后,确定被告应当在多大范围内做出赔偿。所以,损失因果关系属于损害赔偿而非责任构成要件的范畴。(13)本文认为,作为内幕交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不仅直接决定着适格原告的范围,即只有能够证明因果关系的投资者才有资格提起侵权赔偿之诉;更关涉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法律政策倾向,例如肯定因果关系的法域通常明确规定适格原告的直接诉权,而否定的法域则拒绝赋予投资者这一权利。(14)因此,这种因果关系可以说是内幕交易侵权责任成立的前提,乃至整个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制度构建的基石,故而也成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因果关系的认定被认为是所有法律责任理论及司法适用中最为复杂和艰难的课题,一般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已属不易,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更是难上加难。(15)其根源即在于,因内幕交易行为本身的特殊性而导致其因果关系的认定不仅不同于一般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甚至与虚假陈述和操纵市场等证券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认定也存在差异,在后者场合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对内幕交易却无用武之地。 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由美国判例法首先确立。1947年宾夕法尼亚州东区法院对于首起内幕交易侵权私人诉讼案件的原告做出有利判决,主审法官Kirkpatrick在判决中指出:《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b)条和证券交易委员会10b-5规则等反欺诈条款适用于在购买他人所持公司股票时未能披露其基于职务而获悉的、可能对交易对手的判断产生重大影响的董事和高管。(16)由此就将内幕交易纳入证券欺诈(securities fraud)法律制度的涵摄范围之内。而美国的证券欺诈法律制度又深深植根于侵权法的欺诈制度——为使他人依其陈述(representation)行事(如订立合同)而故意向他人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表示——二者的构成要件均为:①存在虚假陈述行为;②涉及事实具有重大性;③被告明知陈述的虚假且引诱原告据此行事;④原告合理信赖被告的虚假陈述并依此行事;⑤原告遭受损失。(17)其中第④项信赖要件被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是关于因果关系的要求,其在被告的欺诈行为和原告的受损交易之间建立了必然联系。(18)因此,在美国司法实务中,对于内幕交易因果关系要件的认定即转化为对信赖要件的认定。 然而,由于内幕交易行为与一般欺诈行为存在实质区别,对内幕交易行为的信赖也无法等同于对一般欺诈行为的信赖,因而对于后者的认定方法难以类推适用于前者。对于一般欺诈的信赖要件,美国法院通常采取的认定标准是“若无,则不”规则(but for rule),即通过概率上的优势来判定被告的欺诈行为是否对原告进行受损行为产生了原因力。(19)详言之:若无被告的欺诈行为,则原告不会进行受损行为,则原告进行受损行为是信赖被告欺诈的结果,二者因果关系得以证成。反之,若无被告的欺诈行为,原告仍会进行受损行为,则原告进行受损行为并不是信赖被告欺诈的结果,二者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原告只需证明被告实施了欺诈行为,并且该欺诈所涉事实具有重大性,即能够对理性人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即完成了对信赖要件的举证责任。这种认定方法背后的司法逻辑是,由于被告欺诈行为所涉事实能够对理性人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那么据此进行相关行为的原告即对欺诈产生了信赖。 上述关于一般欺诈侵权信赖的认定方法,对于积极欺诈行为,如错误陈述或误导——无论发生在交易双方直接接触的私下交易场合,还是出现于匿名的集中交易市场中——均能达致理想的司法效果。然而一旦将其引入到内幕交易领域,就会产生诸多的适用困惑。不同于积极欺诈行为,内幕交易通常是秘密进行的,行为人并没有作出任何陈述,其他投资者并非基于信赖内幕交易人的欺诈行为而作出投资决定的,进而难以在内幕交易行为与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决定之间建立因果关联。(20)故此,为有效破解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难题,仍须借助于其他的论证工具,对此主要有两种理论可供选择。 其一,信赖推定理论(presumption of reliance theory)。此一理论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2年的Affiliated Ute Citizens v.United States案所确立,该案涉及的是被告隐瞒重大信息的虚假陈述侵权。判决指出:在涉及未披露重大信息的案件中,原告无须证明其对被告陈述的积极信赖,只要能够证明未披露的信息具有重大性,即可推定信赖要件的成立。该理论所蕴含的司法逻辑是,如果被告披露了其所隐瞒的重大信息,则原告就不会进行相关证券交易,或至少不会以实际呈现的方式进行。而被告则可以反证原告事实上并未信赖其虚假陈述行为——如即使其披露了该重大信息,原告仍将从事相同的交易——以推翻信赖推定。(21)或许正是看到了内幕交易与隐瞒或者遗漏重大信息的消极虚假陈述在未披露信息方面的相似性,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曾援引Affiliated案的判决来认定内幕交易案中的因果关系。其观点为:内幕交易案同样可以适用信赖推定理论,只要被告未披露内幕信息而进行交易,并且原告如果知道该信息就不会作出原来的投资决定,就可以证明内幕交易与原告投资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22)但第二巡回法院的上述认定方法却遭到了第六巡回法院的反对,后者在1976年案中指出:虚假陈述案中的被告对原告负有积极的信息披露义务,其隐瞒重大信息即违反了这一义务,因此可以推定原告进行受损证券交易是被告故意诱导的结果。而在内幕交易案中,被告不但没有披露信息的义务,而且负有绝对义务保证公司重大信息处于秘密状态,因此难以得出是被告诱导原告进行了受损交易的结论。(23)有鉴于内幕交易和虚假陈述的上述区别,在认定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时类推适用信赖理论并不恰当。 其二,欺诈市场理论(fraud on the market theory)。为解决证券投资者在非人格化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中信赖欺诈行为的认定难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88年在涉及积极虚假陈述的Basic Inc.v.Levinson案中确认了这一新的理论。其要义为:在一个有效资本市场中,证券的市场价格能够及时反映发行公司的一切公开信息(真实的和虚假的),而理性投资者则是基于对市场价格的信赖而作出投资决定的。由于被告披露的虚假信息使市场价格发生扭曲,可以说是对整个证券市场和所有投资者的欺诈。因此,对于原告而言,其只要能够证明系基于信赖市场价格而作出的投资决定,法律即推定其投资决定与虚假陈述之间的信赖关系成立,即使其事实上并不知道该虚假陈述的存在。而被告则可证明原告事实上没有信赖虚假陈述——如原告事先知道虚假陈述的存在或者无论被告是否实施虚假陈述,原告都会进行该交易等——来推翻因果关系推定。(24)欺诈市场理论基于积极虚假陈述能够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不当影响这一特质,从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和真相暴露之间这段期间内进行交易的事实中,推定出该交易是受到虚假陈述诱导的结论,由此合理地证成了虚假陈述案中的因果关系谜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即曾借鉴了这一理论,(25)故此理论和实务界均有观点主张对于内幕交易案因果关系的认定同样可以适用该理论。(26)然而,这种观点却忽视了这一理论适用的前提条件和内幕交易与虚假陈述的实质区别。根据美国法,欺诈市场理论适用的前提是欺诈行为能够对证券市场价格产生不正当影响,(27)无论是作出不实性、误导性陈述虚假陈述行为,还是通过连续买卖、对敲、洗售等手段实施的操纵市场行为均符合这一要求,但内幕交易则不然。为不引起他人注意,内幕交易人往往会采取多次小量交易的方式,来隐藏其行为对证券市场产生的信号。(28)因此,内幕交易通常并不会造成证券市场价格的显著波动,那些主张受到内幕交易损害的投资者如何能说其交易行为受到了被内幕交易扭曲的市场价格的诱导呢?可见,运用欺诈市场理论来认定内幕交易案因果关系仍然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 上述种种认定困境,甚至引发了对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本身合理性的质疑。例如,美国联邦第六巡回法院即曾指出:内幕交易案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原告能够证明其系被告的交易对手(买入被告的股票或将股票卖给被告),或者其投资决定受到被告的影响;但在非人格化的证券市场上,普通投资者并不知道内幕交易的存在,其投资决定是基于所掌握的而作出的,即使没有内幕交易行为,其仍然会作出相同的投资决定,并且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要承担信息不完备而带来的投资风险,因此内幕交易行为并未改变投资者的风险预期和投资决定,因果关系并不存在。(29)同样出于对内幕交易案中的因果关系的怀疑,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至今未曾规定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学理一般认为,如果投资者可依民法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进行索赔,但须承担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从既有的判决结果来看,尚无一起案件的原告举证能够获得法院的认可。(30)从中或可窥探出日本司法届对于内幕交易案因果关系的否认态度。与日本类似,欧盟关于内幕交易的指令也未规定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并且也未有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对此作出规定。(31)我国也有学者对内幕交易案的因果关系持否定观点,其依据主要为,内幕交易行为没有误导证券价格,也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和交易决策;而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主要来自市场信息风险,与内幕交易之间通常没有因果关系。(32)内幕交易案因果关系否定论的实质在于,通过论证投资者进行的受损交易与内幕交易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得出内幕交易不会造成投资者个人利益损害的结论,进而否定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的合理性。 二、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证成 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困难及合理性质疑,无疑给司法实践带来巨大挑战,更对投资者索赔构成严重障碍。为有效破解投资者的举证难题,从根本上消除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功能实现的主要障碍,美国国会于1988年通过《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行法》(Insider Trading and Securities Fraud Enforcement Act of 1988),为提起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投资者创设了明示诉权(express cause of action),即“任何人因知悉内幕信息并进行相关证券交易而违反本法及其项下规则的,在任何有管辖权法院提起的诉讼中,应当对与其在同一时间就同类证券从事相反交易的任何人承担赔偿责任。”(33)这就免除了投资者就其买卖证券与内幕交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只要其能够证明是内幕交易人的同时交易者(contemporaneous traders),法律就直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34)这种在立法中直接推定因果关系成立的做法被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所效仿。新加坡《证券和期货法》(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第234条赋予内幕交易人的同时交易者就其损失提起诉讼的权利,而无须证明因果关系。(35)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1第2项亦规定:“内幕交易人应当对当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负赔偿责任”。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则规定,内幕交易人的交易相对人(those in contractual privity with the insider)享有请求民事赔偿的诉权。(36) 应当承认,由立法直接认可特定投资者的损失与内幕交易具有因果关系,确实能够切实减轻投资者的举证负担,便利内幕交易民事诉讼的实施,但其理论依据却值得商榷。正如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Clark所言,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认定的“若无,则不”规则是一种建立在假设事实(counterfactual)基础上的反证过程,意味着“若没有侵权行为,则受损行为不会发生”的推理。(37)美国第二巡回法院认为该规则在内幕交易侵权中的适当标准(proper test)应当是,“如果被告向原告披露了内幕信息,原告是否会受到该信息的影响,从而采取与其实际行动不同的行动”。据此标准,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通过——被告交易时未披露对于作为理性投资者的原告来说可能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内幕信息——这一事实即可推定成立。(38)显然,这种认定标准建立在如下反证推理之上,即原告作为一名理性投资者如果在进行交易之前获知了内幕信息,就必然会改变其实际做出的决定。然而,这种反证推理本身却存在着严重缺陷,因为其是以原告有权知悉内幕信息为前提的,但这一前提并不成立。正如因果关系否定论者所言,证券法中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在维护市场有效性和保护公司商业秘密、控制披露成本以及防止各类“未成熟”或“软信息”误导市场之间维持平衡,因此并不要求上市公司必须“立即”或披露“所有”重大信息,投资者也就无权要求持有人披露尚未达到披露条件的内幕信息。(39)以投资者对内幕信息的知情权为前提的认定理论的合理性的确值得质疑,但这是否意味着否定论的依据就一定无懈可击,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必然无法证成呢?对此仍须予以深入探讨。 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否定论认为,“纯粹的内幕交易既无人为创造供求,又无人为交易价格,只是内幕交易人利用了市场的价格反应机制,捷足先登而已,其违法了市场公平理念,未必对其他投资者造成实质损害”。(40)根据这种观点,内幕交易与投资者的受损交易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会给投资者造成损害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由于经验、时间和途径的差别,不同投资者掌握的公司信息不对称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基于证券交易“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规律,无论内幕信息持有人是否参与交易,处于劣势的投资者仍然会亏损,这是正常的市场信息不对称风险。(41)其二,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价格并无重大影响,(42)内幕交易人的交易对手不可能知道他是在和内幕人进行交易,他实际上(无论如何)都会以同样的价格与其他非内幕人投资者进行同样的交易,(43)因此,内幕交易没有改变投资者的交易决策。(44)不难发现,否定论的构建基础实际上是信息公开原则,即“有关证券发行、交易的信息要依法如实披露、充分披露、持续披露,让投资者在充分了解真实情况的基础上自行作出投资判断”,(45)并以内幕交易没有违反公开原则为由否认其与投资者损失的因果关系。其具体论证逻辑为:内幕交易人并非法定信息披露主体,其所利用的信息又通常为公司保密信息,因此没有侵害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信息的知情权,与其进行交易的投资者所受损失是应当承担的市场风险,与内幕交易无关。 本文认为,无论是否定论还是既有的肯定论,在立论基础方面均存在缺陷,即二者都是从投资者信息知情权保护的角度出发,认为“内幕人利用其特殊地位获得其他投资者所无法获得的内幕信息,残酷地践踏了其他投资者的平等知情权”;(46)同时通过与虚假陈述进行类比,来论证内幕交易是否对投资者构成欺诈。遵循这种思维模式,肯定论者类推适用了虚假陈述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即如果投资者事先知道了真实信息(或内幕信息),必然不会进行已实际作出的受损交易;而否定论者则以内幕交易案中的投资者并不享有与虚假陈述案投资者相同的知情权进行反驳,进而得出内幕交易与投资者受损交易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据此,似乎否定论比肯定论更为合理,然而,从投资者知情权角度来分析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本身却不合理。因为内幕交易从其本质来看,应当属于违反证券法中公平原则的不公平交易行为,(47)而非与虚假陈述相似的欺诈行为。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投资者能够公平的参与竞争,公平的面对机会和风险”,(48)而内幕交易则是通过不公平的机会获得内幕信息的市场参与者,对其他不知情的参与者所实施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完全违背了公平原则,具有内在的不公平性。对此,否定论者亦予以承认。(49)更为关键的是,内幕交易人凭借其不公平的信息优势以求获利或者避损,必将减少其他投资者的获利机会,因为在亏损概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盈利的概率则因内幕交易的出现而减少,其投资的净回报率因而随之降低。(50)所以,内幕交易侵害的是投资者的公平交易权而非知情权。 在厘定了内幕交易的不公平交易行为性质之后,其与投资者受损交易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难题即可迎刃而解。既有的肯定论之所以在论证过程中遭遇重重困境,就是因为陷入了欺诈行为的思维定势:一方面将内幕交易界定为欺诈行为,类推虚假陈述的规则来认定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却无法解释内幕交易如何能像虚假陈述一样侵害了投资者知情权。这也是其颇受否定论诟病的根源所在。相反,如果从不公平交易角度来分析内幕交易,上述困惑则不复存在,因为内幕交易属于侵害投资者公平交易权的不公平交易行为,那么其与投资者受损交易之间因果关系认定的“若无,则不”规则,即应解释为“如果投资者事先知道与其进行相反交易的投资者持有内幕信息,是否会改变已实际作出的交易决策”。显然,对于任何理性的投资者而言,都可以很容易地满足这一认定规则。如此,否定论认为内幕交易不会造成投资者损害的两点理由也就均不成立,内幕交易与投资者受损交易在事实上存在因果关系因而得以证成。具体依据如下: 第一,内幕交易根本不属于正常市场风险。否定论认为即使内幕人没有参与交易,那些与内幕人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同样会亏损,因为所掌握的信息并没有改变,这也是证券市场风险的必然逻辑。(51)应当承认,证券投资的确具有较高风险,由于专业知识、投资经验、时间精力甚至身份地位等方面差别而导致的信息不均等,是投资者之间盈亏分化的主要原因。并且,根据证券交易“零和博弈”规律,在排除证券本身的利润分配或公司资产增值的因素后,所有投入市场的资源配置只存在主体间的移转,其资源总量并没有发生变化,卖方的亏损或者盈利就是买方相对应的盈利或者亏损。(52)但是,对于受损投资者而言,其反向交易者是否公平竞争,将会对其投资预期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如果盈利投资者的盈利来自于对以公开信息的技术分析与理解判断,对此,不仅法律予以保护,亏损投资者也应当会欣然接受,从而将自己的损失归结为投资风险。反之,如果盈利来自于凭借特殊身份地位而取得的信息优势,则会遭到普遍反对和蔑视,亏损者也不会将其损失归结为市场风险,反而会认为系内幕交易人的“盗窃”和“掠夺”所致。正如美国国会在制定《1984年内幕交易制裁法》(Insider Trading Sanction Act of 1984)时所述:“滥用其他投资者无法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而企及的信息优势是不公平的,并与投资公众对于所有参与者均能遵循相同规则竞争的诚实、公平的证券市场的合法预期不一致。”(53)因此,“尽管证券市场中的信息差异(informational disparity)不可避免,但投资者却不愿意在允许内幕交易存在的市场中进行冒险”,(54)将内幕交易的反向投资者的亏损归结为市场风险的观点难以成立。 第二,内幕交易必然影响投资者的交易决策。否定论者证明内幕交易与投资者受损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第二点理由是,内幕交易没有误导证券价格,不会影响投资者的交易决策。正如前文所述,这一理由是用来否定“欺诈市场理论”在内幕交易案中的适用效力的,其立论基础仍是内幕交易不属于侵害投资者知情权的欺诈行为,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属于不公平交易行为的内幕交易不会影响投资者的交易决策。对此问题的回答,仍须诉诸因果关系认定的“若无,则不”规则,在事实假设的基础上进行反证推理,以判断内幕交易是否构成投资者决定进行受损交易的一个实质因素。同时,由于内幕交易的相对人系由交易系统随机匹配的、不能事先预料和控制,因此,所有与内幕人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均有可能成为其交易相对人;而内幕交易人的所得又直接对应于其交易相对人的损失,所以,可能因内幕交易而受损的投资者是其全部反向交易者。此时“若无,则不”规则需要进行的假设推理则应转化为:如果受损投资者事先知道其反向交易者中有人持有内幕信息,是否会改变已实际作出的交易决策。鉴于内幕交易人通常(如果不是绝对)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这就意味着其反向交易者极有可能受损,而理性投资者则是厌恶风险的(risk averse),当其知道反向交易者中存在内幕人时,必然会改变其原来的交易决策,而不是甘愿沦为内幕交易的牺牲品。对此,就连反对者也予以承认,例如Carny教授在论证反向交易者的受损与内幕交易不存在因果关系时即指出,“假如内幕交易人反向交易者能够察觉出内幕交易的存在,那么理性的做法应当是予以‘模仿’(emulate)并分享内幕人至少一部分的预期所得,而非自甘冒险继续从事反向交易。”(55)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内幕交易能够对反向交易者的决策产生实质影响。 综上,本文认为,内幕交易的实质是通过侵害与其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公平交易权来获取非法收益,而这些对内幕信息不知情的投资者通常是基于对证券市场公平性和诚信性的信赖而进行投资的,如果其知道反向交易者中存在内幕人,必然不会作出导致其受损的交易决策。既然证券市场中任何与内幕人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在事实上均有可能受到内幕交易的侵害,那么内幕交易与投资者受损交易之间“若无,则不”的因果关系即得以证成。当然,在具体的诉讼中,被告可以举证“原告即使知道交易对手为内幕人也仍会进行同样交易”来推翻因果关系,但这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内幕交易能够造成投资者损害的事实。因此,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制度具备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坚实的事实基础。 三、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的具体认定 本文第二部分从宏观层面论证了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确立的依据,即内幕交易能够对其反向交易投资者造成损害,二者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这是否意味着所有与内幕人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无论其在内幕交易之前或之后交易——都会受到内幕交易的侵害呢?根据交易常理显然不是。那么,究竟与内幕人进行反向交易的哪些投资者受到了实际损害呢?这就涉及在具体的内幕交易侵权案件中,如何认定特定投资者的受损交易与内幕交易存在因果关系,即适格原告的认定问题。对此,由于我国立法未予明确,导致学理解释的分歧,例如,有认为内幕交易的真正受害人只能是与内幕人进行交易的对方当事人;(56)有认为将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适格原告界定为与内幕人在同一天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这样界定不仅具有合理性,更具可操作性;(57)还有认为从内幕交易开始至内幕信息被市场完全吸收这段期间内的反向交易者均有权起诉。(58)本文认为,我国学者对于内幕交易侵权诉讼适格原告理解的分歧,亦是域外在此问题上“交易相对人”(privity traders approach)模式和“同期交易人”(contemporaneous traders approach)模式的直接对立的反映。因此本部分将在全面剖析这两种模式内涵及利弊的基础上,探究何者更能兼顾理论逻辑的合理性和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 (一)交易相对人模式 所谓交易相对人模式,是指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适格原告应当是与内幕人进行证券交易的直接对手(direct counterparty),即当内幕信息为利空消息时,从内幕人手中购入证券;或者当内幕信息为利好消息时,将自己的证券卖给内幕人的投资者。此种适格原告界定模式首先出现于1976年美国联邦第六巡回法院对Fridrich v.Bradford案的判决中,其主要依据有二:其一,原告所主张的损害必须与被告的内幕交易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能够满足这一要求的只有内幕人的交易相对人。因为在匿名的证券市场中,被告的内幕交易并不会影响原告的交易决策,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间实际发生了交易,那么原告的受损交易就与被告的内幕交易无关。其二,如果放弃了适格原告的相对性要求,允许所有的反向交易者均可向被告索赔,将会无限放大被告的赔偿范围,使其须“向全世界承担责任”(liable to all the world)。(59)美国第六巡回法院的上述观点被澳大利亚立法机关在制定《1980年证券业法》(Securities Industry Act 1980)所采纳,并为现行《2001年公司法》(Corporations Act 2001)所承继。根据该法,只有将自己的金融商品卖给内幕人的处分人(disposer)或者从内幕人处购买金融商品的收购人(acquirer),才有资格就自己因此遭受的损失提起诉讼。(60)加拿大《商事公司法》(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亦采取了这种界定模式,规定购买或者出售相关证券的内幕人应当向“该证券的出售者或者购买者”(the seller of the security or the purchaser of the security)赔偿损失。(61) 交易相对人模式从传统面对面交易所涉及欺诈侵权的实际出发,认为只有与侵权人存在直接合同关系的主体才会受到前者的侵害,由此推论出在内幕交易侵权案件的受害人同样只能是内幕人的直接交易对手,即享有提起损害赔偿诉讼资格之人;而其他反向交易者所遭受的损失并非对应着内幕人的收益,而是对应着与内幕人进行同向交易的普通投资者的收益,因此没有理由要求内幕人赔偿。其实质是希望通过严格限定原告范围的方式,确保只有内幕交易的实际受害者才能获得赔偿,并避免导致内幕人承担过度赔偿责任(enormous damages)。(62)交易相对人模式的制度初衷固然值得肯定,但其所设计的实现路径却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层面均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其一,在匿名交易的公开市场中,难以确定特定证券交易的相对人。不同于面对面的直接交易,公开市场中的证券交易都是通过交易所的电脑系统自动撮合成交,投资者之间买入与卖出指令的匹配具有随机性,特别是在内幕交易所涉证券交易较为活跃的情况下,买卖双方都同时存在着众多投资者,很难分辨出哪些投资者的交易直接对应于内幕交易,而非其他不知情投资者的反向交易。因此,对于公开市场中的任何投资者来说,证明自己是内幕人的直接交易对手几乎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63)其二,这种模式忽略了内幕交易损害的“可传递性”(transferability)。虽然从理论上讲,内幕交易的危害性最初落在其交易相对人的身上,但该相对人并非必然遭受实际损害,例如,从内幕人手中购买证券的投资者如果在信息公开之间又将该证券卖出时,其自身并未受到任何损失,而是将这种损失的可能性传递给了交易对手,并且其交易对手仍可能将内幕交易的损害危险继续传递下去,直到内幕信息被公开时持有该证券的投资者才是内幕交易的实际受害者。(64)因此,合同关系并非内幕交易损害的必要条件,内幕人的直接交易对手可能并未遭受实际损害,而与内幕人不存在交易对手关系的其他投资者却可能真正受到内幕交易的侵害,所以,交易相对人模式将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原告仅限定于前者而完全排除后者,极易导致享有诉权的主体并无损害而真正的受害者却无权起诉的不合理结果。 鉴于交易相对人模式的上述弊端,一些采纳该模式的国家逐渐开始对其进行反思,甚至予以废止。例如,新加坡《1986年证券业法》曾仿照澳大利亚法的相关规定,将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适格原告界定为内幕人的交易合同相对方,但在经过多年的实践之后,该规定的弊端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影响投资者索赔的障碍。因为在匿名的证券市场中,投资者根本不知道其交易对手是谁,要求其证明与内幕人存在直接合同关系无异于天方夜谭。(65)新加坡立法机关遂于2000年修改法律时废除交易相对人模式,改采同期交易者模式。作为新加坡交易相对人模式立法输出国的澳大利亚也同样意识到了该种模式的缺陷,2003年证券和市场咨询委员会在关于内幕交易立法修改的报告中,明确建议放弃僵化的交易相对性要求,而应将原告范围扩展至内幕交易的所有受害人(aggrieved person)。(66)虽然上述建议至今尚未在澳大利亚转化为法律,但却得到了新西兰立法机关的采纳,后者在2006年修改《证券市场法》时,以受害人取代交易相对人作为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适格原告。(67) (二)同时交易者模式 与交易相对人模式不同,同时交易者模式主张所有与内幕人同时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都可成为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适格原告,而不论其交易指令是否与内幕人的实际发生匹配。此种模式最早由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提出,其在1974年Shapiro v.Merrill Lynch,Pierce,Fenner & Smith,Inc.案的判决中指出,“披露否则戒绝交易”(disclose or abstain)的义务并不仅对与内幕人之间发生交易的投资者负有,而应当向在(内幕交易的)相同期间(during the same period)就相同证券进行反向交易的所有对内幕信息不知情的投资者承担。(68)由此驳回了被告提出的只对其交易相对人承担义务的主张。在五年之后的Wilson v Comtech Telecomm Corp.案中,第二巡回法院进一步明确了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原告范围:“披露否则戒绝交易”义务的对象仅包括与内幕人同期(contemporaneously)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而那些非同期交易者(non-contemporaneous traders)由于其并未遭受与不公平信息优势的拥有者进行交易的不利益,故而无须“披露否则戒绝交易”规则的保护。(69)第二巡回法院的上述审判思想得到了美国国会的采纳,后者在《1988年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行法》明确将内幕交易侵权损害赔偿的明示诉权赋予内幕人的同期反向交易者,至此完成了适格原告的法定化。美国法关于内幕交易侵权诉讼适格原告界定的同期交易者立法模式,被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广泛移植借鉴。 同期交易者模式适用的关键在于“同期”的界定,对此美国国会认为,由于不同内幕交易所涉及证券的交易量等具体情形的不同,难以在立法中准确界定统一的标准,因此应当交由判例法去具体发展。(70)新加坡《证券和期货法》也列举了法院在判断一项反向交易是否与内幕交易同期发生的参考因素:如从内幕交易发生至该反向交易结束这段期间内系争证券的交易量,内幕交易被发现和处理的时间,该反向交易发生在内幕交易之前还是之后,该反向交易发生在内幕信息公开之前还是之后等等。(71)在各法域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同期”开始的时间通常并无争议,例如,美国多数地区法院认为,同期交易者应当从第一次内幕交易开始时计算,即将在内幕交易发生之前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排除在适格原告范围之外,因为在时间逻辑上,投资者难谓其交易受到了发生在后的内幕交易的损害。(72)但在“同期”何时结束方面则分歧严重,大致形成严格和宽泛两种解释进路。严格进路通常将同期交易限定为与内幕交易发生在同一天,例如,美国目前已有许多法院坚持原告的反向交易应当与内幕交易同日发生;(73)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于2006年修改时,对于内幕交易侵权诉讼的原告资格,在“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前加入了“当日”的限制要求;(74)在新加坡亦有学者主张应将同期交易者解释为与内幕人同日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75)与此相反,宽泛进路则主张将同期交易的终止时间延长至内幕信息公开之时。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法律研究院(American Law Institute)所起草的《联邦证券法典》(Federal Securities Code),其认为对于同期交易者的“当日”限定要求存在着涵盖过度(over-inclusive)和涵盖不足(under-inclusive)的双重缺陷。一方面,享有诉权的当日反向交易者可能会在信息公开之前转售证券而无实际损害;另一方面,自内幕交易发生次日起从当日反向交易者手中购入证券并持有至信息公开前的投资者实际遭受了损害却不享有诉权,极易导致内幕人得以规避赔偿责任的不合理结果。因此,对于“同期”较为合理的界定是从内幕交易开始至内幕信息公开这段期间。(76)此种同期交易者的宽泛解释进路亦受到我国香港地区学者的支持。(77) 同期交易者模式着眼于交易相对人模式未能解决的证券交易对手无法识别和内幕交易损害具有传递性这两个核心问题,意识到内幕交易的实际受害人是难以精确认定的,而与内幕人同期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事实上却都处于不公平的信息劣势地位,即都可能成为内幕交易的受害者,于是让这些能够确定的可能受害者来替代无法确定的实际受害者就成为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同期交易者是作为交易相对人的替代者(a proxy for privity)而被创设出的法律概念。(78)此种适格原告的界定模式的确可以解决交易相对人模式涵盖不足的缺陷,却仍然存在涵盖过度的风险,因为那些与内幕人的同向交易者实际匹配成交的投资者也被纳入了原告的范围,但他们的损失并非对应于内幕人的违法所得,而系与内幕人为同向交易的不知情普通投资者的获利或避损。如果这些损失也有权要求内幕人予以赔偿的话,必然会无限扩大内幕人的责任风险,使其赔偿数额远远超过违法所得,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为避免使内幕人承担过于严苛的责任(draconian liability),同期交易者模式对于赔偿总额做出了法律上的限制。例如美国《1988年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行法》规定,内幕人对于同期交易者的赔偿总额限于其通过内幕交易获得利润或避免损失的数额,并且,如果内幕人已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处以罚款的,赔偿总额中应当减去该罚款数额。(79)新加坡亦规定,内幕人对于原告的赔偿数额为原告的实际损失,但应以最高可补偿金额为限(maximum recoverable amount),所谓最高可补偿金额即内幕人获利或避损的数额。(80)此种责任限制制度的设计理念在于,内幕人应当对其内幕交易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根据证券交易零和博弈定律,内幕交易的实际损害数额或原告的实际损失数额,就是内幕人的违法所得数额,以此作为内幕人赔偿责任的最高数额,较为符合事实和法理。由于同期交易者模式已将并非内幕交易实际受害人的那些反向交易者纳入适格原告,实践中就可能出现原告的实际损失数额超过被告违法所得数额的情形,此时则应由全体原告按比例分配被告的违法所得金额。 (三)内幕交易侵权诉讼适格原告的合理界定 通过上文的介绍不难发现,域外关于内幕交易侵权诉讼适格原告界定的两种立法模式,均致力于在使实际受害者得到补偿与避免对违法者课以过度责任之间达致平衡,这也应当成为我国在界定适格原告时所必须坚持的立法原则。 第一,实际遭受内幕交易损害的投资者均应成为适格原告。从理论上讲,只有直接从内幕人手中买入证券或者将证券卖给内幕人的投资者才是内幕交易的实际受害者,这也是交易相对人模式的依据所在,但在公开市场中,证券交易系由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撮合成交,难以事后辨析购买者和出售者。更为关键的是,内幕交易的危害性可由内幕人的直接交易对手通过转售顺次传递下去,直至内幕信息公开为止。如果直接交易对手全部转售了从内幕人处购买的证券,则其并未受到任何损失,不具备起诉的实质条件,由此凸显出交易相对人模式不仅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更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并且,试图顺沿直接交易对手的转售链条追踪证券最终持有人以确定实际受害人的思路仍然不具有可行性,且不提内幕人的直接交易对手本已无法辨认,如果其将从内幕人处购买的证券部分转让给多个投资者,这些后手购买者再次向多人部分转让,更会使得实际受害人的确定难上加难。(81)因此,在内幕交易实际受害者难以准确辨认的情况下,寻找与其最为接近的替代者,就成为界定适格原告的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案,同期交易者模式遂由此产生。同期交易者这一概念不仅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更能契合内幕交易侵权因果关系的本质,因为内幕人的所有同期反向交易者都面临着被随机匹配为内幕人交易对手的现实风险,如果其知道反向交易者中存在内幕人,必然会改变原来的交易决策,而改为与内幕人同向交易,所以其均为内幕交易的可能受害者或最直接实际受害者。为将实际受害者全部纳入同期交易者范畴,“同期”的起止时间宜应规定为内幕交易开始至内幕信息公开,在此之前内幕交易尚未发生,投资者决策不会受到影响;在此之后,内幕人已不具有信息优势,无法对投资者造成不公平损害。 第二,内幕人承担的赔偿总额应当以其违法所得为限。根据证券交易零和博弈的定律,内幕交易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数额等于其违法所得数额,因此采取交易相对人模式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立法要求内幕人赔偿其交易对手的实际损失并无不当之处。但是,如将完全赔偿原则适用于同期交易者模式立法,则会导致内幕人承担与其违法所得不相称的赔偿责任(disproportionate damages)的不合理局面。故此美国、新加坡立法明确将内幕人的赔偿总额限制在其因内幕交易而获利或避损的范围内,其目的在于确保所有实际受害者均能获得救济。同期交易者模式对于未遭受内幕交易侵害的反向交易者也赋予了诉权,这些被扩大进来的原告的损失并非内幕交易造成,原则上不应由内幕人赔偿,但囿于鉴别困难,才允许其与实际受害者一同求偿,对于由此带来的不当扩大内幕人责任范围的风险只能通过限定其赔偿总额的方式予以避免。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内幕人的侵权赔偿数额,我国有学者建议应当实行惩罚性赔偿,即赔偿与其同日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实际损失数额的二至五倍,并援引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作为“立法先见”。(82)本文认为,此种观点既有悖法律责任制度原理,也与域外立法实际不符。首先,民事责任的主要功能是填补损害,而惩罚违法行为则是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的目标。(83)在我国已经确立内幕交易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现行法框架下,引入惩罚性赔偿似乎并无充分依据。其次,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21A(a)(2)条规定,SEC有权对内幕人处以不超过违法所得三倍数额的民事罚款(civil penalties),该罚款性质属于行政罚款,目的在于惩罚内幕人,而非对原告进行赔偿,(84)只是SEC可依民事诉讼程序向内幕人追究罚款,故称民事罚款而已,即美国并不存在内幕交易惩罚性民事赔偿。最后,我国台湾地区规定内幕交易惩罚性民事赔偿系出于弥补行政责任缺失的无奈之举,且其本土学者亦认为该制度的妥适性值得检讨,(85)故不具有借鉴价值。至于学者所言限制赔偿总额必然导致原告只能获得象征性补偿、与其所受损失相去甚远的顾虑,(86)本文认为可以通过由证监会以行政罚款建立投资者补偿基金的方式予以消除。(87) 总之,鉴于公开市场中证券交易的特点,内幕交易的实际受害者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难以进行准确甄别,因此只能由可以确定与其最为接近的主体予以替代,此即同期交易者。在内幕交易开始至信息公开期间内与内幕人从事反向交易的投资者均面临着受到内幕交易侵害的现实危险性,故应推定其受损交易皆与内幕交易存在因果关系,均可以作为原告向内幕人主张损害赔偿。而无论全体原告主张的实际损失数额多么庞大,被告的赔偿总额都不应超过其违法所得金额,否则无异于强制内幕人替其盈利的同向交易者向后者的交易对手贴钱,有违公平,如此方能实现投资者与内幕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认定之所以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根本原因在于内幕交易行为本身的特质:内幕人既不对投资者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也没有通过非法手段影响证券市场价格,故此难以类推适用在一般侵权和虚假陈述中行之有效的欺诈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这也是既有关于因果关系的肯定论无力抵御否定论的抨击之根源所在。然而否定论亦建立在将内幕交易定性为欺诈行为的基础之上,因此仍不具备充分合理性。 本文认为,内幕交易本质上是内幕人利用通过不公平机会获得的内幕信息对其他不知情的投资者所实施的不公平交易行为,而非欺诈;并且证券市场中的理性投资者均是出于对市场公平性和诚信性的信赖而参与其中的,如果其知道反向交易者中存在内幕人,必然不会作出导致自己利益受损的交易决策,亦即符合因果关系判断的“若无,则不”标准。因此,内幕交易与投资者受损交易在事实上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内幕交易侵权民事责任的确立具有坚实基础,我国司法实践亦应以此为依据来认定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 在司法认定的具体规则构建方面,由于与内幕交易存在因果关系的受损害交易主体——有权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在理论上只能是内幕交易的实际受害者,即将证券卖给内幕人或持有内幕人所售证券的投资者,但若要在为数众多的匿名交易者中分辨出这些实际受害者却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用内幕交易开始至信息公开期间内与内幕人进行反向交易的投资者来替代实际受害者,同时对内幕人赔偿总额作出限制,似为能够兼顾补偿实际受害者损失与避免课以违法者过度责任双重价值目标的适格原告界定的切实可行方案。 ①2007年4月4日,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唐电信)董事会秘书将公司2006年业绩预计亏损5-6亿的信息向包括潘海深在内的全体董事作了汇报。2007年4月16日,潘海深将其持有的大唐电信股票13637股卖出,成交金额为279 967.61元。2007年4月18日,大唐电信发布2006年业绩快报,称2006年公司净亏损719016700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于2008年3月2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潘海深卖出大唐电信股票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08]12号)。 ②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一中民初字第8217号)。 ③时任上市公司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关村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的黄光裕于2007年4月至2007年6月28日间,在拟将中关村公司与其经营管理的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事项中,决定并指令他人使用其实际控制交易的龙某等6人的股票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公司股票976万余股,至6月28日公告日时,6个股票账户的账面收益额348万余元。此外,2007年7、8月至2008年5月7日间,黄光裕还在拟以中关村公司收购北京鹏润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进行重组事项中,决定并指令他人使用其实际控制交易的股票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公司股票1.04亿余股,至2008年5月7日公告日时,股票账户的账面收益额3.06亿余元。2010年5月,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内幕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6亿元。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0]二中刑初字第689号)。 ④参见田浩:“股民诉黄光裕证券内幕交易案一审宣判”,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12月21日,第003版。 ⑤2013年8月16日11时05分,光大证券在从事自营证券买卖业务时,交易员分析判断上证180 ETF出现套利机会,而用交易软件发出买单,但由于交易软件先天存在设计缺陷,未经充分测试即被匆匆投入使用,导致光大证券的账户自动巨量买入180 ETF成分股,实际成交72.7亿元,巨额的投入带动了沪市指数的整体暴涨。事故发生后,光大证券交易员根据《策略交易部管理制度》中关于“系统故障导致交易异常时应当进行对冲交易”的规则,开始进行对冲。11时30分休盘后,该公司高管就如何处理过多买入的股票紧急磋商。因为当前交易的“T+l”规则禁止在股票买入当日卖出,为了对冲之前巨额误买的损失,光大证券改用卖空股指期货合约、转换并卖出ETF对冲风险。证监会于2013年11月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光大证券的上述行为构成内幕交易。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3]59号)。 ⑥参见罗琼、张霞:“8.16乌龙指系列案:复杂的赔偿”,《南方周末》2014年8月8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973?from=timeline,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9月1日。 ⑦参见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陈甦主编:《证券法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页279。 ⑧参见耿利航:“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功能质疑”,《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 ⑨参见郭锋:“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探讨”,《法律适用》2008年第4期;陈洁:《证券欺诈侵权损害赔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65;杨峰:“美国、日本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比较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 ⑩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373。 (11)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是英美法系的分类方式,而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是大陆法系的相应分类。详细介绍,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304-321。 (12)See Wilson v.Comtech Telecomm Corp.,648 F.2d 88,95(2d Cir.1981) (13)此处借鉴了侵权法学者关于责任成立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相关论述,本文认为其结论同样适用于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184;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177。 (14)对内幕交易因果关系持肯定态度的主要法域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等,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法域有欧盟各成员国和日本等。 (15)参见赵旭东:“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司法政策与导向”,《法律适用》2013年第6期。 (16)Kardon v.National Gypsum Co.,73 F.Supp.798(E.D.Pa.1947). (17)参见(美)路易斯·罗斯、乔尔·赛里格曼:《美国证券监管法基础》,张璐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667。 (18)"Reliance is an element of a Rule lob-5 cause of action...Reliance provides the requisite causal connection between a defendant's misrepresentation and a plaintiff's injury." See Basic Inc.v.Levinson,108 S.Ct.978,989(1988). (19)参见程啸:《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页176。 (20)See H.M.Friedman,The Insider Trading and Securities Fraud Enforcement Act of 1988,68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483-484(1990). (21)406 U.S.128(1972). (22)Shapiro v.Merrill Lynch,Pierce,Fenner & Smith,Inc.,495 F.2d 228,238(2d Cir.1974). (23)Fridrich v.Bradford,542 F.2d 307(6th Cir.1976). (24)Basic Inc.v.Levinson,485 U.S.224,230(1988) (25)参见奚晓明、贾纬:“《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03年第2期。 (26)参见郭锋,见前注⑨;杨峰,见前注⑨;苑多然:“内幕交易的认定及其民事责任”,《人民司法》2007年第17期。 (27)See Thomas Lee Hazen,Treatise on the Law of Securities Regulation,6th ed.,Vol.4,West Publishing,2009,p.131. (28)See William J.Carney,Signalling and Causation in Insider Trading,36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886-887(1987). (29)Fridrich v.Bradford 542 F.2d 307(6th Cir.1976). (30)参见樊纪伟:“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欺诈民事责任制度及其借鉴”,载《经济法论丛》第25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页237-238。 (31)(英)理查德·亚历山大:《内幕交易与洗钱:欧盟的法律与实践》,范志明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213以下。 (32)参见耿利航,见前注⑧。 (33)See U.S.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s 20A(a). (34)See W.Wang and M.Steinberg,Insider Trading,3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26. (35)See Alexander Loke,The Protected Interests in the Private Right of Action for Insider Trading: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7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Studies,322(2007). (36)See Australia Corporations Act 2001,ss1043L(3),(4); Canada 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s131(4). (37)(美)罗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则》,胡平等译,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页263。 (38)List v.Fashion Park,Inc.,340 F.2d 457,463(2d Cir.1965); Shapiro v.Merrill Lynch,Pierce,Fenner & Smith,Inc.,495 F.2d 228,239(2d Cir.1974). (39)参见耿利航,见前注⑧。 (40)廖大颖:《财经犯罪与证券交易法》,新学林出版公司2009年版,转引自赵旭东,见前注(15)。 (41)参见耿利航,见前注⑧。 (42)Roy Schotland,Unsafe at Any Price:A Reply to Manne "Insider Trading in the Stock Market",53 Virginia Law Review,1443-1446(1967). (43)See Donald C.Langevoort and G.Mitu Gulati,The Muddled Duty to Disclose Under Rule 10b-5,57 Vanderbilt Law Review,1676(2004). (44)See James D.Cox,Insider Trading and Contracting:A Critical Response to the "Chicago School",35 Duke Law Journal,635(1986). (45)参见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订)释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页7。 (46)参见杨亮:《内幕交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6。 (47)参见陈甦,见前注⑦,页234。 (48)李飞,见前注(45),页7。 (49)参见廖大颖,见前注(40)。 (50)参见陈甦,见前注⑦,页235。 (51)参见耿利航,见前注⑧。 (52)参见郑彧:《证券市场有效监管的制度选择》,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页14-15。 (53)参见罗斯,见前注(17),页673。 (54)See United States v.O' Hagan,521 U.S.642(1997). (55)William J.Carny,supra note 28,at 890. (56)参见杨亮,见前注(46),页337。 (57)参见马新彦:“内幕交易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 (58)参见张明远:《证券投资损害诉讼救济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169。 (59)Fridrich v.Bradford,542 F.2d 307,323(6th Cir.1976). (60)See Australia Corporations Act 2001,ss1043L(3),(4). (61)See Canada Business Corporations Act,s131(4). (62)See Hui Huang,Compensation for insider trading:Who should be eligible claimants?,20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14(2006). (63)See Rita Cheung,Insider trading: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private right of action,32(2)Company Lawyer,58(2013). (64)See Veronica M.Dougherty,A[Dis]semblance of Privity:Criticizing the Contemporaneous Trader Requirement in Insider Trading,24 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136(1999). (65)See M.Chew,The Adequacy and Efficacy of the Civil Remedies for Insider Trading:A Comparative Critique,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347(1998). (66)See Corporations and Markets Advisory Committee(Australia),Insider Trading Report(November 2003),Recommendation 9. (67)See New Zealand Securities Markets Act 1988,s42ZA. (68)Shapiro v.Merrill Lynch,Pierce,Fenner & Smith,Inc.,495 F.2d 228,237(2d Cir.1974). (69)Wilson v.Comtech Telecomm Corp.,648 F 2d 88(2d Cir,1981) (70)See Report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Energy and Commerce on the Insider Trading and Securities Fraud Enforcement Act of 1988,HR Rep No 100-910,100th Cong,2d Sess 27(9 September 1988). (71)See Singapor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s 234(5). (72)W.Wang and M.Steinberg,supra note 34,at 521-523. (73)See Donald C.Langevoort,Insider Trading Regulation,Enforcement,and Prevention,Thomson Reuters,2012,§ 9:3. (74)参见赖英照:《股市游戏规则——最新证券交易法解析》(第二版),元照出版社2009年版,页564。 (75)See Tan Cheng Han,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Singapor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51(2000). (76)Federal Securities Code(ALI 1980),s 1703. (77)Rita Cheung,supra note 63,at 61. (78)Veronica M.Dougherty,supra note 64,at 139. (79)See U.S.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s 20A(b). (80)See Singapor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s 234(2),(6). (81)W.Wang and M.Steinberg,supra note 34,at 68-74. (82)参见马新彦,见前注(57)。 (83)参见赵旭东,见前注(15)。 (84)参见赵旭东:“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价值平衡与规则互补——以美国为研究范本”,《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2期;耿利航,见前注⑧。 (85)参见刘连煜:《新证券交易法实例研习》,元照出版社2009年版,页448。 (86)参见耿利航,见前注⑧。 (87)关于建立我国投资者补偿基金制度的构想,参见彭冰:“建立补偿投资者的证券行政责任机制”,《中外法学》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