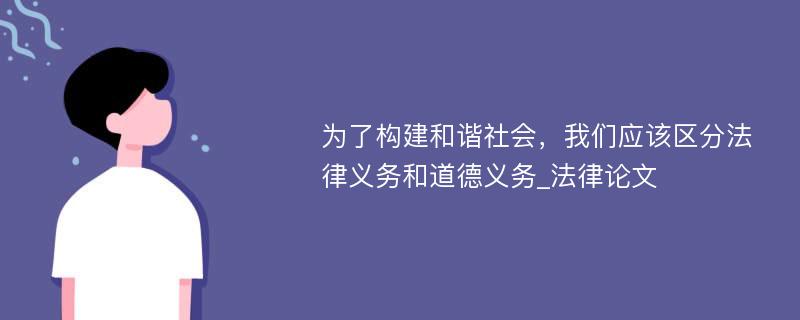
构建和谐社会应区分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务论文,构建和谐社会论文,道德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和谐社会是人类永恒的理想,不懈的追求。近年来,随着中共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以来,更成了理论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而要建设和谐社会,笔者以为,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要认清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两者之间的区别,本文的主旨就是对此加以探讨。
一、两种和谐社会观
古往今来,中外思想家们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颇多,但从逻辑上讲,我们可以根据其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不同途径来划分。和谐社会的建设途径,无外乎两种:一种是通过道德教化,倡导忍让实现和谐;另一种是通过利益的界定实现和谐,也就是说,有两种和谐社会观。
(一)通过倡导忍让的道德教化以止争,建立和谐社会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逐渐成为在传统社会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至今仍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儒家认为和谐意味着没有纷争,而诉讼意味着纷争,因此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没有诉讼的社会。儒家创始人孔子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①而实现无讼社会的途径在于通过道德教化,使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懂得忍让,因此儒家极为推崇忍让,视之为美德,“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②“厚人自薄谓之让,反让为冒。”③儒家认为忍让之所以能够建成和谐社会,是因为诉讼缘起于人们相互间利益之争,而世上既有君子,也有小人。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君子求义,因此能够做到让;而小人求利,不能做到让,因此只有求利的小人才会诉讼,求义的君子不会诉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④,同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通过君子的表率作用,求利的小人是完全能够转化成求义的君子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⑤。《三国志》记载了杜畿息讼的故事作为儒家建立无讼社会的范例。“(杜畿)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畿亲见为陈大义,遣令归谛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有辞讼。”⑥这种“少有辞讼”的社会就是中国儒家理想的和谐社会。
(二)依法界定利益以止争,建立和谐社会
现代法治论者则认为社会之所以产生纷争,出现我们所说的社会不和谐因素,起因在于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彼此间发生利益纷争是不可避免的,要建立和谐社会,只能通过诉讼来解决纷争,从而化解矛盾,平息怨气,实现和谐。德国法学家耶林曾写道:“法的目标是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手段是斗争。”⑦耶林所说的斗争当然不是指自力救济,而是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自己应得的权益。他认为社会之所以产生纷争(或斗争),起因在于人们的权利受到他人的侵害,通过诉讼,使得侵害人以后不敢侵害他人,和平始得建立。饶有趣味的是,我国古代法家代表人物也持有与此类似的观点,商鞅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⑧商鞅认为世人的天性都是追逐利益的,甚至连传说中的圣君尧、舜、禹、汤也不能例外,纷争产生的原因在于“分之未定”,止争的途径在于“定分”。用现代话说,就是要通过确定权利义务的界限,解决纷争,这样建立的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社会。虽然商鞅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依靠法律限制君权的主张,相反却主张依靠法律强化君权,这是他与现代法治论者的根本区别所在。但他看到了人有追逐利益的一面,而且它是无法通过道德教化加以消除的,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只能通过对利益的严格界定,而这正是与现代法治观念相通的,因而两者可归为一类。
二、和谐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石——公正
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时,面对着两种和谐社会观,应当何去何从呢?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求之于经验,正如达·芬奇所说:“不管是谁写得多么好,经验才是最高的权威,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引用这权威。”“经验,一切教师的教师。”⑨
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可以断定,第一种和谐社会观,也就是中国儒家学派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不可取。一则,依据忍让建立的社会不公正。忍让要建立在互忍互让的基础上,人敬我一尺,我还人一丈,这样的人、事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说没有。但是得步进步,得寸进尺的人、事却也屡见不鲜。如果你忍他不忍,你让他不让,造成的结果只能是“脸皮厚,吃个够;脸皮浅,吃一点”,如此建立起来的社会只能使坏人受益而好人受害。这种利益格局不符合人们对公正的追求。因为公正,依照罗马法的定义,“正义⑩是给予每一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11)依据人们对公正的认识,儒家一味倡导忍让所建立起来的“好人受其害,坏人享其利”的利益格局不符合人们得其所应得的愿望,这样的社会是不公正的社会;二则依据忍让建立的社会不可能存在。因为你忍他不忍,你让他不让,这样建立起来的利益格局非但不正义,而且也无法维系。任何人的忍让都是有限度的,当忍让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不可能再忍下去,汉语成语“忍无可忍”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而当人们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的时候,靠忍让建立起来的利益格局就会被打破。因此靠忍让是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的。
为了更清楚透彻地说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之不足取,我们不妨分析儒家所讲的这个杜畿息讼的例子。我们知道,杜畿息讼的秘诀是通过“陈大义”和乡邑父老的“责怒”。所谓“陈大义”无非是用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来教育当事人放弃自己的利益,做好义的君子,不做好利的小人。笔者认为,这种“陈大义”的道德说教非但不符合实际,而且是一种欺骗。就现实生活经验来看,追逐利益是人的天性,难以通过道德教育来消除。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世人又有谁能够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呢?当然,一种思想不符合实际未必就能说明它是骗人的,因为这种不符合实际可能是由于认识上的错误。笔者之所以说它是一种欺骗,原因在于它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们都不愿意舍利求义,而只是在口头上言义,行动上却孜孜求利。首先,这种思想的提出者孔子本人不愿意舍利求义。孔子要求别人舍利求义的同时,自己却不愿将这一思想付诸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这一点可以从孔子本人的言论中得到证实,“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3)据此,我们可知孔子并非真的淡泊利益,而仅仅是教育别人应当淡泊利益罢了,他本人为求利甚至不惜做为人执鞭这种卑贱的工作。孔子这种求利的态度与他本人提出的君子应当舍利求义的说法是完全冲突的。这正应了康德的一句话:“前后一贯是一个哲学家的最大责任(着重号为原著者所加),但却极少见到。”(14)其次,中国传统社会儒家思想的倡导者专制君主们也不愿意这么做。专制君主们独尊儒术,倡导他人忍让,去舍利求义。然而他们自己却干着损人利己的罪恶勾当,“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15)因而被斥之为荼毒天下的寇贼,“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6)自己求利却劝说别人弃利求义,这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这充分表明孔子及其思想的推崇者们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并非是由于认识上的失误,而是有意骗人。因为他们仅仅将这种理论停留在口头上,而不付之于行动中,从而用行动推翻了自己的道德说教,因此这种道德说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这就表明杜畿所陈的“大义”是一种欺骗。正如温斯坦莱所说:“不见诸行动的言词只是一种欺骗”。(17)杜畿所陈的“大义”是一种欺骗,决定了杜畿所谓的“陈大义”只能是一种有意无意地欺骗。而当杜畿“陈大义”不能奏效时,最终依靠乡邑父老的“责怒”来息讼。也就是说依靠社会舆论来强制当事人放弃自己的利益主张。应当说,在传统社会中,社会舆论的压力对于个人来说是非常强大的,因而也是非常可怕的。民国时代的上海女艺人阮玲玉因不堪流言而自杀,足见流言即社会舆论这种软刀子是可以杀人的。甚至到了现代社会,中国仍然有“唾沫星子淹死人”“人言可畏”的俗语,何况杜畿所处的传统社会!因此,乡邑父老的“责怒”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压制力量。应当说,乡邑父老的“责怒”毫无道理。且不说杜畿的品德是否真的高尚大有疑问,即使杜畿真的品德高尚,“有君如此”,为什么当事人就一定要“从其教”?格劳秀斯曾说过:“只要一个人不对其他人造成伤害,那么法律就没有理由阻止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18)应当说,当事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当然有权主张,这并不损害其他人的任何利益。乡邑父老“责怒”的理握何在?这种“责怒”的实质乃是压制,因为它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在这种“陈大义”加“责怒”也就是欺骗与压制的双重压力下,当事人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要按照杜畿的要求也就是长官的意志放弃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谐社会也就因此建成了。然而,当事人的“未尽之意”不可能通过“责怒”而消除,这就必然产生怨恨。正如公孙弘所说:“理得则不怨”(19)理得才能不怨,理不得则不可能不怨,“责怒”不能使人“理得”,因此,靠“责怒”求得的无讼不可能不怨,这就决定了杜畿建立的“和谐社会”是一个有怨即充满怨恨的社会。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儒家理想的和谐社会乃是通过欺骗与压制建立起来的,是与怨恨相联系的,从而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第二种和谐社会观则较为可取,因为它与公正相联系。公正的另一个含义是“互利”,即“一般地说,正义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指在交往中给彼此带来益处。”(20)社会只有在其成员间实现社会公正才能维系,如果在社会中有人受益,有人受害,这样的社会就无法维系。陈独秀曾说过,“骑马者要和马讲团结,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压在我身上相当舒适,我要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满身是汗,你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敏。”(21)分析陈独秀所说的这段话对于我们探讨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谐与团结含义相通,只不过和谐侧重于社会整体,而团结则侧重于组成社会的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社会和谐离不开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而一个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团结的社会也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陈独秀所说的“马”指受压迫者,“骑马者”则指社会的压迫者。马之所以不愿与骑马者讲团结,建立骑马人所理想的和谐社会,是因为骑马者不愿与马在互利的基础上相处,这样所组成的社会也就只是于骑马者有利而已,而对于马则无利益可言,马得不到其所应得,当然也就不愿意与骑马者讲团结,建立和谐社会了。一个社会如果不尊重其组成成员的利益,仅靠欺骗与压制使得人们放弃自己的利益,最多只能换来表面上的一团和气。这种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它只是人们敢怒不敢言的结果,只能积聚人们内心对不公正社会的怨恨。这种怨恨的存在与和谐不相容,因为和谐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物理状态,而且包含了人际关系的心理状态,“和平不仅是免于战争,而且是精神上的和谐一致。”(22)只有人们能够在人类社会中得其所应得,才会认同这个社会存在的合理性,才会热爱社会而不是仇视社会,因此没有公正就没有和谐,公正是和谐社会建立的基石。
三、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探讨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的关系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本文对这两者间关系的探讨仅限于本文主旨,下面我们就从两者间的联系和区别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联系
个体的人生活在社会中,他(她)在享受社会给自己提供的福利的同时,也必然要履行自己对他人、社会的义务。这种义务根据其来源可以分为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法律义务是根据法律规定所赋予人们的义务,对它的不履行将导致法律的制裁。道德义务则有广狭两义,广义的道德义务指人与人之间彼此之间承担的所有义务,它既包括狭义的道德义务也包括法律义务。狭义的道德义务,仅指违反道德规范而不违反法律的义务,若不履行这种义务仅仅导致舆论谴责和自己内心的不安,因为“义务仅仅命令我们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23)不应受到法律的制裁,本文取狭义。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两者之间的联系正如同法律和道德的联系,因为法律和道德正是通过规定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才得以完成其使命的。法律和道德联系紧密,法律要符合道德,“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亦即法律的领域是道德要求的一部分。”(24)道德义务是法律义务的根据,法律义务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不履行法律义务是违反道德义务之中最严重的,换句话说,不履行法律义务是最不道德的行为。同时,培养人们自觉履行法律义务的意识是道德义务的重要使命。
(二)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别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固然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两者间的区别也不容忽视,违反道德义务未必就违反法律义务。道德义务不能通过法律义务的设定来强制履行,卢梭曾说过:“法律的真正目的是维持安宁,而不是培养道德。”(25)正是由于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别造成了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从而损害了公正。在笔者看来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两者起码有以下区别:
第一,职能不同。法律义务旨在防止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伤害。边沁曾指出:“所有法律的总目的在于防止损害。”(26)霍尔巴赫也曾指出:“制订法律,无非是为维持社会并阻止社会成员们互相损害,因此,法律对扰乱社会的人或是作了有害于自己同类们的行动的人,可以给以惩处。”(27)法律义务从人类行为的最低点出发,因为人类如果不能做到不相互伤害,人类社会就无法存续,因此法律义务的设定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
道德义务旨在造就完美人格,使人帮助他人,“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28)培根也曾指出,“‘善’的意义,就是旨在利人者。”(29)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利人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利人包括有偿的利人行为,有偿的利人往往是人们的法律义务,不履行这种义务会导致法律制裁的产生。狭义的利人则仅指无偿的利人行为,本文取狭义即无偿的利人。道德义务从人们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出发。因为如前所述,自私是人的本性,对于自私的人来说,违背自己的本性去无偿帮助他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概括而言,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职能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律义务的职能在于防止人与人互害,道德义务则在于促使人能够利他人,道德义务对人的要求远远高于法律义务对人的要求。
第二,评价标准不同。评价法律义务的标准是行为是否合乎现行法律,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30)因为行为、现行法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因而对于法律义务的评价也就具有客观性、确定性。
评价道德义务的标准是能否做到问心无愧。道德义务侧重于强调行为的动机,要求不得掺杂私利,否则就不符合道德义务的要求。西塞罗曾说过:“为了公平而追求公平。这样的动机和目的是所有美德的特征。”(31)因此对于道德义务的评价具有主观性。道德义务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它据以作为评价的标准带有主观性而不具有客观性。斯宾诺莎曾经说过:“所谓善与恶的概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所以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观点之下,可以叫做善,亦可以叫做恶。(32)譬如说,年轻人在公交车上给老年人让座这一行为,按照中国的道德观念被认为是尊老爱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按照西方的道德观念,年轻人的这一行为却可能被认为是对老年人的歧视。据此可知,不同的道德观会对同一行为作出不同的评价。因此道德义务的评价标准不能是外在的,只能是内在的即义务人能否做到问心无愧。
第三,履行的保障力量不同。法律义务的履行主要依靠他律。由于法律义务旨在防止人们相互间伤害,而如果不阻止人们之间的相互伤害,人类社会所必需基本秩序就无法确立,人类也就无法存续,这就使得法律义务采取他律的形式具有了必要性;同时也由于法律义务评价标准的客观性给他律提供了可能性,法律义务的履行主要依靠他律。这种他律表现为国家强制力,当义务人不履行其法定义务时,权利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法定程序强制其履行其法定义务。当然,义务人不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也会受到舆论和良心的谴责,但法律义务的履行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
道德义务的履行则主要依靠自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强制他人履行道德义务,义务人不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不去帮助他人,只应招致良心的自我谴责。当然,道德义务也有一定程度的他律性,但这种他律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仅仅表现在舆论谴责上。道德义务的履行之所以不应具有国家强制力,是由于现代法治理论是建立在承认人的自利性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不能使用强制力要求人成为不求私利的“圣贤”,强迫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同时由于对道德义务的评价具有主观性、不确定性,强制他人履行道德义务意味着以主观的道德标准取代了有着客观评价标准的法律,如此一来,法律就无法发挥其保障人们权利、自由的作用,马克思曾说过:“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33)因此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应有明确的界限,不能混淆。
四、公正的实现在于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分
(一)在传统社会中,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不分造成公正无法实现
对于民众而言,其私利的侵害者要么来自自己的同类,要么来自国家公权力,两相比较,对私权利而言,国家权力是更大的侵害者。因为即使是把民众当做牲畜的专制统治者,也会出于爱惜自己财产的目的制定法律,防止民众相互伤害。当民众受到来自同为民众的伤害时,他们可以寻求法律救济,从而制止这种侵害,这就大大减少了来自民众的伤害。然而法律却不能约束公权力,因此民众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害就会求告无门,因而没有办法制止这种伤害。正如洛克所说:“他们(专制统治者,引者注)将承认,臣民彼此之间,为了他们相互的安宁和安全,必须有措施、法律和法官;但就统治者来说,他应该是绝对的,超于这种种情况之上的;因为他有权力可以作更多的害人的事和坏事,他这样做是合法的。”(34)由于来自公权力的侵害不受法律限制,这就决定了它对私权利的侵害甚于来自民众的侵害。而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的理论根源,是由于在传统社会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没有严格的界分。
在传统社会,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没有严格的界限,因而统治者有权强迫人们履行道德义务。董仲舒提出:“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35)柏拉图则在《法篇》中提出:“美德是立法者通过立法想要实现的目标。”(36)在传统社会,无论是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如出一辙,法律都是被作为统治者驱民为善的工具存在的。法律既然作为统治者驱民向善的工具而存在,那么任何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都可能受到法律制裁,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37)礼对人的要求是道德义务,而违反礼则会受到刑即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不履行道德义务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而如前所述,对道德义务的要求是至善,旨在造就完美人格,具有主观性,不确定性的特点。法律义务具有客观性、明确性的特点。一旦法律被用来培养道德,那就意味着执政者有权强迫公民尽道德义务就使得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的法律义务变得不确定。法律和道德义务被混淆,法律因此就可以被任意解释,也就不存在对统治者的任何限制了,这就必然导致公权力无限扩张,从而侵犯公民私权利。事实上,统治者侵害民众私权利的胡作非为往往都是打着道德的旗号,通过要求民众履行道德义务的名义来行侵害民众私权利之实的。我们不妨看一下中国古代关于“仁政”的论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主鹯之逐鸟雀也。”(38)我们知道,“仁”与“不仁”是一个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标准,对它的解释权操之于执法者之手,统治者甚至可以以“不仁”的名义任意杀掉不合自己心意的民众。由此可见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不分被统治者利用,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这就在事实上取消了法治。因为所谓法治无非是指人们用客观标准而非主观标准衡量人们的行为,从而防止统治者任意妄为,侵犯民众权利。而法治一旦被取消,民众的生命、自由就完全悬之于统治者之手。霍尔巴赫曾说过:“凡是在法律可以任意解释的地方,人民便是奴隶。”(39)可以被任意解释的法律使人们成了奴隶,而法律之所以能够被任意解释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不分。因此,传统社会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不分是造成公权力侵害私权利的理论根源之所在。
(二)传统社会中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不分的逻辑前提
统治者道德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需要来自外部的任何监督是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不分的逻辑前提之一。如果统治者道德上有瑕疵,那就对统治者的私欲不能不防范,而要防范统治者的私欲,就必须以客观标准而不是统治者主观的评价标准来评价民众的行为。而传统社会的统治者正是被认为毫无道德瑕疵的。董仲舒提出:“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40)既然统治者的权力被认为是受命于天的,而其行使权力的目的在于驱民向善,统治者自身的品德当然是不容怀疑的,因而有权强迫人们履行道德义务。统治者的法令不容怀疑是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应当分离的逻辑前提之二。在传统社会,民众对于统治者的法令,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评判的权利。管子有言:“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41)这就是说,君主是法令的创制者,官吏是法令的执行者,而民众只是法令的遵守者。作为法令的遵守者,民众当然也就没有权利怀疑法令。韩非子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姜太公吕望曾多次求见一位贤士狂矞,狂矞不答应见面,吕望就杀了他。理由是“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42)狂矞没有不做太公吕望顺民的言行,只是不愿意出仕,就被视为大逆不道而被杀掉。对于拒绝出仕的说法,统治者尚且不能容忍,遑论怀疑统治者的法令?
现代社会认为古代人对君权、君主的神话是错误的。依照现代法治理论,个人之所以服从国家的权力并承担税负,以供养国家工作人员,目的是保障自己的权利。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于公民权利,国家及其工作人员行使权力应当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这样一来,义务主体不仅包括公民而且包括国家,也就是说不仅公民对国家负有法定义务,国家对人民亦负有法定义务。公民对国家的法定义务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来源,而国家的法定义务则是人民的法定权利。毋庸置疑,要保障公民的私权利,人们在不得不借助于公权力的同时,还要防范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规定皆禁止”是现代法治社会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项基本原则确立的目的就在于限制国家公权力。因为,一则行使公权力的是人,而追求自己的利益是人的本能,是无法消除的,按照霍尔巴赫的观点:“在这世界上,全无私利的人是绝对没有的。”(43)二则,掌握公权力的人的品德尤其不值得信任。因为权力会腐蚀人,即使是品性善良的人也可能会因为掌握了权力而胡作非为。正如雪莱所说:“很少有人掌握了专制权力而其善良品质不遭破坏的。”(44)而要不使公权力不成为专制权力,就要利用法律来约束公权力,厘清国家和公民各自应尽的法律义务,这就要求从理论上区分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
(三)现代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仍然在于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不分
应当说: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区分是现代法治社会不同于古代人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在当代中国仍然时有越界,而这正是公权力侵害私权利的理论根源所在。笔者从下面两个有关教师权利义务的事例来进一步说明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不分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们首先看一个由于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不分使得公民的道德义务变成了“法律义务”的例子。陕西省勉县教育局于2008年6月2日作出规定:高考的监考老师在余震发生时,要保证将全部学生疏散完毕后才能离开考场,违反规定的,将给予停职或开除的处理。(45)诚然,教师在考生未能逃生时,有帮助考生逃生的道德义务。如果一个教师在地震发生时能够帮助学生逃生,但却不这样做,他就应当受到良心的谴责,社会舆论也应当对此进行谴责,从而树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救助的良好道德风尚。毕竟,谁也不愿意看到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终结。但问题在于:教师在法律上是否有义务冒着生命危险将全部学生疏散?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在法律上,教师具有两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另一方面,他们是公民。教师的法律义务是教师担任教师这一职务所应承担的义务,基于教育活动而产生。是保证其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要求,因此,这种法律义务仅仅限定于教学活动中。根据《教师法》关于教师义务(46)的规定,教师没有在地震发生时疏散学生的义务,更没有必须在学生疏散完毕后才能离开现场的义务。在地震发生时,教师的教学活动就无法进行,教师就不再是教师了,也就不再履行作为教师的义务。教师在地震发生时只作为公民而存在,享有法律规定应当公民享有的权利,承担法律规定公民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了。《刑法》(47)、《民法通则》(48)都规定公民有紧急避险的权利。教师作为公民,在自己的生命遭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损害另一个较小的合法权益以逃生,何况教师在地震发生时逃生并未损害任何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勉县教育局无权设定教师在地震发生时对学生的救助义务,因为教师作为公民所应承担的法律义务的设定属于民事法律制度。《立法法》第8条第7款明确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只能通过法律制定,这就是说,即使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也无权设定教师作为公民在地震中所应承担的对他人的义务,何况作为基层教育管理部门的勉县教育局!根据以上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知道在地震发生时,教师帮助学生安全撤离,纯粹是教师的道德义务而绝非法律义务。因为如前所述,道德义务的职能在于促使人与人互助,法律义务的职能在于防止人与人互害。教师在地震中应当帮助学生逃生,纯粹是人与人之间道义上的互助义务。在地震中,教师固然有帮助学生逃生的道德义务。反过来讲,学生在地震中也有帮助教师以及其他学生逃生的道德义务。然而,这种互助义务的实现只能通过道义上的倡导,而不能强制人们履行。然而,勉县教育局的一纸规定却使得教师在地震中帮助学生逃生的道德义务变成了“法律义务”。应当说,勉县教育局的这一做法是违法的,社会危害性也很大,因为它使得教师在地震发生时逃生的几率大大降低,许多教师可能因此而丧生。我们知道,在地震发生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逃离地震现场的,若地震发生时,教师没有能够将所有学生疏散完毕,岂不是要求教师必须与不能逃生的学生一起去死吗?这岂非殉葬制度的现代版?勉县教育局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本职工作限于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49)却有权作出在一定意义上剥夺教师生命权利的规定。国家公权力侵害公民私权利之烈,可不畏哉!更为可怕的是,这一规定的出台,却得不到纠正,笔者甚至很少听到这一规定合法性的质疑,更少要求对这一严重违法规定相关责任人进行法律追究的呼声。我们知道,当一个法官错判案件时,法律就会通过错案追究制追究违法法官的法律责任,因为有人因错案而受害,这当然是公正的。然而,两相对比,这一限制教师在地震中逃生的违法规定较错案的社会危害性更大。首先,受害人更多。错案中的受害人是个别的,而这一违法规定的受害人却是众多的,它包括勉县全县的教师;其次,受害程度更深。一个错案中的受害人可能损失的只是财产、自由,当然在极个别情况下也可能是生命。然而勉县教育局的这一违法规定剥夺的却可能是全县众多教师的生命。孰轻孰重,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然而国人少有质疑这一规定的违法性,追究这一违法规定的相关责任人的要求更是闻所未闻。国人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之淡薄,发人深省。而国人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淡薄的理论根源,不正是在于理论界对于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区分不够明晰吗?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由于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不分,从而使得国家的法律义务变成了“道德义务”的例子。《教育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50)如此一来,使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至少不低于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就成为国务院的法律义务。然而这项规定落实得怎么样呢?至少笔者作为教师,深切地感到现实与规定相差甚远,教师与国家公务员收入不可同日而语,远不能达到同等的水平。这种社会现象的普遍存在表明国务院以不作为的方式违反了《教育法》,侵犯了教师的法定权利。然而教师却没有法律途径来对自己的法定权利进行救济。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51)国务院不能作为被告来诉讼,这就使得国务院高踞于法律之上,不需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们知道,国务院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而人都是会犯错误的,国务院不可诉的规定使得国务院的任何违法行为都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来加以纠正。只能听之任之。教师依据《教育法》应当享有的法定权利之所以被侵犯而没有救济途径,是因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者规定国务院不可诉,从而抽去了作为法律义务保障的制裁措施,而立法者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则是由于立法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的不同特点。如前所述,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履行的强制力量不同。法律义务以他律的形式存在,具有强制性,当个人、组织不履行自己应尽的法律义务时,权利人应当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法律途径强制其履行法律义务。然而《行政诉讼法》却规定国务院不可诉,这就使得国务院的任何违法行为,都无法通过公民诉讼的方式来加以纠正,而只能通过国务院的自我纠正。这就是说国务院的法律义务本应采取他律的形式,而实际上却是以自律的形式存在的。我们知道,法律义务是以他律的形式存在,道德义务才是以自律的形式存在的。正是混淆了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才使得本应是国务院的法律义务变成了“道德义务”,使得公民在政府的违法行为面前只能望法兴叹,徒唤奈何。
法治社会要求国家和公民都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两相比较,国家在履行法律义务时应当做得更好。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务院,其守法义务应远远高于作为公民的教师,这才符合正义。一则,付出与回报应当紧密联系,有多少付出,就应有多少回报,高付出就应有高回报。反过来讲,高回报就应当有高付出,这样的社会才是公正的社会。国务院是被作为服务于人民大众的社会公仆推举出来的,享受着纳税人提供的较普通人更为优厚的福利,更为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黑格尔曾说过:“一个人享有多少权利,也就负有多少义务。”(52)国务院因而也就较普通公民负有更大的守法义务和责任,要求普通公民做到的,自己更应该首先做到,这才符合正义。其实,就连古人也明白公共事业的管理者较普通人、地位较高的人较地位较低的人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个道理,“禄多者责大。”(53)“一个统治者必须具有一个真正正直的人的品德;但并不是每个公民都非达到同等程度的正直不可。”(54)遑论今人?而目前的情况是,国务院不履行其应尽的法律义务,即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受害人无法追究;基层人民政府的教育管理部门却违反法律规定使用强制手段要求公民去尽道德义务,岂非咄咄怪事!如此行事,焉能服众?不能服众,和谐社会焉能建立?同时,只有国家机关带头守法,才能带动公民遵守法律义务。因为“卑微的人效仿杰出的人,根据‘他们’表现出的追求来决定自己的兴趣爱好。”(55)国家机关的组成人员被作为精英推举出来管理全社会,他们言行势必影响着全社会,国家公权力侵害公民私权利这样的不公正的事情一旦发生,势必会对全社会起到坏的示范作用,正如西塞罗所说:“对有高位的人来说,他们作恶还不是最大害处,尽管本身已很糟糕,更有害的是他们有很多模仿者。”(56)国家机关既然带头违法,做出不公正的事情,那么它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各阶层纷纷效尤,从而引发更多不公正的事情发生。而公正正是和谐社会所赖以建立的基石,公正一旦被破坏,和谐社会当然也就无由建立。因此,以法律约束公权力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之所在。
五、结语
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实现公正,而要实现公正,就要以法律约束公权力,防止其侵害私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约束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以法律约束公权力,就要分析法律何以无力约束公权力。法律之所以无力约束公权力,表面上的原因在于法律对于公权力没有强制力,这就使得法律在公权力面前形同虚设,不能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正如耶林所说:“背后没有强力的法治,是一个语词矛盾—‘不发光的灯,不燃烧的火。’”(57)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公权力有权追究它认为不符合道德的行为,有权强迫公民履行法律义务以外的道德义务而自己却不履行自己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从而侵害公民的私权利。这种社会不公正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理论根源在于人们没有将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加以区别。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不分使得国家和公民各自应尽的法律义务模糊不清了,从而无法约束公权力。它使得本来仅仅属于公民的道德义务,却因国家公权力的肆意扩张而变成了“法律义务”,如果不能履行这种“法律义务”,公民将会受到严厉制裁;与此相对,本来属于国家法律义务的,却因没有法律强制力作为后盾,而变成了单纯的道德义务。因此追根溯源,正是由于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没有明确的区分造成了法律不能约束公权力这一现象。因此要约束公权力,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从理论上严格区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然后我们才可能用法律来约束公权力,切实建设和谐社会。因为只有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才可能有正确的实践。
在本文修改过程中,山西大学武高寿教授提出了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①《论语·颜渊第十二》。
②《左传·昭公十年》。
③《新书·道术》。
④《论语·里仁第四》。
⑤《论语·颜渊第十二》。
⑥《三国志·杜畿传》。
⑦[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⑧《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
⑨[英]艾玛·阿·里斯特、达·芬奇:《笔记》,郑福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页。
⑩笔者认为,公正、正义含义相近,可通用。
(11)(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13)《论语·述而》。
(14)[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15)《明夷待访录·原君》。
(16)《潜书·室语》。
(17)[英]温斯坦莱:《温斯坦莱文选》,任国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0页。
(18)[荷]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19)《汉书·公孙弘传》。
(20)[古希腊]伊壁鸠鲁:《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包利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21)杨杨:《自述与印象: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7页。
(22)[荷]斯宾诺莎:《政治论》,冯炳昆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8页。
(23)[德]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24)[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25)[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页。
(26)[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24页。
(27)[法]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管士滨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87页。
(28)《吕氏春秋·尊师》。
(29)[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3页。
(30)前注(12),第121页。
(31)[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3页。
(32)参见[荷]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页。
(33)前注(12),第176页。
(34)[英]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57页。
(35)董仲舒:《春秋繁露·威德所生》。
(36)[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页。
(37)《后汉书·陈宠列传第三十六》。
(38)《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9)[法]霍尔巴赫:《自然政治论》,陈太先、眭茂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4页。
(40)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41)《管子·任法》。
(42)《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43)前注(27),[法]霍尔巴赫书,第260页。
(44)[英]雪莱:《雪莱政治论文选》,杨熙龄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页。
(45)“陕西勉县:余震时监考老师先跑将被处分”载http://www.xinhuanet.com/新华网,2008年6月6日。
(46)参见《教师法》第8条。
(47)参见《刑法》第21条。
(48)参见《民法通则》第129条。
(49)参见《教育法》第15条第2款。
(50)参见《教育法》第25条。
(51)参见《行政诉讼法》第14~16条规定。
(5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3页。
(53)《说苑·谈丛》。
(54)[意大利]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0页。
(55)[古罗马]斐洛:《论摩西的生平》,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56)前注(31),(古罗马)西塞罗书,第240页。
(57)[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