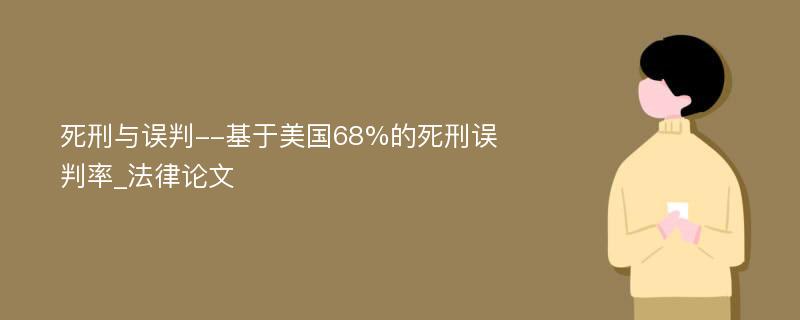
死刑与误判——以美国68%的死刑误判率为出发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死刑论文,美国论文,出发点论文,率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08(2007)01-095-16
2000年6月中旬,美国媒体重头报道了一举世震惊的消息: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项目至2002年才正式结束)表明,美国死刑案件误判率①高达68%,有3个州死刑案件误判率高达100%。这一报道震动了全球法律界,尤其是刑事司法界。我国许多媒体也报道了这一消息[1],有些论著还引用这一结论论证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不合理,难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2](P.318)。
中国死刑的适用范围很广,即使不考虑研究经费的限制以及死刑案件完整的统计资料难以获得,在立法大幅度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之前,在中国进行类似研究都是非常困难的。此外,考虑到中国法学界对死刑的研究目前尚停留在从理论上讨论其存废以及从诉讼程序本身研究如何保障其正确适用,那么美国学者对死刑误判问题进行的精确的定量研究②以及从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多视角对导致死刑误判因素的全方位分析对于中国学者研究死刑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对这一研究结论表示震惊之后,我国却没有学者对这一研究作更深入的探讨,甚至对这一研究作比较全面介绍的论著都尚付阙如。本文试图对这一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结论作一全面介绍,并对其存在的不足及对我国可能具有的启迪价值作一初步分析,以期对我国死刑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以及改革与完善有所裨益。
一、研究的背景与概况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叶,美国犯罪率节节攀升。社会秩序的恶化激起了公众对犯罪的恐惧,赞成死刑的人数随之攀升。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1978年,美国约有62%的人赞成适用死刑,到1994年,这一比例激增到80%[3]。作为对民意的回应,美国联邦国会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叶,美国联邦可适用死刑的罪名拓展到60多项。此外,有些州还通过限制已决犯的上诉权③来加速死刑的执行,意图强化死刑对犯罪的威慑功能。
上世纪90年代中叶以后,美国社会治安有所好转,恶性犯罪率逐年下降,加之在此期间,无辜者在即将执行死刑前被发现无罪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④因而公众对死刑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00年,美国公众对死刑的支持率下降到66%[3],这是自1981年以来最低的。在此背景下,美国政界和法律界出现了反思和主张改革死刑的浪潮。2000年冬至2001年春,美国保留死刑的38个州中有37个州(堪萨斯州除外)酝酿通过制定法律限制死刑的适用。到2002年初,已至少有21州通过了类似立法。新罕布什尔州、俄勒冈州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废除死刑的运动[4](P.1843)。2000年1月,伊利诺伊州州长乔治·瑞安(George Ryan)在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下宣布暂停执行(moratorium)死刑[4](P.1842),并将该州167名死刑犯全部改判为无期徒刑。
在此背景下,各州纷纷推动对死刑的研究。内布拉斯加州立法机关命令成立一个小组,对死刑进行综合研究。内华达州众议院提议并最终通过一项法案,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对本州适用死刑的情况进行全面研究;众议院建议研究委员会考虑扩大DNA测试的适用范围(更好地为罪犯澄清罪嫌)以及禁止对精神障碍者和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可能性。其他许多州,如亚利桑那州、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马里兰州、内布拉斯加州、新泽西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尼亚州等,也都纷纷推动对死刑的研究。在此过程中,美国联邦司法部委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对全美死刑的适用进行研究。⑤这项研究是美国对死刑进行的最完整的一次统计研究,研究对象为1973年1月1日⑥至1995年10月2日23年间美国死刑的适用情况。这一研究由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詹姆斯·S·利布曼(James S.Liebman)教授主持,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许多教授和博士生都参与了这一研究项目。此外,由于该研究涉及到大量社会学和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因而许多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教授和博士生也参与了这一研究。在这一研究中起核心作用的除利布曼教授外,还有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里·费根(Jeffrey Fagan)、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安德鲁·格尔曼(Andrew Gelman)、拉特格斯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生加斯·戴维斯(Garth Davies)、纽约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瓦莱丽·韦斯特(Valerie West)、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统计学系博士生亚历山大·基斯(Alexander Kiss)等。
这一研究于1995年正式启动,2002年结束,前后历时7年。研究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5年至2000年6月,第二个阶段从2000年6月至2002年2月。第一个阶段结束,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份名为《崩溃的制度:1975年至1995年的死刑误判率》(以下简称《报告Ⅰ》)的研究报告,⑦第二个阶段结束,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份名为《崩溃的制度(Ⅱ):为什么死刑案件错误如此之多,应如何应对?》(以下简称《报告Ⅱ》)的研究报告。《报告Ⅰ》主要研究美国死刑误判的现状,全文179页,外加附录270页,近450页。《报告Ⅱ》主要研究美国死刑误判的成因及对策,全文428页,外加附录208页,共600多页。⑦
二、死刑误判的现状
美国实行联邦制,各州在法院设置和审级制度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大致而言,在美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能获得三重救济:一是直接上诉(Direct Appeal),也就是被告方以案件裁判在实体上存在错误为由申请州上诉法院、州高等法院甚至联邦最高法院对案件进行审查;二是州定罪后救济(State Post-Conviction),也就是被告方以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为由要求州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三是申请联邦人身保护令(Federal Habeas Corpus),也就是被告方以宪法权利受到侵犯为由要求联邦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查。
自197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废除此前联邦和各州有关死刑的所有立法,实现死刑制度的革新之后,⑧美国有34个州曾经判处过死刑,但由于有6个州⑨没有一起刑事案件提起过州定罪后救济程序和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在研究死刑误判方面不具有代表性,因而研究人员主要对另外28个州死刑裁判的推翻率进行统计。自1973年至1995年,这28个州作出的死刑裁判中,共有4364件被提起直接上诉,经重新审判,有1782件因为严重错误(serious error)⑩被推翻,推翻率约41%。(11)在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2582件死刑裁判中,有至少248件在此后的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被推翻,推翻率至少约10%。在直接上诉和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案件中,已经提起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的有598件,经审判被推翻的有240件,推翻率约40%。州定罪后救济程序的推翻率为10%,这10%是相对于在此前的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59%(100%-41%)的死刑裁判而言的,相对于全部死刑裁判而言,推翻率为5.9%(59%×10%),约6%。同理,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的推翻率为40%,这40%是相对于在此前的直接上诉程序和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没有被推翻的53%(100%-41%-6%)的死刑裁判而言的,相对于全部死刑裁判而言,推翻率为21%(53%×40%)。三阶段的死刑推翻率相加(41%+6%+21%),总推翻率为68%。这意味着在全美,死刑案件的一审裁判有68%会在此后的救济程序中被推翻,也就是说,每10件死刑裁判中平均约有7件会被推翻。
从各州的情况来看,死刑裁判的推翻率也非常高。在能够计算出推翻率的26个州中,(12)92%的州(24个州)推翻率在50%以上,85%的州(22个州)推翻率在60%以上,62%的州(16个州)推翻率在70%以上,35%的州(9个州)推翻率在80%以上,15%的州(4个州)推翻率在90%以上。此外,还有12%的州(3个州)推翻率高达100%。具体而言,推翻率为100%的三个州是:肯塔基州、马里兰州、田纳西州。推翻率在90%至99%之间的有一个州:密西西比州(91%)。推翻率在80%至89%之间的有5个州:怀俄明州(89%)、加利福尼亚州(87%)、蒙大拿州(87%)、爱达荷州(82%)、佐治亚州(80%)。推翻率在70%至79%之间的有7个州:亚利桑那州(79%)、亚拉巴马州(77%)、印第安纳州(75%)、俄克拉何马州(75%)、佛罗里达州(73%)、北卡罗来纳州(71%)、阿肯色州(70%)。推翻率在60%至69%之间的有6个州:内华达州(68%)、南卡罗来纳州(67%)、犹他州(67%)、伊利诺伊州(64%)、内布拉斯加州(65%)、路易斯安那州(64%)。推翻率在50%至59%的有2个州:宾夕法尼亚州(57%)、得克萨斯州(52%)。弗吉尼亚州和密苏里州的推翻率相对较低,均在50%以下,其中,弗吉尼亚州的推翻率最低,为18%,密苏里州的推翻率次之,为32%。(13)
从纵向来看,自1973年至1995年23年间,美国死刑裁判的推翻率一直非常高。在直接上诉阶段,推翻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其中还有3年(1973年、1975年、1979年)仅在这一个阶段,推翻率就超过60%。(14)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除2年(1993年、1994年)外,在其他年份,推翻率一直都在30%以上,其中还有3年(1980年、1981年、1982年)高达70%以上,有1年(1980年)高达80%。(15)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虽然推翻率相对较低(多数年份在5%以下),但自1975年至1995年,推翻率逐步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自1987年后,推翻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在1987年至1995年9年中,有8年推翻率都在15%以上,有3年推翻率高达20%以上,还有2年推翻率高达25%以上。(16)
三、死刑误判的成因
(一)直接因素
导致死刑误判的直接因素非常复杂。从该项目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被告方律师未能尽到应有的辩护职责。如没有收集到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对有利于被告方的证人未能申请法官通知出庭作证,对控方证据中的虚假或不实之处在审判时未能当庭提出,在控方或法官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时未能及时提出异议,等等。其二是警察和检察官追诉倾向过强。如警察、检察官不收集甚至故意隐瞒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不向辩护方展示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在法庭上故意出示依法不应出示的证据,发表法律禁止的对被告人不利的评论,等等。其三法官行为失当。如法官非法禁止辩护方出示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禁止辩护方对不利于本方的证人进行询问和质证,对陪审团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指示,等等。其中,对被告方权利损害最为严重的是法官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应当判处死刑(17)向陪审团进行指示(instructions)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陪审团将无罪者或没有证据证明有罪者认定为有罪。其四是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如有些法官故意将黑人排除于候选陪审员之外。
由于在不同阶段,法院审查的侧重点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在不同救济程序中,以上因素在导致死刑误判的诸种因素中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有80%的案件(18)因为以上因素导致裁判被推翻。其中,对案件裁判影响最大的是律师辩护的质量,有39%的案件因为被告方律师未能尽到应有的辩护职责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其次是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态度,有19%的案件因为控方故意排除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的证据或有其他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导致案件被误判。与此并列的是法官的行为方式,与第2项因素一样,有19%的案件因为法官在对陪审团进行指示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裁判最终被推翻。最后是法官和陪审员的职业态度,有4%的案件因为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19)
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有74%的案件因为以上因素导致裁判被推翻。与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不同,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对案件裁判影响最大的是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是否妥当,有39%的案件因为法官对陪审团进行指示时存在严重错误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其次是律师辩护的效果,有27%的案件因为辩护律师严重失职导致案件被误判。再次是警察和检察官的职业态度,有18%的案件因为控方故意隐瞒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或有其他违法行为导致被告人被错误地判处死刑。最后是法官和陪审团的职业态度,有7%的案件因为法官和陪审团存在对被告人不利的偏见,如法官故意将黑人排除于候选陪审员之外,导致裁判最终被推翻。(20)
(二)间接因素
影响死刑案件误判率的间接因素也非常复杂。从该项目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九个方面。研究者采用二元逻辑斯特回归分析法(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以及泊松对数回归分析法(Poisson logarithmic regression analysis),对这些因素与死刑裁判推翻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其一是死刑的适用率。通常情况下,指控和适用死刑的比例越高,在证据、事实和法律方面可否适用死刑两可的案件被判处死刑的比例就越高,死刑裁判推翻率也越高;反之,指控和适用死刑的比例越低,两可案件被判处死刑的比例就越低,死刑裁判推翻率也越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死刑的适用率(每1000起谋杀案中适用死刑的案件的数量)由全美的最低点(1,佐治亚州,1995年;宾夕法尼亚州,1979年)上升到全美的最高点(208,爱达荷州,1982年)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几乎增长5倍(由13%上升到75%)。(21)
其二是对严重犯罪适用拘留、(22)定罪与监禁的比例。通常情况下,对严重犯罪适用拘留、定罪与监禁的比例越高,表明该州用以控制和惩治严重犯罪的除死刑以外的替代性措施越广;用以控制和惩治严重犯罪的替代性措施越广,起诉与审判机关在指控和适用死刑以打击犯罪方面面临的压力就越小;起诉与审判机关在指控和适用死刑方面面临的压力越小,可否判处死刑两可的案件被判处死刑的比例就越小;两可案件被判处死刑的比例越小,死刑裁判推翻率就越低。据统计,每100项严重犯罪(23)案件中被监禁的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罪犯由1人上升到4人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由75%下降到36%;每100项严重犯罪中被监禁的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罪犯上升到全美的最高点13人时,(24)死刑裁判推翻率将下降到13%。(25)
其三是死刑案件中从重与从轻情节的数量。死刑是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手段,只应适用于少数最严重的犯罪,因而死刑案件中从重情节越多,死刑裁判被推翻的可能性越低;反之,死刑案件中从轻情节越多,死刑裁判被推翻的可能性越高。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项从重情节,死刑裁判推翻率将降低15%甚至更多,每增加一项从轻情节,死刑裁判推翻率将增长15%甚至更多。(26)
其四是司法经费的多寡以及法院的工作量。通常情况下,司法经费越充足,死刑裁判被推翻的比例越低;反之,司法经费越匮乏,死刑裁判被推翻的比例越高。在美国适用死刑的34个州中,当政府投入的司法经费由平均水平(27)下降到最低点时,直接上诉阶段死刑裁判的推翻率将由25%上升到74%,几乎增长两倍。(28)与司法经费紧密相关的是法院的工作量。在司法经费无法同比增长的情况下,法院工作量也即案件数量的增加意味着法院能够分配到每一案件的经费随之减少,因而与司法经费同死刑裁判推翻率呈负相关关系不同,法院的工作量与死刑裁判推翻率呈正相关关系:法院需要审理的案件数量越大,死刑裁判推翻率越高;反之,法院需要审理的案件数量越少,死刑裁判推翻率越低。(29)
其五是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在美国,公众支持死刑的比例超过主张废除死刑的比例,因而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越高,死刑的适用率就越高。而如前所述,死刑的适用率越高,死刑裁判的推翻率就越高,因而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越高,死刑裁判的推翻率就越高;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越低,死刑裁判的推翻率就越低。在美国适用死刑的34个州中,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法官受到的政治压力处于最低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为16%,当法官受到的政治压力上升到最高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增长2倍。(30)
其六是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与死刑裁判推翻率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在州法院对死刑裁判进行复审的直接上诉阶段以及州定罪后救济阶段,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与死刑裁判推翻率呈正相关关系。在直接上诉阶段,在美国适用死刑的34个州中,当人口密度由最低点上升到最高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由16%上升到60%。(31)但在由联邦法院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的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与死刑裁判推翻率呈负相关关系。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由最高点下降到最高低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由不足30%上升到大约65%。(32)但由于联邦法院系统复审的案件在全部死刑案件中只占很少一部分,因而就全部死刑案件而言,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与死刑裁判推翻率之间仍呈正相关关系。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由最低点上升到最高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增长3到4倍。(33)
其七是低收入群体的人口比例。通常情况下,领取救济金的人口以及州财政收入用于发放救济金的比例越高,死刑裁判推翻率越高;反之,领取救济金的人口以及州财政收入用于发放救济金的比例越低,死刑裁判推翻率也越低。在美国适用死刑的34个州中,在联邦人身保护令阶段,当领取救济金的人口以及州财政收入用于发放救济金的比例由最低点上升到最高点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由20%上升到90%。(34)低收入群体的人口比例与死刑裁判推翻率呈正相关关系可能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相对于白人,黑人的收入通常相对较低,因而低收入群体的比例较高通常意味着黑人比例较高。而由于美国存在对黑人的根深蒂固的偏见,黑人经常被认为与暴力犯罪联系在一起,因而黑人比例越高,法官受社会舆论的影响,适用死刑的比例就越高,死刑裁判推翻率也就随之增高。二是因为低收入者往往被认为更可能实施犯罪,因而低收入群体人口比例过高本身也会增加高收入群体对犯罪的恐惧,导致法官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导致死刑裁判推翻率增高。
其八是黑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如前所述,由于在美国,黑人经常被认为与犯罪,尤其是针对白人的暴力犯罪联系在一起,因而当特定地区黑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增大时,在政治上处于强势地位的白人对暴力犯罪的恐惧就会增加。这种对暴力犯罪的恐惧会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法官对那些应否判处死刑处于两可状态的案件也判处死刑,结果导致死刑裁判推翻率增高。在美国适用死刑的34个州中,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黑人在州总人口中的比例由最低点0.25%(蒙大拿州,1978年)上升到最高点36%(密西西比州,1975年)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大约增长8倍。(35)
其九是针对白人与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当针对白人的谋杀案的比例接近甚至超过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时,白人对犯罪的恐惧会随之增加。白人对犯罪恐惧的增加会形成巨大的压力,使法官在审判时尽可能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导致裁判推翻率增高。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针对白人相对于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由5%上升到100%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将增长1倍;当针对白人相对于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由10%上升到100%时,死刑裁判推翻率大约增长67%。(36)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者认为,要解决死刑误判问题,关键是要控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因为从以上导致死刑误判的9项间接因素来看,有7项因素都是因为其导致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结果导致死刑误判率增高。因而,如果死刑的适用范围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即使存在以上导致死刑误判的诸种因素,也不必然导致误判。而死刑适用范围过广之所以会导致死刑误判率增高,关键原因在于以上因素产生的压力迫使法官将死刑扩大适用于许多证据不太充分、罪行并非特别严重的两可案件,因而要通过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来减少死刑误判,关键是要将死刑的适用严格限制于那些证据充分、罪行极其严重的案件。具体而言,研究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犯罪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度
在英美法系包括美国,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按照这一标准,认定被告人有罪不要求排除“一切”怀疑(any doubt),只要排除“合理的”怀疑即可。研究者认为,就适用其他刑罚,包括长期监禁、终身监禁而言,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都是合理(justified)的,因为如果发生错误,尚有纠正的机会,而就适用死刑而言,仅仅要求排除合理的怀疑是不够的,因为死刑一旦执行就无法补救。近年,美国许多学者都主张提高死刑的证明标准,规定只有达到了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度,才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37)
(二)规定只有在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超过从轻情节、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时才能适用死刑
在美国,根据在审理谋杀案时,从重情节必须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为一级谋杀,从而判处被告人死刑,适用死刑的各州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少数州要求只有在罪行极其严重,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substantially)超过从轻情节,因而只有适用死刑才足以惩罚犯罪从而保护社会时才能适用死刑;多数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等,规定只要从重情节的分量超过从轻情节,哪怕是些微超过,就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还有些州,如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规定即使从重情节的分量与从轻情节的分量大体平衡,也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研究者认为,在从重情节的分量略微超过从轻情节的分量,尤其是从重情节的分量与从轻情节的分量大体平衡时就适用死刑必然导致大量罪行并不严重的被告被判处死刑,导致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死刑误判率增高。因而,美国许多学者主张,立法应明确规定,只有在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超过从轻情节,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时才可适用死刑。(38)
(三)禁止对生理或心理上具有法定从轻情节的被告适用死刑
对于那些生理或心理上存在重大缺陷的被告,研究者主张禁止适用死刑。其一是精神障碍者(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由于精神障碍意味着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减弱,实践中往往是在精神正常者的引诱下实施犯罪的,因而精神障碍降低了行为人的可责性,是法定的从轻情节。(39)其二是未成年人。由于实施了严重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比成年被告人更有可能通过长期监禁得到矫治,因而美国联邦以及许多州都规定,对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40)其三是严重精神错乱者(Severely mentally disordered defendants)。严重精神错乱会影响被告人的行为能力,使其无法有效地协助辩护律师证明自己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不仅如此,对这类被告进行审判并判处死刑需要支付巨额的诉讼成本,以进行医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等方面的鉴定,从而确定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确实严重精神错乱,在诉讼过程中是否有能力放弃权利、供认自己有罪或接受警察调查,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是否可被判处死刑,等等。因而禁止对严重精神错乱者适用死刑近年在美国已成为一般趋势。(41)
(四)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并在作陪审团指示时对此作出明确说明
研究表明,如果能使陪审员确信在彻底矫正好之前,犯罪人将永远呆在监狱里,那么他们通常能够正确确定哪些被告不应当判处死刑而只需判处监禁;研究同时表明,除非审判法官能够使陪审员确信被告不会被假释,否则,陪审员通常不会对犯严重罪行的被告判处终身监禁,而判处其死刑,(42)因而如果法官明确告知陪审团,法律允许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那么,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件将大幅度增加,判处死刑的案件将大为减少。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不仅因为有利于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从而降低死刑的误判率,同时,对严重犯罪适用监禁比例的提高本身也会导致死刑误判率降低,因而美国许多学者都主张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
(五)废除法官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的权力
在美国许多州,法官有权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研究者认为,这实际上是赋予检察官两次请求事实裁判者对罪行并不严重的两可案件判处死刑的权力,是不公正的。此外,由于陪审团是临时组成的,案件审判完毕即行解散,因而不会为寻求连任而屈从于政治压力,而法官在美国多数州都是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并且有一定任期的限制,因而对那些陪审团认为只应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件,法官受政治压力的影响,经常改判为死刑,结果导致死刑适用范围扩大,死刑误判率增高。因而研究者认为,要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就必须废除法官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的权力。(43)
(六)复审死刑案件时进行综合比较,确定哪些案件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推翻那些并非必须判处死刑的案件
为降低死刑的适用率及死刑的误判率,研究者认为,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的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应进行综合比较,确定哪些案件证据充分,情节严重,确实应当判处死刑,哪些案件在事实认定和危害程度上尚有值得斟酌之处,并非必须判处死刑,从而将后一类案件改判为其他刑罚。(44)
(七)要求检察官在提出死刑指控时充分考虑,反复权衡
研究表明,在所有证据都收集齐全之前就匆忙决定提起死刑指控,经常导致因有罪证据不足或此后发现的从轻情节抵消了此前的从重情节而导致误判。不仅如此,由于检察官提出的死刑指控如果此后被非死刑指控取代,或者被陪审团判处非死刑罪名或刑罚,经常被认为是检察官的一种失败,因而这种过分指控一旦提出,又会对检察官产生巨大的压力,促使其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失败,采取一切措施使那些证据并不充分或存在大量从轻情节的案件也被判处死刑,结果导致发生错判。正因为如此,美国许多学者主张对死刑案件制定特殊的起诉政策,要求检察官在决定起诉前反复权衡,尽可能避免提出错误的指控。(45)
(八)确保控方收集的全部有罪和无罪、从重与从轻的证据都能被提交到法庭上
在刑事诉讼中,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案件从重与从轻情节的最佳甚至惟一信息来源是控方的案卷材料,但由于许多州对控方是否必须进行证据展示规定不明,实践中,警察、检察官是否展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往往取决于他们对展示该证据是否会改变案件裁判结果的判断,结果导致在许多州,控方拒绝进行证据展示成为普遍做法。而研究表明,既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同时又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案件错判的风险非常大;研究还表明,依赖陪审团和法官在审判阶段判断哪些案件证据充分,罪行严重,应当判处死刑,哪些案件证据不太充分,罪行不太严重,不应当判处死刑,而法律又不要求控方展示全部证据的案件被错误定罪、判刑甚至将无辜者判决死刑的风险非常高。因而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法律明确规定,控方在提起公诉之前应公开所有案卷材料,将所有证据以及控方卷宗都展示给辩护律师,供辩护律师据以判断案卷中是否有某些材料能够提供给陪审团,用来支持本方的辩护主张或用以证明检察机关的指控不充分。(46)
(九)使判处死刑和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的法官都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
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死刑误判率与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有着紧密的关系。社会公众多数支持适用死刑的政治压力不仅可能使初审法官将大量不应判处死刑的案件判处死刑,而且可能使上诉法官在发现案件被错判时也尽量予以维持而不予改判。为降低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议:(1)采用任命而不是选举的方式产生死刑案件初审以及复审法官。(2)延长法官的任期,无论法官是采用任命还是选举的方式产生。(3)如果法官必须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尽量采用非党派性选举方式,而不采用竞争性选举方式。(4)如果不能放弃经常性的、党派竞争性的法官选举方式,为提高死刑裁判的可靠性,建议改由陪审员决定死刑案件的量刑。联邦最高法院最近指出,这一做法也许是宪法所许可的。(47)
(十)采用合理的方式确定、选任和补偿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吸引大量优秀律师从事刑事辩护
在死刑案件中,为委托鉴定、调查收集证据,辩护律师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经费通常是非死刑案件的很多倍。据推测,在死刑案件中,提供最低限度的有效辩护需要投入的成本,或者说市场上死刑案件通行的收费标准,在美国城市地区通常在5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然而,国家能够补偿辩护律师的费用通常只有市场收费的10%左右,有些州支付5千美元左右,还有些州只支付1000美元,这些费用实际上只够支付在一般盗窃案中进行辩诉交易的费用。过低的法律援助费用导致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往往只有那些缺乏辩护经验、执业能力较低的律师,并且由于经费的限制,他们很少调查收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几乎不寻求专家提供帮助,经常放弃显然有效的提出动议和异议的机会,结果导致控辩双方的力量严重失衡,导致死刑误判的风险增大。
为解决以上问题,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议:(1)确立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的执业标准,规定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律师才能从事死刑辩护;(2)设定法律援助律师的选任方式,尽量避免选择完全免费的律师或靠社会捐助提供辩护费用的律师;(48)(3)为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使其在辩护时有充足的经费作保障,能够聘请专家进行鉴定,聘请调查人员收集对辩护方有利的证据,从而确保辩护质量的稳定、合格。(49)
五、对该研究之评析
(一)关于死刑误判率
尽管前文介绍的美国死刑裁判的推翻率已经非常令人震惊,但实际上,这尚不能完全反映美国死刑裁判被推翻或应被推翻的实际情况,如果能够准确统计和采用更精确的计算方法,美国死刑裁判推翻率可能更高。其一,该项目在计算死刑裁判推翻率时,是以每一阶段已经被推翻的案件的总数除以在该阶段提起上诉的案件的总数,但由于在美国,死刑案件从一审经直接上诉程序、州定罪后救济程序,到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通常要经过10年左右,这必然导致有些在1973年至1995年之间作出,尤其是后期作出的裁判即使是错误的,但到1995年该项目统计截止时上诉程序尚未终结,因而未被计算在被推翻的案件范围之内,(50)结果导致裁判推翻率被低估。其二,由于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实际提起上诉的案件数量无法统计,因而研究者在计算州定罪后救济程序的推翻率时,是以前一阶段,也即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原判,因而有可能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提起上诉的所有案件的总数来替代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实际提起上诉的案件的总数,也即以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被推翻原判的案件的总数除以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原判的案件的总数来计算这一阶段的裁判推翻率。而由于肯定有些案件在直接上诉阶段被维持原判后因为种种原因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没有被提起上诉,因而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实际提起上诉的案件的数量肯定小于直接上诉程序中被维持原判的案件的数量,以后者替代前者必然会导致死刑裁判推翻率被低估。(51)其三,在美国,法院在每一救济阶段均予以维持,最终被交付执行死刑的案件有完整的统计资料,而在救济程序中被推翻原判,未被执行死刑的案件则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这意味着裁判正确的死刑案件不会被遗漏,而误判的死刑案件可能被遗漏,这在客观上极可能导致误判的刑事案件的总数被低估,导致死刑裁判推翻率被低估。(52)其四,研究者计算的被推翻原判的案件的数量只包括那些在上诉过程中被发现存在错误并被法院推翻原判的案件的数量,对那些实际上存在错误但未被发现,以及虽然发现存在错误,但法院基于某种原因而仍然予以维持的案件,(53)均未被计入被推翻原判的案件的范围,这也会导致推翻率被低估。(54)
在该项目的两份研究报告中,“推翻率”与“误判率”经常被混用,在绝大多数本应使用“推翻率”的场合,研究者使用的都是“误判率”或“错误率”。基于表述的方便以及与原文对应,本文在不少本应使用“推翻率”的场合,使用的也是“误判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推翻率与误判率应基本重合,但这两者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肯定有些案件在被推翻原判、发回重审后,初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并无错误,因而再次作出死刑裁判。这类案件被上级法院推翻,因而应当计入推翻率,但由于经初审法院审理认为并无错误,因而应当从误判率中扣除,因此,误判率通常小于推翻率。根据该项目的统计,在被推翻原判的死刑案件中,有18%的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裁判并无错误,被告人应当被判处死刑。(55)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该项目计算的68%的死刑误判率相对于实际误判率被高估了18%呢?
考虑到存在上述可能导致推翻率被低估的因素,回答是否定的。其一,就上述第2项因素而言,其导致推翻率被低估的幅度就达7%。美国学者西夫曼(Shiffman)对1998年至2001年间田纳西州州定罪后救济程序的推翻率进行了精确统计,计算出的推翻率为51%,而本研究计算出的田纳西州州定罪后救济程序的推翻率仅为16%,远远低于西夫曼计算的推翻率。如果美国各州州定罪后救济程序死刑裁判的实际推翻率与本项目计算出的推翻率都存在这种差异的话,那么全美的死刑裁判推翻率就应是75%,而不是本项目计算的68%。(56)这意味着,本项目计算的推翻率比实际推翻率低7个百分点。其二,就上述第4项因素而言,仅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就有44%的案件联邦法院以辩方放弃权利或属无害错误,或两者同时兼备为由对原审裁判中的错误予以忽略而决定维持原判。如果将此类错误计入误判的范围,即使只统计1/3,全美的平均误判率也会从68%上升到73%,(57)净增5个百分点。如果将此类误判全部予以统计,那么平均误判率将上升1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即使仅考虑第2项因素和第4项因素,全美的死刑推翻率就会增长22个百分点,已经足以抵消推翻原判后又被维持原判的案件的比例(18%),再加上尚有其他大量导致推翻率被低估的因素没有考虑(如第1项、第3项),因而美国死刑误判率不低于本项目统计的68%,至少与68%持平是毫无疑问的。
(二)关于死刑误判的成因
从前文的介绍来看,该项目对死刑误判成因的研究似乎已非常全面,既研究了导致死刑误判的直接因素,也研究了导致死刑误判的间接因素;就直接因素而言,既研究了控辩双方,也即辩护律师与警察、检察官方面的原因,也研究了审判者,包括法官和陪审团方面的原因;就间接因素而言,研究者探讨了包括死刑的适用率、司法经费的多寡以及法院的工作量、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等多达九项因素与死刑误判的数量关系。但遗憾的是,研究者却忽视了一些显然与死刑误判关系极为紧密的因素。
譬如,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可能是导致死刑误判的一项重要原因。在研究报告的对策部分,研究者虽然提到,将死刑案件认定有罪的标准由排除合理怀疑提高到排除一切怀疑,将有助于减少死刑误判,但在研究死刑误判的成因时,研究者并没有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缺陷作为导致死刑误判的因素加以研究,因而也就没有具体探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与死刑误判的具体数量关系。其实,排除合理怀疑存在的缺陷可能是导致死刑误判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因。排除合理怀疑的缺陷不仅仅在于其只要求排除合理的怀疑,而不要求排除一切怀疑,也即通常认为只需要达到90%(58)或95%(59)以上的证明程度即可,而不要求达到100%确定无疑的程度,因而可能导致误判,此外,排除合理怀疑的涵义过于抽象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也可能是导致死刑误判的重要原因。在美国,对排除合理怀疑涵义的界定一直见仁见智,从未形成统一的看法。即使是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0年的温希普案件(60)中将排除合理怀疑确定为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之后,美国对排除合理怀疑涵义的界定方法仍然多达数十种,广为流行的也有六种。不仅如此,即使是对这六种流行的界定方式,也有不少学者和法官存在反对意见[5]。既然不同学者、不同法官对排除合理怀疑的涵义都存在不同看法,那么在适用时出现错误、导致误判也就在所难免。
此外,陪审团缺乏正确定罪、量刑的能力可能也是导致死刑误判的重要原因。在美国,死刑案件几乎无一例外都由陪审团审理。传统理论认为,陪审团主要解决事实问题,而事实是一个经验问题,因而外行陪审员是能够胜任的。但实际上,诉讼中的事实认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而总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往往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而陪审团是由法律的外行组成的,对许多基本的法律问题都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一组以佛罗里达州法院的到庭陪审员为研究对象的实验表明,在法官对陪审员进行指示以后,仍然有23%的陪审员认为,当间接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和无罪的可能性各有50%时,也应当认定被告人有罪;只有50%的陪审员知道被告人无需出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有10%的陪审员不知道无罪推定是什么意思;还有2%的陪审员认为证明无罪的责任应当由被告人承担[6](P.480-481)。裁判者对据以作出裁判的法律依据都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误判自然在听难免。
(三)关于解决死刑误判问题的对策
解决问题的对策必须以问题的成因为基础,只有在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源得以消除时,解决问题的对策才是有效的。对死刑误判问题的解决同样如此。但该研究第3部分提出的解决死刑误判问题的对策却并没有严格针对第2部分探讨的导致死刑误判的各项原因。具体而言,在研究者提出的解决死刑误判问题的10项对策中,第1项以及第3至第7项对策指向的都是导致死刑误判的间接因素的第1项,目的在于降低死刑的适用率;第2项对策指向的是导致死刑误判的间接因素的第3项,目的在于降低死刑裁判被推翻的比例;第8项对策指向的是导致死刑误判的直接因素的第2项,目的在于促使警察和检察官全面收集和展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和有利的各种证据;第9项对策指向的是导致死刑误判的间接因素的第5项,目的在于降低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第10项对策指向的是导致死刑误判的直接因素的第1项,目的在于提高律师辩护的质量。就导致死刑误判的直接因素的第3项、第4项以及间接因素的第2项、第4项、第6至第9项而言,研究者则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对策。虽然以上因素有些确实很难改变,甚至无法改变,如黑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针对黑人与针对白人的谋杀案的比例、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等,确实很难改变,但也有一些是可能改变,甚至是比较容易改变的。譬如,缩小严重犯罪案件中保释的适用范围,从而提高严重犯罪案件中监禁的适用比例;通过增加政府对司法的投入或增加法官的职数,从而提高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通过扩大辩诉交易、简易审判等特殊程序的适用范围,从而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调整国家的分配政策,从而缩小低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等等,这些对于降低死刑的误判率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一项历时数年,以解决死刑误判问题为目的的重大研究项目,研究者没有注意到这些显然可行的解决路径,这无疑是一重大缺憾。
六、对中国之启迪
无论是就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以及刑事法学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但囿于篇幅,这里仅从立法,并且主要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就该研究对我国可能具有的启迪价值作一初步分析。
(一)我国的刑事(包括死刑)误判问题现状与成因
我国刑事(包括死刑)误判率比美国高还是比美国低?凭直觉,多数人肯定本能地认为,中国的刑事(包括死刑)误判率绝对比美国低,中国的刑事(包括死刑)误判率不可能达到68%。从现有统计数字来看,这一主观感觉似乎也是正确的。就死刑复核程序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改判的比例通常高于高级人民法院,而最高人民法院改判的比例也就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几[7](P.282)。由于这里的百分之十几和百分之二十几是相对于全部死刑案件而言的,而死刑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只占很少一部分,绝对不超过10%,因而相对于全部刑事案件而言,死刑复核程序改判的比例通常不超过3%(30%×10%)。就审判监督程序而言,改判率通常更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工作报告的统计,2004年,全国法院依法改判确有错误的案件16967件,仅占全年生效裁判总数的0.34%。就二审程序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没有公布全国性统计数字,就笔者在网络上搜索到的地方法院统计的推翻率来看,各地差别很大,多数地方在1%到10%之间,有些地方还不足1%。由于这里的10%和1%是相对于全部刑事二审案件而言的,而全国二审刑事案件相对于一审刑事案件的比例不超过20%,(61)因而相对于全部一审刑事案件而言,二审程序的裁判推翻率通常不超过2%(10%×20%)。以上三阶段相加,中国死刑案件推翻率通常最高不超过6%,普通刑事案件推翻率通常最高不超过3%,与美国死刑案件平均68%,最高100%的推翻率相比,无疑存在天壤之别。
然而,以上统计数字可能只是一种表象。由于我国刑事诉讼的救济机制比美国薄弱得多(下文详述),可能很多刑事案件不是本身没有错误,而是因为救济途径太少或其他某些原因,导致裁判即使存在错误也未被发现,因而没有被推翻。因为就该研究所揭示的导致死刑误判的诸项因素而言,除极少数情形(62),在绝大多数方面,我国与美国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导致刑事(死刑)误判的直接因素而言,我国在该研究揭示的几个方面几乎都存在严重问题。其一,就刑事辩护而言,我国律师辩护率很低,多数地方律师辩护率不足20%。80%的案件根本没有律师提供辩护,意味着绝大多数案件辩护质量都无法得到保障。此外,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由于我国各级财政对法律援助投入的经费非常少,导致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能够得到的经济补偿极其微薄,因而刑事法律援助不仅范围非常窄,而且普遍质量不高。其二,就警察与检察官对证据的收集和展示而言,由于按照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只移送起诉书以及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而各地检察机关又普遍抵制辩护律师到检察机关查阅案卷,结果导致控方收集的大量证据辩护人都无法查阅,许多有利于被告方的证据都被控方“依法”隐瞒。其三,就法官与陪审员的职业态度而言,由于在我国,法官、陪审员与警察、检察官的职责没有被合理区分,法官、陪审员也被要求承担与警察、检察官基本类似的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63)结果导致许多法官、陪审员在法庭上往往倾向控诉方而敌视辩护方:对控方要求出示证据的请求都予以支持,而对辩护方要求出示证据的请求往往予以拒绝;在控方询问证人出现漏洞时积极补充询问,在辩护方询问证人时则经常予以打断、制止,结果导致法庭审判过程中经常出现控审双方联手对抗辩护方的局面。
在导致刑事(死刑)误判的间接因素方面,我国也存在严重问题。其一,就死刑的适用率而言,我国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司法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就立法而言,我国刑法分则十大类犯罪除第9章渎职罪外,其他各章都规定有死刑。刑法分则400多个罪名,规定了死刑的罪名共有70多个。对杀人罪的法定刑,我国刑法还罕见地将重刑规定在前面,轻刑规定在后面,“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也就是说,立法者认为,故意杀人罪通常情况下都应当判处死刑。立法的重刑倾向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也普遍倾向从重判刑。就故意杀人罪而言,实践中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从宽处罚情节,法官通常都倾向判处死刑。尤其是在“严打”期间,除非有法定“应当”从宽处罚的情节,对只有“可以”从宽处罚情节的犯罪,许多法官都不予从宽处罚而直接判处死刑,结果导致我国实践中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的比例非常高。其二,就司法经费以及法院的工作量而言,我国司法系统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仅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10年间,我国刑事案件的数量就整整增加了一倍,而国家对司法系统的投入显然无法实现同比增长,因而各级法院经费都非常紧张,司法人员严重不足。此外,如果考虑到我国法官的工资构成中有一部分必须由法院自筹,那么法院的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其三,就法官受案外各种压力影响的程度而言,我国也存在严重问题。按照我国立法以及实践中的做法,地方人大甚至同级人民政府等许多部门对法院都均有巨大影响力。以人大为例,按照我国宪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各级法院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各级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或罢免,其他法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不仅如此,我国各级法院法官与同级人大任期相同,每届任期五年,五年届满,必须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重新选举或任命。而按法理,人大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必须反映群众的呼声,在我国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倾向重刑,甚至认为现行刑法规定的死刑还不够的情况下,要求各级法院以及法官都必须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必然会导致法官在审判时难以抵制社会公众倾向重刑的压力,在量刑时尽可能判处较重刑罚,将许多不应判处死刑,甚至证据不充分的案件的被告人也判处死刑。(64)其四,就低收入者的人口比例而言,我国同样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随着近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迅速出现了一批高收入群体,但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迅速增长的物质财富未能在全社会实现公平的二次分配,因而贫富悬殊问题在我国异常突出。据报道,我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比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严重。其五,就针对白人与针对黑人的谋杀案的比例而言,我国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我国不存在白人与黑人的种族划分,但却存在基本类似的城乡二元结构。近年,随着城市农村务工人员的增加,以其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犯罪也急剧增加。在许多城市,流动人口犯罪已占全部刑事犯罪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在有些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而农民工犯罪通常都是以非法获取财产为目的,相对富裕的城市居民自然更多地成为他们的犯罪对象。这一现象的蔓延必然导致城市居民对犯罪,尤其是农民工针对城市居民犯罪恐惧的增加,导致法官对犯罪,尤其是农民工针对城市居民的犯罪尽可能从重判刑,甚至尽可能判处死刑。
(二)刑事(包括死刑)误判的发现和纠正必须以严密的救济机制为前提
在美国,死刑裁判推翻率之所以高达68%甚至100%,除因为其死刑案件审判质量较低,死刑裁判存在较多问题外,还有一项重要原因是因为其救济机制非常完备,能够保证死刑裁判绝大多数错误都能得以发现和纠正。
本文第一部分已经提到,美国刑事案件的救济程序包括直接上诉程序、州定罪后救济程序、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三个层次,但这种划分只是对美国刑事案件救济程序的一种类型化概括,实际上,美国刑事案件的具体救济程序远不止这三个层次。在美国,被告人不仅可以直接从实体的角度对案件的定罪、判刑提起上诉(被称为直接上诉),而且可以通过对程序性问题提起上诉来达到推翻实体裁判的目的(被称为间接上诉)。不仅如此,就州司法系统管辖的案件而言,对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问题,在用尽州法院系统的救济途径之后,被告人还可以向联邦法院系统提起上诉。具体而言,如果被告人在州地区法院被认定有罪,那么他首先可以就实体问题向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如果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他可以进一步向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如果州最高法院仍然维持原判,被告人还可以进一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在直接对实体问题提起上诉的同时,被告人还可以通过对程序性问题提起上诉,如以控方某一证据是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应当予以排除,而原审法院没有排除为由提起上诉,来达到推翻实体裁判的目的。在美国,对程序性问题的上诉通常是通过申请人身保护令(65)的形式进行的。申请人身保护令在州法院系统首先应当向案件的初审法院,通常是州地区法院提出。如果州地区法院驳回了被告人的请求,他还可以逐级向州上诉法院、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用尽州法院系统的全部救济之后,如果被告人仍然不服,他还有权进一步向联邦法院系统申请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令在联邦法院系统首先应当向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联邦地区法院如果拒绝了被告人的请求,被告方还可进一步向联邦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如果联邦上诉法院也拒绝了被告人的请求,辩护方最终也可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8](P.599-629)。由以上分析可见,在美国,刑事被告人最多有九次寻求救济的机会。
反观我国,刑事被告人能够获得的救济极其有限。首先,我国几乎没有建立程序性救济机制。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理念上重实体而轻程序,诉讼程序主要被视为实现实体法的一种手段,自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因而除在二审阶段,当事人可仅以程序违法为由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实体裁判外,在其他阶段,程序违法都不构成推翻实体裁判的理由。其次,我国刑事案件的实体性救济机制也非常薄弱。不同于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实行三审终审制以及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弹性审级制,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虽然在判决生效后,被告人还可申请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但由于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特殊救济程序,启动条件极为严格,因而在我国,绝大多数案件被告人都只有接受两次审判、一次救济的机会。再次,就死刑案件而言,救济机制尤其薄弱。就一般刑事案件而言,虽然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条件非常严格,但毕竟尚有启动的机会,而就死刑案件而言,按照现行立法的规定,一旦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予以核准,不管被告人是否服判,都必须立即交付执行,因而被告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申请再审的机会。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已将绝大多数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高级人民法院,而高级人民法院同时又是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结果导致司法实践中死刑复核程序基本上被取消,因而死刑案件被告人在我国实际上只有一次(二审上诉)对裁判表示异议的机会,其能够获得的救济比判处其他较轻刑罚的被告还少,这无疑极不合理。(66)
(三)刑事(包括死刑)误判问题的解决要求进行系统的制度改革
刑事(包括死刑)误判问题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法律以及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要最大限度地解决刑事(死刑)误判问题,必须从以下角度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首先,应改革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刑事诉讼程序存在缺陷是导致刑事(包括死刑)误判的最直接原因,因而要解决刑事(包括死刑)误判问题,首先应当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改革与完善。要改革与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以下措施是必需的: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规定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无钱聘请律师时,都有权得到政府公派律师的帮助;严格规制侦查、起诉机关权力的行使,要求警察、检察机关在收集和出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的同时,也应注意收集和出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强化司法中立,规定法官和陪审员不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职责;将两审终审制改革为三审终审制,使被告人获得更多的救济机会;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使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获得更严密的程序保障,等等。
其次,应完善我国的刑事实体法。如前所述,死刑误判率的高低与死刑适用范围的大小关系极为紧密,而由于死刑的适用范围很大程度上是由刑事实体法决定的,因而要解决死刑误判问题,就必须从实体法的角度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就我国刑法而言,要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至少应注意以下几点:减少规定死刑的罪名,对非暴力性犯罪一律取消死刑;扩大禁止适用死刑的罪犯的范围,规定对精神障碍者(未完全丧失刑事责任能力)、呆傻者一律不得判处死刑;严格控制死缓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规定除在死缓执行期间犯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故意犯罪外,一律不得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加大对可能判处死刑者从宽处罚的力度,规定只要至少有一项从宽处罚情节,被告人就不得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
再次,应改革与完善我国的司法体制。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由于法院的人事、经费等严格受制于地方人大甚至政府等许多部门,因而法官在审判时往往很难摆脱地方人大甚至政府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在全社会普遍倾向重刑的情况下,法官在审判时难免有意或无意地迎合社会舆论或其他外在压力,尽可能对被告人判处较重的刑罚,甚至尽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导致发生误判。因而要解决刑事(包括死刑)误判问题,就必须对我国的司法体制进行改革,使法官在人事、经费等方面能相对超脱于地方,在审判时能免受社会舆论、民愤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另外,应加大政府对司法的投入。案件的审判质量与政府的司法投入有着紧密的关系。通常情况下,政府对司法的投入越充足,法院能够分配给每一案件的资源就越充裕,案件审判质量就越高;反之,政府对司法的投入越紧张,法院能够分配给每一案件的资源就越少,案件审判质量就越低。在我国当前经济条件下,确定政府对司法的投入时,应当做到以下几点:逐年增加对司法的财政拨款,确保司法经费与案件数量以及物价上涨保持同比增长;提高法官待遇,确保法官的经济收入高于同级行政人员;将法律援助费用纳入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项目,并不断提高法律援助费用的比例,最终使所有无钱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能得到政府公派律师的援助,等等。
此外,应努力缩小贫富不均和城乡差距。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贫富不均和城乡差距逐渐扩大。这种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城乡差距如果不能有效缩小,贫困人口,尤其是城市农民工的犯罪率就不会下降。贫困人口和城市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富裕阶层以及城市居民对犯罪的恐惧就不会下降。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法官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倾向判处重刑。因此,要解决刑事(死刑)误判问题,从经济上缩小贫富不均和城乡差距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应努力改变社会公众的重刑观念。虽然司法必须相对超脱于社会公众,从而确保司法的独立与公正,但在现代社会,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最终也来源于公民权利,因而司法权的运作不可能完全不顾忌公众的需求和反应。我国封建社会长期的重刑传统塑造了社会公众普遍的重刑倾向,如果这种重刑倾向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和消解,那么立法和司法界意图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就很难获得社会的支持根基。因此,要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从而降低死刑误判率,从思想意识方面改变社会公众的重刑观念也是非常必要的。
收稿日期:2006-10-15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误判率”实为“推翻率”。“误判率”与“推翻率”是不同的,但由于原报告许多地方将“误判率”与“推翻率”混用,为与原文对应,因而本文对“误判率”与“推翻率”基本不作区分。对于“误判率”与“推翻率”的区别,本文将在第5部分作详细分析。
②西方许多学者正是以死刑误判率过高,并且死刑执行后发现错误很难纠正作为反对适用死刑的一项重要理由。
③在英美法系国家,已生效裁判的救济与未生效裁判的救济未在概念上作明确区分,均为“上诉”(appeal)。
④据统计,自1973年至1995年,美国每执行7至8名死刑犯,就有一名无辜者(参见该研究第二份报告,第377页。该报告的英文名称为:A Broken System,part Ⅱ:Why There Is So Much Error in Capital Cases,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以下简称《报告Ⅱ》);自1973年至2002年1月第1个周,全美有99名死刑犯被证明是无辜的(《报告Ⅱ》第24页)。
⑤由于该项目历时7年,工作量很大,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也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⑥在1972年的弗曼诉乔治亚(Furman v.Georgia)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裁定,美国联邦以及各州有关死刑的立法给予法官和陪审团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武断、不合理,并剥夺了被告人的正当法律程序权”,违背了宪法第8条修正案“不得要求过多保释金,不得科以过重的罚款,不得施以残酷、非常的刑罚”的要求,因而裁决废除美国联邦和各州此前有关死刑的所有立法和所有死刑裁判,并要求此后有关死刑的所有立法都必须遵循该判例设定的公正标准。由于此后美国联邦与未废除死刑的各州有关死刑的立法与此前的相关立法存在很大差异,因而该项目只对1973年以后美国死刑的适用情况进行研究。
⑦这份报告的英文名称为:A Broken System:Error Rates in Capital Cases,1973-1995(以下简称《报告I》)。网址为:http://www2.law.columbia.edu/instructionalservices/liebman/。
⑧这份报告的英文名称为:A Broken System,part Ⅱ:Why There Is So Much Error in Capital Cases,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以下简称《报告Ⅱ》)。《报告Ⅰ》和《报告Ⅱ》均为A4版面。国内尚无中文译本,英文版本可从美国刑事司法改革教育基金会的网站上搜索到,网址为:http://ccjr.policy.net/proactive/newsroom/release.vtml? id=26641。
⑨自1973年以后,美国几乎所有州都要求死刑案件必须自动提起上诉。事实上,实践中几乎所有死刑案件也都被提起了上诉。参见《报告Ⅰ》,第19页。
⑩这6个州是: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俄亥俄州、俄勒冈州。
(11)此处的“严重错误”,是指实体上损害有罪裁断和死刑量刑可靠性的错误。该项目研究的所有推翻原判都是建立在存在严重错误的基础上的。参见James S.Liebman,Jeffrey Fagan,Valerie West,Jonathan Lloyd,Capital Attrition:Error Rates in Capital Cases,1973-1995,Texas Law Review,Volume78,June 2000,p.1851。
(12)就曾经判处死刑的所有34个州而言,共作出了5826件死刑裁判,提起直接上诉的有4546件,经重新审判被推翻的有1852件,死刑裁判推翻率也为41%左右。
(13)有两个州(特拉华州和华盛顿特区)因收集到的数据不完整,无法计算推翻率。
(14)以上数据参见《报告Ⅰ》附录A。
(15)以上数据参见《报告Ⅰ》Figure3,第41页。
(16)以上数据参见《报告Ⅰ》Figure3,第41页。
(17)以上数据参见《报告Ⅰ》Figure4,第42页。
(18)通常情况下,在刑事诉讼中,陪审团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法官认定被告人应当判处何种刑罚。但自上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许多州规定,陪审团对量刑也有一定的建议权。与此相应,法官在对陪审团进行指示时,不仅要就定罪问题进行解释,而且要对量刑问题作出说明。
(19)由于有些案件同时存在以上导致死刑裁判被推翻的因素中的两项或两项以上,因而以上各项因素所占比例相加与以上四项因素总体上在导致裁判被推翻的因素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完全相等。在即将讨论的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同样如此。
(20)参见《报告Ⅱ》,第41页。
(21)参见《报告Ⅱ》,第41页。
(22)参见《报告Ⅱ》,第183页。
(23)此处的拘留是西方意义上的拘留,是对未决犯一种较长时间的剥夺自由,相当于我国的逮捕。
(24)此处的严重犯罪以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布的指标犯罪(FBI Index Crimes)为准。
(25)全美每100名严重犯罪中被监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罪犯的最高人数为13人,最低人数为1人,平均人数为5人。
(26)参见《报告Ⅱ》,第185页。
(27)参见《报告Ⅱ》,第349页。
(28)在美国适用死刑的34个州中,平均司法经费为州人均1.75美元。
(29)参见《报告Ⅱ》,第200页。
(30)参见《报告Ⅱ》,第194页。
(31)参见《报告Ⅱ》,第187页。
(32)参见《报告Ⅱ》,第199页。
(33)参见《报告Ⅱ》,第218-219页。
(34)参见《报告Ⅱ》,第189页。
(35)参见《报告Ⅱ》,第217页。
(36)参见《报告Ⅱ》,第179页。
(37)参见《报告Ⅱ》,第181页。
(38)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1984年通过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也规定:“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
(39)参见《报告Ⅱ》,第400页。
(40)强烈支持死刑的美国刑事司法基金会法律部主任肯特·沙伊德格尔也赞成这一作法:“作为一项政策……一般规则是我们不会将那些真正的精神障碍者交付执行死刑。”见《报告Ⅱ》,第401页。
(41)参见《报告Ⅱ》,第401-402页。
(42)参见《报告Ⅱ》,第403页。
(43)参见《报告Ⅱ》,第404页。
(44)参见《报告Ⅱ》,第406页。
(45)参见《报告Ⅱ》,第407页。
(46)参见《报告Ⅱ》,第409-410页。
(47)参见《报告Ⅱ》,第411-412页。
(48)参见《报告Ⅱ》,第413页。
(49)因为这两类律师在提供法律援助时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作保障,难以保证辩护的质量。
(50)参见《报告Ⅱ》,第418页。
(51)据统计,自1973年至1995年,有高达54%的案件因为结案时间太晚,或者因为复审法院案件严重积压,导致到1995年该研究统计截止时,上诉程序尚未完全终结。参见《报告Ⅱ》,第152页。
(52)譬如,实际推翻率是60%(3/5),但由于州定罪后程序中提起上诉的案件的数量,也即分母被高估,因而实际计算出的推翻率就可能是50%(3/6)甚至是43%(3/7)。
(53)尽管如此,但由于该项目采用了多种途径收集美国死刑案件裁判及其救济情况,据研究者估计,应当收集了大约90%甚至更多的死刑案件裁判及其救济情况,因而这一项目研究结论的可靠度还是很高的。参见《报告Ⅱ》,第16页。
(54)在美国,即使案件实体上存在错误,但法院基于种种技术或政策上的原因,如认为导致案件实体错误的程序瑕疵辩护方未能及时提出(waived error),或属“无害错误”(harmless error)、“非偏见性错误”(non-prejudicial error)等,也可忽略该错误而维持原判。
(55)参见《报告Ⅱ》,第14页。
(56)据统计,有82%的案件法院经重审认为原判确有错误,被告人不应当判处死刑。其中,有9%的被告人完全是无辜的,不构成任何犯罪。参见《报告Ⅱ》摘要。
(57)参见《报告Ⅱ》,第17页。
(58)参见《报告Ⅱ》,第23-24页。
(59)美国华尔兹教授认为,如果用一个一至十分的评分表表示的话,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只需达到九分即可。参见[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60)如在1978年的美国诉费蒂科案件中,初审法院认为将排除合理怀疑界定为达到95%以上的可能性即可。See United States v.Fahco,458F.Supp.388,406(E.D.N.Y.1978),Affd.603,F.2d,1053(2d Cir.1979),cert.Denied,444,U.S.1073(1980)。
(61)Winship,397 U.S.358,364(1970).
(62)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1998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482164件,同期二审刑事案件为70263件,二审率为14.57%。199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540008件,同期二审刑事案件78862件,二审率为14.60%。2000年全国共受理一审刑事案件564023件,同期二审案件87013件,二审率为15.43%。
(63)如对严重犯罪适用拘留、定罪与监禁的比例。
(64)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规定:“人民的司法工作如同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一样,是人民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
(65)在我国实践中,对那些如果证据充分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在证据不足时很少依法宣告无罪,而是作留有余地的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也证明了这一点。
(66)传统上,人身保护令只用作申请法院对政府部门的非法拘禁进行审查。但自上世纪初,人身保护令的适用范围在美国被大大拓展,原则上,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声称他们在宪法上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而州又未能给他们以有效的手段以寻求实现这种权利,那么他们就可以向联邦法院申请签发人身保护令。参见[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著:《美国法律词典》,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292页。
(67)可喜的是,在理论界的大力呼吁下,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规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将死刑核准权正式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