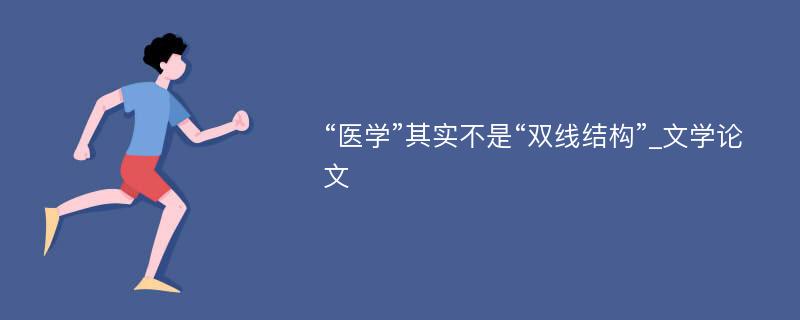
《药》的确不是“双线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91(2002)03-0013-04
《药》是鲁迅的著名小说之一,由于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更是广为人知。同时,《 药》是“双线结构”的说法也广泛流传。
据我所知,最初提出《药》是“双线结构”这一观点的是曾华鹏、范伯群两位先生。 他们在1978年第4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论<药>——鲁迅先生小说研究之一》 。文章在谈到《药》的艺术构思时这样写道:“在一篇不到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同时正 面描写两个故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鲁迅又巧妙地采取双线结构的方式,以明线 来描述华老栓一家的命运,以暗线来叙写夏瑜的故事,两条故事线索像两股山泉,在作 品里并行地奔流着。”此后,“双线结构”的观点就被许多人所盲目服膺。一些具有权 威性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也都采用这一观点。例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 第三册(必修)教学参考书》在讲到“《药》的情节与线索”时就是这样写的:“《药》 的主要情节,由明暗两条线索构成,华家的故事是明线,夏家的故事是暗线。”[1]沈 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语文卷》在“线索”条目中也以《药》作为 “双线”或“复线”作品的范例:“在文章写作中,‘复线’的运用也时有出现。如《 药》就有华小栓吃‘人血馒头’和夏瑜‘英勇就义’这样明、暗两条线索”[2]。
“双线结构”虽然得到许多人的赞同或者默认,然而在我看来,用一明一暗“双线结 构”来概括《药》的结构,是不科学的、不清楚的。这种不科学、不清楚的概括不仅影 响人们对于《药》的结构本身的理解,而且还影响到人们在理论上对于叙事性作品的情 节、线索等概念的理解。
对这种“双线结构”的说法,过去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如湖北的张光怡先生曾于1992 年发表文章对于这种观点进行批驳。他的论文的标题就是《<药>不是“双线结构”》[3 ]。他提出:“教材和教参对《药》的线索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但张先生自己对于《 药》的结构的看法也不准确。他认为《药》是典型的“物线”结构法,贯穿全文的线索 只能是“药”(人血馒头)。因此,张先生的文章对于“双线结构”说的批驳是无力的, 没有能够动摇这种“不准确”观点的权威话语地位。
基于这种情况,本文拟根据自己对于情节线索与叙事线索关系的理解,再次提起《药 》不是“双线结构”话题,指明“双线结构”说“不准确”的症结所在,并阐述自己对 《药》的结构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关于情节线索与叙事线索
对于叙事性作品的“线索”的理解是解释《药》的结构的前提和关键。但理论界对于 “线索”问题至今尚无较为系统的研究,它甚至也是以探讨叙事方式为己任的西方叙事 学的一个盲点。所以我在这里必须首先谈一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据我了解,人们 在使用“线索”这个词说明叙事性作品的情节和结构时,实际上不外乎有两个所指:一 是情节线索,一是叙事线索。
我们先来讨论情报线索。而要讨论情节线索,就不能不从情节开始。在叙事性作品中 ,情节是人物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事件或者事件组合。作品中的人物活动是对现实生活 中人物活动的反映。现实生活中人物活动有着广泛的联系性:或者联系于特定的活动主 体,或者联系于特定的活动目的。反映到作品中的人物活动虽然经过了作家的艺术加工 ,主观想象,体现了作者的意志和情感,但其中一般仍然贯穿着种种的联系。有些描写 意识流的作品看上去似乎所写的事件是杂乱无章的,但意识流本身也是人物的一种有联 系性的活动,只不过它是人们的一种心理活动而已。这些贯穿于人物活动中的联系性就 可以称为情节线索。我们不妨以老舍的《驼驼祥子》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骆驼祥子 》描写了许多活动,如祥子拉车、祥子买车、祥子丢车、祥子的钱被孙侦探诈走、祥子 与虎妞结婚后又买了车、虎妞死后又将车卖掉、祥子道德堕落等。贯穿在这众多的活动 中的联系性是什么呢?那就是祥子为买上自己的人力车而奋斗的经历和结局。在这一联 系性中,活动主体是祥子,活动目的是买车。这一联系性就《骆驼祥子》的最主要的情 节线索。当然《骆驼祥子》中并非只有这一条情节线索。刘四爷的生活经历、小福子的 生活经历也是作品所写的情节线索,但它们不是作品中最主要的情节线索。一个叙事性 作品所写的情节如果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其中必定有一条或一条以上的基本情节线索 。读者把握情节线索比把握情节要困难一些,因为一个作品中的情节是明显出现在作品 中的,而情节线索则往往需要读者凭借生活阅历从情节的显现中去概括出来。
再来看叙事线索,叙事线索是指叙事时所依据的路线,是贯穿于叙事材料之中的脉络 ,是联系、统摄叙事材料的纽带。我们知道,凡是文章都是由话语组成的,而一篇有条 理的文章,其话语总是沿着一定的路线行进的。这路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行文路线或 简称文路。对于叙事性作品而言,行文路线基本上就是叙事路线,也就是叙事线索。或 者可以说,叙事线索是文章的行文路线在叙事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叙事线索不同于情节 线索。情节线索是情节、题材范围内的问题,而叙事线索则是从表达的角度、结构的角 度、文路的角度所作的概括。人们平常在谈论作品的结构时所说的“线索”,就是叙事 线索。叙事线索属于结构的范畴,但叙事线索又不等于作品的结构。结构是一个大于叙 事线索的概念。叙事线索仅仅是作品结构的一个层次,是结构作品的一个手段。譬如, 中国当代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在结构上是倒装的,作品开头写梁冰玉在70年代 末回国探亲,然后再回过头来叙述韩子奇一家人的往事。在探讨这个作品的结构时,我 们首先应确定这个作品是倒装结构,然后才可以在开头部分和主体部分分别去考察它们 的叙事线索。再如要讨论鲁迅的小说《祝福》,也应首先确定它是套装结构,然后才可 以去考察它的不同部分的叙事线索。否则,仅用叙事线索这一概念,是无法解释所有作 品的结构问题的。
情节线索与叙事线索是两个既有联系又含义不同的概念。一方面,叙事线索要以情节 为基础,我们很难看到有哪个叙事性作品完全撇开情节自身的联系性去设置叙事线索。 另一方面,作者常常要在情节线索的基础上从整体结构效果出发去安排设置与情节线索 不完全重合的叙事线索。这就造成了叙事线索与情节线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当某种 情节线索同时也作为叙事依据时,那么它同时也就是叙事线索。例如,老舍的《骆驼祥 子》中,祥子为买车而奋斗的经历和失败结局,既是情节线索,又是叙事线索。再如, 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回国途中和回国后的种种尴尬遭遇也既是情节线索,又是 叙事线索。在一些篇幅较长的叙事性作品中,常常有两条以上的贯穿作品始终的情节线 索。例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有由安娜与渥伦斯基的感情 纠葛和列文与吉提的感情纠葛所形成的两条平行的情节线索。巴金的《家》中有由高氏 三兄弟各自的经历所形成的三条平行的情节线索。这些情节线索同时也是叙事线索。但 在有些作品中,叙事线索与情节线索是不完全统一的。最明显的例子是霍达的《穆斯林 的葬礼》。贯穿于这部小说始终的情节线索只有一条,这就是韩子奇、韩新月一家两代 人的人生磨难、感情纠葛。但作者为了使这部主情主义的作品获得一种类似复调音乐的 特殊结构效果,便将这条情节线索从中部斩断,然后再依据这两段情节线索设置两条叙 事线索,在作品中交错而又平行地展开。
叙事线索与情节线索虽然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确实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以往 人们在谈论叙事性作品中的“线索”时,有时指的是情节线索,有时指的是叙事线索, 有时似乎又均有所指,含混不清。但共同的特点是没有注意到情节线索与叙事线索的区 别。有人喜欢将“线索”与具体的材料的关系比喻为藤与瓜、线与珠的关系,我想这种 比喻是可以被接受的。但藤是什么藤,瓜是什么瓜,线是什么线,珠是什么珠,则是应 当首先搞清楚的。
二、关于《药》的结构
区别了情节线索和叙事线索之后,《药》的结构是不难分析的。
《药》写了两个有密切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故事:老栓买药、小栓吃药、茶客谈论药 的疗效和来源、小栓不治而死因而华大妈上坟是一个故事;夏瑜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 在狱中继续进行宣传斗争、被杀后血被吃、夏四奶奶上坟是另一个故事。虽然由于小栓 吃的药是夏瑜的血而使两个故事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但两个故事仍 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没有疑义的。既然有两个贯穿小说始终的故事,当然也就有两条 基本的情节线索:一条情节线索是华家为小栓买药治病的经历和结局,另一条是夏瑜从 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和结局。这一点我想我与以往的论者没有太大的分歧。
问题主要在叙事线索方面。我认为,《药》只有一条叙事线索,那就是华老栓为小栓 买药治病的经历和结局。这就是以往论者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明确提出的。我们先来看 华家故事的叙述。很明显,华家的故事是依据老栓为小栓买药治病的经历和结局这条情 节线索进行叙述的,买药、吃药、谈药、上坟,四个生活片断的描写都紧紧围绕着这条 情节线索依序进行。因而这条情节线索也就同时成为了华家故事的叙事线索,或者说华 家故事的叙事线索与情节线索在作品中是统一的。但夏家故事的叙事情况则与之不同。 夏家的故事也是依据华家为小栓买药治病的经历和结局这条线索叙述的。鲁迅没有为夏 家的故事另外安排一条叙事线索,而是将其附着在华家故事上进行叙述。附着的方法就 是直接描写与间接描写的结合。《药》除了最后一部分直接描写了两位母亲上坟的场面 外,前面三部分都是直接描写夏家的故事,而间接描述夏家的故事,侧面描写夏家的故 事。那么作品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直接描写与间接描写相结合的附着方法呢?理由很简单 ,就因为夏家故事的叙述借用了华家故事的叙事路线。要按一条叙事线索来叙述两个在 发生场合和发生时间方面不完全相同的故事,可行的方法就是直接叙事与间接叙事相结 合,否则就只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夏家故事的叙述借用了华家故事的叙事线索 这一点在夏家故事的叙事次序上体现得也很明显。作者没有按情节发展的自然联系从夏 瑜的被捕开始叙述夏家的故事,而是让夏家故事的叙述起讫和顺序完全服从于华家故事 的叙述起讫和顺序:先与写老栓买药一起写夏瑜的被杀,再与写小栓吃药一起写夏瑜的 血被吃,然后再借茶客谈论药的疗效和来源的机会回过头去交待夏瑜的被捕和狱中斗争 ,最后与写华大妈上坟一起写夏四奶奶上坟。这样安排正是为了使夏家故事的叙述能够 与华家故事的叙述一致起来,以便使两个故事的叙述使用同一条叙事路线。
至于鲁迅为什么要用华家故事这一条叙事线索叙述华夏两家故事,这里也顺便谈一点 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药》的情节可以用三种方法来叙述。一是像现在所见到的《 药》这样,用华家故事的联系性作为叙事线索来叙述华夏两家的故事;二是使用两条叙 事线索分别叙述华夏两家的故事;三是使用夏家故事的联系来叙述华夏两家的故事,使 用一条叙事线索通过直接描述和间接描述相结合的方法来描叙两个故事,当然是为了节 省笔墨,这是短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追求。所以鲁迅不会采取第二种叙事方法。那么为什 么要让夏家故事的叙述借用华家故事的叙事线索,而不是相反呢?我认为并不是因为那 样写在构思上会更加困难,而是创作意图使然。鲁迅创作《药》,目的是提示群众的愚 昧对于民主革命的制约。所以他要着重展示的不是革命者夏瑜的英勇和高尚,而是群众 对革命的隔膜、冷漠,甚至盲目的敌视。而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应当以华家的经历作为 叙事线索,以便直接重点地描写群众对革命的反应和对革命者的态度。
正是从简洁的艺术追求和《药》的具体创作意图出发,鲁迅采取了用华家一条叙事线 索叙华家、夏家两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结构形式。
三、关于“双线结构”说
我认为,“双线结构”说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双线结构”并没有揭示《药》这个作品只有一条叙事线索的事实。从本文开 头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在曾、范两位先生的文章中,“双线”指的是“两条故事线索” (范、曾两位先生所说的“故事线索”也就是我所说的“情节线索”)。范、曾两先生肯 定已经感觉到这“两条故事线索”在小说的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所以他们用了 “明线”和“暗线”两个词来表达它们。但由于不能在概念上区别叙事线索和情节线索 ,因而他们只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与“明线”和“暗线”模糊地联系在一 起,而不能用“叙事线索”和“情节线索”来明确地界定“明线”和“暗线”。也就是 说,他们所谓的“明线”并不是指叙事线索。因此,《药》只有一条叙事线索的事实在 “双线结构”这个概括语中并没有得到体现。这是“双线结构”说的根本问题。
其次,“双线结构”这个词组本身就包含着逻辑上的矛盾。我们知道,情节线索是存 在于情节内部的联系性,如果不结合它与叙事线索的关系去谈,那它就还只是题材范畴 的问题,而不是结构范畴的问题。只有紧紧围绕着整个作品的叙事安排去考虑,情节线 索才可以进入结构的范畴。就像我们要用一块有图案的布料缝制一件衣服一样,如果不 结合如何剪裁,如何缝制去考虑,那么这块布料上图案间的种种关系就仍然只有衣料范 畴的问题,而不是衣服结构范畴的问题,只有从衣服的整体面貌的角度去斟酌怎样处理 布料上图案间的种种关系,这些关系才具有结构的意义。所以要概括一个作品的结构情 况,只注意它的情节线索而不顾及它的叙事线索,不仅是不全面的、而且是不科学的。 换言之,“双线”与“结构”这两个词在这里是不能搭配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说《药》 是“双故事题材”,但不可以说它是“双线结构”。
再次,曾、范两位先生对于《药》的两条情节线索的认识也不够清楚。例如他们在本 文开头的引文中曾说,“两条故事线索像两股山泉,在作品里并行地奔流着”。实际上 ,两条“故事线索”并没有“并行地奔流”。华家的故事线索是一路向前的,而夏家的 故事线索却是迂回向前的。夏家的故事线索比华家的长,作者将夏瑜牺牲前也就是老栓 买药前的那一段剪了下来,贴在了小说第三部分即茶客谈药那部分上。这怎么能说是“ 并行”呢?
曾、范两位先生毕竟还明确自己提出的“双线结构”说中的“双线”指的是“故事线 索”。而后来的一些服膺者则对这一点也不清楚。例如,《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语 文卷》的“线索”条目中,执笔者一方面界定“线索”是“行文路线”,一方面又大谈 《药》是“两条线索”。[2]
总之,以往被奉为圭臬的关于《药》的“双线结构”说是模糊的、混乱的、不科学的 ,现在到了被扬弃的时候了。我认为,对于《药》的结构情况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小说 以华老栓为儿子买药治病的经历和结局这一情节的联系性为叙事线索,运用直接描写和 间接描写相结合的方法,叙述了华、夏两家有两条基本情节线索贯穿其中的两个相对独 立的故事。为简便起见,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写二”结构。“一”指的是一条叙事线索 ,“二”指的是被叙述的两个故事。
另外,张光怡先生的“药”是《药》的基本线索的观点或者说《药》是“物线”结构 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不错,由于华家吃的“药”就是夏瑜的血,因而这“药”就将华 、夏两家的活动联系了起来。但“药”与“血”的统一所起的作用是对于两个故事的横 向的联结或者粘合,而不是人物活动的纵向的脉络,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药》这篇小 说的叙事线索。这一点我想是不必多说的。
收稿日期:2002-0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