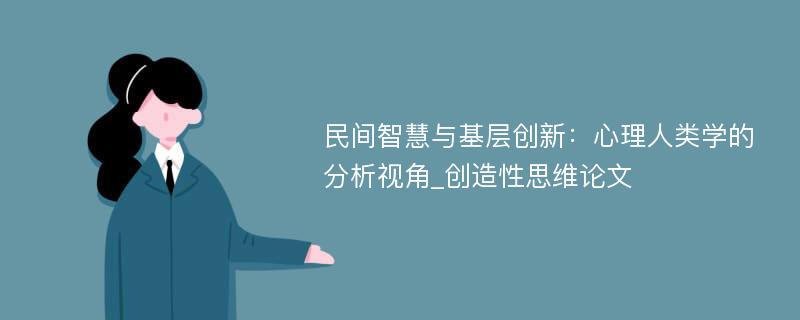
民间智慧与草根创新———种心理人类学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草根论文,视角论文,民间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智慧与创新何以在民间产生? 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这个生物体首要的并且也是时时刻刻都需要处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来分配资源,即:如何来分配机体中保有的水和营养成份。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人们为了在其头脑中有效地构建和维持现代人类文明所设定的世界,花费了巨大的生物能量。现代人类的脑重量大约占据人体体重的2%,而其消耗的能量却占到人体总能量的20%。在所有的人体器官中,没有哪一个像人类的大脑这样消耗了如此之多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脑相当于人体中一个开销庞大的管理机构,其支出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它系统比如心血管系统甚至难以长期有效地支撑和维持其运行。尽管人脑在体内获得了优势资源,但其能量支出也并不是无节制的。事实恰恰相反,人脑在使用心智资源的时候也遵循着“节省律”的原则,即:能少用脑就少用脑,能不用脑就不用脑。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的脑认知系统总是按照一系列既定的规则和方法来处理问题,因为这样做能够有效地节省脑认知资源,所谓的思维定势也由此而生。事实上,人脑所具有的学习能力正是为这种节省律服务的,它帮助人们将其所遭遇的有生存价值的信息保留下来,这样,当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形,他们就能以最有效同时也是最省力的方式做出反应。以学习过程中最基本的所谓“重复效应”为例,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对于同一个客体,人脑对其进行第一次加工和第二次加工(重复加工)时的活动状况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大脑在第二次加工时启动了资源节省机制、以帮助其实现少花力、多办事的目的。 如果我们从上述整体性的生物学立场上来考虑,智慧和创造性思维可算作是人类思维谱系当中的一个“另类”,因为它们要求修改或重塑人们依靠过去的学习和经验辛苦地建立起来的处理问题的程式化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额外的脑力和精力上的支出,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于生物节省律的违背。对于这种另类思维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一个通常的解释是,只有当人们在面临以前所没有遇到的新问题或当那些原有的办法和解决途径无法奏效之时,才会不得不诉诸费时费力的创造性思维,比如由于石油和煤炭能源的诸多弊端而促使人们去考虑开发如何更加绿色环保的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微能源。但也存在许多创新的案例似乎是在原有的方式依然有效的情况下产生的,比如微波炉的发明就并不是因为原来的烹饪加热方式不能使用或不够好用,乃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利益驱动催生了这样的创新思维。美国心理学家斯滕伯格(R.J.Sternberg)提出了所谓创造力的投资理论,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描述这种情形。①该理论认为,可以把某些人一反常态地将心思投注在那些看似不值得花费这么多脑力的普通事物之上的行为理解为一种投资行为,因为他们想要通过新思想新视角使那些看似普通平常的事物实现全新的转变,并最终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升值效果。比如中国艺术家徐冰收集了遭到9.11恐怖袭击的世贸废墟附近的尘埃,并以此作为其艺术作品的原材料,就是一个对于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普通尘埃进行创造性转化并使之成为令人震撼的艺术创作的例子。②斯滕伯格的理论认为,并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时间场合之下都会表现出创造性,他那几乎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假设创造力实际上是由智力、知识、思维风格、人格、动机以及环境等六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只有在这些因素都具备或者都恰到好处的条件下,智慧与创新才会发生。另一方面,从人类文明的历程来看,也并不是所有历史时期所有的人都具有等同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性贡献。事实上,只有在少数历史时期中处于特定机缘上的少数人创造了或至少是有效地总结和提炼了那些使新的文明形态得以成立所必需的思想和方法,而其余的大多数人只是在其后的或长或短的时期中学习、理解并使用这些原则和方法而已。 之所以要在此讨论究竟是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更有可能产生智慧和创造性思维,是因为这涉及到本文的圭题——民间的智慧和创新。当今世界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系统正在变得日益精细化和专门化,除文学创作等少数一些需要相对较少的专门知识的领域之外,大部分领域的创新都需要大量精深的专家知识,这些知识和技能只有经过长期的专门学习和训练才能被掌握,甚至更有一些还需要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的特殊专业领域的第一手阅历经验或者是高级而复杂的专业技术设备和昂贵的实验花销作为铺垫和支撑。作为游离于这些专门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体系之外的民间百姓,他们所能够用于投资创新的知识及其它资本就显得相对薄弱,而在前述更加基本的脑认知资源使用的节省律原则之下,民间百姓更有可能只是创新思想的使用者、追随者而非原创者。那么,在民间何以可能产生智慧与创新呢? 首先,作为社会的主体,广大民众是大部分思想和技术创新的接受者、承担者和使用者。他们人数众多、接触面最广、卷入程度深且情况和条件千差万别,因此比较容易发现其中的问题,这为其智慧与创新提供了前提条件。以2014年国内火车票的网上购票系统为例,该系统是专门的研究机构研发的,其间肯定已经从专业的角度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因素并经过专业的可用性评价,但当其真正投入使用之时,民众仍然发现了其中的许多问题,有的甚至是比较低级的设计缺陷,这是因为不同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网络和电子设备条件及订票环境下超大规模地使用这个系统的缘故。 其次,专业化的研究和知识生产机构虽比较科学和严格,但同时也可能存在过度追求方法的科学性并对全新思路持比较审慎保守态度等方面的局限。与此相比,民间的尝试受到的约束则更少也更加自由,有些创新恰恰在这种自发自由的尝试中产生出来。有事例表明:某些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看似较难解决的问题,采用民间的经验性方法居然得以奏效。比如毒瘾的戒断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生物医学领域尚未解决的一个难题。科学家虽然已经从微观的分子生物学层面到宏观的系统生物学和行为科学层面深入地研究和揭示了成瘾的神经生物学及脑认知科学原理,但是对于应如何帮助人们戒断毒瘾却仍然找不到理想的办法。然而,云南的某个彝族家族利用其传统信仰所采用的戒毒盟誓仪式却使戒毒的成功率和复吸率都远远优于目前医学科学领域的标准方法所能达到的效果。尽管这种戒毒盟誓仪式的适用范围似乎是有限的,但对于发明这种方法的特定的彝族家族而言,他们却是找到了适合于其自身的简便有效的戒毒方法。③再比如人们在经历战争或严重的灾难之后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应激并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如何为这些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援助,帮助他们从应激中恢复过来是灾害心理学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心理学家在5.12汶川大地震的灾后心理援助中发现,当地百姓在临时灾民安置点自发开展的打麻将等娱乐活动,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恢复社会互动获取社会支持,并最终达到减缓焦虑促进睡眠的效果④,而这种源于民间的“麻疗”不但方便易行而且很容易为当地的人民所接受,是专业的心理学人士通常无法想到的。因此,这种民间尝试的自由性、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可以作为系统的专业化的科学探索和知识创新的有效补充的。 再次,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考虑,智慧和创造对于生活在社会相对底层的中国民间百姓而言具有重要的心理意义。跨文化研究表明:对于“是否每个人都需要创新?”这样一个问题,多数中国人回答“是”,而多数美国人回答“否”。可以做个形象的比喻:作为一个社会的普通成员,美国人倾向于将创新看作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食品(比如肉冻),有当然不错,但没有也是完全可以的;而与此相反,中国人则将创新看作是“生存型”的主食(如米饭),人人都要有而且每日都不可或缺。⑤尽管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部分地来自政府的引导,但其中更加深刻的社会心理学原因却在于智慧与创新是民间百姓获得其价值感的一条重要途径。事实上,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在达成对其成员的有效约束、管理、驱动和激励的同时,都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合理的自我价值感,基本的价值感可能包括平等感和自由感,而高层次的价值感则包括优越感和自我实现感。西方社会文化发展出来的模式,是在通过宗教原则以及法律制度保障每名社会成员都具有平等感和自由感的基础上,进而通过个人自由发展和竞争使其能够根据其自身的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优越感和自我实现感。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建构中,并未对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底层成员的平等性和自由性做出信仰上的以及制度上的承诺和保证,因此,人们的价值感是需要其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创造来实现和维持的。例如,老子“以柔克刚”的论断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创造性地为社会的弱势阶层提供了思想武器和价值依据,而庄子故事中的那个著名的异人支离疏则更是通过其身体缺陷这种小的“无用”而创造性地实现了其规避国家和社会强权随意役使的“大用”。 无论人们是通过一种内在的认知重构的方式来获取价值感(如信奉传统道家的修仙隐居或沉溺于武侠和时空穿越);还是采取与外界直接互动的方式,即通过对社会规范的创造性适应或创造性挑战来获取价值感,这些方式都具有三个特点:(1)它们都在实际意义或者是象征意义上挑战了现存的社会规则(在时空穿越的幻想中它们甚至挑战了基本的物理学规则);(2)它们能在不诉诸平等性和自由性等环节的情况下直接引导人们产生出优越感和自我实现感;(3)它们都是一种个人智慧和创造力的高水平发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身处社会底层的百姓会将巧妙地规避或打破社会规则视作是个人获取价值感和优越感的来源。如果说创新过程是一种对于脑认知系统最基本的节省原则的违背,而这种违背又通常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去做的话,那么处于民间的大众很有可能比其他更高的阶层更有理由和动机去创新,因为他们更需要这样一条途径来获取其价值感。 尽管与当今文明世界所公认的、符合官方学术规范的智慧与创新不同,民间的智慧与创新往往来自于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下层或底层,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创造性适应方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在任何特定的社会生态系统中都能将民间的或非民间的智慧与创新截然区分开来。以近年来被热议的所谓民间科学爱好者现象为例,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在十分有限的知识背景和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用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独自钻研如哥德巴赫猜想或相对论等艰深的科学难题,尽管就此行为而言可以说是“民间的”,但就其最初的动机而言却源于官方,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所倡导的“科学的春天”的产物。事实上,现在的民间科学爱好者,其个人心理成长的关键期至少是经历过那个“科学的春天”的时代的,年龄再小的人就不大会表现出对科研的如此热情。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谈论民间的智慧与创新问题时,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而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二、民间智慧与创新的认知过程特征 (一)顿悟与试误 德国格式塔心理学在二十世纪初对创造性思维的产生过程开展了现代科学心理学意义上的研究工作,他们发现包括人和黑猩猩在内的高等生物可以在面临新问题时通过构建全新的知觉或思维“格式塔”(Gestalt,即整体)的形式而产生创造性思维。⑦由于格式塔理论主要建立在对人类知觉过程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不但导致了该学派倾向于将创造性思维的产生过程看作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并在瞬间就充分洞悉和掌握诸要素间内在联系的顿悟过程,同时也导致他们将批评的矛头直指当时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E.L.Thorndike)的尝试—错误理论。尝试—错误理论倾向于将问题解决过程看作是一个盲目的试误过程,即人或动物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情况下,会采取误打误撞的办法,并根据特定的行为能否导致所希望的效果而决定是否采取或保留该行为,从而最终逐步接近正确的解决方案。 然而,当今关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行为学研究却发现:“顿悟”与“试误”似乎并非两个互不相融、相互对立的过程,两者完全有可能相互交织、相互助长。例如,某些看起来是完全随机的尝试可能会因为导致了某些特定的结果或视觉反馈而引发顿悟,从而催生新的更具目的性和组织化特征的系统尝试。这种“试误”与“顿悟”相互交织的创新过程在民间的智慧与创造性思维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这一点在一些社会活动领域可能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对于那些身处特定境遇的人们而言,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应该如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有时他们甚至连自己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获得什么样的状态也并无清晰的认识和了解,他们所具有的可能往往只有模糊的不满、冲动与愿望而已。这种情形就如同伯格森(H.Bergson)在创造进化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尚未进化出眼睛的动物而言,它们也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一种视觉感知能力,而只是抱有一种改变现状的模糊需要而已,乃是这种需要最终促成了创造性适应的产生。⑧比如,2008年在温州街头出现的老人自发组织的舍粥活动,⑨就是一种在现代社会环境背景下试图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体现关爱和平等参与精神的慈善活动,它有别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倡导和有意图的企业策划,是一种民间产生的社会活动创新。但其活动的方式和目标都具有一定的尝试性,实际上是一个“找感觉”的过程。一旦找到了感觉,就会被以更加明确的创新的形式固化下来。例如,“中国大妈”跳广场舞,其实也是一种找宣泄、找归属、找欢乐、找感觉的过程。 (二)学习与创造 我们是一个十分注重学习的民族,有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表明,对于究竟什么才算是创造这样一个问题,西方人认为创造意味着想出全新的或者是原创的东西,而中国人则认为一定要在充分学习和掌握前人的知识、合理吸纳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东西才算是创造。但是,中国人所认为的这种创新性可能更多地存在于正规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之中,那些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研究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但是在民间,这种“先学习、后创造”或“以学习为主,以创造为辅”的程式却不一定总是存在的,这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因为普通的中国人还并不能充分掌握和有效使用当今世界通用的科学技术文献检索和查询系统,有的人大概还存在基础知识上的和外语上的障碍;可能是因为有搞技术的民间人士手头并没有相应的先进技术设备可供使用;可能是因为有的民间学术人士沉浸于传统的中医、易学、玄学乃至传统信仰体系而无法与当今科学观念有机融合;可能是因为有些人出于担心外来的知识会给自己的思想带来束缚或给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体系带来不必要麻烦的考虑而不愿或不能系统学习相关国际科学领域内的理论、范式和发现;还可能是因为在涉及复杂多变的社会变迁及生存技巧方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现成的知识可供学习和借鉴,等等。 这些在学习方面的困难实际上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甚至成就了民间的智慧与创造,使他们能够从行动中学习,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并且得以以一种“直指人心”的方式去直接面对、思考和解决自己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现代心理学关于创造性思维的研究表明,学习过程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人们在学会知识技能的同时,也获得了思维定势,而这些定势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创新思维的障碍,因此,学习与创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成为一对矛盾。尤其是在当今世界以关键科技生长点(如网络和信息技术)为核心迅速膨胀、遍地开花的“碎片化”发展模式之下,传统的体系化知识结构很有可能成为创新思想的障碍。恰恰可能是中国当代民间的智慧与创新在系统知识体系的学习方面的先天欠缺,使其可以更好地适应和利用当今世界的“碎片化”发展方式,并从中获利。 (三)革新与创新 智慧与创新思维最为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当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或当那些原有的解决办法无法奏效之时,可以对旧有的习惯或对当时社会常规的通用的处理方式进行变革。有些变革是深层次的,而有一些则是浅层次或者仅仅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种改进,这样就有了创新与革新之分。比如,中国一汽集团的点焊操作工齐嵩宇发明了一套电阻点焊工艺质量自动监控技术,能够及时发现和补救汽车生产线焊接环节中发生的漏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就是一个典型的技术革新的例子;而与此相比,亨利·福特(H.Ford)将流水线方式引入汽车生产,改变了此前人工制造的方式,并促成整个产业领域制造方式的改变,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深层次的创新。从目前的状况来看,革新仍然是民间创新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最受关注的部分。但事实上,革新的思路不但存在于技术领域,也广泛地存在于民间的文学艺术领域,从戏曲艺人对同一折戏文的反复打磨和改进到影视艺术对同一题材(比如白蛇传)的不断翻拍和演绎,都可以被看作是对原有框架进行革新的范例。 笔者曾从事后的记忆程度以及脑认知信息加工程度等角度比较过人们对于革新与创新产品的信息加工过程,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实验发现:无论是记忆效果还是参与信息加工的脑功能区域的大小,革新的产品均明显大于创新的产品,这是因为革新的东西更加容易与我们以前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建立起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头脑似乎更加倾向于加工革新而不是创新。革新不但比创新更容易为人所理解所接受,而且通常也会比创新更省时省力。相对而言,创新是一种难度大、投入多、风险高的创造过程,所以通常只有在西方新教伦理信念支撑以及相对稳定完善的社会制度保护之下,才更容易出现规模性的、持续稳定的科学技术创新和思想文化创新,而在中国民间往往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革新也有自身的优势,革新投入小而且周期短,吸纳性、灵活性和实用性都比较强;正是凭借这样的特点,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西方在产业技术领域的原始创新优势,使其创新产品的高额获利周期大大缩短。 (四)分析与整合 德国汉学家雷德候(L.Ledderose)通过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品的生产模式,揭示了中国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模件化或模块化思维方式,即中国人会像构建汉字系统那样,通过对某些基本的模件或模块的不断重组而产生出新的创造。⑩从信息加工的角度看,模件或模块的概念与认知心理学中组块(chunk)的概念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所谓“组块”是指一种在长期的学习和训练中形成的知识单元,比如心理学家西蒙(H.A.Simon)等人就曾在一项著名的记忆实验中发现:象棋大师的棋艺之所以高超,其秘诀就在于头脑中储存了关于棋局和对弈态势的大量知识组块可供灵活调用。雷德候通过分析发现的这种模块化创新方式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工艺品生产中也仍然广泛存在。基于“知识或技术模块重组”的创新具有一些特点,首先,它能够实现高效化的创新,尽管创新通常而言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但如果是对现成的模块进行拆分和组合就会相对容易得多,新形式的创造可以在一夜之间被组合而成;其二,它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只要是模块化的东西,就有可能被自由地拆分和组合,而并不会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不同用品的混搭在民间是极为常见的事情;第三,模块组合创新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综合创新,它借助于对各个子系统的重组和集成而实现,但其思考的关注点却并不会触及对基本信息单元以下的元素的分析,这一点与西方注重分析和还原的思维取向是不一样的。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森(S.Ohlsson)从信息加工过程的角度将对知识组块的破解(即所谓“组块破解”)而非知识组块的重组定义为创造性思维,他认为只有打破了原有的组块,达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地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奥尔森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从还原论的角度对创造性思维过程进行界定的方式。(11)有趣的是,汉字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知觉和语义组块系统,汉字中所包含的最基本的信息单元或组块是汉字部首,整个的汉字系统是通过对这些表达一定语义或语音特征的部首的拆分和组合而形成的,而长期流行于我国民间的拆字算卦则是在利用对汉字组块的巧妙拆分和重组的基础上去构建、模拟和预测当事人生活中的关键事件的。笔者曾利用汉字组块性的特点,利用脑成像技术研究和比较了较为常规的汉字部首(组块)水平拆分(如从“旧”中拆出“日”)相比于与较具创造性的汉字笔画水平拆分(如从“四”中拆出“匹”),发现了东方人在脑认知信息加工过程中重“整合”不重“分析”的特点,即大脑在增进“特征整合”层面的思维和信息加工过程的同时,也抑制了“特征分析”层面的加工过程。(12) (五)大C与小c 创造性研究者曾在“大创造性”(大C)和“小创造性”(小c)之间加以区分,“大创造性”指为人类的知识世界所公认的创造性,如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所获得的举世公认的创造性成就;而“小创造性”则侧重于一般人具有的创造性,如通过心理学的纸笔测验所反映的个体创造性。如果从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Popper)所提出“三个世界”区分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划分,则“大C”基本上可以说是属于人们共有的知识文化体系的范畴,而“小c”则更多地具有个人心理和主观世界的意味。作为一种草根阶层的创造,民间的智慧与创新无疑地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小e”,人们根据自己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或所想到的问题,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可能是很有限的知识、能力和资源而构思出来的创造性解决方案,有些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民间创新更是具有自娱自乐的味道,但这些创新与在心理学实验中通常研究的难题不同,它多源于生活并且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方式的巨变,作为“小c”的民间智慧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转变成“大C”的可能性。 三、民间智慧与创新的动机特征 (一)有用与新颖 人们在一般意义上将创造性思维过程看作是一个构建出新颖而有效的问题解决思路的过程,新颖性是指这样的思路并不是人们在通常情况下所采用或者所能够想到的,而有效性则是指对于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或困境而言,这样的思路是适当的。尽管对一项创新而言,新颖和有效是两个密不可分的侧面,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下对这两个方面的侧重仍然可以有所不同。跨文化研究表明,东方人相对比较注重一项创新是否有用,而西方人则对其新颖性的一面更加看重。脑成像研究发现西方被试在看到新异的信息时其脑中负责加工奖赏信息的神经结果会被激活,这表明,不论其有用与否,只要是以前没有见过的新鲜事物,都会使他们获得一种奖赏感。(13)这也就难怪为什么西方民间会产生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发明,而普通民众似乎对此欣赏有加甚至乐此不疲。作为一个靠艰辛的小农生产勉强养活下来的文明,中国人在传统上对于像做无用功这样的浪费是很难接受的,他们甚至很难接受那些与自己当前的生存需要无直接关系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更不要说是花费心思去创造那些没有什么明显用途的东西了。 笔者的实验室也发现,虽然中国被试非常看重创新,但他们对于创新的评价其实是十分苛刻的,假如一项新的发明相对于此前的产品而言在功用方面改进的程度不够大,则就很容易被批判为无用。这种对有用性的苛责在资源匮乏的民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民间的智慧和创新往往都会非常强调其有用性的一面,甚至在一些较为纯粹的理论研究领域,也会强调其实际功效。例如,宋安群的新生物进化论,在理论上总结了生物体在外界刺激作用下所具有的反抗性、平衡性、运动—休息交替性、以及记忆或惯性等基本变化原则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其理论在农业、制药等领域的应用效果,如使试验田小麦增产20%-30%、使棉花结棉桃数增加1倍-2倍、使辣椒抗病性显著提高等。(14) (二)建设与破坏 尽管当谈到高创造性的人物时,人们通常总是想到牛顿、爱因斯坦、达芬奇、释迦牟尼、六祖慧能等这样一些在科学、艺术与宗教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但是,创造力也同样有可能具有阴暗的一面。比如,从单纯的创造性思维的角度来考虑,希特勒及其核心团队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领域都表现出了很高的创造力,在某些军事战略方面其创新性甚至可说远超其同时期许多政界和军界的领袖人物,但他们的这种创造性却最终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将创造性看作是人的“生”的本能的体现,而将破坏性看作是“死”的本能的体现,但却有实证研究发现,儿童在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攻击性行为与其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也就是说,攻击性行为越强的孩子创造性水平越高。 笔者课题组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如果把男女生的数据混合在一起,他们的攻击性分数与创造性思维分数没有相关;如果把男生和女生分开来考虑,女生的攻击性分数与其创造性思维分数表现出负相关的趋势但未达到显著水平,而男生的攻击性分数与其创造性思维分数则呈显著的正相关。这种攻击性破坏性与创造性之间存在的关联可能是因为这两者都包含着一种对现存事物的破坏企图和破坏过程,只是攻击性破坏性重在“破”,而创造性则是“破”、“立”兼重而已。而这种智慧与创新的阴暗面也出现在民间草根之中,这可能与草根阶层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权益较少而所受到的压制较多有关。近年来在网络上出现的针对社会权威的各种妙语连珠“吐槽”正与此种类型心理攻击与宣泄有关。尽管社会上也出现了维护和提升社会正能量呼声,但那些代表正能量的思想在有效调动人们的创造性方面似乎仍难以与那些构思奇妙的吐槽相匹敌。 (三)投资与投机 与破坏性相类似的另外一个民间智慧和创新所可能具有的阴暗面是投机性,虽然前述斯滕伯格的创造力的投资理论在一般意义上描绘了现代人创造力产生的心理学背景,但斯氏的理论主要是在具有相对比较稳定规范的市场规则的情况下才能成立。试想一下,在像传统中国那样一个民生艰难、规矩繁多、管理粗放且在脑认知资源的节省律原则的支配下充斥着不动脑筋的好人的社会里,在那些真正动脑筋的人里面,可能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是在动“歪脑筋”的,他们想的是通过投机取巧的办法来达到一本万利的效果。从古代历史及传说中那些数不胜数的动脑筋的奸臣不断迫害、打压不动脑筋的忠臣的事例,到今天那些炮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高招损招和钻政策法规空子的奇招怪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间智慧和创新所可能具有的阴暗一面,而研究这些对于我们真正理解中国社会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作为人类的智慧与创造性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的智慧与创造性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其自身的心理学特点,而这些特点与草根阶层所处的特定社会地位、所掌握的资源与信息以及所面临的特殊困境有关,从个人化的、心理的视角来分析和看待民间的智慧与创造性或许能够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其本质。 ①Sternberg,R.J.,& Lubart,T.I.An 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 and Its Development.Human Development.1991,34:1-31; Sternberg,RJ,& Lubart,T.I.Buy Low and Sell High:An Investment Approach to Creativity.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1992,1:1-6. ②徐冰:《“9·11”的遗产》,载《南方周末》,2011-09-09.http://www.infzm.com/content/62940,2014年5月9日访问。 ③李宗陶:《彝族虎日戒毒:一次传统文化论的胜利》,载《新民周刊》,2005-02-22。 ④祝卓宏、吴胜涛、王文忠、史占彪、张建新:《打麻将、吸烟、饮酒行为对震后灾区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载《心理科学进展》,2009(3)。 ⑤Niu,W.H.Confucian Ideology and Creativity.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2013,46(4):274-284. ⑥田松:《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7)。 ⑦Kohler W.The mentality of ape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25. ⑧[法]亨利·伯格森:《创造进化论》,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⑨张静:《施粥摊摆上温州街头民政局:是群众自发慈善举动》,新民网,2008-11-27,http://news.xinmin.cn/domestic/shehui/2008/11/27/1450458.html,2014年5月10日访问。 ⑩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1)Ohlsson,S.Information-processing explanations of insight and related phenomena.In:Gilhooley,K.J.(Ed.),Advances in the Psychology of Thinking.Harverster-Wheatsheaf,London,pp.1-44,1992; Knoblich,G.,Ohlsson,S.,Haider,H.,Rhenius,D.Constraint relaxation and chunk decomposition in insight problem solving.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Memory,& Cognition,1999,25,1534-1555. (12)Luo,J.,Niki,K.,Knoblich,G.,Perceptual contributions to problem solving:chunk decompos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Brain Research Bulletin,2006,70:430-443. (13)Lan L.,Kaufman,J.American and Chines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Defining and Valuing Creative Products.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2013,46(4):285-306. (14)有关网站见http://sea3000.net/songanqun/,2014年5月10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