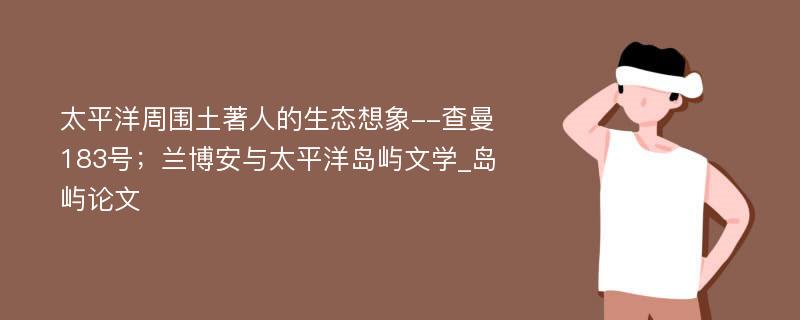
环太平洋原住民的生态想象——夏曼#183;蓝波安与太平洋岛屿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论文,原住民论文,岛屿论文,生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B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1-0132-10
本文探讨台湾海洋作家夏曼·蓝波安跨原住民族的太平洋想象,参照太平洋原住民海洋文学,如汤加作家Epeli Hau’ofa、新西兰毛利族作家Witi Ihimaera以及北美原住民作家Linda Hogan等人的作品,以海洋与岛屿的比较观点,及“流动的主体”概念,强调太平洋另类/原住民(alter-native)航海模式。这一航海模式透过岛屿及海洋景观的主动参与,造就时间与空间的认知,以生态环境与族群记忆带领航行方向,随处充满立足于传统知识、跨越畛域的文化想象,如同实现一段未被“西方文明”轨迹定调的航程,它提供巡航太平洋跨原住民文化想象的“根的路径”,是一个身体、文化皆不被岛屿空间/疆界所限制的主体概念。本文进而由夏曼·蓝波安海洋书写聚焦太平洋原住民的文学/文化特质,以“太平洋”为接触场域、概念与方法,探讨海洋原住民结盟、中心与中心对话、跨原住民流动的典范转移,并由当代跨国主义论述与原住民研究折中处切入,想象跨原住民文化实践的可能,以当代原住民族结盟的“太平洋”拆解大陆/陆地思维,形塑有别于大陆/陆地原住民的海洋原住民想象共同体及其“航行主体”(navigating subject)的“移动性”、“流动性”与“能动性”,开拓原住民研究更宽广的视野。
一、原住民结盟
1989年,美国原住民研究学者Arnold Krupat以“边缘声音—对抗政治”模式(The Voice in the Margin: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anon)建构当代原住民研究方法论,这样的论述存在着“边缘—中心”的高低位阶关系,这又与史书美和Francoise Lionnet在Minor Transnationalism 一书中论述弱势族群的取径相仿。Minor Transnationalism企图为弱势族群文化与全球资本主义和后殖民影响下的“主流—弱势”交互方式引介新的阅读方法,试图将“跨国”(transnational)一词从其全球资本主义与族群吸纳的制式思潮中解放,转化成为“弱势派生”(minority-becoming)概念,认为弱势族群透过全球网络即可不必穿越中心,而依其文化横截性与水平流动性作边陲串连,是“边缘弱势—边缘弱势”的交互方式。然而,这样的交互方式,难道不会在主流强势文化操作中被淹没吗?不同的边缘弱势文化特殊性如何定义?又如何被看到?Chadwick Allen批判当代跨国主义以二元对立的主从关系看待原住民,充满了国家/国族主义的偏见,认为当代原住民研究应以“跨原住民”(trans-indigenous)的新思维与架构,省视原住民文本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反转“边缘—中心”的高低位阶关系,建构“中心—中心”及“原住民—原住民”的对话关系。[1]本文即以Allen之有关环太平洋原住民结盟的论述,作为探讨夏曼·蓝波安海洋书写的依据,逃离国家界线,以广阔的太平洋作为当代原住民文化想象之场域。
近年来试图建构跨原住民结盟的论述俯拾皆是。基于共存共荣的跨原住民性的理念,著名美国原住民研究苏族学者Robert Warrior在2008年即集结多位重量级原住民研究学者创立“美国原住民与原住民研究学会”(Native American and Indigenous Studies Association),五届年会以来,念兹在兹的仍是如何形塑跨原住民认同基础,想象一个跨越国家、地域与国际界线的原住民(研究)社群,追问原住民研究与跨国想象参照并置的基础何在。[2]Warrior在近期再度考掘美国原住民研究跨国转向的可能,以美国研究学会2008—2009年出现原住民会长Philip Deloria为例,阐明原住民研究已然进入美国研究的主流论述,跨国的原住民学者应主导当代文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典范转移,建构含纳原住民经验、历史和现实的学术方法论。[3]原住民论述中少有transnationality或transnationalism等语汇,原因在于原住民的历史现实对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理解,有别于现代性论述中“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思辨方式,美国原住民族称为“印第安民族”(Indian nations),是部落生存主权的宣示,不同于现代国家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及其以民族为群体生活的基本单位所形成的特定政治理念。
2010年,两个重要的国际期刊《美国季刊》与PMLA分别以“原住民性/全球主义”与“海洋研究”作为探索另类接触(alter/native contact)和方法论的场域,两者皆聚焦于跨国/全球想象,也彰显文化流动中原住民议题的重要性,尤以PMLA的专栏“海洋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中Teresia Teaiwa的论文铺陈太平洋视觉文化的“根源”与“路径”,深具启发意义。[4]Middlebrook Jeb主编的《美国季刊》2010年第3期则收录讨论原住民性、种族、性别、当代性、国族、国家权力与全球化现象的相关论文,分为“太平洋空间”、“意外的原住民现代性”、“国家与国族”三大主题,想象美国研究与原住民研究间的另类接触,对原住民研究与跨国主义的交会作了深刻评述。[5]
二、海洋原住民的流动主体
有关跨原住民性的命题,密歇根大学美国研究学者Vicente Diaz的论述可为典范。Diaz身为太平洋岛屿(关岛)查莫罗(Chamorro)原住民,多年来关注跨国文化研究、太平洋研究和原住民研究方法论所构成的三角关系,2001年客座为《当代太平洋》(The Contemporary Pacific)编辑专刊,由“太平洋原住民文化研究”边缘发声,至近期即将出版的论文《主权移动的岛屿》里,[6]提出“太平洋原住民主权”论述。Diaz认为,太平洋海洋原住民的航海文化实践,在来自欧美大陆帝国主义近半世纪的殖民后仍屹立不摇,代代相传,是太平洋原住民串连结盟的依据,成为原初知识(original knowledge)的日常生活实践,其意义有二:(一)在殖民切割的地理位置,以航海知识和航海实践结盟,重新寻回为殖民主义所断裂的政治及文化主权;(二)以原住民跨越领域的海洋论述对抗/批判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的殖民政治。Diaz的“太平洋原住民文化研究”由2001年的“边缘发声”至2010年的“原住民主权”论述,呼应了美国原住民研究由1989年Arnold Krupat的“边缘声音—对抗政治”以至21世纪建构“中心—中心”对话的必然学术转向。
Diaz认为太平洋原住民航海技能代代相传,例如,Caroline Islands称为“伊塔克”(etak/moving island,移动的岛屿)的航行定位知识与西方世界的导航模式不同,成为太平洋岛屿超越国族、殖民以及区域架构限制,由地理所构筑的太平洋共同的文化。“伊塔克”是计算航行距离或航行所在位置的技术,藉由第三岛作为参考坐标,结合对天体的观察,使用三角法测量出发点与目的地间的距离,对太平洋/南岛民族来说,这样的海域空间想象是地图,也是无声的时钟,将时间与空间概念化以定出航行者所在的位置。这项技术在欧洲人开始大航海时代的千年前,就帮助太平洋/南岛民族航行四分之三个南半球,族群散播广大的海域。“依塔克”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制图观念:自我不是经度与纬度的交叉点,不是一个绝对的社会与自然空间,而是像理论与实务的运作——航行者在独木舟上向目的岛屿的星星所在位置方向移动,当作为起点的岛屿消失在视线中时,他开始注意第三岛如何向另一个星座移动,独木舟被视为在星空下静止不动,而岛屿群则在航行过程中不断地掠过,故有“移动的岛屿”之概念。岛屿的移动是一种感知的操作,不以航海图中之俯视角度来压缩和固定空间,而岛屿和宇宙朝向航行者而来。这个“移动的岛屿”概念为原住民及当代跨国文化研究的交会提供一种创新的研究取径,明显不同于西方模式中被动且空缺的空间如“无人之境”和“无人之水”这些被用来合理化疆域扩张的词汇。“移动的岛屿”相互连结的概念,强调在太平洋另类/原住民航海模式中,认知空间和时间需要岛屿及海洋景观的主动参与,而且太平洋原住民对于航海船只的重视,更强调了船只对于构筑岛屿历史的贡献。Diaz也附带提到另一太平洋岛屿原住民航行的“生物定位系统”,称之为“蒲客夫”(pookof),以生态环境带领航行方向。“蒲客夫”是特定岛屿上的特有种生物知识体系,包含各种生物的行为模式与习惯,太平洋/南岛民族藉由生物知识判断他们所处的海域位置,岛屿甚至可以根据生物迁徙的范围放大或缩小,判断岛屿的方式还包括其上空独有的云之形状、洋流与海浪的特征以及星座群等,航海者甚至可以经由嗅觉判断所处的海域位置。太平洋岛屿体现的开放性、内与外辩证的特点反映在陆与海的关系上,随处充满立足于传统知识、跨越畛域的文化想象,由航海原初知识修正当代跨国文化论述,如同是一段航程的实现——一段未被“西方文明”轨迹定调的航程。Diaz对于移动概念的关注提供了巡航太平洋跨原住民文化想象“根的路径”,是一种流动的航行主体的概念——一个身体、文化皆不被岛屿空间的疆界所限制的主体概念。身份认同在岛屿关系中而非在孤立状态下产生,而航程的概念又如同Gilles Deleuze与Félix Guattari所提出的“根茎”,不是找寻起点抑或终点,而是介于两者中间,从二元论逃逸,让既有概念的“唯一真理”松动,强调经由流动而散布的网络,而非结构紧密的树状权力结构,随生态环境/存在结合,取代语言中心主义及语言结构之权力运作,是为建构太平洋跨原住民性的重要取径。
三、夏曼·蓝波安的海洋书写
海洋文化的丰富与辽阔,消融专横霸权的国家疆界,也孕育了夏曼·蓝波安的海洋书写。星辰、风向、海潮、小兰屿暗影都是作家航海的参照坐标。在父祖的海洋故事中,航行的船只,依据Mata no angit(直译成汉语为“天空的眼睛”或“宇宙的眼睛”),对照风向、海潮和小兰屿暗影,在海上用歌谣告诉族人,他们离回航的家还有多远。海上的自我不是经度与纬度的交叉点,岛屿、星辰以及海洋景观具有主动参与的能动性,共同塑造了达悟男人的海洋。
夏曼·蓝波安在2012年出版的小说《天空的眼睛》代序“在冬季的海上我一个人旅行”中,以孩提时的梦境,进入Amumubu(鲸豚)的体内,同游大海的浩瀚。我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鲸豚说:“你的曾祖父跟我说的。”[7]鲸豚身体承载达悟族人的民族记忆,是连结父祖传承的文化载体,与潮间的浮游生物形成绮丽的海洋生态空间,是多元物种繁复的社群,超越人类历史可记的时间,延展为宇宙生态万物的演化时间。夏曼在《兰屿达悟族的海洋知识》中提出“天空与海洋同时是一体的概念”,[8]这在《天空的眼睛》代序中一览无遗。达悟族人在天空里都有其中一颗“眼睛”:“是我的天眼,在没有死亡之前,它会一直照明着我走的路,我生命的力气大的话,或者努力奋斗,努力抓鱼的话,属于我的天空的眼睛将会非常的明亮。”[9]在飞鱼汛期(二月至六月)的五月天,达悟族人随着鲸豚巴瓮飘浮,观看学习海洋的课程,以鲸豚为导师,俯仰之间,天空海洋交融为一体,成为航海的参考坐标。夏曼具现海洋的“多物种社群”(multi-species communities),飞鱼季里,掠食大鱼在飞鱼鱼群群聚的水下尾随浮游,鲸豚一一唱诵大鱼名字:“那些是鲔鱼、黄鳍鲔鱼、浪人鲹、梭鱼鬼、头刀鱼、丁挽鱼、旗鱼等等。”[10]鲸豚巴瓮浮出海面时,像气球似的缓慢浮升,摆尾形成的水压漩涡,浮游生物放射多变的颜色,绮丽色彩瞬间酝成,此刻梦中的孩子说:“天空的眼睛依然令我心情愉悦,我于是仰望许多明亮的眼睛,尔后食指指着一颗最明亮的……愿我自己的灵魂坚实。”[11]Deborah Bird Rose呼吁重新注意把人类与多物种共同体结合的境况/地域连接,这些物种包括曾经被归类于自然的生命或裸命(zoe,bare life),随时会被剥夺消灭,书写多物种社群即在为自然生命列传,使其成为有政治生命的物种(bio),与人类形成共生关系,兼具创造性与能动力。[12]在《物种相遇》(When Species Meet)一书中,Dona Haraway写道:“假如我们领会人类优越主义的愚昧,我们即知‘化成’(becoming)总是‘伴随着化成’(becoming with)的——世界的化成总在紧要关头的接触场域中萌生。”[13]跨物种化成的想法与Gilles Deleuze和Felix Guattari的“根茎”理论若合符节,自然与文化、非人与人类的界线模糊或消失,多物种相遇而产生共同生态的多物种族群。在Alien Ocean 一书中,Stefan Helmreich以崭新的思维,想象海洋/浮游生命与人类生命互相渗透,断言我们正在见证人性也掺杂了其他物种的种性,令物种的垂直/高低位阶关系崩解,人类仰赖海洋生物、大鱼仰赖小鱼、小鱼仰赖浮游生物而存活。[14]
因此,《天空的眼睛》在小说的正式开端,即将叙述分为两线,小说虽以一位历经风霜的老海人为主轴,写他岛上的部落生活、与孙子的相处以及面对远到台湾工作的女儿死讯,然而,在生动的人文写照之中/之外,另有一场海洋生命的生存故事,以“浪人鲹”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者:“此时我的身长已超越一百六十多公分,体重约莫七十多公斤,我这种体型的浪人鲹,他们又称Arilis,他们的祖先说是超越他们想象的浪人鲹巨鱼。达悟人在二月到六月的飞鱼季节猎到我这种鱼,是他们最为兴奋、最骄傲的渔获。”[15]海人的故事是现实的面向,而浪人鲹的叙述则是超越人类历史的神话缘起,传递夏曼一再强调的“原初知识”。浪人鲹由创世说起:天神在海洋开了一道路称之洋流,是飞鱼族群旅行的路线,当时“人与鱼”同时生病,几乎到危及族群、令之灭绝的地步,天神于是请托飞鱼群的头领Mavaheng so Panid(黑翅飞鱼神),托梦给达悟人始祖的先知,令族人学习捕鱼、分类与食物长养生命的方法,因此人类得以存活。鱼类与人类又同样赖海洋为生,黑潮带来浮游生物,成为人鱼共生的起源:“黑潮涌升流的海域,海底海沟宽窄深浅不一,这儿是黑潮南端往西流经的地方,浮游生物多元又丰富,我用腮吸吮浮游粒子来补充养分。”[16]人鱼交融,鱼是人的祖先,又长养人类的生命,是人类知识的起源。人类的故事由鱼的口中/视角述说,老海人的故事也是由老浪人鲹的口中说出,反向拆解人类中心主义。由鱼作为为主体的视角,观看老海人在海洋风浪中与大鱼搏斗的尊荣,评述成熟的达悟男人“最深层的底牌,谦虚的本质,就是凭借猎到的大鱼、飞鱼,或其他珊瑚礁鱼”,[17]成就夏曼所谓“自然人”才有的尊荣、才能参与的与大海生物物种共生的“野性的壮阔奇景”:
上万尾的飞鱼从海里浮冲飞跃,许多的渔夫呐喊着,哇!哇!说是迟,也不算迟,更多的飞鱼自动跃进我的船身内,哇!哇!我的身体也被三、四十尾的飞鱼撞击,显然那位患有幻想症的小子没有对我说谎。哇!这是掠食大鱼在刚入夜之际进行猎杀进食的仪式,这是惊恐的鱼群井然的飞奔,也是稍纵即逝的浪云被我的首航遇见,哇!我说在心里,是幸运也是赞叹的心语,千万尾的飞鱼群飞跃海面一次、两次、三次,之后海洋、飞鱼归于零的宁静,野性的壮阔奇景只留给继续运用初始渔捞渔具的自然人。[18]
如此“自然人”视野里的壮阔奇景,在Witi Ihimaera的《骑鲸人》(The Whale Rider)中,以骑着鲸鱼到新西兰的Pekea创世神话写起。Ihimaera的生态诗学以海洋星球为中心:“突然间,海充满了令人敬畏的歌声。唱着:你召唤我而我带着神的礼物到来。黑色的影子上升再上升,一只巨大的海中怪物突然出现时,飞鱼看到了宏伟巨兽的强大——由海水泡沫的波光闪亮中高高地飞跃而起的鲸鱼。看到跨坐在鲸头上的是个人,骑鲸人看起来很奇妙,水从他两旁涌出,他张开口换气。”[19]《骑鲸人》序幕从飞鱼的视角观看,描述人鲸如同伴/共生之不可分,将非人物种带入一个岛屿的创世史。Ihimaera写人鲸间的密切关联性,像鲸鱼般,骑鲸人从海里冒出头换气,如同《天空的眼睛》的镜像文本;夏曼由鲸写飞鱼,Ihimaera由飞鱼写人与鲸,两个同样书写太平洋海水、生物与岛屿的文本相互呼应。《骑鲸人》序幕后的故事也同样分成两线交融参照的叙述,一个是关于鲸鱼及神话的,以斜体字鲸鱼观点呈现,另一个是人类和现实社会,包括部落和文化政治。这两个叙事交错,使海洋世界充满人性,人的世界又渗透有他物种的色彩,成为跨太平洋、跨族群、跨物种的太平洋生物系谱,抹消人类和动物、自然与文化的人为界线。
《天空的眼睛》是夏曼进入中年的成熟之作,积累数十年的能量,尽情流泻,其过程艰辛漫长。夏曼在青少年时离开兰屿,到台湾求学。之后数十年成为在都市工作的都会原民,并参与了1980年代达悟民族反对台电在兰屿掩埋核废料的抗争,回归到辽阔的海洋,寻找岛民空间、神话和语言,决心成为“真正的达悟男人”:“我想着,这几年孤伶伶地学习潜水射鱼,学习成为真正的达悟男人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能,尝试祖先用原始的体能与大海搏斗的生活经验孕育自信心。用新鲜的鱼回馈父母养育之宏恩,用甜美的鱼汤养大孩子们,就像父亲在我小时候养我一样的生产方式。”[20]夏曼对于敬爱的祖先犹如在身旁守护的亲密描述,让人联想到汤加作家Epili Hau’ofa极具特色的比喻“我们身体里的海洋”(the ocean in us)。海洋联系个体,赋予能量,使个人躯体在回归海洋时成为改变的媒介。在《我们身体里的海洋》一文里,Hau’ofa点出海洋与人体之间微妙的连结,对他而言,“大洋洲”并非意指“国家与国籍的官方世界”,而是指经由海洋血脉“互相连结的世界”,[21]因而,开展了积极扩展大洋洲,以涵盖更大区域及更多物种的可能性。Hau’ofa在文章结尾处指陈:“海是我们彼此间以及和其它人之间的通道,海是我们无尽的传说,海是我们最强大的象征,海洋在你我之中。”[22]
夏曼演绎原住民身体,再现隐藏的过去和压抑的记忆,召唤身体基因作为连结部落知识的场域,和祖先亲密相连——借用莫马戴(N.Scott Momaday)的话即是“身体的记忆”(the memory in the body)——,满溢于夏曼散文的字里行间。这份亲密相连的情感,藉由培养身体的礼节和技艺/技术,以召唤“看海、望海、爱海的遗传基因遗留在自己的血脉里”,[23]忠于原初知识,让身体和自然接触。潜水和标枪捕鱼的身体技能习得唤醒夏曼压抑的基因记忆。跟随飞鱼的路径,夏曼勾勒出移动和逃逸的路径:“飞鱼一群一群的,密密麻麻地把广阔的海面染成乌黑的一片又一片。每群的数量大约三、四百条不等,鱼群队相距五、六十公尺,绵延一海哩左右,看来煞似军律严谨出征的千军万马,顺着黑潮古老的航道逐渐逼近菲律宾巴坦群岛北侧的海域。”[24]飞鱼的“黑色翅膀”每年回来,重复达悟祖先迁徙的路径,也成为族人在海上奋斗的动力来源。海洋的记忆以成群的飞鱼为喻,每一个飞鱼季节,飞鱼的回返延续着在大洋洲岛屿间迁移穿梭的达悟祖先的记忆。多元多样性的生物如“密集的飞鱼群”,海岛居民跟随黑潮的自然节奏跨越疆界。他们的海洋没有疆界,而跨疆越界是达悟族部落族人的特性,也是其他太平洋海岛居民的特性。如Hau’ofa在《我们是海》中明确揭示的:“岛民无法相信其历史开启于帝国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代表着他们族人和文化……他们无法失去和古老过去的连结,而只拥有殖民者所强加的记忆或历史,但现今的跨国体系将他们消融于全球化的浪潮中,完全地泯灭其文化记忆的多样性、社群认知、对祖先和后代的使命,将他们个人化、规格化,并将他们的生活同质化。”[25]两位太平洋作家都在挑战国家/国族典范的正当性,两人皆使用海洋的语汇和海岛的隐喻,追溯殖民者对自然的剥削和广阔海洋景观的图绘,他们皆将生态风险转译为个人和集体的生活叙述。而生态破坏对兰屿岛上的达悟族造成广泛的伤害,兰屿的原住民不仅要和文化失忆及政治专制对抗,也必须对掩埋在他们家乡的核废料抗争。
《海浪的记忆》和《冷海情深》出版相距数年,某些情节隐然延续,老成凋谢,友朋离散,“老人的夕阳已经很低了”。《海浪的记忆》中《树灵与耆老》一篇,老人兄弟的对话被转译为树灵间的对话,树就像人一样有灵魂,凡有灵魂者就是有生命的,自然和部落、老人和树木、客体和主体接续,山海形同日常生活的履践,经验知识源自于自然界,船里的每一片木板就像“上帝”一样神圣,如同是自己的骨肉,上山来探望树灵时,要很虔诚地说:“我是你灵魂的朋友,特别来看你。”[26]树灵与耆老的对话平台立足于达悟族人的生态宇宙观,达悟即是“海洋之子”之意,人需要树木造船、捕鱼,在大海中人与船是一体的,尊敬树是这些住在小岛上的人应有的习俗。耆老们的一生就像平静的大海一样,在一般人透视不到的海底世界,实践他们敬畏自然界神灵的信仰,又从自然界的物种体认到尊重自己生命的真谛。船板破损得不能出海后,耆老就会选择死亡的时间:“我的耳朵经常听到他们说这样的话:‘我在选择我的死亡季节。’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气候、日子、时辰死亡。”[27]耆老与船板生命一体,回归树灵,“我山里的树就送给你造船”。[28]夏曼说:“当时我虽然听得懂我们的语言,却不明白其意思,父亲们惯用被动语态,以鱼类、树名等自然生态物种之习性表达他们的意思。所有鱼类的习性、树的特质、不同潮流等的象征意义,我完全不懂。深山里清新的空气吸来很舒畅,但我却像个白痴。”[29]“被动语态”、“鱼类”、“树名”、“自然生态物种”、“潮流”等环环相扣,逆写“人本主义”的思维,而由都市返乡的“现代”孩子浑然无知,“像个白痴”。这样的世代断裂有赖族老身体实践/展演予以修补:“我仔细地看着长辈们砍树的神情,挥斧的同时,他们长年劳动肌肉呈现的线条,如刀痕般深刻。”[30]山海的经验以身体实践的劳动力为挹注。部落的记忆,沉淀在老人的身体里,伐木如同仪式,经由身体的仪式、身体的礼节、身体的技法、身体的符号系统的展演实践,召唤沉淀的历史记忆。在《冷海情深》的《黑潮的亲子舟》中,夏曼也以和父亲选树、伐木、造船的经过道出一个达悟老人面对生命、生活和大自然的方式与态度。父亲是个“说故事的人”,父亲用诗歌、祝祷、先人的事迹,讲述生活的体验、生命的哲理和属于达悟的风俗与传统,一边叙说——教育作者如何选择材质、如何祝福山林的神祇,一边完成父子俩的造船大业。父亲说起夏曼祖父年少时在海洋的一段经历,如何听从老人家丰富的经验而躲过海上的风暴。这样“口耳相传”的学习方式,使个体的生活经验既独一无二又众纳百川,每一个讲述者与听话者身上同时掺杂着前人与自身的印记,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在不同的实践中获得重生。父亲也教夏曼认识各种树木,并道:“树是山的孩子,船是海的孙子,大自然的一切生物都有灵魂。”[31]人与泛灵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关系是原住民部族书写的主轴,父亲的诗歌、祝祷、故事即是仪式,仪式具有“中介”效应,紧密牵连人与自然、个人与族群。
四、夏曼·蓝波安与太平洋原住民文学的“跨原住民性”文化实践
夏曼跨越人类中心界线,其文化地址逃逸了汉族中心的知识/权力规训,朝向太平洋原住民结盟:
“世界地图是什么意思,一个岛接一个岛在大洋洲,他们皆有共同的理想,便是漂泊在海上,在自己的海面,在其它小岛的海面,去追逐内心里难以言表的对于海的情感。也许是从祖先传下来的话。”达悟就是吃飞鱼长大的不变的真理,飞鱼是生存在海里,千年来此不移的情感,在生出来的那一刻即孕育的了。[32]
这种立足于海洋原住民的论述,重新定义了陆地与海岛的关系,如同Hau’ofa的《我们是海洋》(We Are the Ocean)中的“群岛的海洋”(a sea of islands)之论,崩解了殖民主义的划界,也解构了陆地观看“远洋中散落孤岛”(islands in a remote sea)的思维,转化海洋之“无人之境”为“多物种共生连续”(multispecies connectivities)的繁复绮丽的世界,形塑岛屿/岛民之中心—中心、原住民—原住民的对话与结盟。《我们是海洋》集结Hau’ofa过去三十年来发表的海洋论述,跨越大洋洲,重现蕴藏航海家反身性(reflexivity)和能动的星球图像。作者身体力行,刻画“圈内人”的岛屿观点,创造航海家式的星象海图,其中,《我们的群岛海洋》(Our Sea of Islands)、《我们身体里的海洋》(The Ocean in Us)、《值得铭记的过去》(Pasts to Remember)以及《我们内部的处所》(Our Place Within)四个篇章,呈现了作者追求更强大更自由的大洋洲观点,自诩为“海洋人民”,守护拥有全世界最大水域的太平洋,将海洋视为连系的主体,抗拒殖民霸权在海洋水域切割、将岛民局限在“远洋里的小岛”的分离空间/论述。海洋远古以来就是原住民巡航的航道,拼板舟/独木舟来往频繁,在空间中旅行,在时间里巡航,再现海洋原住民文化为整体,在当今太平洋研究当中,得到许多正面的响应。
岛屿作家为“远洋散落的海岛”注入活力,岛屿成为充满流动性、隐喻、图绘、行动力、社群和希望、相互连结而成的“我们的群岛海洋”。由太平洋内部重新建立的“大洋洲”,成为重建新的太平洋岛民“海洋意识”的方法。夏曼的作品应放置于太平洋原住民作家的网络中阅读,印证“跨原住民性”的文化实践,由原住民文学/艺术/文化想象的交流互通,充实“跨原住民性”的肌理。由文学走向论述的架构,想象力成为社会的实践,如同当代文化论者Arjun Appadurai所言:想象力在全球文化过程中已然具备批判能量,是一种“社会实践”,在个人主体能动与全球文化过程的可能性间协商,其作为社会现实,也牵动全球秩序的重整。[33]从大陆/陆地转向海洋,以“太平洋”为文化生产场域,并由现代性人本思维转向人与非人互为主体的生态伦理,“太平洋”是经由海洋血脉相互连结的世界。在Elizabeth M.Deloughrey的《路径与根:加勒比与太平洋岛屿文学导航》(Routes and Roots:Navigating Caribbean and Pacific Island Literatures)一书中,Deloughrey以陆地和岛屿之间的“潮汐辩证”(tidalectics)为立论依据,检视岛屿作家如何书写“路径”与“根”之间复杂的关系,以海洋为历史,藉由太平洋岛屿航海文学,将跨海洋想象论述化,成就海洋诗学。Deloughrey的语汇是“潮汐辩证”,借用加勒比海诗人、历史学家、理论家Barbadian Kamau Brathwaite于1974年所提出的理论架构,以海洋潮流在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往复循环、持续不断地活动之模式,动摇或颠覆国族、族裔或区域论述之框架,结合交错的史实、跨文化的根源、多元及融合,成为“在海面下的团结/融合”(The unity is submarine)。这样的概念着重地理空间的流动性,强调时间的循环而非线性前进。历史是一个不断被复写的文本,一代又一代,如同海浪一次又一次在沙滩上留下痕迹也带走沙砾,以海洋与岛屿为中心,不以岛屿为弱势边缘,强调文化地理学的模式,以厘清岛屿历史与文化生产,为海洋及陆地、离散与在地以及路径与根之间复杂多变的交错关系提供有力的论述架构。“潮汐辩证”动摇岛屿孤立的迷思,视“岛屿如世界”,将“岛屿世界化”,陆与海之间存有一种充满能量、经常变动的关系,由此我们便可重新检视岛屿文学复杂的空间和历史。
由“潮汐辩证”观看太平洋岛屿文学,首重太平洋的“原住民性”(indigeneity)。原住民的知识系统、文化想象以及自然生态与人类共荣和谐的传统宇宙观是太平洋原住民书写的共同命题,也是夏曼海洋书写持续展延的养分,在集体结盟中创作,又能再现达悟族人独特的智能与知识,并开创承先启后的海洋诗学,应是自称“中年海人”的夏曼现阶段的主要关注点。捕鱼不再只是对治物质/身体饥饿的方法,而是求得灵魂坚实的路径。靠近黑潮水域为太平洋海洋丰富生态系统所滋养,达悟人几世纪以在祖岛Pongso no Tao环境所发展的传统海洋生态知识过着富饶的生活。在1950年代,当时的台湾当局于兰屿本岛建立四个工营、十个退伍军人农场和驻防军队的总指挥部,此后兰屿又成为台电储存核废料的场所,情势严峻;纵使如此,保留在歌谣、神话和故事里的达悟传统知识成为维持海洋文化于不坠的动力。在夏曼新出版的小说《天空的眼睛》里,延续对海洋生态的关怀,展现海洋、星辰与多物种的成熟知识,透过说故事、歌谣、捕鱼及划乘拼板舟的肢体技巧和传承召唤海洋的记忆。有趣的是,在“代序”中,Amumubu(鲸豚)的出现,似乎呼应了Lawrence Buell、Joni Adamson与Jonathan Steinwand等人所谓的生态文学的“鲸豚转向”(cetacean turn)。Lawrence Buell在“Global Commons as Resource and as Icon:Imagining Oceans and Whales”一文中,试图反转海洋与鲸鱼为全球共同消费/滥用的资源和表征的谬误,重新定位两者成为星球想象与意识聚焦的小宇宙。[34]如果像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言:“人性/类在于对他者意图接近”(“To be human is to be intended toward the other”),[35]或如Levinas伦理哲学所标举之对他者的责任观照,那么对Buell而言,海洋与鲸鱼可说是陆生人类演进的他者(radical other),鲸鱼更是海洋生态知识的隐喻。
如何在伦理关系的想象里拆解人本与大陆/陆地中心思维,成为21世纪文学与文化论述最大的挑战,也是以跨原住民观点对比太平洋海洋书写的重要命题。文本例证俯拾皆是:例如,以太平洋西北岸马卡族(Makah)捕鲸传统为主题的两部小说——北美(太平洋西北岸)原住民作家Linda Hogan的People of the Whale(2008年)与太平洋西北岸加拿大原族作家Charles Hall的The Whale Spirit(2000年),即由大陆的越界诗学转向海洋的流动叙事。北美原住民马卡族居住于华盛顿州西北突角的尼湾(Neah Bay)地区,猎鲸是马卡人长久以来重要的经济与信仰活动,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传统延续的意义。20世纪初,马卡族为保护鲸鱼,同意禁止族人猎补鲸鱼,而此禁令于70年后方得恢复。1999年5月17日马卡人捕获灰鲸的当天,美国主要电视新闻网以现场联机方式播出马卡人所有的活动与祭仪,但恢复捕鲸却又代表着复杂且多层次的文化碰撞与冲突,牵动了人类与海洋及海洋生物的互动关系,更可见社会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冲撞及异文化传承之间的运作与角力,在马卡部落、其他原住民部落与美国主流社会都引起诸多的讨论。Linda Hogan以长期与Brenda Peterson所做的灰鲸生态观察记录Sightings:The Gray Whale’s Mysterious Journey为本,[36]将长久赖鲸鱼为生的马卡族人虚拟为小说里的A’atsika族人。A’atsika族人与鲸鱼之间关系亲密,在传统文化中,他们相信自己是鲸鱼的后代,捕鲸更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从捕鲸前后的仪式,到吃下鲸肉的过程,族人的身体与灵魂都与鲸鱼紧紧相连,死后,族人的灵魂会回到海上,变成鲸鱼的一部分。这样的传统部落在白人治理下,逐渐沦为放弃文化传统的弱势族群,以1999年的捕鲸事件为引,作者追溯白人政府长期的殖民暴力,而迄今犹在的欧美帝国霸权与文化优越感,使得海洋民族放弃海洋传统,面临存亡绝续之危机。小说中海洋所塑造的感官经验与身体技法成为部族复原疗伤的触媒,开启主角Thomas记忆的窗口,蛰伏在身体血液中的故事、记忆逐一被召唤出来,形成抗拒大陆霸权殖民条约及政策宰制的力量,个人、社群、海洋/土地及鲸鱼/星球想象合而为一,更展现从地方盱衡寰宇的永续关怀,由生态观点反思原住民传统。Hogan探讨现代原住民必定应对那些考验他们与环境关系的复杂议题。故事中的角色Ruth回想当她和Thomas还小时,鲸鱼往南迁移的情景:“一大群,喷水,它们呼吸的水气上出现彩虹。而当它们北迁时,可以看到小小黑黑的幼鲸闪耀夺目。每个人看着它们通过,尾鳍从水里翘起,水花溅起然后它们潜入水里。”[37]那时有鲸鱼、神奇的章鱼及人类和海洋及其神秘关系的故事。然而,Thomas退役时,部落议会决定部落应藉由重建文化捕鲸业来重拾传统,声称捕鲸将激活经历多年悲惨的高失业率、贫穷、酗酒、家庭暴力及吸毒问题的部落文化和经济。Hogan以古老的人与鲸的盟约,对捕鲸争议采取协商形式,以鲸鱼的观点来看宇宙,以鲸鱼古老智慧指出人类历史的囿限。Hogan写道,鲸鱼身上覆盖着藤壶和其他海洋生物,鲸鱼非个别生物而包含整个宇宙生命,杀死一只鲸鱼,人类便杀死了宇宙里的一个星球,这便跨越人鲸界线,开启了对他物种的视野。正如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言,在星球寰宇间,人类只是过客,星球是我们共同责任,Hogan以海洋的生态诗学,修补人天失落的亲密关系,反思部落文化的现代社会实践,应是太平洋原住民书写的共同取径。
五、结语
新西兰毛利族诗人Robert Sullivan的作品《星舟》(Star Waka)以海洋、星辰构筑舟子,而舟子则是文化载体的隐喻。《星舟》是由101首诗组成的诗组,共2001行,涵盖太平洋巡航、个人与国族、诗人与毛利人双重认同、殖民与当代分歧之政治议题,以及世代交替之中家族的时光递嬗,有古老的神话传说,也描绘90年代居家生活。以文字为“舟”,是毛利语waka的意涵,如同太平洋航程,航行于殖民帝国与太平洋岛屿之间/之外,海航诗歌充满原住民之能动的文化差异面向。夏曼·蓝波安的书写则是达悟族的拼板舟,海洋与星辰交错,以文字为舟,体现跨太平洋海洋原住民的原初知识。2011年在夏威夷举行之APEC领导人会议,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即以夏威夷原住民语OHANA“家人”为喻。[38]这种跨越后殖民太平洋海域的宏观地理与微观政治,其实已是太平洋岛屿原住民千年以来的实践。以原住民之能动熔冶回归广阔的海洋场域,“我们的群岛海洋”是岛民叙述展演与言谈操练的空间,也是永续生存挣扎的场域,蕴含着星球视野与原民能动。如Hau’ofa所言,从一个海岛到另一个海岛,太平洋岛民航行、贸易和婚嫁,也扩展了可供财富流动的社会网络;海洋提供水道,将邻近海岛连结成区域互惠团体,彼此相互融合,让文化特性透过海洋传播;海洋的岛民突破藩篱,他们在故乡周围移动、迁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穷困,而是因为他们被不自然的国界所拘限因而与他们传统的财富资源分隔,他们移徙也是因为“在他们的血液中有移徙的因子”。[39]
如Rob Wilson所言,因有富含蕴育及滋养生命的海洋资源共享,我们可以展望自然生态与人类共荣和谐的未来及跨国合作的可能性,由于海洋构成星球90%的生物圈,星球应该叫做“海”而非“地”(球)。[40]面对人类科技的威胁,海洋需要更宽阔的定位。海洋生物寻求一个更具世界观、能连结跨越藩篱的共居意识,海洋蕴育的生物即可视为星球公民。夏曼·蓝波安的故事、意象和传说透露强烈的海洋共同体意识。人类仰望天空,大鱼猎食飞鱼仰望海面,被猎杀的飞鱼散落海面的波光鳞片,犹如星光一样,海天一气,是为“天空的眼睛”,从达悟族人的观点看,每个人的灵魂都住在某一颗星星里面。太平洋岛民的自我想象是星球的而非陆地的,这是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指的人类未来。对Spivak而言,作为想象平台的不是全球(globe)而是星球(planet)。在本质上,Spivak质问:我们是谁?我们能在何种平台上想象成一个共同体?在Death of A Discipline 一书中,Spivak将星球性(planetarity)定义在地球的物质性(materiality)上,主张人类想象的共同体,不需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这与Laurence Buell所谓的“全球生态情感”(ecoglobalist affect)若合符节。[41]在广义上,“全球生态情感”是对邻近的居住环境有着情感依附,这情感依附至少可定义为某种想象的特定地点和全球区域脉络的繁复联系:邻近和远处、内部和外部、人和非人藉由星球意识与想象,相互依存,拆解国家主义的局限,超越国族,以星球生态环境为依归,形成共有共享的社群,结合海洋原住民特质,转化成星球意识,去人类中心,省思海洋/液态环境、人与动物(非人)的伦理关系,乃为人类演进之自然历程,成就人类永续共存发展的基础。
海洋不是阻隔,而是通路。太平洋的拼板舟/独木舟/星舟,以行动划过海洋,连结起部落与部落、部落与国家、人类与多物种互为主体之生命共同体。在转译跨原住民文本过程中,我们面向的不只是达悟族群的未来,也是世界所面向海洋的未来;不只作为跨原住民族群共同省思,也让世界学习海洋岛屿与岛民的谦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