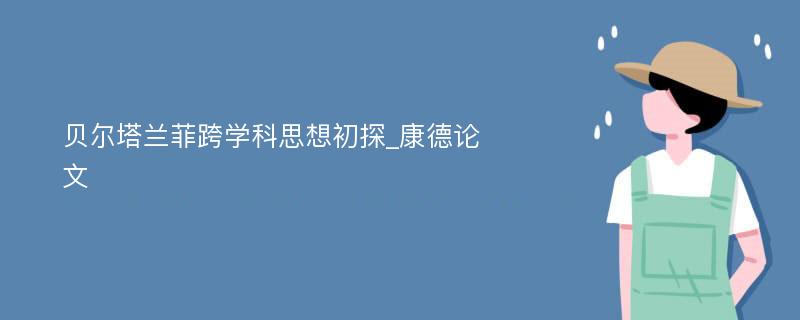
贝塔朗菲的跨学科思想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贝塔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941.1;G304 文献标识码 A
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Bertalanffy L V,1901-1972),既是一位在跨学科研究领域成就卓越的科学家,又对跨学科研究中的理论问题颇感兴趣,有不少很有见地的见解,有必要对此作初步探讨。
1 对跨学科研究的关注
六十年代初,贝塔朗菲在为加拿大爱得蒙顿市艾伯塔大学跨学科教育委员会所写的一份题为《民主制度与社会名流:教育探寻》的研究报告中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研究是某种新东西,是最近十五年以来的发展”[1]。这种观点似乎流传甚广,这种研究的原型是在福特基金会的赞助下,由一个心理学家、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心理分析学家等共同参加的关于行为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某种跨学科研究的计划。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工作与科学一样古老,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学领域以及人文科学中绝大多数伟大的发现都是跨学科的,即都超越了当时存在的“学科”和“学部”的界限。因此,历史上许多成就卓越的科学家都是通才式的跨学科研究者。
在贝塔朗菲看来,就是现代系统方法,也“不能把它看作一时时髦的产物,而应把它看作与人类思想史交织发展的一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最古时代起,在欧洲哲学中就存在系统的观念。”[2]譬如,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哲学科学中,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及其固有的整体论和目的论的观点中,其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就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贝塔朗菲还列举了一系列有系统思想的跨学科研究的思想家,如基督教神秘主义者阿列奥帕基特、十五世纪的大思想家之一——库斯的尼古拉、提出单子等级与现代系统等级观点很相似的莱布尼茨,以及黑格尔和马克思。
贝塔朗菲还举例说,在伽利略奠定物理学基础的时候,他就注意把有计划的观察与数学方法结合在一起,而在此之前它们是分离的。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人文科学中。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Ranke L V,1795-1886)在搜集了维也纳、威尼斯和罗马的档案从而奠定了现代组织论基础的时候,他把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同古文献学、天主教神学、关于教皇的银行业务往来的研究以及一些其他的“专业”都结合起来了。类似地,德国著名语言学家、童话作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之一——格林(Grimm Jakob,1785-1863)发现的语言对应规律——格林定律,也是明显地跨越某种单一学科界限的,它的研究甚至超出了与他直接有关的各种不同的语言学科。英国学者迈·文特里斯(Ventris M)于1953年释读线形文字B之所以能成功,靠的就是把希腊语和某些奇特的,比如象破译古文献密码之类的学科结合了起来。至于要说在达尔文的著作里,以及在诸如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里,一共包含多少不同学科,那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贝塔朗菲还特别强调,以为上述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思想巨人们的事业,或者是由于现代科学的专业和学部还没有形成所引起的,那是一种误解,因为一个完全相似的发展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信息论的创始人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前主席沃伦·威沃尔先生在1961年就曾说过:“大约在1920年,化学和物理学之间的界线就开始消失了。在用途这个层面,例如属于化学的烹调层和属于物理学的五金器具层上,人们仍然可以分辨出两种不同的事物类。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现在已经融为一体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生物学现在正处在完全被其他科学吸引并逐渐消失的过程中。一个现代分子生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超微观的细胞学家。元素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起源,它们现在都已变成一个庞大的问题里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了。”[1]贝塔朗菲认为,沃伦·威沃尔这是对现代科学发展综合趋势的一种极妙的描述。
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趋势,贝塔朗菲可谓感触颇深。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从一个后来叫做‘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传统中教育出来的”[3]。在通向一般系统论的道路上,贝塔朗菲的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得到了来自其他诸多学科的响应,[4]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支持,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尔丁K等人工作的支持。在这一时期,他进一步接触到许多新的学科,特别是维纳的控制论,申农的信息论,冯·诺伊曼与摩根斯坦的对策论,还有洛特卡A对联立方程体系的研究结果,等等。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思想正是在这些学科交织中酝酿成熟的。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评价这一工作时所指出的:“这种综合是前人没有过的尝试。”[5]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1969年年逾古稀时还受聘于美国布法罗(Buffalo)的纽约州立大学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授,更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七十周年诞辰时,国际上的科学家为他举行庆祝会,并出版纪念文集《由分到合》(Unity through diversity)。[5]因为一般系统论是“科学研究的跨学科领域”[6]、是“系统方式的特殊领域”。[6]而作为其中一个方面的系统哲学,则“是由于引进作为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与经典科学的分析的、机械的、线性因果性的范式相反)的‘系统’概念和使用新的认识论范畴而产生的。”[6]
2 从对康德的责难看跨学科研究
系统地研读贝塔朗菲的论著,尤其是读他的代表性著作《一般系统论基础、原理和应用》,其涉及的领域之广确实令人惊叹。在分析人类科学中的“系统”概念时,贝塔朗菲提到了大哲人康德。[7]他指出,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有一句名言,他说有两样东西使他满怀不可名状的敬畏感——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准则!康德的时代正是德意志古典主义的高峰,1800年前后,短短的几十年内,德意志大诗人、大作家、大哲学家群集,而康德正是伽利略和牛顿以来物理科学发展的最高综合。
贝塔朗菲声称,仔细想想康德的言论,我们会感到奇怪,他在能够发现的可敬畏的事物中,他真应该把第三样东西包括进去,康德没有提到生命——生命有机体的奇迹般的组织和领悟物质大世界的精神小世界,这两方面他都没有提到。作为人类理性的巨人,康德的失误是不难理解的。同时,物理学几乎达到了一个顶点,而康德本人,就曾在太阳系的起源的著作中对物理学作出贡献;同时在希腊和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中,道德准则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此相比,生物科学和心理科学的发展才刚刚起步。
对康德的失误的分析,是贝塔朗菲用现代通才的标准在评价康德。
在贝塔朗菲看来,现代科学的各门不同的学科,已经逐渐形成相似的一般概念和一般观点。一般系统论是关于“整体”的一般学科,它比康德学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广泛的适用性。一般系统学会最初的纲领规定,该组织的目的是促进可应用不止一种传统知识部门的理论系统的发展,其主要职能为:[7](1)研究各个领域中概念、规律和模型的同型性,并促进各领域之间有益的转移;(2)鼓励欠缺理论模型的领域发展适当的理论模型;(3)尽量减少不同领域中重复性的理论工作;(4)通过加强各专家之间的交流来促进科学的统一。因此贝塔朗菲这样来描述一般系统论的主旨:[7]
(1)各种不同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走向综合的普遍趋势;(2)这样的综合看来要以系统的一般理论为中心;(3)这样的理论可能成为非物理领域的科学面向精确理论的一种方法;(4)这一理论通过寻找出能统一“纵向地”贯穿于各个单个科学的共性的原理,可使我们更接近于科学大统一的目标;(5)这一理论能够导致迫切需要的综合科学教育。
在贝塔朗菲看来,现代技术和社会很复杂,传统的方法和手段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整体或系统的方法,需要通才或具有多学科知识的人。各级系统都要求进行科学的控制,诸如发生严重环境污染所导致的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国家机关、教育机构或军队等正式组织;社会经济系统、国际关系、政治和威慑中产生的重大问题。不管科学的认识有多么深刻,科学的控制能实施到什么程度,甚至或者要求到什么程度,但实质上存在“系统”问题即关于大量“变数”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不容争议的。技术上要求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提出新的概念和学科,比如控制论、信息论、对策论、决策论、回路理论、排队论等等。这里一般的特点就在于上述理论与学科是特定和具体技术问题的产物,但其模型、概念、反馈、控制、稳定性、回路理论等,已经远远超出专家们的业务范围,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并且独立于他们的专业知识。
提出上述主张,是因为贝塔朗菲目睹了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资料数量庞大,方法技巧和理论结构极为复杂,必然使学科愈来愈专门化。因此,科学被分割为无数的学科,不断产生着新的分支学科。结果,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可以说都囿于他们自己的小天地,作茧自缚,很难互相对话。而实际上,在差异极大的一些领域里,都独自地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和概念,跨学科研究大有可为。正如贝塔朗菲本人曾经指出的,“‘系统’概念是极为宽广的,它描述各种不同学科所研究的大量对象的最一般的特征。一般系统论(原译文为‘普通系统论’,引用时改译为‘一般系统论’——引者。)的跨学科性质由此而来。”[2]l实际上,正如笔者过去在探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时所指出的,贝塔朗菲关于一般系统论的工作就是一种通过“方法的融合”而进行的一种跨学科研究。[8]
3 跨学科研究面临的障碍
现代社会面临日益复杂而综合的各种跨学科课题,进入了真正的大科学时代,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甚至不同文化之间能够进行充分的沟通。但是,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斯诺(Snow C P,1905-1980)在《谈两种文化及再谈两种文化》这一著名的讲演中尖锐地指出的,由于我们的专业化教育的狂热推崇和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社会模式固定下来的倾向,于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两种文化的分裂。一种是人文文化——代表是人文学者,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种是科学文化——代表是科学家,并尤以物理科学家最有代表性。双方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尤其是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之间缺乏理解,甚至还存在着敌意和反感,但大多数是彼此之间缺乏理解,他们对对方都有一种荒谬的、歪曲的印象。他们处理问题的态度是如此不同,以致于在情感的层面上,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人文学者往往习惯于用克制压抑的语气讲话,他们对他们的前辈诚惶诚恐,自愧弗如;他们还特别看不惯科学家那种近乎狂妄的坦率,他们看到科学家们经常兴致勃勃地否定前人的结论和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做出了什么新发现的样子,总感到不舒服。在人文学者看来,科学家是些粗俗不堪、浅薄狂妄的人,他们意识不到人类的处境是多么地令人绝望和悲惨。而科学家又往往觉得人文学者软弱迂腐,无病呻吟,不关心同胞的实际生活,常常陷入一种道德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满足于一种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
斯诺认为,尽管两种文化圈中“两群人智力相似,经历不同,社会出身也没有明显的差别,收入相差天几。但是他们几乎已经完全不再相通,在知识上、道德上和心理气质上,他们的共同点已经如此之少,以至于不象从巴林顿(Burlington House——英国地名,引者)或南肯星顿(South Kensinton——英国地名,引者)到切尔斯(Chelsea——英国地名,引者)去那样,倒象必须越过一个大洋。”
“实际上,人们要走比越过一个大洋更远的路——因为在越过几千英里的大西洋后,人们会发现,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美国纽约市作家、艺术家等聚居的地区,引者)的人和切尔斯的人说的是完全一样的语言,这两个地方又都同麻省理工学院有来往,而科学家们说的却象是西藏的方言。因此,这不只是我们的问题,稍微夸大一些说,应归于教育和社会的一些特性,稍微缩小一点说,应归于英国社会的另一些特性;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整个西方的问题。”[9]
其实,不仅在两种文化之间,就是在人文文化或科学文化内部,也存在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沟通困难的问题。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国际上,“系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吸引了众多领域的专家来从事一些新的研究。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侧面了解到一些特点,从而选择了他们认为适合的名称,但疏忽了这些侧面却通过接口而形成的一个总体,于是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所指出的,“人各一词,莫衷一是”。[10]例如,1976年美国科学院约请一些专家编写了一份讲几个颇具实效的名例的报告,但最后对这个报告的命名却产生了麻烦,于是不得不宣称采取权宜之计,妥协命名为“运筹学/系统分析”。类似地,英国曾出版“国际系统工程学报”,问世不久,为了避免读者甚至是投稿人对“工程”一词的过分狭义理解,于是便改名为“国际系统分析学报”。
斯诺认为,两种文化的分裂对社会是一种损失。一个人文学者不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好比一个科学家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文化的分裂会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再也无法在同一水平上共同就任何重大社会问题开展讨论。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了解一种文化,因而会使我们对现代社会作出错误的解释,对过去进行不适当的描述,对未来做出错误的预测。
贝塔朗菲认为,斯诺所讲的两种文化的对立,即科学与人性、技术与历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诸如此类的对立是跨学科研究的最大障碍。因此,他发誓要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设桥梁,[7]使两种文化在大科学时代充分沟通。贝塔朗菲深深地感到,教育与现代社会的迫切需要已经不相适应了。但遗憾的是,人们对“跨学科的”、“综合性的”,也就是“通才”(Generalist)教育的责难还不时听到。尽管这种责难来自不同的源头和阶层,但大致可以把它们归结为三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那些现代社会中的专门化了的学科及其学者们会感到不那么舒服。这就是把现代人装进去的那种“胶囊”(encapsulation)。他们的智力世界往后退缩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厉害,甚至于象得了神经性精神病那样,在狭窄的领域里激烈地竞争。
第二,有些人甚至认为专门化还不够。实际上,如果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对于我们文明的历史基础和社会问题的动力知道得多一点,或者历史学家对于人与所有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理论,对于人的心理动机,对于群体心理学,对于现代生活的规则等都有了解,那么,这对实现更理智地使用现在由我们所支配的那些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是大有帮助的。
第三,现代的专家教育显然接受了报酬递减律(diminishing returns)(即资本和劳动力等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单位生产的增加量不随资本和劳动力增加,反而递减)的观点,使专业化教育的增长并不能使科学技术相应增长。很显然,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不动脑子地按指定的程序办事的新的“专家”群,而是能够进行跨学科研究的现代通才。
4 跨学科研究人才的培养
贝塔朗菲强调,跨学科研究是一个混合而成的领域,它包括从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到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等范围广泛的研究领域。即使是在今天看来普遍被视作是一门独立的专业和学科的遗传学,也是吸收了动物学、植物学、农学、细胞学、生物化学、辐射物理学和一些别的“专业”和“学部”参加的“跨学科的”领域。象信息论、控制论、一般系统论、生物物理学、比较文学这样一些领域,就更非那些只懂得某种单一专业的“专家”所能为之。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生机勃勃,这就迫切需要造就更多的跨学科研究人才。
作为一个在跨学科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长期在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的教授,贝塔朗菲经常思考跨学科教育问题,他认为他所接触到的许多关于跨学科教育的思想是乱七八糟的糊涂思想,其实施计划也显得过分简单化。[1]譬如,无休止地增加一些大学课程,等等。
在贝塔朗菲看来,增加或者并列各种不同方面的课程,既培养不出“教养”,也不能带来“通才”教育。现在学校中的这种专门化情形不能用要求理工科学生选修一些属于人文科学的课程的办法来解决。他甚至举例论证自己的观点,很难想象,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会变得热衷于蚯蚓的解剖,或者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却热衷于英国查理一世时期的长期会议。要想用这种方法来培养通才,那就好象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年)笔下的《匹克威克外传》中所描述的匹克威克俱乐部中那些可敬的会员们所用的方法,他们为了写一篇关于中国形而上学的深奥的学术论文而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去查找“中国”和“形而上学”这两个条目。
贝塔朗菲认为,现代科学发展的明显特征之一,是过去互相孤立的科学的各个领域之间越来越走向有限制的融合。正象需要有关本专业的事实、理论和技术等各种知识一样,学生们也需要有多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知识,而究竟这在什么程度上是必要的和可行的,这既取决于该专业,又取决于学生的职业目标。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在某些纲领性的宣言中,往往被歪曲了。
实际上,每一个人能够而且必须寄予热望的唯一的东西,就是经过选择的有限的知识,即从科学知识的各个门类中挑选出来的实用知识及对原则的理解。这不论是对跨学科的和包含一门以上的传统专业的专家来说,还是对强调整体性原则的通才来说,都是适用的。在教学、研究和实际应用中,针对一定目标所能做出的最恰当的选择,乃是科学进取精神的指路格言,跨学科研究人员的知识并不象集邮者收集邮票那样越多越好,而是重在对知识作有效的选择,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在动态中不断趋于合理,相对于所研究的课题,最起码应该是够用的。
基于对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趋势的认识和对跨学科研究特点的具体分析,贝塔朗菲提出了实施跨学科研究人才培养的具体建议。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建议是相当实际的,因为它们不是为未来设计雄伟计划,而是每天能实现的,且又不要求增加教育、设备、经费,或在原有的学部之上再增设新的研究机构或类似的承诺。具体说,贝塔朗菲的跨学科人才培养计划是按照如下的思路构想的。
第一,为所有大学的学生设置适应性课程。贝塔朗菲认为,今天的学生可能成为未来智力上的领袖,他们除了需要专业训练以外,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还迫切需要一般的“适应性”。培养这种适应性绝不能用把某些自然科学课程插入人文科学课程之中或者相反的办法,而是在不牺牲“深度”的前提下,通过仔细选择课题来实现的。因此,适应性课程应该含有“最好的课程”的意思。
第二,把几个专业合而为一的课程。考虑到各专业之间的日益增加的相互作用,并且为了把已经变得过分纷杂的课程之间经常发生的重复减少到最低程度,对于这种综合性的一体化课程予以考虑。譬如,在某些医学院中,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或者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心理学,可以作为一门合而为一的课程来讲授。在贝塔朗菲看来,这样做的效果是将会有一幅活的有机体的更有生气、更加新鲜的图景出现在我们面前。
第三,通向文学博士、理学博士或哲学博士学位的跨学科教育计划。在贝塔朗菲看来,什么是跨学科的计划与什么是专门的学部,二者之间的差别是不固定的。对于那些在大学尚未取得作为一个系的地位的领域,显然需要特别的关注,这往往是科学版图上被人忽视的无人区。例如,细胞化学和组织化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力学、理论生物学、生物学的历史与哲学、一般行为科学和一般系统论,等等,就属于这样的领域。
第四,旨在培养科学通才的多学科的研讨班。首先,这种研讨班是为特别有才华而又具有满腔热情的学生开设的;其次,这种研讨班不能按指令行事而必须根据有关的学科和教授们的共同兴趣有机地成长。最后,必须及早地注意到跨学部的哲学博士教育计划将会提高大学的声誉,当然,也能提高每一篇按所确定的那个方向完成的哲学博土论文的水平和声誉。
贝塔朗菲关于跨学科研究人才培养的思想与其关于通才教育的思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由于本文的侧重点是探讨贝塔朗菲的跨学科思想,有关贝塔朗菲的通才教育思想,笔者另有专文作系统研究,[11]这里就不赘述了。
收稿日期:2001-1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