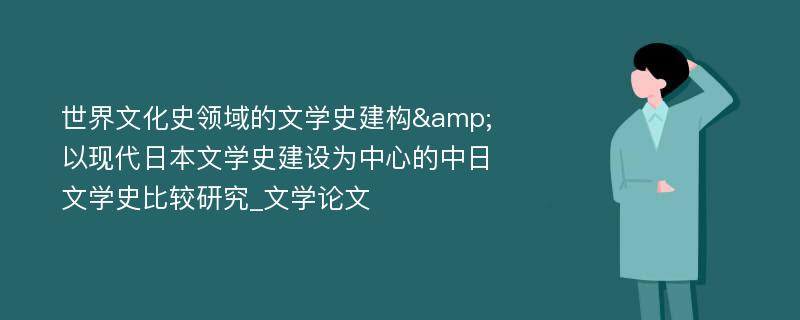
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史建构——以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建构为中心兼中日文学史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日本论文,近代论文,中日论文,世界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10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5-0005-10
中日两国文学史是在欧美列强伴随军事行动觊觎东方,实施殖民化,两国学者在面临危机的境遇中应变的产物。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对西方的强势话语,通过建构自己的“文学史”,显示本民族文化、文学在世界的价值与地位,力图以此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重塑国家形象,是当时中日学者的共同思考,文学史著即是这一思考的成果之一。同时,它首次显示了中日文化在世界文化场域中(至少纳入了欧美诸国)寻找“他者”形象,发现“自我”,激活自身传统的追求。但是,作为悖论的另一面,中日文化同时也把自己的文学(包括批评话语)纳入到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体系(这当然是个渐进并始终充满矛盾的过程)。于是,围绕文学史的不断思考、重写,中日两国的文学、文化既各自与西方文化形成繁复的动态,同时中日两国的文学、文化交往也纳入了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互动网络之中。
论述近代日本文学史的产生不能不追溯近代日本文学研究方法确立的过程。在这方面“从芳贺矢一博士的日本文献学出发是至今也无疑义的。”[1] 留学德国的芳贺矢一(1867—1927)认为文献学是“通过文献,并以此为根据,了解日本的真相的学问”(《日本文献学》),即文献学以探明日本的国民性为主要任务。接着在佐佐木信纲和池田龟鉴的进一步推动下,这一研究更明确地成为“必以探讨民族固有的精神生活为首任”的学问,而且“在这一意味上,文献学研究、国文学的历史研究、文学批评研究都是密切相关的。”[1] (P51)并认为国学具有与西洋文献学相等的地位。
从“日本文献学”出发,对传统的国学重新整理而确立新的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意图便产生了,这是明显地受近代以来“世界史”观念的影响,在“国民国家”观念下,寻找“他者”后的一种“发现”。在这里,有必要回顾西方的“文学史”的产生。
文学史著作首先作为西方文化的结晶出现于19世纪,一般以丹纳的《英国文学史》(1864)等为代表,它是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物。正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共同体”,抛弃这一说法可能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它反映了文化(包括语言文学)在塑造国家形象中的独特作用。对于与文学史密切相关的文学历史主义,美国学者Lee Patterson指出:“要增强在阐释中的可信性必然促使利用历史文脉的愿望,19世纪的文学历史主义认为文化的各个部分,都受贯穿于文化整体的价值观的支配,这是当然的思考。为此,对于时代精神(Zeit geist),即掌握特定时代文化行为的价值,必须予以探究。这一历史主义同时通过确定的历史的文脉,进行同质化,成为完璧式的建构。在把过去同质化的倾向里,爱国的民族主义和过去在文化统合的名义下使其反抗声音沉默的意志使之强化。历史学,特别是在德国是适应国家统一的趋势而得以发展就绝不是偶然的了。”[2] 日本近代文学史的先驱者芳贺矢一首先着眼于德国的历史主义,日本明治时代无论在文化、文学还是政治、法律诸方面对德国情有独钟就非常好理解了。
对于文学史的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解还不应忽视法国在19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以朗松为代表,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的索尔蓬法“乃是与美学相对的历史的方法。是通过文献学的运用,实证的文学研究。”[3] 包括法国“比较文学”的产生,都是“比较先进的法兰西民族文化试图向欧洲乃至世界说明自己优越的产物。”[4] 文学史写作实乃是塑造民族精神的行动,激发爱国激情、唤起民族主义的重要举措。为此,朗松说:“我们不仅是在为真理和人类而工作,我们也在为祖国而工作。”[5]
日本最早出现“日本文学史”的时间恰恰是日本民族主义上升之际。明治2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始于条约修改①,它由反对明治政府对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称西方列强的追随姿态而开始(参见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民族主义的高涨”一节)。联系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在近代东西文化互动的轨迹。
我们从日本最早出现的《日本文学史》中可以得到相同的印象。在这本《日本文学史》的“绪言”中写道:“著者二人在大学就读时,常常共同翻阅西洋文学书籍,对其编纂方法之妙由衷赞叹,其中有文学史著作,对其文学发达详加介绍,对此研究的路数之完备深感惊喜。”由于在世界文化场域中形成了“他者”,反观自己,则产生了本国文学的自觉。“我国亦有不劣于他们的文学书,也应产生不逊于他们的文学史之感慨,勃然而生。”[6] 明治23年成为日本近代文学史发轫年绝非偶然。正如日本著名文学史家久松潜一所说:“在明治时代国文学的复兴是由于植根于文学的自觉和日本的自觉起了巨大的作用力。文学的自觉从明治18—19年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清晰可见;日本的自觉则有明治21年《日本人》杂志问世,日本学的名称亦出现,进而有国史的编纂于明治21年开始。这就使国文学上产生了国文学史……到了23年,对醉心于西欧开始反省,日本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结为一体……‘教育敕语’发挥了真正的威力,在这一年随着上田万年国文学(卷一)的发表,芳贺矢一、立花铣三的国文学读本问世,接着出现了作为近代日本文学史嚆矢的三上参次与高津锹三郎的《日本文学史》,可以看出这一潮流的动向。”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寻找“他者”的同时就是“自我”的产生。日本明治年代以后,新名词从域外纷至沓来,所谓近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术语体系逐渐确立。文学批评术语的实质性转型也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它来源于西方,但进入日本学术话语网络,又必然经过翻译(哪怕是音译)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术语”就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小场域,它既使自身纳入西方文化话语之中,又通过复杂的张力,不同程度地保存、改造自身原有的话语。顺便提及,中国近代文学术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日本也始于此时,因有另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首先对于“文学史”这一概念,日本最早的“文学史”开创者们认为“正如历史可分为世界史与各国史一样,文学史亦可分为世界文学史和各国文学史两种。前者是综合各国人智的发达、进步,从文学上予以观察;后者乃是对一国内之文学现象进行历史的叙述。”[6] (P1)在《日本文学史》第二章则名为“给文学下定义之困难——文学定义”两位作者首先指出明治维新之后,出现对“文学”了解的广泛性,但对于到底什么是“文学”则难以表述,同时援引“古今东西”之定义回溯对“文学”的认识。已经表达出了“文学”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认识。撰写者指出:“叙述人的生活、禀性和与之相关之事者称之为文学。”[6] (P13)之后,又指出:“所谓文学乃是某种文体,巧妙地表现人的生活、思想感情,想像兼有实用、娱乐之目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又能传布大体的智识。”[6] (P13)我们知道,在西方“文学”从泛指一切文本到确定为指那些具有审美象征性的特殊文本,是在20世纪起始阶段。在这里本书撰写者显然已经进入西方话语体系来表述“文学”概念。
纵观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学史著,都是发展变化的,随时代变化而不断重构。
“文学史”的不同建构往往围绕文学史与历史、文学与相关学科的不同视点,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范式。
文学史的本质涵义应提升为对“文学性”的把握,也是对人的存在本身的深入理解的过程。中日两国文学史的书写,显示出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结构。正如日本学者森修所说:“论及新的文学史立场……与其说是方法论,莫如说是其对于研究对象文学自身的追问。”[1] (P148)。
近代以来,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对于“文学”人们从不同理解中不断寻求对话。这对话也生动地体现在文学史著里。这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没有一个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只有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文学性。”[7] 接受西方话语,给“文学”以新的界定,并将本国文化产品经典化,使它走向神圣的殿堂,特别是“小说地位”的颠倒,是近代文学史上的突出事件。以西方新概念为标准,与西方文学比肩,产生了小说地位在东方日本发生逆转式的提高。把" novel" 置换为“小说”,并认定它是最先进的文学体裁,再以这一概念指向广泛的日本古典作品,再由文学史家使之经典化。于是,910年问世的《竹取物语》在1905年的藤冈作太郎的《国文学全史·平安朝篇》中被赋予最崇高的地位。这是日本文学史在发轫期的走向,它也直接影响了我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史。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是不会满足于把文学作为历史文献来考察的。对于芳贺矢一文献学的质疑就产生了从主体人的立场出发的文学史(风卷景次郎为代表)、从文艺学(样式、形式)出发的文艺学史观(冈崎义惠为代表)和历史社会学文学史观的文学史。成为20世纪初至60年代最主要的几种文学史流派。首先风卷景次郎质疑了文献学的文学史观,他认为我们审视文学史作品时,我们感受到的作品和没有感受的作品间已经产生了区别。“这样捕捉到的作品系列,就不能仅以文献对待了,是作为文学自身的东西被感受到了。”[1] (P107-108)正如森修所说:“这是主体立场”观点。
日本近代文学文学史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变貌,从探讨文艺本质入手,产生了冈崎义惠(1892—1982)的《日本文艺学》(1935)。冈崎义惠作为美学家大塜保治(1868—1931)的弟子,亲炙大塜所讲授的康德、黑格尔美学,对狄尔泰的阐释学也有深入研究,这对他形成新的文学史观具有重大影响。在昭和10年(1935年)10月出版的《日本文艺学》把文学史置于文艺学的附属地位。他认为“‘日本文艺学’的终极目的不是对历史事实的追查,而是对于文学本质的探讨”这种内部研究的趋向,必然要超越文艺史而进入对文学本质(即文学性)的探究。接着他在《日本文艺的样式》中作了如下表述:“文艺学即使以文艺理论为对象,亦涉及文艺的历史,但均不是为了理论和历史,乃是为了弄清文艺的本质……为此,在文艺学中即使涉及历史现象,也是很有限度的。”[1] (P115)正如森修指出的:冈崎的文艺学“结果必然是取否定文艺史的立场”[1] (P116)
冈崎义惠专注于日本文艺样式论研究,实际是从形式主义(内面)出发对文学性的叩问。对于冈崎的论述,他的后继者北住敏夫提出了质疑,他指出了冈崎论述中的悖论、矛盾性,他认为“对文艺的传统、变换视点作为体系来把握,将之归为静止的类型状态时,这恐怕就是样式吧。但是,必须对于文艺的动态的个性作直接把握的历史的传统观点,又是具有自体独立意义的东西。”[1] (P122)北住敏夫抓住了这一矛盾,但他也未能提出解决的方策。他说:“大概精神科学的对象,即使置于历史研究,也必然给予我们内在的个性意味。对这一意味是由我们来理解的。为此,认识文艺就必须依靠文艺理论,因它是建立在理论与历史相互关系之上的,将文艺现象按时间顺序,根据相互关系来捕捉文学意味亦无妨。历史的观点、理论的观点,未必非得整合在一起,作两立之物考虑也可以吧。”[1] (P122-123)
显然冈崎为了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已经否定了它与有关领域的内在联系,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言“(冈崎)氏所设想的方法明显与历史方法相对立,两者之间没有一点妥协、折中的余地。”[1] (P118)今天看来这种文学史观的片面性是不容否认的。
在不同特点的日本文学史中,称作“历史社会学派”的文学史写作是其重要一翼。日本文学史家认为,这一派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三十年代),作为它的前奏,实际已从“日本文献学”吸收了这一方法的“探索国民思想、精神”的内核,从文学作品研究日本人的恋爱观、自然观、政治、道德、宗教、思想、人生观诸层面。正如作为历史社会学派文学史萌芽的藤冈作太郎的《国文学全史·平安朝篇》(明治38年)中所说:“探求国民思想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为其宗旨,已显示了这一文学史识的初衷。除了文学的自觉、日本的自觉与来自西方的影响密不可分,据调查藤冈写作文学史著时深受丹纳、勃兰兑斯和其他欧洲文学史著影响[1] (P82)
作为日本文学史的历史社会学派的确立既有流行的欧美文学史论的影响,同时应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巨大影响力。在大正十年(1921年)二月《播种人》创刊,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兴起,受前苏联文学理论影响(普列汉诺夫等)在昭和初年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论达到高潮。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篠田太郎的《国文学概论》(1931)、《从历史唯物论看近代日本文学史》(1932)、山元都星的《日本文学史——从社会学角度看》(五卷1939-1941)等。这些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产物。在昭和6—8年(1931—1933)年《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20卷)出版,在这当中津田左右吉的《当代文学的社会性》、三木清的《现代阶级斗争的文学》、土居光知的《文学论》、阿部次郎的《比较文学》均属于这一系列。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历史社会学派对立足于德国文献学立场的冈崎义惠的著作《国文学概论》进行了批评。在昭和10年至11年间,逐渐以近藤忠义《日本文学原论》(昭和12年成书),永积安明的《古典文学的传统》为代表而形成了历史社会学派。应该说对文献学派局限的批评促使了历史社会学派的壮大。在昭和12年(1937年)近藤忠义出版的《日本文学原论》中对这一派作了如此界定:这一方法:“乃是对作品及作家活动的确认,历史意义的确认,但绝不是年代的定位和当时世态的理解,只能是在文学艺术范畴里作家活动、作品全部存在置于历史、社会观点下给予把握。”[1] (P85)正如日本文学史家所说,当时虽然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在1934年被强行解散,在它三年之后出版的此书所采取的“现实主义立场”不能不说继续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学理论。
历史社会学派得以进一步发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昭和20年,随着败战,民主主义高唱的自由时代来临了”[1] (P88)。在世界上“介于世界两阵营的日本,产生了日本民族自觉的高涨,国民文学的讨论更加热烈。”“这一时期成为历史社会学派最活跃时期。”[1] (P90)许多成果体现在对日本古典文学研究中。概言之,是把文学研究与文献学、民俗学、神话学结合起来,突出了注重文学的历史性的同时,加强对其文学性的探讨。日本文学史家西乡信纲无论在他撰写的《日本古代文学史·修订版》还是和永积安明、广末保合著的《日本文学的古典》(第二版,1966)中都体现了历史社会学派的新发展。特别是围绕“古典”的辩证的文学史观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古典既是过去的同时也是现代的,为此它总是新的,不可避免地被世代重新阅读的命运。”在由西乡撰写的收入本书的《如何阅读古典》一节中说:“古典尽管是过去所创作的作品,但是能越过若干世纪的时间,不断地为新时代所阅读。把这一现象称为永远性应该不会有异义。但是,在这里容易被遗漏的视点是这一永远性是以历史作媒介的。古典,首先是为当时而作,对同时代产生作用力,也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具有跨越若干世代的力量……优秀的古典被世代反复阅读,在于它表现人的本性(重点原有)并非是将其归拢在一起,而是组织起不同种类、层面的经验、蕴藏了多元的音阶的看法是正确的。”[8]
在这里我们已感受到了与后来的新历史主义史观相通的东西。这就再一次说明文学史的撰写是与时俱进的,随着对“文学”本身的深入探究,任何一种史识都将变貌、发展,绝不是一旦出现就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理论日盛,并广泛地影响了日本。在日本文学史界出现了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并推出了一批新的文学史著。新一轮的重写文学史有许多复杂因素,究其实质,主要症结还是在东西文化场域中,对日本文学(文化)走向的再思考。一些文学史家旨在对明治维新以来“自明”成见的反思,特别集中在对“现代性”的再认识成为建构新的文学史的焦点。
在众多的新论中,柄谷行人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具有代表性。这本著作的一些篇章初见于20世纪70年代末,成书于1980年(讲谈社出版)。在该书“后记”中柄谷强调必须把“日本”“近代”“文学”“起源”加上括号,以示对这些概念内涵的重新思考。他从“起源”切入,对“日本近代文学”不证自明提出质疑,从被颠倒的事物现象中观察深深隐藏起来的“起源”。在本书第1章《风景的发现》里写道:“‘普适的东西’在19世纪西欧确立的同时,它自身的历史性就被遮蔽了。‘历史主义’和‘文学’同样是在19世纪确立起来的支配概念,历史主义地看待过去,是以‘普适的东西’作为自明的前提的。”[9] 他长篇援引了明治文坛巨子夏目漱石的《创作家的态度》,重新评价了漱石当时对西欧中心主义的拒绝和质疑。柄谷认为漱石揭示了“历史主义里潜藏着西欧中心主义,或者说对把历史看作是连续的、必然的观念提出异议。他(指漱石——引者)还拒绝通过作品向‘时代精神’、作者所谓Whole(全体)的还原。而是朝向‘仅就作品所显示的特性’的探讨。这一想法有些形式主义的味道,但是比它走在前面。”[9] (P15)
8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历史观、文学史观也反映在其他一些日本文学理论家的著作里。小森阳一指出:“在新闻界概念随意流行的背景下,称作‘近代’的概念就会有了极为流通的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里,‘近代’这一概念是一种花言巧语,是起着给某作品、某作家以特别好的权威标签的机能,即是所谓‘近代’”。[10] 很显然,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对“现代性”反思的产物。鲍曼说:“后现代主义话语,涉及作为西方文明自我命名之‘现代性’本身的可靠性,……它意味着蕴含于现代性思想中的那些自我论断的特征,现在已不复存在,或许过去也不曾存在过。后现代主义讨论涉及西方社会的自我意识。涉及这种意识的根基(或根基的缺失)。”[11] 在这里鲍曼揭示了西方面对自身文化危机的反省,即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由于经济、军事的强势,同时建立了强势话语,而一直自言自语,缺乏“他者”的话语必然走向反面,寻找“他者”才能发现“自我”,东方曾经通过西方的“他者”发现了“自我”,同样,西方也要从东方的“他者”对“自我”再发现。中国俗语中有“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缺乏他者参照的文化是缺乏生命力的。正是基于此,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重复反思“历史”。日本学者指出:“‘历史’这一概念本身,作为在各色人物和社会集团的力的关系中被构成的话语加以把握,围绕‘历史’的韬略布置亦是围绕近代的权力关系的争斗场。另外,‘文化’这一概念,也作为每个当事者分别被置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脉中被不断塑造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争斗的场来被重新把握。它并不具备实际的价值,而是作为不断提出新的问题的场被发现。正因为如此,在‘历史’和‘文化’之中,我们作为怎样的主体被建构的?对此必须使之问题化。”[12] 包括柄谷行人在内的日本文学史家这种力图克服把“历史”“文化”看作一成不变的客体的二元论,将“每个人”都置于历史、社会的网络之中动态地把握,成为他们建构、书写新的文学史的新思路。
在这里已显示出“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传统的历史观试图建立一个线性发展的谱系,“在这样的历史观中,历史事件有其成因,历史演进有其发展趋势,通过研究历史,人们可以把握历史的总体脉络,预测历史前进的方向。”[7] (P671)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对此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同时期存在着以不同原则对知识进行分类的知识型。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离不开他们身处时代的知识编码。”[7] (P672)他进一步得出“不断进步的历史是一种话语表述。”[7] (P672)新历史主义对文学史的撰写给予了很大影响,一些文学史家引入了新历史主义的“文本的历史性”(historicie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euality of history)的双向关注,这也就必然将文学置于更宽广的文化网络之中,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界限模糊起来。这也是我们所看到的日本新近文学史新貌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这里我们毋须对《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作详细的介绍与复述。我们仅从这部史著中的“发现”这一关键词来窥伺一、二。在整部著作的六部分中,有三部分出现“发现”这一关键词,至于在行文中所见更是频频。他结合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和《忘不了的人们》(明治31年)阐释了如下观点:“从《忘不了的人们》这一作品所感受的,不但是风景,而且有某种根本倒错的的存在。进而言之,即‘风景’是在这一倒错中被看出的。如前所述,风景不单是在外的东西。为了风景的出现,就非变化知觉的样态不可,为此就需要这种逆转。”[9] (P27-28)
《风景的发现》这一章读起来比较艰涩,但是,结合全书的文脉还是可以把握柄谷所要谈的内容。他曾在本文先说了一句:“我想说‘国文学史’实乃也是在‘风景的发现’中形成的吧。”[9] (P24)接着说“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的装置,一旦完成,它的起源就会遮蔽起来。在明治20年代的‘写生主义’里虽已有风景的萌芽,但还没有决定性的颠倒。它基本还是以江户文学延长线的文体写出的。在这之后,作为与之断绝的是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和《难忘的人们》(明治31年——1899年)。特别是《难忘的人们》如实地反映了风景在成为写生之前的价值颠倒。”[9] (P24-25)在此我们不能长篇引用国木田的本文,为了说明柄谷的观点,有必要作如下介绍。《难忘的人们》写的是一名叫大津的文人在多摩川客店偶遇名叫秋山的旅伴,向他介绍自己写的《难忘的人们》手稿。所谓“难忘的人们”不是指“朋友知己和对自己有恩惠的师长、同学”,而是指“忘了也没关系,但又难以忘却的人”。《难忘的人们》中大津在轮船甲板上偶见附近孤岛上一个赶潮的男人,看到他朦胧的人影,却在10年间一直难以忘怀。
为了明确柄谷的论述,《难忘的人们》的这一段应该译介:
“今夜我独自一人再次面对孤灯,催发的生的孤独让人难以承受,哀情阵阵袭来。这时,我的自我似乎戛然折断,莫名地涌出对人怀念之情,各种往事和友人浮现脑际。这时油然浮在心头的正是那些难以忘却的人。不,可以说是我看到的是站在他们周围光景里的那些人。我与他们有何不同?此生不都是身处天涯之一隅,匆匆行路,携手共归无穷天国的旅人吗?当这样的思绪从心底泛起,我不知不觉泪流双颊。这时已处于无我无他之境,无论对谁都难以忘怀了。”[9] (P28)
对此,柄谷紧接着对“风景”的“发现”作了阐释。他说:
“在这里,‘风景’是与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津对无从说好的人感到‘无我无他’的一体感,但反过来说却是对眼前的他者表示出冷淡。换言之,只有对周围外部不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man)那里,风景才被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9] (P29)
柄谷行人在后面反复谈论明治20年“现代的制度已经确立起来,而‘风景’不单是作为反制度的东西,相反其本身正是作为制度而出现的。”[9] (P48)尽管柄谷的论述仍然费解,但是,如果联系国木田独步整个创作历程和其他文学史家对他的评论,还是可以理出端绪。
1961年出版的由柳田泉、胜本清一、猪野谦二等人以对谈方式写出的《明治文学史》中,在论及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时,他们有如下对话:
平野(谦):再说哀感吧,看来是“物哀”吧,恐怕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常感的奇特感情难以表述的很好表现吧?作为思想也许是幼稚的,但是作为文学的结晶,它的结晶度是相当高的,我感到所执著的东西始终与此相关。
猪野:我感到这是作为文学的无可替代的发现。
柳田:在当时如此写作不是新的文学吗?为些现在的文学史上未给予的革新的位置,再给予独步文学不好吗?[13]
可以说柳田泉等人已发现了独步散文之新,它的新恐怕既与“物哀”仍有血缘联系,但已表现为吸收了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精神(虽然柄谷不想把这一点引入)的话语已成为“先文本”——一种装置存于他的头脑里,为此“风景”才被发现出来。包括国木田独步受二叶亭四迷翻译屠格涅夫作品的影响均不可低估。小森阳一指出:“正如独步自己所明确告白的那样,他是在读了二叶亭四迷的《幽会》之后才发现武藏野橡树林之‘美’的。并不是通过观赏事实上的自然风景而感受到‘美’,而是通过翻译文体的框架,凭借新的语言风格找到了‘美’。”[14] (P184)这恰恰说明,在八十年代以来重写日本文学史当中,一些学者所探讨的就是西方话语如何作为一种“装置”进入日本文学,改变了日本文学的面貌。这是柄谷在《起源》中聚焦的核心问题。在《内面的发现》中对“文言一致”的重新审视,对“儿童”的发现的梳理,都是循这一思路的思考。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但是反拨者所围绕的问题意识仍然没离开这一框架。
龟井秀雄的《明治文学史》可以作为另一个个案分析。本书虽有侧重从文体形成的角度重构明治文学的倾向,但它的根本出发点在于突破过去那种套用西方模式,按时间顺序对文学进行“史”的界定的老框框。龟井认为:“阅读行为的根源在于同未知的东西的碰撞,为了对它的理解而动员‘知’的活力,通过经验而感觉到文本的历史性、唤起自身反思的历史性等。”这一见解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是相通的,也显然受了克里斯蒂娃等“文本间性”理论的启发。为此龟井认为,借助于按物理时间顺序整理的年表,由于要使年表的知识优先,这种含有历史感觉的距离感,即文本与自己存在的历史差异感可能会消失,这对文学鉴赏有负面效应。为此他从文本是多层的系谱的交结点的思考出发,指出“一个文本乃是先前的几个文本的再构建的产物。换言之,每个文本自身,都在叙说与先行文本的关系,使自身历史化。”[15]
再看他对岛崎藤村的《春》的新的自身历史化的阐述。藤村的《春》在发表之前在报纸的文艺栏中已出现了“现在藤村正以‘文学界’同仁为模特儿构思作品”的文字。事前就确定了阅读方向。在这篇小说里,藤村作为岸本(主人公之一),而北村透谷与青木作了置换。“所引用的青木的文章均为北村透谷的随笔。”[15] (P231)如透谷的《厌世诗人与女性》(明治25、26《女学杂志》)的文字成为《春》中青木的文章,如“恋爱是使刚愎的青木哭泣的微妙的音乐。”而透谷在上文中有“恋爱超越了使刚愎的拜伦哭泣的微妙的音乐。”[15] (P232)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多引,在本书中龟井把“文学史”作为生产的文本来看待,注视过去被忽视的媒体与物语之关系、读者的生产性等等。
这种新变化在这本文学史著作中得以开拓,亦在别的文学史著中体现。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小森阳一等主编的《岩波讲座·文学》丛书,在这方面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在第一卷“文本论”里,多位专家梳理了东西文本的产生、发展的历史。从口承文学到今日的电子文本,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文本世界,不与时俱进地追踪时代脚步,无从认识文本的实质,也不可能深入理解“文学”的实质,即使在今日,对文学实质的认识仍在继续,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恐怕这是东西文化交融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发之一。
当今被称作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全球化与地域化同时呈现出鲜明的特征,特别在文化上,各国文化并未因全球化而趋衰落,在某种意义上,各有特色的差别倒是互补的前提。重视地域文化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可以说,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中日文化文学交流,互为借鉴,在东西文化融合中将发挥新的巨大作用。
对两国构建近代以来文学史历程的回顾,反思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规律性问题已成为中日两国学者的共识。对此,一位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学者说:“我想,今天我们回顾早期文学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还是在于借此机会反思近百年来文学史著述所经历的过程,从中了解我们今天有关文学史的观念、概念、语言,并不是在一旦接触了西方文学史的条件下,就立刻简单生成了的,而是经过了与传统的长期磨合,经过了对传统的改造与吸收,经过了对文学史在西方所具有的内涵与形式的误解与歪曲,然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16]
中日两国在一百多年来走过了各自不同的历程,这也反映在文化、文学诸方面。在当今都面临在世界文化场域中如何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的问题。笔者曾在多篇文章里论述日本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独特的参照系作用,这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同样,因为中日在历史上文化交流的渊源之深,中国也是日本文化发展的独特参照系。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互动性将更为突出。
毋庸讳言,由于中、日两国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意识形态上亦有很大不同。近代以来,反映在文化上的差异值得中日两国学者认真研究。我们不妨再从文学史谈起。
前面说过,对近代以来出现的文学史著作的再版,重写文学史的论争,我国稍晚于日本出现(我国是在1985年左右)。近年我国重新刊印了近代最早的几种文学史著[17],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绵延不断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都与日本的重写文学史成为前后。在阅读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著时,必然浮现那段国耻难忘的近代岁月,一些先觉者出于爱国之心想重塑中国文化形象,重振国民精神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林纾是中国近代译界第一人,他以翻译近200部左右西方文学著作的实践而体会良深。在翻译狄更斯作品后,他对狄氏能以深入揭露时弊而赞叹不已,称之为“无一不足为环球法,……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同时抱憾“所恨无迭更司其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他寄希望于李伯元之后来者“惟孟朴及老残二君,能出其绪余”,要拭目俟之,稽首祝之。[18] 他还将我国古代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悉与狄更斯作品比较,他在盛叹《红楼梦》为“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之后,对比狄氏作品,指出不足在于“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而狄更斯“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18] 虽有简单比附之嫌,透漏出的发挥文学的特殊功用之心是明显的。
由于日本率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又发展成军国主义国家,反映在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观中的意识形态性必然产生与中国文学史观迥异的因素。当然,这里绝非说日本近代文学史都有这样的政治色彩,但至少在相当多的作品和文学史观里已有突出的体现。和三上、高津的“日本文学史”产生同年(明治23年)的矢野龙溪的《浮城物语》(载邮便报知新闻)就宣扬了明治政府的“南进”思想。作品的主人公作良义文、立花胜武(隐喻为文武结合)指挥一群“志士”乘海号王,直捣印度尼西亚,每到一处则大发:“此地于我得保护之,且为我版图之一附庸。”[19] 殖民主义面孔昭然。它的根源不能不追溯到福泽谕吉(1835—1901)的“脱亚入欧论”。这种理论虽然不能说它导引日本近代以来各个领域的全部,但是对于包括文化、文学在内的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是确实的。
竹内好在论述日本文化时曾说过近代日本文化中有着一种“优等生情结”,即“我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接受了欧洲文化,因此落后的人民当然会接受我们的文化施舍,也必须接受。[20] 这种情结实际上已成为日本式的“东方主义”,即虽然日本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历史渊源上属于东亚,属于汉文字圈,从思维上迥异于西方文化。但是,以西方为标准的“优等生”情结,转而蔑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这在明治时代一些人的头脑里已非常突出。
近年,一批有识的日本学者从文化中最核心的问题“语言”入手,批判潜隐其中的“日语民族主义”。其中小森阳一的著作《日本近代国语批判》极具启发性。他在《作者后记》中说:这不只是“在‘语言学’、‘国语学’、‘日本语学’方面起到了推陈出新的作用,而且还对‘历史学’、‘思想史’等学界的理论预设予以决定性的转换处理。”[14] (P310)小森指出写作此书是要“澄清近代日语与日本近代文学之关联。”[14] (P311)语言问题对近代中、日两国来说是文化中最深层次的问题,也是文学史撰写中的核心问题。现在日本许多学者的视点已关注于此,这是非常值得瞩目的。在《近代日本的批评》一书中,野口武彦亦说过:“明治时代的日本所直面的与其说是思想,莫如说是语言问题。”[21]
小森阳一等学者论述了从明治时代之前,日本就出现了的对“汉字”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日本称作日清战争)后,力图消去“汉字”这一“他者”以高扬日本民族主义乃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还有谷崎润一郎(1886—1965)这样的作家还珍爱汉字。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小森阳一重新认识日本近代以来日本的国语教育问题,尖锐地指出了它在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当中的重要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朝鲜,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时,当时任台北帝国大学教授的安藤正次在1940年的《台湾的国语教育》中这样表述:
“在台湾推行的国语教育之所以能够看到今天这样的成果,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实行了通过国语教育逐渐使外民族皇民化的政策,同时又不强行要求国语。”
对此小森指出:“所谓‘皇民化’,不是通过‘强行要求’或‘镇压’来达到的,而是自发地学习‘国语’,学成者将在‘皇民’这一平等性中得到承认。”[15] (P254)语言问题的实质不是昭然若揭吗?在那场侵略战争前夕,作为舆论之一的“所谓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里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日本要作亚洲的执牛耳者,包括在文化上,亦是“魁首”。
在21世纪的今天,中日两国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这当中,文化建设是重要的一环。中国政府多次表明自己不管任何时候决不谋求霸权,在文化上亦是如此。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自有其历史存在。中国文化在发展历程中亦在朝鲜半岛、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其实这同时也是共建。面对新一轮的东西文化交融,我们有理由共同努力,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共同发展。同属东亚汉文字圈国度的中日两国应当为这一伟业共同作出贡献。研究文学史重构的根本目的即在于此。
注释:
①指1858年(安政五年)德川幕府与美国之间签订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后,明治政府面临修改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课题。
标签:文学论文; 日本文学史论文; 风景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明治时代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世界文化论文; 武藏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