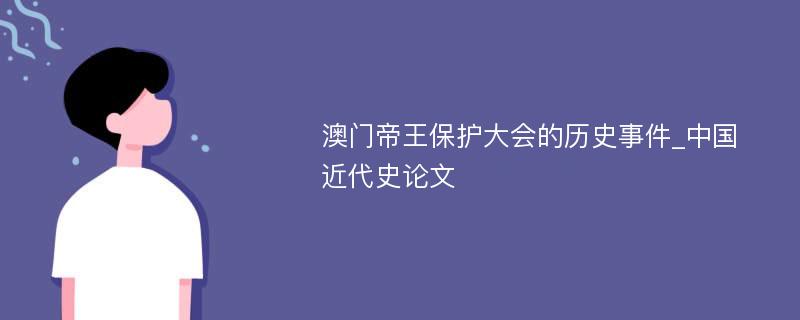
澳门保皇总会史事钩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钩沉论文,澳门论文,总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1/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4)02-0001-07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会,与后党势力所控制的清廷展开斗争,力图推倒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实现光绪复政,以重振维新大业。保皇会最盛时在海外200多处建有组织,并曾在澳门设立总会(或称总局、总部),以主持全局性会务。关于澳门保皇总会的情况,由于史料缺乏,以往人们知之甚少,近年来始有一些学者在论述澳门历史以及保皇会庚子勤王活动时,对其有所涉及和揭示。但是有关澳门保皇总会史事的一些基本情况,迄今仍有不少模糊不清之处,需要作专门性的钩沉与考证,方能窥其真相。本文就此试作一些探讨。
一、关于澳门保皇总会设立的时间
保皇会于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与当地侨商李福基等人集议创立,这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关于澳门保皇总会设立的时间,迄今却未见有明确的记载。考保皇会创立之初所制订的该会章程,即《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中,有设立“总公司所”的条文:
一、立总公司所,择近内地通海外者为之。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皆港澳、日本忠义殷商合股所办,主持正论,激昂忠爱,薄海共信,今公推为总公司所。两报即为本公司之报,凡同志皆阅此二报。各埠捐款皆匯汇《知新报》、《清议报》妥收,有报馆印章及总公司所印章、总理印章之收单为据。而《知新报》与香港接近,皆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港澳皆公举忠义殷实巨商为大总理,总管收支各款及公司中各事。更立协理、干事、书记数人,皆公选通才志士任之,以通各埠,任各事。两报地名,今将西字附印。(注:光绪二十五年已亥冬印本,收录于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44~263页。又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版的上海《亚东时报》第二十一册刊有《保救大清皇帝会例》,其文字与《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有关部分基本相同,康有为在1899年10月2日写给谭朝栋、黄仕初等人的信里也都提到有《保皇会序例》,可知该章程后又改作《保救大清皇帝会序例》。)
然而这个条文,与《序例》中其他不少条文一样,都还只是一个规划,还没有能够加以实施,因此在保皇会成立后的数月中,无论是在横滨,还是在澳门,都未见有保皇“总公司所”或者“总会”活动的记载,实际上保皇总会机关并未正式成立。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澳门“总会”、“总局”的活动,是在1900年春季之后方才见诸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会人士的往来函件之中。例如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在致康有为函中,谈到对澳门保皇总会工作情况的不满,说:“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为不足以语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并表示,自己愿归港、澳“握其枢”,以“主持大事”[1](P199~200)。3月28日梁启超致澳门《知新报》同人书中,更直言道:“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无所旁贷。”[1](P207)同日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里也写道:“澳门为通国总会,必当更定一办事条理乃可。”[1](P210)可见澳门保皇总会此时业已存在。另外,上引梁启超的几封书信中,都曾讲到他自己抵檀香山后多次致书澳门总会的情况:“弟子来此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3月13日函),“弟子到檀以来,曾发八信往,至今未得一复字,本会亦未得其一信,而金山本会(按:指旧金山保皇会)来函,言今年未得总会一字,如此成何局面?”(3月28日函)可知澳门保皇总会的设立,当在其到檀香山之前。考梁氏此次抵檀的时间,是在1899年12月31日(已亥十一月二十九日)[1](P188),也就是说,澳门保皇总会的设立,最迟应不晚于这个时间。
还应当注意到的是,在1899年12月31日之前的两个月里,身为保皇会会长的康有为恰巧逗留在香港(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的家属避难至澳门,1899年10月底,康氏为探视母病,从加拿大假道日本回到香港,逗留两个多月时间,于1900年1月27日离港赴新加坡)。应当说,这绝非时间上的巧合,因为保皇总会既然是海外各处保皇会的总部机关和中枢所在,地位重要,其设立不可能没有会长在场,而且以康氏之性格,亦不会将如此重要的人事安排和会务大事假手于他人。所以澳门保皇总会,当是康有为此次在港逗留期间所建,其设立的时间,应是在1899年11~12月间。
二、康有为何以选定澳门为保皇总会驻地
保皇会创立初期所制订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中,原规定将“总公司所”(即总会)设于港澳和横滨两处,并以两处原有之《知新报》和《清议报》作为保皇会的机关报。然而后来的事实却是并未在横滨建立总公司所或总会之类的机构,港澳(具体而言是澳门)成了此一时期保皇会总会的唯一驻地。试观较《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晚数月时间形成的保皇会章程的另一文本——1900年仰光中华日报局所印的《保皇会草略章程》,其中关于总会的地点已不再提及横滨,而是明确规定:“总局设于香港、澳门,以便办事。”[2](P264~265)而保皇会人士在此一时期的相互通信中,更直认澳门为“总局”、“总会”、“总部”所在。此即为明证。
康有为何以选定澳门为保皇总会的驻地,而不选横滨、香港或其他海外地方呢?考其原因,约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地理位置因素。康有为建立保皇总会,首先是为了在国内开展武装勤王活动的需要,因而总会的地理位置要选在既靠近中国内地、又与海外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即所谓“近内地通海外”之处,港澳一带恰好符合这个要求。而以香港与澳门相比较,两者虽然地理位置相近,但康有为认为“港太近城(按:指广东省城广州),且人多口杂,行事易泄”[2](P137),而澳门则相对要偏僻一些,不易引起清廷注意,更适宜于流亡在外的康有为和保皇会的人士在此开展活动。
二是地方政治因素。澳门此时正处于葡萄牙统治之下,清廷既无法对其进行控制,而葡人在当地的管辖又比较松懈,从而为康有为和保皇会人士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
三是澳门维新力量的基础比较雄厚。自甲午战后维新运动兴起,澳门就逐渐成为维新派活动的重镇,戊戌政变之后,国内维新派人士惨遭迫害,维新活动的阵地被摧毁,而澳门的维新力量却未受多少损失,维新报刊《知新报》也继续发行,在海内外的影响甚巨,这就为保皇会的活动和保皇总会的设立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四是由于康有为对横滨方面的失望。保皇会建立之初虽曾计划在横滨与港澳同设总部,《清议报》也同《知新报》一样被赋予机关报的重任,但是因为此时在横滨活动的梁启超等人正同革命派的孙中山商谈两派合作之事,对办保皇会态度消极,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也迟迟不登保皇会文字,引起康有为的极大不满。因而康氏后来在致徐勤的信里写道:“卓(按:指梁启超)近经痛责后,来书引过。然如去年事,及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汝等近来不敬如此,市井人尚不至是,而谓学道者如是乎!违命专横既久,自忘其不可矣。”[2](P133)加上康有为1899年10月底由加拿大假道日本来港时,日本政府拒绝他在横滨上岸,也使他对日方是否能够容留、支持保皇会的活动存有疑虑。在这样的情况下,康有为自然要舍弃横滨,而选择澳门作为保皇会总部的驻地。
当然,澳门虽被确定为保皇总会的驻地,但其不少工作仍需要在香港进行,一些人员亦来自香港,因此康有为在设立保皇总局时,又有将港澳的力量联为一体的想法,澳门总会后来又被称之为港澳总会、总局,原因也在于此。
三、澳门保皇总会的人员构成
可能是由于秘密工作的缘故,澳门保皇总会未曾留下其人员名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会负责人在同澳门总会人员的通信中,也多以字、号或隐语相称,从而给了解澳门保皇总会的人员构成造成一定困难。现只能根据相关资料作一些考察分析。
澳门保皇总会人员,由在澳门(或者香港)长期生活的维新派人士和临时奉派来澳工作的人员两部分人组成。属于前者目前可考知的主要有:
王觉任,字镜如,广东东莞人,康门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长期在澳居住,曾任《知新报》撰述,是澳门保皇总会初设时的负责人。康有为对其颇为信任,曾多次向人夸赞“当今办事极要之时,镜(按:指王觉任)极从容”[2](P105);“镜实美德,宽博有谋,沉密可托,无过之者”[3](P333)。但保皇总会成立不久,王即因母病归省,离开澳门。后期根据康有为的指令,王又“强出任事”,重返澳门协助主持总会工作。
何廷光,字穗田,原籍广东顺德,澳门当地巨商,少入葡萄牙籍,《知新报》创刊后与康广仁同任该报总理,保皇会成立后积极参与会事,并从经济上多所赞助,故被康梁等人所倚重。康有为曾称赞道:“如港澳中办事多年、忠义热心第一者,莫如何穗田、邝寿文二人。”[4](P51)关于何在保皇会中所任职务,一说其为澳门“分会长,并兼总会财政部长”[5](P73);另一说其为“保皇总公司大总理”[6](P317)。
邝寿民,康门弟子,居港人士,据保皇会的《敬告各埠同志书》中称,他和王觉任“家皆素封”,“自戊戌以来,力任会事,万恐千惊,忧疑无数,始终担荷,舍家忘身”。因为他在香港开有店铺,故总会在港事务多由其负责,“凡同志应接往来,迎送招待,买物办事,零碎重叠,以百埠及局内人办事之付托,其繁夥不可思议,寿民一一理之”;“数年以来,港无会所,皆以寿民之店为之”[4](P266~227)。
陈士廉,字介叔,康门弟子,居澳人士,澳门保皇总会设立初期曾协助王觉任主持会务。
何树龄,字易一,广东三水人,康门弟子,居澳人士,曾任《知新报》撰述。
刘桢麟,字孝实,广东顺德人,康门弟子,居澳人士,曾任《知新报》撰述。
梁应骝,字少闲,康门弟子,居港人士。
属于后者目前可考知的主要有:
徐勤,字君勉,号雪庵,广东三水人,康门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曾任《知新报》撰述,戊戌政变后赴日本,1900年4月从南洋返回澳门,接替王觉任主持保皇总会的工作。但康有为对其工作状况甚为不满,故不久又加派叶湘南到澳门,并要王觉任“强出任事”。庚子勤王运动失败后,徐勤和澳门保皇总会的工作颇受海外保皇会众和华侨的非议,康有为曾致书侨商邱菽园,解释他当时何以安排徐勤赴澳门主持保皇总会事务的原因,称:“仆于用人,才性略皆知之。勉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所长,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而勉忠直之美,任(按:指梁启超)最敬之,识人最多而有望,任累书劝其归办事,仆但令其往吕宋游说。适镜母病将死,于是勉替之。至六月时,仆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复命。勉性强直,又管财权。强直则多以声色加人,管数则以出纳节制见嫌于人。故数月以来,谤书已多,皆由此故。”[3](P332)康的话虽有推卸责任之嫌,却也可以从中窥知当年澳门保皇总会人员更迭的一些内幕。
叶湘南,字觉迈,康门弟子,1900年夏奉康有为之命从日本返澳,会同徐勤一起主持保皇总会事务。按照康有为所发指令,叶与徐二人的分工是:“内事筹划、接信电、复信电,湘可专之;其应接人士,抚绥豪杰,则勉意气激扬,能感动人,勉则专任外交可也,与湘分职。”[2](P134~135)相比之下,康有为当时对叶湘南的信任明显超过徐勤。
韩文举,字树园,广东番禺人,康门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曾任《知新报》撰述,1900年夏奉康有为之命从日本返澳门,参与保皇总会的工作。据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一文记述,韩在康门弟子中属思想较为激进者,其人“品学兼优,迭任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神户《东亚报》、横滨《清议报》、《新民丛报》各报主笔,自号扪虱谈虎客,鼓吹民族主义最力。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间有排满言论,以畏惮其师责备,往往假借扪虱谈虎录栏中发表之”[7](P30)。
欧榘甲,号云樵,广东归善(今惠阳)人,康门弟子,是《知新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00年夏奉康有为之命从日本返澳门,参与保皇总会的工作。欧的思想倾向与韩文举颇相类似,据载其“少与邑中秘密会党游,持论激烈,行文高古,尝在《清议报》痛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理,康有为斥为大逆不道”[7](P30)。
梁炳光,字子刚,旅日粤籍侨商,为横滨福和商店少东主,康有为的慕名拜门弟子,得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信任,庚子勤王期间被派赴澳门总会,专门从事广东方面的武装发动工作,是康氏勤王计划中“以大事托之”的“统兵之人”[3](P330)。据桑兵先生考证,保皇会人士通信中常常提到的“井上”,就是此人,井上是他的日文名字或代号[8](P71)。
张学璟,字智若,康有为的慕名拜门弟子,奉派由日本来澳从事武装勤王活动,据说他和罗润楠二人“任事沉毅,在康徒中以交通会党绿林著称,主任孙康合作之说亦最力”[7](P31)。
罗润楠,字伯雅,康门弟子,奉派由日来澳活动。
除上列人士外,根据康有为、梁启超、徐勤等人的往来书信,此一时期参与过澳门保皇总会工作的还有“南村”、“克”、“春孺”、“季雨”等,所指何人需进一步考订方能确定。
从上述已知的澳门保皇总会人员情况来看,基本仍是《知新报》的老班底,而且多为康门弟子。此一时期先后主持澳门保皇总会会务的王觉任和徐勤,都是康有为万木草堂办学时的大弟子,又都担任过该堂学长,深得康有为的信任,故能被委以澳门保皇总会总办的重任。其他总会中的康门嫡系弟子,如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陈士廉等,也都担当重要的角色。而澳门当地巨商何廷光,虽被任命为总会财务总管之职,实际上却未能与闻机要。梁启超曾在致康有为的书信里写道,“穗田(按:指何廷光)吾知其为总理,而非能定主意之人”[1](P233);冯自由后来在《革命逸史》一书中述及此段历史时也说,何当时“仅为一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特康梁之一种工具而已”[5](P74),当系实情。
四、澳门保皇总会的运作状况
澳门保皇总会设立后,其内部机构的设置、分工与运作,并未能够及时走上正轨。初期主持会务的王觉任,“谨有余机变不足”(梁启超语),遇事独断独行,行动诡秘,以至引起海外各地保皇派人士的很大不满。梁启超在致澳门总会以及康有为的书信里,多次批评澳门总会运作上的缺陷:“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无所旁贷。但弟遥揣情形,似觉未免散漫。他事且不论,即如檀山开会以来,仅得总会一信,而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不免有相怪责之意。”[1](P207)“澳中名为总局,而经两三月无一书与各会,实足以灰人心,(弟子现每水船,必有信遍寄各处。)乞严定职守以军令行之为盼。”[1](P214)“澳门总会似太散涣,弟子始终忧疑之。譬如今弟子有事欲与总会相商,不知商于何人乃有力量。……请先生明示,亦望告其人,使自行其主权,勿放弃责任。”[1](P229~230)
梁启超还曾向康有为提出整顿澳门总会会务的办法:“澳门为通国总会,必当更定一办事条理乃可。弟子之意,当设一总理,总持各事,设一司会,专掌会计出纳,……设通信员二人,一专主与南洋、澳洲各会通信,一专主与日本、美洲通信。凡已开会之地,每水必有一信往,报告中国近事及各埠本会之情形(亦令各埠每水报告总会),未开会之地,设法查访其热心人,即与通信。设议员十数人,专主议行各事,各专责成,井井有条乃可取信于人。”[1](P210~211)
鉴于这些情况,同时为了加强总会的工作,康有为于1900年4~5月间,先后调派徐勤、叶湘南、欧榘甲等人返澳门,一时保皇会精英云集于此。康有为指示徐勤等人:“港澳办事,当分内政、外交、理财、书札。”“事多人散,宜有专责。……大概言之,湘(按:指叶湘南)之综核,可专理财;雪(按:指徐勤)之开诚,可专外交[二事寿(按:指邝寿民)皆可帮办]。而镜(按:指王觉任)总内政,此合中之分也,如日本内阁之法。”“刚、智、雅、实、南村、云、颖、克及办事诸子,有事可公议。”康有为又对澳门总会日常事务的处理作出细致的规定,包括“写信必用密格,以免遗失”;“来款无论何处汇到,每月收支造具清册,一存港澳,一寄星洲”;“每信存稿列号,以便稽核”;“查探各事,必取精警聪明之人,日日奔报”等[2](P123)。尽管如此,澳门总会的运作情况此后仍不尽人意,因此不仅继续受到梁启超等人的批评,而且招致康有为的严厉斥责。追随于康氏左右的思庄曾致书徐勤写道:“自义和变乱,半月有余,往港函电纷纭,不知其数,乃绝未得详复。此间虽苦心筹划,终不能遥断,故长者(按:指康有为)怒气如山,痛恨切至,言及,港事,疾声厉色,无日不恨公责公,以为误天下大事。”[2](P196)然而澳门保皇总会运作不良的状况有其深层原因(下目对此将有论列),实非徐勤一人之责,故经此次痛责之后,其情况并未见有多少好转,直到1901年初它停止运作为止。
五、澳门保皇总会的主要活动
澳门保皇总会设立时,正是康有为等人筹划发动大规模武装勤王运动之际,两广地区和长江流域被确定为两个经略的重点,长江流域勤王起义的组织主要由唐才常及狄葆贤等人在沪、汉一带进行,而两广地区武装勤王的发动则成为澳门保皇总会的主要任务。所以澳门保皇总会成立之后,即以绝大部分精力投入此项任务之中,具体来讲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网罗豪杰”。即联络各地会党首领、散勇头目、防军员弁乃至对清廷不满的社会名流,组织勤王军。经过康有为和澳门总会的努力,这方面有一些收获,先后与康有为以及澳门总会建立联系或者答应参加武装勤王的,有多路人马,包括会党人物区新、傅赞开、康四、林玉、陈廉君、陈翼亭、陈紫瀛、李立亭,团防首领谢元骥,曾任台湾义军统领的丘逢甲,曾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等。他们有的还曾亲自来到港澳,与保皇总会接头,秘密筹划起义事宜。因此,康有为在1900年夏曾对两广勤王作出十分乐观的估计:“西省中现有版筑三千,康四之数万,三品亦来在港,李立之弟亦在港,李立亭已来归,伏莽已全归我牵制,不患无人。又有薇老(按:指唐景崧)在桂留驻,不患无人。而版筑劲旅可以扫地,同翼之正军前驱。计至当时沿省附从,拥众万矣。”[2](P116)又称:“今日之正办,但在多得数万金购数千械,分给翼亭、区、傅、徐老虎数军,则横行江湖,可操必胜。”[2](P118)回澳主持保皇总局事务的徐勤也相当自信地表示:“百事俱备,只欠东风。”康有为、徐勤的这种乐观态度虽然受到梁启超的质疑,嘲讽其“东风固欠,而百事所缺,亦实多多”[1](P231),但那会儿一时之间澳门总会成了华南各种勤王力量的调度中心,却是事实。
二是接受、经管各处捐来的勤王款项。保皇会组织武装勤王的活动经费,基本来自海外华侨的捐助。据有的学者考证,整个勤王活动中经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和各地保皇会的努力,在海外募集到的捐款数约在40万元左右,而实际到手的大概不出30万,其中除了直接拨给自立军起义使用的10万有零外,其余有17万是用于两广勤王的开支。另据梁启超1900年5月19日写给叶湘南等人的信里称,“澳中款项已得十万内外”[1](P226),如果加上5月19日之后续得的部分,澳门总会在这一年度收到的款项当可达到17万这个数字。这些海外汇澳的款项,来之不易,所以康有为一再叮嘱澳门总会:“款原应极撙节,似此区区救中原,岂能妄支。”[2](P105)并指令澳门方面对各地汇解之款要“每月造具收支总册,一存港,一报星洲,以凭核算”,总会额支公款细数及额外支款,同样也要造册上报[2](P153)。但是澳门总会对这些款项的管理和使用似未能完全按照康有为的要求去做,以致屡被指为帐目不清、浪支滥用,康有为甚至气愤地责骂在澳门办事的弟子们:“开一剃头铺,尚有铺章,安有如许大事而绝无章法如是乎?”[2](P153)另外,款项的分配和使用也引起了澳门总会内部人际之间的一些矛盾,乃至于相互攻讦[2](P147)。勤王运动失败后,海外华侨更怀疑捐款被康有为及澳门总会负责人所侵吞或挪用,从而加剧了与康氏及保皇会的疏远。
三是购运枪械。武装勤王必须要有武器,因此购买和运送枪械到中国内地成为澳门保皇总会又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时期致澳门总会人员的书信里,曾多次言及此项事务,强调其重要和紧迫性,指示要以所收款项的大部分用于购买枪械,并将“所购军械弹药发各军,按月收支存贮造册报,一存港中,一存星洲”[2](P153)。现存保皇会1900年制订的电报密码本中,亦多有“△△肯助运军火至△△地”、“乞设法购△△”、“要鸭利刀△△”等字样[2](P548~551)。因此尽管事涉机密,这方面留存下来的资料极少,现已难得其详,但是澳门保皇总会从事了若干购运枪械的行动,却是可以肯定的。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曾电告清驻英公使罗丰禄照会英国外交部,要求英方干预康梁党徒从南洋、港澳等地购运枪炮入粤的活动,声称:“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8](P53)当时的报端也有一些蛛丝马迹的透漏,如上海《申报》1900年5月8日转载香港报纸的一则消息言道:“香港某日报登澳门来信云:自去岁至今,一年之内,匪党之由澳门私运洋枪入中国者,多至二万杆。日前又有德人运到洋枪六千杆,此外未及查知者,更不知凡几。[9](P293)此则消息中虽未指明运枪支入内地的“匪党”究竟是些什么人,但根据时间、地点和枪支数量来判断,很可能与保皇会的勤王行动有关。
四是组织暗杀行动。暗杀政敌是康、梁策动武装勤王时辅助使用的手段,根据康梁的指令,澳门保皇总会曾负责组织对刘学询、李鸿章等人的暗杀行动。刘学询是李鸿章的心腹幕僚,曾参与策划诱捕康有为,1900年初李鸿章奉命来粤办理除康和对付保皇会的活动,刘学询追随其左右,被保皇会视为死敌。梁启超在1900年3~4月间致澳门保皇总会人士的信函里,曾一再敦促对刘、李特别是刘学询下手,认为“肥贼(按:指李鸿章)刘豚(按:指刘学询)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义人人知之,人人有同心。而弟所独怪者,总会现时款项虽非大充,然亦未至尽绌,何以数月以来,无一毫动静”[1](P206、222、238)。1900年4月24日,刘学询在由澳门返回广州途中,遭刺客枪击受伤。事后保皇会人士的通信中称:“此正我保皇发轫之先声,亦不得谓无敢死之士。虽未能致之死地,庶足以寒奸贼之胆,壮我民之气也。”[4](P277)可见这次刺刘行动与保皇会有关,很可能就是澳门保皇总会所策划。此外,由澳门保皇总会的刘桢麟等人主持,还曾策划派人赴京刺杀荣禄,“以报六君(按:指戊戌六君子)之仇”,但后来并未能够进行[2](P462)。
六、澳门保皇总会停撤的原因
澳门保皇总会设立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适应保皇会在国内特别是两广地区开展武装勤王运动的需要,然而到1900年8月之后,保皇会在国内的活动连遭挫折,首先是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义遭镇压,接着两广武装勤王的行动计划也胎死腹中,保皇总会在澳门的工作亦受到清廷的严密监视,越来越难于开展。值此状况,康有为对澳门方面的兴趣和期望迅速消失,开始考虑停撤澳门保皇总会的问题。1901年初,根据康有为的指令,澳门保皇总会“暂停”工作,机关报《知新报》停止发行(现存《知新报》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1月20日即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出版的第133册),徐勤等保皇会的骨干分子也纷纷撤离澳门,总会的原有职能(如接收各处汇款、通信等)改由康有为在庇能(槟榔屿)亲自经管。康氏1901年7月致谭张孝和域多利保皇会的两封书信中有言及此事之文字:“澳局因各省委员常驻窥探,连捉吾党,屡泄事机,故我阳命暂停,并《知新报》亦行停罢。此实不得已苦极之事。自外视停罢之后,乃再行密开。”[4](P33)“澳局暂停,因各省督抚密派委员常川驻扎,密查我事,故拟欲合先离之法,先将总会暂裁,及《知新报》、储才学堂一律停止,使其无从稽查,亦无由知我消息。盖凡办事,近城则消息易泄,去年之事即败于泄。今一切密事,改由庇中,若有书,可直付来。”[4](P34)
按照康有为信中的说法,澳门保皇总会只不过是“暂停”、“暂撤”,避一避风头而已,将来还准备“再行密开”。然而实际上,此后保皇会的活动重心再也未曾回到过澳门。虽然在保皇会后来几年的历史上,仍有“港澳总局”的名目出现,但已主要是指香港方面的活动[2](P215~216),故又被人称之为“港局”,而且其工作任务和权限也已不能同当年的澳门总会相比。因此可以说,澳门保皇总会的历史到1901年初已经基本结束。
澳门保皇总会共计设立1年有余,曾被康有为等人寄于厚望和委以重任,但最终却未能有所作为,不得不以停撤告终。其原因有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有关(主要是自立军起义及惠州起义失败后,清廷加强在各地、尤其是两广的戒备,勤王力量受到震慑,难于有所作为),亦有与澳门总会工作本身的缺陷有关。现就后者再作一些分析。
首先,会长与总会机关相分离是一个大的缺陷。澳门总会是保皇会的中枢机构,起着联络调度各路勤王人马、接收和分配饷项的领导性作用,但是作为保皇会会长的康有为却并不在澳,而是在新加坡进行遥控(当时的通讯手段还较落后,主要依靠书信进行联络,而澳门与新加坡之间的书信往来有时需1个多月),这样就难免产生调度乖方、指挥不灵等问题,加之康本人的战略决策又时有变化,对先取广东还是主攻广西长期摇摆不定,致使前敌指挥更加无所适从。面对此一缺陷,康有为亦曾考虑自己返回港澳、亲自主持总会工作的问题,梁启超也极力加以怂恿,但最终未能成行,无法弥补这一缺陷。
其次,澳门总会自成立之后一直处于涣散和效率低下的状态,后虽有多名保皇会精英奉派返澳任事,仍难有起色。其中关键问题是主事的康门弟子们原先大都是一介书生,缺乏政治经验和组织能力,而且仓促受命,临时搭建指挥班子,内部矛盾甚多,运转起来自然相当困难。还有一点是他们和乃师康有为一样,门户之见甚深,用人偏好同门,这无疑是阻断贤路,难以成大的气候。
其三,澳门作为勤王活动的指挥中枢,虽然有其有利的条件,但也存在着不利的一面。从地理条件上讲,澳门地域十分狭小,在未引起当局和清廷注意的情况下,尚可因其偏处一方而成为保皇人士及家属的活动与避难之所,但一旦被注意,举手投足皆在官方监视之中,原有优势即不复存在。康有为后来在总结澳门工作教训时讲:“试问今日之事为何事乎?乃秘密之事也。稍有疏泄,则办事者杀身无地矣。港、澳皆驻委员(按:指清廷所派侦缉人员)密查我事,同志数人知之。然今各事犹皆败于泄,致使大款涂地,人才陨落。”[4](P32)此处说的就是这一情况。而且澳门此时的对外交通、通讯、金融等都还不够发达,许多事情上不得不仰仗香港,这也给保皇总会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从社会条件上讲,康有为等人在澳门虽有比较坚实的工作基础,但基本局限于华人知识分子和少数商人,既缺少地方政治势力的支持,又没有雄厚经济实力赖以支撑。保皇总会开展勤王活动的经费几乎完全依靠海外汇来的捐款,数目有限,时有不继之虞,而澳门本身又无从筹措巨款,势必穷于应付。此外,澳门正处于葡萄牙统治之下,而葡人此时唯英人之马首是瞻,英人虽对康有为取保护态度,但从维护自己的利益考虑,反对其在两广发动武装勤王、尤其是由港澳起兵袭取广州的计划。英人这一态度,势必影响到葡人。澳门保皇总会的活动不能见容于港英和澳葡,自然难于生存。
收稿日期:2003-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