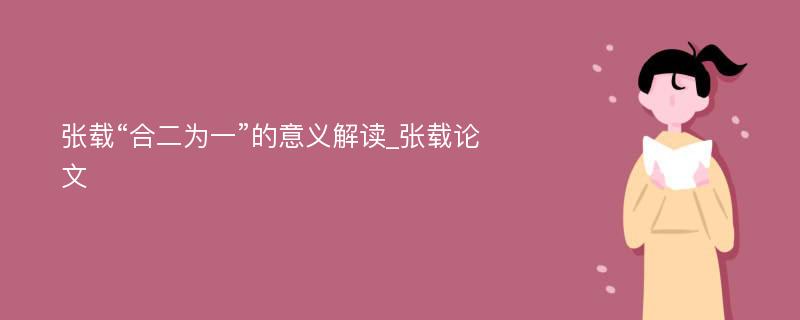
张载“合两”成性义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性”可以说是张载哲学最重要和含义最丰富的一个范畴。作为宋明理学气学派的创始人,张载对传统儒家疏于考量的“性与天道”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张载的性论,又是他哲学体系中最不易理解的一个部分。张岱年先生言:“张子的性论,最不易了解,因其合宇宙之性与人性为一。”(张岱年,第215页)这种合一是了解张载性论的一把钥匙,因为“合”之本身便是张载性论构成的基本方法。
一、“尽性”与“成性”
张载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张载集》,第9页)性是合太虚与气化之“两”而成的。虚与气双方的存在和作用无时不在,它们共同构成了张载哲学的对象世界。而张载对之加工的统合兼体,就产生了“性”的范畴。如此得来之“性”,其意义往往是与“尽性”的诉求联系在一起的。张载云:
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之。(同上,第7页)
“至静无感,性之渊源”说明的是“人生而静”的天性,天性本体之“至静”状态表明属于渊源潜存之未发;而有识有知的物交客感,自然是感于物而动的已发。未发与已发,静渊与客感,只有充分了解感与无感即尽性之人,才能将其统一起来。联系到他的“合虚与气”,只执著于至静无感之虚或物交客感之气,都是偏于一方而造成了虚气的分离,所以都不能尽性。
但是,虚与感的问题在张载还有更深刻的意蕴。张载分析说: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惟屈伸、动静、终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万物而谓之神,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同上,第63-64页)
此处之“感”与物交“客感”之感有别,牟宗三先生云:“案此感即‘感而遂通’之感,非物交之‘客感’,故曰神。此性体之神用也。”(牟宗三,第423页)所谓“感而遂通”,即《周易·系辞上》所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参照朱熹《周易本义》的解释,“此四者,易之体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体;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动静亦如此”。因此,卦体本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然一旦有动,则能感通天下,这可以说是天下最为神妙不测的作用了。
朱熹以体用关系解寂然与感通,并以此揭示易体、人心之神妙,是否合乎《周易》之“本义”暂且不论,其对于了解张载的思想却可以提供一种帮助:感通说明的是性体作用的神妙不测,而由此神妙不测又可以通贯性的本体。所以像神、道、性这样一些范畴本来都是相通的,只是人们从万物变化不测而把它叫做神,使万物通达无碍而把它叫做道,又因万物无不具此体而把它叫做性,其实都表述的是同一种体用关系。当然,要真正把握这一关系,又需要从屈伸、动静、终始双方的往复变化中去体会和归纳。(注:张岱年先生解释张载语云:“性即全宇宙之本性,乃总一的;而其中含两。所谓两即内在对待。惟其含两,故不能无感。实言之,宇宙万物之本性,即屈伸、动静、终始之能而已,此即所谓性,即所谓道,亦即所谓神。此总一之性,乃即人的本然之性。人人物物皆禀有此性,不过有显露与不显露之别。”(张岱年,第213-214页))
可以说,比起《乐记》从“人生而静”的天性出发议论人“感物而动”的静、感机制来说,张载这里的性不能无感之说,已取消了由静性到动欲之间的时间差,即完全移到本体论上来谈性与感。“感”成为性体的最突出的特征,所谓“天所不能自已者谓命,(物所)不能无感者谓性”(《张载集》,第22页)。说明天道流行不已,生生不息,而天道所生万物,由于天道与性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同时禀有了不得不感通之性:“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同上,第63页)性源于天,性即天道也就是当然之义。而天道实际上也就是易道,所以“易”之寂然感通之性也就为万物所共具,而非人性所独享。
于是,一方面,“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同上,第21页)。性体于万物,为万物存在之根据,属于普遍性的范畴,故在天在人,无不是由天而受命,由命而具性,由性而必感。性之体用也就一以贯之,生生不已。而另一方面,由易之寂感的进路,也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由“易”而识性与天道的方便法门。
张载说:“不见易则何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则何以语性?”(同上,第206页)何为“易”?“易乃是性与天道,其字日月为易。易之义包天道变化”(同上)。“易”之所谓“性与天道”可由“日”、“月”两字来构成,合此“两”字正好统摄了“易”之深意:因为“阴阳之义配日月”,又“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周易·系辞上》),故日月天象的循环照耀,鲜明地体现了阴阳造化之性。这样,“易”字“合两”而含性藏天,张载给人们提供了一条循易而知性的道路。但此一条道路不仅是尽性的方便法门,也是儒、释之间得以区分的一个根本标准:
释氏之言性不识易,识易然后尽性,盖易则有无、动静可以兼而不偏举也。(《张载集》,第206页)
儒家之尽性的关键,就在不是只论虚无,而是要兼举实有(气),否则就只能停留在泛泛地“言性”而不能“尽性”上。
在这里,张载“尽性”所要求的兼而不偏,实际上关注的是性的“合成”的问题。正是依赖于合成的机制,性作为总体才能生成:“性其总,合两也。”(同上,第22页)“合两”就是合无与有、虚与气、神与化等等。然而,由此反推,性既然是“合两”而成,从逻辑上说,就必然会存在一个“合成”之前的“未成”,从而与天道即性的架构在形式上产生了冲突。究其缘由,实在于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性虽为万物所共具,“尽性”却只有人才能作为,合两“成性”属于人之自觉。
从来源看,“尽性”源于《中庸》,“成性”却取自《周易·系辞上》,二者在道德创生的方向上可以说是正相反对:“尽性”是从人到天,从尽己性到尽人性、尽物性,最后与天地相参;而“成性”却是自天而人,即由“一阴一阳之谓道”而来的“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后者按张载的解释,“言继继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同上,第187页)。连续性在这里是问题的基础,人承接循守天道不息不止便是善,而此道能在自身不息的道德实践中体现出来即是性,所以“成性”的实质其实在“见性”。但此见性不是一时一刻,而是勉勉不息,继善与成性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当然,就主体条件而论,成性者之间并不完全相同,如仁者、智者便各有所长和各自用力之所在,但他们最终都能够见性有成:“犹勉勉而不息,可谓善成,而存存在乎性。”(《张载集》,第187页)这种存而又存的不已之功,正是成性与否最重要的标志。也正因为如此,自天而人的成性与自人而天的尽性也就贯通了起来。
张载又说: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长,顺焉可也。存虚明,久至德,顺变化,达时中,仁之至,义之尽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继其善,然后可以成人之性。(同上)
天德神妙,可存守而不可致思;大化流行,可顺承而不可助长。如此一种自觉存、顺之功,只要勤勉不息,便能进达天德,随时合乎中道,这就是仁义的最高境界。不论微妙(性)还是彰显(天道),只要存顺不已,便是继天之善而成人之性。这样的继善成性,已经超越了单向的从天到人,而是通过人自觉的道德创造即成性的工夫去实现的。
二、性善恶混与“善反”
继善成性只能在勤勉不息的道德实践中才能实现,这就不得不考虑当性未成时的善恶状态或阶段。在这样的阶段,人的活动尚未发生,应当属于先天的领域;与此同时,善与恶又是相对的,善未得继而恶亦不成,从而形成了善恶混而未彰的状态。即他所称:
性未成则善恶混,故亹亹而继善者斯为善矣。恶尽去则善固以亡(注:此“亡”字《张载集》校改为“成”,然“成”字恐非,因张载下句明言“舍曰(成)善而曰成之者性”。牟宗三云:“从表现上说,善恶相对而施设。及至无恶而全善,则‘恶尽去’,恶之名不立。恶之名既不立,则亦无所谓善,而‘善因以亡’”。(牟宗三,第439页)),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也。(同上,第23页)
从文本的角度说,《周易·系辞上》的“继善成性”说并未涉及到“成性之前”的问题,自然也谈不上善恶混。张载提出善恶混的问题,重在说明先天善恶未分未形,以强调人在后天的道德创造,即只有于此勤勉不倦者,才可望实现善。在这里,善之成形彰显,同时意味着恶之尽除;而一旦恶被尽除,也就无所谓善。这一道理,老子其实早已言之:“(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老子》,第二章)
就此而言,张载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如司马光的性善恶混是不相同的。司马光是从现实人性善恶兼有立论,张载却是将其限制在现实人性未成、人为未施加之时。于是,结果就会是:或者因性未成、善恶未开而人不觉,或者因恶尽去、善无所谓而恶无须说。故从首尾两端看,性善恶混又可以理解为某种意义的性无善恶。究其所以然,实在于张载比较彻底的有无虚实通为一物之说。善恶之有(善恶混)与无(无须说)之通贯则正是其表现。
当然,首尾两端往往又只是一种逻辑的抽象,在现实性上,人是终始处于除恶成性的过程之中的。故他又说:“纤恶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恶未尽,虽善必粗矣。”(《张载集》,第23页)继善成性实际上是以人力改造善恶混的过程,即尽除恶方成性,如果恶未尽除,善哪怕是占有绝对多数的比例,以质而论,仍然不是继善而是“继善恶混”,所以说是虽善必粗。
在张载,性未成之善恶混,重在强调人性的开发存在向善和向恶发展的两种可能,它们都需要在后天的道德实践中去加以验证或实现。所以对人来说,性(善性)的意义正在于它是“未成”。同时,天赋人性的未成或曰善恶混,并不影响天以善为人生的价值指向,并成为人之道德创造的原动力。也正因为如此,他就可以说:
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过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于人无不正,系其顺与不顾而已,行险以侥幸,不顾命者也。(《张载集》,第22页)
“性于人无不善”并不等于先天性善,因为此善是“系”于人之善反与否的后天道德创造的。而所谓善反,其实就是除恶,恶除尽才有性善或者说是成性。这种除恶成善成性的人生实践,就是张载的“继继不已”之功,“继继不已,乃善,而能至于成性也”(同上,第266页)。
“顺命”和“继继不已”在张载是密切关联的,它说明张载的善反并不是要超越天道气化、干预人之受命本身,而是重在谨守中道和顺承天命的自觉。至于通常所谓张载天地之性纯粹至善的说法,实际上是把后来朱熹的观点加在了张载头上。张载只讲到: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同上,第23页)
又说:
人之气质美恶,与贵贱寿夭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今人所以多为气质所使而不得为贤者,盖为不知学。……盖学至于如天则能成性。(同上,第266页)
气质之性是善恶混的,但人可以通过学习和善反的功夫移恶、除恶。善反所成之性是天地之性,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天地之性为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先天性善。张载的“存存在乎性”和“继继不已乃善”已说得非常明白,即只有在人勤勉不息的道德创造中才能有善和成性。不论是“存”还是“成”,都是指人为的工夫,换句话说,天地之性善反则存,不善反则不存。既然天地之性的存与不存取决于人的善反不善反,那么也就不难判定,在张载这里,人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天地之性在。
相反,善恶混杂的气质之性倒是与人受气禀形同在的,因为它本属人之定分。但此定分只是天定,人却是可以因学而移其恶的。由于气质之恶本在不断移除之中,所以君子不会执著于所禀受的气质之性;而不执著于气质之性,目的在于成(存)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说到底是一个全与偏的关系。他云:
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天本参和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尽性而天矣。(同上,第23页)
性之刚柔、缓急、才与不才,都是一偏,所谓除气质之恶,其实就是去偏,它的正面表述就是自孟子以来的养气,以最终回归天道本来的参和兼通。如此便是反本,便是尽性、成性。这样一条进路,可以说是通过形而下的养气修身去成就形而上的本体、性体。
三、“生之谓性”与“有无皆性”
以养气尽性为人生的价值选择,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自然主义的“生之谓性”说的再次否定。张载认为告子的“生之谓性”说十分不妥,因为“以生为性,既不通昼夜之道,且人与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诋”(同上)。
所谓“昼夜之道”,就是神化不测的“一阴一阳”之道,即天道(易道)本身。《周易·系辞上》有“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之说,张载发挥说:“神易无方体,‘一阴一阳’,‘阴阳不测’,皆所谓‘通乎昼夜之道’也。”(同上,第9页)“通”之意即兼体无滞。他又说:“体不偏滞,乃可谓无方无体。偏滞于昼夜、阴阳者,物也;若道,则兼体而无累也。”(《张载集》,第65页)可告子的“以生为性”说却正是偏滞于一方。因为凡生都相对于不生,言昼则不能舍弃夜。性范畴的意义,正在于兼体无累,不落一边,从而才享有本体的资格。这可以说是从本体论上对告子“生之谓性”说的否定。而从生成论、道德论的角度看,人、物均有生,故无法得以区分,从而无法说明人之移恶就善的道德创造的必然性。
当然,以“生之谓性”为谬,并不等于凡人之生者均不可谓性,而是要将其放到有无虚实的兼体中去把握。张载是始终坚持“合两”成性的,在此前提下,方可以说生之事是性。他云:
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同上,第63页)
是否尽性就在于是否能合两为一,这是儒家性论与佛老性论最根本的区别。饮食男女无疑属于生之事,是实有,但在这里却是性本体的直接实现,尽性之功本在其中,否定了此有之用,也就否定了无之体,所以佛老不可能真正把握真理。
从概念上说,合两为性与有无皆性是有区别的:“合两”意味着“通为一物”而不可分;有无皆性则是任一物均可谓性,所以饮食男女皆性也。但总体上二者又是相互发明的,有饮食男女之实事,就必有天德良知之虚理,“是岂无对”?佛老之错误,不在于崇尚虚无,而在于否定实有。所以,性与天道必须要整体地把握。这固然不能像传统儒学止步于“天用”,但更不能像佛教只妄意“天性”,而以天地万物为虚幻。“体虚空为性”的真实合理是建立在“本天道为用”的基础之上的。佛教“不识造化”便妄谈性命,所以根本站不住脚。
当然,如果仅就虚空性体而言,佛教的“实际”、“真际”等约与儒家的“诚”、“天德”等概念相当,他本人亦称“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同上)。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彼语虽似是,观其发本要归,与吾儒二本殊归矣”(同上,第65页)。就是说,儒、佛的本体概念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实质上却是不同的。因为人生、有为、世界等等在儒家看来正是诚之现实的概念,佛教都斥之为幻妄而予以拒绝,结果,诚的概念也就被彻底地空掉了。进一步,张载的性虽然是合虚与气而成,但这种“合”不是一种物理层面的外在的捏合,而是性为气所内涵的有机构成,即所谓“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虚)乃气所固有”(同上,第63页)。在如此的架构中,论气是彰显性之实存,论性则是深究气之清虚。后者便是他的“神”的概念:“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神者,太虚妙应之目也”。(同上,第7、9页)“神”的概念是说明太虚本体微妙应和“可象”气化的名目的,这可以说是从作用的角度去发明虚体,但落脚点还是在虚实有无的统一。又如所谓“神,天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同上,第15页)。天德就是天性,性与天道、本体与作用都统一于气化流行之中。作为对以空寂、虚幻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佛教性空说的批判,张载是以虚性内含于实气来建立起自己的性与天道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