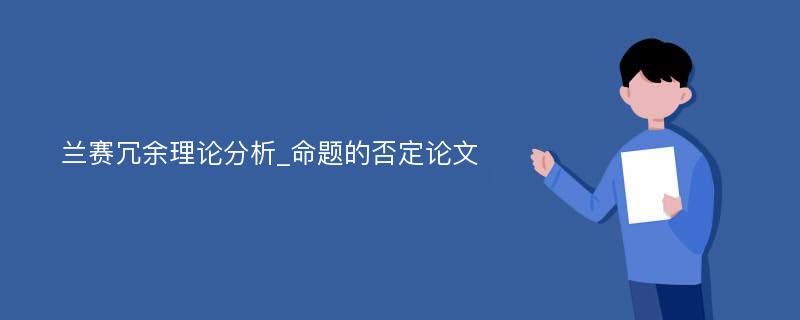
兰姆塞真之冗余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冗余论文,探析论文,兰姆塞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55(2009)01-0038-05
英文Truth是当代西方哲学界特别是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界比较热门的一个概念,也是逻辑学的一个关键性概念。在我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中一般将其译为“真理”。鉴于在当代逻辑学与西方哲学中,Truth的一般涵义是指其值为真的命题或语句,即真命题或真语句,本文倾向于将其译为“真”而非“真理”。
何谓真语句或真命题?说一个命题或语句是“真的”是什么意思?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不同的真之理论。从历史上看,真之理论至少包括符合论、融贯论、实用论、语义论、冗余论等等。
真之冗余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兰姆塞(F.P.Ramsey)。按兰姆塞的观点,“地球是圆的,这是真的”等同于“地球是圆的”。因此,当我们说一个陈述或观点是真的时,我们仅仅表现的是把一个特性赋予一个语句或命题,我们在事实上没有赋予任何东西,好像我们仅仅陈述命题或语句本身。所以,说一个命题“是真的”对于该命题是“一个很明显多余的添加”。兰姆塞的真之冗余论对于现代真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其后,艾耶尔(A.J.Ayer)、斯特劳逊(P.F.Strawson)、霍里奇(P.Horwich)、格罗弗(D.Grover)等在冗余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诸如极小主义理论、代语句理论等,从而形成了一个关于真的“收缩论”。
本文依托兰姆塞的主要相关著作,力求按照他的思路,解读其冗余论的基本观点,并加以评析。
真是什么?当我们说一个观点或陈述是“真的”时,它的特征是什么?这是真之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真之本性”一文中,兰姆塞开篇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区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是真?”,一个是“什么是真的?”。兰姆塞认为,如果一个人问真是什么?他可能希望的回答或者包括列举所有的真(观点或陈述),或者就是关于真的检验标准——一种区别于假的方法,但事实上“我们并不希望学会一种区别于假的完全精确的方法,而是仅仅要知道‘真的’这个词的意思”①。因此,在真之理论中,我们关注的不是前一个问题,而是后一个问题,即说诸如“‘查尔斯一世被斩首’是真的”或“‘地球是圆的’是真的”时的意思。
要讨论“什么是真的?”,首先必须考虑的就是描述词“真的”和“假的”主要用于哪类对象,这就涉及到了真之载体或真值载体的问题,真值载体是指什么能具有固定的真假从而成为真值的承载者。弄清这个问题,是讨论有关“真”问题的基础。兰姆塞在论述其观点时,谈到了三种真值载体,“我们可以用‘真的’和‘假的’来描述心态(mental states),如信念、判断、观点或推测;我们也可以用‘真的’和‘假的’来描述陈述句;此外,根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我们也可以用‘真的’和‘假的’来描述命题,这里的命题,指判断的对象和语句的意义,但它们自身既不是判断也不是语句。”②
以上三种真值载体,分别对应于“心态说”、“语句说”和“命题说”。在逻辑学领域,命题说和语句说是两种较为主流的观点。但兰姆塞却不认同,首先,他谈到“命题不适合做真值载体,因为它是否存在本身就有疑问”③。他认为,虽然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是,命题在最基本的意义下是要么真要么假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某人相信的是一个真的或假的命题进而推出信念的真假。但,命题的存在本身是有疑问的。
关于“语句说”,兰姆塞认为,“很明显,陈述的真与假,依赖于其意义,即使如一些人所说的,判断并不比语句表达得更多,这些语句的真也并不比简单地与其等同的判断的真更为基本。”④
在否定了关于真值载体的“命题说”与“语句说”的同时,兰姆塞开始论证其“心态说”的合理性。在论证之前,他诠释了一个新的概念——“信念”。在他看来,日常语言中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词项能够满足他心目中真值载体的要求。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建议用“信念”或“判断”作为同义词来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信念”与“判断”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应用。兰姆塞对“信念”一词有了新的诠释和要求,这也使得信念能真正地充当起真值载体的角色。
兰姆塞认为,作为真值载体的信念,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第一,信念有命题指称。“一个信念必定是关于某物或其它事物的如此怎样的信念:比如地球是圆的。在这里,我把‘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叫做该信念的命题指称”。“一般地,在逻辑上,我们要表示两个人的信念相似,我们并不说两个人有相同的命题指称,而是说他们在同样的命题中给出他们的信念。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命题指称这一特征的存在,而只是提出了一个如何分析这一特征的观点。因为,没有人能否定这一点:在说到一个比如‘地球是圆的’的信念时,我们是把该信念归于某些特征,虽然这些特征存在于与某一命题的联系之中是很自然的,但我们认为不是命题而是命题指称的特征。”⑤
第二,信念的命题指称必须是命题。“命题指称并不局限于信念,我的关于地球是圆的知识,我的关于自由贸易比保护更优越的观点等等任何形式的思维、知识及印象——都有一个命题指称,这是仅有的或真或假的思维状态。仅仅想到拿破仑不能说是真的或假的,除非想到的是他曾是什么或他曾经做了什么如此之类,因为如果指称不是命题,如果语句表达的不是指称,那就既不真也不假。”⑥
第三,信念具备肯定或断定的特征。“有三个形式相同的命题指称:我可以希望明天是好天气;我想知道明天是否有好天气;我也可以确信明天是个好天气。我们不能将希望、愿望等称为真的或假的,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命题指称,而是因为它们缺乏被叫做肯定或断定的特征,一旦这一特征不同程度地缺乏,我们就不能说它们是‘真的’或‘假的’,虽然所需要的程度是最轻微的并且当只是为了讨论其后果时我们能够说某一假定是‘真的’。”⑦
可以看出,兰姆塞所理解或要求的“信念”超越了命题的抽象实体,但同时又具有命题指称的特性,能很好地承担起真值载体的功能。对此,著名逻辑学家哈克(S.Haack)有如此的评价:“考虑到由符合论的装饰品——事实与命题——所引起的困惑,冗余论的简朴性是极其诱人的。可以理解兰姆塞把这看作是他理论的一个长处,避免了关于事实的性质和个别化的符合解释所引起的困难。”⑧
在确立了真之载体是“信念”之后,马上要回答的下一个问题就是:“真”的意义是什么?说一个信念是“真的”是什么意思?对此,兰姆塞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设想一个人相信地球是圆的,那么,他的信念就是真的,因为地球是圆的;或者推广来看,如果他相信A是B,那么,如果A是B,则他的信念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
以上关于“真的”的解释看起来是很清晰的,但要构造其精确性定义还存在困难。原因在于:一个信念的命题指称可能有大量不同的复杂的形式,我们不能将所有的信念都描绘成“A是B”。例如,信念可能是“A不是B”、“如果所有的A是B,那么或者所有的C是D,或者一些E是F”,等等。事实上,我们不能在可能出现的形式数目上进行限制,因此,真的定义必须要涵盖所有这些形式。但,如果我们尝试这么做的话,会发现这将永无止境。因为我们必须说:一个信念,如果它是“A是B”这样的信念,那么,当A是B时,它是真的,如果假定它是“A不是B”这样的信念,那么,当A不是B时,它是真的;假定信念是“或者A是B,或者C是D”,则或者A是B,或者C是D时,它是真的,……为了避免这种无限性,兰姆塞认为,我们必须考虑一个所有的这些形式都能被包括的命题指称的一般形式,这个一般形式就是信念“P”。他说“不管任何信念,我们都可以符号化为一个信念‘P’,这里的P是一个可变的语句,就如A和B是可变的词或词组一样。”⑨以这一概括为基础,兰姆塞给出了“真的”的如下定义:“一个信念是真的,如果它是一个信念‘P’,并且p”。⑩
对这一关于“真的”的定义,兰姆塞作了一些解释。他认为,这一定义可能看起来有些奇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P是一个可变的语句或语句变项,也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个包含了动词的语句。事实上,“P”确实包含一个动词,比如它可能是“A是B”并且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以“并且A是B”为结束。
应该说,兰姆塞的这个定义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真”的实质性的信息,他对“真”的分析只是建立在对真之载体——信念的分析上,即信念如何能成为真的载体,进而论证一个信念是“真的”,需要具有怎样的特性。按照兰姆塞的观点,“真的”可以转化为“有其命题所指并且断定它”,因此,“真的”定义也可以是:对于所有的p,如果我们断定p,那么p。
兰姆塞对“真之本性”的分析着重于对“什么是真的”的分析,这是冗余论的特点。一些冗余论的批评者们从上面的表达式出发,认为兰姆塞没有分清“被断定”与“是真的”的区别:“我们不能接受真理收缩论的另一个理由是:它把‘是真的’和‘被断定的’两个不同语词加以混淆并等同起来。我们说‘p是被断定的’,这是一个语法概念。我们说‘p是真的’,这是一个语义概念,它们属指号学的不同范畴,因而不能混同。因此,不能用一个去代替另一个。”(11)关于这一批评,我们认为并不公平。事实上兰姆塞并没有将两者混同,相反,他看到了两者的区别并试图加以区分。对于“是真的”,他认为‘真的’一词必须在有命题所指并且要对其断定下才能使用,于是,他将两者的关系通过一个表达式来描述:“一个信念p是真的,当且仅当有信念p,并且断定它。”
在确定了真之载体是信念,且给“真的”信念下了一个定义之后,兰姆塞提出了其真之冗余论:“该信念是真的”中的“是真的”完全可以删去,因为该信念本身已是一个完整的语句,不需要在后面添加一个多余的谓词“是真的”。
兰姆塞具体通过如下三个陈述来说明:
地球是圆的。
地球是圆的是真的。
任何相信地球是圆的人都真地相信着。
兰姆塞认为,很显然,这三个陈述是互相等值的,在意义上不可能断定其中一个而否定另一个。例如,说地球是圆的是真的并且地球不是圆的,这显然是荒谬的。具体而言,第一个陈述没有涉及到真,它只是说地球是圆的;在第二个陈述中我们增加了“是真的”,但并没有改变陈述本身的意义;至于第三个陈述,它的意思就是从地球是圆的而来的,在某种意义上,除了它考虑的跟某人相信或说出它的可能性有关外,它的涵义并不比第一个陈述多。因为,“任何一个相信地球是圆的人都真地相信着”只意味着地球有任何相信地球是圆的的人相信它具有的性质,那就是:地球是圆的。(12)
在“事实与命题”一文中兰姆塞则着重就两个方面来分析这种多余性。他认为,一方面,事件“凯撒是被谋杀的是真的”的意思就是凯撒被谋杀,“凯撒被谋杀是假的”的意思就是凯撒没有被谋杀。我们使用“真的”、“假的”这些词,有时仅仅是为了强调,或是出于风格的选择,或表明我们在论证中所声明的立场。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他被谋杀是一个事实”或者“他被谋杀是反事实的”。另一方面,我们有陈述,但不能在陈述中用普通的语言消除“真的”和“假的”这些词。因此,如果我说“他总是正确的”,我的意思是他断言的命题总是真的,似乎不存在没有使用“真的”的任何方式的表达。但假如我们如此操作:“对于所有的P,如果他断定P,那么P是真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置函数P是真的就简单地等同于P。例如,“凯撒被谋杀是真的”的赋值与“凯撒被谋杀”的赋值是相同的。在英语里“是真的”是给予语句一个动词,忘记了本身“P”已经含有一个(变)动词。考虑命题只有一个形式被谈论,说相关形式aRb;那么“他总是对的”能够被表达为:“对于所有的a,R,b,如果他断言aRb,那么aRb,”在这里,“是真的”就是很明显的多余的成分。这样分析就显得清晰些。(13)
通过上述分析,兰姆塞得出结论:一个信念P是真的,当且仅当P。“P是真的”完全与P相同,所以,“真的”和“假的”这两个谓词是可以被删除的,并且删除它们不会造成意义上的损失,“真的”谓词是多余的。
对于冗余论,很多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看法,集中到一点就是“真的”这一谓词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消去的,“真的”并非总是多余的。例如,逻辑学家哈克认为“兰姆塞的冗余论在面临命题形式复杂化时,‘是真的’不能够消去,如,‘对于所有对象(命题?)p,如果他断定p,那么p’。这里被约束的‘p’在语形上像单独词项一样,因而,最末尾的‘p’就必须作省略理解,理解为隐含地包含着一个谓词,目的是为了把它变为一个语句范畴中的东西,能够放在‘那么’的右边,那么从语法的角度来看,就有:
对于所有的命题p,如果他断定p,那么p是真的。
但是,如果这一分析最后表明包含着谓词‘是真的’,则真并没有被消除,并且它不是多余的。”(14)
我们认为,哈克并未分清冗余论所消去的是哪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本身就是语句的谓词,充当的是谓语的成分,这是不能消去的。兰姆塞所消去的是作为一种真值函项语句联结词,即把它们应用于一个真语句就产生一个真语句之类,类似双重肯定作用的“是真的”。依我们的看法,兰姆塞提出真之冗余论的目的不在于一定要去掉“是真的”,或者说一定不能再使用“是真的”,而在于分析“‘是真的’是可以消除的”。他所完成的工作是证明“p是真的”可以简单地等同于“p”,从而推出结论“‘是真的’可以消去”。这点他已经做到了。兰姆塞的另一句话实际上是对他工作侧重点的强调:“问题不在于真和假的性质,而在于判断和断言的性质,因为真正分析困难的是‘他断言aRb’”(15)
可见,兰姆塞所研究的真仅仅强调的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谓词,添加在“真语句”后的词“是真的”,它实际了是一个真值函项语句联结词。它们起着类似加重肯定或加重否定的作用,从认知内容和真值函项上看,这样的附属物是多余的。但冗余论从未要消去充当本身语句谓词的“是真的”,即并非自然语言中运用广泛意义上的“真的”。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抵挡众多对冗余论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主要的想法是:“如果‘真’这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是不必要的,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个词?这是一般的冗余论要解释的。”(16)
我们一般把兰姆塞的真之冗余论归属于真之收缩论,与真之收缩论相对应的是真之坚实论,它包括真之符合论、真之融贯论、真之实用论等等。
兰姆塞是收缩论的开创者,也是收缩论的代表人物,但似乎兰姆塞对真的分析却很容易令人想到符合论。
菲尔德(Field)就把兰姆塞归于符合论的派别。他认为,对于兰姆塞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关于真和假的特性的问题,而是关于判断和断定的特性的问题。在真概念应用于命题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冗余的,说命题“恺撒跨过卢比肯”为真等于直接说“恺撒跨过卢比肯”。但我们所关心的真正问题是,是什么使得一个陈述或思想状态表达命题“恺撒跨过卢比肯”,是什么使得一个陈述或思想状态具有真值条件“恺撒跨过卢比肯”。他写道:“根据兰姆塞的看法,‘表达一个真命题’显然是一个符合论概念(即不是一个收缩论概念)。这从兰姆塞对是什么使得一个思想状态表达命题“恺撒跨过卢比肯”所给出的解释中显得很清楚。这样一个思想状态必须具有兰姆塞所认为是‘词语,大声说出或对自己说出或仅仅是想象的’的‘思想因素’;思考‘恺撒跨过卢比肯’就是处于这样一种思想状态当中,这种思想状态把代表恺撒的思想语词,代表跨过关系的思想语词,以及代表卢比肯的思想语词(以正确的方式)连结起来。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语词代表恺撒,或跨过关系,或无论什么,这一点并未得到分析。但很清楚兰姆塞认为对是什么使得一个思想符号代表一个对象或关系给出某种自然化的解释是恰当的。显然按照这种看法‘表达一个真命题’的概念行为根本不像消引号真或其它从最小资源定义得到的概念。”(17)
兰姆塞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从来没有使用‘符合’一词,但我们的定义仍可能被称作‘真之符合论’。如果是对‘A是B’而言,我们还可以根据事实上A是B从而说它与‘A是B’的信念相符合。”(18)
因此,可以认为,兰姆塞的冗余论在形式上属于收缩论,它提议将多余的谓词“是真的”删去,但实质意义上有符合论的痕迹:说p是真的就等于说p。这种解释与亚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是什么不说是什么,不是什么说是什么,这是假的;是什么说是什么,不是什么说不是什么,这是真的”有某些渊源关系。但是,与传统符合论不同的是,真之冗余论强调对命题指称的分析。
兰姆塞认为,对命题指称的分析虽然是很小的一部分,也是很容易的一部分,但是却不能忽略。因为这正是真所依赖的,我们只有通过分析指称来定义真,而不能通过真来定义指称,故如果不对命题指称这一词项进行分析并使用它,将会忽略和掩盖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就会像冗余论批评者所谈到的,出现将“真的”与“断定”倒果为因。只有当我们知道信念的结构,我们才能说连接真信念与事实的是什么类型的“符合”。例如,如果是“A不是B”,则没有如此的事实与之符合,如果我们不知道命题指称的分析并且不相信这种分析,我们就不能描述这种“符合”的本质。
相比传统的符合论,有了命题指称的分析,也使得信念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正确地被描述,可以摆脱符合论的很多困境。例如,如果信念是析取性的,比如琼斯认为史密斯或者是个说谎者或者是个傻瓜,那么,我们不能说通过“析取的事实”即“史密斯或者是个说谎者或者是个傻瓜”就得出结论:信念是真的。但如果史密斯或者是个说谎者或者是个傻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能,我们对此进行命题分析,就可以得到结论:信念“史密斯或者是个说谎者,或者是个傻瓜”为真。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⑨⑩(12)(18)F.P.Ramsey,the nature of truth,in Michael P.Lynch(Editor),The Nature of Truth: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The MIT Press,2001,p433,433-434,434,434,435-436,435-436,436,437,437,437,439-440。
⑧(14)哈克著,罗毅译:《逻辑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9,163页。
(11)弓肇祥:《真理理论——对西方真理理论历史地批判地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3)(15)F.P.Ramsey,Facts and Propositions,in his Philosophical Papers,ed.by D.H.Mell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34-51,34-51.
(16)M.P.Lynch,Deflationary Views and Their Critics Introduction,in The Nature of Truth:Classic and Conemporary Perspectives,The MIT Press,2001,p421-431.
(17)Field,Hartry."The Deflationary Conception of Truth",in Graham MacDonald and Crispin Wright(eds.),Facts,Science,and Morality:Essays on A.J.Ayer's Language,Truth and Logic,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p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