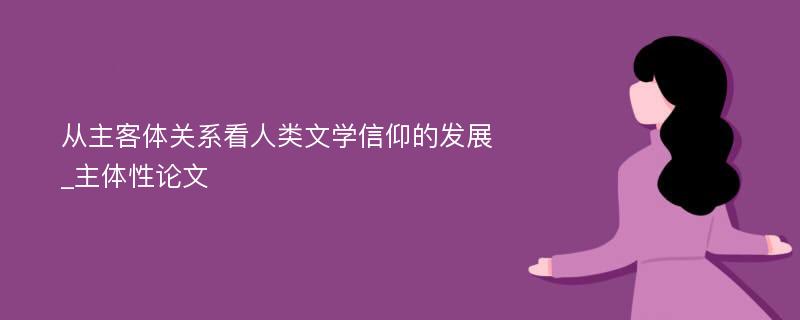
从主客体关系角度看文学中人类信仰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度看论文,主客论文,人类论文,关系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3)04-0059-04
为了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认清今天的位置,确定未来的合理走向,不致在太过漫长的旅途中迷失自己,人类必要反思历史,尤其是文学史。因为文学比历史记录了更鲜活的生命体验,其触角更自觉地探测到人类心灵深处。对这部人类的心灵史进行宏观的纵向考察,可以发现在人类深层心理结构中,信仰问题是挥之不去的永恒情结。文学与信仰根深蒂固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具有对有限现实、对知识、实证的超越性,都体现了对人生目标、终极意义的求索,都有较强的主体性投入,将感觉、情感、想象、理性与非理性因素高度聚合。而信仰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植根于人类生存、发展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中。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所面对、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这种主客体关系可以笼统地分为两大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中不同层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文出于论述问题的需要,对后者暂且忽略。
只从人与自然构成的主客体关系状况看,随着人类认识及实践能力的发展,人在自然面前的主体性地位一直在提高,但有一个事实亘古至今地苦恼着人类,那便是在自然客体面前主体的有限性。信仰起源的根本原因及其意义就存在于有理性的人类对自身有限性的自觉以及克服这有限性的努力之中。我们这里所用“信仰”一词是广义的,不局限于对某种主张、主义或宗教的绝对信赖和尊崇,而泛指对某种价值或力量的信奉与敬仰。有这样的信仰,人类就有克服有限性的精神力量,有对未来的信心,有当下生存的坚定立场和明确态度。否则,有理性的人类会感到难以承受的彷徨和恐惧,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当代,这一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由于信仰植根于人类面对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状况及对主体有限性的超越性想象,伴随人类主客体关系的发展,文学中人类信仰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阶段:对神灵的信仰——对人类自身的信仰——信仰危机。反思这一发展历程有助于我们在当代寻找合理的意义建构方式,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远古人类主客体之间力量相差悬殊,主体性不发达,致使人类以文学的方式建立了对神灵的信仰,这表现了主体性的迷茫和幻想提升,也成为人类度过荒蛮、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支柱。
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看,与辽阔而苍莽的自然力量相比,远古时期童年人类的认知及实践能力实在太低下了,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和生死等问题迷惑不解,他们甚至无法理性地把自己与其面对的自然世界加以区分。虽然不能实际地解释与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但远古人类比今天更强烈更直观地感觉到那无处不在起作用的外在自然。在自然的神秘力量面前,人类倍感渺小与恐惧,但萌生中的主体意识决不甘心这渺小与恐惧,虽然凭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与自然神力抗衡,但战胜自然的渴望是那么强烈,主体只有与客体的力量趋向均衡,在主客体关系的和谐(哪怕是幻想的和谐)中才会得到安宁。作为自然发展的最高成就,人类自有其独到之处,理性与想象联手帮助人类找到了克服有限性的途径,他们“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1](P113),于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春夏秋冬生老病死……一切客体的自然的现象都得到了神话化的解释和安排,世界于是成为有秩序、可理解甚至可控制的了。人类找到了可供信奉的价值或力量,建构了对神灵的信仰。一方面,灵魂不死的观念超越了肉体生命有限性的恐惧,使人面对无法逃避的死亡,也能“得到与超自然的势力证为一体的慰安”,其意义“乃在战胜为量极大的恐怖与为害极烈的恐惧”[2](P43),更何况人们将圣贤豪杰的灵魂“从灵魂群中选拔出来,用供物和牺牲来敬奉它们,当干旱威胁着他的庄稼的时候,就求它们降雨;当他出征时,就求它们保佑胜利;当他病时,就求它们医治”[3](P5),这就为有限性的主体力量找到了神性的支援;另一方面,万物有灵的观念化解了自然的冷漠与疏远,“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4](P220),人格化的自然神似乎以感性的方式直觉地揭示了主客体有着同构性,有着沟通的可能,这表达了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尊崇,也同时表现了人与自然的贴近,对主客体之间和谐的最初渴望。
此时人类自身与外部自然处于主客分化的边缘,在意识中没有精神的和物质的理性两分法和严格界限,主体自身的感觉、情感、想象与理性混沌交融,与外在世界的形象、属性也是交相渗透,可以说此时人类的主体与客体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都处于混沌的统一状态。
人类早期的神话、传说形象地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主客不分混沌统一的世界。由于对神灵的信仰使人类保持了对客体力量的敬畏和尊崇,由于努力提升自身主体地位、贴近自然、贴近神以求得主客统一的要求的合理性,由于人类最初的整体意识及自身的天真无邪,使文学呈现出红日初升般的光辉、璀璨与美丽:创世之神不论是上帝、神母还是盘古,都是一种“先天地生”的神圣性存在,是他们将自然的混沌化为秩序;各种英雄神话不论是西方的游历、冒险还是中国战胜自然灾害为群体利益而做的牺牲,都闪烁着人类自由、智慧、勇敢的光芒;至于死亡,不论是西方的来世、彼岸,还是中国的垂死化生,都表达着沟通幽明、超越有限、将生的意义传递下去的信念;不论是希腊神话中诸神与人间尘世利益的联系,还是埃及神话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有人性的动物神,都表现出人类对客体对象满怀感情的态度,传递出人类沟通主客体、克服主客对立的渴望和信心。这时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是神魔化的,有着想象中的神魔才具有的超自然的力量,充分体现了远古人类主体性的幻想提升:为人类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勇杀巨龙的卡德摩斯、炼石补天的女娲、偷息壤治洪水的鲧、各式各样的光明之神、保护之神、智慧之神、爱情之神、婚育之神……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这是一列光辉灿烂、缤纷神奇的形象长廊。
能以想象建立这样一种神灵信仰真是人类的幸运:人类借此克服了主客体之间力量相差悬殊造成的主体性迷茫及恐惧,减少了科学出现以前的许多困惑,建构了一种主观的也是合乎逻辑的世界模式,以完整的生命体验的方式将感觉、情感、想象、理性与非理性因素高度聚合,增强了主体的精神力量,有了生存发展下去的坚定立场和勇敢态度,这成为他们战胜有限、度过荒蛮、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支柱。
二、近代人类理性、科学的发展极大增强了与自然抗衡的力量,人类不断通过现实手段克服主客矛盾,战胜了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与迷茫,从而建立了对自身的信仰,文学进入人的自觉、人的主体性确立并大发展时期。
对神灵的信仰表面上似乎呈现出人类主体性的否定形式,而实际上,在那特定的发展阶段,人类是在幻想中努力提升着自己的主体地位。神人同形、半人半神的形象既是形象化的客体力量,同时也是与之相当的形象化的主体力量,人类在对无法控制的自然神力的尊崇中也深深隐藏着对自身的尊崇,虽然“这尊崇还比较含蓄,披上了神格的外衣,但已是文明力量和科学力量直接形式的前兆”[5](P275)。
经历了漫长的与自然抗争的艰难历程,人类在神灵信仰时期孕育着的文明力量和科学力量终于成为强大的现实力量。如果说神话时期的人类对世界万物的主观性解释还是主客不分的,是人类初期各种意识雏形相互交织的混沌体,是人类早期的宗教、哲学、道德、艺术及科学意识的总发端,那么,伴随着人对自然的斗争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挺进,伴随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及自然人化的不断发展,人类理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原先以为有某种神力作用的自然现象,现在可以用科学加以认识并控制了,原来对象是有规律的,认识了规律就可以把握对象,在对象面前成为主宰,这极大地鼓舞了人类的自信。此时,人类主体性的发展克服了对自然的恐惧与迷茫,彻底击退了对神灵、对外在力量的信仰,他们惊喜地发现真正伟大的是自己,并将对自然神力的崇拜转向了自己,人类建立了对自身的信仰,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社会与自然的主宰,并不断在战天斗地的现实斗争中创造新的神话——人自己的神话。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自己的神话真的建立起来了,而且其辉煌程度远超过了幻想中的神话世界:在现实中,认识和改造客体对象的结果和需要催生了越来越细致的科学学科,“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更成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6](P84),一部技术发展史就是人类生物器官不断延伸、物质手段日益丰富、精神自信日益增长的辉煌历史,是人的力量击退神灵力量的高歌猛进的历史:现代化大规模高科技的机械制造,比神话中能制造精美盔甲和初级机器人的万能的制造者火神赫淮斯托斯更具神力,今天的互联网比那个希腊神话中能飞速传播消息的信息女神俄萨更像信息之神,今天的宇宙飞船也会使那些插上翅膀飞上天空的神话不再是神话,现代的核武器当然也会使那个浸了冥河之水而刀枪不入的大英雄阿喀琉斯丧失神性……在神灵信仰时期人类幻想中崇拜的神力成为现实中人自己的实际力量了,自然不再有令人敬畏的独立的生命和意志,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进入现实性统一的进程。这种现实统一不同于神话时期的幻想统一,是以现实行动征服自然力为其实践手段、以现代的科学意识为其理性支持的。
在文学中,古代神灵信仰、神话传说中透露出的排斥死亡试图战胜有限性的虚幻主体性不见了,人类理性而勇敢地接受了必然一死的事实,承认人生的有限,承认主体力量的有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彼岸而是此岸,终极意义不在死后而在今生,肯定现世,肯定自身,要将有限的生命活出质量。文学中的形象由神魔化进入常人化,人的形象彻底取代了神、魔,成为作品的核心。当然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是人类将对神界、对上天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人间的过程,先是人间的“大人物”:帝王、圣贤、侠客、英雄、巨人,然后是普普通通的平常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活中的各色人等都在文学中获得了自己个性化存在的权利和地位,人类的一切感觉、情感、想象、体验和理解,一切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及悲欢离合的一切命运都在文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发挥。屈原的《离骚》与但丁的《神曲》都成为有代表性的文学符号,传达着热烈、忧伤、执著的对真理的追求;《十日谈》中的人物强烈地肯定追求着现世欲望的满足,《巨人传》中的人物更是以“为所欲为”的行为方式冲破一切精神奴役的时代巨人。唐传奇中的名妓、书生,“三言二拍”中的市井小民,《三国演义》及《水浒传》中的英雄们,以及司汤达、福楼拜、狄更斯、萨克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老舍、沈从文等艺术大师笔下的银行家、高利贷者、骗子、强盗、野心家、流浪汉、小市民、泼皮无赖、公务员、小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商人、车夫都成为被着力关注的主要角色。在这个时期,文学的主题就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及发展,个性原则成为文学创作及评论的重要原则,现实主义精神成为最有力量的文学精神。文学不断坚定人的这一信念:虽然主客矛盾依然存在,自然与社会的不如人意总是难免,但通过自己的主体奋斗会改变一切,所以鲁滨逊在荒岛上的征服、拉斯蒂涅在陌生化的大都市中的炎炎野心、于连们在充满阻力的社会环境中不懈的抗争、黛玉们为自己的情感和命运执著的痛苦都被充分肯定着,即使主人公的最后结局也许是悲剧,但人的主体性就在这抗争中成长。
人类对自身的信仰使其在神灵世界的支撑消失之后重又找到了精神上可以安顿之所,对自我的信赖使其达到了心理上的完满自足,保持了现实态度上的坚定,他们的前进义无返顾,坚信经过理性、科技、实践过程的发展,经过改造、创造、征服,人类一定会在现实世界建起自己永久的幸福安康。虽然此时人类将其主体地位绝对化已埋下危机的伏笔,但他们坚信只要自己足够坚定和努力,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三、现代人类将其主体地位绝对化,不断加剧着对自然客体的否定,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主客体关系的断裂,人类由主体性的片面扩张导致失落,走向新的迷茫,陷入信仰危机,这使现代主义文学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孤独、荒诞、绝望及荒凉,否定性成为文学的重要倾向。
由于在人的信仰时期,人类力争与自然之间主客体关系的统一是以科学意识为其理性支撑、以现实行动征服自然为其实践手段的,这其中就已隐藏着对自然客体的敌对态度。人类对自身信仰的发展使其将主体地位绝对化终于成为否定性的力量,毁掉了人类在漫长的艰难历程中建立起来的绝对自信。
当人类理性克服了神灵信仰时期的原始的蒙昧,明确地将主客体进行了二分,借助科学、实践确证了自身的伟大力量,他们踌躇满志地战天斗地,欢呼着在地球上建立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曾经引导人类战胜愚昧、追求真理的理性被胜利的喜悦蒙蔽了,这时他们将在自然面前的主体地位当作了主人的无上权威,从单一主体的霸主立场出发肆意掠夺、改造、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便逐渐演变成了割裂与对立。一方面,主体的欲望、自信、技术能力无限制地膨胀、发展,一方面,作为发展的结果和新的动机,人化自然的范围、人造物的种类和力量也无限扩大了。这时人类骇然发现,自然并未臣服于人类的统治,而是随时以其固有的法则无情地嘲弄、惩罚着人类,并以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威胁着人类的将来:人口爆炸,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核武器、生化武器的存在,新的疾病种类的出现……此时对人类长远未来的潜在威胁恰恰来自人类自身发展的片面性。人类发明发展了极其复杂且引以为骄傲的科技手段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欲望,但同时却使人类所依赖的人造物越来越多了,在一个技术统治的世界,人类一不留神便身不由己地陷入被动之中!机械文明中的科学化、专业化、工业化的片面发展及人类主体欲望的片面扩张终于成为强大的分割力量,造成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以及个体的人自身内部感觉、情感、想象与理性之间的分裂与对立!本来是一个整体的世界变得支离破碎了,人类主客体之间应保持的和谐统一遭到了破坏,人类终由主体性的极度膨胀扩张而导致失落,陷入新的恐惧与迷茫之中。这时的人类,经历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已经在理性上否定了神灵信仰,又对自身力量及行为的合理性产生了深重怀疑,对自身的信仰已难以为继,这种对客体与主体的双重否定,使其不可避免地落入信仰危机之中。
信仰危机令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派文学呈现出全面否定的倾向:人物失去了自身的坚定性和明确态度,人的主体性表现为无所皈依的迷茫和恐惧,文学中的人物既没有了神灵信仰时期的神性力量,也不再有人的信仰时期精神上的神圣性和完满自足,而成了物化的人、异化的人、扭曲化的人,在形式上成为人异化为非人的象征符号,传递着痛楚而无奈的孤独感、绝望感、异化感、荒诞感、死亡感……。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加缪《局外人》中的莫尔索承受着与世界不可沟通的孤独;在尤奈斯库的《椅子》中物与环境的力量令人窒息,无数的椅子令两个老人无立足之地,只有投海;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表现着绝望的企盼或企盼的绝望;奥尼尔《毛猿》中的扬克可以看作人类走进危机历程的象征:他健壮、有力、凶猛、好斗,代表人类前进的力量充分自我肯定,但在发展中丢掉了自我满足的状态,而陷入孤独,无所归属。对比一下是耐人寻味的:希腊神话中的火神赫淮斯托斯在埃特拉工场用银子制造了两个能行动的女孩为阿喀琉斯大将运送东西,在科学未得昌明之前这种机器人的幻想是浪漫而美丽的,人的主体性就在这幻想中成长;而历史发展到今天,在恰佩克的《万能机器人》中,高度发展的机械文明使现代人沦落为机器人,人类就要停止生育,似乎走到了末日;古希腊神话中代达罗斯为自己和儿子制造羽翼飞上天空逃离了弥诺斯王的迷宫,人类的足智多谋是诗意的、值得赞美;而今天,在著名的电子游戏“世界末日”中,高度智慧的人类为防备外来入侵者而巧设的迷宫却成为自己逃亡的障碍,惊恐万状的人类幸存者拼命追寻最后一枚尚还完好的火箭,以便飞往运行在遥远轨道上的宇宙空间站,希望有朝一日重新主宰地球,而食人怪物穷追不舍,将人类的落伍者异化为食人怪物的同类,深思恍惚的幽灵,痛苦万状的鬼魅,狂魔般的机器人……
感到痛苦与绝望的主体还是有心灵的主体,还是在信仰危机中不甘心危机的主体,而到了后现代那里,文学中的信仰危机不再呈现为主体的痛苦绝望,而是表现为“无信仰”或者说“反信仰”:所谓的填平深度、取消意义、平面化、无中心、怎么都可以……在这个信仰危机的时代,罗伯-葛利叶有句话广得认可:“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7](P313)。
四、结论:
从主客体关系角度考察文学中人类信仰的发展不难看出:在神灵信仰时期,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达到了高度聚合并保持了对自然客体应有的虔诚和敬畏;在对自身的信仰时期,人类过于推崇自身的理性力量,对自然的态度也逐渐演变为割裂与对立,在这个人类主体性大发展时期人的片面性也在暗中发展;现代派文学中普遍表现的信仰危机正是由于现代人类将其主体地位绝对化,不断加剧了对自然客体的否定,最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主客体关系的断裂所造成的。
主客体相分裂的倾向伴随着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尊崇逐渐增长,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文主义者阿诺德(M·Arnold)曾揭示的“我们所尊重的机械文明”和“使得人性成为特殊的尊严、财富和幸福的思想与感情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中国1923年爆发的“科玄论战”、英国人C.P.斯诺在1959年所总结的“斯诺命题”[8]、当代世界性的学术话题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从根本的意义上看无不是人类主客分裂意识的表现,这种分裂直接造成了信仰结构中价值因素同真理因素的分裂,是现代人类信仰危机的深刻的认识论根源。
后现代的“反信仰”并不是摆脱信仰危机的方式,有理性的人类是注定要追求意义的。走出信仰危机的正确选择在于价值与真理、意义与存在的统一。这里的真理或存在的真相是:就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言,人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再“战天斗地”也改变不了对自然界整体的依赖性和不可超越性;就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言,两者根本就是相对待而存在的,人类要刻意成为自然的主宰这种绝对主体中心的僭妄,既违反了存在的真相,又破坏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思想和实践方式。人类要追求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克服绝对主体立场,建立主客体关系立场。我们不仅要关注客体主体化,更要认可和尊重主体客体化,既不能把发展片面地定位于对客体的创造与征服,也不能脱离客体而孤立地追求主体的发展。只有在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双向互动的动态统一中,在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对象化、对象不断人化的双向建构和生成中使主客体的关系不断在新的更高的层面达到统一,人类才能永续性地不断走向新的更高阶段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