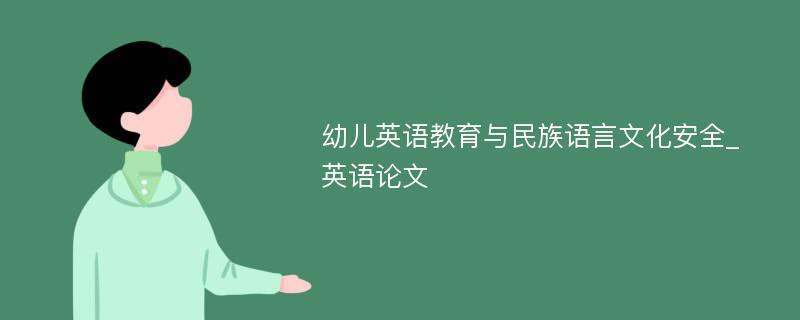
幼儿英语教育与国家语言文化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语教育论文,幼儿论文,语言论文,国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目前,中国的幼儿英语教育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形成了与小学、中学和大学英语教育相呼应的“幼儿英语热”。但是,在这不断升温的“幼儿英语热”中,教育界是否应该冷静而理智地思考一下:在幼儿教育阶段开设英语课程是否适当?这是否符合外语学习的教育规律?虽然已有不少论文声称在学前教育阶段开设英语课程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并具有诸多优势——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目前国内乃至国外针对此一论点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而这其中有不少是外语教育方面的专家和权威。事实上,世界外语教学界就幼儿英语教育的合理性问题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而国内幼儿教育界将此远未达成共识的教育问题匆促付诸实施并盲目跟风,是否显得过分草率和不尊重教育规律?是否会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这些都是值得当前教育界人士深思的问题。
二、幼儿英语教育与国家语言文化安全
(一)幼儿英语教育与国家母语安全
幼儿英语教育会加剧当前国家母语安全危机。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卷》母语也称为第一语言,它是一个人所属民族的民族语言。母语不仅仅是语言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和范畴,它还走进了社会学视野,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母语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构成要素之一,它是民族的重要标志和象征,母语在国际、国内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直接关涉到该民族的文化独立和文化安全。然而,当前国内的语言教育状况导致母语产生安全危机。所谓母语安全,指的是社会母语(社会母语是与外语相对应的,它是整个社会对外交流的语言,因此它必然是也只能是这个民族的标准语——民族共同语)的安全,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中之一便是社会母语的地位是否能得到保障。而当第二语言(外语)超越了母语的位置,就会产生母语安全问题。在当下的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和社会对于英语的过分强调,并通过成熟完善的体制化(如教育)和非体制化(如考试)的方式具现和突出其优势地位,以此日益强化着受教育者和国民的外语意识;于是,在官方许可和民族认同的共同合力作用之下,“外语热”在我国不断升温,英语在我国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已处处显示出其强势语言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与“外语热”和外语的强势语言身份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作为母语的汉语陷入“汉语冷”的尴尬境地及其弱势语言地位。从国民教育体系中英、汉语言课程设置的比重、时长对比,各种与应试者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考试中英、汉语话语权力的大小和重要性的不同(如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学位考试,职称考试,各种就业招聘考试等等),非英语专业教学中对于全英语教学模式的推崇和原版英语教材的大量引进和使用,教学方法上对于“洗脑式”教学方法的提倡和运用,社会对于英语知识和能力近乎完美的重视和追求而对于受教育者汉语水平低下的无动于衷和不以为然,以及目前我国全民母语水平日趋下降的现实状况,我们不难判定,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已超越了作为第一语言的汉语,中国的母语安全问题已经凸现。
而在此背景下的幼儿英语教育无疑会进一步加重当前国家母语安全危机的现状。第一,众所周知,幼儿阶段是幼儿语言习得及语言能力形成的关键阶段,同时也是幼儿语言学习的黄金时期。一些教育工作者正是认识到这一年龄阶段对于受教育者语言学习的有利时机和条件,因此将外语教育引入到幼儿语言学习中。其主观愿望无疑是美好的:及早、快速提高幼儿的英语水平,并为其今后的外语学习打下牢实基础。但是这种英、汉交互式的双语教育模式,无疑会对幼儿的母语习得带来负面影响。在幼儿教育阶段,幼儿的语言经验还比较缺乏,其思维方式和语言感觉尚处于起步和塑型阶段,语言辨别能力不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同步学习,势必会造成不同语言在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等方西的交互干扰,并最终导致两种语言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效果大大下降。而对于幼儿母语学习而言,由于第二语言内容对于母语的负面干扰,幼儿的母语水平和能力下降,而这一阶段又处于受教育者语言习得的关键时期,因此幼儿在此阶段获得的母语知识、语言经验、语言能力及思维习惯等都会根深蒂固、难以矫正,并从此影响他们一生的母语水平。因此,在幼儿教育阶段,相对于单一的母语语言教育模式而言,双语的语言教育模式更易引发并加重母语安全危机。第二,幼儿英语教育会强化幼儿的第二语言认同感,但同时却会加深其对母语的疏离感,并由此而为将来的母语安全埋下隐患。幼儿英语教育本身就是外语教育非理性化的产物,提倡者只从单纯的有利于语言学习的角度出发推行幼儿英语教育,而对有可能造成第二语言对第一语言的排挤则视而不见或认识不足。从表面看,在幼儿英语教育中,母语与外语似乎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整个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中国民对于外语和母语所持的鲜明“亲—疏”态度模式必然会对缺乏辨识能力和文化立场的幼儿通过外语教育形成同化影响,并进入其意识深层而成为集体无意识。由于这种语言态度模式过早在幼儿的潜意识中积淀、定型,母语便难以在幼儿的心理认知和文化认同中奠定主体地位,母语在工具和文化的重要性上被第二语言遮蔽,这样,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形成盲目的外语崇拜意识而不自知,而母语安全危机也会随之更加严重。
幼儿英语教育在当前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在倡导者的潜意识里存在着这样的理论预设:外语学习越低龄化越好,因为这样可以摆脱母语的干扰,从而学到标准、纯正的外语。外语在中国属于第二语言,而根据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第二语言的学习是在第一语言(即母语)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主要依靠的是一种“迁移”的方法。“所谓‘迁移’,是说学习者已经把第一语言与自己的思维和经验联系在一起了,掌握第二语言只需要把第一语言的意义迁移到第二语言的形式上”。这样,第二语言的学习便与第一语言的习得紧密相关,而且“学习第二语言的水准和质量是与第一语言运用能力成正比的。”因此,要真正学好第二语言,还必须首先学好第一语言;第一语言非但不是第二语言学习的妨碍和干扰,而且还是学好第二语言的必要基础和有力保障,真正对第二语言学习形成干扰和“负迁移”的是水平和能力低下的第一语言习得。而在幼儿教育阶段,儿童的母语学习尚处于起步阶段,其语言知识、语言经验比较缺乏,语言能力、认知能力比较薄弱,其语言综合素质和整体水平不高,而在此基础上的第二语言学习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因此,要真正提高全民族的外语水平,在幼儿教育阶段应切实搞好的是第一语言教育,而不是外语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学习者未来的英语学习打下扎实的第一语言基础,否则最终既会贻误学习者第一语言习得与提高的有利时机,又会使受教育者的英语水平无法真正实现提高。
(二)幼儿英语教育与国家文化安全
幼儿英语教育会加深当下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由于上个世纪“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文化运动对民族传统文化一次次地否定和打倒,以及西方文化借“全球化”之机在中国扩张蔓延,再加之文化接受主体在面对本土与异域两种文化时截然不同的亲疏态度,结果造成本土文化传统的严重断裂和西方文化的肆意横流,并最终引发中国文化的安全危机。当前中国文化安全危机的实质是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所谓文化认同危机,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成员不再真正了解自己的传统,不再真正为自己的民族性感到自豪,不再真正信仰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转而信仰、认同和推崇他种文化(往往是某种外来强势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在当前中、西文化大交汇的文化语境下,由于在许多场合和领域中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在场或话语声音微弱,而强势的西方文化的渗透却无处不在并在众多文化活动中扮演着权威的角色,掌控着话语权力,再加之文化成员自身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严重缺失,于是国人便自然而然地对西方文化予以认可并接纳,承认其文化霸权;更为严重的是,在长期的西方文化接触与接纳过程中,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抗体的缺乏,国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意识逐渐被西方文化所统辖和置换,并最终形成认同西方文化,漠视甚至拒斥本土文化的文化取向。例如,社会上普遍存在、并愈演愈烈的崇“洋”、尚“洋”之风——追逐洋明星,迷恋洋商品,以购买和消费洋货为荣,以过洋节为时髦、时尚——则是国人西方文化认同心理的具体文化表征;而另一方面,则是国人民族文化认同的逐渐式微:对国产商品的鄙夷不屑,对传统节日的淡漠失忆,对传统文化的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在科技、学术等领域则普泛存在着以西方的标准和模式为参照系来衡量、评判中国科技、学术的文化成规和集体无意识。
幼儿英语教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教育,同时它还是一种文化教育: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具体体现,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世界观等都深蕴于语言符号的能指之中。因此,幼儿学习一门外语,同时就是接受一种异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两者是二而一的东西。但是,在习得一门外语时,如果学习者不能坚定地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则极易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和殖民,并对本民族的文化安全带来极大危害:“长期学习一种外语,尤其是一种时时处处都展示为强势的他国语言,不仅可能会让年轻人的母语水平下降,而且会让他们的思维习惯和世界观都发生根本变化,会让他们不由自主地倾心于某种外国文化。而在当今快节奏、多变化的生活方式中,他们很可能在对自身文化根本不了解或没时间了解,在不会比较也不想比较的情况下,就被外国文化‘俘虏’。这种精神上的被‘俘虏’并不一定指精神道德的衰退或下降,而是指一种与狭隘民族主义反向,但却相似的偏激、固执和忘本。学习他人本来是为了改良自身,但如果其结果是改掉了自己的身份和盲目崇拜他人,就会出现对外交流与革新自我之间的‘恶性互动’,并可能进而成为一种对中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社会群体或思想力量。”
在学前教育阶段,幼儿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体认尚未成型,自身民族的文化身份尚未在其意识中确立,更勿论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过早引入强势的西方文化势必会影响他们对自身文化的了解与认同,并在整个社会对西方文化盲目认同与追随的现实语境和氛围下,最终加剧和加快整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疏离和消解;同时,由于受教育者接触西方文化的时间提前,相应地在其一生中西方文化影响的时间就会延长,这无疑就会使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和牢不可撼,而自身民族文化则因话语声音的微弱而极有可能由文化的中心地位被排挤到边缘,并居于次要地位,从而在文化生活中沦为西方文化的注脚与附庸并最终丧失话语权力。
从文化深层的角度来看,幼儿英语教育会与后续英语教育和目前中国文化失语的社会文化语境一起,影响受教育者个体传统文化基因的形成,并最终引发基因性的文化灾难。文化基因不同于生物基因,后者具有一种先天生成性,即在生命个体诞生之时即已成形、铸就,它主要与生物因素、自然环境相关;而文化基因是后天生成的,基因的编码、排序、组合等主要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它直接决定文化的表现形态——不同的文化基因产生不同的民族文化,文化基因伴随着文化个体的逐渐社会化而渐渐成型,而社会化的早期是个体的文化基因形成的关键期。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文化基因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渠道,教育的内容决定着受教育者个体文化基因的具体文化样态,并由此而决定着个体的文化取向和文化行为表征。因此,综而言之,包括幼儿教育在内的早期教育对社会个体的内在文化基因和外在文化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在幼儿教育阶段引入英语教育,由于当前中国文化严重失语的现状,以及中国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西方文化恶性膨胀,中国文化急剧萎缩),这种畸形的文化现象势必会通过英语教育给幼儿在文化基因的形成上带来不利影响:一方面,西方文化很容易直接侵入或强行嵌入中国文化的基因序列中,并对中国文化基因形成大面积的更替、置换;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容易对正在成型中的中国文化基因产生影响,使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异,并与中国文化形成本质的差异。由于这些影响发生在文化个体的文化基因形成的关键期(幼儿阶段),它改变了中国文化基因的结构与内核,因此,相对于文化基因成型期(成人阶段)的西方文化影响而言,它无疑会对文化个体的文化态度和取向产生更为根本性的制导作用。而这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发生文化基因畸变的文化个体,在深层的文化心理和表层的文化行为上,则势必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文化认同危机,并最终给国家文化安全带来危机。这种由于英语教育的低龄化扩展和延伸而引发的基因性文化危机对于民族文化的命运是灾难性的:因为这种由变异的文化基因控制的非常态、非理性文化态度模式会自动生成且难以矫治,而且往往都会演化成为一种固执的文化思维模式和深层的集体无意识。
幼儿英语教育项目的开启无疑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在我国西方语言文化教育已经实现了对受教育者个体整个学校教育阶段的“无缝”覆盖。它同时也标志着西方文化已从民族文化之根上开始对中国文化的渗透、改造与置换。它意味着西方文化已通过合法化的教育渠道和体制化的方式进一步牢牢掌控了国人的思想文化意识,并更进一步在当前中国文化教育软弱无力的背景和形势下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
三、结语
幼儿阶段是社会个体一生教育的起始阶段,儿童的语言之根、文化之根在此阶段已开始植下。而幼儿英语教育项目的启动无疑是对植根不深、扎根不稳的儿童民族文化认知和文化体验的巨大冲击,由于它是从文化和教育的本源和根本上对民族文化的撼动和熏染,因此其影响必然是重大而深远的;而且,由于它是在中国文化生态已严重恶化并发生安全危机的背景下生发的,因此幼儿英语教育无疑会进一步深化和加剧国家语言文化安全危机。
综而言之,笔者认为,在幼儿教育阶段,语言文化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幼儿对民族语言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增强其对自身语言文化的热爱之情,从而初步建构其民族文化身份,铸造其文化主体意识,并形成初步的文化认同,为将来后续教育中民族文化认同的进一步强化打下坚实基础。而从国家语言文化安全的角度着眼,从真正有利于外语学习的角度出发,在幼儿教育阶段则不宜推广和施行英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