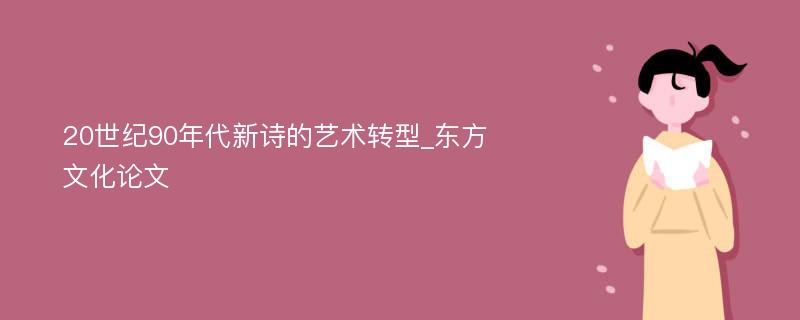
九十年代新诗的艺术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诗歌经过一番蓬蓬勃勃的发展,为新诗史涂上浓浓的一笔之后,八十年代末进入了它的低潮期。于是许多人发出了一些感叹,认为新诗将走向衰亡。个别好心人并未对这一现象进行准确分析,只根据民间诗社的活跃和新诗集出版的增多,又盲目乐观地说,新诗正走向辉煌。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妥当的。都未能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都是从个人的好恶和单纯的意愿出发得出的结论。我认为,由于政治因素的制约、经济大潮的冲击和通俗文化的排斥,新诗和其它纯文学品种一样都受到很大影响,失去了一些阵地,但是,它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如野火烧不尽的青草一样,仍在茁壮地成长。不论是所谓的公开诗坛,还是所谓的地下诗坛,都有好作品产生,只是它的形态、艺术方法及风格都产生了一些变异,也即是说,正经历着又一次艺术转型。当然,它也并不是走向辉煌。因为它真正的繁荣并未到来。它只是处在一种痛苦而又自慰的蜕变过程中。下面,对其艺术转型的几个特点略作评析。
智性思维的扩展
诗是情感的产物,新时期初期和中期的诗歌确实曾以其热烈喷发的激情感染世人,相对说来,智性思维的内涵比较薄弱。或者只在部分诗人的作品中有所体现。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在许多诗人的作品中,智性思维的花朵都越开越盛,似乎成了一种较明显的趋势。当然这种智性思维并非排斥感情,而是从感情出发或把感情升华后的提炼和结晶,正如桑塔雅纳所说:“诗的思维的指导原则往往是情绪或感受。”诗中的理性成分应和激情成分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见《诗歌的基础和使命》载《西方现代诗论》第10页)。但是二者并非相等。九十年代许多诗人的作品,其理性思索是显著增多了,带给读者对社会人生更多的哲理思考。如老诗人牛汉《梦游》的第一稿,虽写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但九十年代才经过审订后正式发表,他借一个梦游患者梦游的经历,不仅写自己对光明——漆黑的夜中“那一束雪白的亮光”的向往,而且深刻地揭示了那颠倒黑白的年代对人性的摧残,诗人以梦游者清醒的口吻写道:“二三十年来/我顽强的身上/留下了一块块乌黑的伤疤/它们都是在阳光之下/受到的重创/而在这漆黑的夜间梦游/没有摔伤过一回/即使摔倒在地上/也不会感到一点疼痛”。这近似偈语式的剖露心迹,使人深深思考动乱年代极左路线对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另一老诗人李瑛,多年来总是唱着激扬而火热的歌,有了复杂的人生经历进入到老年之后,其诗作中的智性思维有了更多的展露,他的新作《生命是一片叶子》可说是智性思维的艺术结晶。如《蝴蝶标本》通过做成标本的蝴蝶阐释生命的意义:“对这个美丽的世界/再不能创造,也不能欣赏/它已经不会知道/伙伴们以及/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树枝和草叶/都在寻找它/比一片飘落的叶子还轻/因为它已失去了生命/也许只有在这时/它才更深地理解生活”。不经过人世沧桑的诗人,是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喟的。此外,李瑛还在《寄居蟹》中通过蟹的口吻揭示了斗争哲学的内涵:“在充满掠夺的世界/称呼虾或者蟹并不重要/我只想用身体/向你诠释一个定义/屈辱地活着并不难/正直地活着却不易/单靠躲避不够/必须准备自己的钳子//是的,有什么比这只巨大的钳子更重要/生活就是这样残酷与率直”。这种以阐释哲理为主,体现明确的是非判断的诗,在李瑛过去的作品中是较少见的。艾青说:“诗人只有丰富的感觉力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丰富的思考力,概括力,想象力。”(《诗论·思想》)这丰富的思考力和概括力,正是创造智性思维花朵的动力。
但智性思维的表现形态却是不同的。如上述的牛汉、李瑛的诗作,多从具体形象的感受生发出哲理的判断,直接袒露胸怀,为世人提供某些警策之思。也有的只是展示现实中不曾有的意象或在常规下难以互相衔接的意象,使读者去体味那独到的哲思。如老诗人安谧的《可以走了》和《鸟》。先看前者:“能听针落/于惊雷吗?/能观日出/于日落吗?/好,可以走了。”于惊雷鸣天之际可以镇静地听到银针落地,于日落西山的黄昏时刻而乐观地看到明天的日出,这要何等的胸怀与气度!这只有经过人生的许多苦难和狂风暴雨后有了顿悟的人才能办到。而此刻的他才算真正成熟并懂得了人生,即便叫他离开人世而去,他也心中无憾了。此诗蕴藏的人生哲理是非常丰厚的。再看后者:“树上十只鸟,/击落了一只。/其余的仍/眨眼于枝头。/沉静/完好如初。”诗人以平静的语调描绘了一副生活中的“反常”画面,十只鸟被击落了一只,其余却未被惊散,反而麻木地在枝头眨眼,似乎悲剧并未发生。这平静中含着诗人心中巨大的风暴,也包孕着人生的深刻哲理:麻木的人只要危险不降临自己头顶,仍然苟活于世。同样的还有女诗人王尔碑的《猫头鹰的眼睛》:“你在审视我吗/审视我的灵魂吗/宇宙间只有你了/一个森林女王傲岸地睡了/你是站着做梦的/你的眼睛是两颗星儿/一颗,望着白昼里的阴影/一颗,望着阴影后面的太阳”。前二句是对猫头鹰的设问,以自己头脑的简单去衬托猫头鹰观察事物的深邃和深刻;后面两节则是通过对清醒的猫头鹰眼睛的咏赞,含蓄地昭示出某种哲思,颇耐人思索。
也有的以语言的机智与巧妙地联结,造成某种精巧与幽默的语言氛围,从而揭示哲思。如中年诗人桑恒昌的《寺庙所见》与《打蚊子》。前者云:“敲穿几代木鱼/未见醒来一个菩萨/既然已经灵魂了/何必再血肉”,内里隐现着对某种高尚精神的肯定与对世俗观念的否定;后者云:“一掌/把蚊子/浮雕在墙上/正法之后/用我的血/写它的罪恶”。此诗让我们想起韩瀚写张志新的《头颅》,二者都是用极短小的语句包含丰富的社会内涵。《打蚊子》不但用语巧妙,而且含着深刻的哲理。消灭罪恶,伸张正义,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与此对映成趣的是,老诗人孔林的《滴水集》,却又是以优美、简炼的语言去阐发人生的哲理。如其中的几首:“切莫感叹日月之轮摇得白发苍颜/看西山枫树一片/霜天下高擎火焰”(《意志》);“我是用我的思维掩埋白昼和夜晚/尽管花季已过/根不会沉默”(《思维》);“时光匆匆岁月匆匆人如顺水而流的小舟/生活是一首远歌/莫让它落入浅滩”(《岁月》)。这些清新隽永的三行小诗,也给人以多重的思考。
在一些青年诗人的作品中,哲理性的思维原本就有很大潜力。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他们更着意向人们揭示其对人生的思考,有的甚至带有一点寓言的特点。如青年诗人谭延桐的一首《鞭子与陀螺》:“陀螺对鞭子教练说/我好好转就是了/鞭子什么也不说/鞭子好威严/看不出瘦瘦的身影竟裹着无边的火/陀螺很卖力气地转/不是怕火烧疼了自己的血/是怕一旦停下,便再也站不住脚/是的,转给自己看/对得起自己,不能白白地活/鞭子感动过牛羊,也感动过烈马/有不少英雄传说/鞭子老了/老了的鞭子在梦着顶呱呱的来者/来者呢/地球是陀螺,生命也是陀螺”。这俨然是奴隶主与奴隶、大人物与小物鲜明的对比画面。作者在平静地叙述中表示了对被奴役者的同情和对奴役者狂妄野心的嘲讽。内涵比较丰厚。其它如郝永勃的《渴望真实》,谷未黄的《野狼群》,蔡嘉彬的《豹》,高柳的《鱼的正剧》都含有作者自悟后的生活体验,给人留下思索的空间。
这种智性思维扩展的趋势,出现并非偶然。火山喷发后必有一段沉默,激情发泄后也有静静的思索。诗坛在八十年代的一番热烈的呐咸和喧闹的争论后,也必然进入一个思考的时期,诗人们逐渐开发自己的智性思维,也就顺理成章了。
东方文化因子的强化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台湾新诗曾经历过向西方现代诗移植而又回归东方文化的过程,其中有经验也有很大教训。七、八十年代以来,大陆诗坛也曾兴起一股向西方现代诗学习的热潮,朦胧诗派,新生代诗群走在前列。其中当然也吸收了不少有益的营养,引起新诗在审美观念,艺术方法诸方面的深刻变革。但是,由于某些人的盲目照搬或单纯模仿,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从而使新诗和广大读者逐渐疏离。随着新古典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艺术主张的传播,更主要地是由于社会的大动荡后引起的社会反思,许多诗人便主动地在自己的作品中使东方文化的因子更加强化。但是,这并非是向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正如艾略特所说:“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的或胆怯的墨守前一代成功的地方,(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的了。”(《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有心的诗人在经过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后,发现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中竟然有那么多值得借鉴的优秀成分,他们或者化用,或者翻新,从而使作品染上了浓浓的东方文化色彩。
这种对东方文化因子强化的现象,情况又各有不同。有的是把东方文化精神作为作品的灵魂或内核,从而展示出一种东方文化的神韵。如“东方神秘主义”的倡导者山水诗人孔孚,他主要是把禅道精神纳入自己的作品,追求和大自然契合无间的境界,使作品显得更为空灵和飘逸。他写峨嵋山水和帕米尔高原的诗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如他写戈壁落日的几首小诗:“一颗心/燃尽”(《戈壁落日》),原文为“很辉煌/又有些悒郁/一“颗心/燃尽”,《诗刊》96年5月号发表时删改);“两个火人都老了/笑笑分手”(《大漠落日》之一);“一颗躁动的灵魂/去也拥抱着波浪/美到/死”(《大漠落日》之二);“天地/将合/沙夜哭”(《大漠落日》之三);“圆/寂”(《大漠落日》之四)。这一组精巧短小的大漠落日诗,却有内在的深厚的力度,不仅保留了诗人以往的忧患意识和生命感,而且把一种道家无极的宇宙观及佛家的超脱尘世的静谧境界纳入诗中,也可说是儒道佛的一种有机结合。
也有的诗人在追寻本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的壮阔背景,又带有强烈的文化寻根色彩。如朝鲜族青年诗人南永前,从远古神话中探求本民族的诞生及繁衍的历史,张扬一种民族自豪感,达到了力度和审美的某种结合。在朝鲜民族的远古神话中,把自己归结为是熊女和天神在檀树下结合后诞生的民族,故而把熊女视为始祖母。作者在《熊》一诗中便赞颂这位祖先:“蹀躞于葛藤缠绕浑沌之莽林/蹀躞于水草森森蛮荒之黑沼/悠悠岁月经蹀躞/闭锁于寂寥之树穴/尝尽野艾之苦涩辛酸/咀嚼山椒之断肠裂胆/以星为眼/以月为腮/以甘露为血液/化为芙蓉娇娇之熊女/世间精灵之始祖母”。这首诗初稿写于1987年,但于九十年代选入诗集出版,标志著作者对古老民族文化的追寻。他九十年AI写作的诗仍沿袭了这一走向。而彝族诗人吉狄马加,不仅写古代彝族祖先对龙的图腾崇拜,也写了彝人对民族狩猎生活的向往。如《鹰爪杯》,诗人先在题记中说:“不知什么时候,那只鹰死了,彝人用它的脚爪,做起了酒杯。”接着便展开了诗的联想:“把你放在唇边/我嗅到了鹰的血腥/我感到了鹰的呼吸/把你放在耳边/我听到了风的声响/我听到了云的歌唱/把你放在枕边/我梦见了自由的天空/我梦见了飞翔的翅膀”。作者实际上写了鹰之魂,也即是彝族人民飞翔的灵魂。对鹰的崇拜也体现在满族诗人的诗中,刘德昌的《鹰星》,杨子忱的《鹰》,都是通过对鹰的咏赞,张扬一种民族精神。如杨子忱《鹰》中的句子:“鹰神/给予了我们/如此神勇/我们还山河/无尽灵魂/在同一天地间/穿行”,人即是鹰,鹰即是人,他们共同拥抱着大自然。
这种东方文化因子,还体现在某些诗人对题材的选择和意象的运用上。如女诗人王尔碑写罗汉和观音的诗,即是从带有东方韵味儿的素材中提炼成篇的。且看写普陀山“沉思罗汉”的小诗:“古寺的风铃重复着音乐的童年/诸神睡了乘暮色归家去了/你坐着,坐在马可波罗的船上/穿过重重雾峡重重风浪/潮声,起伏着不可名状的祈祷。”真是一派恬静的佛地风光,连起伏的波涛似乎都入禅了。青年女诗人路也的诗具有浓郁的现代意识,但是她却能把许多富于东方情调的意象入诗,造成一种东方文化氛围。如《梦游者的春天》,本是写离别后的愁绪的诗,她却从古诗词中找到了自己的灵感:“我就是那个比黄花还瘦的女子/在这个春天转世/吟了海棠,咏了柳絮/却找不到一个词牌来写爱情/女人们代代相传的遗产/像病菌一样在血里涌动”。从思想上说,是对传统中的封建意识的背叛,艺术上则又吸取了古诗词中的典故而构成新的意象。
这种带有东方文化色彩的运用,在一些吟咏古迹名胜的纪游诗和山水诗中就更突出了。孔孚、晏明、苗得雨、刘章等老诗人都在这方面做出了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以“反文化”或“消解文化”为旗帜的新生代诗人或稍后一点的校园诗人,也有些作品开始向东方文化靠拢,或以之为素材直接吟咏,或以之为引子借题发挥。如叶舟的《大敦煌》组诗,陈超的《博物馆和火焰》、阿坚的《眺玉泉山》(涉及到清帝乾隆),程维的《听琵琶古曲:十面埋伏》,袁勇的《屈原赋》等,都开始与东方的古老文化接轨。程维的《听琵琶古曲:十面埋伏》,便以听古曲为由,把楚汉相争的悲怆历史、项羽和虞姬的悲剧命运概括点出,并展示出古典音乐给自己的心灵感受,颇有味道,看其前面的一节:“一只手/制造十面埋伏的紧张气氛/一阵紧似一阵的音乐/如百万雄兵/把项羽和天下最美的女人围在核心/手挥琵琶。挑起:楚汉相争/弦是长枪/指是刀剑/弦和指相碰。有画戟/方天”。比起老年中年诗人此类的作品,语言比较通畅和口语化,叙述的语调代替了繁富的意象营造。虽然仍保持了新生代诗人或后期校园诗的风格特点,但是内里的东方文化因子却得到了强化和展现。
走向呈现与隐现的艺术手段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新诗大多是以纯现实主义的再现客观世界和纯浪漫主义的强烈地表现自我内心世界展示在诗坛上的。此外,还有一股象征主义的艺术潮流,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新颖之作,但它只是处在从属地位,由于历史的原因,并未造成更大的影响。新时期以来,各种艺术方法纷呈,不但传统的艺术方法(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产生了变异,而且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常采用的方法逐渐扩大了领地。当然,由于古老传统文化强大的影响所造成的中西文化少有的强力碰撞,大多数诗人并不盲目照搬套用西方的艺术手段,而是用东方文化之火去熔解它,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方法。这就是由再现和表现走向呈现和隐现。爱尔兰诗人叶芝在《象征主义》一文中曾谈到诗人风格变化的内在原因,可为我们的佐证:“随着这种本质变化,也就是重新回到想像,我们会理解到唯有艺术规律——也就是世界的内在规律——才能够支配想像,产生风格上的变化”。(《西方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九十年代新诗在艺术手段和诗人风格上的变化,也是诗的内在艺术规律作用的结果。因为诗歌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诗人美学观念的更新而逐渐嬗变的。
所谓呈现,既不是对现实生活做直接的外在描绘,也不是诗人直抒胸臆式地放怀高歌,而是诗人把内在的思想感情或某种情绪、感觉溶入客体物象中,从而形成某种意象和象征,又隐约透出诗人的一丝情怀,给人以较多的品味和遐想。这其中已接受了一些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但又不扑朔迷离、使人难以理解。如老诗人郑敏的近作《外面秋雨下湿了黑夜》,是一首和孩子离别时写的诗:“外面秋雨下湿了黑夜/你不再听见落叶叩阶/雨,天上的、人间的,一样压抑/悲痛只能小声低语/隔着淡棕色的地板,相遇/我们各在长室的一隅/隔着的是波涛狂潮/海洋的一岸,我看着你低沉的眉毛/命运只给若干假期/停车场上两辆,暂时相依/相近又相远,在街的另一端/孩子,你已走出母亲的路灯”。这是诗的前几节。老诗人并未直接倾诉离别之痛,也未着力描绘外部世界的具象,而是把内心的隐痛溶入秋雨、黑夜、落叶、隔海的波涛等带感情色彩的意象中。另一老诗人昌耀的近作《享受鹰翔时的快感》虽有更多的主观感情的披露,但也并非直抒胸臆,而且带有某种神秘性和超现实性,也属于呈现的范畴:“痛快的时刻,一个烤焦的影子/从自己的衣饰脱身翱翔空际。/我,经常干着这样的把戏,/巧妙地沿着林海穿梭飞行。/奇怪,每一株树冠顶端必置放一只花盆。/我感觉自己是一只蹲伏在花盆的影。/我不想为自己的变形狡辩:这是瞬间逃亡。/永远的逃亡会加倍痛快,而这纯属猜想。/须知既已永远而去谁又曾回来复述其乐?/只有这一次我听到晨报登载一条惊人消息/说是昨夜人们看到诗人只身翱翔在南疆天宇。/我怀着一个坏孩子的快乐佯装什么也不曾得知。”这自然是诗人灵魂出窍时的想入非非,但也采用了非传统的艺术手段写了自己想象中的心灵感应。
诗人采取呈现的艺术手段打开其艺术世界时,可以是对实有的景物和自然现象的自由联想,注情入内。也可以是对虚幻的景物和自然现象生发奇特的心理感受,创造出一种超现实的景观。前者如老诗人塞风的“向日葵”:“对于向日葵的诱惑/只有太阳/它即或站在雨中/也在寻找那个方向/火苗状的金环/是爱情的开放/如果不背过身去/它永远鲜活光亮/。这虽然仍是咏物,但其思想和感情的内涵却丰富多了。韩作荣的《黎明的船》,在恬静中展现出诗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船泊在水里/背水的船靠着船/黑的水痕区分真实与虚伪/灰的水彩淋漓/浸染水的深奥,初晨的薄光/年轻的烟缕颤动/于水中嵌满褶皱/蜷缩的帆,直立的桅半寐半醒/和自己的影子抗衡/只有礁石沉静于空间和水/沉稳,坚硬/而灰暗掩饰不住的一抹葱绿/亮在水湄/用草叶支撑黎明”。诗人观察自然现象很细腻,并把一种内在的生命感揭示出来了。后者如叶延滨的《凝视》:“当天鹅凝视着我的时候/那托起天鹅的一池碧水如我的心/宁静的世界谁也没有发出声音/只有悄悄从我足下发出的根须伸入土地/让我变成一棵树/不用再说话/当母狮侧头凝视我的时候/我屏住呼吸变成一块石碑/石碑不用说话/因为上面刻着我的最后一首诗/那诗会让每个人沉默——死得高贵多么幸福/当金鱼瞪大眼睛望着我的时候/我也傻傻地成为哲学家/是鱼儿在鱼缸里得到自由呢/还是失去自由才有鱼缸的鱼?/鱼儿不说话我也不说话/谁先说话,谁才真傻/傻子就是诗人啊/你知道吗?当你望着我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是天鹅,是母狮,还是金鱼……”这当然不是诗人的一篇自我宣言,而是揭示诗人在奇特的联想中人和自然和社会的某种微妙关系。诗中的物象是虚幻的、超现实的,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隐现是一种更为神秘和充满象征意味的艺术手段。孔孚提出的东方神秘主义的诗学主张其核心就是隐现,所说“神龙见首不见尾”,“远龙”是也。其中既有东方哲学的玄秘色彩,也有西方哲学的超现实性表现。孔孚、安谧、昌耀的一些诗,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我们再以几位诗人的诗作为例。如晨声的长诗《大林莽》,他用怪诞的意象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神秘性很强。他力图写个人的迷失到寻找自我然而更加迷失的心灵历程,象征种种矛盾对人的精神的挤压。如诗的第二节:“一条蛇/穿过秦砖汉瓦/在瘾足鸦片饱尝弹药之后/拖着长长的响尾缱绻而至/……眨眼间/被阴森森的蟒腹吞没/停/止/空间被覆盖禁锢/死神用冷幽幽的舌尖/刺探耳膜/一声声怪叫撕肝裂胆/令所有的神经末梢悚然倒竖/每一棵树都长着阴谋/每条根系都拥有一片腐土/所有的路都布满迷失/抵触的目光/一一成为方向的囚徒”。这似乎写的是森林,又不是森林;是中国的近代史,又并非实写。诗行充满神秘性和象征性,作者的主观感情均隐藏于怪异的意象之后,这和通常写林莽的诗不大一样。同样,隐现的艺术手段在一些短章中也常见到,王燕生的组诗《散淡的闲云》可谓佳作。如其中的《穿越》:“风的疼痛/夹在两片落叶间/风未找到归路/树已穿越了风/那些迷失的花朵/瞬间/便进了鸟声”。诗人把人的某些感觉赋予了风、落叶、树、花朵和鸟声中,并有通感手法的插入。诗人以一种超现实的艺术触觉使自然界的物象变形。又如《古寺》:“古寺的年轮/一声声/被木鱼刻进深山/松充满禅意/柏己入定/墙上栖满斑蝶/老去的鸟儿/不舍昼夜/啄食沙弥额顶的香火”。这首诗神秘性更强。亦运用了通感。这充满禅意的古寺正是诗人心智的外在的体现。诗人的主观感情隐而不显,只从特定的意象中暗暗透出。另一诗人孙国章的组诗《痴情痴语》,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没有风的日子》:“树不说话/叶子低垂/蝉声/很冷/孤独/蛇一样行走”。诗人也运用了通感手法。但是其主体情志还是没有直接倾泄出来,而是从诗人展示的客体物象中隐现出来。这正符合东方神秘主义创作主旨。
九十年代这几种新诗艺术转型的特点,只是从部分诗人的作品中概括出来的,并不能代表诗坛的全貌,如有的中老年诗人仍坚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作,同样有佳作出现;有的青年诗人仍在做着创作先锋诗的实验,积累着他们的创作经验,今后也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但是,本文所探索的新诗在三方面的艺术转型特点,还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它为诗坛带来新的气息,预示着新诗未来的更加多元化和走向繁荣,正如老诗人苏金伞在一首诗中写的:
二十一世纪
新诗将从幽谷中
走上新的境地
二十一世纪也许
能成为诗的世纪
96.9写于山东大学泰和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