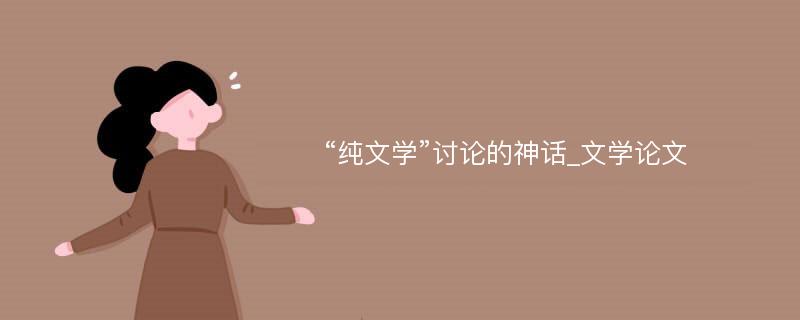
“纯文学”讨论迷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思论文,纯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40(2006)02-0068-05
一、“纯文学”讨论与80、90年代文学历史
2001年,《上海文学》第3期开辟“纯文学”讨论专栏,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自主性”、“文学主体性”主张和90年代“纯文学”观念的弊端进行批判,这是横亘在20年之间的一次文学对话。除个别作家以决绝态度提出捍卫“纯文学”创作宣言般悲壮的声明,[1] 对“纯文学”的精神内涵作出明确界定之外,“纯文学”讨论一开始就跳过了“什么是纯文学”的考究,直接进入“纯文学”历史。李陀的《漫谈“纯文学”》[2] 指出,长期以来,“纯文学”这样一个概念相当流行,90年代,“纯文学”观念仍然被大多数作家和批评家所信奉。李陀的文章和蔡翔的长篇论文《何谓文学本身》[3] 都语焉不详地认为:“纯文学”这个概念在80年代开始提出。参与讨论的文章在描述“纯文学”历史时,观点惊人的相似:1985年前后由“先锋派”和“新潮批评”逐渐形成“纯文学”观念,直到90年代,社会语境变化后仍然有大量作家坚持着80年的纯文学观念,从而导致了当代文学脱离了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成为“私人化”的东西。
但是,这样的普遍性陈述容易让人们对80、90年代文学做出缺乏事实根据和深入探讨之后的错误印象和主观臆断,无论讨论者如何表白自己是“亲历者”。如果作为一个概念,“纯文学”并不是由某个作家或某个文学流派提出。在80年代文学期刊中,我们并不容易找到“纯文学”字眼。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当代文坛,“实验小说”、“先锋小说”、“新潮小说”、“新历史小说”、“身体写作”、“另类”、“新新人类”等文学称呼都出现过,它们不是以“纯文学作品选”、“纯文学作家”以及“纯文学”等称呼出现的,也没有几位作家自封或者承认自己是“纯文学”作家。这些现象说明:当时作家和文学评论都没有把这些文学现象作为整体化的“纯文学”范畴来理解。而讨论者恰恰是把这些写作纳入了所谓“纯文学”一体化的理解。如果作为一种观念,“纯文学”观念也不是一种80、90年代作家共同遵守的创作理念,创作确实发生了回避或者抵抗政治意识形态的明显趋向,但是创作观念尤其是作品的表现千差万别。不应该把“纯文学”史等同于80、90年代文学史。如果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从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的纯与不纯已经界限模糊,正如陈思和所言,文学已经进入“无名时代”。与其说文学—市场关系凸现,市场开始形成新的“意识形态”,不如说文学创作观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距离感和疏离感。一部分老作家开始看不懂新作家的作品,一部分中年作家开始不再理会“文学新潮”,一部分新作家根本不相信什么“纯文学”。在这样的文学境遇中,“纯文学”讨论者却仍然捡拾其认识论,试图对80、90年代做出“纯文学”一体化的文学史叙述。这种梳理表现出的毋宁是僵化的文学认识论“旧识”: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规约的历史语境中把文学推向审美的极致,企图提倡卸掉文学的羁绊和条规;在摆脱这种历史语境后又忍受不了“文学不可承受之轻”,反过来重新强调文学的“文化政治”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文学史叙事的循环其中并无深奥哲理,也无助于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比如,李陀对“纯文学”的梳理,不过是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1985年前后的“实验小说”的评论,[4] 这是当代文学史教材已经形成的既定结论。在对当下文论语境的焦灼思考中,“纯文学”讨论以回避文学本体论的形式,悄然略过了对“纯文学”得失的历史评价,把80、9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整体描绘成只属于“纯文学”的历史,忽视了对作家创作多样性和不断超越既定文学面貌的努力的深入探究,潜在地为80、90年代中国文学命名为“纯文学”,削平了当代中国文学不断生成新的可能性的参差不齐的趋势和鱼龙混杂的局面。
二、“纯文学”讨论的理论支撑和现实语境
“纯文学”讨论表现出的不是对于文学自身的真正关注,而是认识论导致的“文学工具论”的卷土重来。在对“纯文学”反思中,李陀和钱理群[5] 的一致性在于:都自认是“纯文学”主张的“始作俑者”;都认为80年代“纯文学”的提出是他们借文学审美本体论来潜在地对抗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的一种策略;都自认“纯文学”观念严重影响了当代文学创作、文学教育和中国文学的趋向。这样自我忏悔般的文学评论并不具有感人的学理力量。一方面,“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是在当时国家文化政策范围内开始“突破”的,首先不是来自文学评论家的反思,包括“新时期”这个概念也是套用的执政党的文件;另一方面,1985年前后,文学创作中出现“现代派”以及与“现实主义”面貌迥异的文学文本,是新中国28年文学受政治意识形态掌控的反弹,不是“纯文学观念”的理论制导。而且,文学创作和实验出现各种可能性并非一个“纯”字所能统摄。“纯文学”讨论对20年文学的“追认式”叙事,把“纯文学”观念夸大为文学评论的历史功绩,错误地指认为属于几个文学评论家历史局限,以把“纯文学”观念作为影响当下文学创作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纯文学”讨论几乎众口一词地这样描述20年文学史,而没有出现不同的描述方式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潜在形成了对80、90年代文学的阐释话语的垄断。
当代中国文论一直处于一种几乎高过“五四”时期的焦虑和困境之中。“五四”时期接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困境和焦虑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歧化选择”[6] 的多种可能性,在一种未完成的文化系统之外开辟了探索可能性的开放的视野。当代文论与“五四”对话之间横亘着几十年的文学历史的沧桑变化,这些变化作为“历史流传物”(加达默尔)使当代文学评论的理念深深植根其中,熏染着传统的不可摆脱的历史规定性。同时,在新一轮大规模译介西方文论的过程中,重现了西方文论接受史中“唯恐落伍”的赶超心态。我们生活在无数历史时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又是生活在“五四”以来由西方理论渗透的中国文学评论传统之中。但是,当代文论既不真正相信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也不彻底相信西方文论。于是,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梳理,自从“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重写文学史”热潮以来,一直以一种所谓“本土化”的接受心态,在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审美理论这两条线之间徘徊,其中所使用的两大利器即认识论和文学社会学。其中文学经典的意义就被表述为文学以怎样的审美形式表达了何种社会观念和思想。“思想”取代了“内容”,“审美”取代了“形式”,成为继“内容—形式”二分法之后的“思想—审美”二分法。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到“内容和形式”,再到“思想和审美”,这正是认识论和文学社会学统摄之下中国当代文论的似曾相识的面容。20年来,在眼花缭乱的西方文论的理论旅行中,袭其表、去其实的域外借鉴,不仅没有解决我们的文学问题,却牢固了“文学工具论”的顽固底盘,种种文学阐释与把艺术看作是认识现实的形式的艺术认识论[7] 的方法论相去不远。正是这样的理论支撑,使“纯文学”讨论搁浅在“文学与现实”的维度裹步不前。“纯文学”讨论几乎成为这样一个问题:弄不清楚“现实”是什么,就无法弄清“纯文学”是什么。其中一个顽固的观念是:当代文学因为不关注现实(政治、底层、市场意识形态、“先富起来”的人的“第一桶金”等),所以是“纯文学”;“纯文学”不关注现实就会丧失文学功能,丧失读者,丧失和现实的深切联系,就会偏枯甚至寂灭。难道“纯文学”观念导致了一个极端,现在要把文学创作从这个极端拯救过来,再次走向“干预生活”、“写真实”的“螺旋式前进”吗?这是历史的循环,还是文学史叙事意识形态中文学的终极被表达为“‘现实’之真”的意识的循环?80、90年代的文学问题关键在于文学语境转化中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文不对题”导致的历史局限,而并非或主要不是文学创作的历史局限。当“怎么写”在文学中出现不同的探索方式的时候,文学评论的“怎么看”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当80、90年代文学作为“纯文学”史的发酵期而被概括出来,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就被当代文论赋予了一种文学退化论的叙述思维。“美学热”兴起的80年代中期,其黄金特征正是中国人文学界借助西方美学掀起中国文论革命、颠覆“十七年”以来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观念和理论。但是,借助西方美学激发文学研究新思维是一回事,紧跟西方理论“潮流”、惟西方理论是从是另一回事。在狂热的线性思维的“现代化”视野中,西方文论不证自明地成为我们的理论先导。当代文论普遍回避了官方对电影《苦恋》的批评、“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背后的文化含义。在这些呈现冷战思维的政治性批判的背后,暗含了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警惕和拒斥。当代文论却远远没有认识到如何保持它的界限,也远远没有预料到陷入西方文论的严重后果。当嫁接的“思想史代替文学史”的认识论和社会学框架无法与中西方哲学“接轨”的时候,当代文论必然陷入了焦虑和困境之中。
从9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文化研究”逐渐取代“后现代”成为中国文论的“显学”。随着西方“文化研究”著作和理论的大量译介,中国文论并未出现一片生机,相反带来的却是更大的失语和“文不对题”。我们在文化研究对待文学研究的态度上再度陷入了矛盾之中,“文学审美”、“文学性”、“文学自身”重新受到“文化研究”的巨大冲击。因此,当下中国文论的困境又表现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冲突问题及其解决方式。这种冲突和以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阐释与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阐释对立一样,又重新被表述为文学审美和文化政治实践的对立和矛盾。在文学的内外部之间,我们原地踏步,犹豫徘徊,陷入了无根的游走。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当然开拓出了文学研究的巨大阐释空间,各种“学”和方法当然丰富了我们阐释文学的各种技巧,但是,文学是什么?我们据此对文学进行阐释的前提是什么?这些问题已经被作为“本质主义”而轻易忽略了。近年来,有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论,开始当代文学理论的“寻根”工作,就是对文学本体论的再次寻找。“纯文学”讨论的重要性不在于从文学—社会(现实)、文学—政治(文化政治)的认识论工具对80、90年代文学做出“纯文学”史叙事。它本来就不应该是所谓“纯文学”概念的追认和自我检讨,而应该是一次文学本体论的深入思考。这种貌似对文学历史负责的态度遮蔽了对文学本体论的认识和检讨,与80年代“精英主义”共享了文学评论的共同资源,本身就值得反思。
三、“文学性”与文学本体论
“纯文学”讨论作为一个栏目结束以后,引发的对80年代“文学自主性”、“文学主体性”、“文学自律”、“文学审美性”等文学话题的反观更加耐人寻味。其中值得重视的是2003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师生对“文学自主性”的讨论[8] 和2003年发表的王晓明和蔡翔的《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1》。[9]
“文学自主性”讨论包含了对“纯文学”讨论的检讨。比如,“文学自主性”是否是被建构的?今天讨论“文学自主性”本身的依据是什么?无疑,这种讨论超越了对纯文学历史的考察,深入到对80、90年代文学的发展逻辑及其历史语境的探究之中,并引发出对文学自身的深入探究。洪子诚认为,李陀的文章“牵涉到对这十多年来文学成绩、问题的估价,以及对文学在当前社会、文化中的位置的看法”。“问题是,当前提出‘自主性’问题,是因为它被过分强调,以致文学在社会现实面前软弱无力,还是在90年代‘自主性’被过多削弱需要我们通过反思加以维护?”[10] 吴晓东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提问:如何使文学自主性的概念重新介入今天的历史境遇?今天的文学自主性应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实践状态还是理论状态?我们今天讨论的文学自主性与80年代“纯文学”的自主性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文学自主性”的范畴与80年代的“纯文学”的范畴是不是同一性的范畴?今天的文学的危机是文学在90年代语境中的历史性危机,还是80年代文学自主性观念的后果?[11] 这里,文学性的范畴恰是一个大家都不愿再提起的那个文学本体论问题。吴引用了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对审美维度本身的强调:“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文学的革命性,只有在文学关心它自身的问题,只有把它的内容转化为形式时,才是富有意义的。因此,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之维。艺术作品的直接政治性越强,越就会弱化自身的异在理论,越会迷失根本性的、超越的变革目标”;“艺术作品只有作为自律的作品,才能同政治发生关系”。[12] 马尔库塞强调的艺术自律打破了我们的文学社会学阐释,赋予了文学—政治一种崭新的审美解释。贺桂梅针对李陀《漫谈“纯文学”》中的观点,发出了这样的质疑:“不能泛泛地说九十年代文学创作没有关注现实,不论哪种作品,作者都会认为他或她所看到的那些东西就是一种现实。”[13] 其中有位讨论者还认为,“将文学只看成是历史之外的‘飞地’,或是只将它的自主认作是历史的意识形态诡计,都不能说明其内在的复杂性”。[14] 这次学理性很强的“文学自主性”的讨论,最终回到一个问题上来:对80年代文学“去政治化”的过程现在看来已经相对明晰,但是今天谈论“文学自主性”的前提和依据却值得质疑和思索:文学是否有它自己独立的言说方式?换言之,文学的自主性是否是文学言说世界的前提?
这个问题在王晓明和蔡翔的对话文章中再度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框架内被提出来。“对话”从西方“文化研究”谈起,期望将90年代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转化到文学及文学批评中来。蔡翔坚持了他在《何谓文学自身》中的观点:80年代文学“一方面是个体的自主性、自足性和自律性,但是另一方面,当时的文学也多少忽视了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联系”。“人的本质的现代化”和“人的解放”的诉求以一种个体的普遍性忽略了这种诉求可能产生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而这些问题在今天被重新尖锐地提了出来。[15] 王晓明重申了9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他思考的问题侧重“文学研究怎么样来处理人跟那些所谓的‘外部’因素的关系”,希望文化研究能成为其间的桥梁。在对人的认识和对文学的认识的关系上,他认为在强调文学“本身”价值的时候,很容易把这种“本身”与文学的所谓“外部”因素分隔开来,这实际上与80年代对人的抽象的内在性的强调密切相关:正是那个被抽离于社会环境之上的人的“本质”,构成了文学的“本身”的基础即文学本身和人本身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比如当人们一谈到“城市人”,就是孤独、陌生感那一套,一讲到“女性”,就是与男人的冲突、身体的自觉等,这正是一种“抽象”在起作用。[16] 在此基础上,王晓明触及到了文学“如何理解人”的关键问题:一个是人的现实的存在状况。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个层面是人的可能性:所谓文学的独立的“审美”价值,正是超越人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体现人的超越性和可能性,因此,文学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的诗意的、精神的那一部分。由此出发,王晓明发现了90年代文学问题的关键在于:体现人的超越性和可能性的文学作品逐渐减少,“用某种社会中层生活的经验,替换掉了原来蕴涵在八十年代那一套抽象的人的概念当中的比较多样、因而具有反抗意义的生活经验。这转换的结果不但会影响对人的现实状况的理解,也同样会影响对人的精神的可能性的体会”。[17] 王晓明在这里真正与80年代他的“审美批评”分道扬镳:不是回到80年代的“文学回到自身”,而是在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深化对人的精神状态的理解。在90年代“审美”已经转换成为社会中层文化的一部分的时候,“它不但无助于认识人的复杂的现实境况,还可能妨碍对人的多样的精神可能性的揭示”。[18] 依然追求文学的“美和诗意”,但是“审美”必须要在对人的精神状态的文化研究中被重新阐释,而这种对人的精神状态的理解正是当代文学“文学性”的丰富内涵。王晓明特别强调“诗意”的两个基本维度:“一个是从人的现实生活来说的,就是诗意应该和现存的压抑性的东西构成一个对立;另一个是从人的可能性来说的,就是诗意构成人不断自我更新的一种动力。”[19] 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代文学避免以新的抽象性的“文学自身”观念形成新的压抑机制,才能把“美和诗意”从压抑机制中解放出来。
在“纯文学”讨论及其激发出的对文学的思考中,讨论者均回避了本应为题中之义的“文学本体论”问题。这个“陈旧”的问题无时不萦绕着这些文学的讨论,冷眼旁观这些讨论怎样在“文学器论”的或深或浅的争论中坠入泥淖。当代中国文论的焦灼心态以及人文知识分子对把握当代中国文化的雄心纠缠在一起,使这些讨论者企图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和走向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其中存在着若干潜在的思维前提,比如:文学作品的成就取决于对当下社会的深入把握尤其是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准确理解;作家对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水平的高低;文学作品的质量通过如何对把握到的社会现实进行审美处理来衡量;文学应该重新认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社会学真理等等。这些潜在前提在对文学经验属性的批评方面显示出了文学批评对当下中国现实状况的急切关注,但是无法触摸文学本身,倒是把文学研究牢牢固定在文学社会学、文化学批判视野中,并且正在形成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等待着文学进行另一次悲壮的突围。王乾坤在《文学的承诺》一书中说,对本体论的不察,是进入文学性的巨大障碍;“没有本体论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是无根的”。“文学本体论一词意味着在形上识度探寻文学自身的原因,而我们从这种本体论中,感觉不到作为文学的文学这样的‘存在论’识度,有的则一开始就将本来属于情感范畴、审美范畴的文学,置于反映论或者认识论的基石上。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中,很难有真正的文学讨论,甚至很难提出真正的文学问题”。[20] 正是在这一维度上,王乾坤也对纯文学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本体论意义上的纯文学、文学性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某物,不是一个关系性对象,对此我们不可能有通常的实体性定义。当我们把文学当作一种关系性对象而定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已经不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学的某种属性。”[21]“纯文学”讨论、“文学自主性”讨论、“美和诗意”的讨论,虽然没有对“文学”和“纯文学”下实体性定义,但是无一例外地回避了文学本体论的思考。在讨论的背后,我们明显感到了他们已经梳理出了诸多文学的实体性定义。这些讨论超越了文学反映论,但是又捡拾起文学认识论的思维工具,把文学的认识价值抬到了文学的“终极视域”的平台上来,从而丧失了对文学本体论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历史的考察,回避了对80、9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审美自治”、“文学性”问题的形上思考。正是因为这种思考的缺失,文学研究失去了它本来应有的“文学性”根据,使“文学性”的讨论在“真”的范畴上,在文学与其他经验对应物的关系上,在文学的经验属性上徘徊不前。正是因为缺乏对事物的“究竟”不予置疑,文学不仅无法穿透一切经验,而且无法不做经验的附庸。因此,在文学创作的政治束缚和学术强制消退后,文学创作和评论仍然陷在社会学、历史学的语法规则中而不自知,中国文论也难以见到根本性的转机。
标签:文学论文; 纯文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