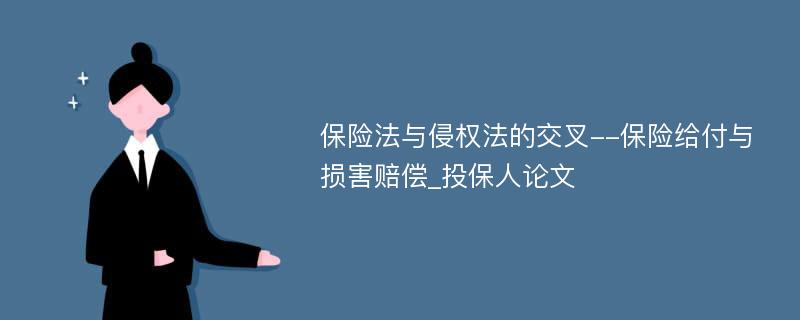
保险法与侵权行为法的交错——保险金给付与损害赔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险法论文,保险金论文,损害赔偿论文,侵权行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起
在发生侵权行为的情况下,被害人不仅可以依据侵权行为法中的有关规定向加害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同时,如果该被害人又是相关保险契约的被保险人或保险金受益人时,他(她)还可以向该保险契约上的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当保险金得以先行给付时,能否从加害人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额中扣除这一部分呢?民法上一般将此问题纳入损益相抵的研究范围,认为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保险金均不能作为损益相抵的对象从损害赔偿金中扣除。①
可是,最近有关特殊的“为了他人利益的伤害保险契约”引发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再思考。通常的伤害保险是以被害人为投保人(保险费支付人为被害人),而该保险契约中的投保人却为侵权行为人,即被害人领取保险金是以加害人支付保险费这一金钱支出为前提的。有这样一起案例,西安某商场为顾客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依照该保险条款规定,凡是在该商场购物期间发生的意外伤害,均由保险公司负责给付定额的保险金。1998年10月3日,五岁的陈鑫随姨妈在该商场购买饮料时不慎从二楼跌落,经抢救无效死亡。其监护人在得到了保险公司所支付的三万元保险金后依然向该商场提起了损害赔偿请求,并主张不应从损害赔偿额中将其已受领的保险金扣除,而商场则认为若不扣除,其投保该保险就变得毫无意义。② 此案中,由于保险费支付人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商场,在算定其损害赔偿金数额之时,若不能将保险金适用于损益相抵,似乎有悖于市民社会一般朴素的法感情。③
在我国保险法及民法学界,对如何调整保险金与损害赔偿金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还无较深入的研究。而日本法依托于该国成熟的保险制度,在此领域有着深厚的理论以及丰富的判例积累,特别是近年来引起广泛争议的机动车搭乘者伤害保险与损益相抵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性质与上述我国案例如出一辙。为此,笔者欲以检讨日本法在此问题上的解决方法为切入口,不仅从被害人,更从加害人的角度,对保险金的受领如何适用损益相抵法理进行深刻反思,试图在解释论及立法论两个层次上为我国相关问题的解决整合出一个合理的支撑框架。
二、日本法的检讨与研究
1.损益相抵的法理
损益相抵是指在侵权行为的被害人基于该侵权行为蒙受了损害但同时又获得了利益的情况下,将该利益从损害赔偿的范围中扣除的方法。④ 不过,日本的现行法中并没有关于损益相抵之明文规定。一般认为其直接源于侵权行为法中所存在的“原状回复理念”及其所包含的“利得防止”思想。即侵权行为被害人虽可就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获得补偿,但绝不能因其获得任何利益,侵权行为法中所规定的“损害”,应当是指经过损益相抵之后的真正的损害。⑤
传统上,将该利益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作为损益相抵的判断标准。⑥ 但是,由于一般情况下相当因果关系之认定并非易事,所以仅以此为依据无疑会使判断标准显得相当暧昧。对此,颇具影响力的学说主张应当将重心从相当因果关系转移到该利益对于损害而言具有何种实质性、机能性这一点上。四宫和夫教授认为,首先该利益须以侵权行为为契机而产生,并且其“实质上应当具有补偿损失或替代损害的目的及机能,即两者之间要具有‘法的同质性’这种关系”⑦。
笔者赞同四宫教授的主张,认为应当将以侵权行为为契机的全部给付(利益)暂且都纳入判断的对象范围,然后以该给付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同质性”为标准,对何种给付可以成为损益相抵的对象作出最终判断。此外,更重要的是,在“同质性”这样的判断标准自身也非常抽象的情形下,不仅需要将损害与利益放在一起进行实质性的比较,还须将损害赔偿的目的与机能、既得利益的目的与机能等一并综合起来予以考虑。⑧
日本最高裁判所(以下简称“最高裁”)也作出了如下判断:“在被害人由于侵权行为受到损害,同时又基于同一原因获得利益的情形下,只要损害与利益之间存在着同质性,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就有必要将该利益额从加害人的损害赔偿额中扣除,以此谋求损益相抵的调整。”⑨ 无疑,这是纠正了以往暧昧标准的合理判断。
2.损益相抵与保险代位的关系
如上所述,损益相抵的作用在于防止被害人的不当得利,而众所周知,损害保险中的“保险代位”制度也以“防止被害人得利”为其目的之一,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首先,从被害人(被保险人)的角度出发,无论是基于损益相抵还是基于保险代位,其结果都是缩减了加害人的损害赔偿数额。为此,有学者认为保险代位实际上是“损益相抵的一种变形”。⑩ 但是,此问题的考察对象不应仅限于被害人。若单从被害人的角度来分析,保险代位与损益相抵的结果确实都是缩减了加害人的赔偿金额。但若从加害人角度来分析,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即在损益相抵的情形下,加害人所应支付的损害赔偿金额被缩减,加害人的责任在此范围内得到了免除;而在保险代位的情形下,被保险人拥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只是在其受领的保险金范围内转移给了保险人,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明确区分损益相抵与保险代位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而从前的民法理论似乎将两者放在同等位置上加以对待了。
其次,有学者提出,损益相抵和保险代位是两种不同层次上的制度,前者用以决定加害人的损害赔偿额,后者则是赔偿额决定以后的问题,两者处于一种前后关系之中。(11) 但是,可以成为损益相抵对象的给付(利益)存在着两种形式:一种是所谓金钱评价问题。例如在算定因死亡而发生的逸失利益时需要扣除生活费及养育费。另一种是所谓损害的重复填补之调整问题。例如从侵权行为人以外的第三人处受领了不同于损害赔偿金的其他给付。在与保险代位的关系上,需要研究的是后者。(12) 此情形下的损益相抵是将第三人给付金额从损害赔偿额中扣除,其结果使得加害人免除相应的赔偿责任。此时,损益相抵与保险代位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两者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事例中。
在明确了损益相抵的意义及内容的基础上,下面让我们从一般的保险入手对保险金与损害赔偿金之间的关系逐一进行梳理。
1.一般的保险与损益相抵
关于一般的保险契约,最高裁以生命保险金、火灾保险金、定额伤害保险金均具有保险费对价的性质,或者,因具有保险费对价的性质,所以其支付是依据侵权行为以外的其他原因(别个契约)等几乎相同的理由,判定三种保险金都不能成为损益相抵的对象。(13)
此结论虽然得到了学说的一致支持,(14) 但大部分学者对其法理依据表示了反对。首先,损害保险的场合,保险费的对价应是保险人的风险负担而非保险金本身。(15) 这是因为,若保险期间内无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不仅不需要支付保险金,连保险费也无需返还。并且,上述三例最高裁判所判决中,被害人都是投保人,保险金与保险费之间处于一种对价关系的说法在此场合或许还能有一席之地,但在加害人为投保人的场合,即加害人承担保险费、被害人受领保险金时,此见解则难以成立。其次,虽然保险金的支付依据为保险契约而非侵权行为,但只要保险金的支付原因与基于侵权行为的死亡或伤害原因是出于同一事实,那么认为两者之间毫无关系的主张未免过于拘泥于形式了。(16)
最高裁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最高裁大法庭1993年3月24日判决(民集47卷4号第3039页)是一个有关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损害的原因)的发生而受领了遗属年金的案件。在此判决中,最高裁虽然肯定了损害与利益的发生是基于同一原因,但依然作出了不应将保险金从损害赔偿金中扣除的判决。也就是说,此判决与以往的判决不同,以往的判决以否定两者之间存在着同一发生原因来否定损益相抵,而此判决是在承认该保险金的取得与侵权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否定了损益相抵,将判断的标准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同一原因”转移到了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同质性”上。
依据前述损益相抵与保险代位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关于损害保险金,其受领行为的发生是以加害行为为契机的,并且,其目的当然为补偿损害,所以其与加害人的损害赔偿金之间具有“同质性”。因此,为了“防止被害人得利”,损害保险金本应成为损益相抵的对象而从损害赔偿金中扣除。但是,此结果将导致加害人得以免除相应的赔偿责任,有违社会通常观念,为此,作为一种法政策,保险法上针对损害保险设立了兼具“防止被害人得利”与“阻止加害人免责”这两种机能的强行法规——保险代位制度。并且,由于保险代位和损益相抵这两者不能存在于同一个事例中,因此损益相抵在损害保险契约中原本就无适用余地,也就是说,在讨论损害保险金能否成为损益相抵的对象之前,该问题就已经得到了解决。第二,关于生命保险金与定额的伤害保险金,由于其不具有损害填补的性质,与损害赔偿金之间不存在同质性,因而不能成为损益相抵的对象。
2.搭乘者伤害保险与损益相抵
对于上述一般的保险,搭乘者伤害保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保险是日本任意机动车保险中的一个附加险种,以搭乘于被保险机动车内正规乘车位置之人为被保险人,当由于该机动车的运行所引起的急剧、偶然、外来的事故造成被保险人身体受到伤害时,由保险公司向其支付约定的保险金。其特征为:第一,被保险人为非确定。在投保人为受害人的情况下,该保险的性质是“为了自己利益的伤害保险契约”,而若被害人为投保人以外的搭乘者时,该保险的性质则是“为了他人利益的伤害保险契约”。第二,该保险为定额保险。第三,该保险在其条款中排除了保险代位制度。这其中,尤其是被保险人不确定这一特征成为引发问题的主要原因。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判例的立场:
(1)损益相抵否定例
最高裁在有关搭乘者伤害保险的判决中,首先以该保险为定额保险,在保险条款中排除了保险代位等为理由,认定其不具备损害补偿的性质。其次还着眼于该保险所具有的,为处于责任保险保障对象之外的亲属提供保护这一机能,在综合各类因素之后,作出了搭乘者伤害保险金不应从损害赔偿额中扣除的判断。(17)
最高裁在此判决中并没有直接使用损益相抵这一用语,而是通过分析搭乘者伤害保险金(利益)的目的和机能,认定该保险具有“鉴于投保人及其家族成员、友人等搭乘被保险机动车的机会较多,通过向上述的搭乘者或其继承人支付定额的保险金,达到对其进行保护的目的”,从而否认了该保险金与损害赔偿额之间存在“法的同质性”,得出了不应将其从损害赔偿额中扣除的结论。因此,应当认为最高裁的判断正是遵循了损益相抵的法理。
另有学者认为,依据搭乘者伤害保险的定额性直接就可以推导出其不具有损害补偿的目的,从而不适用损益相抵的结论。(18) 但是,只要是定额保险就不适用利得禁止原则,加害人的责任也就不能得到免除这种观点只不过是一种原则性的一般论,如果法律规定或者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约定免除加害人的责任,即使是定额保险金也有可能成为损益相抵的对象。例如,根据德国航空法的规定,如果定额的伤害保险的保险费是由航空公司来支付,那么航空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在该保险金金额限度内可以得到免除(《德国航空法》第50条)。最高裁判决也只不过是就搭乘者伤害保险这一险种,对其具有的定额性特征予以了重视,而并没有进行“凡定额保险的保险金均不应从损害额中扣除”这样一般论性质的论述。因此,在搭乘者伤害保险的情形下,要将其具有的家族、友人保护机能等因素综合起来,才能够对该保险的损害补偿性予以否定。
最高裁判所判决前后的下级审判决几乎都不承认损益相抵,理由均为搭乘者伤害保险金不具有损害填补的目的,因此与损害赔偿金不具有“同质性”。(19) 但是,搭乘者伤害保险有着上述被保险人不特定的特征。在“为了他人利益的伤害保险契约”的情况下,加害人大多是负担保险费的投保人,此时,被害人对保险金的受领是基于加害人投保的保险契约。如果不能从加害人的损害赔偿额中将该保险金扣除,就加害人而言,缔结该保险将变得毫无利益。
(2)损益相抵肯定例
对此问题,存在着从正面承认损益相抵的判决——高松高等裁判所1991年2月26日判决(以下简称“高松高判”)。(20)
该判决以加害人为保险费支付人,如果不将搭乘者伤害保险金从损害赔偿金中扣除有违公平原则这一考虑为中心,通过判断该保险金具有损害赔偿的性质,认定了其为损益相抵的对象。关于损害赔偿性的理由,该判决首先将搭乘者伤害保险分成了加害人承担和不承担侵权行为责任的两种情形。对于后者,认为该保险金的性质为抚慰金因而不具有损害赔偿性;对于前者,认为可以对加害人的意思进行合理的解释,即应当承认该保险金对被害人而言具有损害赔偿性。可是,且不论不以任何法律、条款为依据将一个保险契约解释为具有二元性的契约是否显得过分随意,判决所做的解释是否真的合理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由于搭乘者伤害保险的特征之一为该保险金的给付是与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无关的定额支付,所以,该保险起着保护经常搭乘该机动车的投保人(所有人)或其家人、亲友等搭乘者的作用。因此,应当认为,一般情况下投保人在缔结该保险契约时,并没有将该保险金用来充当保险事故发生时的损害赔偿金之意。并且,若采此意思解释的话,投保低额的责任保险即可规避因可能承担赔偿责任所带来的风险,这对自愿投保高额责任险的投保人而言显然缺乏公平,(21) 为此,不得不认为高松高裁的这种拟制性解释缺乏合理性。
其次我们来总结一下学说的评价:
高松高判没有能够得到任何学说的支持。不过,有学者虽然对其结论持反对意见,但赞成其提出的需要“将加害人的意思予以合理的解释”这一着眼于加害人立场的视点。山下友信教授认为,在搭乘者伤害保险是“为了他人利益的伤害保险契约”之时,除了由保险契约关系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外,投保人与保险金受益人之间还存在着实质上的原因关系。如果这一关系不存在,保险金受益人的保险金受领就将成为不当得利。(22) 因此,高松高判的错误在于其意思解释的内容本身。鉴于该保险的目的,山下友信教授将该保险金理解为抚慰金;(23) 仓泽康一郎教授认为其意思是“即使超过了向被害人或其遗属应履行的赔偿责任,也要使其享受到该保险利益。这与责任保险契约时投保人具有的事故赔偿责任免脱之意有着本质上的差异”(24);金泽理教授将投保人的意思解释为:“一般来说,使用机动车最频繁的该机动车之保有人(投保人)或其亲属成为人身事故被害人的可能性非常高,因此在碰撞事故中,将搭乘者伤害保险作为对方机动车无责或赔偿资力不足等场合的一种自卫手段来考虑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投保人主要是为了保障自己或亲属的利益,而就他人的伤害支付保险金只不过是一种附随的意思而已。”(25) 这些判断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很难说何者最为正确。总之,学者们认为搭乘者伤害保险金不具有损害赔偿的性质,与损害赔偿金之间没有“同质性”,因此不能成为损益相抵的对象。
综上所述,搭乘者伤害保险中,不仅在投保人=被害人的场合,即使是在投保人=加害人、被保险人=被害人的场合,不应将该保险金从加害人的损害赔偿金中扣除在判例和学说上已经成为了定论。可是,对于加害人支付保险费这一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如果不作任何评价的话,显然对加害人有失公平。但是,既然否定了该保险金的损害赔偿性,就必然推导出其不能从赔偿额中扣除的结果。笔者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抚慰金时对该事实予以斟酌,因为该保险金具有加害人对受害人表示谢罪的性质。
3.搭乘者伤害保险与抚慰金斟酌
(1)判例与学说的现状
关于抚慰金的性质,日本的学说存在着损害赔偿说与制裁说的争论,但判例在算定其金额时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态度,对应当予以斟酌的各种事项没有进行任何限制,包括“当事人双方的社会地位、职业、资产、加害的动机及形态、被害人的年龄、学历等诸多事情都应予以参酌。”(26)
上述最高裁1995年判决维持了第二审判决所认定的抚慰金金额。许多学者以此为依据,或认为其对抚慰金斟酌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或认为其采取了否定的立场。(27) 但是,抚慰金算定时的斟酌是指由裁判官针对各案件综合考虑所有的因素,最后根据自由裁量确定抚慰金数额,因此,不能仅以最高裁偶然确定了与原判决同样的抚慰金金额为由,断言其否认了抚慰金算定时的斟酌,至多看成既非肯定也非否定。最近的下级审判决几乎都是在否定了损益相抵的同时,将加害人支付保险费这一事实在算定抚慰金时加以了斟酌,采此立场的判决基本上占了全部判决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理由无一例外,均为在“加害人支付保险费的场合,搭乘者伤害保险金具有加害人对被害人的慰问金性质,通过对此慰问金的受领,被害人的精神痛苦得到了相应的补偿”。(28)
学说对此问题分为“斟酌肯定说”和“斟酌否定说”两派。与下级审判例同样,大多数学者采斟酌肯定说。(29) 此外,斟酌肯定说中又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只要被害人受领了搭乘者伤害保险金,就应对其加以斟酌的“广义抚慰金斟酌说”;二是搭乘者伤害保险金的受领只是在加害人负担保险费的前提下才允许斟酌的“狭义抚慰金斟酌说”。针对斟酌肯定说,作为少数派的斟酌否定说提出了如下疑问:
第一,将不具有损害赔偿性的搭乘者伤害保险金在损害额算定(抚慰金的性质实质上是损害补偿)时予以斟酌是否妥当?(30)
第二,若将抚慰金的性质理解为损害补偿,那么抚慰金算定之际的斟酌岂不等同于从损害额中的扣除?(31)
第三,理论上对于通过斟酌应该减少多少抚慰金金额并没有一个明确标准,由此裁判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是否显得过大?(32)
第四,从保险契约的构造出发,将搭乘者伤害保险金的性质理解为抚慰金的意思解释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将1000万日元左右的该保险金作为抚慰金来处理是否有违社会对抚慰金的一般认识?(33)
(2)研究情况
笔者支持“狭义抚慰金斟酌说”。
关于上述问题一,笔者认为虽然搭乘者伤害保险金不以损害赔偿为目的,但加害人负担保险费这一事实应该使被害人的受害感情些许得到了安慰。况且,毫无疑问,无论抚慰金的性质是对被害人的损害补偿还是对加害人的制裁,其对象都是被害人的精神痛苦。因此,在算定抚慰金时予以斟酌乃是理所当然的。关于问题二,如果将“抚慰金算定时斟酌加害人负担了保险费”理解为“从抚慰金中扣除或将其减额”的话,的确存在着否定说所指出的问题。但笔者认为,这里的斟酌并非“扣除”或“减额”之意,而是与在抚慰金算定之际,必须要考虑到被害人的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情况等许多因素一样,将“加害人负担保险费”这一事实也视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即在此场合,被害人或其遗属的精神损害额是斟酌了加害人负担保险费这一事实的结果,这与从已算定的损害额中扣除保险金给付额的方法完全不同。(34) 关于问题三,斟酌肯定说自身也发生了意见分歧,有见解认为导致抚慰金数额大幅减少的斟酌有失妥当;(35) 也有见解认为不能以此为理由将斟酌的范围过于标准化,(36) 这种意见分歧体现了该问题具有相当大的困难性与争议性。但是,既然已将抚慰金斟酌委任于裁判官的自由裁量,那么,即使在客观上有必要将一定水准的社会评价定额化,对于个别事由,笔者认为将其作为抚慰金金额决定之际的调整要素加以斟酌即可,没有必要将斟酌的数额作为一般论来进行讨论。关于问题四,确实,将搭乘者伤害保险金理解为慰问金的意思解释或许可以说是忽视了社会常识所理解的慰问金所应有的金额。不过笔者认为,如果对照前述金泽教授和仓泽教授所进行的意思解释来考虑,此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即,第一,该保险金首先是为了自己或家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即使具有相当高的保险金额,也不会立即违背一般社会通念。第二,该保险金还可能是针对他人伤害进行给付的保险给付金,这种场合,加害人的意思是:即使超过了向被害人或其遗属应履行的赔偿责任,也要使其享受到该保险利益。所以,此时该保险金的金额即使高于社会常识上的抚慰金数额也无不妥。
“广义抚慰金斟酌说”强调了抚慰金在损害赔偿额算定之际的调整及补偿机能,认为只要能够算出妥当的赔偿额,就不必局限于保险费的支付人是否为加害人。(37) 不过,笔者认为,既然是为了能够算出“妥当”的赔偿额,其斟酌事由也必须是“妥当”的。一般认为,虽然加害人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被害人的精神痛苦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可以经加害人的损害赔偿或多或少地得到些愈合。而无论抚慰金的性质如何,都不能否认其事实上能够使被害人对加害人进行制裁或者报复的感情得到一定满足。(38) 认为应将加害人负担保险费这一事实作为斟酌事由也正是考虑到了加害人怀着诚意向被害人支付了抚慰金,因而必须兼顾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公平。反之,如果搭乘者伤害保险的投保人是加害人以外的第三人,那么被害人即使受领了该保险金,其精神痛苦及对加害人之愤怒感情恐怕也难以得到抚慰。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在保险费是由加害人负担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被害人的痛苦得到了愈合,因而得以将该保险金在抚慰金算定之际予以斟酌。
三、中国法的解决路径
以上我们详细论述了日本保险法上有关特殊的伤害保险契约问题的解决方法。在同样缺乏相应法律规定的我国,不仅可以借鉴日本保险法解释学上的成果,还应当将其运用到立法论上,对此问题给予事前的根本解决。
1.法解释论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确定了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须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等六种具体情况(第10条),而当其不能满足疑难复杂案件的解决时,法官也可以依据自由裁量权基于合理原则追加其他斟酌因素。(39) 虽然《解释》并未列举加害人道歉(包括通过金钱给付形式)这一情形,但由于精神损害赔偿是以加害行为的可归责性以及道德上的可谴责性为基础的司法评价,且立法者及学者们亦都明确了其具有补偿受害人损失及制裁加害人的双重功能,(40) 因而在侵权行为被害人因加害人缔结的保险契约而受领了保险金的情况下,可以认为加害人的保险费负担缩减了其道德上的可谴责性,同时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及对加害人的怨恨感情也因上述保险金之受领而得到了一定的缓和。为此,对本文开头案例所提示的商场所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之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展开与日本法同样的法解释,在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之时通过斟酌加害人负担保险费这一事实的办法予以解决。
2.立法论
但是,无论法官自由裁量的过程多么合理,如果被斟酌的数额低于加害人所支付的保险费,其抵触情绪一般而言很难消失。就前述商场的案例而言,其后果为商场很可能终止续保,不仅被保险人因而无法得到更有利的保障,相关险种也会因此而萎缩,这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及保险人三方均为不利。为此,根本的解决方法在于从立法论上明确此类特殊的伤害保险金可以从损害赔偿金中扣除。上述日本法中的搭乘者伤害保险,其保险金的扣除之所以被否定,原因在于无法将其解释为与损害赔偿金具有相同的“法的同质性”,从而不能适用损益相抵的法理。而若能事先将定额的伤害保险金之法律性质界定为损害赔偿,此问题则可迎刃而解。具体应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该险种为强制付保的情形下,可在相应的特别法中予以明确规定;第二,该保险为任意付保的情形下,可在条款中明确约定,当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为被保险人兼保险金受益人,投保人为加害人时,该保险金的性质为投保人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保险金受益人申请保险金须以免除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受领的保险金数额为限)为前提条件。(41)
“为了他人利益的保险契约”性质上属于“为了第三人利益的契约”,通说认为,此种契约只能赋予第三人权利,而不得约定其义务。(42) 不过,笔者认为此见解的含义应当仅停留在“不能使第三人只承担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利”,而非“不能使第三人承担任何义务”。当事人可以在契约中约定第三人取得权利的条件,(43) 或者说使其承受附随的负担。(44) 因此,在投保人为加害人的伤害保险契约中,即使被害人的保险金请求权附有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这一条件,也不违反契约法的相关原理。况且,虽然被害人可请求的损害赔偿金在其受领到的保险金范围内相应缩减,但这对损害赔偿总额并无任何影响。最后,或许有人会质疑,既然如此,对被害人而言该保险的实际意义何在?回答是,存在于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负损害赔偿责任或者加害人无资力之情形中。
注释:
① 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私保险。保险依经营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公保险与私保险。前者主要指政府用以实现公共政策的社会保险,其加入大都具有强制性,因而其保险金与损害赔偿金之间的关系一般都由特别法来明确规定。而私保险的加入以自愿为原则,侵权行为发生时,一般情况下,受害人并不当然拥有保险金请求权。况且,保险契约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随着险种的发展日趋复杂,法律也难以事先对私保险范畴内各种保险金给付与损害赔偿金数额之间的关系予以规制,只能依据民法及保险法的一般法理寻求最善的解决路径。
② 参见中华保险网,http://www.123bx.com/insurance/223/baoxian42211_1.html.
③ 我国保险法明文规定:除投保人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父母以及与其有抚养等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外,凡以其他人的生命或身体作为保险标的的,须征得该人的同意(第53条),并且,除非投保人为被保险人的父母,否则投保人不得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为被保险人投保死亡保险(第55条)。而此“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缔结显然未经被保险人的同意,况且受害人为五岁的儿童,故该保险合同的效力可能会受到质疑。“团体保险中被害人的同意”是保险法中的重大课题,对此笔者欲另撰文详细阐述,就结论而言,保险法中的上述相关规定都是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而本险种的被保险人为不确定之人,且其本人为保险金受益人,因而不易发生故意导致保险事故的情形,若认定该合同无效,反而使受害人失去保险保障,显然有失公平。因此从解释论上,应当承认本合同的效力。此外,可能会有观点认为,此时商场应当投保责任保险,而非意外伤害保险。但是,在商场对顾客发生的伤害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责任保险无法起到保护被害人的作用,因此,不能混淆两险种的性质及功能。
④ 参见平井宜雄:《债权各论Ⅱ不法行为》,东京:弘文堂,1992年,第145页。
⑤ 参见加藤一郎:《不法行为》,东京:有斐阁,1974年,第245页。
⑥ 参见我妻荣:《新订债权总论》,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第128页。
⑦ 四宫和夫:《不法行为》,东京:青林书院,1987年,第601页。
⑧ 参见吉村良一:《损害的重复填补及其调整》,《法学教室》1996年第190号。
⑨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决1993年3月24日,民集47卷4号,第3039页。
⑩ 参见四宫和夫:《不法行为》,第603页。
⑾ 参见能见善久:《判例批评》,《商法(保险、海商)判例百选》,东京:有斐阁,1993年,第69页。
⑿ 参见洲崎博史:《损益相抵与保险代位》,金泽理等编:《裁判实务大系26——损害保险诉讼法》,东京:青林书院,1996年,第156页。
⒀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决1964年9月25日,民集18卷7号,第1528页;最高裁判所判决1975年1月31日,民集29卷1号,第68页;最高裁判所判决1980年5月1日,判例时报971号,第102页。
⒁ 参见田边康平、石田满编:《新损害保险双书2》,东京:文真堂,1983年,第287页。
⒂ 参见大森忠夫:《保险法》,东京:有斐阁,1985年,第57页。
⒃ 参见山下友信:《保险契约与损益相抵》,《现代的生命·伤害保险法》,东京:弘文堂,1999年,第278页。
⒄ 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决1995年1月30日,民集49卷1号,第211页。
⒅ 参见松本克美:《判例批评》,《法学教室》1995年第178号。
⒆ 参见岳卫:《搭乘者伤害保险与损害赔偿》,《立命馆法学》2003年第285号。
⒇ 肯定损益相抵的地方裁判所判决还有宇都宫地方裁判所判决1983年1月31日(交通民集17卷3号,第611页)、高松高等裁判所判决1993年6月17日(机动车保险期刊1036号)。
(21) 参见落合诚一:《判例批评》,《商法(保险、海商)判例百选》,东京:有斐阁,1993年,第140页。
(22) 参见山下友信:《生命保险金取得权的固有权性》,《现代的生命·伤害保险法》,第58页。
(23) 参见山下友信:《保险契约与损益相抵》,《现代的生命·伤害保险法》,第271页。
(24) 仓泽康一郎:《搭乘者伤害保险与损害赔偿》,《铃木辰规教授花甲纪念——保险的现代课题》,东京:成文堂,1992年,第408页。
(25) 金泽理:《搭乘者伤害保险与损害赔偿》,《创立60周年损害保险论集》,东京:损害保险事业综合研究所,1994年,第760页。
(26) 参见日本大审院判决1920年5月20日,民录26辑,第710页;最高裁判所判决1965年2月5日,集民77号,第321页。具体地说,在交通事故中,作为增加抚慰金金额的事由可以是:事故发生后加害人对被害人的态度非常不诚实的情形(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决1987年5月29日,交通民集20卷3号,第731页);加害人的过失极为巨大,导致被害人被全身碾断而死亡的情形(横滨地方裁判所判决1989年4月24日,交通民集22卷2号,第502页)等等。最近,在所谓“片山隼君事件”中,裁判所认为遗属“为了查明本案事件的真相”而做出的“热情和努力在抚慰金算定之际应予以充分的斟酌”(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决2001年3月15日,交通民集34卷2号,第384页),表明了斟酌事由具有多样性。
(27) 参见出口正义:《判例批评》,《ジユリスト》1996年第1091号。
(28) 参见岳卫:《搭乘者伤害保险与损害赔偿》。
(29) 参见松村弓彦:《判例批评》,《NBL》1996年第601号。
(30) 参见出口正义:《判例批评》,第93页。
(31) 参见洲崎博史:《定额保险与损益相抵——以搭乘者伤害保险的问题为中心》,《商法、经济法的诸问题——川又良也先生花甲纪念》,东京:商事法务研究会,1994年,第340页。
(32) 参见北河隆之:《搭乘者伤害保险金是否应从损害额中扣除》,《损害保险研究》1991年第53卷3号。
(33) 参见松村弓彦:《判例批评》。
(34) 参见山下孝之:《搭乘者伤害保险金与损害额的控除》,《私法判例リマ一ク·ス》1996年第12号。
(35) 参见和根崎直树:《搭乘者伤害保险》,盐崎勤编集:《现代裁判法大系25——生命保险、损害保险》,东京:新日本法规,1998年,第360页。
(36) 参见杉田雅彦:《搭乘者伤害保险与损害赔偿》,金泽理、盐崎勤编集:《裁判实务大系26——损害保险诉讼法》,东京:青林书院,1996年,第413页。
(37) 参见金泽理:《搭乘者伤害保险与损害赔偿》,《创立60周年损害保险论集》,第771页。
(38) 参见吉村良一:《不法行为法》,东京:有斐阁,2002年,第18页。
(39) 参见关今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第439页。
(40) 参见唐德华:《加强司法保护,维护人格尊严》,《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10日;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2页。
(41) 关于保险条款对当事人的约束力问题,参见覃有土:《保险法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江头宪治郎:《商取引法》,东京:弘文堂,2005年,第386页。
(42) 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43) 参见叶金强:《第三人利益合同研究》,《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4期。
(44) 参见我妻荣:《债权各论上卷》,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第1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