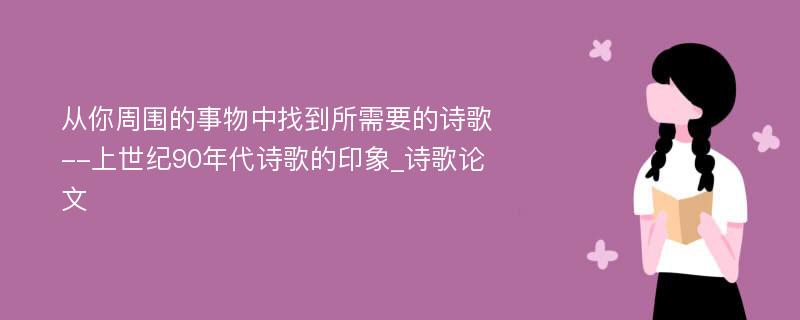
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九十年代诗歌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句论文,诗歌论文,事物论文,印象论文,身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从诗人孙文波的诗中借来的。孙文波近年在《山花》上发表组诗《母语》,其中的一首题为《改一首旧诗……》:
重读旧诗,我感到其中的矫揉造作。/第一句就太夸张:“他以自己的/胡须推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一个人的胡须怎么可能推动时代的风尚?/想到当年为了它自己颇为得意,/不禁脸红。那时候我成天钻研着/怎样把句子写的离奇,像什么/“阿根廷公鸡是黄金”之类的诗句/写得太多啦。其实,阿根廷公鸡/是什么样,我并没有见过;黄金,/更是不属于我这样的穷诗人。写它们,/不过是觉得怪诞,可以吓人一跳。/现在,写了十年诗,我才明白,/谁也不会被我吓一跳,搞糟了的/不过是自己。现在,我终学会/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
孙文波对旧作的反思,不仅仅是他个人对诗的重新发现与认识,同时也代表了90年代青年诗人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心态,即由过去对现实的漠视、回避,转入对现实存在状况的敞开与关怀,由对隐喻、象征意象的迷恋,转入让存在诗中直接呈现自己。这些诗美追求上的变化,体现了青年诗人在经历了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践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比起青春期的自我宣泄及形形色色的语言实验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更见难度、更具功底的写作。
“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强调的是应当把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诗人不能成天沉浸于乌托邦的幻想当中,更要关怀世界,关注自己及周围人的生存状态。这一原则给90年代诗坛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诗的民间性的呈现。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个启蒙的时代、浪漫的时代,90年代则是个现实的时代、凡人的时代。随着启蒙与浪漫时代的结束,是激情与理想的淡化。诗人离开了语言迷宫与象牙之塔,回到民间去寻找诗情与诗魂,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趣味,一种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格调在诗中呈现出来。
90年代中国人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90年代诗人的“身边的事物”,往往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以及面临生存危机的疑惧与焦虑。李霞的组诗《现代生活》,把现代生活中常见的广告、自由撰稿人、高速公路、女交警等写进了诗歌,体现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现代人的焦灼感。陈超的《本学期述职书——“现实主义”而且“白话”》,透过一个高校教师写期末述职书的苦恼,展示了人文知识分子在当前时代的窘困的处境。谢湘南的组诗《呼吸》则描述了深圳打工族的原生态:《零点的搬动工》、《深圳早餐》、《一起工伤事故的调查报告》……仅从这些题目,也略可窥见打工生活的紧张、单调与严酷。竹马的《我和我的工厂》,不同于五六十年代来流行诗坛的那些轻松地歌颂劳动、欢快地抒发工人主人翁感的作品,而是透过抒情主人公的自白,展示了90年代工厂面临的凋弊、严峻、艰难的生存现实以及人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的心态:“我的工厂沉重 我也沉重/我沉重得像废弃的厂房和残损的设备”,“就像一颗螺帽一丝丝游离自己的位置/总是需要扳手不断地加以紧固或者/再加上一个螺帽加以防护 我不知道/我是机器上的第几个螺帽或者哪一种扳手 我只知道在这样的往复中不甘或者安然”。这里打动人的是,作者不是以诗人的身份俯视现实、游离现实,而他本人就是现实,已成为庞大而衰老的机器的一部分。
“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要求诗人最大程度的向存在敞开,这自然会带来艺术手段的变化。一般说来,浪漫时代的诗人,更多地凭藉激情展开幻想的翅膀,构筑超越日常生活的审美空间;而平凡时代的诗人,则更多地依赖日常经验与个人体验,否则诗歌会显得空疏而飘浮。舒婷、北岛那一代朦胧诗人,着意将生活的秘密溶解在意象中,将深挚而多层次的情感寄寓在冷隽的暗示与象征中,不是按现实的时空秩序,而是按诗人情感的流向和想象的逻辑来重新安排世界。诗中的意象不是客观事物的直接反射,而是在经过诗人心灵世界的过滤后有所模糊、有所省略、有所变形。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也给后来者的逾越平添了难度。但朦胧诗人的时代毕竟过去了。90年代严酷的现实迫使诗人正视基本国情、直面生存处境,并探寻从寻常琐屑的生存现实中发现诗意、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诗歌材料的可能性,叙事性话语的加强就是其中之一。
90年代诗人的叙事,与传统的叙事相关,但不是一回事。传统叙事的基本元素是故事、人物、环境,其主要特征是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客观的讲述,如黑格尔所说:“史诗就是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注: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99页。)而在现代生存场景挤压下,当代诗人的叙事不是以全面地讲述一个故事或完整地塑造一个人物为目的,而是透过现实生活中捕捉的某一瞬间,展示诗人对事物观察的角度以及某种体悟,从而对现实的生存状态予以揭示,这是一种诗性的叙事。朱文有一首诗,题为《黄昏,居民区,废弃的推土机们》:
还差一百米的距离,就可以进入/居民区,但是不长的一条路,够他们走一生。//这些推土机,这些奇怪的游民。/引擎已被阉割,命运早已注定。/此刻,带着钢铁的最后一份/矜持,去试图了解当地的风俗。//能否在天黑以前,被居民区接纳,他们显然没有太大的把握。//这群冲动的词语,愤怒依旧,/搁浅在这里,已失去最初的指向。/谈话的双方,以及那次谈话的/背景,因为已被接纳,而从这里永远消失。//只剩下他们了,/钢铁一般的词语,/词语一般的钢铁。//拓荒者的胸怀里,/居民区华灯初上。
进入90年代,房地产建设开发成为遍及全国、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身边事物”。围绕着拆迁安置等实际问题,社会上积累了重重的矛盾。朱文由于是写诗,无须乎也不可能像通讯报告那样交代拆迁的起因,以及造成当地居民与推土机对峙的来龙去脉,他只选取了居民区与废弃的推土机的默默对峙的场景,形成了一幅充满着张力的图画:被阉割的引擎、一百米的距离、谈话的双方、黄昏的灯光……暗示这里围绕拆迁曾进行紧张激烈的谈判,谈判未果,推土机隆隆推进,遂出现了愤怒的居民砸毁推土机引擎的事件。目前,黄昏降临,剑拔弩张的对峙虽暂时平静下来,但更大的冲突也许还在后边。90年代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尖锐的矛盾,以及人们心理的失衡,就这样通过叙事性场景显示出来了。朱文还有一首诗题为《生计问题》,写诗中的“我”搬家后,遇到一个新房东,他是一家发动机配件厂二分厂厂长,这位厂长善意地关心“我”的生计问题,而“我”却对厂长说,这个问题离你倒更近一些,你厂子的职工怎么办呀!于是导致厂长更深地考虑几百个职工的生计问题。
如果说朱文的《黄昏,居民区,废弃的推土机们》等诗是通过叙事展示了90年代的较为普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心态,那么庞培的《上午的记事簿》展示的则是一个较为个人化的文本:
早晨载重卡车的体积,/和晨光吭哧吭哧的声音,/辗转着这冬日的街道。/一个远方的问路人途经我书店,/他那往前举起的手指和他背上肮脏的行李,/是我在一天的开始的全部收获/(我在他脸上看到某种若有所思的表情)
市区各主要马路,/像刚刚缠上绷带的手一样干净。/我在消逝的夜里带着某种凶恶的斗殴和药碘气味,/侧身拉起寒天里铅质的卷帘门。/一个死于外省的友人的脸,/突然出现一本书的封面。
这里直接写的是清晨在一家个体书店门口远方人问路事,间接写的是头天夜里发生的一场斗殴。既没有复杂、紧张而有序展开的情节,人物也失去了在传统叙事中的中心地位,不过场景的作用在诗中却膨胀起来,透过这样的平淡的生活场景,当代人在生活重压下的灰色心态展露无遗。
在90年代青年诗人的笔下类似的个人化的叙事,所占比重是相当不小的。其实,诗的写作,从来就是一种极富于个人气质的书写,总要打上个体的、私人的烙印。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与人的交流变得越来越不易沟通,诗人往往面向内心,同自我交谈,或与潜在的、隐匿的读者对象交谈,诗歌也变得越来越内倾。因而个人化写作是诗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保持写作的独立性与纯洁性所作的一种努力。何况,个人化写作,并不像一些人仅从字面上理解的那样,是与社会生活完全背离的。实际上,个人生活始终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细胞,正是无数的个人生活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整体,个人化写作与“自恋癖”、“自闭症”等是不宜划等号的。我们肯定青年诗人关注时下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关注国计民生,写出格局宏伟、富有社会意义的大制作,同时我们也尊重他们展示私人空间、保留个人化叙事的选择。那种动不动就以“脱离时代、脱离人民”来指责个人化写作的作法,是不足取的。
“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除去强调上述的个人视界中原生现实的实录外,还涉及多种多样的叙事方式与手段,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颇受读者欢迎的戏剧化的叙事。
西渡的《在硬卧车厢里》是他的诗歌写作由对纯粹抒情的迷恋转入对日常经验关怀的一个标志性文本。此诗的写作缘起是诗人在硬卧车厢里邂逅了一对陌生的男女。诗人把他观察的结果适当地加以调整和安排,用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写出了这首诗。戏剧的几个要素在诗中已基本具备。地点:开往南昌的硬卧车厢。时间:符合“三一律”的不超过一天。人物:男主角——一位民营企业家,女主角——一位图书推销员,还有一位作为这个事件的旁观者兼记录员的作者。情节:幕启时,男主角正在车厢里用大哥大遥控北京的生意,引起了邻座的女主角的注意,于是她说话了:“‘你原先的单位一定状况不佳/是它成全了你,至于我,就坏在/有一份相当令人陶醉的工作,想想/十年前我就拿到这个数’。她竖起/一根小葱般的手指,‘心满意足/是成不了气候的。但你必须相信/如果我早年下海,干得绝不会比你逊色!你能够相信这一点,是不是?’”这是一段放到戏剧中也绝不会逊色的台词,话中有话。女主角是一位有丰富经验的猎手,她知道如何吸引男人的注意。她不是那些青春浪漫的追星族,更不是为了金钱而随时准备投怀送抱的三陪小姐,她知道要夺去一个男人的心,首先要引起男人对自己的重视,因此她一方面先抓住男方的弱点:“你原先的单位一定状况不佳”,而自己则有一份“相当令人陶醉的工作”,从而制造了一种心理优势,告诉男主角:你可不要小看我!这一招果然有效,男主角先是“不失风度地道歉”,然后开始叙述他的奋斗史,他的失意、挫折,他后来的成功,他未来的抱负。此时女主角也改变策略,由开始的高傲与盛气凌人,变为温存、体贴:“几乎像一对恋人,他撒开一袋方便面/‘让我来’,她在方便面里冲上开水,/‘看你那样,就知道离不开女人的照顾。’”普通的动作,普通的对话,但后边有丰富的潜台词,作为旁观者的诗人不失时机地补上了:“如果把‘女人’后面的补充省略也许/更符合实际情况”。结局:“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城市/他们提前下了车,合乎情理的说法是/图书推销员生了病,因此男人的手/恰到好处地扶住她的腰,以防她跌倒”。据西渡本人讲,这首诗便是他目睹了上述景象后,就在硬卧车厢里写下的。在这里日常经验与诗贴得是那么近。而这一幕场景已足可以令我们体察到商品时代导致的人的道德标准的失衡与人性的扭曲。这首诗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方面是诗人对当下经验的批判性介入,另一方面则得力于诗人这种戏剧化的叙事策略。
如果说西渡的《在硬卧车厢里》是叙事成分的正剧化,那么在伊沙笔下,则更多的是叙事成分的喜剧化。这是他1995年写的《〈等待戈多〉》:
实验剧团的/小剧场//正在上演/《等待戈多》//老掉牙的剧目/观众不多//左等右等/戈多不来//知道他不来/没有真在等//有人开始犯困/可正在这时//在《等待戈多》的尾声/有人冲上了台//出乎了“出乎意料”/实在令人振奋//此来者不善/乃剧场看门老头的傻公子//拦都拦不住/窜至舞台中央//喊着叔叔/哭着要糖//“戈多来了!”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这首诗写了一幕发生在荒诞戏演出时的荒诞闹剧。此诗的前半部分是铺垫,也是造势。实验剧团在小剧场演出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这是正常的:左等右等,戈多不来,也是正常的,因为剧本就是这样规定的。可就在这一切似乎正常之中,反常的事件出现了:剧场看门老头的傻儿子冲上了舞台,哭喊着要糖。更令人惊异的是观众的反映:观众把这位大活宝看成是戈多,惊叹着说:“戈多来了!”并起立鼓掌。舞台上的荒诞与现实中的荒诞交织在一起,令人喷饭,同时也触发人们对这种“荒诞复荒诞,荒诞何其多”世界的思考。伊沙针对新生代诗人“语言实验”的经验与教训,提出:“我的实验是为阅读的实验,目的在于激活诗歌。”“我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无法‘阅读’。我深知这离我最近的问题正是指向未来的路标。‘为实验而实验’的写作年代已经结束了,当‘实验’不再作为一种姿态而被人摆弄的时候,真正的‘实验’才有了可能。 ”(注:伊沙:《为阅读的实验》, 见《诗歌报月刊》1996年第5期。)伊沙这种为阅读的实验,采取了多种表现方式, 包括这种高度夸张的、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对伊沙这类先锋诗人的作品,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可以这样评价,也可以那样评价,但不存在看不懂的问题。
由上述朱文、西渡、伊沙等人的诗,我们可以觉察到,“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这一原则的实施,已经使90年代诗人在语言观念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80年代的新生代诗人普遍存在一种“回归语言”的倾向。韩东提出:诗歌以语言为目的,诗到语言为止。其主旨是把诗从一切功利目的中解放出来,使其呈现自身。“非非主义”则提出“诗歌从语言开始”,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他们的“超语义”创作实验。尽管这些诗人“回归语言”的着眼点和操作手段不尽相同,但都视语言为诗的根本问题和归宿。这种“回归语言”的诗学观念给传统诗论以强烈冲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诗人通过形形色色的语言实验,也确实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诗歌文本,丰富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表现手段,使人们意识到,在回到语言本身的诗中,语言已不能再简单地视作某种意义的载体,而是一种流动的语感,读者虽难给予确切的解释,却可以像体验生命一样体验出它们的存在。不过任何理论都有它的局限与误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里,很多合理的东西很快就走向它的反面。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代诗人在“回归语言”的旗号下玩起了语言,他们打破了传统的诗语言与非诗语言的界限,在“实验”的旗号下,一些轻飘的语感训练和无聊的语言游戏纷纷出现,更严重的是对语言施展暴力,如评论家崔卫平所描述的:“从一种‘奇迹’的效果出发,任意改变一个词原先的用法,无端杀死一个词原先的含义,毫不相干的词语被粗暴地捆绑在一起,结果却并未赋予和产生任何新的含义,因此看上去狰狞可怖,花里胡哨,实质空空洞洞,毫无新意”。(注:崔卫平:《诗歌与日常生活》,见《中国诗选》第1期,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进入90年代以后,诗人们纷纷对这种情况进行反思,周伦佑说:“90年代诗歌写作则要打破这种对语言的神话,不是不要语言,也不是不重视语言,而是不再把语言看作神圣的中心而迷信它。破除‘语言中心论’便是把诗和诗人从最后一个‘逻各斯中心’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使诗纯然地面对自身”。(注:周伦佑:《新的话语方式与现代诗的品质转换》,《文论报》1993年7月3日。)翟永明也在一篇文章中说:“90年代以来,我对词语本身的兴趣超过了以往往何时期,当然,它们仍然贴近我内心的情感,我对纯粹的文字游戏一向不感兴趣,我所说的是过去不为我所注重的口语、叙事性语言以及歌谣式的原始语言,都向我显示出极大的魅力和冲击力,来自词语方面的重负(我对自己的某些局限)被逐步摆脱了,一切诗歌的特性以及这个时代的综合词语都变得极具可能性”。(注:翟永明:《面对词语本身》,见《作家》1998年第5期。)翟永明还说,她所期待的,就是“默默地、像握住一把火似的握住那些在我们体内燃烧的、呼之欲出的词语,并按照我们各自的敏感或对美的要求,把它们贯注在我们的诗里”。(注:翟永明:《面对词语本身》,见《作家》1998年第5期。)这些话也反映了90 年代相当一部分诗人在创作中的追求,不再热衷于去搞激进的语言实验,却力求用多种手段让语言更贴近自己的内心。
应该说,90年代的诗坛已初步展示了诗人面对语言的多种风采。
臧棣是80年代开始起步,到了90年代才产生重要影响的诗人。他把自己在90年代的诗合集命名为《燕园纪事》,便是颇有意味的。实际上在诗集中并没有一首题为《燕园纪事》的诗,可以让诗人借过来做诗集的名字。他之所以用《燕园纪事》命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燕园,表明了诗人求学与工作的环境,亦是他诗歌取材及触发灵感的最重要的来源。“纪事”与其说是诗体,倒不如说表现了他90年代以来的美学追求,那就是从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捕捉诗意,从日常经验中发现诗情。《燕园纪事》里收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诗或小叙事诗,它依然是一本抒情诗集,但是与追求“纯诗”理想的早期的臧棣作品大异其趣,而是注重日常生活经验的开掘。尽管是在燕园,但是臧棣的笔也不限于写未名湖、图书馆、教工宿舍这些与知识分子生活紧密相关的东西,他的视野要宽阔得多。小保姆、摇滚歌手、建筑工地的看门人、工程师、艺术家……等是他关注的人,过街天桥、施工现场、地下通道、露天舞会……等是他取材的背景。在《建筑工地的看门人》一诗中,臧棣这样描写这位看门人:
现在,整个黑暗之网中/只有我和他:两个因为特殊理由/而没有睡去的人。在由砖头和木板/搭起的简易工棚内,他的老婆在打鼾//工地进口处的一盏白炽灯/用这鼾声来给它自己催眠/而他对此置若罔闻。他穿着褪色的制服/他曾有过的经历使他不满意现在的工作//为运材料的卡车开门,巡视盗贼/可能渗入的角落:他有怨气,他讨厌黑暗/讨厌在黑暗中应尽的义务。他不理解/黑暗中也许会有更多的机会,他想像他老婆那样//在黑暗中酣睡,做各种各样的梦/他踢水桶,敲木板,让水龙头哗哗作响/把游戏机的声响开至最大:他的手指动得/如此频繁,甚至超过了在蜜月中的次数
作为90年代的诗人,臧棣将他的眼光凝聚到最普通的小人物身上:这位看门人由于对现在的工作的不满,所以借值夜班的时候撒气:踢水桶,敲木板, 让水龙头哗哗作响……这行为传达了他心理的不平衡。 90年代的社会心态,在最枯燥的生活场景中、在最平凡的小人物身人,被诗人艺术的眼光烛照无遗。就这样臧棣的诗与90年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比起他的前期作品,诗的语言品格也有所丰富。
当然,“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并不意味着只要那种白描式的叙述就够了。实际上,许多诗人也在尝试着把“身边事物”与隐喻、象征等诗性话语巧妙地结合起来。
作为朦胧诗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小斌,进入90年代作品不多,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这首《候车记事》:
我放下旅行包/在一棵高大的红枫树下等候汽车//有很多人看着我/一位好心的同志走过来/“同志,汽车站在那一边”//我内心微微一笑/其实那古老的站牌是我早已看见//那是一块新油漆的站牌/上面写有很多古老的地名/中国,我要去一个地方/我这个幻想家要去的地方/你神圣的站牌上也应该写上//我在这高大的红枫树下等候汽车/那边,雾花的青雾在站牌上弥漫/这边,我这棵红枫如同火炬在招展//红枫树啊/是我的站牌/我从这里转向未来
此诗以记事为名,而且确实也是从候车开始写起的。不过诗人不在那新油漆的站牌下候车,而偏偏在高大的红枫树下候车,这迥异常人的行为,足以启发人把“候车”与某种精神状态的东西联系起来。细味全诗,不难发现“候车”在诗中带有“期待未来”的象征含义,而红枫树也不再是一般的树,而成为导向未来的航标。诗人从现实生活的一个寻常细节切入,思路却从具体的候车行动中扬升起来,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梁小斌式的诗性思维模式,但就对纪实的强化而言,与前期完全建筑在象征意象基础上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作品已有了明显的不同。
再如刘玉浦的《刺猬级诗人戴月逃亡》,诗情的触发也是从身边事物引起的。诗人在小序中交代了写作缘起:“昨夜幸得一西山籍刺猬,个大肉肥。束于纸箱之中。早起见箱破绳断,纸箱又变成了纸箱”。本是刺猬逃亡,到了诗歌中,诗人代刺猬立言,刺猬便不再是原来的刺猬,而是与诗人二位一体,成为“刺猬级诗人”,于是顺理成章的,刺猬的逃亡也就不再单纯的是刺猬的逃亡,而成了诗人的逃亡。这便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暗示了90年代的某些诗人面临商品经济大潮和大众文化的冲击,而采取的“精神逃亡”的生存策略。
当我写就这篇90年代诗歌印象的时候,新年的钟声早已响过。望着台历上醒目的“1999”,我的心很难平静下来,常识告诉我,一个完整的时段的起迄与历史的转折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一个完整时段的起迄又往往会对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像百年起迄这样重要的时刻,不是每个人的一生都能赶得上的,因而必然会使人,尤其是对时光流逝最为敏感的诗人,触发丰富的诗情与无限的感慨。这些年一直在精神病院生活的诗人食指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写一首题为《世纪末的中国诗人》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年轻时付出十分惨重的代价
到中年做出难以想象的牺牲
谁知又遇上一场前所未有的
私欲和利已大作的暴雨狂风
那就让该熄灭的成为灰烬
该被吹散的不必留踪影——
而我却在贫寒中苦苦地
精心守护着艺术的火种
食指对诗的这种锲而不舍的追求,不仅是他人格的写照,同时也折射着世纪末每一个诗坛守望者的心态。因而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尽管90年代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潮流使诗人处于空前的窘境,尽管90年代的诗歌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执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诗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贴近,但愿我们也能主动去拥抱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