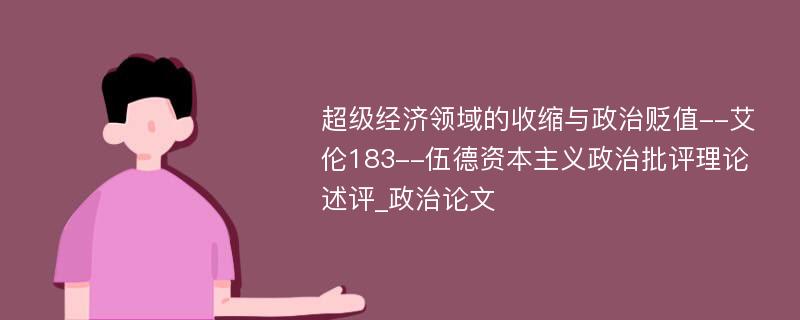
“超经济”领域的收缩与政治的贬值——埃伦#183;伍德资本主义政治批判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述评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伍德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位知名的左翼激进理论家,埃伦·伍德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历史的顶点。因此,她从多方面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深入批判。在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政治是一个重要关注点。伍德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这一命题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超经济”领域的变化,揭示了“公民社会”和“形式民主”背后潜藏的权力资本化的逻辑,并用“政治的贬值”这一结论洞穿了资本主义“超经济”产品丰裕的神话。 一、资本主义“超经济”领域的变化 伍德认为,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相比,资本主义最大的变化是占有剩余等行为不再采取政治强制的方式,从而使“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相分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分配、社会劳动和资源的配置、市场的运行以及所有权等完全是“纯经济的”,而不受“政治”力量左右。然而伍德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同“政治”的分离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即“经济”领域的分化意味着传统的榨取剩余那部分政治权力被转移到资本手里,而不是“经济”领域已彻底地、真正地“去政治化”。事实上,“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表明资本主义“超经济”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一)“超经济”领域的收缩 伍德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剥削与强制的分离导致了一些新现象:政治的公共功能更加突出,公民的政治权利扩大,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生活领域形成,等等。这些新现象给资本主义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超经济”领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强化。但是在伍德看来,这是一种严重的视觉误判。“如果说政治的自治,社会身份的公开,超经济产品的广泛分布是部分事实,他们实际上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并且是微不足道和矛盾对立的部分。”①实际的情形是,较之以前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的“超经济”领域非但不是强化和拓展了,反而是大大地收缩了。 根据伍德的分析,资本主义“超经济”领域的收缩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干预并压缩了“超经济”领域。一方面,“资本使私人获得了控制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同时把社会和政治责任让给了形式上独立的国家”②。另一方面,经济规则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方式牢牢控制了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要由市场逻辑严格地决定。”③“所有处于直接生产和占有之外以及处于资本家直接控制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服从于市场以及超经济产品商品化的规则。”④第二,资本主义时代政治的自治权比前资本主义时期削弱了。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意味着把原来的一些政治功能转到了独立的经济领域,政治和国家更明显地被特殊的经济需要和占有阶级的需求所支配。 可见,“超经济领域的收缩是资本主义经济剥削从超经济权力和身份中分离开来的一个不同后果”⑤。然而让伍德感到荒谬的是,“正是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贬低超经济产品价值的特征在表面上加强了超经济领域并扩大了超经济领域的范围”⑥。以至于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似乎在经济之外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生产有着自己专门的场所,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有严格的区分;司法和政治不再限制甚至基本不干预剥削。简言之,似乎在生产和剥削以外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广阔的生活空间,其中存在着同经济不直接相干的社会身份、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由此形成了一个广阔的“超经济”空间。按伍德所说,产生“超经济”领域被强化的错觉虽然荒谬,但并不足怪,因为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具有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意识形态神秘化面具背后的能力”⑦。她要强调的是这种错觉可能带来的危险:对于左翼来说,如果在分析资本主义时把这种表面现象当作一种真实的情形,那就等于“把障碍误认为机会”⑧,并在构造政治策略时“自拆台脚”⑨。 (二)“超经济”产品的广泛化 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令劳动大众获得了更多的“超经济”权利,“超经济”产品呈现广泛化的趋势。然而,资本主义“超经济”产品的广泛化是否代表了一种真正的社会进步,这是需要深度追问的问题。 伍德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占有权与“超经济”力量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超经济”力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就必然导致“超经济”产品的稀缺。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超经济”产品、特别是那些与公民权相联系的“超经济”产品,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分布得更加广泛。这种广泛体现在:摆脱了对占有者的人身依附,劳动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身自由;传统上规定的身份和法律的不平等被废除,劳动大众不再被排斥在公民权利之外;在统治者和服从者之间通过政治划分来体现特权和劳动分工已不再必要,尽管“经济”遵循它自己的规则,但民主可以被设定在形式上独立的“政治”领域内。总之,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的是,资本的剥削已不再与“超经济”身份、不平等或差异相联系,榨取剩余是发生在形式上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之间,而不以司法和政治地位的差别为前提。诚如伍德所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以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先决条件,没有规定的权利或义务,没有法律上的特权或者无资格。”⑩ 同前资本主义时代相比,资本主义“超经济”产品的增加无疑是较大的进步。对此伍德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她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超经济”产品的广泛化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首先,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占有被转移到经济领域,财产权和经济力量的作用凸显出来,自由、平等和其他公民权同剩余占有已基本没有关联。这就使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在不从根本上触动资本和劳动之间财产关系的同时,允许民众政治权利的扩大。其次,“资本主义对被剥削者的社会身份的结构漠不关心,这使它能够前所未有地丢弃超经济不平等和压迫”(11)。这种对“超经济”身份的漠不关心也使它能够非常有效而灵活地运用“超经济”身份作为意识形态掩护。如果说“超经济”身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突出的是剥削的关系,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典型地被用于模糊资本的主要压迫方式。再次,政治权利的增加也是大众长期不懈斗争的结果。资本主义不是从一建立起就自愿地把政治权利给予劳动大众。“只是经过长期的和很多受到抵制的人民斗争之后,这些权利才最终被赋予工人阶级。”(12) 然而伍德也提醒人们,超经济产品的广泛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使大众获得了彻底的解放,甚至连政治的真正解放都远未实现。事实上,资本主义是通过贬值的方式克服“超经济”产品的短缺的。“资本主义通过贬低这些超经济产品的价值,使得空前的超经济产品分配成为可能。”(13)以公民权为例,资本主义通过限制公民的权力来扩大公民的范围,从而使公民团体既包含精英又包含大众,但是他们的公民权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造成的公民权贬值是现代民主的一个基本特征”(14)。自由和平等也是如此。尽管劳动者在政治上摆脱了依附和被强制,但“纯经济”强制在他们的生活中却无处不在。因此,对于“超经济”产品的广泛化是不能过于乐观的。“如果我们忘记了他们公民权的历史前提是政治领域的贬值,是削减了公民权并将其原有的一些特权转给了私人财产与市场的纯经济领域(在那里,纯经济优势已经取代了司法特权和政治垄断)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新关系,我们就不能估量他们的得失。”(15)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在一个纯‘经济’权力代替了政治特权的制度中,公民权的含义是什么?”(16) 二、“公民社会”和“形式民主”:权力资本化的“超经济”装饰 专制政权对大众的统治罪恶深重,它所制造的等级和不平等也让社会丧失活力。因此,新的有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的过程中高举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旗帜,号召人们抵御国家压迫的危险。然而伍德认为,在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后,这些有产者虽然在形式上兑现了上述政治进步,却巧妙地抽干了其真实的内容。 (一)“公民社会”——资本掌控的逻辑 伍德指出,同资本主义特有的所有制相联系,现代“公民社会”代表着一种人类关系与人类活动分离的领域。它既不同于国家,又不同于家庭私人领域,而是“包含着除家庭私人领域和国家共同领域之外的社会交往的整个范围”,并且“更加明确地包含着一种包括市场的范围、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竞争场所在内的特殊的经济关系网”。(17) 从历史发展看,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的逐步确立,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赋予“社会”必要的权力以制约国家,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与此相应,“公民社会”的自治获得了统治者和国民的共同认可,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形式。这种新的社会关系形式将“许多曾经属于国家的强制功能”转移到由新的财产所有者掌控的“社会”领域,从而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 按伍德的分析,“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同隶属于公民社会的自由和体现在国家中的专制之间的对立相对应。“公民社会”的早期设计者们主张通过在“社会”内部组织和加强与国家相抗衡的力量,以抵御国家压迫的危险,并为国家行动设立一个适当的界限,因此“公民社会”观念凸显的是“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对立。后来,虽然“公民社会”包含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非常广泛的制度和关系,但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国家与非国家之间或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对立。“西方社会的一个首要特征是,它使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并因而有了一个政治自由的独特发展形式。”(18) 然而,当代“公民社会”的实际运行状况和效果如何?它真的只是为了抵御国家压迫的危险吗?关于这一点,伍德的认识深刻而全面。“‘公民社会’赋予了私有财产及其所有者一种支配人民及其日常生活的权力,一种众多专制国家都渴望拥有的、由国家执行而无人负责的权力。”(19)在这里,国家的一些强制功能以“私人”权力的形式得以持续:资本的逻辑掌控着一切,市场的强制力量空前强大且无所不在,它“使所有人类价值、活动和关系屈从于自己的规则之下”(20)。就此而言,不仅国家的强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公民社会的强制统治所取代,而且“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集中和浓缩”(21)。所以,“‘公民社会’不但构成了‘公共’和‘私人’之间的一种全新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私人’领域,该领域包括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共’存在及其自身压迫,一种独一无二的权力和统治结构,以及一个无情的系统逻辑”(22)。 伍德进一步指出,较之于国家的强制特性,“公民社会”似乎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这实际是一种严重的景观扭曲。这种扭曲淡化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私人”属性,掩盖了“资本主义自身特有的社会关系特征、特有的占有与剥削方式、特有的再生产法则以及特有的系统规则”(23)。因此,她强调,“公民社会”尤其是其当代观念潜藏着巨大的意识形态阴谋。这主要体现在:它通过强调国家压迫的教训,来遮蔽“公民社会”强制的危险,从而“削弱我们抵抗资本主义强制的能力”(24);通过把社会分解为没有中心权力结构、没有整体统一、没有系统强制的许多碎片,从而将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体统一性及其存在的问题有效地概念化;通过“将‘经济’包含在一个多样的非国家制度和关系的更大的领域之中”(25),“把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经济”)归纳为现代社会中多元而异质复杂的众多领域中的一个”(26),从而把人们的意识吸引到经济和剥削以外的宏大且分散的场所。“当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制度被简化为众多机构和关系之中的一种,在概念上等同于家庭或者自愿结社时,资本主义的总体逻辑和强制性权力就会消失。”(27) 伍德认为,当前的“公民社会”新概念也将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巨大风险。首先,它使人类解放被寄托于“公民社会”的自治之中,寄托于其扩张和发展之中,寄托于摆脱国家束缚及保护形式民主的努力之中。这不是在引导人们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在诱使他们去适应资本主义。其次,对左翼来说,把阶级淹没在诸如“身份”那样包罗一切的范畴之中,用不精确的“公民社会”概念取代社会主义,将使剥削和统治的关系再次趋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这“等于是向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神秘化投降”(28)。最后,“公民社会”可以被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和掩护物,而市场同其他分歧少的东西合在一起可以被用作一种明确的有吸引力的目标,诱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东欧,公民社会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从维护政治权力和文化自由到后共产主义经济市场化以及这些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每一个事件。”(29) (二)“形式民主”——“超经济”产品广泛化的海市蜃楼 民主的悠长历史传统最远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崇尚自由的雅典人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发明了民主概念,并赋予被统治阶级一种独特的公民身份。现代意义的民主则肇始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维护贵族特权、反对君主侵权而产生的“大众主权”传统中衍生出来的现代民主概念,历经新兴有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反复博弈、美国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劳动同资本的不屈斗争等,最终把古希腊的观念推向了一旁。 按伍德所言,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肌体内包含着自由主义的基因。当贵族统治和“超经济”的剥削模式被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取代时,“来源于传统特权的自由观念可能会继续保留一段时间以便适合于有产阶级的利益”(30)。虽然“设计它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创造的新的权力形式”,但“这些观念目前甚至可能会达到在公民与国家之间更加民主地交流的目的”。(31)所以,把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结合起来是资本主义的发明——“只有随着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出现,‘自由主义民主’的观念才能成为可以想象的”(32)。具体地看,资本主义之所以使自由主义民主成为可能,是因为它具备了这样的前提:“一方面,目前存在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其中‘超经济’的……地位与经济权、占有权、剥削和分配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另一方面,目前存在一个经济领域,该领域有其自身的、不依赖于司法和政治特权的权力关系。”(33) 同古希腊民主一样,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将公民身份从社会经济状况中分离出来,这让民主在政治领域的扩大成为可能。然而存在的重大区别是,两种民主在同经济的关系上有各自的特殊内容。在古代雅典,公民的权利不是由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民主的公民权意味着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超经济”的剥削——他们的政治参与也减少了他们所遭受的经济剥削。从这些意义上说,雅典的民主不是“形式”的民主,而是真实的民主。在资本主义民主制中,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决定公民的权利,因此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是民主的;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占有剩余的权力不依赖于司法特权或公民地位,经济“已经完全超出了公民权、政治自由和民主责任的范围并获得了其自身的生命力”(34),因此政治并不能直接影响或有效改变经济领域的状况。这就大大限制了民主的真实性。那么,这种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现代民主赋予自由的真正地位又如何呢?对此伍德也给出了最贴切的说明:“在一个法律或政治地位不再是我们生活的首要决定因素、我们的活动和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我们合法的政治身份范围之外的社会中,按照这些条件界定的自由所忽略的东西太多了。”(35) 所以,对伍德来说,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所破解的问题是极其有限的。它既“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强迫的全新领域,包括其从国家到公民社会、私有财产乃至到市场强制等众多权力的重新分配”;也“没有触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广大领域……这些领域是由所有权、市场‘法则’以及利益最大化原则支配的,而不是以民主的可说明性为条件”。(36)事实上,只有“使自由主义民主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才成了这种民主的“可说明性的范围”。(37)这样的民主当然仅停留在形式上,是缺乏社会含义的。 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地位,伍德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与‘形式民主’联系起来代表着一种进步和退步的统一,它既是对民主的加强同时也是对民主的贬低。”(38)具体而言,相对于缺乏公民自由、法律规则和代表原则的政治形式而言,资本主义“形式民主”当然是一种进步,但由于它在历史上和结构上是与资本掌控一切的逻辑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是民主理念之内容的减少。从实质看,“形式民主”真正维护的是经济领域的“民主权力”。对于资产者来说,保护这种“民主权力”的不可侵犯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对于劳动大众来说,经济领域的“民主权力”仍然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因此,“历史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可能属于民主的其他传统,属于被自由主义民主所遮蔽的传统,属于在其字面意义上是大众权力的民主观念”(39)。 三、资本主义“超经济”领域变化的多重效应与政治的贬值 (一)“超经济”领域变化的多重效应 资本主义条件下“超经济”产品的广泛化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众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利,但“超经济”领域的收缩使民众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等权利实质上相当有限。伍德因此提醒人们,资本主义“超经济”领域的变化具有多重效应,它带来了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公民身份和阶级地位以及国家和公民社会等方面的分离。 1.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的分离。平等是资本主义“超经济”产品的重要内容,它使公民身份与其社会经济状况得以分离开来,从而体现了资本主义进步的一面。但是在伍德看来,这样的平等是不彻底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是分离的:占有剩余的行为发生在经济领域,不直接依赖于政治权力;政治权利不能影响占有行为,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劳资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换言之,由于主要的生产者并非在法律上不独立或在政治上被剥夺了公民权,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和剥削与政治的平等共存。所以,“资本主义民主中的政治平等不仅能够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同时存在,而且还能使这种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基本保持不变”(40)。 2.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分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但是,由于被剥夺了劳动条件,他们不得不用其劳动力交换工资以获得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的生产者服从并独立于其政治地位之外的经济强制。……工人既服从于资本的权力又服从于竞争规则和利润最大化原则。”(41)可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雇佣劳动者被赋予了“超经济”领域的自由,但这种自由被资本的经济强制所湮没。这样,不仅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是分离的,而且政治自由还可能会掩盖经济上的不自由。 3.公民身份和阶级地位的分离。资本主义“超经济”产品的扩大使劳动大众拥有了公民身份,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存在的现实和被剥夺者的阶级地位。资本主义制度下公民身份和阶级地位的分离体现在:一方面,公民身份不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因而劳动大众享有大量的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占有剩余的权力不依赖于司法特权或公民地位,公民身份就不会直接影响或有效改变劳动者的阶级地位——“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即使在具有司法平等和普选权的情况下也能够继续存在”(42)。所以,资本主义时代公民身份从社会经济状况中的分离“也使得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与阶级不平等能够同时存在”(43)。 4.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分离。资本主义“超经济”领域收缩的表现之一是原有的一部分政治功能被转移到经济领域,从而使剩余占有同政治强制相分离,并把政治中的公共职能完全丢给国家。同时,资产阶级还创造了“公民社会”这一社会形式,以抵御国家的专制和强迫,由此出现了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分离。这一分离造成的结果是国家的强制、政策和行政职能的重新部署,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些重要部分的重新部署。“它必然伴随着国家的‘公共’领域与资本主义财产和市场规则领域的新的分工,其中占有、剥削与统治从公共权威和社会责任中分离出来……”(44)于是,“公民社会构成了一种社会权力的新形式,其中许多曾经属于国家的强制功能被转移到了‘私人的’领域,转移到了私有制、阶级剥削和市场规则之中”(45)。伍德指出:“在西方,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分离的确产生了自由和平等的种种新形式,但它也创造了统治和强迫的种种新方式。”(46) (二)资本主义政治的贬值 前资本主义时代政治权力对剩余占有具有直接支配作用,它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因而人们对政治权利的渴望热切,这就导致政治产品的短缺。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一个空前巨大的社会变化在政治领域发生——大众被赋予平等的公民身份,民主、普选、自由、自治等成为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资本主义似乎用魔法在一夜之间克服了政治产品的短缺。然而在伍德眼里,资本主义的这些创造并不神秘。她用“政治的贬值”这一结论洞穿了资本主义政治产品丰裕的神话。 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导致政治的贬值,这种贬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政治在社会中的地位看,经济领域的自治、资本力量的强大不光使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也使政治的自主权减弱。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和“政治”的分离、剥削从直接强制中的独立、国家公共职能的凸显,让一个独立的“纯政治”领域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含义。资本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即便不考虑它通过财产权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攫取的直接权力,人们也很容易发现,它通过使全部社会生活商品化,让市场需要统治整个社会,并支配劳动和其他资源的分配、生产和消费——已扩展到政治远不能对之进行控制的程度,更“践踏了我们对自治、选择自由以及民主自治的所有渴望”(47)。较之资本的强大力量,政治的影响力相当有限。当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服从于资本的需要时,政治的地位可想而知。 其二,从政治对大众的价值看,政治产品的广泛化并不代表政治对大众的真实意义同比增加。无需赘言,当“劳动大众”最终加入了公民共同体,传统的身份和法律不平等的消除,对于这些目前“自由而平等”的个体来说代表着一种进步;公民权的获得又赋予这些个体以新的力量、公正和权利。“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他们公民权的历史前提是政治领域的贬值,是削减了公民权并将其原有的一些特权转给了私人财产与市场的纯经济领域(在那里,纯经济优势已经取代了司法特权和政治垄断)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新关系,我们就不能估量他们的得失。”(48)与古代民主中的公民权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利所散发的光芒要黯淡许多。“因为当政治权力变得较少地排外时,政治权利也就失去了其大量的权力。”(49)“所以今天纯粹政治权利的扩张无法产生像前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同样的效果。”(50) 其三,从政治参与的效果看,“究竟资本主义是增加了抑或减少了我们管治自己,控制自己生活的权力呢?”(51)答案显然很明了。资本主义具有使民主政治远离社会权力中心的非凡能力。它采用代表制、普选制等政治设计,“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扩大公共领域中公民身份和行动之间的距离”(52),从而淡化政治参与的效果。例如,美国的“开国者”们就把代表制用作一种使人们远离政治的手段。 总之,尽管资本主义推动了政治产品的广泛化,以“公民社会”抵御国家的专制,用民主制度来促进自由,但在伍德看来,这些改变都是表面的,只有政治的贬值才是资本主义变化中实实在在的内容。 四、评价与结论 在当今批判资本主义的诸多理论中,伍德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视角独特,分析深刻,极富洞察力。这一理论包含多方面的积极因素。 第一,伍德以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为切入点去审视资本主义政治,这令其理论见解独到,极具说服力。应当说,伍德的批判是独到而犀利的。她能发现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多重效应、能揭穿资本主义政治进步的虚假性并解释得令人折服,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她找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这一准确的切入点。 第二,伍德从资本主义政治的贬值中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欺骗性,从而昭示了反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对于伍德来说,资本主义的民主、平等、自由等并不具有真正的进步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已令其失去了实质性内容。这样,伍德就透过资本主义政治的贬值洞察资本主义制度的欺骗性,将被巧妙掩饰的“剥夺”再一次暴露在大众面前。这样的分析揭穿了资本主义进步的虚假神话,从而昭示人们去反对资本主义。 第三,伍德关于“公民社会”和“形式民主”的分析敏锐而深刻,并由此说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这样的理论推进是合乎逻辑的。伍德发觉了“公民社会”中资本的逻辑掌控一切的秘密,并清醒地意识到当今“公民社会”理论中潜藏的意识形态阴谋,这无疑是极为敏锐的,也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她通过对“形式民主”的分析说明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必要性,由此导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这在逻辑上是严密的。 当然,伍德的资本主义政治批判也有不尽合理的地方。如伍德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的虚伪性是对的,但对其形式中包含的积极因素肯定不够。事实上,这种虚伪性并不能完全遮蔽资本主义政治哪怕是在形式上的进步意义。尽管资本主义离实质性政治进步还有一定距离,但其在形式方面的不少设计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毕竟,任何内容都离不开形式,好的表现形式或多或少总能促进内容的改进和完善。所以,伍德在这方面的批判显然不是很客观,立场上稍显偏激。又如,伍德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的局限性,坚持大众所受的压迫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样的分析不乏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缺憾,最明显之处就是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缺乏合理的估计,对统治者化解危机的技巧过于轻视,这也是其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再如,伍德对“公民社会”的批判过于强调其被资本掌控、为资本服务的一面,而对其社会积极意义显然估量不足。 毋须赘言,一种通过“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而改变了的剩余占有方式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它所依托的社会形式也必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当不少人沉醉于资本主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及其带来的解放时,伍德发现了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关于这个世界的现实和未来,她给我们的忠告是:“我们不得不从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汲取的教训是,一种人道的、‘社会的’、真正民主和平等的资本主义,是比社会主义还要不切实际的乌托邦。”(53) 注释: ①①[加拿大]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黄任译,重庆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77页。 ②同上书,第276页。 ③同上书,第276-277页。 ④同上书,第276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同上书,第278页。 ⑧同上书,第279页。 ⑨同上。 ⑩同上书,第205页。 (11)同上书,第279页。 (12)同上书,第199页。 (13)同上书,第279页。 (14)同上书,第208页。 (15)同上。 (16)同上书,第200页。 (17)同上书,第237页。 (18)同上书,第240页。 (19)同上书,第251页。 (20)同上。 (21)同上书,第252页。 (22)同上书,第251页。 (23)同上书,第236页。 (24)同上书,第239页。 (25)同上。 (26)同上。 (27)同上书,第242页。 (28)同上书,第259页。 (29)同上书,第241页。 (30)同上书,第229页。 (31)同上书,第229页。 (32)同上书,第230页。 (33)同上。 (34)同上书,第229-230页。 (35)同上书,第230页。 (36)同上。 (37)同上。 (38)同上书,第249页。 (39)同上书,第232页。 (40)同上书,第209页。 (41)同上书,第198页。 (42)同上书,第209页。 (43)同上。 (44)同上书,第251页。 (45)同上书,第250页。 (46)同上。 (47)同上书,第259页。 (48)同上书,第208页。 (49)同上书,第233页。 (50)《民主与资本主义:彼此是友是敌?——伍德(E.M.Wood)访问记》,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038610/discussion/16825899/. (51)同上。 (52)[加拿大]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15页。 (53)同上书,第289页。标签: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伍德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