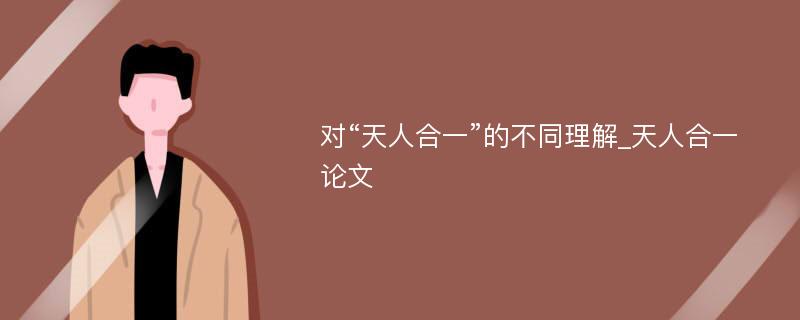
对“天人合一”的不同理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中,学术界对“天人合一”这一重要命题有不同的理解,且有争论,主要分歧有以下几点。
一、“天人合一”中的“天”,指的是什么?
第一种观点认为,“天”就是指大自然,而“人”即指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合一。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高级的物类。天地与人都是气所构成的,天地的本性与人的本性也是统一的,人民都是兄弟,万物是我们的朋友。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儒道墨等学派中都有。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思想中的“梵我一如”,与“天人合一”相同。宋代理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印度思想。于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宋儒理学中就占了主导地位。宋儒的代表人物是张载,他的《西铭》最完整最具体地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不否认人与自然的区别,但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不是敌对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1]
第二种观点认为,“天”是指封建伦理道德。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与“主客”、“自然和人”虽有部分重叠,但并不是一回事。“天”被神秘化、伦理化了,“人”也往往被剥夺了主体性,或被唯心地注解了。儒家“天人合一”论的直接目的是维护封建制度的神圣性,是要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作为经世的标准。无论是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还是《易传》的“天生神物,圣人则之”;无论是董仲舒的“人副天教”,还是程颐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都是以天人感应或伦理本质上的天人同构为共性的。这实质上是把封建人伦放大到天命的高度。“天人合一”强调的是封建人伦的客观必然性、永恒性,与“人和自然的统一”无涉。西方人站在当代文明的高度,可能从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到某些可以借鉴的因素,可能从中国“天人合一”论的保守性中得到某种启迪,以反省西方近代文明对“发展”的盲目崇拜,仅此而已。[2]
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观点相近。认为在古代,“天人合一”在理论和社会生活中虽然包含生态平衡,但并不是主要的方面,主要方面是服务于政教伦常,协调人际关系,建构社会秩序;而从生态平衡上讲“天人合一”,突出它的重要地位,是现代的观念。“乾卦所讲的是天道,君道,父道,夫道。坤卦所讲的是地道,臣道,子道,妻道。照易传这样一讲,好像四大绳索都是生于自然,因此是合理的不可改变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第355页)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周易》之所以能流传不衰,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应该倒过来讲,是“道不变天亦不变”,这个“道”就是封建统治之道。这个封建统治之道的稳定,是封建社会的经济要素没有变动的缘故。[3]
二、“天人合一”的命题是否矛盾?
一种观点认为是矛盾的。如果这里的“天”指的是自然界,那么,天的规则是自然法则,人的规则是社会规则,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就因为他突破了动物的界限,这才能使人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第一个起点就是天人不合一;天人不合一是人类诞生的撬板。所以,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很伟大,他还分辨了人与自然界的根本不同,在于自然界有“气”、有“生”,唯独没有“义”,而人不仅有“气”、有“生”还有“义”。“天人合一”是说,人也是自然的一员;“天人相分”是说,人是自然界中唯一不靠本能适应自然、而具有能动性以改造自然的动物。人类的进步、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动力来自“天人相分”,而不是“天人合一”。人在自然的怀抱里改造自然,使自然成为“属人的”存在,而不是倒过来,使人成为“属自然”的存在。[4]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矛盾。因为天人合一观念的核心是人顺应天道自然,而不是违背它。这不但不是说要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相反,要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中体现人与自然的一致与和谐。《荀子·天论》反对“从天而颂之”,主张“制天命而用之”,也是这个意思。古人对禹治水的评价是天人合一观念的典型体现。理解了这个,也就理解了天人合一。孔子、孟子高度评价禹治水的功绩,因为他顺应水势就下的自然规律,采用疏导水流使之注入大海的办法,解决了水患问题,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合一。鲧治水,则违背水势就下的自然规律,采取垒坝堵水的办法,使人与自然不合一,不和谐,所以人们对他持严厉批评的态度。可见天人合一观念不是要人做自然的奴隶,只是要人在对自然采取行动时对自然规律要顺,要合一,不要逆,不要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不宜对自然使用“征服”、“战胜”的字眼儿。[5]
三、能否以“天人合一”、“天人相分”来区别东西方文化?
一种观点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人类文化基本上有两大体系,即东方文化体系和西方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以古希腊、罗马为源头,中间有断层,一些阿拉伯国家保留了一些,直至现在形成以欧洲、美国为代表的文化。东方文化是以中国为主,加上印度、韩国、日本。东方西方思维方式不一样。西方是分析,越分越细;东方是综合,讲整体概念、普遍联系。天人相分(或曰主客二分)是西方文化的特色;天人合一(或曰主客混沌)是中国文化的特色。[6]天人相分唤起了人征服自然的能动性。这既是西方科技发达的文化根源,又是当代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文化症结。天人合一则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既是中国科技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又是中国文化在当代走向世界的依据。天人相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而天人合一的生命自觉却能使中国文化摆正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使精于器(科技)而疏于道(天理人伦)的西方文化得以拯救。西方文明之器与中国文化之道相结合,是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7]21世纪应该是以东方文化为主体的、融合西方文化的新文化。[8]
另一种观点反对这样分,认为这样分是一种任意的虚构。首先主客二分不能涵盖西方文化的特色。在把握主客关系问题上,古代东西方哲学及文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把近代从培根开始的科学主义精神当作主客二分的文化模式,以表征西方文化,是以偏概全,是对文化史的一种任意而粗鲁的肢解。它不能说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因素在西方文化史中的地位。第二,主客二分的科学主义态度,并不直接就是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文化症结。实际上,当资本家的发财欲使他掠夺性地向自然索取资源时,“主客二分”论当局限于哲人的书斋里,很难找到先聆听“主客二分”文化,再后学后用的征服自然者。反过来问:主客浑沌或天人合一就可以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吗?过度的放牧引起的草原沙化,过度的垦殖引起的山林水土流失,在亚洲美洲都存在。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史,并不能归咎为主客二分文化。在所谓天人合一的文化古国,那些急于脱贫的人何曾想到天人和谐的祖训而放慢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呢?第三,中国历代也有天人相分的观念。如春秋时期就有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之说,战国时有荀子的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之说,唐代有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和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之说。这些绵绵相续的天人相分的思想,并没有导致中国出现西方那样的近代科技和近代工业。[9]
(《哲学动态》1995年第8期)
主要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