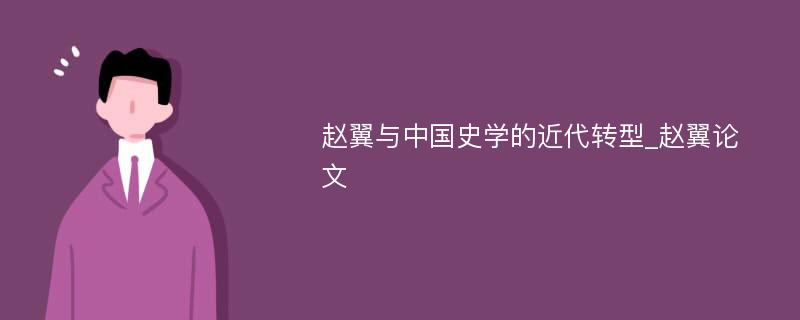
赵翼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新史学,并非如时下学术界普遍论定的产生于19世纪末西学东渐以后,而是晚明以来中国史学界自我发展和更新的产物。自李贽始,中国史学就开始挣脱儒家道统的囚缚,而日益增长着追求对历史真实之确切可靠的认知的近代性因素。到了乾嘉年间,终于产生了一部全面揭露和批判历代“正史”之作伪的史学巨著——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它标志着中国史学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方法论上都已经远离了孔子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的传统,而近乎达到了以求真为第一要务的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水平。
本文拟从研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入手,辅以赵翼的其他著作,从史事、史法、史论三方面来论说赵冀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贡献。
一、揭露历代正史之作伪
赵翼对于历史研究的最大贡献,也是他的史学考据的最大特色,是全面、系统地揭露历代“正史”的作伪。他告诉人们,不仅历代的所谓正史作伪,而且作为正史之依据的历朝“实录”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实录。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不仅需要学者有渊博的知识、非凡的史识,更需要学者有积学求真的勇气和无所畏惧的胆略。赵翼不仅有学、有识,而且有胆,所以才能写出《廿二史札记》这样一部可以说是专门揭露历代“正史”之作伪的史学巨著。
赵翼论史,最重求真、求信。他把真实性看作是史学的生命,所以拒斥一切以虚伪的道德言辞和政治实用主义的需要来隐瞒、歪曲和篡改历史的行为。因此,他对孔子作《春秋》所开启的“为尊者讳”的“掩护之法”颇有微词,对陈寿作《三国志》以来被修史者“奉为成式”的“一定书法”更深致不满。他批评说: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方法。……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
对于被陈寿《三国志·魏志》掩盖的历史事实,赵翼一一加以揭露。如齐王曹芳被废,全是司马师一手策划,而太后不知,然而“《魏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又如高贵乡公之被弑,乃司马昭一手策划,而《三国志·魏志》则伪造了一份太后“言高贵乡公之当诛”的诏令。(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陈寿固然可以“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来辩解,然而对于前一个朝代的曹魏之事,陈寿也是百般回护。如曹操东征徐州,“所过无不屠戮,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而陈寿作《陶谦传》则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为徐州太守陶谦杀害,故曹操志在复仇,而事实上杀害曹嵩的乃是投奔了东吴的张闿,非陶谦所谋。陈寿乃“故坐谦以杀嵩致讨之罪”,而为曹操掩盖罪恶。此外如《华歆传》,绝口不提其奉曹操之令“入宫收伏后”、使伏后惨死于暴室之事,《孙资刘放传》硬把助司马懿弄权的大奸大恶之徒写成正人君子(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如此等等,把陈寿迎合皇权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而肆意剪裁、歪曲和篡改历史的证据——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对于李延寿所修撰的《北史》,赵翼亦指出其“多回护之处”。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条中,赵翼指出;“孝明帝之崩,本胡太后倖臣郑俨、徐纥所为,魏收书及《北史》本纪皆不见其迹”。(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在《北史全用隋书》条中,赵翼更明白地指出,《北史》“于隋则全用《隋书》,略为删节,并无改正,且多有回护之处。如隋文帝之篡,《隋书》本纪既循历代国史旧式,叙九锡文、禅位诏,并帝三让乃受,绝不见攘夺之迹矣。《北史》亦一一照本抄誊,略无一语差异,只删去九锡文以省繁冗而已。”(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北史》不但为隋文帝掩饰攘夺之迹,而且还在《文帝论》中歌颂隋文帝“树基立本,积德累仁”。对此,赵翼谴责道:“隋文以诡诈攘位,有何积德累仁耶!”(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
《北史》非信史,《南史》亦非信史。“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所不同的是,南、北史为避繁冗,仅存其一二诏策。又: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盖因“南北交兵,各自夸胜讳败,国史固各记其所记。延寿则合南北皆出其一手,惟恐照本抄誊,一经校对,则事迹多不相符故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对于《旧唐书》的真实性,赵翼亦提出了颇为有力的质疑;对于其中的明显的隐瞒史实和作伪之处,亦一一予以揭露。在赵翼看来,历代官修的所谓“实录”、“国史”,没有不作伪的。他在《廿二史札记》卷十六《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中说:
若实录、国史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
例如,皇太子李弘乃是被武则天毒杀,章怀太子李贤也是被武则天迫令自杀,《旧唐书》皆隐而不书。白马寺僧薛怀义为武则天宠幸,被任命为行军大总管,后因其横恣杀之,《旧唐书·武后纪》竟一字不提薛怀义。张柬之等人被武三思诬陷至死,《旧唐书》中亦不书。穆宗以下诸帝皆宦官所立,《旧唐书》本纪亦绝不书,此本纪之回护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至于列传中的隐瞒作伪之迹,就更不胜枚举了。例如《李辅国传》,不载唐代宗派人深夜将其刺杀之事,但云夜盗入其家杀之;《鱼朝恩传》不载帝使人擒缢之事,但云自缢死。“盖当时朝臣本以为盗杀及自缢,故国史从而书之,此又列传之回护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宋史》的真实性,赵翼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大奸大恶……固不能讳饰,其余有过必深讳之,即事迹散见他人传者,而本传亦不载。有功必详著之,即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而苟有相涉者,亦必曲为牵合。”(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为了纠正《宋史》的失实之处,赵翼专门写了《宋史传附会处》条、《宋史数人共事传各专功》条、《宋史各传错谬处》条、《宋史列传又有遗漏者》条等等,对《宋史》的失实处一一予以揭露。
《明史》是清朝政府编撰的,赵翼身处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虽然不可能完全直言无忌,但仍然对《明史》的回护失实之处多有揭露。如明太祖疑忌徐达、刘基之事,《明史》不载,赵翼根据史实指出“帝于达、基二人疑忌可知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宋纳任国子监祭酒,“极意严刻,以称上意,监生自缢者月不乏人,死必验视乃殓,其酷甚于周兴、来俊臣”,然《明史·宋纳传》绝不提及。张辅随英宗北征,逃归后自杀,而《明史》却说他死于土木之难。杨廷和之入阁,乃是由于宦官刘瑾之力,《明史》对此绝不提及,反而把他写成刘瑾的政敌,(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如此等等。乾嘉年间,一般读书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而赵翼竟敢于揭露当代官修史书的作伪,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二、辨析真伪之方法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赵禹在《廿二史札记》中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历代官修史书的回护作伪失实之处,而且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然而,赵翼依据什么来确证历代官修史书作伪失实呢?这就不能不论及他的史学方法了。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小引》中说:
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
诚然,把历代官修史书的本纪、列传、表、志参互勘校,以发现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确是赵翼考辨史实真伪的一个重要方法。本纪中对帝王的恶行予以隐瞒,可以在后妃、臣僚的列传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此一列传的失实之处,又可以借助其他的列传来予以纠正。将本纪与列传、列传与列传的记载反复进行比较、辨析,总可以得出一些比较接近于事实真相的结论。例如,关于隋文帝之死和隋炀帝继位的情节,本纪中写的全是谎言,说什么隋文帝临终与百僚辞诀,握手欷歔,且有遗诏称“恶子孙已为百姓除去,今嗣位者乃好子孙”等语,“一似凭几末命,寿考令终,并非遭害者”,隋炀帝谋害其父及矫诏即位之事,绝不见形迹。仅仅在《宜华夫人传》中略露端倪于隐约之间,然亦未尝直书。赵翼将《隋文帝本纪》与《宜华夫人传》参互比较,发现二者之记载明显自相矛盾,经过仔细求证,据实恢复了隋炀帝弑父篡位的历史真相。又如,《宋史》的列传,在传主的本传中往往“详著其善”,而将传主的恶行零零散散地写在其他人的列传中。对此,赵翼仿照吴缜作《新唐书纠谬》的方式,不旁采他书,仅就《宋史》中的自相抵牾者,抉摘数十条以资辨正,内容涉及宋代的数十位重要人物。
然而,赵翼使用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对正史的纪、传、表、志的参互勘校,而且还包括他所极力掩饰的据稗乘脞说以驳正史之讹。生在文网极密的时代,他不得不对自己采用的这一方法有所掩饰,在《小引》中说自己“不敢据稗乘脞说以驳正史之讹”。冠于《廿二史札记》卷首的《小引》之所以要掩盖这一点,乃是为了迷惑清廷的文化特务的,而这种自我掩饰的门面话与书中的内容相对照则绝不相符。
事实上在《廿二史札记》中,赵翼经常采用依据私史或野史资料“以驳正史之讹”的方法。在这部书中,赵翼正《三国志》之误,依据的是《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世语》、《魏末传》等书;正《旧五代史》之误,依据的是欧阳修私撰的《五代史记》(后人称之为《新五代史》);正《明史》之误,依据的是王圻的《稗史汇编》、王琼的《双琼杂记》等书。例如,关于魏文帝曹丕的那位甄夫人的死因,陈寿的《三国志·魏文纪》但书夫人甄氏卒,绝不见暴亡之迹”,而赵翼则依据《汉晋春秋》,指出甄夫人乃是因为曹丕宠信郭后及顾、阴二贵人,以至于死,殡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可见甄夫人乃是被杀。(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对于高贵乡公被弑之事,赵翼指出:“此事见《汉晋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语》、《魏末传》,是司马昭实为弑君之首。乃《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司马)昭奏,……转似(司马昭)不知弑君之事,而反有讨贼之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如此等等都是据稗乘脞说以驳正史之讹的显例。在官修的所谓“正史”与学者私人修撰的史书两者之间,赵翼更相信私家所撰的史书的真实性。他强调指出:“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私史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据实记载为官修史书所隐瞒和歪曲的历史事实,它是与官方话语不同的民间话语,是学者们赖以不朽的“一家之言”;如果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们照搬官方话语,“依样葫芦,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之言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在赵翼的诗作中,更完全抛弃了所谓“不敢”据稗乘野史以驳正史之讹的掩饰,鲜明地提出了史策未必真而传闻未必伪的观点。他以自己的切身体验证明,所谓“青史”的真实性根本就是靠不住的,其《后园居诗》之五写道:
有客忽叩门,来送润笔需。乞我作墓志,要我工为谀,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吾聊以为戏,如其意所须。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此文倘传后,谁复知贤愚。或且引为据,竟入史册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注:《瓯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710、392页。)
这与其说是一首诗,毋宁说是一篇以诗说理的史论。那个时代的很多文人学者,或为了生计,或囿于人情,不得不写谀墓之作。而这些谀墓之作,大都与事实有很大出入,赵翼由此联想到,后人依据这许许多多的墓志铭而作的史书,又有几分真实性呢?由此得出了“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的结论。这在当时真可谓是震聋发聩之论。他把这一观点运用于《宋史》的辨伪,指出《宋史》之所以不可尽情,原因之一就在于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
他看到历代官修正史之所以不可尽信,除了出于政治伦理的原因而歪曲历史外,政治腐败所造成的史官之人格卑下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史官们往往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褒贬之权来谋取私利,从而导致史书失实。对此,赵翼亦据实予以揭露。例如他认为《魏书》之所以是“秽史”,除了“趋附避讳”以外,还在于史官魏收在修史时接受贿赂、搞有偿修史:“《北史》魏诸臣传,多与魏收书相同,惟《尔朱荣传》,当时谓荣子文畅遗收金,请为其父作佳传,收论内遂有‘若修德义之风,夫韦、彭、伊、霍斯何足数’等语。”(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由此看来,判别史书记载之真伪,除了必须考虑政治利益的因素以外,史官人格之高下也是判别其笔下的历史记载是否真实可信的一个重要因素。
赵翼的《咏古》诗又云:
闲翻青史几悲凉,功罪千秋少尺量。(注:《瓯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710、392页。)
煌煌青史的真实性既不那么可靠,那么,又如何衡量千秋功罪,又如何能够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那么,又该到何处去寻找历史的真实呢?赵翼除了就正史之纪、传、表、志参互勘校以发现出隐瞒了的历史真相,除了据私史和野史资料以驳正史之讹外,更把目光投向了民间传闻,认为正史既然可以作伪,那么民间传闻倒反而有可能存真。他在《关索插枪岩歌》的结尾处感慨地写道:
呜呼!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注:《瓯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710、392页。)
这在当时真是十分大胆而新颖的议论,一种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进步倾向的议论!当然,赵翼并没有说凡传闻皆真,他所说的具有真实性的传闻,不仅有历史遗迹作为佐证,而且可以借助于理证来说明其不悖于情理。他考知随诸葛亮南征的关索其人的存在,尽管关索其人不见于正史的记载,但赵翼仍认为民间关于关索的传闻是确实可信的。这一结论的作出,就是把民间传闻与历史遗迹的考察和揆诸情理的理证相结合的结果。
三、寓于史学考据中的进步思想
一位历史学家,只要他不再为专制统治者歌颂升平、粉饰黑暗,而是致力于拨开重重叠叠的迷雾去揭示历史的真相,那么,他就毫无疑问地是一位具有科学思想和进步倾向的历史学家,——反映历史前进方向的进步思想也就寓于对于社会历史之真实的揭示之中。即使史学家并不明白地说出他的思想倾向,读者也会从他对历史真相的揭示中看出他的思想倾向。何况,作为一位有真性情的历史学家,纵然客观环境再严酷,也不可能把他的思想感情完全窒息,总会在他的著作中有所表现。赵翼正是这样的一位通过揭示历史真实来表现思想倾向、寓思想于考据之中的进步学者。
赵翼是通过历史考据来表达其反对专制暴政的思想的。对于专制政治祸国殃民的本质,赵翼有很深刻的认识。《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分封宗藩之制》条,揭露明代各地的藩王强占民田民宅、强抢民间女子、侵夺国税、滥杀无辜、藏匿亡命,甚至养群盗劫财江湖间的罪行。卷三十二《遣大臣考察官吏》条,据陶宗仪《辍耕录》,揭露奉命考察官吏的大臣多挟势取贿,以至民谣曰:“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又重。”又引永乐年间邹缉之言:“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养活之计,有司奉承惟恐不及。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贿赂。”又引其后梁廷栋之言:“巡按御使之弊,盘查访缉,馈遗谢荐,有司所出,多者二三万金。国家多一巡方,天下加派百万。”(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明初吏治》条说“嘉、隆以后,吏部考察之法徒为具文,……举劾惟贿是视,而人皆贪墨以奉上司,于是吏治日偷,民生日蹙,而国亦遂以亡矣。”(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这段话对明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的揭示十分深刻。专制官僚体制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
对于专制法律的残酷性,赵翼亦通过考据予以揭露和抨击。《廿二史札记》卷十四有《后魏刑杀太过》条,后有按语,考证族诛之法之起源和变迁。他指出。族诛之法,本起于秦,一人有罪,延及三族,此三族乃指父族、母族、妻族。“汉高祖使萧何定律,有夷三族之令。……至魏晋之际,益惨酷无人理”,乃至姑姨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顾炎武认为以父、母、妻为三族,始于晋朝的杜预。赵翼订正了这一说法,并借此以批判专制暴政之酷虐,指出:“然一人有罪,害及无辜,秦、汉以来,以此法枉杀者不知凡几,又况后魏之诛及五族耶?”(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有《五代幕僚之祸》条,卷二十六有《秦桧文字之祸》条,卷三十二有《明初文字之祸》、《明初文人多不仕》条,都是对历代专制暴政迫害知识分子的抗议。特别是对宋明以来专制统治者大兴文字之狱、以思想言论治罪的专制暴政的抗议。在《五代幕僚之祸》条中,他揭露了五代时那些拥兵自重、残民以逞、实行封建割据的武夫们如何“恃权任气,又往往凌蔑文人,或至非理戕害”的事实,感慨地写道:“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秦桧文字之祸》条云:“秦桧造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风望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当时因语言文字稍触其忌而横遭诬害者不计其数。“桧又疏禁野史,许人首告,并禁民间结集经社。……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明初文字之祸》条云:“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赵翼根据《朝野异闻录》、《闲中古今录》等野史笔记,一一予以揭露。赵翼揭露暴君奸臣之所以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或是因为其自身学问不深,所以对知识分子心存疑忌,如明太祖朱元璋;或者是因为自身有不可告人的罪恶,怕知识分子予以揭露,如秦桧大兴文字狱,禁野史,禁民间结社,都是害怕知识分子们将其罪恶大白于天下。赵翼身当清朝政府大兴文字狱的年代,有理由认为他对历史上文字狱的揭露是针对满清王朝的。
中国传统政治,是以维护专制皇权为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一姓之兴亡”高于“生民之生死”。然而,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李贽公然为历事四姓的冯道翻案,认为冯道善尽“安养斯民”之责。王夫之更鲜明地提出了“一姓之兴亡,私也;生民之生死,公也”的命题,以人道主义为政治伦理的至上原则。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曲折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有《张全义、冯道》条,虽然该条开始时斥此二人历事数姓君主,然而以下的文字却是为此二人翻案的:“盖五代之乱,民命倒悬,而二人独能以救时拯物为念。除本传所载,不必再述外,其见于他书及别传者:全义事朱梁以免兵革,招复流亡,使得仰父俯子。”(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对耶律德光则言,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论者谓一言而免中国之人夷灭。在汉祖时,牛皮禁甚严,匿者死,有二十余人当坐,道力争得免。……是道之为人,亦实能以救济为心,公正处事,非貌为长厚者。统核二人之素行,则其德望为遐迩所倾服,固亦有由。至于历事数姓,有玷臣节,则五代之仕宦者,皆习见以为固然,无足怪。”自晚明李赞在《藏书》中为冯道翻案以来,这是笔者所见到的又一篇为冯道翻案的文字,其中体现着以人民的福祉为至上的观念。
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四《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条中,赵翼还以欣赏的笔调,借用野史笔记的资料描述了明代中叶“每出名教外”的傲诞士风。他写道:“《明史·文苑传》,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乃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文征明书画冠一时,周、徽诸王争以重宝为赠。宁王宸濠慕寅及征明,厚迎延,征明不赴,寅佯狂脱归。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抵应,分巡者窘而去,于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此等恃才傲物,跅
弛不因,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注: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2、123、124、124—125、272、273、277、275、345、347、347、500、724、724、124、341—342、273、460、464、763—764、760、345、476、566、586、742、783—784页。)这种新兴气象,就其蔑视中古教条、崇尚艺术,以及王公贵人或尊重和推崇艺术、或附庸风雅的情形来看,很像是意大利佛罗伦萨诸城文艺复兴时代的状况。赵翼对历史上知识分子受迫害的时代无不加以谴责,独心仪于明代中叶以后那种有利于知识分子张扬其个性的社会氛围,由此亦可见他的思想倾向。
赵翼的史论还涉及思想史领域。由于他具有科学家式的缜密和严谨,又具有诗人的性灵,所以能敏锐地发现程朱理学在学理上的谬误,提出超迈前人的新见解。其《檐曝杂记》卷五中的《僭删朱子中庸首节章句》条,就是一篇从学理上揭露朱熹学说之谬误、进而明辨人性与物性之区别的哲学史短论。在这篇短论中,赵翼敏感地意识到,程朱理学在学理上的一个重大谬误,就是把人性混同于物性。按照朱熹的“理一分殊”的观点,不仅人具有健顺五常之性,而且这一健顺五常之性也流行于狭义动物界中,天道与人道是合一的,这就有把禽兽之性等同于人之性的嫌疑。而赵翼则以朴学家的“察分理”的思维方法,注重考察人性与狭义动物界芸芸万类之特性的区别,强调“五常之德”是人所特有的,必须把人性与物性划清界限,并且据此批评朱熹“语多窒碍”。(注:《檐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4—95、36页。)这是赵翼的一大特识。当然,在赵翼以前,王夫之就已提出了“天道不遗于禽兽,而人道则为人之独”的命题,但王夫之的著作在乾嘉年间尚未大行于世。没有证据表明赵翼读过王夫之的著作。
赵翼在北京时,通过与在朝廷任职的西方传教士接触和到京城宣武门的天主教堂参观,亲身考察西洋的天文历法、音乐及望远镜、自鸣钟等,为之大开眼界,他在《檐曝杂记》卷二中写道:“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注:《檐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4—95、36页。)由此亦可见,赵翼的思想,已经初步突破了民族的狭隘性和片面性,是一位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成就的学者,一位初步具有世界眼光和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学者,一位初具现代意识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