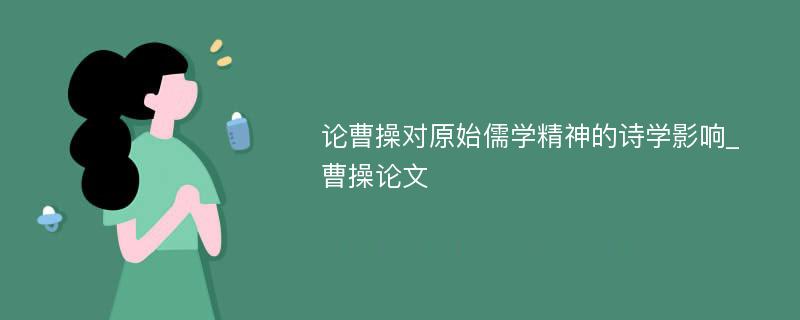
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的诗论文,原始论文,精神论文,论曹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曹操诗歌在中国诗史上的最大价值是突破了两汉经学的樊篱,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于诗歌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国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
关键词 曹操 原始儒学 天下意识 忧患意识
归根结底,诗人的地位取决于他给流变的诗史所注入的新内涵。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原始儒学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曹操诗歌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突破了两汉经学的樊篱,全方位深层次地诗化了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意识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壮丽诗篇,从而,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
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诗的天下意识
众所周知,儒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众多的流派。夫子之道以何统而贯之,迄今聚讼非一。笔者认为,若用一语来概括原始儒学之基本精神,只能是“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在原始儒家的理论中,修己是条件,安百姓是目的。“安百姓”又称平治天下。平,即平暴除乱,安定社会秩序;治,即治理疏导,使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之路。每一位“士”、“君子”都应该具备“修己以安百姓”的品质。为了“修己以安百姓”又必须具备两种相应的精神风貌:一是天下意识,二是忧患意识。是否具备此两种精神乃是区别君子儒与小人儒、志士之仁与匹夫匹妇之仁的根本标志。〔1〕曹操诗歌便是此两种精神风貌的艺术性再现。
天下意识即是以天下为己任,自强不息,日新不已的精神。曹诗的天下意识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以平治天下为己任。
曹操早期对汉室抱有幻想,入仕之初,他打击浊流恶势力,上书为党人领袖请冤。后来,他目睹了东汉政权的腐朽,逐渐认识到汉不可为,于是利用自己日隆一日的政治军事权力,走上了重造天下之路。我们认为,在曹操的思想中,儒学占据主导地位。有时曹操虽以两汉经学叛逆者的面貌出现,但其精神在本质上却走向原始儒学人文精神的回归。〔2〕
曹集中流布最广、堪称压卷之作的是《短歌行》“对酒当歌”。陈祚明云:“此是曹孟德言志之作”(《采菽堂诗集》卷5); 张玉谷云:“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古诗赏析》卷8)皆深得诗人之旨。这首诗之所以撼动人心,不仅在于它吟唱出了生命如露般的忧思,还在于它坦露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的胸怀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抱负。如果只有前者,那么诗人与《古诗十九首》中的沉沦颓废情调无以区别。因为有了后者,才使诗人生命苦短的悲哀不再暗淡;因为有了生命苦短的体认,乃使诗人一统天下的壮怀更显慷慨激烈。“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诗人之理想,是诗人之追求,是诗人精神世界之写照。《易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斯语最足以表征原始儒家的人生态度。能够与天地合其德的人,应当像日月星辰那样,健运不已;像天地万物那样,生生不息。因而,人生而在世,应当自觉自愿地承担起改造世界、治平天下的重任。曹操说过一句令腐儒吐舌的话:“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人或以此认定老瞒之狂妄,我却以为此语不仅符合历史真实,亦契合儒学之义。孟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下》)据此可证,具有强烈的自信心乃是原始儒学崇高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必然产物。
赤壁之战败北后,曹操见孙刘联盟一时难以攻克,转而经营北方。日月迅迈,老之将至,眼看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难以完成统一大业,于是,他写下了令后世慷慨之士击节不已的《龟虽寿》。诗中,他把自己比作伏枥的老骥。老骥之志仍在千里,垂暮的烈士仍然不失英雄本色。
显然,终其一生,曹操从未放弃平治天下的责任与使命。
其二,以平治天下的历史人物为楷模。
曹操所歌咏的历史人物以《短歌行》“西伯周昌”最为集中。诚如陈师贻焮先生指出:“他将对这几位古人的赞颂写在《短歌行》中,除了有邀誉、辟谣的现实政治意义外,也是他英雄怀抱的抒发。”〔3〕按之于《论语》,原来,其中的几位历史人物都是经过孔子所推崇或肯定的。特别是周文王更是儒家所谓的“圣人”。孔子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矣。”(《泰伯》)此诗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将如此多的受孔子肯定的历史人物写进一首诗中,予以热情地歌颂,是史无前例的;将孔子的语录和思想化为诗的语言,并在其中融入自己的热诚,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此两点充分表明:曹操深受孔子思想影响,志在以周文王、齐桓公等人为楷模,创造出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
需要辩明的是,后儒对曹操诗中称颂、比拟周文王、周公之语的诘难与诟病。朱熹云:“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朱子语类》卷140)刘克庄云:“身为汉相, 而时人目以汉贼,乃以周公自拟,谬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73)……朱氏诸儒不是以民心的向背为准则,不是从汉魏之际历史运作的大势出发,而是依据汉儒所制定的封建伦理纲常来评价历史人物,所以视操易代革命为奸贼之篡逆,视操称颂儒家圣人为遮人耳目之伎俩。我们认为:汉室失德日久,早已名存实亡;曹操集团统一北方,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在曹操统治期间,政治较为清明,社会风气大有好转,阶级压迫有所减轻。曹操的统一大业是进步的历史举措,曹操重建天下的行动符合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论,曹操的行为足以与周文王、周武王推翻暴殷、重建天下之事业相提并论。所以,曹操平治天下的行动应该予以肯定。〔4〕而曹操对周文王、周公等人的歌颂,正表现了他拯世安民之志。其三,以开创太平世界为终极目标。
原始儒家“修己以安百姓”,意在创造一太平世界。此太平世界分为两个阶段:“王道之始”(见《孟子·梁惠王上》)是其初级阶段;“大同”世界(《礼记·礼运》)是高级阶段。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以诗的形式出现在曹操的《对酒》中。本诗“采用颂的形式,模拟躬逢其盛者的口吻,以极大的热忱,讴歌太平时代的终于到来,从而表达了诗人颇带浪漫色彩的政治理想。”〔5〕试将《礼运》中的“大同”世界、孟子的“王道之始”与曹操的“太平时”予以比较,其相似之处在于:政治清明,人民知礼守法,安居乐业。五谷丰登、物产丰富,人民无养生丧死之憾;社会秩序安定,窃贼不作,路无拾遗。人与人之间友善和睦,老有所终,幼有所长;从三者对比中可以看出《梁惠王上》与《对酒》所表现的是有阶级有差别的初级社会;《礼运》描绘的乃是平等自由而泛爱众的公天下社会。曹操理想社会形态与儒家理想社会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与《对酒》类似的还有《度关山》一诗。此诗劈空提出:“天地间,人为贵”。标明曹操对人的重视,此与原始儒家人与天地参的观念一脉相承。他主张“立君牧民,为之轨则”,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正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再现。民本思想固然不同于今日的民主政治,它是以君为本位的。所谓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的重心在于存社稷、安国家。但在封建时代,这种思想自有其积极意义,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重视民的利益,较之于扰民、害民的弊政毕竟是一种进步。曹操对君民关系的认识,基本上符合儒家传统政治思维模式。
二、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曹诗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6〕忧患意识是伴随着天下意识而产生的。《易经·系辞下》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耶?”首次明确地揭示了忧患意识与政治的联系。《诗三百·国风·黍离》抒发了下层士人在西周故宫墟址上所产生的黍离之悲,此亦是忧患意识的表现之一。到了孔孟,进而规定了忧患意识的内涵:一是忧患的超越性:“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只有摈弃了物质享乐层面的忧患才可称忧患意识;二是忧患的长期性:“君子有终身之忧”(《孟子·离娄下》)。忧患意识并不是一时一地偶然兴起的,它伴随着士人的终身,“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范仲淹《岳阳楼记》)终身没有不忧患之时;三是忧患的广泛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忧患意识不是为了一己之忧,也不是为了一个家族、一个政治集团之忧,而是为了天下之人、天下之事。
曹操诗歌感情沉恻,悲笼域内,强烈表现出作者的忧患意识。曹诗的忧患意识,向外表现为忧国忧民;向内表现为忧自己年寿不永,无法完成统一大业。
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突出反映在“诗史”性作品中。《薤露行》、《蒿里行》乃“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卷7)。 此两篇前后相衔,可视为汉末战乱诗史的上下篇。上篇从汉室“所任诚不良”起笔,写了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因犹柔寡断,反遭杀身之祸;继写贼臣董卓把持国柄,肆意杀戮。初平二年(190)董卓焚烧洛阳, 胁迫献帝西迁。下篇写关东义士,兴兵讨卓。因人心不齐,半途而废。军阀们为了私利,互相残杀,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写尽了汉末战乱所造成的深重灾难。“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和“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表现了曹操体恤民情、关怀民瘼的民本主义精神。建安七年(202), 曹操颁布《军谯令》,其云:“旧士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据此可知,曹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原始儒学所倡导的仁民爱物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所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和统一大业都基于拯世济民的基础之上。
曹操对自己麾下的将士也颇为关怀。《苦寒行》写战争时期行军之苦。结尾云:“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东山》是《诗三百·豳风》中的一篇,写士卒久戍归乡之情。《毛诗序》云:“《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曹公之诗一则以周公自况;二则在于说明,经过艰苦的行军作战,自己体察到了当年周公的心境;三则表白:自己怜悯士卒,体贴士卒,并不想让士卒跟随自己去忍受征战之苦,但是要平暴除乱,又不得不如此。他在《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中云:“自顷以来,军数征行,……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这种体恤下属、同情将士之心亦属忧患意识。
年寿不永、功业难建的忧患主要反映在创作于晚年的游仙诗中。曹操的游仙诗,虽有享乐主义思想倾向,但主要是忧患意识的再现。前者暴露了作者思想中庸俗的一面,后者与言志之作同旨。《精烈》云:“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秋胡行》云:“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表明到了桑榆暮景之时,诗人功业难就的忧患愈加深刻,无法排遣。“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秋胡行》)明确告诉后人,诗人所忧并不是为了一己的享乐,而是忧愁壮志难酬、功业难就。这乃是诗人忧患的唯一原因。从这里我们也可推知曹操晚年热衷于写作游仙诗,并不是相信神仙道教,而是借以消解其忧患意识。
曹操诗中所表露的这种责任感、使命感与忧患感,与原始儒学精神出自同一机杼。原始儒学“诗言志”的理想至此得以落实。“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战国时代,“志”尚有“记忆、记录、怀抱”等多种意义。〔7〕但在《论语》与《孟子》中“志”的意义比较集中,即是指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里仁》)“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尽心上》)到了荀子将“诗”与“志”相联结,他说:“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原始儒家借诗来言志的思想在两汉不仅未能贯彻,反遭曲解。汉儒所理解的志乃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沦落为政教工具的诗歌其致命弱点在于虚假和装腔作势。曹操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真情真志倾注到诗歌创作上之后,才形成了有血有肉的壮美诗篇。表现士人责任感、使命感、忧患心的诗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言志之作。
三、莽苍悲凉,气盖一世:曹诗的艺术风格
对曹操诗歌艺术风格的体察,古人有大体相近的看法。归纳起来,一是悲,一是健。当然,悲与健不是孤立的,而是悲中有健,健中有悲。悲中有健即为悲壮,健中有悲即为雄健。悲壮与雄健凝成了笼罩天地的浩然之气。方东树评《薤露行》曰:“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恣真朴。”评《苦寒行》云:“取景阔远,写景叙情,苍凉悲壮,用笔沉郁顿挫,比之《小雅》,更促数噍杀。后来社公往往学之。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满意。后惟杜公有之。”(《昭昧詹言》卷2)斯语揭示曹诗风格甚为精当。
巡视诗史,不能不肯定:诗以天下意识忧患意识为主旨,诗风以悲壮雄健、浩气奋迈为特征的诗歌完成于曹操之手。《诗三百》非一人一时之作,诗风纷呈异彩。“曹公四言,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沈德潜《古诗源》卷5)《楚辞》的艺术风格“微婉隽永”、 “瑰琦卓诡”、“严华高整”(李维祯《楚辞集注序》),与曹诗风格判然有别;汉乐府以叙事为主,风格多样。“魏祖慷慨悲凉,自是此公文体如斯,非乐府应尔”(冯班《钝吟杂录》);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诗品》),“反复低徊,抑扬不尽”(沈德潜《说诗晬语》),缺乏英雄之气;孔融、王粲、曹植辈与曹诗风格相似,然其气度、胸襟不如曹操,诸人诗作气象亦与操不尽相同。徐祯即说:“气韵绝峻,止可以孟德道之;王刘文学皆当袖手耳。”(《谈艺录》)刘熙载亦说:“曹公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艺概·诗概》)徐刘之说,颇得要领。
此一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诗歌风格并非空穴来风,从根本上探究,实由原始儒学基本精神所导出。
儒道与中国艺术精神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非三言两语所能阐清。简言之,儒家重视诗与文学艺术,道家否定之。但是,中国纯艺术精神并不由肯定艺术的儒家开出,反而由否定艺术的道家开出。徐复观先生指出:“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8〕由于道家脱离了仁义道德的根源之地,所以他们的理论直接沾溉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论和创作。严格地说,孔子并不重视诗,孔子所重视的乃是诗歌的社会作用。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所谓“兴”即是“引譬连类”(孔安国注)、“感发意志”(朱熹注),显然“兴”的功用在于唤醒人们的社会性情感——仁心。“观”、“群”、“怨”与“事父”、“事君”之说更坦白地讲明了诗与伦理政治的关系。总而言之,孔门的诗学观念是围绕着社会政治伦理观念提出的,孔孟没有明确论及诗歌艺术本体范畴。如此,似乎儒家与艺术精神没有联系。此又不然。儒学之道在于“修己以安百姓”。在安百姓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流露出深刻的忧患意识。这种精神风貌连同平治天下之举本身就是一曲雄壮的歌。方东美先生说:“天地之美寄于生命,在于盎然生意与酣然创意。这是中国所有艺术形式的基本原理。”〔9〕原始儒学精神最具备此种昂扬奋发、引人向上之品质。当这种生意与活力形诸于诗歌创作之时,其作品必然产生“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
中国诗史上首次集中体现出“浩然生气”与“酣然创意”的作品,出现在“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的建安时代。曹操诗风尤为典型。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给曹诗以刚健之力、浩然之气;深沉的忧患意识给曹诗以凝重之态、悲壮之势。曹操诗歌的这一风格在中国诗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诗圣杜甫沉郁顿挫、地负海涵的艺术风格即与之有内在联系。此点已为古人所注意,上引方东树之语即为明证。当然,在深入体认原始儒学、人性思想、政治思想之后,杜甫诗歌更贴近原始儒学精神,其诗歌艺术成就更加博大精深。但曹诗孤明先发,功不可没!
四、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曹诗的意境特征
王国维《人间词话》以有境界为诗之本。进而又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据此,所谓意境是由真情灌注于客观物象所形成的画面。曹诗不仅有意境,并且其意境有自己的特征,即阔大雄奇之境的创造。
意境的构成离不开客观物象。曹诗中的自然景物描写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对自然美极为关注,首次创作出完整的山水诗。“《诗经》时代的人生活是茫然的,缺少自觉性,虽有诗歌作品,并不欣赏自然。”〔10〕《诗三百》中的山川日月,草木鸟兽只用来起兴,或者作为人的生活环境的一角来孤立描写,尚未构成独立的审美境界。屈原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描写主要用比喻,是《诗三百》中“比”法的深化。建安时代,“叙景已多、日甚一日”(吴乔《答吴季野诗问》)。曹操是这一转捩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诗中写景成分较多,第一首由自然意象构成的山水诗即出自其手,这就是他的《观沧海》。曹诗景物描写中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阔大雄奇之景的偏爱和阔大雄奇之境的创造。
以《观沧海》为例。钟惺云:“直写胸中眼中,一段笼盖宇宙气象。”(《古诗归》卷7)沈德潜云:“有吞吐宇宙气象。 ”(《古诗源》卷5)钟沈二氏将此诗之妙和盘托出。 浩瀚无垠的大海正如同英雄广阔的胸襟,英雄眼里的大海乃是英雄气概的外化,大海与诗人之间有同形同构之处,二者已交融为一体。只要将六朝模山范水之作与此诗略作比较,其间高下不言自明。
通观曹诗,不难发现:诗中多写萧杀的秋冬之景,绝少春风和煦、春光明媚、姹紫嫣红的阳春天气;所写的动物多是凶禽猛兽,不写温驯的家禽、依人的小鸟;所写山水以高山峻岭、深湍急流为特征,不写青山秀水。曹诗的这些特征,前此,并不多见。前苏联学者列·斯托洛维奇说:“在崇高的范畴中数量方面具有本质意义,在同美的比较中,被审美评定为崇高的现象的宏伟、威力和硕大可观得到正确地强调。”〔11〕无疑曹诗景物描写构成了崇高之美。但是,曹诗中的崇高与原始儒学精神有无内在联系,我们尚不能轻率地下一结论。因为对自然“大”美的重视,不是儒家的专利,先秦道家亦以“大”为美。而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后者更关注自然“大”美。
表面看来儒道两家都讲自然,但对自然的理解和所汲收的成分并不相同。道家所谓的“自然”主要是指自然而然,取消人为因素。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显然,原始儒家将君子的精神、品质、情操、抱负与自然联系了起来,他们所法的不是天的自然性而是天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品质。相应地,儒道两家对于崇高的理解亦有内在差别。道家追求无限之大美。庄子认为,尧之治世“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天道》)。这与孔子恰恰相反,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唯大,唯尧则之。”(《泰伯》)在孔孟看来,唯有救世济民之功业才可称为最壮观的美。如此,孔孟与庄子对大美理解的区别甚为显豁,“前者指的是个体的道德精神的伟大,具有浓厚的伦理学的色彩,……后者指的是不为包括社会伦理道德在内的各种事物所束缚的个体自由和力量的伟大,它没有什么伦理学色彩,已经是一个相当纯粹的美学范畴。”庄子的“大”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便形成“乘物以游心”的艺术境界,具有空灵虚静之妙;孔孟的“大”经过与天下意识、忧患意识的感应交流,便转换成与道德功业相系的阔大之境,具有挥洒酣歌、刚健挺拔的阳刚之气。
至此,我们可以肯定曹操诗歌中的阔大雄奇之境源于孔孟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理想。
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说诗晬语》)曹操以周公自命,巨手创业,“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魏武帝纪》)其襟怀抱负不可谓不大;“周公所谓多才多艺,孟德诚有之”(张溥《魏武帝集题辞》),学识不可谓不博。其诗亦可誉为“天下第一等真诗”。吉川幸次郎先生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曹操,陶渊明、杜甫、李白的文学,也许就不能产生吧?即使产生了,恐怕也是取别一种形式。”我以为这并非危言耸听,自有其道理。的确,曹操在诗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戍马倥偬之中,他“朝携壮士,夜接词人,崇奖风流”(胡应麟《诗薮》外编卷1), 领导了建安诗歌的新潮流;他率先借古乐府以写时事,为乐府诗闯出了一条新路,为唐代杜甫的新题乐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奠定了基础;尤为重要的是,曹诗在摆脱两汉经学家诗教说的束缚之后,大胆地反映现实,讴歌理想,将原始儒学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从哲学思想转化为文学艺术;并以原始儒学之人文精神灌注于诗境、诗风,创造出苍凉悲壮、雄健慷慨的诗歌风格和阔大雄奇的审美境界。因之,我们认为曹操不仅“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也是一位改造诗歌的祖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方东树授予他“千古诗人第一之祖”(《昭昧詹言》卷2)的桂冠。
收稿日期:1995—02—21
注释:
〔1〕详见拙文《道统说辩难》,《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2〕参见拙文《曹操与儒学》,《文史哲》1993年第2期。
〔3〕陈贻焮:《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4〕我们的肯定并非像孟子那样否定血流漂杵的史实。 我们在肯定周武王、曹操平暴除乱的历史功绩,又不能掩饰他们曾枉杀无辜的罪行。
〔5〕陈贻焮:《论诗杂著》,第25页。
〔6〕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 年版,第21页。
〔7〕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第10页。
〔8〕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第41页。
〔9〕方东美:《中国人的人生观》,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0 年版,第126页。
〔10〕郑临川:《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第64页。
〔11〕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页。
〔12〕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页。
〔13〕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中译本),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标签:曹操论文; 国学论文; 忧患意识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曹操后人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三国论文; 孟子论文; 短歌行论文; 对酒论文; 孔子论文; 儒家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