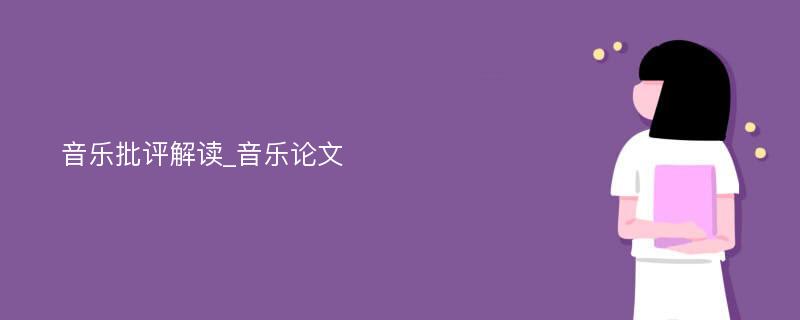
音乐批评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J605.1
最近,读了一篇关于音乐批评的论文(注:傅建生:《上海,一定要重视音乐批评》,载《上海艺术家》1998年第3期。)。 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上海各音乐表演团体、研究机构、新闻媒体均无音乐评论的意识,有关部门及领导层也无音乐评论意识,这既不利于新时期的音乐发展,也不利于上海作为国际一流大都市的精神文明建设。
我以为该文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反映了中国音乐批评普遍状况的问题。
一、音乐批评存在的几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音乐批评缺乏较独立的学术批评的根基。回顾历史,有悖于学术精神建立的不利因素有以下几点。一是简单用政治话语批评去主宰音乐批评的方向,以政治话语概念批评的运作。如左倾右倾、保守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阶级斗争、封建主义、新旧文化等。要么,泛泛地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词语来掩饰音乐批评缺少多维视角、多样化的建立。二是音乐审美批评标准的均同化、标准化、齐一化或单一化,如音乐表演中,民族器乐比赛显出“大珠小珠落一盘”,各地区器乐风格流派多样化标准荡然无存。民族声乐比赛也出现“千人一面、千人一嗓”,中华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特色难以凸现。而流行音乐的商业化包装及发行数量,专业音乐表演与创作的“国际性”获奖或媒体新闻成为替代音乐批评的更为实利价值的证明。三是音乐批评主体性的缺乏(包括音乐学术主体与文化主体)。有一种“寄生式”的音乐评议现象,当作曲家写的作品演出之后,便给予“吹捧”或“解释”。以致于有人认为搞音乐学的就是写“吹捧”文章的。应该说,音乐学不是音乐创作的“附庸”,音乐学是相对独立的,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紧密相关的学科。站在作曲家的角度对作品予以解释是可以采取的一种角度,但它不代表音乐学的主体。此外,在当今世界跨文化音乐运作中,文化的主体性批评也关系到音乐文化发展自主性的问题。四是音乐批评者的知识结构素养问题。“音乐批评”这一概念,有两种含义:其一指对音乐或作品的直接审美反应或陈述(话语);其二指对此种反应或陈述(话语)作理论的阐述。审美反应是心灵深处各种情绪的投射;而理论的阐述则是一种批评的批评,要求有人文学科等方面的根基。目前,真正具有人文学科功底的音乐评论家还较少见。
其次,音乐批评的封闭性。其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学科的封闭性,就音乐谈音乐,与艺术批评、文化批评完全相隔绝;二是缺乏国际性视野,缺乏跨文化的音乐比较批评,如流行音乐与专业音乐中,简单地把一切引进本土的东西都说成“创新”,而没有提出在哪方面是本土所创造的“新”。正如比利时著名史学家亨利·皮朗所揭露的:“沉湎于欣赏自己的民族,必然夸张其创造性……比较方法使历史以真正面目出现。原来被认为的高山,只不过是一丘陵,原来被引以为荣耀的民族天才创造的事件,不过是模仿精神的表现。(注:(美)斯塔天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三,音乐批评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如将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理论探讨简单归纳为“欧化道路说”与“传统发展说”,二者互为对抗。如“坚持我们的文化自性,就排斥了国外优秀文化”,简单的好/坏、祸/福(像中国儿童从小看电影一开始就要分清好人与坏人)。再如“西方音乐传入中国是好,是坏,是祸是福”等等。好像这些问题只有对错判断,黑白两色之分,而谁又不知世界音乐应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缤纷的图景呢?这实际上就是基于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框架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构成了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争鸣的某种张力场,也是音乐批评中政治批判左倾与右倾的二元对立模式的体现。其结果必须导致“你死我活”,“打倒”、“摧毁”、“征服”,不给妥协、合作、对话留下空间,最后结论必然是一元论的。20世纪西方哲学出现的号称“哥白尼式革命”的人类认知范式的语言学转向,它提示我们应从“打倒”孔家店,“摧毁”旧文化,先进“征服”落后转向阐释(如哲学解释学),转向对话,转向多元互补、共建的音乐批评。那种往往把自己当作正确、“真理”一方的发言,简单把对方当作谬误的批判已经过时,西方哲学解释学消解了二元对立,也为音乐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基础。
二、音乐批评的解释学基础
我同意“音乐批评是三度音乐创作”的看法。尽管人们说:音乐是一种非言语的交流,音乐不表达具体概念,但对每种音乐的喜好都有它自身文化语境的一种语言表达及分类,而音乐的文化意义由此而生成。在此,我拟借用解释学的角度来考虑“三度音乐创作”的概念,以此来深化音乐批评的人文科学方法。
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从古典解释学(即古希腊时代)到施莱尔马赫(1768—1834)的语话的解释和心理学的解释方面将古典解释学系统化,到狄尔泰(1833—1911)的方法论解释学、海德格尔(1889—1976)的本体论解释学、伽达默尔(1900—)的哲学解释学、哈贝马斯(1929—)批判的解释学、利科尔(1913—)的现象学解释学等,它们力图打破西方两大哲学思潮(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僵持格局,通过语言问题,融合了不同派别的文化哲学内容。哲学解释学对理解问题的研究,对人类所有理解方式所共有的东西的本源性探究,阐明了人类与历史、世界、语言等关系的一种本质,并揭示了人类所有生存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一种本质特征。无需赘言,解释学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已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已广泛渗透、运用到各种学科中去,如文学、艺术、美学、历史、宗教、社会学、语文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乃至科学哲学等等。
我以为音乐批评借用解释学有3个可以申发的方面:1.注重音乐理解的历史性;2.注重音乐理解的创造性;3.注重音乐解释的文化主体性和实践性(注:王岳川:《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现代解释学之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音乐的理解的历史性。对音乐如果没有历史性(如各民族音乐的历史性)的理解和把握,理解其音乐在细节与实质上就会出现困难和偏差。客观性的解释(如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着重对历史现实本身的探讨,并与历史文化融为一体;主观性的解释(如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解释学)讨论的“不是存在以怎样的方式才能被理解,而是理解是在什么方式下存在的。”将理解看成人的存在方式本身,理解不是去把握事实,而是去理解一种存在的潜在性和可能性,理解主体的显现,在于关注本体人的存在及理解活动的最基本模式,即批评主体的存在。在音乐批评中,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历史解释都具有存在的意义。
2.音乐理解的创造性。本体论解释学强调理解要对传统持开放态度,对解释者存在的具体环境开放。理解是人自身存在的本体论结构,理解具有无数的可能性,也可以说,历史往往是各种理解“偏见”构成的历史。这种“偏见”主要是人无法根据某种特殊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去对古代音乐或外文化音乐加以“客观”地理解。日常我们喜欢用“盲人摸象”的成语来批评人们的“偏见”,但人们在生活中很难避开这种“偏见”。也许,正是所有盲人的“偏见”构成了“大象”的真实。或许说,历史是由各种“偏见”构成的历史,它反映了“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伽达默尔语)今天,我们如何理解世界上各种文化传统相互影响的音乐,理解各种文化相互认识的各种“偏见”,也是开放性解释传统的理解过程。它是音乐批评创造性的一部分,它是一种真实世界解读的“镜象”,它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缤纷的图象。在此,我们不能以“对/错、黑/白”简单的二元划分去对各种音乐批评做论断,如批评“新潮音乐”就是保守,就是否定“新音乐文化”;相反,需要从批判解释学的角度,批判压制多元理解的社会传统,寻求音乐多种意义的生成。
3.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和实践性。解释学认为理解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形式,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文化的音乐理解世界,同时也是在认识自己。音乐理解在跨文化理解中是具有鲜明主体性特征的。理解含有文化解释,解释具有意义,而意义与实践关系紧密相联。存在于多元文化中的主体性文化批评在当今全球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将作进一步阐释。
三、当代音乐批评多维视界的建构
音乐批评必须走向多维视界的建构,以此才能摆脱“一言堂”、“一元论”音乐批评的历史影响。以下将主体性批评、边缘批评、后殖民批评、人类学的文化批评等理论观念引入音乐批评,并略作阐释。
1.音乐的主体性批评。20世纪,西方音乐教育、音乐学科理论在中国的移入,促成了中国人音乐思维的一种开放性,作为“新的”音乐学科理论,其标准和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音乐学科为典范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传统音乐在西方音乐学主体及音乐实践中处于学术的边缘,即在音乐标准、音乐认识论方面深受西方影响。这些问题也同样反应在中国文化的其它领域,如今天中国文学界对此的反省意识要比音乐界超前许多。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随意举出几篇文章题目即可感觉到文学界对此问题反省的力度:如《主体缺席的概念晚餐——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失态管窥》(注:王列生:《主体缺席的概念晚餐——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失态管窥》,载《思想》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传统的断裂与现实的困惑——从古文论一视角看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注:张瑞德:《传统的断裂与现实的困惑——从古文论—视角看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载《思想》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当代中国文论的“文化失语症”——兼论文学批评的话语形态》(注:徐岱:《当代中国文论的“文化失语症”——兼论文学批评的话语形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作者们指出,我国当代文学评论的“失语”现象,已对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文学批评事业构成了障碍。中国音乐批评也存在着主体性丧失的问题。笔者已在《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危机的思考》(注:管建华:《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危机的思考》,载台湾《北市国乐》1996年2、3期。)一文中有所涉及。
主体性批评的丧失也是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发展考虑的问题。哈佛大学的黑人教授亨利·盖茨鲜明地指出此问题:“我们作为批评家,是否能避与‘理论’的一种‘模仿鸟’关系,一种注定是派生的,经常发展到拙劣模仿程度的关系。(注:(美)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权威(白人)权利与(黑人)批评家;或者,我完全不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他还讲:“一个文学的传统就像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过去,它的被公认的传统所决定的。”“为了彻底重新安排日常生活并使之人性化而支持对文学艺术的探索的那种文化观念和黑人的批评语言。我们必须鼓励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对风格与主题、内容与形式、结构与情调等问题进行最充分而最具有讽刺性的探索,这一切在我们最崇高的艺术形式中,在黑人的声乐和器乐中,对于我们都是十分熟悉而生动,在这些艺术中思想和艺术融为一体,无论我们听贝西·史密斯(歌唱家,有“布鲁斯女皇”之称)还是听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约翰·科尔特兰(爵士乐萨克斯管演奏家与作曲家)都是如此,然而,黑人的批评文本的思想状况怎么样呢?我们自己的批评话语的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以谁的声音讲话?难道我们只是重新命名从白人那一方那里接受过来的术语吗?正由于我们必须鼓励我们的作家去迎接这场挑战,作为批评家的我们也必须求助于我们自己思想和感情的特殊黑人结构以发展我们自己的批评语言。我们必须通过求助黑人土语——当没有白人在场时,我们相互间讲的语言——来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中心论点是:黑人用黑人土语使他们的艺术和生活理论化,除非我们求助于土语,以使我们的阅读理论和模式具有坚实的基础,否则我们将淹没在内拉·拉森的流沙中……(注:(美)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权威(白人)权利与(黑人)批评家;或者,我完全不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盖茨提出的问题值得中国音乐批评界深刻反思。
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今中国文学界关于主体文学理论话语失语症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部分思考:“所谓‘失语症’,并不是说我们的学者都不会讲汉语了,而是说我们失去了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基本运思方式,因而难以完成建构民族生存意义的文化任务。”“既然失语症的实质是范畴、运思方式和文化根基的失落,那么重建中国学术话语的工作也就要首先从发掘和整理中国传统话语入手,从现代的学术视点出发,通过中外文化的比较,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清理,对传统文化的思维、言说方式进行重新审视,对其传统文论的范畴和言说方式的内在文化意蕴进行更深入的发掘。(注: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文论失范与文论失语”,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过分地看重了西方理论范畴的普适性,把某些文论概念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而对文化的差异性和任何一种理论范畴所具有的先天局限性重视不够。于是人们习惯于把某些外来的理论范畴作为普适性的标准框架,用它们来规范和解释中国艺术和中国文论范畴,把这种操作视为天经地义的事。甚至当我们一些人无法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概念时,仍然不去反思自己的操作本身的合理性,反而把这种困难作为中国文论概念‘不科学’、‘不适用’的例证。(注: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文论失范与文论失语”,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值得思考的是:今天,我们是否还在把西方音乐体系作为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教育批评普遍性的标准框架?
以上不厌其烦地引用当今文学理论批评的反思,其重要意义在于,促使中国音乐主体性批评的思考与建立。
从文化上来看,西方音乐学及学术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是强势文化的现象。对于中国音乐学界,不了解当今西方音乐学术状况,采取封闭、拒斥的态度是不可取的;然而,没有分析与自身的思考与选择也是不可取的。杜维明先生的观点对我们有参考价值。他认为,要改变依然属于强势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关键在于东方——例如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能不能以自己的本土经验对西方的普世化价值提出挑战和回应。他讲,这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其本土的或“当地”的经验要有全球的视野,而不是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本土经验;二是要对西方理论模式普世化的前提提出挑战。长期以来,“西方的普世化”和“东方的特殊性”是中国人的一种认识定势,从“五四”时期起确立的任务,就是如何用西方的普世化把东方的特殊性打破,使东方走向普遍化即现代化。甚至中国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问题上也不是一种平等对话,只是如何将普通真理运用到中国本土。这种倾向直到现在还是主流,很多已经普世化的价值确实都是西方的价值(注:盛宁:《“文化熔炉”、“文化战”、“多元文化”——美国文化转型格局面面观》, 载《世界文学》1998年6期。)。
以上杜维明先生的看法也值得中国音乐界深思。
2.边缘批评。“边缘”指文化的边缘,即处于主流或中心以外的文化各个部分。今天,我们从媒体中可以看到流行音乐、交响音乐在音乐生活中已构成“中心”或“主流”,而中国传统音乐或少数民族音乐相对处于“边缘”位置。这似乎也折射出当今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文化位置,即“中心”与边缘文化理论(弗·杰姆逊)。站在“边缘”位置对当今主流音乐文化进行批评,实际上是加强音乐文化对话意识的一种方式。
3.后殖民批评。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的话语,其方法多样,如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方法。当今,不少第三世界文化学家、文学理论家以一种深厚的民族精神和全球文化发展的思考,介入这场国际性讨论,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如跨国音乐业),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当今中国音乐界有必要考虑后殖民批评。借此,一方面扩展音乐批评的视野,另一方面,从中西音乐理论探讨的对抗转向对话,并寻找中国音乐的文化定位以及在世界多元音乐文化中的位置。
4.人类学的文化批评。在西方,文化批评已广泛地被社会科学家以及知识分子所接受,并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理念。西方当代文化批评最为重要的推动者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派人物包括M·霍克海默,T·阿多诺,H·马尔库塞,W·本雅明等。他们使人们认识到文化批评作为社会理论的功能所显示的重要性(注:马尔库塞、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在当今,进化论的衣钵依然根植在某些现代流行思潮中,现代化或发展的连续论,传统/现代,无文字/有文字,农业/工业等二元对立模式,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教条为依据,强化着欧美的自鸣得意式的文明观。人类学家博厄斯是对那些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的知识教条提出挑战的批评家。他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努力消除古典进化论的谬误,而他的学生:米德、萨丕尔、帕森斯、本尼迪克特等则是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旗帜下,成为对社会文化批评为主的学者。
近年来,反思人类学(reflexive anthropology)的出现,继续了人类学的文化批评(注:王铭铭:《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当代西方人类思潮评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首先,它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异文化”研究和人类学解释性的重新思考,引发了80年代以来对民族志的文本加以分析、解剖和批评的潮流。也有人主张创造一种后现代人类学或后结构人类学,对现实主义的民族志作出重新思考,并提出了“实验民族志”,其特点有三:1.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的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2.对文本组织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3.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象进行阐释。为了揭开民族志的“客观科学”的面具,“实验民族志”主张人类学者应主动把自己当成“意义的创造者”,利用人类学知识,展开对权力和霸权的批评。它的社会哲学来源主要有3 种: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关系的分析、知识社会学派与文本学派的理论、福柯对话语(discourse)的洞见。 实验民族志提出了田野工作的认识论问题,它不仅是关心人类学者的“自由”,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场合与文化碰撞进行阐述。这种有意识的文化反映,以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为先导,其采用3种方式:1.对异文化经验的表述;2.对人类学者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过程的反映;3.反思人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艺术。
解释人类学的文化批评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不仅能从异文化研究中提炼出具有思想的个案,而且能赋予本文化以充满民族志意义的理解。其方法以认识论批判(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与跨文化并置(cross cultural juxtaposition)(注:《国外文化人类学新论——碰撞与交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这两种方法均以“变熟为生”(defamiliarization)为基本批评策略的变并形式, 是一种“陌生化”的方法。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的《莫扎特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注:汤亚丁:《〈莫扎特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评价》,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4期。 )即采用了这种“陌生化”的方法。其中以“火星人”的角度,置熟悉的西方音乐文化为陌生的事物,火星人也通过“田野工作”以民族志的形式客观地记叙了西方人的音乐生活,促使读者获得文化差异的意识。它不仅具有超现实主义批评的意义,而且也是一种艺术表达的策略,整个写作产生了一种新文本和话语的形式。这种严肃的文化批评,把从边缘地区获得的见识带回中心世界(西方工业音乐文明),打破西方人一成不变的思维和概念化方式,并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人原有的音乐文化认知的基础。
跨文化并置的陌生化的批评是更为经验、更为生动、直率的文化批判。所谓并置,是以国外民族志与国内民族志加以比较,以有关他国文化的大量事实去探索国内批评对象的具体事实。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采用了并置批评法,是对萨摩亚儿童养育文化的叙述,而这种叙述是作为一种教训被提出来与美国儿童教育实践相并置的。以下是一音乐跨文化并置批评法的例子。
当今音乐人类学对西方音乐教育已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即出于此。施瓦德隆在他的《音乐教育与非西方传统》一文中,对音乐教育中引进非西方传统音乐,并将非西方音乐教育与本身传统音乐教育在目的、方法、手段、理解、音响、记谱、教学等方面作了并置式的提问与评论。该文最后讲:“上述这种思考是相互关联的,它们还没有穷尽所有的问题,对音乐教学过程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理解。虽然,批判哲学使这种探索更加复杂化,但它毕竟有助于跳出西方价值的圈子,弄清在拯救包括音乐在内的当今教育中的各种出发点。明言之,这里提出的音乐教育中的有关非西方音乐的各种问题和观点,是与盛行于西方的固定价值、外显行为学说和实证主义态度相悖的。当人们深思音乐艺术的本质以及日增的全球交流趋势时就会看到,西方世俗文明对言语——认知的理性依恋是怎样的一种悲剧。(注:(美)施瓦德隆:《音乐教育与非西文传统》(刘沛译),载《中国音乐》1995年4期。)”
四、音乐批评阐释的文化意义
音乐批评的阐释是培养文化中的各种对话与协调,它是促成音乐文化机体正常代谢的“维生素”,具有打通古今中西南北关系的各种隔膜,促成各种音乐视界的融合,形成在全球思维框架下各种文化批评及观念影响的相互作用,显示“君子和而不同”原则的和谐发展的音乐文化状态,也打破目前“西方化模式”与“多元文化”之间矛盾的日益紧张的关系。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部分本土音乐学者与本土艺术家在工业化、后工业化(文化工业、信息社会)的浪潮中,为保存和重释中国传统音乐,为建立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为在后殖民文化语境中(即音乐的落后/先进、传统/现代、错/对、高/低的二分法中)为伸张中国传统音乐价值及历史存在的合法性而孜孜不倦地努力。这种努力是各种文化的音乐中“互为主观”(哈贝马斯语)、交流、对话的基础,是中国音乐在全球多元文化中建立自己主体性批评的开始。走出这一步,中国人会去思考中国对未来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看法以及个性和可能做出的贡献。
收稿日期:1998-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