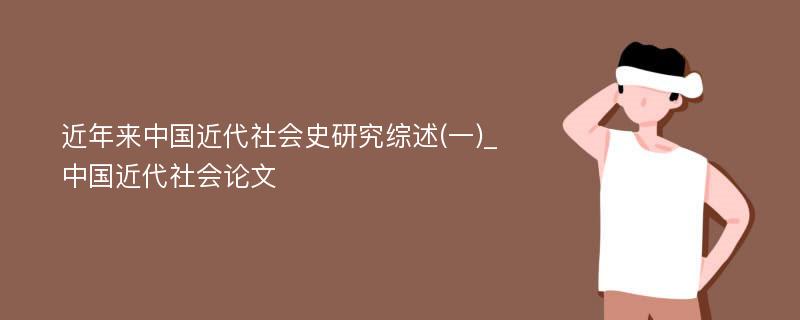
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概述(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史研究自80年代中期兴起以来,十几年间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不但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其专业研究队伍也日益壮大。对之进行归纳与总结,不但可增进学者对目前研究状况的了解,也有助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鉴于以往相关综述多对辛亥之前的近代社会史研究状况较为关注, 对1911—1949年间的社会史研究则相对注意较少, 故而本文拟对1911 —1949年中国近代社会史各主要专题研究作一概述,以弥补这一不足。
一、婚姻与家庭
传统婚姻制度沿袭数千年,至民国初年时仍居主导地位。其弊端很多,梁景和将之归结为无自主性、买卖性、抑女性、承嗣性及繁缛性。(注:梁景和:《论中国传统婚姻陋俗的特征》,《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此外,早婚现象亦极为突出。 傅建成利用大量的民国县志,考证了华北农村极为普遍的早婚现象。他指出,在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四省的广大农村,早婚现象极为严重。而且,早婚现象在贫富家庭间和不同区域间都存在差异。一般地说,无论是订婚抑或结婚,相对富裕的家庭都早于相对贫困的家庭。而在二者内部,相对富裕的家庭偏重于男子早娶、女子晚嫁,贫困之家则突出于女子早嫁、男子晚娶。故此,夫妻年龄差距过大是这种早婚现象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而这不但使夫妻双方在心理、习惯、志趣等方面形成障碍,在生理上也会产生不协调的缺陷。(注:傅建成:《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早婚现象》,《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
性比例失调与溺女之风亦影响农村婚姻甚巨。李金铮以定县为例,对二三十年代冀中农村的性比例失衡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指出,男女在家庭经济中的不同影响、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妇女地位低下及其较易死亡等,都直接导致了性比例偏高的现象。性比例的失衡对男女婚姻产生了不良影响,不但剥夺了部分男性的结婚权利,还造成了极为普遍的男子早婚或晚婚现象。(注:李金铮:《二三十年代冀中农村性比例失衡的实证分析》,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忻平亦将性比例失衡归结为上海青楼业繁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注:忻平:《20—30年代上海青楼业兴盛的原因及特点》,《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 )徐永志则利用大量县志资料分析了近代极为盛行的溺女现象。他指出,人口过剩、社会生产力停滞、人们生活状况普遍恶化、重男轻女的思想以及厚嫁之风,都是造成溺女之风的主要原因。而溺女之风对社会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除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外,还助长了民间收养童养媳、早婚、买卖婚姻及其他婚姻陋习的流行,并增加了刑事诉讼案件,影响了近代家庭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注:徐永志:《近代溺女之风盛行探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剧变时期。传统婚姻制度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新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当然,婚姻制度的变迁远非一日之功,而是自清末维新、辛亥革命到民国成立等长期社会演变的结果。徐永志分析了清末政治变革对婚姻观变迁的推动作用。他在文中指出,维新派最早对封建婚姻予以抨击,他们不但热情介绍西方的婚姻礼俗,以开拓人们视野,并进而提出了婚姻改革的方案。而资产阶级走得更远,明确提出了“婚姻自由”的口号,并具体指出了实现婚姻自由的途径与方法。(注:徐永志:《清末政治社会变革对婚姻观变迁的推动》,《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 )随后,徐永志又分析了清末民初婚姻变化的轨迹。首先,父母主婚权下移,一部分较开明的家长开始尊重儿女的选择,个人的意愿在婚姻中受到或多或少的重视;其次,新式婚礼开始出现,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带头树立新风,操办具有西方色彩的新式婚礼,而且这种新式婚礼在民初以后已影响到乡镇,并具有了一定地域和阶级范围的普遍性;再次,癖好华丽、追求享受的时尚,也在婚姻中有所反映,突出表现在结婚用具的变化上。但与此同时,广大农民在婚事上则变得更加艰难,突出表现就是民初早婚的盛行。清末民初婚姻的变化既是中西文化接触的结果,又是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传统婚姻的继续,从而显示出继承与发展、新与旧冲突而又由旧趋新的总体性特征。(注:徐永志:《清末民初婚姻变化初探》,《中州学刊》1988年第2期。 )行龙亦分析了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潮现象。这种婚姻新潮首先表现在主婚权利、媒介形式、择偶标准与范围、离婚再嫁等方面的开放和自由上;其次表现为婚姻礼俗的删繁就简方面;再次,买卖婚姻风气盛行,亦为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去土求洋”倾向、地域的不平衡性与时代的局限性等,都是清末民初婚姻变化的显著特点。另外,这种变化也经历了一个由城市渗透到乡村、由沿海波及到内地的过程。(注:行龙:《清末民初婚姻生活中的新潮》,《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民国时期的婚姻形式虽出现变化,但旧的传统婚姻形式仍在广大农村居于主流。在地处偏隅的根据地,仍存在不少的婚姻陋俗。对此,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在发展生产、坚持抗战的同时,对传统婚姻陋俗进行了改造。李晓晨分析指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各抗日民主政权,采取说服教育的渐进方式,以转变人们的婚姻观念,并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婚姻秩序,逐渐打碎封建婚姻枷锁。经过婚俗改革,追求婚姻自由、主张新事新办的新风尚在华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蔚然成风。(注:李晓晨:《试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婚姻风俗改革》,《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傅建成则指出,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主要通过颁布、制定婚姻法规以达其改造旧婚姻制度之功效。在法规中,除强调保障婚姻自由、反对早婚、禁止买卖婚姻、保护妇女权益之外,还体现出了保护抗日军人权益的原则,以便安定军心,提高抗日军人对敌斗争的积极性。这些规定从法律上否定并冲击了旧的制度,为建立新型的婚姻制度奠定了基础。(注:傅建成:《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谭双泉、 李招忠则对根据地的婚姻立法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根据地婚姻立法对旧式婚姻采取多改造、少破裂的原则,对结婚自主权的保护着眼于男女双方,而对离婚自主权的保护则侧重于妇女的婚姻权利。通过规定,根据地婚姻立法对中国妇女的婚姻自主权、人格权、财产权等都给予了法律保障。(注:谭双泉、李招忠:《根据地婚姻立法与人权保障》,《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3期。)
家庭制度在民国时期亦发生变化。陈蕴茜着重分析了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由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开化,城市家庭制度也随之开始了自身的革命。首先,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在这种小型的家庭中,夫妇与子女成为家庭的中心,人格对等的夫妻关系逐渐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子女们也开始自由择业、自主婚姻;其次,家庭功能开始变化。家庭所具有的综合社会功能逐渐瓦解,其经济功能也发生变化,家庭生产消费已向社会生产消费转化。同时,家庭单纯的生育功能亦开始降位,人们转向生育之后的教养,重男轻女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此外,传统家庭的娱乐与宗教功能亦逐渐衰落。(注:陈蕴茜:《论民国时期城市家庭制度的变迁》,《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邓伟志在研究了自太平天国至民国时期的家庭变革之后,得出的结论也与此基本一致:中国近代家庭变革的走向,简单说来,就是家庭功能在一天天地由多到少,家庭规模在一天天地由大到小,家庭结构在一天天地由多到少,家庭规模在一天天地由大到小,家庭结构在一天天地由紧到松,家庭观念在一天天地由浓到淡,家庭理论在一天天地由浅入深,由旧变新,月异日新。另外,其变速呈波浪式发展,有急有缓,时急时缓。(注: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陈亚平对近代华北农村家庭制度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了与上不同的结论:近代华北农村既然没有脱离传统的农业社会,则大家庭制度作为一种理想的家庭制度不会有实质上的改变。(注:陈亚平:《近代华北农村家庭制度探微》,《学术论丛》1998年第5期。)
乔志强与董江爱探究了近代华北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利弊。他们指出,近代农民的家庭赡养观以孝为核心。这种以孝为核心的农村家庭养老制度有其积极的一面:不但使老人在失去劳动能力之后可安度晚年,又可使近代社会减轻负担,而且,年轻一代在赡养老人的同时,也获得了对家庭财产和其他权利的继承。这不仅对家庭延续发展有关键作用,对社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它也有其不利的一面:老人权势过重,年轻一代才能无法发挥,不但使得生育成为第一需要,大家庭的弊病也随之而来。(注:乔志强、董江爱:《近代华北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利与弊》,《学术论丛》1998年第1期。)
二、社会习俗与风尚
社会习俗与风尚是特定的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气质性格、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的综合反映。当社会处于巨大变革的时期,其社会习俗与风尚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胡绳武、程为坤分析了民初社会剧变时期的风尚变迁。民国初年,一股改革不适应民主共和制度的社会风尚的潮流蔚然兴起。剪辫易服、迫令放足、破除神权、反对迷信、改革旧的婚丧礼俗等,都是民初社会风尚演变的主要内容。这些新的风尚表现出追新慕异、去土存洋的特点,包含着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哲理取代儒家伦理纲常等进步的内容,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除陈规陋习、为社会前进开辟道路的美好愿望。(注:胡绳武、程为坤:《民初社会风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社会风俗在转化过程中,通常表现出新旧并存现象,并且常会遭到迟滞保守历史惰性的阻挠。焦静宜即分析了民初华北农村社会习俗变化中的逆向势力。他指出,守旧观念是破旧立新的思想障碍,习惯势力是移风易俗的社会阻力,落后的生产力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使迷信活动历久不衰,而新生的腐化现象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催化剂。(注:焦静宜:《浅析民初华北农村社会习俗变化中的逆向势力》,《南开学报》1996年第1期。)
社会风尚主要通过衣、食、住、行、娱乐等方式表现出来。罗玲具体分析了南京社会风尚的概貌。作为民国政府的首都,南京的社会风尚反映出中西合璧的特性:服饰等级制度被废除,表现出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征;吃西餐成为时髦,中国其他地方菜系也在南京得到了很大发展;建洋楼、住洋房成为一种风尚;传统的以人力和畜力为驱动力的交通工具仍然存在,西式马车、黄包车和自行车也颇为流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小汽车、摩托车、公共汽车等也相继出现;茶馆酒楼散落在青楼之中,电影院、弹子房、舞厅等西式娱乐场所也相继出现。从总体来看,南京的社会风尚以崇尚文明为主,但它始终受到政府行为的制约。(注:罗玲:《民国时期南京的社会风尚》,《民国档案》1997 年第3期。)
李少兵分析了民国习俗西化的问题。他指出,中俗西化现象在民国时期极为普遍,其特点有四:打乱了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价值评定秩序,重商思潮深入民心;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具有“度”和“量”的限制,中俗西俗彼此交流,共存共容;西式风俗在城市显于农村,在沿海显于内地。(注:李少兵:《民国风俗西化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
社会习俗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反映,王守恩从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变化中透视出早期现代化对人们心态层面的影响。他指出,清末民初社会风俗的移易,使社会风尚发生以下几方面的转折:由守旧到趋新,从安土重迁到离土离乡,从贱商到重商,大家庭崇尚的衰微。社会风尚在转化过程中,表现出了删繁就简、弃旧从新、封建性减弱、民主化倾向增强等特点。这种变迁实质上是社会风俗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演变,即社会风俗现代化的开端,对整个心态层面的现代化发挥着积极作用,但这又仅仅是开端与起步而已。(注:王守恩:《从清末民初社会习俗的移易看中国早期现代化对人们心态层面的影响》,《学术论丛》1998年第1期。)
近代中国风俗的变迁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李占才专就铁路在近代中国民俗嬗变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铁路的引入,引起了民俗心理的更新。人们产生了纳新意识,增强了时间观念,加快了生活节奏,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父母在,不远行”的传统心理。人们日常生活习俗的改变与铁路也有很大关系,距铁路线愈近,其变化也就愈早愈快。(注:李占才:《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黄兴涛、刘辉对五四时期的废娼运动进行了分析。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纷纷倡议废除娼妓,并提出种种方案和具体办法。此次废娼运动前后历时五年,形成以上海、广州、天津为中心的三个高潮。但综合观之,五四时期的废娼运动主要停留在舆论阶段,付诸实践者极少且无甚结果。(注:黄兴涛、刘辉:《五四时期的废娼运动初探》,《史学月刊》1992年第3期。 )严昌洪研究了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中国传统丧葬礼俗崇尚厚葬,带有浓厚的封建等级性与迷信色彩。民国年间,历届政府和民间团体对丧葬礼俗的改革作了一定的努力。其突出之点便是在国丧中吸收了西方丧礼中臂缠黑纱和下半旗的致哀方式,开追悼会亦为其中最有意义的一项改革措施。传统丧葬礼俗中的严重弊端,也通过取缔停柩、设立公墓、反对厚葬久丧、提倡薄葬短丧等措施予以禁革。官方和民间的这些禁革虽未能完全奏效,但其中一些办法、规则、公约等,在各地丧葬礼俗中却部分地得以实施并固定下来,沿袭至今。(注:严昌洪:《民国时期丧葬礼俗的改革与演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杨兴梅则利用大量档案资料, 对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作了综合评述。她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实施近代以来的禁止妇女缠足政策,经过10年的大力提倡,不缠足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仅从执行较好的云南、山西两省来看,妇女缠足者仍居相当比例。究其原因,各级政府向百姓宣传的广度、深度,特别是针对性不够,而且各级人员执行禁罚的方式也常常违反了民间的社会风习。(注:杨兴梅:《南京国民政府禁止妇女缠足的努力及其成效》,《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女子服饰的变革亦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吕美颐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女子服饰式样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初,出现崇尚男装、青睐西式服装的趋向。民国初年,因其处新旧交替时代,服装样式也呈现出多样性特点。旗袍在二三十年代尤为流行。从总体上看,女子服饰的变迁与社会近代化的潮流相适应,追求适体与方便成为女子服饰发展变化的总趋向。(注:吕美颐:《中国近代女子服饰的变迁》,《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金炳亮亦分析了民国时期女子服饰的改革问题。 他指出,民国初期,政府所实施的服饰改革仅限于男性,引起了女权领袖的不满。她们也提出了更新女子服饰、简化女子装饰的问题。但一般妇女对此并未作出积极响应,她们所热衷的是服饰的随意性、多样性和奇异性。从总体来看,民初女子服饰的变革既具开创性,又有很大的盲目性。(注:金炳亮:《民初女子服饰改革述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
三、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
分析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即是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江沛分析了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他指出,民国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碰撞时期,其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颇具规模的人口流动,日益弱化的宗族形态,家庭范式的趋于小型,农村阶层变动剧烈,秘密结社与土匪风行等,都是新时期所特有的变化。(注:江沛:《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张静如等则以两本书的篇幅分析了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变迁(注: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静如、卞杏英主编:《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方面指出了民国社会日益进步的趋势,另一方面从深层意义上揭示了两个政府统治走向崩溃的内在原因。继《中国近代社会史》一书对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框架结构提出设想之后,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注:乔志强、行龙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又于不久前问世。该书范围广泛,构架新颖,从人口、婚姻、宗族、阶层等社会构成,到物质生活、风俗习惯、人际关系、心理等社会运行,再到基层政权、地方自治等社会功能以及灾荒、匪患等社会问题,几乎无不涉猎。不但内容丰富,且不乏真知灼见。无论从体系上看,还是就内容而言,该书都不愧为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但也许是篇幅太大、材料不易收集的缘故,有些章节所用二手材料过多,稍微影响了全书的质量。李正华分析了乡村集市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影响。他指出,乡村集市是社会性与经济性的统一,同时具有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功能。在其初始阶段,其经济功能受到很大局限,其社会功能大于经济功能。进入近代以后,其经济功能逐渐向着部分或完全取代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与古代集市相比,近代集市呈现出传承大于变异的特点,尽管随着时代的剧变,这种变异的速度和力度都远远大于此前任何时期。(注: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的变迁》,《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抗战时期的社会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发生了重大变化。范忠程分析了抗战与湖南社会演进的关系。他指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促进了湖南社会的改观和阶级关系的改善,增强了湖南人的政治整合力和民族凝聚力,从而成为湖南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注:范忠程:《抗日战争与湖南社会的演进》,《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潘洵、杨光彦则简要回顾了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他们指出,人口流动是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突出事项,其中,不但包括其他地区向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也包括西南地区向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动和西南地区内部的人口流动。社会意识在抗战时期也发生了变化。抗战以前,西南地区农民思想保守、民族意识缺乏、国家观念淡漠,而抗战则唤醒了西南农民的民族意识,绝大多数农民能够深明大义,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农业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也有了提高与变化。(注:潘洵、杨光彦:《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农村的社会变迁》,《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姜涛对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的稳定性给予了关注。他指出,自清代以至民国,乡村中的地主与农民已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上的差异,虽然组成各个阶级或阶层的个体成分不断变更,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及各阶级所占有土地的比重,却始终是十分稳定的。其原因很简单,在土地集中的同时还存在着反向的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土地分散。(注:姜涛:《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陈亚平也分析了近代华北农民的社会流动。他指出,近代近百年华北农村的社会分层模式,并不完全是一种封闭的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而是一种相对开放的阶级制度。他对农村社会流动趋势的看法与姜涛不同,认为其总体趋势是下向流动:对广大小农来说,他们面临的是无产化半无产化的命运,而地主阶级稍有不慎,也会沦落到乡村社会的下层。(注:陈亚平:《近代华北农民的社会流动》,《学术论丛》1996年第1期。 )张庆军对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的结构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性别比例偏高;青壮年人口占较大比例;已婚率普遍低于乡村;四民之末的商业和工商业就业人数占据了绝对优势;教育程度有所提高,文盲人数也呈减少的趋势。(注: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
唐润明分析了抗战时期重庆人口的变迁及其影响。他指出,由于外地人口的迁入,战前十年间重庆人口即增加了一倍有余。1937年抗战爆发后,重庆虽为陪都,由于一般难民并不明了战争的发展态势,未将重庆作为其主要避难场所,政府当局也为了防备日机轰炸而明令人们向四乡疏散,故而在抗战初期的1937—1940年,重庆人口虽时有增加,但下降的幅度更大。1941—1942年,因市区扩张及难民的陆续涌入,重庆人口缓慢增长。1943—1945年,受战争的直接影响,重庆人口猛增,重庆也因而成为战时大后方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城市。这些迅速增加的大批人口,在促进重庆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进步的同时,也给整个重庆社会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注:唐润明:《刍论抗战时期重庆人口变迁及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四、流民与难民
流民、难民与移民虽不是同一概念,但相互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在社会动荡、灾难重重的民国时期,由三者所组成的巨大流离群体, 已构成了当时一大社会问题。 王印焕从小处入手, 细致分析了1927—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的形成原因。她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严重的人口压力与阶级分化的结合,以及频仍的自然灾害、战乱及匪患等,共同导致了河北流民问题的严重局面。(注:王印焕:《1927—1937 年河北流民问题成因探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池子华在分析流民现象过程中, 着重强调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在流民现象形成中的影响。他指出,自然经济解体所产生的推力与中国近代工业化所产生的吸附力相结合,加速了流民现象的发生。宗族制度的分裂,也孕育了部分流民。此外,当行乞江湖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它对流民现象的产生无疑更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注: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流民问题的产生原因之后,王印焕系统考察了河北农民离村后的地域流向与职业流向,并指出了它所产生的双重社会影响:一方面促进了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又具有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大片土地荒芜以及助长社会动荡因素的负面影响。(注:王印焕:《1928—1937年河北农民离村后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池子华亦对流民的流向、影响及其治理,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新颖的思维方式给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由于特殊的原因,抗战时期的难民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群体,孙艳魁对此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他指出,抗战时期的难民,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所构成的一个松散、复杂、流动性很强的群体,其产生、存在与消亡与这一战争相始终。他们一改传统的流徙方向,纷纷涌向我国的西部,这固然与日本侵略的由北向南、从东向西的推动有关,也深受政府西迁的影响。(注:孙艳魁:《抗战时期难民群体初探》,《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在另一篇文章中, 孙艳魁对抗战时期的难民垦荒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在抗战时期,后方大量可垦荒地的存在与大量农业人口的闲置,使组织难民垦荒不但必要,而且可行。故此,无论是国民政府抑或边区政府都实施过这一政策。通过这一活动,不但救济了数以十万计的难民,而且增加了社会财富,加强了中国抗战的物质力量。(注:孙艳魁:《抗日战争时期难民垦荒问题述略》,《民国档案》1995年第2期。)为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系统, 孙艳魁写成了《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一书,对抗战时期难民的状况、特征予以分析,并详述了政府各界对难民群体的救济政策及其善后工作。(注: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移民东北也是民国时期一大社会现象。李德滨、石方对近代以来黑龙江的移民概况进行了研究。他们不但对民国时期黑省的移民分阶段作了地理分布、迁徙状况的分析,还对日伪统治时期的国内移民与日本移民作了概述。(注: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张利军对“闯关东”的移民潮予以简要分析。他指出,到东北的移民,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他们到东北的原因,固然有政府移民实边政策及东北自然经济吸引力的影响,而更大的驱动力则是华北自然经济环境的不断恶化与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注:张利军:《“闯关东”移民潮简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赵风彩亦分析了20世纪初叶的东北移民。她指出,本世纪初,为了瓜分中国,日俄两国都大批向我国东北移民。对此,中国政府一筹莫展。而关内自发的移民队伍,则在事实上起到了巩固边防的作用。此外,他们在促进东北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使我国的人口分布更趋合理。(注:赵凤彩:《二十世纪初叶东北移民研究》,《人口学刊》1988年第1期。)
东北移民队伍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达于高潮,对事变之后的移民情况,朱玉湘、刘培平作了认真分析。由于日本侵略的原因,关内向东北的移民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有着很大的区别。事变前,关内向东北的移民有组织,有计划,数量大,范围广,居住性移民增多,农业移民呈上升的趋势;而事变之后,移民数量忽高忽低,流动性增强,居住性减少,带有很大的强制性。“七·七”事变之后,移民东北活动又有了新的特点:日伪对关内劳动力的掠夺,更具组织性与计划性,大量使用战俘作劳工是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注:朱玉湘、刘培平:《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除关内人民向东北移民外,日本也向我国东北进行移民活动。高乐才分析了1905—1931年日本向中国东北的试点移民活动。日俄战争之后,为防俄国报复及巩固其在华势力,日本策划并实施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试点的侵略活动。尽管日本为此费尽心机,但由于日本经济匮乏、经营不善、自然社会条件的差异以及中国人民和东北当局的抵制与反对等原因,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农业“试点”移民活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注:高乐才:《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 )季淑芬则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狂潮。她指出,在“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前的十几年间,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活动,具有缓解日本国内社会阶级矛盾的紧迫性、移民的军备性、移民输出的强制性和移民宣传的欺骗性等特点。(注:季淑芬:《试论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相对于东北移民来说,西北移民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但它在近代移民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张嘉选对三四十年代“开发西北”声浪中的“开发青海”口号进行了评述。他指出,“九·一八”事变所导致的民族危机与东北资源的丧失,使国人纷纷将目光转向西北,“开发西北”一时间成为时髦的话题。“开发青海”、“以青海为中心”等议题亦由此而发。在作者看来,“开发西北以青海为中心”的议题,从交通、人力、物力等方面来看条件都不具备,因而此建议实不可行。尽管如此,当时的学术界和舆论界还是就如何开发青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屯垦青海,发展农业、畜牧、交通,农、牧、林并重等多种建议。虽未付诸实施,却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注:张嘉选:《三、四十年代“开发青海”述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与之相对的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却因抗战时期移民的涌入而得以发展。孙业礼指出,因战争影响,大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迁入陕甘宁边区。这批移民在促进边区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对边区工商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影响。(注:孙业礼:《论抗战时期移民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西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随着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的迫害, 大批犹太难民移居中国也成为30年代所特有的现象。周建国分析了30年代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原因。一方面,西欧国家对犹太难民采取拒之门外政策,美国亦实施限制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有着许多相互通融之处,故此自古代始便有犹太人来到中国。再者,上海在30年代也有着吸引犹太人的特殊性:首先,上海是当时中国乃至远东最欧化的城市,且有着一个繁荣的租界,为犹太人提供了合适的谋生条件和生活环境;其次,“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当局推行“亲犹”政策;再次,上海一度处于“大门洞开”的特殊开放状态,以致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进入的城市,为犹太人的入境提供了便利。(注:周建国:《论三十年代初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原因》,《史林》1992年第2期。)
五、灾荒与救灾
灾荒,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刘仰东称之为“社会史研究的另一个视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了《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一文,将1917—1939年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一一公之于众。(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 《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极其严重, 吴德华将其特点归结有四:灾荒连年;多灾并发;灾域广泛;东南以水灾为主,西北以旱灾为主。至于其后果,吴德华亦归纳为四点:灾民遍地;农业受损;城市遭劫;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反抗斗争迭起。究其原因,除地理、气候条件之外,剥削严重、战争破坏、水利失修以及生态植被的破坏等,也导致了灾荒的严重局面。(注:吴德华:《试论民国时期的灾荒》,《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李文海等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一书中记述了1915年珠江流域大洪水和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甘肃大地震等灾害,精密分析了人口激增对灾荒的重大影响, 再现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灾荒画卷。 在分析1928—193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时,李文海等指出,此次灾荒不但使西北成为“活地狱”,亦使华北大平原变成了废墟,而游民与匪患则成了与灾荒共时的社会现象。(注: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31年江淮水灾异常严重,王方中称其为“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自然灾害”,李文海等也称之为“百年罕见”。究其原因,二者都认为,雨量集中、生态破坏、水利失修、政治腐败等酿成了这次水灾。李文海一书主要记述了此次灾害的规模、流程及灾难景象,而王方中则着重分析了水灾对30年代经济的深远影响;不但恶化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并加重了30年代的经济危机。(注: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张水良在阐释1927—1937年国统区三次大灾荒时,除介绍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与1934年全国大水灾之外,对1931年江淮水灾也着墨最多。他指出,三次灾荒对社会经济冲击惨重,不但加速了本已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的崩溃,更招致了都市城镇工商等业的进一步衰落。(注:张水良:《二战时期国统区的三次大灾荒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魏宏运以大量的报刊资料研究了1939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程度及其救济情况。在分析灾荒对经济的冲击时,魏宏运指出,“这种周而复始、带有周期性的灾荒,是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经常出现间歇、甚或停滞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注: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江沛在研究三四十年代灾荒的时候,除分析其经济后果外,还从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灾荒与农村社会文化的关系。他指出,由于灾害的无情与人们的孤立无助,故而在灾荒中他们有时便会显露出其动物性野蛮、残暴、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的一面。同时,多灾的环境也造就了人们刻薄吝啬、冷漠无情、视钱如命、缺乏人性、道德颓丧的饥荒心理,而迷信风行就更与灾荒关系密切。(注:江沛:《三四十年代的灾荒与华北农村社会》,《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2期。)
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灾况亦极为严重。夏明方以一个个鲜活的实例, 记述了大饥荒中食子鬻女的凄惨景象。 (注:夏明方:《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纵横》1998年第5期。 )李文海上引书则以更加翔实的资料,记述了此次灾荒,并详细对比了国统区、敌占区、解放区三种不同政治势力对灾荒所采取的态度与措施,以铁的事实表明:惟有中共所采用的群众性生产自救的办法才是缓解灾况的正确途径。此次灾荒中,河南受灾最为严重,孙子文对国民党政府救济豫灾活动作了分阶段的介绍:先是调查灾情,拟定救灾计划与方法;接着全面展开救灾工作;随后,加强地方自救工作;最后,招抚灾民自耕,安排种子农具事宜。其措施在救灾初期曾起了一定作用,但终因战火、腐败等原因而难收实效。(注:孙子文:《1942—1943年国民政府救济豫灾述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
在救济灾荒的办法中,工赈以其既可缓灾民粮食之急又可为地方谋长久之福利的性能而见长。刘五书粗略记述了民国历届政府所实施的以工代赈措施,其办法主要包括疏浚河道、铺设公路、开挖水渠、植树造林、开发实业等。至于其作用,刘五书指出,它既有灾区重建性质,有助于减少灾民的依靠性与改善灾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同时也能增加贫困者的就业与收入。但是,在具体实施中,以工代赈办法往往又因灾民缺乏热情及工程的暂时性而使实施者难达目的。(注:刘五书:《论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赈救荒》,《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
标签: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中国服饰论文; 婚姻与家庭论文; 历史论文; 民国生活论文; 近代史研究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移民论文; 史学月刊论文; 民国档案论文; 家庭论文; 春秋战国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