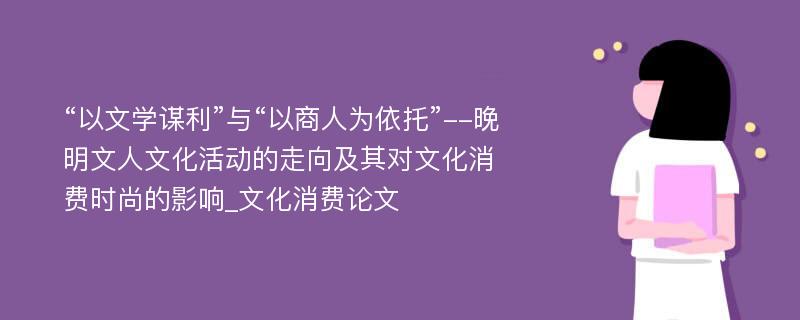
“以文征利”与“倚商事文”——晚明士人文化活动的趋利化及对文化消费风尚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商事论文,文化活动论文,风尚论文,以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晚期,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城镇的发展,文化活动覆盖社会阶层的广度较以前有显著的扩大,在城市生活中,扮演传奇、刻书传看、制售玩赏各种雅致的竹木牙角“时玩”等,依凭着日益兴盛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发展,逐渐成为城镇市民广泛参与的行为,不再专属于士大夫阶层。
随着经济因素的大规模渗入,以文化资源为依托的文化消费品生产日益兴盛,文化因素逐渐成为一种“资本”。作为文化消费者和文化生产者主体的士大夫阶层,认识到了文化的资本作用,自觉地将文化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来使用。文化活动的经济化及经济活动的文化化对塑形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有相当大的作用。可以说,晚明时期的中国,士大夫的素质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就当时各类文化活动中的经济因素作一探析,并力求寻绎其背后的原因,是理解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门径,甚至是理解“文化中国”的一个门径。
一 “士商合流”
自汉代以来,重农轻商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四民之首的“士”不仅拥有思想文化的独占权、解释权,还是统治集团的构成成员;农被称为“本业”,工商乃是“末业”。在自然经济时期,“崇本抑末”无疑是平均社会财富、抑制豪强兼并的一个可行措施。以“末业”逐利的商人无论在财富积累上如何“富酹公侯”,社会地位向来低下,社会形象一直不佳。
但在明代中后期,这种情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流频繁,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商人阶层在急剧增容,他们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社会阶层地位也在发生着变化,商人在向“士”的阶层流转、士越来越多地干起了逐利的营生。有时候,在商人和士人之间,界限变得很模糊。传统的义利观,也随着这一变化而发生着悄然的改变。
明人何良俊的家乡是当时的富庶之地松江,他曾经对松江一地从事商业人口的增加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即大部分居民还是从事农业,但“自四五十年来……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耕作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人口的转移,转移的人口,有“蠹食官府”,即成为政府管理体系中的临时、辅助人员的胥吏;有进入城镇或在乡村“游手趁食”,后一种人物的出现其实具有某种城市发展的功能性需要。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正说明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迅速。
商人不仅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并且凭借其财势,已经隐隐然与自标清高的士大夫分庭抗礼。陈登原的《国史旧闻》曾经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个名叫邹望的无锡富豪与本乡官僚顾可学兴讼,而对他进行“经济封锁”的故事:“城内外十里,悉令罢市,顾在寓,几无菜腐鱼肉为餐。”这位炙手可热的工部尚书大人,已经不是过去广有田亩、事事不必仰给于人的田舍翁,而是居住在城市的居民,他的衣食住行离不开商人。
二 义利观的变化
义利之辨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耻于言利,曾经是士大夫普遍的信条。如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① 又如孟子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仁义而已”,与士君子所担当的重大责任相比,孜孜于个人微末小利就显得很没有品味,利轻而义重,在“生”的条件获得满足的前提下,一个有道君子应该“治生不屑于谋利”②。当然,士人谋名谋利也自有他途,那就是参加科举。
在这一时期,影响于士大夫及整个社会最显著的思潮,莫过于王阳明心学的兴起。王阳明倡导“致良知”,主张“心即是理”、“心外无物”,既然“心即理”,那么求为圣人之道,就不必假于外求,只要向每个人的内心去求索即可,“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③。余英时认为,“阳明之学‘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之间造成的隔阂”④。
王阳明之后,有一位王艮,他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⑤,而这位学者本身就是一位商人,以商人的身份成为一位有影响的儒家学者,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到了李贽,更是提出“天下尽市道之交”,用今天的话说,一切人际关系都可以用交易的原则进行描述,孔子和七十子的关系也无非如此,“身为圣人者,自当有圣人之货”,这“货”又正好是七十子需要的⑥。
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的“四民”高下的划分,过去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虽然“四民之业,惟士为尊”,但是也不妨“无成则不若农贾”⑦,甚至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同时也颠覆了“本末”的旧说,认为“工商皆本”。如李梦阳就认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货财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⑧。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缙绅大夫多以货殖为急”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了。何良俊也描述了士大夫如何通过科举中式之后获得的社会地位来谋取经济利益的情况:“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日逐奔走于其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⑨。作为社会思潮和风尚的倡导者,士大夫这个角色的转变为义利观的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徐阶在苏、松一带广有田宅,“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⑩,此外他还在松江、苏州和北京开设钱庄逐利(11)。一时名士如王世贞、董份等人,也都是通过贸迁有无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豪(12)。
甚至在一些地方,科举的魅力已经逊于经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13)
三 以文化为资本
不耻言利的观念使得“业儒”的传统士人的生存方式发生着变化。士人过去所拥有的文化技能,正逐渐并愈加普遍地成为他们经营商业的资本,自觉地将文化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来使用,这种行为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治生”。商人的力量在壮大,他们的社会影响日趋活跃,文人能不能“治生”有时候甚至已经不仅仅是逐利的问题,如上所述邹望与顾可学的故事所预示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正在受到财富拥有者的挑战。王阳明的学生咄咄逼人地问:“岂士之贫,可坐守不经营耶?”他也只能回答:“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只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14)
文人“终日只作买卖”,当然还是先从他们擅长的诗文书画开始。替人写诗、词、歌、赋,序、跋、传、铭等以获取润笔费成为文人特别是著名文人的经济来源之一。提供这项服务的文人,从内阁首辅、大学士、六部尚书,到各级官员,乃至一般的生员、没有功名的“山人”,几乎遍及士人的各个阶层。明中期以后,付润笔已经成为社会公例,如常熟文人桑悦,“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15) 此公从未白写文章,即使有人托关系强求,也要求摆上银元宝来“发兴”。
著名文人的文章往往价格不菲。王应奎《柳南续笔》曾经提到钱谦益晚年贫困,专门以卖文为活,甚至在病重时仍旧孜孜于此:“甲辰夏卧病,自知不起,而丧葬事未有所出,颇以为身后虑。适盐使顾某求文三篇……润笔千金。……越数日而先生逝矣。”(16) 三篇文章可获得千金之偿,足为料理身后事之用,此可谓“老于文章”。又据李日华自己在《味水轩日记》中的记载,项又新为其母六十大寿而向李求文,这篇文章的代价是“以黑缘绒一端,靖窑白瓯四只,文徵仲行草书《独乐园记》一册,陈白阳花石一幅,馈余作润笔”(17)。项又新为大收藏家项元汴之子,也是李过从甚密的朋友,朋友之间尚文价如此不菲。
至于画家,从吴门画家开始,通过绘画来谋生已经成了非常正常的事情:“唐子畏(唐寅)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薄面题曰‘利市’……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是见精神否。’(俗以取人钱为精神——原注)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清物,则曰:‘青羊绒罢。’”(18)
当然文人的“治生”非止一端,他们有的出入大人之门为幕府,有的印书刊文,有的专门买卖字画古董等。为了获得以售其技的机会,有的文人成了日奔走于权贵门下的清客,当时称之为山人。如著名的山人陈继儒,有诗讽刺他是“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文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19)。
《万历野获编》记载过山人黄白仲,“惯游秣陵,以诗自负,僦大第以居。鲜衣盛服,乘大轿,往来显者之门”(20)。居然可以凭借打秋风成为巨富。“山人”可以说是在科举正途难以走通的情况下不少文化人的一种谋生选择,实际上,他们已经是职业的文化人。
而文人与商人的合作,在刻书业最为典型。冯梦龙因为“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21)。所谓“贾人之请”,就是双方基于利益而进行的资本与智力的对接。
四 社会各阶层消费趋向的文人化
明代中叶开始,追求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时髦的风尚。过去由士大夫阶层专享的文化享受,不仅富商大贾、富裕市民,甚至一般大众也开始涉略。既然“四民”之间都无所差别,那么过去的专属,今天则不妨一体通用。
“僭越”提供了使得市民可以向士大夫仿效的通道。所谓“满街皆圣人”,意味着士大夫不是文化独占者。文化消费不再专属于士大夫的特殊消费,而是贯穿到整个社会阶层,低阶层的文化消费有了通道。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为恢复汉人衣冠,将有关服饰、厅堂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建立了严格的法律惩处措施,如《大诰续编》:“一切臣民所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毋得僭分。敢有违者……事发到官,工技之人与物主各各坐以重罪。”(22)
但是,逐渐地,这样的规定就在日新月异的服饰变迁中被实质性地废弃了。如张瀚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经丝绞罗,六品以下用绞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僧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23)
所谓“僭越”,就是不顾自己的社会身份,对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阶层的一些穿着、居室、消费习惯的模仿。由于士大夫阶层对此有独享的权利,那么他们的所服所好,必然地在“僭越”的气氛中被一次又一次地拷贝,进而文化集团的消费趣味,就成了整个社会的消费趣味。反过来,这种趣味又加强了文人士大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销自己的技能与立场更加顺畅。如松江一地,“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姐,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24)。这段记载形象地说明了豪门贵室是如何将“新事百端”推广于社会的。
士大夫集中于园林、古董、字画、时玩、家班戏乐等“雅”而耗费颇“靡”的文化消费,需兼具学养和巨金方消费得起。
商人的崛起使其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士大夫一样消费,于是江南地区呈现出了“郁郁乎文哉”的盛况。商人们在江南一带大规模“招养食客,资助士人,校雠书籍,从而在淮、扬、苏、杭一带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氛”。商人们“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25)。
商人们在江南地区建造的园林也非常多,这些园林大都取法自然、朴素淡雅,有的商人凭自己的理解将画家作品中的画意通过造园工匠之手转化成现实,还有的商人专门聘请书画家和园林设计师直接参与园林的建造。
经济发展和商人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巨商在文化消费上可以比肩于士大夫,而且中小商人群体的扩大也带动了整个市民阶层的文化消费。修建园林、购买字画、古董、时玩、藏书、组织家乐戏班,士大夫的文化消费充满了文人雅趣,且颇为奢靡。身份和经济上的差距并不妨碍市民阶层对于士大夫文化消费的模仿。书画、时玩、古董的赝品和仿冒品在当时大规模地出现,虽然不排除有人以假乱真谋取财富,但很多仿冒品是为了满足市民低层次的文化需求,即知假买假。
市民对于通俗读物的需求推动了这一时期印刷业的商业化。销路广大的大众读物占据了印刷业的半壁江山,包括通俗文艺作品、通俗实用读物、童蒙课本、时文选本、年画、日历及迷信用品等,一改此前印刷业主要供给经史子集的状况,大众读物同样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它其实无形中达到了对于下层民众进行传统文化教化的目的。为了满足大众的需求,有些读物有文有画,生动易于理解,民众乐看爱买。读书不再仅是“读书人”的特权。
大众对于戏曲的消费不似士大夫家的亭台楼榭,演出者也不是蓄养的加班,但是江南一带,每逢岁时节令、集市贸易,职业戏班往往到空间广阔、可容纳大量观众的地方演出,比如田间、通街或建筑物前的空旷之处,这种演出规模一般很大,可容数百成千人观看。“架木为台”,临时搭建,然后“慢以布,环以栏,颜以丹款”,戏班往往选择喧闹的、最易聚集民众的地方来进行演出。
总之,士大夫阶层掌握着社会价值取向的话语权,引导文化消费风尚,巨商对此亦步亦趋,社会大众模仿复制,消费本阶层的通俗文化产品。晚明时期,中国进入了第一个较具普遍意义的“文化消费时代”。
注释:
① 《论语·里仁》。
② 李开先:《闲居集》卷七《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敏渭崖霍公墓志铭》。
③ 王守仁:《传习录》,三一九条。
④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91、51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 王艮:《王心斋全集》卷四《杂著·明哲保身论》。
⑥ 李贽:《续焚书》卷二《论交难》。
⑦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三○六。
⑧ 李梦阳:《空洞集》卷四四。
⑨ 何良俊:《四友斋丛书》卷三四。
⑩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四,页39,中华书局,1984年。
(11) 傅衣凌:《明清封建地主论》,《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12) 范金民:《明代江南进士事功述论》,赵毅、林风萍主编:《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597,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 《雍正朱批谕旨》第47册。
(14) 王守仁:《传习录拾遗》,十四条。
(15)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文士润笔”条,页16,中华书局,1982年。
(16)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卖文条”,页180,中华书局,1983年。
(17) 《味水轩日记》卷一“十一月三日”条,《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页1107。
(18)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文士润笔”条,页16,中华书局,1982年。
(19) 黄协勋:《锄经书舍零墨》卷三。
(2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三,中华书局,1959年。
(21) 冯梦龙:《喻世明言·序》
(22) 朱元璋:《大浩续编·居处僧分第七十》。
(23) 张瀚:《松窗梦语》。
(24) 范镰:《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
(25) 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页57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