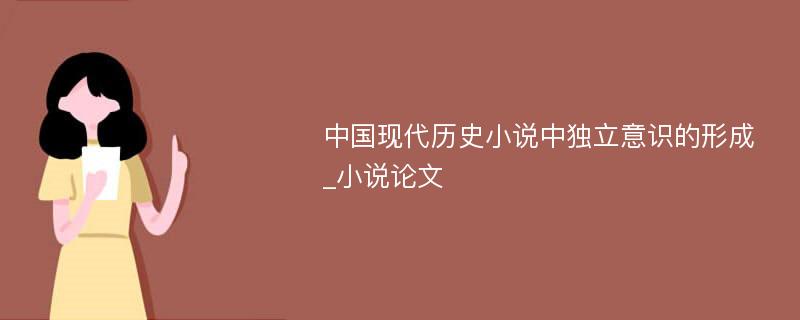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独立意识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历史小说论文,意识论文,独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有着悠久而强大的史传传统,这种强大的史传传统一方面给文学特别是小说提供丰富滋养,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从史传中受益无穷;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和史传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历史小说往往通过攀附史传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甘作“史传”之附庸,“羽翼信史而不违”①,以能作为“正史之补”而沾沾自喜;把“史家妙品”看成是对自己的最高褒扬。这严重妨碍了小说包括历史小说独立意识的产生。到了近现代,随着封建价值体系的崩溃,笼罩在史传上面的神圣光环消失,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从史传的压抑中解脱出来。在本文中我想探讨的问题是,在近现代,从史传取材的历史小说怎样从史传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逐渐获得自我意识或独立意识。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独立意识表现于多个方面,本文只围绕有联系的三个问题加以探讨,这三个问题分别是:“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名称之辨析、历史小说的历史性问题、历史小说的小说性问题。
一、“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
在名称上,中国古代有“讲史”、“演义”,而无“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一名的最早出现为1902年。此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发起“小说界革命”。在同年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14号上有一篇署名“新小说报社”的文章,名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此文称《新小说》所介绍的小说有“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等十类,“历史小说”被排在第一位,可看出梁启超对它的重视。历史小说被定义为:“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厘然已。”② 由此定义可看出,虽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小说报社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小说”的名称,且对历史小说给予了极大重视,但他们的历史小说观依然停留在传统“讲史”、“演义”观的水平上,这与他们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忽略小说作为文学的自身特征有关。这时期,持有此种历史小说观的不在少数。陆绍明把小说分为十一类,“历史小说”同样位居第一,他对历史小说的特征作了如下描述:“例胜班猪,义仿马龙,稗官之要,野史之宗。万言数代,一册千年,当时事业,滴纸云烟”。③ 吴沃尧认为历史小说“谓为小学历史教科之臂助焉可,谓为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焉亦无不可。”并赞同友人“历史小说者,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的看法。④ 可以说,忽略或不理解小说的文学特性,就不可能有历史小说独立意识的产生,而认识到小说之文学特性的,皆对历史小说采取了更为现代的看法。如黄人认识到小说是“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⑤,这是一种现代文学观,有了现代文学观,才有可能对传统的“历史小说观”提出自己独特的批评意见:“若近人所谓历史小说者,但就书之本文,演为俗语,别无点缀斡旋处,冗长拖沓,并失全史文之真精神,与教会中所译土语之《新、旧约》无异,历史不成历史,小说不成小说”⑥。黄人还认识到历史小说创作与史传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写作路径:“盖历史所略者应详之,历史所详者应略之,方合小说体裁,且耸动阅者之耳目。”⑦ “方合小说体裁”一语,说明他已明显意识到历史小说应以文学为本位,而不是攀附史传,仰人鼻息。稍后于黄人,周作人同样从小说是“文章也,亦艺术也”的观念出发,对传统的历史小说观作了批评,提出“历史小说乃小说取材于历史,非历史而披小说之衣”的观点。⑧
新小说报社在使用“历史小说”一词后,这一名称便与“政治小说”、“军事小说”等其他名称一同流行开来。这种小说分类植根于梁启超等人对小说社会功能的看重,“政治小说”、“军事小说”的提法,不自觉地暴露了分类者意在“政治”“军事”而不在“小说”,“历史小说”同样如此,这点可从新小说报社对“历史小说”的定义中看出。因此,这个名词在当时的迅速流行并不说明人们已经拥有了现代历史小说观,恰相反,只不过说明了传统讲史、演义观在人们头脑中的巨大影响而已。因此,对这样一个普遍流行的“时髦”名词进行一番辨析就显得很有必要,通过辨析,可以澄清人们对历史小说的认识,有助于历史小说独立意识的真正确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鲁迅、瞿世英有了“历史的小说”的提法。在《〈罗生门〉译者附记》一文中,鲁迅称《罗生门》是一篇“历史的小说”,而不是“历史小说”,作为“历史的小说”,《罗生门》的特点是“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⑨。无独有偶,瞿世英也指出历史小说一名“似不妥”,并和鲁迅一样使用了“历史的小说”这样一个比较拗口的名词⑩。他们不约而同反对“历史小说”一词的使用,主张改用“历史的小说”这样一个名词,从中可隐约看出他们对流行的传统历史小说观不满,并立意标榜一种新的“历史小说”观。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小说”一词在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曾被使用过,鲁迅、瞿世英对此词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日本作家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特别是森鸥外的影响。不过,鲁迅提出“历史的小说”一名,反对采用“历史小说”的提法,固然是受日本学界的影响,但其用心,应该是害怕“历史小说”名词的使用引起更多误解,希望借“历史的小说”一名词的使用,使人们更清楚、准确地认识历史小说的小说性质,从而根本上把它与传统的“讲史”、“演义”区别开来,这种严谨学风和良苦用心值得后人学习。鲁迅、瞿世英对“历史的小说”一名的使用说明了现代历史小说独立意识的进一步增强。遗憾的是,可能因为拗口,这个名词最终并没有取代“历史小说”一词而被大家广泛使用。
二、历史小说的历史性
鲁迅、瞿世英对“历史的小说”一词的使用,强调的是历史小说的“小说性”,梁启超等人的“历史小说”一词强调的是历史小说的“历史性”。名称的不同反映了历史小说观的差异。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不管是“历史的小说”,还是“历史小说”,它们都体现了这一小说体裁身份的双重性和暧昧性。这一体裁的自身特点决定了组成它的两要素即“历史”与“小说”之间,存在着既紧张冲突又亲密合作的复杂关系,因此,现代历史小说在确认其自身的过程中,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其实要解决的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历史小说的历史性,一个问题是历史小说的小说性。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我们首先谈第一个问题。
历史小说既然是历史小说,它的取材只能是历史而不是其他,而要从历史中取材,便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作家怎样看待历史与历史记述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历史观问题。在传统的讲史、演义小说中,作家与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是统一的,都是建立在儒家教义的基础之上。因此,当作家由史传取材时,他对史传记述抱的是毕恭毕敬的态度,对史传的精神不敢有丝毫违背,史传的记载代表“圣经”和“律法”,对他不但“信”而且“威”。然而,随着封建社会解体,以儒家教义为核心的一套旧价值体系彻底崩溃,旧史学消亡,新史学诞生,新的历史观包括资产阶级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取代的旧的历史观,于是,对于已有的“历史”及其载体“史传”,就必然会产生新的解释与看法。梁启超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11) 在梁启超那里,正统史传的内容、价值及叙述方式皆受到了否定与质疑。
正统史传的权威建立于“信史”的标榜上,但随着史学界“疑古”思潮流行,以及对历史叙述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信史之“信”越来越遭受人们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传统“信史”与“小说”的真值在现代发生了一次戏剧性的倒转,信史不“信”,而小说不“假”:“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12) 这种观念,甚至被历史学家所赞同:
小说并不是“御用”的产物,无所谓拘忌和束缚,以社会史料的价值论,与其读完一部某时代的史书,其了解程度反不及看完一部那同时代的小说。(13)
在吴晗那里,历史与小说的严格界限已不复存在,历史成了“小说”,因其不信;小说成了“历史”,因其真实。历史与小说“真值”的倒转,说明了历史观、文学观的巨大变迁。正统史传在历史学家和小说家那里成了有待进一步加工的原材料:需要他们根据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给予重新阐释,这也是现代历史小说家处理历史记述的共同态度。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原初的历史史实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存在着“我眼中的历史史实是什么”的问题,这一观点由谢六逸表达得非常明显。在谈到现代小说的主题时,他认为一部作品的“主题”有时早就存在于材料里,但多数是由作家对于材料的解释产生的:“对于一种材料,一个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下解释的时候,将有几种不同的‘主题’发生,是难说的”,他的结论是:“作家对于材料的解释,成为重大的问题。”(14)
谢六逸这里所说的材料当然包括历史记载。鲁迅认为历史小说创作应“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在现代人对古事的再度阐释上,这一点也可从鲁迅本人的作品得到验证,茅盾便认为《故事新编》给予后来作者影响很大的一点便是“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15) 作为一个历史小说的实践者,郑振铎在这方面所持观点与鲁迅相同,针对宋云彬《玄武门之变》拘泥史实的创作倾向,他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新的历史故事,我以为至少不是重述,而是‘揭发与解释’”。(16) 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郭沫若起步较早,其观点应该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自己历史小说的创作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喻”。(17) 这种观点是从他的创作中直接总结出来的。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历史小说家在重现历史史实时,很多都抱着“求真”的信念,想“掘发”历史的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也是“信史不信”的观念影响所致,如郭沫若认为:“古人的面貌早经歪曲,或者本是好人而被歪曲成了恶人;或者本是无赖而被粉饰而了英雄,作者为‘求真’的信念所迫,他的笔是要采取着反叛的途径的。”(18) 在此观念指导下,《孔夫子吃饭》把“大圣人”的“领袖欲”那一面“恢复”了过来;《秦始皇将死》着重描写了秦始皇将死前的忏悔心理。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郭沫若笔下的孔夫子与秦始皇是否如他所说的那样,一定就是古人的“原貌”呢?应该说并不是,他们其实也是郭沫若自己眼中的“孔夫子”与“秦始皇”,是经过作家“现代眼光”过滤而成的一个全新创造。可以说,不管现代历史小说家怎样标榜“求真”,“还古人古事一个本来面目”,他们笔下之真仍然是作家用现代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解释后之“真”。现代阐释学认为,绝对的历史之真很难达到,人们只能达到相对之真,因为这“真”必然受主体所处时代以及主体自身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刘圣旦是三十年代出现一个历史小说家,他把自己出版的一部历史小说集命名为《发掘》,目的是要发掘“埋葬在历史里的故事”,但他明确宣称,对于历史“至于应如何看法,那自然,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见地”。(19) 他本人对历史史实的发掘, 就是站在同情农民起义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立场上进行的。其他,如茅盾、郑振铎、孟超等人对农民起义的歌颂,显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观支配下,对历史作重新解释的产物。对历史人物进行大胆的重新阐释,这种创作倾向鲜明地体现在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中。他的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的重要特色,在于用弗洛尹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重新阐释古人的行为。冯至四十年代创作的历史小说《伍子胥》,在对历史人物的解释上比施蛰存走得更远。在冯至笔下,伍子胥对生与死的抉择,流亡途中的生命体验,皆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在冯至和施蛰存那里,历史小说历史性的获得,都不是通过一味信守史传达到的,恰相反,在不违背起码的史实基础上,现代知识的运用,创作主体生命体验的积极投入,皆有效激活了历史,使人物再生,历史小说的历史性也由此产生。而那些拘守史传的,反而会落入“历史不成历史,小说不成小说”的身份危机中,到头来也终将失去其历史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多数现代作家、理论批评家一致认为历史小说历史性只能从对史传的颠覆与再度阐释中产生,一味信守史传反而会使历史小说失去历史性。由此可见,在对历史小说历史性这个问题的解决上,现代作家、理论批评家显示了充分的自我独立意识。我在上文已经指出,现代历史小说在确认其自身的过程中,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性,一个是小说性,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同时必然要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因为作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不但要意识到自己创作的是“历史”小说,还要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创作的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历史性是历史小说的特殊性,但历史小说作为小说的普遍性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在“历史性”与“小说性”两者中,“小说性”占据着本体地位,就如杨书案先生所说,“‘历史小说’这个名称,它的基本词,或者说基本概念是‘小说’”。(20) 现代作家对历史小说“小说性”或“文学性”的清醒认识,标志着现代历史小说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最终形成。下面就谈谈这个问题。
三、历史小说的小说性
现代作家对历史小说“小说性”的认识首先表现在他们对传统“讲史”“演义”体“小说”身份的清算上。随着现代文学观的确立,西方关于小说的定义“在想像诸事实之系列里显示人生之真”(21) 被大家普遍接受,这种小说观认为, 小说作为现代艺术之一种,其所表现的只能是“想像的事实”,而不是“历史的传记”。这种主想像、主创造、主虚构的小说观确立后,成为一种价值尺度,现代作家用它对中国古代的小说类型进行重新排序和定位,传统的“讲史”、“演义”小说由最高等级被降至最低等级,甚至被驱逐出文学殿堂。胡适认为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全用历史的事实,便成了‘演义体’,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没有真正‘小说’的价值。”(22) 在胡适看来,历史小说要取得“小说”的合法身份,必须在历史事实之外加以艺术的想像与虚构,在“历史”与“小说”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演义体”丧失了这种张力,便失去了小说身份。1944年,浦江清在追溯中国小说的发展演变时也指出,中国小说中讲史、演义小说,“既要敷衍史事,即不能发挥虚幻文学的最大功能。……严格说来,已不合乎西洋意义的小说,更不是现代意义的历史小说”(23)。从演义体小说地位的一落千丈,可看出历史小说观念的巨大变迁。
现代作家对历史小说“小说性”的认识其次表现在他们对历史小说虚构特质的强调上。现代文学观是一种虚构文学观,这种虚构文学观决定了现代作家对历史小说的虚构性有更充分的认识,这一点可从鲁迅和郁达夫的历史小说创作和理论得到说明。鲁迅曾将历史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一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24) 对后一类历史小说,鲁迅更为欣赏。1934年, 郑振铎以郭源新的笔名发表历史小说《桂公塘》,这篇小说系根据文天祥《指南录》写成,属“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类。鲁迅对这部作品所作评价是:“但以为太为《指南录》所拘束,未能活泼耳,此外亦无他感想。”(25)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还是“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固然与作家创作风格、审美趣味的差异有一定关系,但史实处理的不同态度也反映出作家历史小说文体独立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作家创作主体性能否充分发挥的问题。若过为文献所拘,对之亦步亦趋,则艺术想像与虚构的空间会相应缩小,作家对史传的依附性随之变大,发展到极端,则会使历史小说偏离文学本体,成为“故事体的中国史”,从而丧失其小说性或文学性,历史小说的审美功能也将丧失。鲁迅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他描述自己《故事新编》的创作“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26),对这里的“信口开河”一词不能只作字面意义上的理解。“信口开河”指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在不违背基本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家对历史所进行的大胆想像与虚构。这种大胆想像、虚构的目的是为了复活古人古事,而历史小说最终为“小说”而不为“历史”也在此一举。由于鲁迅有比较强烈的历史小说独立意识及对史实处理的合理把握,《故事新编》才成为现代历史小说的典范。和鲁迅使用“信口开河”一词相似,郁达夫用“空想”一词来强调作家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大胆想像和虚构:“小说家当写历史小说的时候,在不致使读者感到幻灭的范围以内,就是在不十分的违反历史常识的范围以内,他的空想,是完全可以自由的”(27)。这种“空想”观建立在“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的认识基础上。
历史小说必须取材于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必然要贯穿着“贵实”与“贵虚”或“贵幻”的争论,在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贵实”与“贵虚”两种创作实践和主张,鲁迅将历史小说分为“言必有据”与“随意点染”就说明了这种情况。由于旧的文学观念的制约,在古代历史小说创作中,“贵实”派一直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而在现代,随着虚构文学观的占据主导地位,在历史小说创作和理论中,“贵虚”派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一派的代表有鲁迅、郁达夫、许杰、冯至、巴金、李拓之、施蛰存、孟超等人。鲁迅的《故事新编》出版后,许杰对其“油滑”手法给以很高评价,他认为,不能以“言必有据”来要求《故事新编》,“这种地方,如果一定要顾全到史事,要问史实是否有此等根据,那么,作品的精神,就会无形被阉割了的”。“所谓历史小说,与其说是历史,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的记录,毋宁说它是小说,是文学,是艺术创造”。(28) 冯至的历史小说《伍子胥》可以说对历史进行了最为大胆的想像和虚构, 称得上是历史诗化小说的典范,这部小说的创作与他“不顾历史,不顾传说”(29) “不受历史传说的约束”(30) 的创作理念密不可分。巴金坦言自己的小说《马拉的死》“末一段与历史事实不合,但和历史记载决不会有多大的冲突”(31)。孟超也认为“小说终究不是历史,写小说剪裁、铺张、描写、想像,这些笔法皆不能免”(32)。以上诸人皆反对“言必有据”的创作方法。和他们比起来,“言必有据”派的力量明显要小得多,只有宋云彬、郑振铎等数人而已。“贵实”派力量的衰微也说明了现代作家对于历史小说的本体特征与审美特性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
现代作家对历史小说“小说性”的认识还表现在他们对文学创作与历史创作不同特质的把握上。历史小说创作属于文学创作,这决定了文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历史学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不同的,现代作家对这一点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在《历史小说论》一文中,郁达夫比较了历史学家与小说家面对历史的不同态度:
小说家的读历史,和历史家的读历史不同。历史家当读历史的时候,要以理智判断,辨别记事的真假,推寻因果的关系。而小说家读历史的时候,只要将感情全部注入于这记事之内,以我们个人的人格全部融合于古人,将古人的生活,感情,思想,活泼泼地来经验一遍,完全不必起道德的判断,考证的申辩的。(33)
历史家面对历史采取的是科学、理智、考证的态度,小说家面对历史采取的是艺术、情感、审美的态度。虽然小说家在具体创作过程中,面对历史记载不可避免地要引入科学、理智、考证的态度,但若将此种态度发展到极端,以此种态度为主导,就会导致小说家对自己身份的误认——小说家变成了历史学家。可以说,“言必有据”派对于史传记载的处理,就是将此种科学的、理智的、考证的态度发展到极端的结果,不能以艺术、情感、审美的态度去复活古人古事,造成此类小说艺术审美品格的降低。因此可以说,历史小说家文体独立意识的另一重要表现,也就是他能切实认识到自己“小说家”的身份,以情感的、艺术的、审美的态度去亲密接触历史,复活历史。《采石矶》这篇成功的历史小说,便是作家以情感的、艺术的、审美的态度处理古人古事的一个结晶。
注释:
①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出版,第111页。
②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新民丛报》14号(1902年)。此文实为梁启超所作。
③ 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载《月月小说》第1卷第3号,1906年。
④ 我佛山人(吴沃尧):《〈两晋演义〉序》,载《月月小说》第1卷第1号,1906年。
⑤⑥ 摩西(黄人):《〈小说林〉发刊词》,载《小说林》第1期,1907年。
⑦ 蛮(黄人):《小说小话》,载《小说林》第2期,1907年。
⑧ 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载《河南》第4、5期,1908年5、6月。
⑨ 鲁迅:《〈罗生门〉译者附记》,载《晨报副刊》1921年6月17日。
⑩ 瞿世英:《小说的研究》(中),载《小说月报》第13卷18号,1922年8月。
(11)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九·新史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
(12) 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开场白》,艾以、曹度编:《废名小说》(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38页。
(13) 吴晗:《历史中的小说》,载《文学》第2卷第6号,1934年6月1日。
(14) 谢六逸:《小说创作论·主题小说》,见《文艺创作讲座》第1卷,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版。
(15) 茅盾:《〈玄武门之变〉序》,见《玄武门之变》,开明书店1937年版。
(16) 郑振铎:《〈玄武门之变〉序》,见《玄武门之变》,开明书店1937年版。
(17)(18) 郭沫若:《〈从典型说起——豕蹄〉的序文》,载《质文》第2卷第1期,1936年10月10日。
(19) 刘圣旦:《发掘》,上海天马书店1935年版,第12页。
(20) 杨书案:《历史小说创作回顾》,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21) 俞平伯:《谈中国小说》,载《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1928年2月10日。
(22) 胡适:《论短篇小说》,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23) 浦江清:《论小说》,见《浦江清文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24)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25) 鲁迅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信,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页。
(26)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27) 郁达夫:《历史小说论》,见《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
(28) 许杰:《论鲁迅的历史小说》,见《文艺·批评与人生》,江西战地图书出版社1945年出版。
(29) 冯至:《〈伍子胥〉后记》。
(30) 冯至:《诗文自选琐记》。
(31) 巴金:《〈沉默〉序》。
(32) 孟超:《〈骷髅集〉自序》,见《骷髅集》,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印行。
(33) 郁达夫:《历史小说论》,见《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1926年4月16日。
标签:小说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玄武门之变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鲁迅论文; 故事新编论文; 梁启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