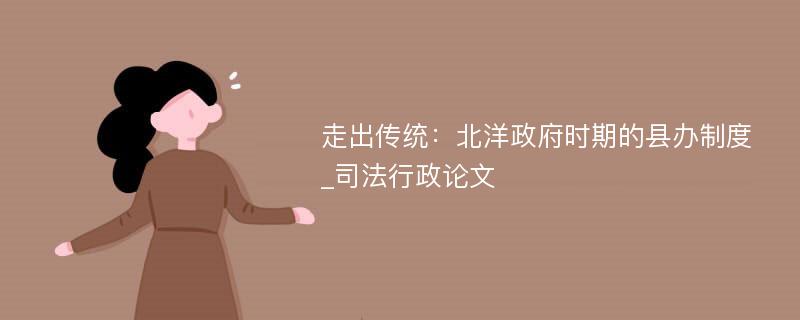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公署论文,时期论文,传统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5-0053-06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政治动荡,国家分裂,民生凋敝。但是,自20世纪初开始全面启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却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县行政制度方面也是如此。这一时期的县公署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承袭了清代的州县衙署制度,但后者组织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主要弊病已经开始得到克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县行政制度已经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关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学术界迄今尚无专题研究。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194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和钱实甫著《北洋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对于北洋政府关于县公署内部组织和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制度设计曾有记述,但极为简略,且仅限于制度设计而不及其施行情况。此外,80年代以来,一些地方人士根据自身回忆或采访撰文记述新中国成立前本地县乡行政的运作情况,其中对于北洋政府时期县公署裁革幕友、胥吏和县知事兼理司法等情况有所涉及(载各地政协编辑的地方文史资料)。这些记述为我们进行有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但其本身尚难视为研究性工作。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北洋政府的有关制度设计为经,以散见于各种史料中的具体实例为纬,相互参证,加以探讨,以揭示这一时期县公署制度的实相,并分析其承袭清代旧制而又有所革新的双重性质。
一 清代州县衙署制度的落后性
清代州县行政实行“正印官”独任制,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佐贰官员均非“正印官”属员,不被纳入主干行政系统;一邑之中,财赋、司法、治安、农桑、教化、赈济等全部政务均责成于知州、知县。州县官员的治所称衙、署,由大堂、二堂等公干场所、州县官家庭及亲随居住场所和胥吏房、差役房、库房、监狱等组成。(注:州史目、县典史作为州县官的属员,其官署一般设于州县治所内;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佐贰的官署或设于治所内,或设于冶所外,均属于独立官署。)州县官到任,率自辟之幕友和人身依附于己的家丁、常随入住州县衙署,以幕友主持钱粮会计稽核、诉讼公文批答等政务,以常随、家丁管理印信、仓库、监狱及充当门丁、跟班,以吏、户、礼、兵、刑、工等房胥吏办理文书档案事务,以壮、快、皂等班差役办理催征赋税、指传人证、缉捕盗贼等外勤事务。这种衙署,既是官吏的办公场所,又是他们及其家庭的私人居所;而办公人员,又多为州县官任用的私人。清代州县衙署的这种建筑布局和组织结构,充分体现了当时州县行政的封建家长制、家产制特征,故清代州县行政制度可以名之为衙署制度。
从现代的角度看,清代州县衙署制度存在以下主要弊病:
第一,州县官事务繁剧,主要履行政治统治职能而很少履行社会职能。就制度而言,清代州县官本应在一邑之中兼负政治统治和社会建设职责,“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兼平决狱讼,凡户口、赋役、钱谷、赈济、给纳之事皆掌之。县民男女有孝悌、行义、公忠、节烈闻于乡闾者,申请奖恤以昭激劝而励风俗。地方有警,则躬督属员及驻防官兵,率民壮干捕上紧防剿以保无虞。”[1](卷二,政治志)但在“正印官”独任制下,兼理这些政务为知州、知县力所不能及,他们往往“仅以钱谷、狱讼为职务,民间利病漠不相关”[2](下册,p725),其地方建设职能因此而废弛。
第二,州县官兼理行政与司法,不符合现代政治的权力分立和制约原则。
第三,“正印官”之下不设职能性官员,而以幕友、家丁、胥吏、差役等私人势力来履行公权,因此而造成吏治的腐败。幕友、家丁、胥吏、差役不具有正式庄重的公职身份,不享有合法薪饷、津贴等公职保障,不受国家制度的有效监督和约束,因此势必导致贪污、受贿、勒索的合法化或半合法化,必然导致州县行政的人治化、黑社会化。对此笔者曾有撰文阐述,不再赘述。(注:参见《清代州县治理结构述要》,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辑(2003年)。)
第四,办公费没有保障,靠陋规、勒索维持行政运转。清代实行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没有州县一级财政,包括州县官俸廉在内的州县办公费,在州县经手征收的田赋等国家“正项”中坐支,称州县存留。州县存留的数额和开支项目均由国家规定,载诸《赋役全书》。由于州县存留数额极少,致使大量必不可少的支出没有合法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存留制度形同虚设,州县财政实际上由州县官大包干,即不问各州县合法收入如何,州县官均必须保证完成额定起运藩库任务和本州县各种费用的开支,而州县官的浮收、贪污、勒索和收受陋规也就因此而被合法化或半合法化。于是,州县财政成为州县官家产。州县官为了增加自己的个人收入,对在州县存留中列支的壮、快、皂等各班差役的工食银一般不予发给,州县衙署各班差役“惟借鱼肉乡民以自肥”;衙署各房的办公费则本来就不在州县存留中列支,书吏“均无薪给,纸笔亦由自备,惟借陋规以资生活(如考试及狱讼当事人均有应纳费用,余可类推)”[3](卷六,法制略)。(注:参见拙文《清代州县财政探析》,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2001年第1期。)
清代州县衙署制度的上述弊病,是中国传统县政体制封建性质的主要表现。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克服清代州县衙署制度的这些弊病,从而使得中国的县行政体制开始走出传统迈向现代化。
二 县公署组织的改革
州县衙署组织的改革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过程中就已经开始。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要求裁汰州县胥吏和差役。上谕说:州县衙门书吏“往往勾通省吏,舞文弄法,朋比为奸”,州县差役“百般扰害闾阎,甚至一县白役多至数百余名”,命令“各衙门额设书吏均分别裁汰,差役尤当痛加裁革,以期除弊安民”[4](吏政部,卷首,谕旨)。由于这种改革没有能够设计一种新的机制来承担胥吏和差役所承担的行政功能,因此不可能得到落实。至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直省官制通则》,对州县衙署组织的改革作出了建设性设计。它规定:将从前各州县所设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典史等大多处于州县主干行政之外的佐贰杂职一律裁撤,同时设置“佐治各官”办理州县各方面行政事务,其中警务长掌理消防、户籍、巡警、营缮及卫生事宜;视学员掌理教育事宜;劝业员掌理农工商务及交通事宜;典狱员掌理监狱事宜;主计员掌理收税事宜[2](上册,p503~510)。“佐治各官”既不同于虽处州县主干行政系统之内但却不属于国家职官的幕友、胥吏,也不同于虽属国家职官但却处于州县主干行政系统之外的佐贰。佐治各官的特点在于,他们一方面由司道考录、督抚委任并报部备案,属于国家正式职官;另一方面作为职能性官员又隶属于“正印官”。这样,“正印官”独任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任用幕友和胥吏办理州县行政事务的作法就被否定,州县衙署组织开始具有科层化特点。同年清政府还下令,裁汰州县差役后以“增给饷薪”和经过训练的巡警来替代其职能[5](p5645~5646)。
《直省官制通则》未及实行而清亡,北洋政府时期,只有个别省份的县公署组织曾与《通则》模式相仿。(注:山西省1918年开始实施《县公署组织条例》,各县行政公署设立承政员、承审员、主计员、管狱员、实业技士、宣讲员和视学。见山西日报馆:《山西用民政治述略》,第4页,山西日报馆印刷部1919年版。)但是,健全县署组织、以正式国家行政人员取代幕友、胥吏办理县政事务的改革并未中断。1913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了《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6](p21),其中规定县公署可以设置两种“佐治员”——科长和科员,还可以“酌设技士办理技术事务”;各县知事公署分设各科办理行政事务,各根据本县事务繁简设2至4科,以数序命名,称第一科、第二科等。各科人员编制,科员为2至4人,技士至多不得超过3人;为“缮写文件、办理庶务”,各县公署可以“酌用雇员”。《组织令》关于县署组织的这种设计,其精神是与《直省官制通则》一致的。首先,它规定设立的县署各科,其职能与《直省官制通则》规定的佐治员基本相同。如直隶规定各县公署设立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科,小县设二科,分别掌管内务、财政和教育实业[7](经制志·行政);河南令各县公署设总务、内务、财政三科[8](p43~46);甘肃天水县1913年设立总务科掌管司法、教育,设立经征局掌管田赋粮款[9](p53~57)。其次,它与《直省官制通则》一样,规定科长、科员和技士属于国家正式公职人员,“由该省行政长官委任”。再次,科长、科员等佐治员以及“缮写文件、办理庶务”的县署雇员是作为幕友、胥吏的功能替代者设置的。从一些地方的实际情况看,县公署组织的改革也包括以政警取代差役来执行县政外勤职能。
在政治动荡的北洋政府时期,上述旨在以科层机构和正式公职人员取代幕友、胥吏、差役等私人势力来承担行政职能的县公署组织改革,在各地的实际实行情况很不平衡。在不少地区,县署科长、科员往往只是由幕友改头换面而来,“六房”胥吏与“三班”差役也往往没有彻底裁撤;但是,大部分地区县署各科起码在形式上已经设立,各科科长、科员、技士也起码在形式上属于国家正式公职人员;其薪酬已经不是由县知事个人发给,而是从国家公费中支领(详见下文)。大致说来,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县公署组织改革的实际实行情况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其一,较为彻底地废除了任用幕友、家丁、胥吏、差役办理县政的制度。例如,直隶广宗县1913年奉省令改组县公署,“裁去六房及三班名目,内分为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科”;不久“以县小复并为二科,置科长二人,科员四人,书记十人,缮拟文书;设政务警察传案催粮,免除各项陋规。自科长以下,均支给薪水工食,其纸张笔墨亦由县署支领,数百年积弊为止一清”[3](法制略)。甘肃天水县在1913年取消“六房”胥吏,设立总务科、经征局;四班衙役只留少数人,供总务科差遣[9](p53-57)。
其二,县公署组织有所损益,进行了部分改革。例如,直隶青县1913年将书吏“十房”改组为两科,刑名、钱谷幕友分别改为第一、第二科科长,“各科书记若干人,多以旧吏充之”。但四班差役被取消,改组为承发吏和司法巡警,并另组游击队以缉捕盗贼[10](经制志,时政篇)。
其三,县公署组织在形式上得到改变,但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房吏和差役仍是县政的实际执行者。例如,湖北汉阳县民国初年“废除三班六房旧制,改设第一、二两科……旧时书吏、书办改称为科员、司事等职称,但名变而未(未字衍)实未变。所以传案、催粮仍由旧日差役承办。……吏役大多也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11](p104);陕西千阳县署清代存在八房书吏和四班差役,民国改元后没有裁革,但在其上设立三科进行管理[12](p108)。
其四,县公署组织沿袭清代旧制,几乎连形式变化都没有发生。例如,河南巩县“民国建元以后,地方一切行政,仍沿用清制,无大改变”。至1927年北伐军到达巩县后,才把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改为书记处;八班衙皂改为政务警察等[13](p92)。(注:另据刘慎言《回忆巩县旧政权的两三事》:河南巩县清代设十三房胥吏和八班差役,民国初年只是将十三房并为十房,直到1928年才废除胥吏十房而改为科。见《巩县文史资料》,第6辑(1990)。)陕西南郑县“1912年至1927年仍按清制设六房四班”,六房胥吏“分掌日常公事”;四班差役站堂、行刑并分四乡“承办催、捕传递差役”[15](p116)。
尽管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县公署组织改革的推进极不平衡,但就国家建制而言,县公署赖以承担行政职能的已经不是幕友、家丁、胥吏、差役,而是正式的科层机构和公职人员;幕友、家丁、胥吏、差役作为清代县政的遗存势力尽管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彻底消亡,但已呈现无可避免的衰落之势。中国的县署组织已经开始走出传统而迈向现代。有当时人指出,经过民国元年至国民政府初期20余年间的“数次改革”,封建时代胥吏、差役制度的弊端已经有所革除,虽然“彻底改革”尚未实现,但“较诸之清末之百弊丛生,相去远甚,不得不谓渐入光明之路也”[15](卷三,政治志上)。
三 县司法独立的起步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地方官集行政与司法职权于一身,这种制度的改变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近代中国(州)县司法与行政的分离发轫于清末“预备立宪”,至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大致完成(注:1935年和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法院组织法》和《县司法处组织暂行条例》先后开始实行,至1942年10月,各地共设立地方法院390处,审判权独立的县司法处864处。见国民政府行政院编:《国民政府年鉴》,第三编,第5页。中心印书局1942年印行。),而两者之间的北洋政府时期,则属于一个曲折而缓慢的推进阶段。
清末,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思想传入中国,人们对行政官员兼理司法的制度提出批评。清政府也认为,州县官兼理司法不利于他们集中精力办理行政和地方建设事务。1907年,总司核定官制大臣奕劻在奏陈地方官制改革情形时指出,当时州县官对于“繁剧之邑”各项“新政”办理不力的重要原因,在于“词讼綦多”,即使“贤能之官”也“苦日不暇给”。因此,地方官制改革须将“分设审判各厅以为司法独立之基础”作为重点,“使州县各官,不司审判,则尽有余力,以治地方”。《直省官制通则》规定,在各省“分期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同年,清政府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1909年又颁布了《法院编制法》,对于在各州县设立独立的初级审判厅作出了规定。民国改元后,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4月通过决议,规定清末颁行的《法院编制法》继续适用。
北洋政府时期,县司法与行政分离的改革进展曲折而缓慢,但总体说来仍然有所推进。
清末民初,司法管辖范围为一(州)县的地方审判分厅仅仅在少数地方设立,至1914年4月,正在筹划帝制的袁世凯以“经费人才两俱缺乏”为理由下令“概予废除”[16](p697)。但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在政策上又重新肯定了地方独立司法机构的设置。1917年4月,北洋政府公布《暂行各县地方分厅组织法》。这个文件规定:“凡已设地方审判厅地方,得于附近各县设立地方分厅,即称为某处地方审判厅某县分厅。”这种县地方分厅,可以设于县知事公署之内,其司法管辖区域与所在县的行政区域相同,但基本属于独立的司法审判机关。因为按照这一文件的规定,地方分厅“受各该本厅之监督”,而不是隶属于县知事;其推事官、检察官和书记官均为国家荐任、委任官员。此外,地方分厅还设承发吏、司法警察、检验吏,可以使用雇员[17](p280~281)。这一文件还规定,“凡未设地方厅及地方分厅各县,应设立县司法公署”。据此,北洋政府于1917年5月又公布了的《县司法公署组织章程》(若干条款于1923年4月修正)。根据这一文件,县司法公署不像地方审判分厅那样与县行政系统截然分立。首先,司法公署设在县公署内,由审判官司与县知事共同组成,其书记官“由审判官遴员会同县知事派充”;其次,除审判由审判官进行外,其他“关于检举、缉捕、勘验、递解、刑事执行等事项,概由县知事办理,并由县知事完全负责”。但另一方面,县司法公署的设立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与行政的分离。首先,审判官、书记监等县司法公署主要官员均非县知事属员,由省司法机关任命;其次,“审判事务概由审判官完全负责,县知事不得干预”;第三,县知事在司法事务方面,也同审判官司一样受高等审判厅长之监督[17](p299~300)。
北洋政府时期,只有极少数地方依据上述两个文件设立了地方审判分厅和县司法公署,据统计,至1926年前者为23所,后者为46所[18](p836)[19](第3251号)。除此之外的全国绝大多数县分实行的是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制度,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13年1月至1914年4月,县司法事务由县知事与帮审员共同负责。在清末“预备立宪”中,司法独立呼声甚高,民国改元之初其余波犹盛,所以当时县司法制度的建设尚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取向。1913年1月,北洋政府颁布的《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各县地方之未设有审判厅者,除依现行法律办理外,得酌设帮审员一至三人,管狱员一人”;各县帮审员由县知事提名,省司法筹备处任命,司法部备案,具有相当的独立性[6](p21)。《组织令》的这一规定当时在许多地方得到了落实。例如,直隶省于1913年令各县设立了审检所,置帮审员掌理司法审判事务,县知事任检察官,在县公署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民国《青县志》记载,该县1913年县署改组,“将司法一部分划出,别立机关,名曰审检所,如管狱员、司法科、检验吏、承发吏、司法巡警皆属司法一部分”,以上级派来的法官恽××为主任,以县长兼任检察官[10](经制志,时政篇)。《文安县志》记载,该县“民国二年设审检所,所设帮审员,由高等审判厅委任。设司法股,书记十人,司法巡警十八人,检验吏一人”;司法经费也单独列支,全年3840元[20](卷十二,法治志)。山东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据《馆陶县志》记载,该县于“民国元年冬,奉令颁《县公署暂行分科治事章程》,乃设有司法专科,掌理民刑诉讼、批判、预审等事件。旋奉令改设帮审员,承办审判民刑诉讼案件,县知事仍有兼理事务之权”[21](政治志,制度)。当然,由于帮审员设于以县知事为长官的县公署之内,司法与行政之间的界限不可能彻底划清。以上文所述直隶文安县情况为例,其“司法巡警均由行政警察兼之”,司法书记也属于行政系统。在有些县,则根本不设帮审员,司法审判仍由县知事负责,直隶望都县就属这种情况[23](卷四,政治志)。
第二阶段始于1914年4月,县司法事务由县知事负责,承审员协理。(注:《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章程》于1921年1月、1921年3月和1923年3月三次进行修正。)1913年1月以后实行的以帮审员任审判的县司法制度,在当时人看来存在两个缺点:一是帮审员多由司法专业毕业的学生担任,他们缺乏实践经验;二是政法权过于独立。对此直隶《广宗县志》记载说:1913年后“充帮审员者多系政法学校毕业学生,成绩甚寡”[3](法制略);《南宫县志》则记载说:1913年“始派法政学生于各县”任帮审员,他们“经验幼稚,为世诟病”;“且三权之理论虽充,及征诸事实,其窒碍亦殊多端”[23](法制志,新政篇)。当此之时,袁世凯又正在准备复辟帝制,县司法改革的取向于是发生转变,由强调司法与行政分立转为强调两者的合一。在这种背景下,北洋政府颁布了《县知事兼理司法事务暂行条例》和《县知事审理诉讼暂行章程》。
《暂行条例》规定,“凡未设法院各县之司法事务,委任县知事处理之”,明确了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原则。同时又规定,各县可以设立承审员“助理”县知事。关于县知事审理诉讼事务的范围,《暂行章程》规定:“凡未设审检厅各县,第一审应属初级或地方厅管辖之民刑诉讼,均由县知事审理。”这两个文件颁行后,各地帮审员及其他相对独立的县司法机构均撤消,实行县知事兼理司法而以承审员“助理”的制度。例如,直隶广宗县1914年“审检所裁撤,司法仍归县知事兼理,改设承审员”[3](法制略);南宫县帮审员改为承审员后,除司法经费仍与行政经费相互划分外,司法事务“一秉承于县知事,检察审判之权,知事仍兼之”[23](法制志,新政篇);广东大埔县1912年曾设立职权完全独立的“专审所”,“直隶地方审判厅,由省司法派专审员一人,专办民刑诉讼”,这个机构1914年被裁撤,“复由县知事兼理初级诉讼,就署中设一承审员掌其职”[24](经政志上);浙江省1916年在护国运动中宣布独立,各县知事署内恢复设立审检所,次年3月又全部裁撤[25](p212)。
与前一阶段的帮审员制度相比,承审员制度下的县司法独立性明显减弱,基本处于县知事的控制之下。但是,较之前清州县官集行政与司法于一身的制度来说,承审员的设置仍然具有司法与行政分离的意义。《暂行条例》规定,承审员可以独立审理案件,“由承审员与县知事同负其责任”;承审员由县知事在合格人员内提名,但其任命权在各省高等审判厅长[16](p591~592)。1923年,北洋政府发布命令扩大了承审员独立审判的权力,规定在设有承审员各县,属于初级审判厅管辖范围的案件“概归承审员独自审判”,但仍须“以县公署名义行之,由承审员负其责任”;属于地方审判厅管辖范围的案件“得由县知事交由承审员审理,但县知事与承审员同负其责任”[16](p593,595)[19](第1532号)。此外,北洋政府1914年颁布的《县知事征收司法各费稽核规则》规定,各县司法收入中的“五成状纸费”和“诉讼费”须上解司法部,这也蕴含着县司法独立的意义[19](第859号)。
县监狱管理作为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在北洋政府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同县行政相分离。清代州县监狱主要用于监禁待质人员、开始审讯而尚未结案的涉案人员和已被判处徒、流、死等刑罚而尚未执行的囚犯,设吏目、典史掌管,而州县官一般也委派私人参与管理。此外还存在班房、饭歇等差役私押场所。民国改元后,监狱和班房均继续存在,后者一般改称看守所。北洋政府于1913年1月颁布《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在规定设立帮审员以增加司法审判独立性的同时,也尝试寻求狱政的独立性。它规定:“未设审判厅各县,可以酌设……管狱员一人,由各县知事呈由该省司法筹备处长委任,并报告司法总长。”是年,司法部还制定颁布了《看守所暂行规则》和《监狱暂行规则》。此后,各地纷纷设立管狱员管理各县监狱,有些地方并兼管看守所。例如,直隶威县1913年“裁撤吏目,改管狱员一员,专管监狱及看守所一切人犯”;“其从前经县长添派之监狱班管一差”也经管狱员据理力争而停派[15](卷四,政治志);直隶文安县1913年将清代的督捕厅改为管狱署,“设管狱员一人,由高等检察厅委任;官医一人,看守四人;看守所看守二人”。监狱经费不在行政经费中列支,“管狱员薪俸、官医薪水,监狱及看守所看守人工食,监犯、押犯各口粮,并提拨高等检察厅分监经费以及零星杂支,均由司法项下开支。”[20](卷十二,法治志)
四 法制化行政经费制度的建立
改革清代州县的封建家产制财政,建立法制化的财政或经费制度,是实现县行政制度现代化的基础。在这方面,北洋政府时期也有所建树。
州县财政制度的改革,在清末“新政”中已露端倪。清代道、府作为州县官的直接“上宪”,不仅俸廉微薄,而且国家财政不给予办公经费,因此向所属州县摊派杂费和索受陋规被合法化,“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明目张胆,昌言不讳,与之而俨然成例,取之而不觉其非”。针对这种情况,直隶总督袁世凯于1902年提出在各州县实行以裁革陋规、核定公费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令各州县每年将原来私相馈赠上司的陋规,一律直接解交布政使司库,专款存储,用以支付道府经费。同时核定道府经费,令“道府厅州各将每年应得属员规费据实开报,和盘托出”,按其向来所得陋规之多寡明定公费等差,每月各道350~1000两不等,各府500~600两不等,各直隶州50~100两不等。此项制度实行后,“道府厅直隶州不准与所属州县有分毫私相授受”,否则严惩[4](财政部,卷十二,《道府厅州所有各项陋规一律酌改公费析》)。 袁世凯的这一改革方案得到了清廷的批准,通令各省“依照直隶奏定章程”一律实行[4](财政部,卷首,谕旨)。这种改革具有使州县财政和道府经费制度走向法制化、合理化的进步意义。
民国改元后,北洋政府进一步对县财政制度进行了改革。由于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实行以及辛亥革命后各项制度的更新,原来州县存留中科举、祭祀、驿站、差役等费用均无须开支,因此民国改元后州县存留制度被废除,“各县正杂各款涓滴上解”。与此同时,采取措施核定各县的行政和司法经费,并规范其经手征收的赋税和行政性收费。1913年9月北洋政府发布教令,令各省将属县划分为等级,核定公费,各省区先后实行。如直隶1914年将全省119县划分为七等,其中“特别大缺”7县,每月公费1900~1400元不等;一等缺13县,每月公费1300元;二等缺21县,每月公费1100元;三等缺26县,每月公费950元;四等缺22县,每月公费850元;五等缺21县,每月公费750元;六等缺8县,每月公费600元[26](《直隶省各县公署现行暂定经费等级数目单》)。此外如京兆特别行政区将所属20县“按县缺繁简,别为七级”,贵州、福建将所属各县分为一、二、三等,安徽省将所属各县“就缺分繁简列为甲、乙、丙、丁、戊五级”,公费均各有差等[19](第793号,第1255号,第1220号,第1149号)。核定公费后,县公署科长、科员、技士、书记等行政人员和其他雇员均按固定标准从公费中支领薪金,改变了清代家产制财政下由州县官支付幕友、家丁薪酬或根本不给薪酬的制度。如直隶盐山县公署公费总额最初每月750元,后增为950元,其中县知事薪俸250元;科长2人,其中一人薪俸60元,另一人50元,共110元;科员3人,薪俸分别为30元、25元和20元,共计75元;书记18人,每月薪金共180元;公役14人,每月津贴共84元。以上各项每月开支共699元,所省251元作为办公费、杂费和零星开支[27](法制略,新政篇)。
赋税征收和诉讼司法是清代州县衙署的两项主要职能,但在州县存留制度下却没有合法经费,其运作前者靠漫无限制的浮收,后者靠名目繁多的规费。民初核定公费后,各县额定公费大部分被用于县公署人员的薪水开支,赋税征收和诉讼司法经费仍需采取其他财政措施才能保证。在赋税征收方面,建立地方附加或提成制度,“以资征收粮租之费”[27](法制略,新政篇);司法经费则与县公署行政经费同时核定,分别列支。例如直隶各县司法经费分甲、乙、丙三等,分别为300、400和500元;据《文安县志》记,承审员及其他审判系统人员薪水,管狱员、官医薪水、监狱、看守所看守工食以及监犯、押犯口粮等均由司法项下开支[27](法制略,新政篇)[20](卷十二,法治志)。1914年,北洋政府还颁布《县知事征收司法各费稽核规则》,规定在没有设立审检厅各县,状纸费的50%和罚金、没收款项及没收物品拍卖所得款项归各县留用[19](第859号)。
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使得县行政经费和财政制度开始走向法制化。有地方志记载说,民国初年核定县公署公费后,“自知事、科长以及书记、警吏等之薪工,概由行政、司法经费分别开销,不似清代吏胥差役(例有工食,官不发给),专事敲诈勒索为其唯一之生活费矣。”[15](卷三,政治志上)国税附加、提成和司法收费制度的实行,也使得清代漫无限制的赋税浮收和诉讼规费开始得到规范。此外,县公署设置科层机构统一管理各项经费和财政收支,结束了清代州县官对于财税的家产制管理。当然,改变清代那种家产制财政,实行县公署行政经费制度的法制化,是一项十分深刻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它不可能在动荡的北洋政府时期根本完成。在许多地方,胥吏、差役制度继续存在,他们仍靠勒索陋规办公和度日;在有些地方,县署的科长、科员仍为县知事自辟之掾属,他们掌管县经费和财税收支,必然使得家产制财政的革除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法制化的县公署行政经费制度在形式上已经建立起来。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县行政的现代化改革经历了一个延续不断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自清末开始,中间经过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一直持续至人民政府时期,至今也不得谓彻底完成。作为这一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北洋政府时期对于县公署制度所作的改革尽管存在很大局限性,却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第一节所说清代州县衙署制度缺乏地方建设功能的弊病,在北洋政府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革。不过,这一点不是体现在本文所论及的县公署制度中,而是体现在这一时期以地方“四局”为主干的自治行政中。对此笔者曾有专文探讨,这里不再赘述。[28]
【收稿日期】2003-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