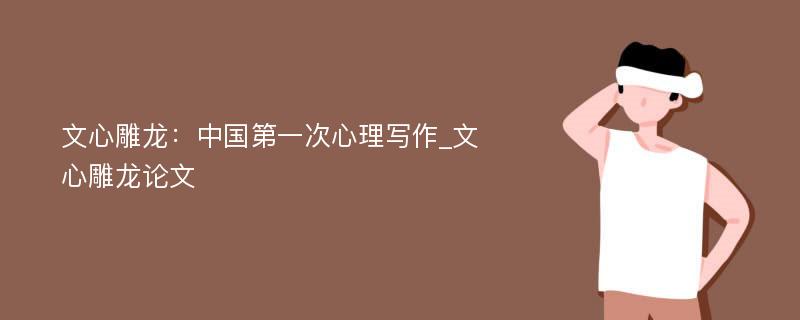
《文心雕龙》: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论著论文,第一部论文,中国论文,心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1-0093-05
对于《文心雕龙》,一些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写作学或文章学性质的书;另一些则认为它是文学理论乃至文学史、文学批评或美学理论著作。这种分歧源于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文学”认识的变迁。20世纪初,在西方文论与美学的影响下,随着“纯文学”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美学”等学科应运而生。假如站在这些新学科的基点上反视中国古代,当然找不出“纯粹”的、完全符合西方话语的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将史传、诸子、论说乃至祝盟、铭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等都视为“文”来加以论列,这类著作所论的对象尽管不完全是“纯文学”,但多少也包含了一定的文学性,更何况刘勰所论毕竟也包含着诗、骚、赋等部分“纯文学”,所以,全书所论种种也多与西方框架中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和“美学”等有相通或相同的地方。因此,将它作为一部“文学理论”或“美学理论”来读也未尝不可。在对中国文学观念进行“现代化”实乃西方化的一段时间里,就是以“纯文学观”来阐释《文心雕龙》,并将它“提纯”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用传统的、民族的文学观念来审视它时就会发觉,《文心雕龙》所论的“文”并不是“纯文学”,而是“杂文学”或“大文学”,于是就自然而然地觉得,说《文心雕龙》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或“美学”理论著作就不妥当了。在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曾指出:“《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1](P416),可惜他没有展开论述。后经王运熙等阐发,“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做法”[2]的认识逐渐深入人心。时至今日,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文论或美学著作的人,恐怕也不会否定《文心雕龙》所论的是“杂文学”,从而完全否定它是一部“写作学”或“文章学”的看法。但这并不能使人们就此放弃专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或美学的角度研究《文心雕龙》,因为这部书确实包容着丰富而精深的文学理论。反过来,认为这部著作的“宗旨是指导写作,是一部文章做法”的学者,也认识到它“由于广泛评论了作家作品,系统研讨了不少文学理论问题,总结其经验以指导写作,因此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空前巨著”[3](P7)。王运熙曾用十万字的篇幅将《文心雕龙》写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尽管目前对《文心雕龙》有倾向于“写作学”与倾向于“文学理论”这两种不同的认识,但由于刘勰所论的“文”本身包容着现代通常所认识的“纯文学”,这就决定了他在总结当时“杂文学”写作法的同时,也包容了从现代意义上所理解的“文学”理论。从本质上说,这两种提法并不是排斥而是相互通融的。假如从刘勰的原意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文心雕龙》是一部写作学著作;而假如从当前旨在借鉴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或美学理论的立足点出发,也不妨将它看作是中国古代一部最伟大的文学理论专著。
研究《文心雕龙》的关键是抓住它的理论核心,唯此才能纲举目张,认识到它的整个体系和学术价值。其实,抓准《文心雕龙》的理论核心并不难,它的书名就是一把最好的钥匙。可惜的是,对于《文心雕龙》的书名,千百年来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者多;认真思考、心领神会者少。近二十多年来,一些学者关注了《文心雕龙》的书名,但往往给人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之感;一些学者已经抓到了痒处,却不能进一步生发。而这个问题恰恰是研究《文心雕龙》基础的基础,很有必要对它的书名作一番诠释。
其实,关于《文心雕龙》的书名,刘勰在《序志》的开头就将“文心”与“雕龙”分别作了说明: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
“用心”一词,可能借鉴于陆机《文赋》首句:“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李善注云:“用心,言士用心于文。”这就将“用心”解释为“专心”、“着力”的意思。这是第一种理解。后人认为《文心雕龙》是“讲如何用心写文章”,即由此而来。有人将“文心雕龙”四个字理解为“写文章的用心在于要把文章写得像精雕细刻的龙文一样美”[4],实际上也是因为这样来理解“用心”的。至清代,顾施祯在《昭明文选六臣汇注疏解》一书中注释《文赋》“用心”两字时曰:“用心,作者之意。”这是第二种理解,即将“用心”解释为“用意”,恐怕与原意相距更远。后人将“文心”理解成“文学思想”、“文学的心”、“文学创作的原理”[5](P101-103)、“文章的本质和精粹”[6],恐怕都与此相近,不甚确切。其实,刘勰的“用心”不同于李善、顾施祯等所理解的“用心”。“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中的“用心”,实为动宾结构短语,是“使用其心”的意思。如《孟子·告子》云:“心之官则思”,今人因而常常推论古人心目中的心是一个思维器官。用心,可理解为思维活动。其实,古人心目中的心,即同今人的脑,统管着人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情绪等一切心理活动。使用心,就是要使整个心能活动起来。作家写作的过程,包含着各种心理活动的复杂过程。这样,“为文之用心”一句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作家写作时的整个心理活动,假如将它仅仅限定在“创作构思”方面,就未免显得太狭了[7]。作家临文写作时的心理活动,当然包括原则的遵循、方法的运用、态度的端正、灵感的触动、构思的经营、想象的驰骋、意象的形成、风貌的呈现、修辞的选择、技巧的借鉴,乃至关系到与客观时势的盛衰、写作主体的修养、客观批评的标准等种种问题。可以说,作家为文时的“用心”关系到写作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临文时的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活动与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关系。因此,“用心”两字统领了全局,这是全书的理论核心。难怪刘勰感叹道:“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关于“雕龙”两个字,刘勰在《序志》中解释时说:“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由于这里用了“岂取”两字,从而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理解。李庆甲曾将它概括为“否定”说、“无关”说、“肯定”说三种[5](P93—100)。其实,这一句“与《文心·杂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句一样,都是用反诘语气表示肯定,句末‘也’字作疑问助词用”[3](P3)。假如结合刘勰将“雕龙”用于书名,在《时序》篇中又以褒扬的态度来提到驺奭,以及全文都用漂亮的骈文来写作的话,当为肯定“驺奭之群言‘雕龙’”无疑。他这是借用战国时驺奭之文善辩饰,似若“雕镂龙文”,人称“雕龙奭”来形容自己的著作,也是“雕缛成体”。裴骃释“雕龙”为“雕镂龙文”,无非是形容其雕刻之精与图文之美。刘勰所说“雕缛成体”之“缛”,就是繁密、细致的意思。梁代江淹《别赋》有云:“赋有凌云之称,辩有雕龙之声。”又将雕龙与善辩联系在一起。所以,“雕龙”两字,含有精、美、密、辩等几层意思。刘勰即借以形容自己的著作是富有论辩的色彩,且写得十分精美、细密。
这样,将“文心”与“雕龙”合起来看,“文心”是中心词,“雕龙”是修饰语,用来形容如何论“为文之用心”的。个别学者将“雕龙”视为中心,于是将书名理解为“为文之用心”在于“要把文章写得美”,显然与全书首先强调原道、征圣、宗经等理论倾向不合[4]。近有学者又将它们视之为平列的结构,表明“他在撰述之时,是分别从构思与美文两方面着手而进行探讨的”,所证的例子是萧统《文选序》中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卞兰《赞述太子赋并上赋表》中的“沉思泉涌,华藻云浮”;谢惠连《雪赋》中的“抽子秘思,骋子妍辞”等,认为“文心”与“雕龙”犹如“沉思”与“翰藻”、“沉思”与“华藻”、“秘思”与“妍辞”一样两两相对[8]。其实,“文心”与“雕龙”是不能与这些例子比对的。这些例子确实符合当时“骈体文的写作特点”,而“文心”与“雕龙”并不是“两两相对”的组合。况且,恕我孤陋寡闻,历来的文章题目,很难见两词骈对的。“文心”与“雕龙”是一主一副,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将“文心”像“雕龙”般地加以论述,或者说“雕龙”般地论述“文心”。这样,“文心雕龙”的意思就是:将写作的心理活动用精美的文辞予以细密地论述。据此书名,可知《文心雕龙》是一部用美文来细致、系统论述写作心理活动的著作。或者说,《文心雕龙》是一部以写作心理学为核心的美文体文章学,书名本身已清楚地表达了全书的性质与宗旨。
围绕着“用心”即写作心理活动这个理论核心,《文心雕龙》用五十篇文章,加以系统论述,结构十分严密。其最后一篇《序志》,相当于现代的“自序”,但循古代的通例,将它置于篇末。其余四十九篇的安排,极具匠心,其概略即在《序志》中有所说明: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搞《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在这里,刘勰将前二十五篇称为“上篇”,后二十四篇称为“下篇”。“上篇”中的头五篇为“文之枢纽”,也就是作文的根本和关键,是开展心理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五篇中又分了两组。《原道》、《征圣》、《宗经》为一组,《正纬》、《辨骚》为第二组,从正与奇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说明。前三篇中以《原道》篇为纲。《原道》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文章产生的“自然之道”;第二部分论述儒家圣典所文之道。这篇的第一段实为全书的纲中之纲,即开宗明义地点明了文章是由天、地、人“三才”之中独具“性灵”的人的心理活动的结果:秉有智慧的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就是说,为文的过程是沿着天地→心生→言立→文明的轨迹自然地进行的。最后一句“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点明了书面的“文”乃是人“心”的产物,人类的心理活动是为文的根本和关键。这也就是刘勰作《文心雕龙》的基点。这里所说的文章生成的“自然之道”恐怕与道家的“自然”并无多大的关系。《原道》的第二部分,就是接着上文,例举孔子等儒家圣人、经典是如何表现“天地之心”,“原道心以敷章”的。最后点明了道、圣、经三者之间的关系:“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引启了下面《征圣》、《宗经》两篇。所以,《原道》、《征圣》、《宗经》这三篇实际上是从三个层次阐明一个问题,其总纲就是“原道”两字。其“道”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写作自然之道,其次才是儒家圣典根据这一原则所表现“天地之心”的道。儒家圣哲所作的“道之文”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情信而辞巧”,“衔华而佩实”。这是“用心”写作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在《宗经》篇中,刘勰提出宗经的“六义”,实际上是这个目标的具体化: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这样,《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实际上已经道明了“为文之用心”的基本原理与追求目标,但这主要是从正面来树立典范。接下来,刘勰将《正纬》、《辨骚》两篇也纳入“文之枢纽”之中,作为另一组文章。“纬”和“骚”本是两种文体,但都“去圣之未远”,一为“前代配经”,一是“依经立义”,曾经风行过一时,虽有荒诞不经、夸诞失实之弊,然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所以,在刘勰看来,取儒经之“正”,酌“纬”、“骚”之“奇”,相互结合是写好文章的关键。《辨骚》篇的最后说:“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其论文心的大旨:以原道、征圣、宗经为根本,走正道,求征实,再在正纬、辨骚的基础上,酌奇与取华,以达到奇正相谐、华实并茂的境界。这也就是刘勰论述“为文之用心”的总的指向,是符合道的具体表现,是写作文章的总体目标与原则。
从第六篇《明诗》起,到第二十五篇《书记》,先后分成了两类。前一类是论有韵之文,从《明诗》论到《杂文》共十篇;后一类是论无韵之笔,从《史传》到《书记》也是十篇。这说明,刘勰当时已经比较清楚地辨别了“文”与“笔”的不同。刘勰将这二十篇文章分别予以“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将每一文体的起源与流变的脉络进行梳理,阐明这一文体名称的含义,再选评一些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最后揭示写作该文体的基本规范与特征。因此,曹学佺将这些文章归结为“铨次文体”(《文心雕龙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这些文章是“论文章体制”或“论体裁之别”(《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因而现在的研究者也往往将它们看作是“文体论”或“分体文学史”。假如仅从这二十篇文章孤立来看的话,的确会只见刘勰在这里“辨体”、“遵体”,完全可以将它们看作是“文体论”或“分体文学史”。这或许也是人们不易看清《文心雕龙》是一部主要论“为文之用心”、论写作心理的一道幕障。但是,假如将它们放在整部《文心雕龙》中,从刘勰的整体构思来看,这二十篇文章无非是想通过不同文体的溯源释名、流变梳理与代表作家作品的评价,以进一步论证不同文体的作家写作时的心理活动与创作思维都应该遵循“文之枢纽”所定下的总的原则。它们实际上就是“枢纽”以下的分论而已。例如,《明诗》篇云,通过“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鉴;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这个经“铺观列代”后所明之“纲领之要”即是:“舒文载实,其在兹乎!”再如,《诠赋》篇最后归结到“立赋之大体”为:“物以情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颂赞》篇论颂体的特点是:“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至于论“笔”一类文体的,如论《章表》也强调“华实相胜”,论《诸子》肯定“揽华而食实”,论《书记》要求“志高而文伟”,如此等等,可以说这二十篇“文体论”都紧紧围绕着“文之枢纽”所定下的、遵循“心生”、“言立”“文明”的轨迹,追求“情信辞巧”、“衔华佩实”的总体目标与原则。它们就是“枢纽”之论的应用与细化。
假如说上篇中的前五篇是纲,从“道”的层面上提出“为文之用心”的理论原则,接着的二十篇主要是通过分论不同文体的流变与特点来进一步肯定其理论原则的话,那么下篇中的二十四篇是打通了各种文体,从“术”的层面上来统论一些心理活动的规则与方法。
在后二十四篇中,首论《神思》。论“神思”并不是如有些论者所认为的是论灵感,或论想象和构思,而是统论创作时的心理活动,从感物兴起,到想象立意,以及心境的虚静、文思的迟速、语言的选择、技巧的运用,再到最后的改定。主要侧重在搦笔临文时的秉心总术,是“文心”活动最直接的表现,对下面各篇而言,是具有一定的统摄性。所以,黄侃说它是“提挈纲维之言”[8](P91),理当放在下篇之首。
作家写作心理活动的取向、特点,取决于创作的主体,所以刘勰接着论《体性》,论作家先天的才、气与后天的学、习。由于主体的个性特点不同,各人的“文心”也必然不同,创作出来的作品就风格各异。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性情”。刘勰虽然强调先天的才性为主,但也重视后天的学习,要求作者在追求雅正的前提下,结合自己的个性特点练才,以求“功以学成”。此篇可以看作是对《神思》篇的补充。《神思》篇是论临文写作时的“用心”,《体性》篇则补充了临文写作前作家应具备的必要条件,所以接在《神思》篇之后而在以下各篇之前。
然后,刘勰论述了“文心”取向、写作时开展心理活动的几个要点。这里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在全局层面上需考虑的,有的是在具体的修辞层面上需要注意的。对全局性层面上要考虑的问题,刘勰在《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等五篇中作了论述。《风骨》篇要求作家在“情与气偕,辞共体并”的主导下追求明朗刚健的文风;《通变》篇指出了文章发展的规律是既通又变,所以作家必须“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以求把握大势,适时创新;《定势》篇则要求遵循“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原则,依据不同体裁所确定的规范来写作;《情采》篇强调要摆正情志与文采的关系,认定“心术既形,英华乃赡”,“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镕裁》篇强调了“情周而不繁”,要恰当地表达情理,就必须剪裁浮词,这可视为对上一篇的补充。
接着,刘勰从修辞与表现手法的层面上较为具体地论述了一系列问题,有《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等九篇。当时的文坛流行骈文,讲究声律、辞藻、对偶、用典等形式美,刘勰精于此道,《文心雕龙》便用骈文写成。他认为,写好这类美文的关键在于遵循“秉心养术”的原则,以“心”为主导,所谓“属意立文,心与笔谋”,“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对于比兴、夸饰、隐秀等比较传统的修辞手法,刘勰也紧扣心理活动的不同情况来加以论述,如论《隐秀》,开头即说明了“隐秀”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指瑕》一篇,不同于前八篇的正面论述,它从反面指摘的角度来谈,但着眼点仍是一些具体的修辞手法,重点在与上相关的一些枝节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前八篇文章的补充,在总体上可以归在一组。
接下来的《养气》、《附会》、《总术》等三篇是对自《神思》至《指瑕》各篇所论问题的补充、协调与总结。《神思》篇讲了创作时的心理活动,《体性》篇讲了创作主体的个性特点,但创作主体在具体创作时如何很好地进入神思的境地,进行艺术构思,还关系到主体临文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养气》篇论述了作家只有“清和其心,调畅其气”,保持良好的心境,才能在“用心”时思路通畅。《附会》篇则是在前面各篇侧重对各个问题进行分论的基础上,强调要有一个统一的布局与结构,合理地将各种材料连缀聚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最后《总术》一篇,具有总结性的意味。前面讲了种种“为文之用心”,虽强调了“用心”根本要原于道,但大量讲的是具体的“用心”之术。这各种各样的术并非不重要,“若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很难保证写好文章。刘勰强调了术的重要性之后,又认为这些术尽管繁多,但它们之间还须协调,所谓“文体多术,共相弥纶”,而且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将它们处理好,统一成一个整体。刘勰写这篇“总术”,就是要将各种各样的“术”“总”起来,“譬三十之幅,共成一毂”,围着一个中心转,达到“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目的。而且,这篇《总术》也像一根线一样把前面所论串了起来。
《文心雕龙》对于“为文之用心”的论述,从基本原则到具体方法,从各体文学的分析,到一般理论的总结,主要的问题大致都已谈到,但刘勰并不满足于此,还要通过论述写作心理与时代的关系(《时序》)、写作心理与自然的关系(《物色》),以及作家论(《才略》、《程器》)、批评论(《知音》)来进一步拓展思考“为文之用心”的眼界,丰富论述的内容,提升理论的高度,达到了更加完美的境界。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文心雕龙》的主旨就是论“为文之用心”,也就是论写作的心理活动。《原道》等五篇论“文之枢纽”,揭示了实为“天地之心”的人心是文章产生的根本,“心生”而“言立”而“文明”。儒家圣人将“道之文”写成了“言之文”的典范。这类经典的基本特征就是“情信辞巧”与“衔华佩实”。这是指导写作心理活动的总的原则。以下二十篇,通过对不同文体写作特点与历史的考察,进一步论证了以上原则的正确性。下篇从《风骨》至《总术》篇,就是在上篇确立的原则下,将各种文体打通后,正面论述了一系列临文写作时心理活动的特点、规则、方法与问题。此后《时序》至《知音》五篇补充论述了与临文写作时心理活动具有密切关系的几个重要问题,使得全书的结构更加完整、系统。
刘勰在构建以上体系时,从基点上认为儒家的圣人是“原道心以敷章”的典范,最后在《序志》篇中又说:“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用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尽管从他长期在佛寺里从事佛经的整理工作,最后则出家为僧,肯定受到了当时流行的玄学的熏染,但从其写作的这部《文心雕龙》来看,刘勰是明确而自觉地遵循儒家的经典思想来论文的。《文心雕龙》不愧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写成的、研究与总结写作心理学的理论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