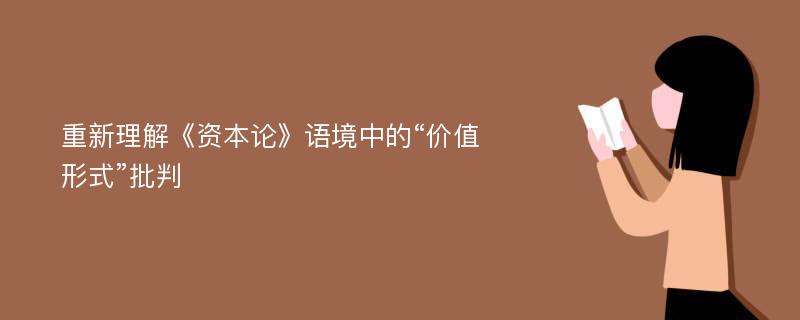
摘 要:《资本论》的“价值形式”一节蕴含着极大的阐释空间,可以认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整个写作思路均受其影响。在学术界流行的阐释习惯中,往往对价值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统治方式”具有浓厚的兴趣,却遗忘了对价值形式的历史性作深入的前提批判,从而导致价值形式这一解释原则的泛化。为此,我们将对其进行反思,将价值形式转入到社会结构这一前提给予深层批判,并以破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矛盾与主体行为塑造双重向度理解解放的理念,从而试图为政治地理解《资本论》提供阐释的可能空间。
关键词:《资本论》;“价值形式”;解放
《资本论》语境中“价值形式”的研究需要被高度关注,这是因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建构原则来看,资本主义以拜物教的“支配方式”完成了现实存在物在其表面上以颠倒的方式显现的任务,《资本论》就是要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窥探出社会的一般形式与社会的特殊表现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自身的批判,以寻求一种激进政治的改变图景。应该说,依此方案探究社会这条道路从来不孤寂。与阿多诺交往颇深的索恩-雷特尔回忆其思想历程时认为,在1921年,他已经通过对社会的商品形式的研究,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导原理。[注][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更为集中地将价值形式作为《资本论》研究主题的,当然可追溯自20世纪早期的卢宾(Isaak Illich Rubin),他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文集》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学不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层面,而是分析其社会形式,即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总体”。[注]Isaak Illich Rubin,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Black Rose Books,1972.p2.几乎同时,帕舒卡尼斯在《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也指明了对法律的分析应该参照商品世界的方法论原则。此种理解后来在德国新马克思解读学派(Die Neue Marx-Lektüre)的研究中得到更进一步阐释,作为阿多诺学生的“新解读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与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以及第二代学者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等人更是深化了价值形式的研究。在此之后,价值形式的研究又于英语世界大体在两个向度上加以扩展:一个向度是“新辩证法学派”。代表人物亚瑟(Christopher Arthur)、史密斯(Tony Smith)等人极力倡导“体系辩证法”,并论证《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之间的“同构关系”,“《资本论》就是一部根据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逻辑所建立起来的经济范畴的体系理论”。[注]Tony Smith,The Logic of Marx’s Capital, Albany: Sunypress,1990.ix.另一个向度则是开放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诸如博纳菲尔德、霍洛威等人的研究,在他们看来,价值形式构成的“支配方式”可以在哲学语言上表述为“同一性”,而借助阿多诺的视角,“辩证法不仅是一个前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逆行的过程”。[注][德]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因而,他们又极力主张“非同一性”的抵抗姿态。但是,他们依然将价值形式作为“支配方式”的一个既定前提,在对待价值形式的“同一性”方面,并没有能够将价值形式与社会结构关联起来进行研究。
为此,我们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加固那些已经纠偏的理论成果并同时追问,在《资本论》的“价值形式”一节中,人们以价值形式的表现机制言说当下所受到的统治时,是否遗忘了对交换价值的历史性作深入的前提批判?形式分析的解释原则泛化之后,我们能否在社会结构的矛盾与主体两个方向上给予修补?我们如何从以资本主义交换方式为主导的社会形式进展到对社会的普遍的一般形式?讨论这些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如何走出价值围城已经成为了马克思解放观念是否失效的关键之问。
虽然系统功能学派对名物化的语篇功能展开了不少有意义的探索,但与词汇语法层面的研究相比还十分不足,在研究视角的广度和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拓展。为了更好地把握语篇层面名物化现象研究的现状、研究热点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拟通过运用知识图谱分析软件“引文空间”(CiteSpace),对比分析国内外核心期刊近20年来发表的文献,全面考察国内外学界对英语名物化现象研究的趋势,以期为今后英语语篇名物化现象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价值形式的建构逻辑:表现与遮蔽共存
在《资本论》发表20年前,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第七个说明”中已经重点批判了“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之后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的讨论中自然不会犯相同的错误。因而,在我们提示价值形式对马克思整个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意义的时候,也必须将价值形式所“遮蔽”的特定社会形式重新打开,这样才能对价值形式有一个完整的理解。
我们先来看“价值形式”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整个运行机制的意义。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价值犹如一个“指南针”,它规定着人们生活的航线。也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家们一直为价值问题争论不休,辩论主要在价值唯名论与价值实在论两派之间展开:一方如贝利等人认为价值只是一个想象的东西;另一方则以李嘉图等人将价值作为某种自然物自身固有的属性。诚如广松涉的看法,劳动价值论在他们那里是为了说明交换正常比率,“交换在需要同样时间的产品之间进行是符合投入劳动价值学说的最终命题”,进而,迫于经验的事实,“劳动价值被实体化了”。[注][日]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118页。这种实体化的迷恋进一步延展、传播,似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讲的不过就是原先古典经济学家所在意的“最终命题”(价值就是劳动时间的投入),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价值的理解,持有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观念的学者认为劳动的情感转向、非物质劳动等新劳动方式兴起之后,价值领域必然发生“度量危机”,进而依靠价值度量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终于可以退场了。这里的问题依然是陷入到价值实体化理解的困境。当马克思在对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之后,即人们实际上所从事的劳动,即使认知资本主义所说的情感劳动也好,仍然是具体的有用劳动,它通过劳动的对象化展示出使用价值。但是,与商品使用价值完全不同的商品价值与这种劳动没有任何关系,后一种劳动是适合于一切社会的,前一种价值所指向的劳动显然是特定社会形式的表现。原先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劳动价值论的“劳动”在此已经无法对接了,原因在于“人类学意义的劳动”与“作为商品的劳动”之间的差别没有得到思考,从而让劳动呈现为社会劳动的那种动力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也没有推进。《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作为第一章第一节附录的“价值形式”,在后来的版本中被并到第一章中作为独立的一节放在“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之后,现在看来,可以作为他强调超越并弥补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缺环的文本处理。
按照上述价值形式的存在前提批判的原则,我们需要将价值形式自治的现象看作是一种“动词化”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名称。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要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所使用的经济范畴,只是被当作一个既定的名词术语所使用,而这些经济学家们却没有思考这些名词术语是一种社会关系建构过程的“动词化”的结果。形如资本只是我们“死劳动”的凝结,不能理解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名词。因为作为名词意味着一个封闭的不可能改变的“同一性”,而作为“动词”则是说,“同一性”不是名词的、静止的,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这样才能够在这个动态之中寻找改变的可能性。对于价值形式的理解也是一样,正如霍洛威所说的,从 “形式”(Form) 向 “形式过程”(Form-process)的转变, 或者更好的是, 从“形式”(Form) 向“形成”(Forming) 的转变, 如果名词变成动词,如果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所有形式都被理解为“形式过程”(Form-process), 那么商品就被理解为商品化, 货币被理解为货币化, 资本被理解为资本化。[注]John Holloway,We Are the Crisis of Capital: A John Holloway Reader,PM Press,p.14.一旦这样理解,思考价值形式便会从一种“形式”转向了价值形成过程,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构成的“结果”。一旦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将这种价值形式看作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的普遍性原则。我们将价值形式作动词化理解就是让人们看到,它并非普遍,而是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才能成立的,“与价值概念相关的东西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被看作一种其阶级结构采取工资关系的形式,而商品是劳动产品最突出的社会形式的社会系统”,进而,“价值论只对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体系有效:商品体系”。[注][加]伊恩·斯蒂德曼、保罗·斯威齐:《价值问题论战》,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0-193页。显然,我们同意,只有在商品交换体系占主导的社会形式下,价值形式才呈现为一种“自治”的形象,才能够不断地将人们的生活本身“价值化”。所以,那些只愿意站在对于价值形式建构现实生活这种“同一化”的过程来看问题,而否认价值形式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形式作为前提的人,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时已经说出其中的原因,他们总是“把价值规律说成是既不受土地所有权也不受资本积累等等的破坏的时候,实际上不过是在着手把一切似乎和这种见解相悖的矛盾或现象剔除掉”,由此,这种政治经济学“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也就必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232-233页。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根据2011年WHO公布的具体数据显示,肺癌在发病率和病死率高居全球癌症首位[9]。有文献表明,即使在如今化疗高治疗率状况下,仍有一部分患者因为治疗过程产生并发症并恶化,导致治疗效果依旧不佳[10-11]。说明肺癌患者在接受化疗的早期康复中,护理方案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这一视角的代表人物亚瑟认为,价值形式解释原则与黑格尔的思考方式极为相似,主要在于,当某物成为商品交换过程中的那个作为统一形式的“一般等价物”的时候,它将被看作为是无差别的抽象本质,而失去了其特殊性,黑格尔也是“从特殊而有规定性的东西的抽象开始的”。依据这样的视角来看,“黑格尔使偶然经验实例脱离范畴的‘纯思’与商品获得忽略其自然形状的价值形式时的实际过程存在高度相似性”,对后者来讲,“在价值形式中不仅是形式和内容是分离的,而且形式本身也变成自动的了,结构的辩证发展实际上是由形式决定的,这些价值形式如商品、货币、资本,最初只是纯粹形式,随后在物质生产中获得它的基础”。[注][英]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亚瑟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在其《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的结论部分,他说出了将马克思的价值形式与黑格尔辩证法作一种“同构性”理解的原因,那就是价值形式拥有与黑格尔绝对精神一样的“总体化逻辑”,“所有不具有‘概念性’的东西都降格为它的承担者”,[注][英]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1页。显然,亚瑟不能理解的是,黑格尔从“实体即主体”的视角,确立了一种剥离掉实体本身,即抛弃内容的形式辩证法时,它遗忘了辩证法恰恰是一种切近实体自身的过程,而不是远离实体的过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精神很轻易地就能渗入、囊括、统一以及引导物质性”,之所以如此在于,“思想的深层结构和物质世界的深层结构,对于黑格尔来说,最终是同一的”,或者说,他的“《逻辑学》中的范畴序列和历史的发展序列是平行的”,从而也最终构成了“黑格尔赋予精神以引导物质展开其潜能达到完满和谐的力量”,[注][加]罗伯特·阿尔布瑞顿:《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和解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2-73页。这样一来存在本身固有的“开放性”被强行在精神的领域中给“和谐终结了”。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没能给物质存在本身以独立的地位,特别是对思想与存在本身的“非同一性”给予足够的空间,从而将现实生活的原则完全精神化。一旦将价值形式也理解为这样一种辩证法原则,将价值法则作“精神化”处理,就会必然远离人们的生活过程本身。今天当学术界将价值形式自主性放大,并以“资本逻辑”话语横行流布时,我们确实需要对这种近黑格尔式的《资本论》解读给予反思性批判,“资本逻辑”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外部反思”的概念形式,而内在的“实体”依然是人们的“生活本身”。
觉醒的公民意识是公民写作的前提,也成为平民非虚构写作的孵化器。公民意识是一种现代意识,是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健康全面的公民意识是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核心素质。公民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认识到上述价值形式泛化解释原则的缺陷,并非是全盘否定这一研究方向的价值。毫无疑问,我们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价值表现形式泛滥的时代,处于让人无比压抑的商品交换社会之中。但这只是我们要描述的人的存在困境的“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描述货币起源的价值形式发生机制,不单纯是为了告诉人们价值对人们生活的建构,更为重要的是在拜物教批判的方向上,让我们的眼睛从价值主导的社会扭转到特殊的社会形式上去,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关注,也就是将价值形式化过程本身看作是一个结果、一种特定社会关系建构起来的现象,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寻找如何走出现有的价值构建的生存状态的路径。
二、价值形式分析的解释原则泛化及其反思
当我们以价值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表现机制去深入理解当代生活,的确我们能够看到那一系列的“表现为”:诸如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率等一系列的转化。在马克思那里,转化即“表现”,这种转化如上所说,它在遮蔽的意义上,正是资本主义故意祛除社会性质特殊性的结果。可以说,遮蔽机制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得到了最佳的实现,如果仅仅站在价值形式分析的表现机制的一面来看,显然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但是,在遮蔽的一面,也就是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产生的”的一面出发,才能够真正理解这种“表现机制”。不过,在“表现机制”之中,它已经构成一个解释体系,一旦我们从价值形式这一单一的建构社会生活的机制来看待现代社会,那么,我们只能如新辩证法学派亚瑟那样,将这一机制泛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原则。这一原则现在似乎甚为流行,《资本论》的解读不幸在很大程度上被带进了这座围城之中。当下,它表现为资本逻辑从宏大向微观生活层面的全面覆盖,这里从一开始就是从对人否定的资本、价值出发的叙述模式,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成为了整个现代商品交换社会的主导原则。
在《资本论》的“商品”章中,马克思借助价值表现形式对这种转换方式给予了详尽的说明。为了解开“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的谜团,马克思是以“对象规定性”这一“中介”对商品属性开始讨论的。所谓“对象规定性”就是商品的内在价值不能够通过自身给予直接呈现,而是必须通过和其他商品等价关系的中介来完成,“通过价值关系,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具体来看,马克思讨论四种价值的表现形式:第一,简单的价值形式:X量A=Y量B,在价值形式的四种类型中,所有的“=”号都并非是A=B,而只是一方B作为另一方A的表现形式。诸如,“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做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做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就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在交换为主导的社会中,人在人才市场上,人(作为劳动力主体)=商品,这里的“=”意味着人只是表现为商品,它必然含有超出商品属性的“剩余”,即作为人的属性,这是表现形式无论如何表现也只能属于被表现者的“有限性”的方式。也就是说,这个“=”号实质上蕴含了资本主义的双重秘密:一方面,在交换为主导的社会建构之后,看起来“相等”只是表现为“相等”,诸如马克思在论述平等时,也讨论过平等意味着不平等,大致就是将这里的经济语言以“政治语言”的方式陈述而已,这一批判是集中火力用在“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上的,因为政治解放就是用这种表现为“相等”的权利、平等此类现代政治术语来召唤政治主体的。另一方面,A表现为B,已经意味着这个社会自身是没办法出场的,它必然需要一定的中介,如马克思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但是中介之后的双方已经出现了“裂缝”,等式一边作为“无限”、“普遍”,而另一边则体现为“有限”、“特殊”,如果将表现形式混同为被表现者,那就是马克思批判的“拜物教”。到了第二个阶段便进入到扩大的价值形式中:实质上这里纯粹是一个坏无限的表述,XA=YB=ZC=2盎司金=……这是一个表现永远不会完成的永恒运动,结合我们在第一个阶段中所说的,这里马克思的“=”不能仅仅看作是表现在一个特定领域(经济领域)中的现象,这种逻辑还会被推展到政治领域、思维领域等。在商品交换与人的“同一性思维”方面的“=”的研究已经在阿多诺那里得以展开了。在第三个普遍的价值形式阶段,这种不停的无限性扩展的等号必然要寻找到一个核心,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等号序列的其中一项被抽出来以一个“有限”的方式来担当无限,真正的价值形式才能够打通完成这“惊险的一跃”。马克思是以“20码麻布为例子”,讲述了无限与有限统一于20码麻布之中,从无限这一普遍性意义上讲,这个地位可以被置换为任何一个商品,显然价值形式的展开就必然出现“有限替换无限”的拜物教。如果再进一步将那个等式序列中的2盎司金看作是天然的可以承担起这种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体的话,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第四个阶段货币形式阶段。
如上所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正是价值形式运行法则的前提,它延伸出不断地表现的社会形式,同时,它也是一个掩盖遮蔽的形式。只有完成这一步,才能够使得人们彻底遗忘了这一交换的历史性特质,遗忘对于价值形式的前提的发问,或者说彻底忘掉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绝佳地完成对整个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掩盖。对此,马克思是通过“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给予分析的,从而力图将价值形式的遮蔽的一面打开。其中的关键就是对拜物教批判所蕴含的历史性展开论述,从而进一步对接了“价值形式”分析的核心指向:“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对于这种遮蔽的批判用了一个比喻,“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在商品交换社会中,物拥有了商品形式并被看作物自身的属性,了解到这一点,劳动成为商品,并展现出劳动的二重性特征便清晰了起来。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家们之所以看不明白,就是在于他们理解“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当人们只能构想按照价值形式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运行的逻辑的时候,人们由于拜物教的机制已经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们的劳动已经发生了二重性的分化,一方面是有用劳动,另一方私人劳动必须同其它的私人劳动相等同,这样私人劳动才对生产者自身起到作用。在价值形式中,当我们看到XA=YB=ZC……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因为各自蕴含的抽象劳动具有等同的社会性质并能够交换,但这又是一种颠倒,因为,“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所以马克思告诫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同理,这一点是今天通向正确理解价值形式的基本方向。
基于上述原因,马克思改变了价值概念的发问方式,转向了对“人类学意义的劳动”为什么会呈现为“作为商品的劳动”这一动力学机制的分析,不再沉迷于价值所指向的劳动时间的实体性追问,这便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关键所在。这一点齐泽克给予过论述,“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关键在于避免对假定隐藏在形式后面的‘内容’的完全崇拜性迷恋:通过分析要揭穿的‘秘密’不是被形式(商品的形式、梦的形式)隐藏起来的内容,而是这种形式自身的‘秘密’”。[注][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但是,绝非说内容不重要,因为,“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3页。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秘密”的发现,但是对于形式本身却不能做出解释,所以,马克思对此推进的工作界限十分明确,如他自己所说,“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来看待价值形式的解释原则是否具有自治特质。对价值形式建构的“表现机制”与社会真实存在之间是否是“同一”的,是这一思考方向的入口。一旦我们证明了“表现机制”与现实生活本身是两个不同的结构原则,那么价值形式建构现实生活的原则本身也只能是一部分,而不是生活本身的全部,从而价值形式具有的自治原则也就只能是有一定“限度”的解释原则。现在,我们展开对现实社会存在本身的分析,诸如我们先行回到价值形式分析的“简单价值形式”阶段。在这里,20码麻布并非是1件上衣,实质上,从使用价值的角度看,麻布无法等同于上衣。然而,只有当20码麻布=1件上衣时,交换这一行为才得以可能。这里出现了一个形式逻辑的矛盾:A在同样的时间、同等的方式下等于非A。此种价值形式运行原则所遭遇的困难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我们在现实社会存在论的层面上完全按照“同一律”的思维思考问题,不可能在现实层面既是A又是非A。然而,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价值形式的运行法则完全与同一律无关。这进一步意味着,马克思通过这个简单形式要告诉人们的是,在逻辑上人们遵守同一律,但在商品交换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当然不仅是经济生活),人们又是排斥同一律的,因为20码麻布=20码麻布并非是价值形式,它需要在一种非同一于自身的物上加以表现才行。逻辑与存在之物相互脱离了,思考的整个逻辑、叙述与所指向的现实存在相距甚远,并非一回事,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马克思运用这种价值形式的分析直接瓦解了黑格尔的“思存同一性”原则。
显然,这四种价值的表现形式对于理解马克思将自己区分于古典经济学家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他没有迷恋于20码麻布=1件上衣之间需要依凭于抽象劳动这一实体性追问。因为按照这样的追问,产生价值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一样,是逃离具体社会形式的人类学意义上劳动,那么价值就不再是一个需要任何社会存在形式为前提的了,反而恒定于任何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正是这么理解的,也很自然地将这一表现看作天然的,并去考量表现之间“=”号秘密的根由。但是,马克思实质上所要揭示的秘密是,为什么劳动产品会表现为价值形式,这是要对一个前提的存在展开批判性分析,那就是商品交换社会作为一个基本的背景,然后才会有将异质性的商品相互表现的可能。
磷肥是作物必需的第二大营养元素肥料,对促进作物生长和保障粮食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土壤中的含磷量非常低,全国大约有80%的土壤缺磷,合理搭配施用磷肥对作物增产的效果非常明显。“自从有了磷肥,我国的粮食产量才开始大幅增长。可以说,如果没有磷肥和磷肥工业的支撑,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张福锁表示,“多年来,中国磷复肥大国地位持续巩固,在技术、装备、产品、服务创新等方面不断实现超越。”
因而,价值形式一直到货币形式完成时,它仅仅是一个表现出来的思想的逻辑。如果说,上述是一个不停地表现、不停地同一化的过程,现实存在本身就已经在简单价值形式中的“=”号的意涵中给明确了,那就是无论如何表现也是与现实存在自身完全不同的,它仅仅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类似于商品B占据了商品A的位置,虽然人们认定商品B仿佛就是商品A本身,但也毕竟只是“仿佛”。也正是在价值主导的“同一性逻辑”与现实存在的“非同一性逻辑”之间存在裂缝,才构成了我们不断去寻找价值同一化的裂缝,这是人类逃离资本主义的希望。因而,对那些只从价值形式主导的“同一性逻辑”出发进行需要修补的原因在于,谈论价值形式的运行法则就意味着已经将人“否定”了,我们每个人在资本的世界中作为不可见的,而可见的尽是货币、商品等一系列价值形式。这样,我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改造的理念一开始就“颠倒了”,我们的出发点不能从一个已经“否定”我们的价值形式或者说资本逻辑出发,任何将人作为“客体”(否定)对待的思维都与人的解放的思考相距甚远。那么,从价值形式表现的商品世界出发永远摆脱不了将人作为“客体”这一困境。一旦我们从否定人、将人作为客体来加以对待的时候,人的解放从思考的那一刹那就已经错失了方向。
三、从“表现的社会”到“社会自身”的进展:复调式解放路径的再思考
既然我们已经通过上面的分析,认识到“价值形式”只是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时,它才构成为社会的运行法则,诚如马克思所述,“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而我们今天在谈论《资本论》的时候,更多的是在谈论作为“结果”的价值形式运行的规律及其相应的统治方式。但是,在价值形式的围城里思考解放只能是一个“悖论”,当我们把“围城”(价值围城)作为思考的起点,这已经将主体作为“否定”的视角来展开了,现在必须转换视角到另一种视域中,即寻求解放的路径显然要跳出价值形式的解释原则,深入到其前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并厘清这种特定的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仅为“社会”在某一阶段的现象,也正是奠定在这一基础之上,才产生各种拜物教的现象。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句话得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在这里,财富如果说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那么,财富本身及其所对应的社会应该是如何的?仔细体会这段文字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财富如果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特定的社会形式,它就不需要以他物来表现自己。离开了商品交换这一前提,作为表现形式的“价值形式”对于财富来讲是毫无意义的,财富就是财富,无须表现。或者说社会的财富就是物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因而第一句就已经说明了价值形式的表现法则的前提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第二,从财富的实体使用价值不再被表现来看,我们可以进一步地得出,私人的有用劳动本身在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劳动就表现为劳动自身,而不再是私人劳动表现社会劳动的形式。有用劳动存在于一切社会中,或者说有社会就有有用劳动的存在,它是独立于所有社会形式之外的“人类存在条件”。第三,在财富、有用劳动不再被表现的社会里,恰恰就是社会自身,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的组织方式伴随一切社会存在,他们自己也回到了普遍的状态。一旦财富、有用劳动都需要表现、拥有表现形式的社会,恰恰也是社会进入到特定社会形式的状态,“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2页。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形式所呈现的“表现的社会里”,掩盖了人类劳动的真正的财富特质,所以,马克思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也“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形式,就像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第四,要突破这种拜物教,就需要走出这种表现的社会,回到社会本身。“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的形态,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这一社会要求的是,它在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自由人联合状态,它不再是任何一种被新的操控所主导的社会,既不是观念的(上帝)、也不是资本的,或者是技术所操控的社会,在现有的社会形式及其之前的形式中,这种主导与控制一直存在。那么,马克思所要说的解放莫非是说,不要再让这种操控主导的社会形式占据着社会的位置,让表现为资本主义、表现为价值形式统统退场的努力。而这样一个让社会成为社会自身的努力,却不能直接说出,犹如不能为上帝画像,它只能通过倒逼的方式得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未来社会的描述正是如此,他将此理解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
那么,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或者说人类解放的路径到底是怎样的呢?马克思有过这样的回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7页。。对于价值所建构的现代商品交换社会来讲,首先得承认要改变“现存的事物”是这样一种“阶级关系”,作为资产者的一方拥有生产资料,而另一方只能提供劳动而受雇于资产者,这在当时的欧洲,马克思是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形式为例讨论的,英国虽然以“制度”推进了这一阶级关系的进展,强化了私有制以及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关联,但是,所有制结构下的阶级关系成为了全部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由此,传统马克思主义解放路径的理解,全部落在这种阶级关系的改造上,消灭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度。因为,正是存在这样的制度形式才会存在作为特定社会形式现象的“价值形式”,并将其赋予整个社会的主导建构原则,破解这一运行原则当然需要改造私有制结构这一“前提”。但是这一方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受到了很多争议,他们认为这过分地以“决定论”思维方式为基础,特别是受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些论述的影响。他们质问,我们能够将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世界的一切对人的宰制都归咎于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资本主义并不是今日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还存在其他的因果过程在起作用,并促成了种族主义、族裔民族、男权主义、种族屠杀、战争及其他重大的压迫形式,当然,这些并非是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压迫形式,但是资本主义依然介入其中,使得压迫更为复杂与严重”。[注]Erik Olin Wright,Envisioning Real Utopias,Verso,2010,p.38.他们基于这种矛盾“不平衡”的视角,给予了革命的广阔的“空间”维度。现在人们在当代激进左翼那里看到了所谓各种社会革命新的续写方式,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主张现实存在的矛盾是多元的,不可统统化约为单一性的“支配性结构”(阶级关系结构)。但是,他们反对单一性又跌落到另一个单一性陷阱中,他们仅仅从另一个单向度的“支配关系”入手去寻求解放的出路,诸如“技术批判论”者不过是将技术设定为单一性的“支配结构”,其实与“资本批判论”者将资本作为主导型的支配权力是一致的。之所以最后纠结于谁才是“支配结构”的主宰者问题,就在于我们已经习惯地将支配的一方作为思考的起点。相反,如果我们将解放重新理解成从“表现的社会”到“社会本身”的进展,也就意味着从劳动入手,劳动不再完全朝向价值化的表现,人真正成为思考解放的起点,主体必须审慎面对一切因价值或者其他支配结构所强加的统治方式,必须理解资本的强大正是主体所制造的,只有主体自身才能使得资本变得弱小起来。这一点在如今哈特、奈格里指认的“生命政治”下成为,生活与生产的界限模糊之后,主体所有的劳作(Do)都被价值化了,主体自然也就没有了自己的生活、自身的发展,自我的思想,同样也就没有了主体的历史,现代史完全堕落为“资本史”。这里没有主体创造解放的空间,因而在《资本论》视角下去阐释生命政治的向度依然是从“否定主体”出发的。
由于KL距离的不对称性,目标函数倾向于使用大qij的值来映射大的pij。ST-SNE使用梯度下降法最小化目标函数,梯度可以整理为如下形式:
一切还是要回到人的生活本身来看,在马克思的眼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们行为本身的价值化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与马克思表述的“生活过程”是同一个过程,在“生活过程”中,人们“从生活主体出发,把个人的现实生活,作为整体的、并且是不停止的活动过程来认识的。根据这个概念,我们能把个人在生活中相互联系的社会现实的总体,作为个人的生活活动的产物以及展开来进行动态的把握”。[注][日]岩佐茂等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页。这意味着主体自身创造社会现实,主体行为自身就蕴含着“解放”的可能性。不过,不能忘记的是,个人依旧是在一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下,即以资本为建构原则的生产关系中生活的,虽然他能够以拜物教批判的视野,用一种心灵抵抗的方式去督促其改变他自身行为,去创造“解放”的可能空间,但终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阶级结构无法彻底的撼动,“这样做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说来是再容易不过的,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7页。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解放绝不意味着一种静态的、彻底的终结状态,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观念中,正是暗含典型的黑格尔“正-反-合”的三段式的辩证法理解方式所致,“综合是对立面的和解,换句话说,是劳资之间关系的妥协”。[注]John Holloway, Fernando Matamoros, Sergio Tischler, eds.Negativity and Revolution: Adorno and Political Activism,London: Pluto Press, 2009,p.4.相反,解放应该是作为主体自身为摆脱现在的价值形式化生活的开放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结构固化的前提下,主体依然有一些日常生活意义上解放的可能。这种解放的途径在于,拒绝将劳动朝向资本、价值的方向,在资本对劳动“同一化”的吸纳过程中作出的“非同一化”的努力,将劳动转变为自我创造的过程。在这个层面来讲,伸张任何一种解放路径都是在为限制资本的无限膨胀作出努力。
Re-understanding the Criticism of “Form of Value”in the Context of Capital
Sun Liang
Abstract: The section of "form of value" in Capital contains a great deal of space for interpretation.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the whole writing thoughts of C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 are influenced by it. However, in the maj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ademia, there is a strong interest in the various "forms of domination" appeared through the value form, by which,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the value form is forgotten that leads to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 of the value form. Therefore, we will reflect on such 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ze deeply for the premise that the form of value is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tructure. We should crack the concept of liberation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capitalist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subject behavior, so as to provide the possible space for the political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
keywords:Capital;Form of Value; Liberation
收稿日期:2019-01-15
* 本文系教育部后期资助“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人的价值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8JHQ026)、上海市浦江学者人才计划“拜物教批判方法论语境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项目编号:17PJC032)、华东师范大学文化观念与价值创新研究基地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6-0125-09
作者简介:孙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轻 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