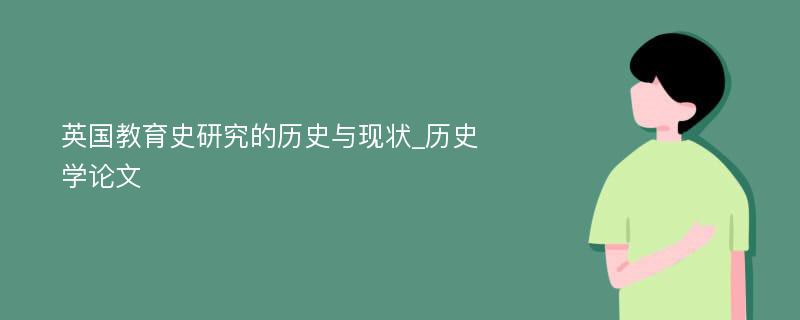
英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史研究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4)02-0001-04
序言
关于教育史研究在西方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近年的发展,我们知之甚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有关资料奇缺,一方面是该课题未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此,我国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几乎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国外的交流寥寥无几,对国外最新动态茫然不知。无疑,这种状况是极不利于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的。对教育史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有利于该学科研究总结历史的经验,不断推进学科的发展和完善。2001年,笔者之一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习,在半年中,得到了教育史教授理查德德·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教育学院丰富的资料,为笔者完成此文提供了保证。
本文依据的主要资料包括:理查森(W.Richardson)发表在《教育史》刊物1999年1-2期上的论文《历史学者与教育学者:战后英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发展》,论文第一部分介绍了1945-1972年英国教育史的发展,第二部分介绍了1972-1996年英国教育史的发展;戴维·克鲁克(David Crook)和理查德·奥尔德里奇主编的《面向21世纪的教育史》(2000年出版);彼得·戈登(Peter Gordon)和理查德·斯赖特(Richard Szreter)主编的论文集《教育史:一门学科的形成》(1989年出版)等等。
一、教育史研究在英国的起源和早期发展
教育史是作为教育学科的一门分支而产生的。19世纪中叶,德国埃尔兰根大学矿物学教授劳默尔(Karl Von Raumer)出版了三卷本的《教育学史》,该书被公认为西方早期教育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之后又有施密特(Carl Schmidt)、施密德(Carl Adolph Schmid)等人的教育史著作,这些均对英美教育史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英国教育史的先驱是奎克(R.H.Quick),早年对德国的访问,引发了他对于教育史的兴趣。他于1868年出版《教育改革家》一书,被公认为英国第一本和最伟大的教育史经典著作之一,该书深受劳默尔《教育学史》的启发。他说劳默尔是“我常常求助的权威”[1](P114)。1881年,奎克开始在剑桥大学教师训练联合会为学生作关于教育史的系列演讲,直到1883年因健康原因离职。之后他的朋友和同事布朗宁(Oscar Browning)接任了他的工作。布郎宁曾任伊顿公学教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及大学历史讲师,1891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日间训练学院院长。他的著作有《教育理论史》(1881年)、《教育理论史入门》(1914年)。像他的前任一样,布郎宁借鉴了劳默尔、施密德等人的著作。
英国教育史的另一个重要先驱是佩恩(Joseph Payne),他于1872年晋升为教师学院(College of Preceptors)教育学教授,这是英格兰大学设立的第一个教育学讲座。他讲授的课程不仅包括教育理论和实践,也包括教育史。遗憾的是,由于资金原因,该讲座只维持了两年。佩恩的讲课和论文于1883年以《约瑟夫·佩恩的著作》之名出版。像他的朋友奎克一样,佩恩在讲授教育史时,运用了德国的资料,也受惠于奎克的《教育改革家》。
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是较早建立教育学讲座的大学,基金来自导生制创始人之一贝尔(Andrew Bell)的遗赠。讲座的名称为“教育理论、历史和实践”。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米克尔约翰(J.M.D.Meiklejohn)在1876年的就职演讲中,强调具有人文主义影响的历史方法对教育研究的意义。爱丁堡大学教授劳里(S.S.Caurie)对教育史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撰写了多种关于教育史的论文和著作。他承认自己的研究受惠于德国的施密特和施密德。
19世纪90年代,随着教育学科开始在大学获得一定的地位,英国教育史迎来了它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当时教育学在理论上主要基于三个支柱,即教育哲学与教育原则、教育心理学以及教育史。在此期间建立的各个日间训练学院都按政府的规定开始了教育史的研究。在1890年颁布的287号文件中,政府对这些新建学院的教师和课程都相当明确地进行了规定:“师范教师必须讲授教育理论和教育史。”[2](p67)当时大学的学院或系所教授的教育史内容包括英国教育机构史、“教育化社会的兴起”,以及著名教育思想家和教育改革家的著作。从1890年至1902年间,有19所大学建立了培训师资的日间训练学院。
英国最早建立大学日间训练学院的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始于1890年10月。亚当森(John William Adamson)任院长并担任教育史和教育理论课的教师,1903年升任教授。他于1919-1935年改任剑桥大学教师培训联合会的教育史讲师,被认为是“他所处时代的最卓越的教育史家”[3](P5)。其代表作有《现代教育先驱》、《教育简史》、《1789-1902年的英国教育》,后一部书成为英国教育史里程碑式的著作。不仅如此,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顾问,在20世纪的前20年中,他促成了许多重要的教育史著作的出版。
除了以上提到的奎克、佩恩、亚当森等人,利奇(A.F.Leach)、沃森(Foster Watson)、亚当斯(John Adams)等都为英国早期教育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到二战前,英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已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范围涉及一般教育史、专门科目教育史、专门时期教育史或专门领域教育史、教育家个人传记、教育机构或制度的发展、妇女教育史等方面。除了书籍以外,期刊和学会出版物也刊载了大量关于教育史的文章。此外,教育年鉴和政府报告也有关于教育史的条目和内容。最后,攻读高级学位的研究生也对教育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期英国教育史研究主要是在大学教育系或教育学院中进行的,教育史成为师资培训的主要课程之一。而大学历史系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史,教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专业历史学者除了对自己所在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感兴趣并进行了一些研究外,很少涉猎教育史领域,他们甚至瞧不起在教育系中所进行的教育史研究。
二、战后至70年代初英国教育史研究的发展
二战后英国教育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专业历史学者开始介入教育史的研究。因此,考察教育史的发展需从历史系和教育系两方面着手。
战后约十年中,遭受战争重创的英国百废待兴,教育史发展缓慢,教师培训所使用的教材没有突破史料编纂的传统。直到50年代中叶,变革的帷幕才徐徐拉开。
大约在1955-1970年间,由于面对一系列的挑战,英国专业历史学者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研究重点。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首先提出了“世界历史”的概念;1961年成立的海特委员会(Hayter Commission)鼓励重新评价英国以外的文化,如西欧文化和北美文化;尤为重要的是,人们对传统的政治和制度的历史日益不满,史学家出现了明显与“更新、更时髦的学科”如社会学相联系的倾向。随着老一辈大学史学教授的退休,信奉“新”历史的新一代史学教授登上历史舞台,结果:一是在本科课程中扬弃中世纪研究而逐渐重视“世界”史;二是强调历史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这些学科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偶尔也有教育学。
与此同时,大学里的教育学研究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战后初期所有英国大学都创办了教育系,教学围绕着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管理和心理学进行。教育系也和历史系一样,课程内容陈旧,教师更替率低,弥漫着保守气氛。60年代随着教育系的大发展,旧的传统开始面临挑战,尤其是教学人员的更新和增长,为革新创造了机会。
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史研究经过战后一段时间的缓慢发展,到6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关于教育史的讨论和争议逐渐增多。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者和教育学者互相敌视的现象,在英国重现。在历史系,一些新的历史学派开始形成,这些学派对教育颇感兴趣;而教育系中致力于教育史研究的学者也着手进行组织,重新确定自己的兴趣范围,并寻求与历史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合作协议。1972年,一份新的教育史专业期刊问世,意图是加强教育学者与历史学者之间的联系并弥合两者的裂痕。
关于教育史在历史系和教育系中的各自发展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专业杂志窥见一斑。1947-1966年间,英伦三岛由大学历史系编辑的主要杂志共发表80篇有关教育的文章,教育史研究范围的拓展速度相当缓慢,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每年平均增加5篇。与此对照,《英国教育研究杂志》自1952年创刊到1966年的15年中,共发表108篇关于教育史的文章,占其文章总数的70%,这些文章大多是由大学的教育学者所撰写的,只有4篇出自历史学家之手。该杂志刊登的教育史领域的文章比英国所有由历史系编辑的杂志上刊登的教育史的文章之和还要多。[4](p9-10)
战后20年中,历史系和教育系的研究兴趣有较大不同。历史系主要致力于大学的研究,1968年印出的有关牛津这一所大学的书目就达809页;教育系着重于中小学校、教育与工业化、国家教育方针等主题。
60年代,英国教育史领域出现了类似美国的修正主义的激进观点。1960年西蒙(Brian Simon)的著作《教育史研究:1780-1870》问世,明确地表明教育学者已从伟人生平研究转到激进的批评这一重要的新定位。西蒙是英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他坚定地认为:阶级矛盾应是英国教育学者进行历史研究的重点。1963年,汤普森(E.P.Thompson)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赞成西蒙的观点,认为共产党历史学者组织关注的问题应成为历史辩论的中心舞台。但他关注的主要领域是劳工组织而不是教育。1965年,西蒙第二本关于政治教育史的著作问世,书名为《教育和劳工运动,1870-1920》,这本书引发了争议。赞同者称新书“巧妙、权威地叙述了教育的历史,非常值得推荐”,反对者称新书的主要缺点在于“把教育上的阶级冲突这一主题过于简单化了”[4](p18)。
1964年,英国教育与科学部接受罗宾斯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建议,决定设立教育学学士学位(BEd)。随着教育史逐渐成为新学士学位的一个必需成分,刺激了教育系和教育学院中的教育史研究。
1967年,教育史协会宣告成立,成员主要来自教育系的教育学者。最初的气氛是相当乐观的,人们谈到教育学学士学位设立后对教育史不断增长的兴趣,但会上也听到了一些焦虑的声音和争议,如关于教育史课程的内容、由谁来教授教育史、大学教育史是否应和历史系架起桥梁等等。不久,来自历史系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牛津大学的哈里森(Brian Harrison)尖锐地批评了大学教育系中历史学的削弱现象,他说,“教科书没有涵盖各层次的教育史,而且只有在教育系中才学习教育史。在大学历史教学大纲中,没有包括文法学校、公学和公共教育的历史,甚至连有关的选修课都没有”。他认为除非历史系开设教育领域的课程,否则“那些令学生备受折磨的、乏味的教育史教科书就不可能得到改进”[4](p19-20)。移居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斯通(Lawrence Stone)抱怨教育系的教育史研究无论从资料搜集还是从理论框架上来说都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因而“它对许多问题的解释都是试验性的、暂时的”[4](p20)。
显然,1968-1970年间来自历史系的对教育学者的一系列攻击,正是对10年前发生在美国的由贝林(Bernard Bailyn)发起的指责的回应。从这时起,历史系的教育史研究开始增多。
1967-1971年间历史杂志上刊登的教育主题的文章比前15年的总数还要多。大量的专著也纷纷问世。历史学家逐渐不再把教育史看作是一门已到终点的学科,而是将它看作一个有前途的、迄今为止被忽略的领域,而这一领域恰恰是解决许多范围广泛的问题的途径。
到1970年,英国教育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比一战以后的任何时期都更广为人知,它在历史杂志上获得空前的大空间,它成为教育系教育学学士学位的一门核心课程。1970年,教育史协会决定创办一份专业杂志《教育史》,两年后该杂志正式发行。
三、7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教育史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大学的历史学者和教育学者对自身的前景充满信心,教师队伍的不断扩大,赋予了他们自信和创新的愿望。无论是大学历史系还是教育系或教育学院,专业都获得稳步发展。然而,仅仅几年间,历史学者和教育学者都面临着新的变化和生存危机,前者较快地摆脱了困境,后者则陷入持续的衰退之中。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十年中,历史系的专职历史教师的人数增长了30%,其中1/3的人的年龄都在35岁以下。这一时期被看作是“英国专业历史学者的黄金时代”。虽然后来大学拨款委员会为了应对石油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萧条,在1974-1981年把给予每一名学生的拨款缩减了10%,但它同时也决定增加文科学生的数量,于是历史系本科生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此外,历史学科的学术组织也获得稳定的发展,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二者都具有稳固的基础。历史系完全是自治的,新型的科技学院(Polytechnics)也开展了小规模的历史教学。然而到80年代早期,历史学科出现衰退趋势,一方面政府实行紧缩政策,一方面人们对历史学科的未来普遍感到悲观。所幸这种情况并未持续下去,1989年《国家课程》的制定被看作是加强了历史学在中小学中的地位。同时,大学也开始重新补充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人员。从总体上看,到1992年,历史学明显“不可能步古典文化的后尘而处于边缘地位”[5](p115)。
与历史学相比,教育学科的经历更为坎坷。1970年,英国共有157所教育学院,其核心课程由四门学科组成: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在1972-1973年间,对教育学者不利的气氛逐渐形成。由于石油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萧条,教育系和教育学院成为缩减的目标。在学术方面,人们对新的教育学学士学位的智力水平仍表示怀疑,在其建立七年后,仍有40%的大学拒绝承认它。此后,政府继续实行紧缩政策,着手改革高等教育,教育学院或关闭,或被并入科技学院或综合大学。从1972年到1982年,教育系和教育学院的入学率下降了75%。许多教职工面临重新安置或提前退休的问题。同时,政府中有影响的人物毫不掩饰他们对大学教育系的轻视,教育系所进行的研究不被重视,被认为是一个受时尚和一时爱好所控制的领域,并且从整体上看,“很难想象英国大学或科技学院的教育系有名副其实的智力特色”[5](p115)。此类批评使教育系的影响逐渐减弱。甚至有人说:“教育学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从1983年起,政府决定逐步重新确定教师培训的内容,此举既损害了大学教育系中的教育学者的信心,也降低了他们在大学中的地位。1996年,政府研究评估处的调查结果表明,在69门学科的质量排行榜上,教育学位居第58位。教育系和教育学者们这种不稳定的地位,无疑影响了教育史研究的水平。而在历史系,由于具有较好的前景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结果,到20世纪90年代,历史学者掌握了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领导权。
自20世纪中期起,历史学者开始对教育史这一主题发生空前的兴趣,在教育史协会1967年成立后,有些历史学者还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教育系和教育学院里,历史学仍然是“教育研究”的基础组成部分。英格兰27所设立教育学教授席位的大学教育系里,有5位教授的研究领域是教育史。的确,1968-1971年间,历史学者曾尖锐地批评教育系的研究传统,但是二者之间的桥梁似乎正在架设,裂痕也在弥补。教育史协会成员虽然大多数来自教育学院,但他们主动邀请、吸引大学历史系中的一些资深人物和杰出青年在协会的一些会议上发言。此外,教育学院和大学教育系补充了相当数量的历史学者。然而,经历了短期的有限合作之后,从20世纪70年代起,又恢复到了50、60年代的局面:教育学者和历史学者再一次各自工作,很少相互交流;大学依然存在着对专攻历史的教育学者的轻视。1975年,约翰·赫特(John Hurt)在一篇文章中连珠炮似的攻击说:“虽然过去的25年间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章,然而这一学科的严肃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对于这种奇怪现象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上面列出的这些书没有几本是由在大学历史系或其他学术机构工作的历史学者撰写的。大多数书籍和文章都是出自教育系,而在教育系里,还坚持认为教育史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历史学的分支呢!”[5](p121)
历史学者和教育学者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在《教育史》杂志上,由大学和科技学院历史系的人发表的论文仅占全部论文的4%,在历史系所编辑的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教育学者更少。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什么专业历史学者参加教育史协会的会议了。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教育系中专攻历史的教育学者的前景越来越凄凉了。当1987年教育史协会召集一场会议来评论教育系在教育史领域越来越低的地位时,会议的气氛虽斗志旺盛却不免有些悲观和听天由命的味道。
教育史在教育系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看,政治对教师培训课程的干涉,威胁到一个世纪前建立的历史观。同时70年代非常诱人的研究生学习此时也衰退了。此外,人们批评教育学院或教育系中的历史研究存在诸多不足,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仍是十分传统的。因此种种,教育系中专攻历史的专家无论在概念上和体制上都受到围攻。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教育系里的历史学的衰退进程加快了。教育史协会会员逐渐减少,虽然《教育史》和《教育史学会简报》仍在定期出版,但其他活动逐渐压缩。1986年,教育史协会暂停出版历史资料的系列导刊,1987年,庆典出版物也停止了,1990年年度《论文集》停止发行,这些都表明历史学在大学教育系中的地位跌至低谷。历史学的职位和课程正在减少。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种历史学衰落的气氛也可以从那些向《教育史》投稿的作者们的地址上反映出来,这些作者的地址都表明他们已退休了。
与教育系历史学衰退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历史学者进行的教育史研究正呈上升趋势,文章数量增多了。如英国历史系所编辑的所有杂志一年中发表的有关教育的文章在1977年到1996年翻了一番。在历史系,对教育学的兴趣持续增长,新的课程不断开设。80年代中研究教育史的学生在数量上也有所增长,有几种杂志还开辟了教育专题。这种局面的结果是,虽然整体上教育系的历史研究衰落了,但历史学者则完全占据了这一领域,并成功地界定了这一领域的范围。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历史学者取代教育学者成为确定教育史领域内容的正式角色。
结语:面向21世纪的英国教育史研究
教育学院或教育系中教育史研究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衰落还将持续多久?还有复兴的可能吗?此时下否定的结论恐怕为时过早。历史系的教育史研究究竟能够走多远?它能完全替代教育学者的教育史研究吗?此时下肯定的结论也是为时过早。我们将拭目以待。
事实上,教育史在教育学院的前景并不是一片暗淡。如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王学院是伦敦大学教育史研究中心,但随着1983年查尔顿(Keneth Charlton)教授退休,教育史研究中心移至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在这里,教育史仍在硕士和高级学位课程中被讲授,并不断获得外界资助。这些导致了大量教育成果的出版,如对教育与职业部的文化与历史研究、对伦敦地区教育福利事业的历史研究等等。实际上,由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Econon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利弗休姆基金会(the Leverhulme Trust)以及纳菲尔德基金会(the Nuffield Foundation)提供给英国教育史研究的大量和有声誉的资助是90年代教育史发展最有意义的特征之一。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著名的教育史教授理查德·奥尔德里奇(Richard Aldrich)和他的同事戴维·克鲁克(David Crook)都对教育史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们承认教育史领域正面临变革,而不承认教育史正走向衰落。他们相信:“根据研究和出版的成果,英国教育史以相当强的势头进入了21世纪。”英国教育史协会的旗舰刊物《教育史》最近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协会会员人数令人鼓舞地保持稳定,每年召开的年度会议依靠奖学金和其他资助,吸引了许多学生会员。[6]
教育史研究在历史系中的发展更是令人鼓舞,甚至有人大胆地推测“很可能教育史会从教育系消失而在历史系找到自己的重要位置”[2](p73)。当然,这种推测正确与否,尚需时间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