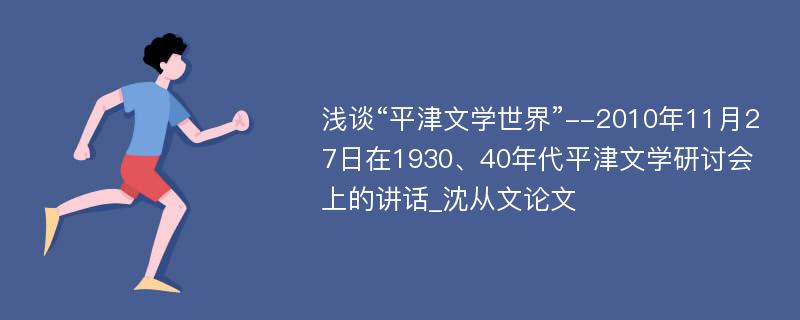
“平津文坛”漫议——2010年11月27日在“1930、40年代平津文坛学术研讨会”的演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津论文,文坛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年代论文,漫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平津文坛”的概念,按理顺着“平津”的说法天然就是成立的。而且此概念内在地包含着时与空两面,空间不用说了,时间方面即现代以来“北京”改称“北平”有多么久,这个当年的中国北方文坛便有多长——大致从1928年到1949年的北平、天津两地的作家群体、报刊及出版物的文学生长状况等,就都涵盖在里面了。1930年代上海是全国的文学中心,北方主要有京派文学等。京派活动的范围包括天津,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作为“京派重镇”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由沈从文在北平编,报纸却是在天津出的。到了1940年代,平津均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现在谈“沦陷区文学”一般是指东北沦陷区、平津沦陷区和上海沦陷区这样三块。这些都不会有什么争议,只是很久不大重视罢了。
不重视将平、津文坛合一,往往与人们的视线被“中心现象”遮蔽,来不及将其他地方顾及、细化有关。比如一谈到“五四”文学,北京是发祥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青年》作家群是焦点;一说到1930年以后的文学,中心转移到了上海,“左联”在上海,海派文学在上海,自然眼睛都盯在那儿。本来从晚清的政治地图看,北京是京畿重地,天津卫是保护京畿的门户,京津两个城市一体,并有合理分工(一个是政治城市,一个是商业城市;一个大陆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到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南移之后,平津地区便一起失落。旧的文坛打散后,该如何重新聚集,就演变为自备一格的文学环境了。
一 京派-北方左联-北派通俗:文学形态多样的文坛
京派形成了能自立于强大的上海左翼文学之外的“纯文学”,是平津文坛最显著的特色。那时在中国任何地区都不可能构成如此的纯文学的创作条件,这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不过京派的纯文学并没有那么“纯”。中国没有真正的形式主义的写作,京派作品大部分具有温和的社会性。因为纯文学创作是没有普通市民读者市场的,靠的是校园的依托:从校园精英文化生长出来,还基本由校园读者来消费,循环不已。所以当年的京派作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师生组成,他们多半不等着稿酬买米下锅,可以相对从容地写作。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教职到北京参与杨振声编辑教科书的班子,与张兆和结婚,接编天津《大公报·文艺》,三事联办,到10月就在自己编的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批判“玩票白相”的上海文人,引发了“京海论争”。第一个在上海写文章回应北方发难的苏汶(杜衡),在《文人在上海》里就认为一味指责上海文人“爱钱,商业化”是并不公平的,因这边“不容易找到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结果是“急迫的要钱”,“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①暗指京派作家大部分在大学任教,不像海派作家需牢牢依靠稿费活着的状态。这对于一定的写作态度、作品品质、工作方式,对于写什么和怎样写,确实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点杜衡说的倒是真话。
我们还可以举话剧在平津的情况来补充说明之。作为北方话剧运动中心的天津南开学校,远在晚清就由校长张伯苓带头发动,1914年成立南开新剧团,几十年坚持演出,其宗旨为“练习演说,改良社会”,以提高学生素质为主。张彭春在美国学成戏剧归来后更对新剧团作大力的推进。到1930年新剧团演出高尔斯华绥(英)《争强》;1934年重排保留节目《新村正》;1935年隆重推出莫里哀(法)《财狂》(即《悭吝人》),曹禺任主演,林徽因任舞台美术设计。但这些都是依托校园的,与处于话剧中心地的上海话剧演出团体不同。有趣的是,1935年曹禺的《雷雨》在国内和日本首演,到第二年职业性“中国旅行剧团”终于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连演三个月,场场爆满,标志了中国话剧商业演出的成功。几乎同步的,曹禺本人参加母校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不是校庆游艺,便是慈善赈灾,票价一般2角起(对本校游艺演出经常是免票的),实际不计成本(如竟规定“视线不周之座位,均行划出,概不售票”)②。南开新剧团排练一部戏的成本可从曾被当局明令停演的易卜生名剧《刚愎的医生》(即《国民公敌》)透露出来,1928年曾确切记下“赔了六百多元而不能公演”③就知道成本的大概了。而如在校外演出,剧票贵者可卖到2元、1元。1929年新剧团和南开大学女同学会在天津法租界明星大戏院联合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可怜的斐迦》两剧,便是这个高票价,有明确的账目可查;“共售票得洋1076元,除广告、印刷、租金及其他用费360元外,下余716元。”这里没有列出制作的成本,只有演出成本,故低于600元(估计前后都在演此剧目,无需专置布景服装)。这余钱716元后来“以一半捐入天津联合筹赈会,以一半归入校友楼(科学馆)捐款”。④这就是非商业性话剧依托校园而存在的南开新剧团经济状况:它不等着给演职人员发工资,它能找到学校或资助人来做布景服装,即便有了困难也是暂时的(大不了不演。南开新剧团几次不运作的时候校内的话剧演出照样活跃),显示了与京派文坛一样“不差钱”的特点。
平津文坛也有左翼,那才是穷困的文学。除了平津那么多中学、大学里有左翼的文学结社,有校园的左翼文学刊物、文学墙报、油印出版物外,最重要的是存在于1930年至1936年间的“北方左联”和短期的“天津左联”。“北方左联”又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也有称为“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似乎名称也难统一。主要的人物有潘训(漠华)、谢冰莹、杨刚、陈沂、台静农等。因为是地下活动,究竟有多少盟员,领导层如何,是隶属上海左联总盟还是独立自成系统,目前研究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它有过几个机关刊物,确实有左翼作品在发表,这一点无疑。如1933年王志之、潘训编辑的《文学杂志》,出版四期(三、四期合刊),发表过鲁迅、茅盾、丁玲、张天翼、艾芜、宋之的、王志之、孙席珍等的作品。同年还有张盘石、陈北鸥主编的《文艺月报》,仅出版三期即遭查禁,登载过茅盾、吴组缃、穆木天、金丁、陈北鸥、张我军等的作品。北方的左翼文学,为什么没有沪地兴盛?原因有两点:一是离政治热点远了。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在南京,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曾经在上海,都不在北平。不是政治压迫严重的地方左翼被压得抬不起头,而是恰巧相反,越是压迫重的地区反抗的力量越大。所以第一线的上海喊声四起,刀光剑影,北方则相对沉寂。二是左翼文学也离不开出版市场。印刷业、书局、发行渠道自来集中在上海,到了1930年代,上海进入现代繁荣期就越发如此了。老牌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外,1920年代中后期成立的良友图书公司、开明书店、现代书局,都敢出左翼的书刊。“良友”在丁玲被捕后迅速推出《母亲》;“开明”出《子夜》;“现代”出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不算,被封后不得不出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周报和月刊,但主要经营的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月刊,就既登新感觉派小说、象征派诗,也登鲁迅杂文!所以能推动左翼蒋光慈名声大噪的,当然是上海的出版界,北平就没有这样的出版魄力。就连原先与新文学关系不一般的北新书局,在1927年也把总店迁往上海,余下的几个书局朴社、星云堂等便十分可怜。左翼文学不能在贫瘠的出版环境下生存,所以它并不因北方当局控制薄弱,或者天津也和沪地一样有外国租界可用以掩护,政治迂回空间大,而就能作强势的发展。
平津虽非左翼文学生长的理想之处,却是北方市民文学的福地。平津原来的传统市民社会到了近代虽发展缓慢,但天津的部分现代化延伸使它成了上海的某种压缩版,便有了一些例外。天津与上海一样连着海运贸易,租界里有万国的金融银行,街市发达,现代商业文化与齐鲁燕赵的传统文化相混杂,就形成了品味与南派读者不尽相同的北方市民读者群体。这是北派通俗文学生存的基础。较早的张恨水是安徽南部人(地理位置也属江南),他北漂到北京参与《世界晚报》创刊并连载《春明外史》而走红。但后来,渐渐有了以天津为依托的津籍通俗作家,远远超过了北平。写言情巨作《红杏出墙记》的刘云若是天津人氏,最初的《春风回梦记》在津地《天风报》连载出名,后来的作品都连载于津门的副刊、画报。而上承平江不肖生、下启金庸的武侠大家还珠楼主的代表作《蜀山剑侠传》,从抗战前连载到抗战后,最初也是在天津《天风报》跨出连载第一步的。至于所谓“北派武侠四大家”的宫白羽、郑证因都是天津人,朱贞木虽是绍兴人,却在天津电报局当课员,与还珠楼主是同事,受其影响才走上写武侠之路的。宫白羽少年时代起在北京接受教育,先受新文学刺激,所以自当北京邮员始,就写信向鲁迅、周作人求教。鲁迅指导他到公共图书馆自修,所写文字经鲁迅推荐发表多篇。但等他回到天津入了报社,写出的却是用“白羽”为笔名的社会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天津作为通俗文学的北方基地,在市民社会、市民读者的特殊性上值得我们注意。
这就可以看出当年平津文坛的独特了。这里生长的文学,形态多样。左翼虽然薄弱,但它是作为京派根源的中国学院文化的现代营垒(包括一部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史),是京派的栖息地;又拥有现代市民社会的丰富土壤,是后来居上的北派通俗文学发祥之所。
二 外来作家-学院派作家-新老市民读者:超出地域范畴的文坛
研究香港文学有一个“南来作家”的概念,我们观察平津文坛可注意“北来作家”。平津文坛主要的作家群是“京派”,如果我们去检点一下文学史,那么能占据一定历史地位的平津作家其中大概七八成都是“京派”。我们不妨取钱锺书小说里的一段话做根据(注意那并非是正襟危坐的“京派论”,而是用调侃口吻道出的,更见得真切),来看京派作家的来源:
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的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入籍归化的国家,不住的挂在口头上。⑤
所谓“南方人”,一般是对长江以南包括长江流域住民的统称。“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属于作者的感觉和印象,但真是准确无误的。我现在来给钱锺书的话做注脚,取比较狭义的27位京派作家(新月、语丝诸身份比较复杂者,先行割爱)来统计,结果是原籍和出生地都属南方的有周作人(浙)、废名(鄂)、俞平伯(浙)、沈启无(苏)、丁西林(苏)、沈从文(湘)、卞之琳(苏)、梁遇春(闽)、朱自清(浙)、朱光潜(皖)、林徽因(闽)、孙毓棠(苏)、何其芳(川)、梁宗岱(粤)、汪曾祺(苏)等15人;原籍本为南方,由父辈或祖父辈迁京津定居者,按照中国的习惯仍应算南人的是曹禺(鄂人生于津)、凌叔华(粤人生于京)、林庚(闽人生于京)、焦菊隐(浙人生于津)、江绍原(皖人生于京)共5人;纯平津籍和北方籍的有萧乾(京)、冯至(冀)、李广田(鲁)、李健吾(晋)、师陀(豫)、杨振声(鲁)、李长之(鲁)计7人。这样初步统计,京派之中的南籍与北籍的比例是20:7。平津籍的作家主要未统计在内的是老舍,还有刘云若等几位市民作家,而属于南籍却不能算入“京派”的平津作家,至少还有胡适(皖)、徐志摩(浙)、闻一多(鄂)、冰心(闽)、梁实秋(浙人生于京)、张恨水(皖)等,且都是大家。所以这个“北来作家”的名单并不完全,而外来的文人占了大多数,平津籍本身却很少,是没有疑义的。这与晋宋两朝南渡,长江流域经济逐渐超过北方之后南方的发达有关。由文化而及政治,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更是南方优于北方。北迁官僚阶层文化积累的优势,当然造成这种平津文人多南人的典型现象。
这种南人优势便是文化优势。以上统计过的27名京派作家,如果再从是否属于大学师生的背景或有无受过大学教育的背景来调查,就更加彰显。如果连沈从文这样仅有小学不完整学历的作家,因胡适的举荐始在中国公学教书,继而在青岛、北平、昆明的大学任教后,他也具有“大学师生的背景”了,那么27人中就只有一人即师陀和大学无缘。而26名与大学有关的京派作家,如按是否出国留学或曾出国访学来统计,15人是具国外留学访学经历的,11人没有,前者超过一半,比例也相当惊人,这样便明白京派的知识精英比例有多么高了。
南人北上,又是高学历,这种学院文化的创作会带来哪些特色,我们将在下一节集中讨论。但是在平津,一方面原来以中原为基础的北方传统文化必然要受到南方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学院能够伸向世界文化的触角必然是绵长、灵敏的,所以平津文坛的地域特点就会受到消解。它与其他各地文坛固守地方的文化就不尽相同,更呈多元性。“京派”写作几乎没有北京天津味,京味都留给了老舍,留给了通俗文学,于是纯文学这一块就显得开放超然得多了。
老舍的创作给我们启发之一,是如何来看待平津的市民读者。在老舍的《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里面,老派的市民安分守己,朴素信实,衰败、妥协、封闭。为什么老舍写老派市民充满同情?写洋学生出身的人物就带嘲笑、揶揄?因为平津地区在清朝覆灭、民国北洋政府垮台这两次历史大变故中,沉淀下无数的老派市民。老舍的满族身份使得他视野之内充满这些市民。老舍师范毕业只受过中等的新式教育,如果不是到英国教书,他的淡漠“五四”、淡漠新文化的态度不知何时能够改变呢。所以老舍的母亲所构成的市民社会,必然不是读“京派文学”的洋学生,而只能是读通俗文学的旧市民读者。平津读者至少有这样的分野。
这样的平津文坛,高可悬于古城洋场之上,低即沉于市井里巷之间。为什么北方好的大众画报如老牌的《北洋画报》,还有《一四七画报》、《三六九画报》都在天津?为什么从事纯文学作家都不往天津去?而宫白羽在北京时想搞的是新文学,搞通俗文学时节就回到天津?那是因为津门这地方才有商业文学的气息。而在北平,就会出现林徽因东总布胡同的“太太的客厅”,以文学谈吐的高雅、前卫和女主人亲做的西式点心出色而闻名。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文学沙龙,是敌伪时期北平八道湾周作人的“苦雨斋”,那里的周的友人和“四大弟子”拥有的是象牙塔里的文明批评及得半日之闲于瓦屋纸窗下的清茶一杯。这与上海文坛比较,就容易避俗。平津文坛因它的特殊文化结构,终成为一个并非世外桃源的,却带点超越的文化地带。
平津文坛还是个互渗、互补的文坛。纯文学以北平为主,俗文学以天津为主,是自然的分工。但不是说北平的俗文化的底子不厚。如果不厚,怎么能产生张恨水,产生老舍?也不是天津出不了大作家,而是出了作家就自然流到北平去了,像曹禺、李霁野、焦菊隐。“五四”时期北京有著名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到了北平时期,好的副刊在北平编,却都在天津出版了,如《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的“文学周刊”都是如此。平津文坛的辐射力当然遍布国中,但它最能互补互渗的是东北文坛,所以这是一个好题目,可以研究关永吉、李克异、梅娘等三类东北乡土的、现代派的、通俗的作家,如何流向平津的。至于延安文学、华北解放区文坛和平津的关系,更是个新课题。比如我听跟着贺龙到过冀中根据地的沙汀说过,他很惊奇于华北的农民有观看露天的广场话剧的喜好。如果说和河北定县熊佛西的“农民戏剧实验”有关,那么熊佛西是“燕京”出身,从美国留学回来也是一直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便涉及了平津文坛。这对于我们加深认识这个文坛,都不无关联。
三 旅居催动回忆-书斋前卫-民间意识:文学中心之外的文坛
我们来初步探讨一下,这样的独立于文学中心以外的文坛,会给创作带来些什么特质。
既然很大一部分的作家是“外来”的、“北来的”,那么,他们在平津这块文化土壤上就不是本土作家,而是“旅居作家”。这种“旅居性”所带来的是“回忆性”的写作。这一点,鲁迅在总结“五四”时期北京的“乡土文学”时,就已经充分注意到了。他说起蹇先艾、裴文中、许钦文等人来是: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⑥
这里使用的“侨寓”一词,就是“旅居”。而旅居者容易产生的是“乡土文学”。因为被生活从故乡“放逐”,便只好“回忆”——鲁迅说得很是清楚明白。《父亲的花园》是许钦文一篇小说的名字,你可说凡回忆乡土的写作都是在重返“父亲”带给你的那个童年百草园。这类乡土回忆在“五四”作家手中侧重于对封建乡土的“暴露”,而在“京派”文人笔下已是诗化般的再造重铸,及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我们看沈从文《边城》的题目,他已经是站在中国首善之区、中心之地来看待自己遥远的故乡土地了。《从文自传》里,《我所生长的地方》、《我上许多课仍不放下那一本大书》、《学历史的地方》这些题目在时序上都是回述。而《湘行散记》这部散文集子本身就是作者回乡探母病的“湘行”记录。沈从文的湘西辰河上下仍是明丽,但现代的“侵入”已是无可避免。鲁迅《故乡》式的返乡叙事,就是沈从文的回忆写作。废名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桃园》、《河上柳》也是对湖北黄梅家乡逝去的人物、人情的回溯。《桥》的开篇《万寿宫》写祠堂壁上漫漶的文字,“请看,这里有名字,‘程小林之水壶不要动’”,就引你发童年之幻想了。在这方面沈从文起初是学废名的。师陀是倒叙的里手,《无望村的馆主》、《果园城》这种名目及内在弥漫的忆旧的气息是如此浓厚,《落日光》、《里门拾记》这些散篇仿佛在低吟衰败的乡土,如烟,如泣。而萧乾的第一个小说集名为《篱下集》,述说他少年时代在京城寄人篱下的日子,他的幼年情结无处不在。京派“最后一个作家”,并未真正在平津写作却最得老师沈从文真传的汪曾祺,借故乡高邮写乡土社会,写“最后一个”用木车床劳作的《戴车匠》,写“最后一个”孵鸡赶鸭出神入化的《鸡鸭名家》,他的继承性的突出之点,也在这里。正像我们如果要继续寻找京派回忆性写作的精品,剖析每一个京派个性鲜明的回忆性写作的特点,是举不胜举的。这是“旅居”带给作家的恩物,造成了现代中国乡土文学奇峰迭起的不凡景象。
此外,平津文坛既然拥有众多文化教养很高的作家,就必然给写作带来书卷气,带来书斋文化的气味。那么多大学教授组成的作家队伍,很多人是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兼任的。周作人教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兼通现代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江绍原本来的专业是宗教学,又心仪民俗学而与周作人不断切磋、请益。像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都一边写诗、写散文,一边研究古代学术。废名在北大教国文、英文、古典诗歌研究(开陶渊明、李义山的课),还讲《孟子》、《论语》;他研究古典哲学、佛学,与熊十力观点不一,争论时竟至交手打架;发表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同期,在佛学刊物上发表论文《佛教有宗说因果》,1940年AI写作成主要的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平津作家中甚至有的文学仅是副业,比如林徽因的主业是古建筑;长诗《宝马》的作者孙毓棠,是清华大学历史教授;中国独幕剧、轻喜剧的重要作家丁西林,在英国学的是物理、数学,且始终是国内著名物理研究所的主持者。这样的一群作家,他们文学创作的知性特点便十分明显。连与乡民联系紧密无隙的沈从文,都有对《法苑珠林》佛经故事改写小说的兴趣,写成了《被刖刑者的爱》、《扇陀》等。京派剧作家充满睿智,剧本适合于书房阅读甚于剧场演出的,如李健吾的代表作《这不过是春天》,书面性就非常强烈。“苦雨斋”的闲话小品,从题目看多序跋、书简、学术随笔,文题多忆旧录和读书记,谈古论今,舒展平淡。俞平伯的小品多历史记游体、学术文,喜写梦,为重刊《陶庵梦忆》写跋,写过《芝田留梦记》、《梦游》、《梦记》诸文,百则笔记总名《古槐梦遇》,真是书斋说梦不止。周作人借谈俞平伯的文字,总结这一派崇尚自然的絮语文的好处,是“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⑦,强调了“知识”。他说的“趣味”多半也是文人的,所谓涩味、简单味,从书本中来又回到书本去的味。
平津学院派的文学会有先锋意味,是它与世界文学进程保持同步的一个明证。沈从文的“本色乡土”内含的现代性叙述,要到昆明时期才使前卫性尽显;林徽因的小说刘西渭却从一开始就说像英国现代体;废名的先锋性无论诗歌小说都很显著,再添加上东方的“禅意”;何其芳获《大公报》文艺奖的散文集《画梦录》被公认颇具实验价值。我们再看京派诗歌,内含了中国现代主义实验诗的一大系统(当然左翼诗歌里如后期创造社也有象征诗),从最早的“抒情诗人”冯至到年轻的“汉园诗人”之一卞之琳,从早期象征诗到后来成熟的十四行诗和现代诗,也是平津文坛生长出来的硕果。一直到沦陷前后还产生学院派诗人陆志韦、吴兴华等。因为华北沦陷区既有乡土写作、通俗写作,小说方面还有袁犀(李克异)的《贝壳》、《绝色》、《手杖》的现代派创作,现代主义引入是很全面的。假若从李金发最初的现代主义诗集都是在北新书局出版算起,先锋文学持久地在风沙漫天的北方徘徊,究其因,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最后还应提到平津作家的民间趋向。平津文坛再超越,它毕竟是中国北方的文坛,它不可能不受到平津地方文化的浸染。鲁迅引过黎锦明的话来说,“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⑧。这包含了四合院的灰墙、街市的灰土和沙尘蔽日的天空,却并不是全然颓废的“灰”,而是胡同文化的淳朴、传统、守旧,安分守己、吃喝拉撒睡的“灰”,是小民的有活气,也易混吃等死的“灰”。我们读老舍、老向(王向辰)的文字,老舍从小羊圈胡同贫民区出发的叙事,老向的小说集《黄土泥》、《民间集》,从河北黄土泥写到北京胡同的黄土地,两人都熟知北地的民俗,如婚丧、问巫、玩耍、杂艺,从中了解民性。焦菊隐能将“北京人艺”最后带入表现北京平民最普通的社会人生的境地去,这不是一日之功。“平民意识”成为平津作家普遍的思想倾向,不论是在东直门城墙根长大的萧乾,还是名门闺秀出身的冰心、林徽因都有。萧乾写《邓山东》、《印子车的命运》很自然,冰心会写《分》,林徽因写《窗子以外》、《文珍》、《绣绣》。将劳动人民收入自己眼底也不为怪,林庚在诗里不还将北京的街头摄入了吗?所以,北平、天津的民间营养丰厚,一定会进入文学。如果北平的胡同大杂院可以进入老舍笔下,高门深院可以在张恨水的《金粉世家》里得到表现,北平天津的风格也会迂回曲折地进入北方技击派的武侠小说之中,如郑证因熟悉北平武门(曾在北平国术馆学太极拳),又熟悉津门帮会仪式和黑社会内幕,其武侠小说的“阳刚”之气正是北派苍茫、阔大的一个代表,并对以后硬派技击小说的发展发生着影响。民间血液流淌在平津文坛之间,与文人传统一旦拍合,必是北方的优势。
于是,我们看到北方文坛执了两头:南人占多数的北方文人圈子必然令南北融和;纯文学和政治文学、消费文学的兼有,同样也会使三者相互掺杂。它如果永远离开“中心文坛”,就可以长久地不归并到一统的文学模式中去,那会有怎样的前程呢?不过这仅是我的一个假想。
2011年8月9日修改
同年8月24日修改毕
注释:
①苏汶(杜衡):《文人在上海》,《现代》,1933年12月1日第4卷2期。
②《南开话剧编演纪事(1909-1949)》,收《中国话剧先行者张伯苓张彭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8页。
③同上,第407页。
④同上,第424页。
⑤钱锺书:《猫》,《人·兽·鬼》,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⑥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页。
⑦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78页。
⑧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标签:沈从文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天津历史论文; 老舍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鲁迅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