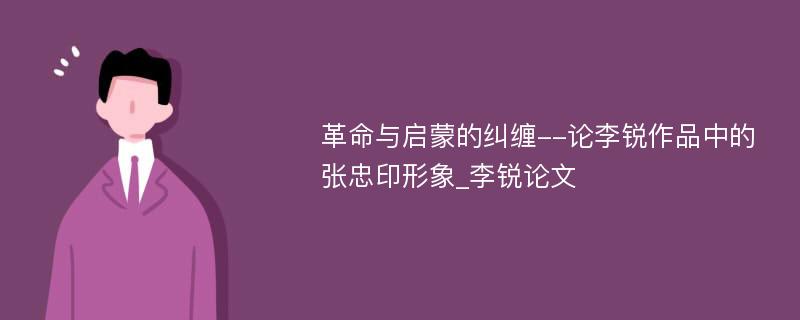
革命与启蒙的纠葛——论李锐笔下的张仲银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纠葛论文,笔下论文,形象论文,李锐论文,张仲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概由于自己“文革”期间六年吕梁山插队经历的关系,李锐小说描写的多是“文革”背景下吕梁山区的风土人情、民间风俗、自然风光与农民日常生活,而知青则是一个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出没其中的形象(该形象也可能是知青的变形,比如像《无风之树》中苦根那样从“上边”派下来的、有一定文化的年轻干部)。知青和农民、知识分子与乡村、革命与民间传统的关系,则成为李锐小说着力处理的重要主题。李锐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般具有双重特点,一是有知识(当然是相对于当时吕梁山区村民而言)并热心革命,二是在他和乡村村民、包括当地村干部、大队干部之间,总是存在严重隔阂,具体表现为他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理想总是无法得到村民/村干部的理解和呼应,或被后者严重曲解和歪解(但正如我下面的分析将会表明的,这歪解从另一个角度看却又出奇准确地表达出农民对中国革命真正本质的深刻把握),结果导致他深刻的孤独感。 这两方面的纠缠与龃龉,演绎出知识分子与民间、革命理论与民间伦理的一连串的恩恩怨怨。 一 自豪与孤独: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情感结构 张仲银的形象最先出现在李锐的中篇小说《北京有个金太阳》(1993)中,后来又在长篇小说《万里无云》(1997)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书写(但基本情节具有明显的连贯性乃至有相当部分重复)。这个形象集中体现了李锐对于知识分子、革命、民间三者关系的思考。 张仲银是五人坪唯一一个知识分子,他有文化,会唱歌,擅口琴,是“方圆十里的山沟里最有学问的人”①。中师毕业后,他学习回乡青年邢燕子,到农村从事教育事业,成了一位乡村教师,还以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瓦西里耶芙娜鼓励自己(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和那个时代的其他知识青年一样,都受到五六十年代革命榜样教育的深刻塑造)。虽然身为教师,但张仲银不只是、而且主要不是来五人坪传授知识的,他更是一位热心的革命者,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鼓动者。他在五人坪的主要活动不是教书而是鼓动革命(破四旧、斗地主、写大字报、抓阶级斗争,等等)。当然,鼓吹革命和传授知识在农村也不是绝对不相关,或者说,知识传播也是张仲银接受的革命使命的一部分,正如鼓舞张仲银来五人坪的乡村革命教师邢燕子和瓦西里耶芙娜,都与传播知识有关。革命理论毕竟也是通过知识承载的,没有最起码的知识,就没有办法传播与接受革命理论。②但与传播知识相比,张仲银更能找到自己生命存在感的无疑是革命,革命可以极大满足他的成就感、在场感和中心/广场情结——在小说中表现为渴望被人注目、一呼百应,渴望自己成为榜样和偶像(顺便说一句,这恐怕也是革命之所以能够让人心醉神迷的潜在秘密之一)。用小说中反复出现、张仲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来表达,这种感受就是“自豪”。③ 遗憾的是,张仲银的自豪感因为不被村民(包括自己的学生)理解而伴以深刻的孤独。尽管乡亲们对仲银极度敬畏,对他的知识、文化,他的歌和他的口琴,崇拜有加,却唯独不懂他自己最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热情。小说一开始就写到张仲银领着一帮学生唱革命歌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学生们无比欣喜、激动万分,扯着嗓子狂吼,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歌词及其传达的革命思想。他在五人坪豪情满怀地传达中央文件,张贴各种各样的批判刘、邓、陶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但所有这些革命举动无不石沉大海,毫无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政治的张仲银被村民们审美化了,村民们在学习中央文件时听到张仲银“铿锵有力的朗诵”,“都很惊奇,都说仲银的学越教越有样了,都说,听听,念得多好听”。④殊不知张仲银希冀村民们的反应不是“好听”,而是激发起他们的革命热情。 不甘认输的张仲银学毛主席的榜样搞起了戴红袖章活动。不但自己戴,而且给每个学生一人戴一个。可惜的是,“学生们纷纷把红卫兵袖章装进兜里,做了擦鼻涕的手绢。”于是“深深落空”的张仲银只好一再重复那句话“唉,全部没文化,没有共同语言”⑤,回到自己的自豪与孤独。 张仲银这种既自豪又落寞的情感结构是耐人寻味的。这表明他生活在知识分子与村民、革命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并置、冲撞和分裂中。革命的崇高伟业许给他“自豪”,但它和乡村的深刻隔阂又带给他“孤独”。他自然不愿孤独,可“自豪”又很不易(自豪感需要观众的呼应),于是就只好别扭地“自豪与孤独”着。不得已他就拿毛主席曾经借用的陆游词“已是黄昏独自愁”自况,把这句词写在纸上,挂在办公室墙上。可惜不但农民,就是大队支书赵万金,也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不仅不能理解仲银的革命理论,也完全不能理解这个革命家的那份孤独。 对群众极度失望的张仲银决定独善己身:停课闹革命,自己一个人出去参加大串联。谁知大队支书赵万金得知后,拿着村民们凑的五斤鸡蛋和十斤面粉(在当时的农村是真正的奢侈品,只有过年过节或女人坐月子的时候才吃一点)挽留他,于是发生了下面有趣的对话: 仲银说赵书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现在这不是请客吃饭么。我怎么能为了你这五斤鸡蛋十斤白面,就不革命,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呢。赵万金就又老练地笑了,赵万金说,看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一点鸡蛋白面和革命不革命有啥关系,要说呢,现在正要打倒当权派,仲银,你吃了这些鸡蛋白面,也误不了你打倒。其实呢,一个农村土干部,不打倒吧,哪一天不是在泥里土里滚呢。⑥ 赵万金和村民们不可能理解张仲银离开五人坪的原因是要去首都北京闹“革命”(这个动机处在村民的价值观和理解能力之外),还以为他是嫌农村穷(这才是乡村文化能够提供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村民的这个举动使他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到了无以倾诉的孤独”(连他离开五人坪的真正原因也不能够理解),于是干脆“闭上嘴什么话也不说了”。⑦但另一方面,象征五人坪古老乡村伦理的五斤鸡蛋十斤白面最后还是感动和挽留了张仲银(虽然他在理智上并不认同),阻断了他“走向天安门广场的道路”。这个戏剧性的情节表明:张仲银的精神世界仍然保留了前革命时期的乡村伦理(虽然并不纯粹),他并不是一个与乡村民间彻底决裂了的、纯粹的革命知识分子。在五人坪村民的鸡蛋白面与张仲银小时候“母亲的鸡蛋”之间,存在有意味的关联性。这大概就是张仲银和北京知青刘平平、李京生等人(张仲银称之为永远不知道农民需要什么、最终要离开五人坪的“大雁”)的区别:与北京知青不同,张仲银的根还是在民间。无论是在“文革”时期还是后“文革”时期,张仲银都属于五人坪而不是北京。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张仲银只好通过把自己打成“反革命”的荒唐方式发动了一次闹剧式的“革命”:给县里写匿名信,撒谎说自己从事反革命迷信活动,引得县公安局的老张来抓他。在张仲银看来,“他和老张的这场游戏”是“让旋风重新旋转起来的唯一力量”。⑧“革命”的风暴终于刮起来了,被打成“反革命”的张仲银终于被公安局的老张抓走。 这有点像张仲银对革命、革命烈士的意淫,更是自己对自己的意淫:想象自己像一个慷慨激昂、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充满自豪感,带着“居高临下”的眼光走向刑场(之所以说这是张仲银自己对自己的“意淫”,是因为无论革命组织还是村民群众,没有任何人理解他这烈士般的“自豪感”)。张仲银的“革命”举动至此真的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可以理解为李锐对“文革”时期革命知青理想主义的讽刺?)。当然,连意淫的幻觉也一个接一个破灭,进监狱以后再也没有人理睬这个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家。于是,他盼望公审大会,不停地询问“什么时候开我的公审大会”,希望借此又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因为开公审大会是“全县轰动的大事”,那时候“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人们的眼睛全都盯着我的公审大会”。⑨可惜这个公审大会始终没有开。张仲银接着意淫的企图没能实现。他被不明不白地关了八年。没有任何意义,没有获得任何人的理解(从村里唯一的共产党员赵万金,到后来的队长荞麦,再到深爱他的荷花),虽然所有人都替他鸣不平。原来意淫自己也这么难,真是天可怜见。 二 革命和反革命的倒转 《万里无云》开篇就是村妇荷花的独白。时过境迁,时间已经进入所谓“新时期”⑩,张仲银和当初那个热恋他、却根本不理解他的荷花也都老了。如今荷花对他痴情依旧,但隔阂也依旧,他们仍然无法相互理解。革命过后,五人坪的村民们还是那么愚昧,那么封建,他们正在举全村之力大搞祈雨活动,而主持和负责这场封建迷信运动的,正是张仲银当年的学生、现在的队长赵荞麦,以及另一个学生高卫东(绰号“臭蛋”,扮演祈雨的道士),而原来作为教室的庙,则被腾出来搞祈雨仪式。如果说《北京有个金太阳》中象征民间迷信的庙被用作教室象征着革命对于民间的胜利,那么,如今庙碑腾出来祈雨则暗示了革命的彻底失败。因此,到了后革命的所谓“新时期”,我们发现革命却原来几乎没有动民间迷信的一根毫毛,后者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这既是革命的失败,也是启蒙的失败(革命和启蒙都主张破除迷信)。张仲银这个最反对迷信的人,当初因被自己诬为搞“迷信活动”而锒铛入狱,而今天大搞迷信活动的正是他教育出来的那帮学生。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讽刺。 仲银对于这次迷信活动好像不置可否,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怀着自己的小算盘(祈雨结束后队长荞麦答应盖一个新校舍)参与了这次活动。当然,仲银内心还是不认同迷信活动的,还是满嘴毛主席诗词或语录,只是在这个既倒退(大张旗鼓地搞迷信活动)又进步了(不唱《北京有个金太阳》而改唱《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五人坪,他更孤独了,村干部和村民虽然还貌似一如既往地尊重他,甚至还怕他(队长荞麦和假道士高卫东都如此),但他们更不理解张仲银了。仲银成为没有任何用处、到处闲逛的、彻头彻尾的多余人(所谓“人影子”)。 在《北京有个金太阳》描写的毛泽东时代,张仲银虽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一心热衷革命却被无情戏弄,但还不完全是一个“人影子”,在一个既没有流行歌曲,也没有商品经济的革命时代,借助革命运动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威力,他至少还能让学生围着自己唱革命歌曲(虽然听不懂歌词);而实在不能发动革命的时候,他还可以通过闹剧的方式搞革命,拿自己开刀,把自己弄进监狱,大到意淫革命的目的;而今,革命者张仲银连把自己打成反革命、弄进监狱的力量也没有了(试想一下《万里无云》中的张仲银如果再来一次“自我揭发”会有什么人理睬他)。失去了任何威力和作用之后,张仲银熟悉的革命文化(以毛泽东诗词为象征)一转身已经成为笑料,成为中国式后现代文化的戏谑、戏仿的对象,而且戏仿者还只能是张仲银这个当年的狂热革命者本人,别人连戏仿和调侃革命的兴趣都没有。小说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或许就是张仲银“为人民喝酒”的那一段: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仲银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张仲银同志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为五人坪的人民群众喝酒,为五人坪的子孙后代喝酒,就比泰山还重。张仲银烈士永垂不朽!吕梁英烈,教师楷模。人民的好儿子。团中央委员邢燕子,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11) 这是张仲银在陪同队长赵荞麦和商人二梁一起喝酒(目的是让二梁出钱盖一个新学校,原来被学校占用的教室要恢复为庙)微醺时候的独白。这个十足的大话文本可谓小说的神来之笔。毛泽东(革命领袖)死了,“大雁”(北京知青)飞走了(回到了北京),只有张仲银坐了八年监狱后回到五人坪,无所事事,堕落到陪酒这般田地。心有不甘的他遂拿毛泽东的革命宏文为自己荒废的青春祭奠。拿自己心目中曾经的中国式“圣经”如此这般开涮,大概也就酒酣之际才敢吧(酒后吐真言?)。此时此刻的张仲银心潮澎湃,五味杂成,百感交集。想起了自己闹剧式的革命生涯,莫名其妙的八年牢狱;想起北京知青都走了,只有自己还在五人坪:“黄鹤(北京知青——引注)都飞走了,都飞回北京去了。毛主席死了,北京落满了黄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现在落满了黄鹤。就剩下我一个人在五人坪。”(《万里无云》,第48页)更想起了记载在一块冰冷石头上的五人坪历史: 是的,是的,我又回来了,在经历了两千九百二十个日日夜夜后,我又归于土地,我又归于石头,我又归于孩子们噼噼啪啪的无知无觉的踩踏。我无处可飞,无处可去,我只有“零落成泥碾作尘”,我只有变成石头和黄土。……我喝酒完全是为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12)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风起兮云飞扬,今有勇士兮赴铁窗。人民教师张仲银烈士永垂不朽!人民万岁!黄土万岁!石头万岁!吕梁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历史在此做出的不是重复,而是“天翻地覆慨而慷”!此时此刻,人民教师张仲银目视远方,昂首阔步,“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此时此刻,人民教师张仲银向黄土走去,向历史走去,向石头走去,向铁窗走去,走上刻骨铭心的纪念碑。(13) 毛泽东诗词,碑文,古诗词,革命口号,全被一锅煮。然这篇看似疯疯癫癫、热闹非凡的后现代绝妙好文,骨子里却透出一股子透彻的悲凉,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14) 更具有戏剧性的是,革命文化在后革命时代的五人坪不但被张仲银这个革命者自己拿来肆意调侃、戏谑,它还参与了“新时期”五人坪的这场“反革命”迷信盛典(前现代抑或中国式后现代?):假道士高卫东(臭蛋)身穿八卦道袍,装神弄鬼,背上背的却是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他的老师、人民教师张仲银则助之以大合唱《北京有个金太阳》,“戏台上的响器们就呜里哇啦地敲打起来。吹打的是《北京有个金太阳》。”(《万里无云》,第121页)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成为祈雨的法宝,反革命者的护身符,革命歌曲成为祈雨仪式的伴奏。这真是极大的讽刺:革命和迷信组成了亲密无间的联盟,革命其实就是反革命。 这个绝妙的闹剧同时也是残酷的真理:难道不是这样吗?“文革”时期的个人迷信难道不是把革命所要铲除的封建残渣余孽变本加厉地发扬光大了起来吗?假如我们把现代革命的理念定义为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那么,窃取了革命名义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骨子里就是一场最反革命的闹剧。这才是真正的讽刺。 在祈雨仪式中癫狂的五人坪,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进入所谓“新时期”,这就难怪毛泽东依然被奉为“神”,难怪有了毛泽东像这个护身符,道士臭蛋就显得如此理直气壮:“我一出去,我就得把这十里八乡的人全他妈的给镇住。我身上背着他(毛泽东——引注)呢,我就不信镇不住这些个老百姓。你们谁也不知道,我在半夜里就把他背到后背了。我只要把他背到身上我就没办不成的事情”,“有他保护我就没办不成的事情”(15)。 最后,《北京有个金太阳》中的革命狂热分子张仲银用疯狂的举动把自己送进了监狱,而《万里无云》中心灰意冷的张仲银因为参与迷信活动再一次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当张仲银因为用《辞海》帮助臭蛋解释“旱魃”一词而被指控参与迷信祈雨活动并引发山火,烧死两个孩子,再次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他没有醉,但却成了一个真正的疯子:“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只喝过一次酒。喝酒属于正常人的正常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公民不许喝酒。”(16) 依然是疯疯癫癫的调侃戏谑。当然,我说的调侃戏谑是一种客观的文体效果。在张仲银,这种“调侃”可能不是有意识的。张仲银是革命文化的畸形遗产,在后革命时代,他也没有任何促使他反思革命和自我反思的思想知识,也就是说,他并无革命文化之外的资源去反思革命文化。因此,极度失望之后的他,大概也就只能这样拿革命话语和革命话语自己玩了。 三 张仲银的孤独是启蒙者的悲剧吗? 如上所述,张仲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非常罕见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既不是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如《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也不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启蒙知识分子(如《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更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从情感角度划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革命知识分子(特指无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下同)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之一,是前者有知识但并不孤独。至少在真正成为革命者的那一刻,他已化身群众,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彻底融入了集体主义,因此是不存在孤独的。孤独以及自以为是的骄傲(不同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自豪),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情感,是革命者必须加以彻底铲除的幼稚病,铲除之后方能成为革命知识分子(林道静等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知识分子乃至革命英雄的道路,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独、孤芳自赏,根本缘于他还不革命或者还不够革命,因此瞧不起人民群众,不能融入革命洪流,把“小我”变成“大我”。(17)一旦革命了,这个原先孤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也就不再孤独了。他的“小我”升华为“大我”,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了,还怎么可能孤独呢? 但张仲银的情况却有些特殊。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他有文化,是村里唯一一个大学生、中学教师,当然属于知识分子。同时他又积极革命,满嘴毛主席诗词,口口声声要在五人坪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典型的革命知识分子。但与文学史上革命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同,张仲银这个村里唯一的文化人却既革命又孤独,既豪情满怀又寂寞难耐。“自豪又孤独”是他到了五人坪后最强烈的双重感受。 显然,不能把张仲银和乡亲们的隔阂简单理解为农民和文化人的隔阂,理解为农民没有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张仲银每次发出“都没有文化,没有共同语言”的感叹都是在他的革命宣传失败之时,而不是传授知识遇阻的时候。这是颇堪玩味的,因为这些农民虽然没有文化却极度尊重和崇拜文化人(他们为了挽留他不惜拿出最最珍贵的鸡蛋和面粉)。也就是说,张仲银的孤独与其说是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的革命。越革命越孤独。村民们欣赏他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但对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行为却始终不能理解,遑论积极响应。于是,由于革命和群众的隔阂,革命知识分子也有了孤独问题。 那么,张仲银的孤独是源于启蒙吗?张仲银的孤独是启蒙知识分子的孤独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回答:到底什么是启蒙?张仲银是不是启蒙者?由于作者李锐自己和不少评论家都认定《万里无云》表现的就是启蒙和启蒙者的悲剧,张仲银的孤独就是启蒙者的孤独,因此,这个问题应该在这里重点加以讨论。 李锐的一篇题为《毁灭之痛》的文章提供了他自己对于张仲银形象的解释。李锐说:“《无风之树》写的是巨人和矮人之间发生的悲剧,《万里无云》写的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悲剧。带着知识和真理来到穷乡僻壤的小学教师张仲银,是一个忘我献身的启蒙者,那只金光闪闪的铃铛在地老天荒之中发出的是真理的召唤。可神圣最终导致的是彻底的悲剧。这样的故事和悲剧不止发生在中国,不止发生在以前,它们在人类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它们就发生在此时此刻,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张仲银是以古往今来一切读书人的身份自居的人,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启蒙者。”(18) 可见,李锐明确把张仲银定位为“神圣真理”(作者没有对“神圣真理”这个术语做具体界定)的“启蒙者”,把张仲银的悲剧看作一个启蒙者的悲剧,甚至是“一个古往今来的启蒙者”的悲剧,“一切读书人”的悲剧。他的失败源于群众的愚昧无知。同时,由于张仲银还是“文革”的热心鼓吹者,李锐实际上也把“文革”悲剧“提升”为启蒙悲剧。这貌似提升了小说主题的哲学高度和普遍意义,实际上却失去了对具体中国问题的判断力。 我以为,李锐创作的张仲银形象是深刻而有丰富含义的,但他对于这个形象的上述解释却是似是而非的。他并不了解自己创造的这个形象。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把狂热、盲目地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张仲银当作了启蒙知识分子,把“文革”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成了启蒙“真理”,最后则是合乎逻辑地把“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把“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响应者(包括张仲银,也包括类似张仲银的一代知青)的悲剧,当成了启蒙和启蒙者的悲剧。 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启蒙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两者基本上是重合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标志是受到现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崇尚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人民主权等文化价值与政治理念。在现代中国作家的笔下,这些人常常与大众之间存在深刻隔阂,不能得到大众的理解,因此是孤独的。(19)但张仲银显然不是启蒙知识分子,他的孤独不但不是因为他的知识,更不是因为他怀抱什么启蒙理想而不能实现。无论是在《北京有个金太阳》中,还是在《万里无云》中,张仲银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也不是因为这些思想意识得不到村民和学生的理解而感到孤独(参见上文)。 李锐创造了张仲银,却不理解张仲银。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文学理论问题。 遗憾的是,这个似是而非的“启蒙者悲剧”说被很多人重复,以至于批评界一致把张仲银的悲剧理解为启蒙者的悲剧,把这部小说的主题理解为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反思。比如王德威说:“《万里无云》最值得注意的,是李锐对于启蒙理念及教育方法的省思”(20),“‘启蒙’(enlightenment)是中国现代化的要项之一:自清末以来,开发民智一直是革命论述的重点,而以普及教育为首要之务。”(21)在这里,“启蒙”、“革命”、“现代化”以及“普及教育”这几个现代性的关键词连成一串,它们在王德威的笔下即使不是同义的,至少也是同类的。至于它们在中国现代史语境中发生的微妙语义变化则被忽视。更有进者,王德威一方面指出了张仲银与毛泽东之间的精神联系(他说“张仲银独白的部分大量援引毛泽东诗词,革命口号及政党文学,他俨然成了‘毛语’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却又把他联系于“五四”以降通过教育与知识救国的启蒙话语系谱和启蒙者形象(从鲁迅到叶绍钧),仿佛张仲银的悲剧就是鲁迅等的悲剧。(22) 不得不指出,这种解读是对《北京有个金太阳》《万里无云》所塑造的张仲银形象的严重误读。张仲银怎么可能是一个“五四”反封建式的启蒙者?他的那套拷贝了毛语录的所谓“革命”理论,与以民主、自由和个人解放为诉求的启蒙话语有什么联系?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不能因为张仲银有知识有文化从事教育鼓吹革命,就认定他是启蒙者,“启蒙”这个词除了有传授知识和普及教育之外,更有一层内涵是秉持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理念,而张仲银信奉的恰恰是反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文革”版革命理论,他的那点文化全部被用来传达中央文件和毛主席指示,写大字报,从来没有向乡亲们或学生们灌输过一丁点儿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的确,同样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思想,但“文革”时期的革命理论却完全走向了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反面,越来越回归到中国式的封建专制文化。“五四”反封建的启蒙者,无论是鲁迅还是叶绍钧或他们笔下的知识分子,以及柔石笔下的萧涧秋,都是信奉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张仲银不是。一个狂热的革命分子高喊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到了一个穷乡僻壤不择手段地发动群众搞革命,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和“启蒙”挨得上边吗? 当然,张仲银的知识结构中除了意识形态话语、毛泽东诗词(也是意识形态话语的一部分),还有传统诗词。举一个知识上的小例子,张仲银知道司马迁和陆游。但他知道的司马迁只是毛泽东文章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司马迁,他不了解像他一样困厄过但最终奋发独自撰史并在史书中“粪土万户侯”的司马迁。所以,张仲银喝大了的时候想到的“重于泰山”的死,自然是“人民勤务员张思德”的死,而非司马迁的死,更不可能是遇罗克、张志新等民主人士的死。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解读《万里无云》《北京有个金太阳》中的张仲银形象,那么,他的悲剧只能说是在中国非常具体特殊的语境中发生的现代性悲剧,是违背了启蒙承诺的那个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姑且借用汪晖的术语)的悲剧,而不是什么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悲剧,更不是启蒙现代性的悲剧。如果把“文革”悲剧泛化为现代性的悲剧,把张仲银的悲剧泛化为启蒙者的悲剧,那么其结论必然是:启蒙和现代性本身导致了张仲银及其置身的五人坪的悲剧。这样的思考路径不仅不能诊断和解决中国具体的现代性问题,而且必然导致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既然现代性本身不可救药,那么,除了倒退到前现代(这个出路显然被李锐否定),剩下的就只能是绝望和悲叹。而如果张仲银的悲剧不是什么启蒙者的悲剧,更不是现代性的悲剧,而恰恰是违背了启蒙的中国式“现代性”的悲剧(李锐的小说客观上写出了这点,但李锐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而且误解了这点),那么,为了避免张仲银式的悲剧(同时也是中国式的所谓“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悲剧)的再次发生,就只能进一步地启蒙。 四 革命和启蒙的合与分 到这里为止,本文一直是在对立意义上使用“启蒙”与“革命”、“启蒙知识分子”与“革命知识分子”这两个术语的。其实,这只是为了权且沿用建国后的惯例。这两个二十世纪出现频率最高的所谓“超级能指”的恩恩怨怨,实在有一个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从晚清到“五四”,传统知识分子大致分化为新式的或具有革命倾向的,与旧式的、具有保守倾向的两种。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具有启蒙思想,他们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接受了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崇尚民主、自由、个性解放。革命与启蒙本是同根生,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和苏联革命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革命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一类信仰马克思主义且大多加入了共产党,可称为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另一类则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可称为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其实都是革命党(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赞成革命),两类知识分子也都是革命的。但随着国共两党的逐步分化、对抗以及共产党政权的确立,“革命”这个术语在大陆基本上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比如俄国苏维埃领导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同义词,“革命知识分子”也逐渐变得专指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而仍然坚持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则基本上被划入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畴,或者不够革命或者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来,在建国后的革命话语系统中,革命就和启蒙、革命知识分子与启蒙知识分子开始分道扬镳。 也就是说,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逐步走向激进化,也逐渐偏离了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启蒙内涵,把后者当成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并改变了对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把他们从原先的联合对象、统战对象,一股脑儿打成“反革命分子”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23)到了极“左”的“文革”时期,中国的革命理论更是完全走向了对启蒙的否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早已臭不可闻,民主或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玩意,或被等同于群众专制)。在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是反启蒙的封建文化的大复辟不是没有道理。 人们一般只在形式意义上把革命理解为通过暴力进行的激进社会变革——常常涉及政权更替、道德重建、社会乃至人性重造。但这种形式上的激进变革如果从实质意义上加以分析,则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一套真正现代的新制度和新价值取代旧制度和旧价值,以人民主权的国家取代君主专制的国家,以自由民主取代极权专制,以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体性取代从属人格(这种革命甚至可以通过非暴力形式进行,比如东欧国家在1980年代末的和平革命);另一种是在激进形式表象之下换汤不换药,甚至在“革命”名义下导致旧制度和旧习俗的大复辟(参见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和农民起义(陈胜吴广的“彼可取而代之”)就属于这种“革命”。 “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向往的那种革命就是以自由民主、人民主权和个性解放为核心的革命,它与启蒙原本就并不矛盾,它就是以启蒙为先导的(参见上文)。这个意义上的启蒙者与革命者的角色原本也不背离。启蒙和革命的目的都是反专制,争取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以人民主权的国家取代君主专制的国家。但“文革”时期那种红卫兵造反式的所谓“革命”,恰恰是对民主自由、个人权利、人民主权的践踏,是对启蒙观念的背离,因此,只有这种败坏了的“革命”才是与启蒙为敌的,才是启蒙的对立面。 《北京有个金太阳》中张仲银狂热向往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了启蒙价值和理念的败坏的革命,这个革命的结果当然是除了闹剧般地把张仲银自己搞进监狱外一无所获。五人坪的农民们不但依旧愚昧,甚至更加愚昧。正因如此,《万里无云》中描写的五人坪虽然在新时期唱起了流行歌曲,但是骨子里依然故我——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被启蒙。这样,祈雨闹剧,作为一种典型的蒙昧迷信,上演于被反启蒙的“文革”式革命洗劫的五人坪,也就不必奇怪。王德威教授不明白这个道理,结果是把祈雨酿成的火灾惨剧(夺去两个花样男女孩童的生命),归结为笼统的启蒙或革命之罪,以至于发出“多少代的孩子被革命行动、启蒙话语‘救’得面目全非?”的似是而非之问。(24) 无论是《北京有个金太阳》中的张仲银,《万里无云》中的张仲银,还是“文革”时期的知青,他们都不是启蒙意义上的革命者,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革命者。他们钟情的所谓“革命事业”就是“文革”式群众专制,他们献身的教育事业也不是倡导民主自由理念的启蒙教育,而是为了培养“阶级斗争急先锋”。张仲银确实反复说五人坪的农民是“榆木脑袋”,但他想要做的与其说是“开发民智”(其实“开发民智”的意思不仅是识字画画,而且更重要的是进行现代公民教育),不如说是号召他们起来搞“阶级斗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张仲银的革命当然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马克思心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和超越,它发生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自由民主等启蒙价值的更加彻底的实现。马克思从来没有简单否定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成果,更不简单否定自由民主的启蒙理想。他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就是每个人的自由的彻底实现。当然,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理想的社会制度,也不认为自由民主等价值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实现,这是他所以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但是这当然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反对自由民主等价值理想。 但李锐似乎不能清理革命和启蒙的这些复杂关系,也不能区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革命。李锐显然把“文革”时期的红卫兵造反也都看成了革命,正如他把它们都看成了启蒙。进一步的结果就是把知青、红卫兵、张仲银之类“革命者”的悲剧,混同于一般革命者的悲剧,而忘记了其实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即“五四”时期以自由民主、人民主权、个性解放为根本诉求的革命。 把张仲银(以及“文革”)的革命悲剧混同于“现代”“真理”“信仰”“启蒙”或者“现代性”的悲剧,表面看使得李锐的反思获得了超越性的普遍意义,实则是使这种反思最后走向神秘主义与虚无主义,或大而无当的反文明、反现代立场。这些都会导致一种貌似的深刻。把知青和红卫兵的理想主义的幻灭普遍化为整个现代性或现代启蒙理想的幻灭,源于作者不能对中国革命悲剧的特殊性进行具体分析,而是动辄上升到“启蒙悲剧”“文明悲剧”“现代悲剧”的所谓“高度”。 同样是在那篇《毁灭之痛》中,李锐谈道: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无风之树》,而最喜欢的小说人物是张仲银。(25)关于张仲银和作者自己的关系,他坦言:“张仲银就是我。张仲银的时代就是我的时代。张仲银经历的所有激情、坎坷、献身和幻灭,就是我的经历。张仲银的精神史就是我的精神史。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不幸,我的张仲银经历了两次心死。……成就了他和埋葬了他的,都是他以为可以启蒙的大众。”(26) 这段话道出了张仲银和作者李锐本人(考虑到李锐的插队经历,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与李锐年龄相仿的一代知青)的血脉联系。(27)张仲银这个形象大体上表现了作者对知青的理解,也融入了自己对知青的复杂感情。对这个形象,李锐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既不乏揶揄和批评,也不乏同情,他塑造的张仲银可笑可悲也可叹甚至可爱(“毁灭之痛”这个标题就颇值得玩味)。 对知青和“文革”的反思与批判在李锐的小说和创作谈中比比皆是(正是因为这样才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李锐在不同的文章中多次指责“文革”经历者(当然也包括知青)不反省自己当年的信念和狂热,总自以为自己是单纯的受害者;但作者同时又一再把张仲银解释为“忘我献身的启蒙者”,一再为张仲银的孤独和不被理解一掬同情之泪。这一切导致了作者对张仲银这个人物——实际上也是对知青运动、对上山下乡,甚至对“文革”——的暧昧态度。这种暧昧态度甚至使得李锐的《北京有个金太阳》《万里无云》以及其他很多散文、随笔和创作谈等等,成为分裂的书写。请看下面这段话: 在我的故事里,在贫瘠苍凉的吕梁山上,自然和人之间千百年来的相互剥夺和相互赠予,给人生和历史留下了一幅近乎永恒的画面……如今,来启蒙的巨人们,带着他们的真理和信仰,带着他们的革命和暴力,带着他们的激情和冷酷,闯进这个千载悠悠的画面,以革命、进步和现代的名义,他们打破了什么?当他们的信仰在历史的风雨中剥蚀殆尽,最终随着漫漫黄土一起流失而去的时候,这个悲剧又留下了什么?我们可以期盼它终有一天会和千百年来所有逝去的生命一起,在一个非人所料的去处沉淀出一片广阔的沃土来吗?为了免于再次的幻灭,我宁可不信。 为了这遥远到目不可及的期盼,为了这不信,我写下了自己的悲剧,在苍凉的黄土高原上留下依稀而无人听到的歌哭。(28) 这里说的“来启蒙的巨人们”显然喻指当初满怀理想来“广阔天地”闹革命的知青,包括张仲银,也包括《无风之树》中的青年革命者苦根儿。(29)李锐的这段肺腑之言充满了明显的言说困难,它充分表明李锐的“文革”书写或知青书写是一次自我拆台的(既是理想又是悲剧)、分裂的书写。但这分裂又是似是而非的,因为李锐把反启蒙的中国式悲剧简单地当成启蒙悲剧加以祭奠,把热心“文革”的革命青年张仲银等同于一个热心传播知识和鼓吹自由民主的启蒙知识分子。这样一来,李锐当然也就不可能找到克服、治疗和超越张仲银革命病和革命悲剧的正确道路,陷入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 注释: ①⑤⑥⑦⑧⑨(18)(25)(26)李锐:《北京有个金太阳》(初刊《收获》1993年第2期),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8、21、26、192、189、189页。 ②这和在知识分子内部搞革命不同,后者恰恰要对自己的原有知识进行革命。实际上中国革命领袖们一直致力于处理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让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民接受革命教育积极参与革命。他们的方法是在形式上把革命理论通俗化、大众化,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要突出革命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后者才是民间话语能够理解的。只有当革命理论转化为老百姓的生活哲学时,革命动员才是有效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革命理论通俗化、大众化的杰作。对老百姓而言,分田地是打土豪的动力,只有能够分到田地,打土豪才有吸引力。这个通俗化、大众化了的革命理论,或许就是西方革命理论的中国化吧。 ③“自豪”是1950—1970年代最常见的抒情词汇之一,是那个时代所形塑“情感结构”(威廉斯语)的——一个空洞的、被滥用的、也轻而易举产生认同奇效的词语。 ④《北京有个金太阳》,第5页。革命者与村民的这种隔阂在李锐的其他小说中也多有表现。比如在《古老峪》中,那个到偏僻古老峪宣读文件、鼓动革命的工作队员小李也是一位文化人。在小李给社员们念文件的时候,队长女儿深情地一直盯着他看,致使他以为对方是被自己宣扬的革命理论迷倒,可以当“古老峪的先进”;殊不知她的回答却是:“我啥也听不懂,我是看你念得好看。”原来如此!于是小李心里“不由得升起一阵悲哀来”。(李锐《厚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⑩准确说是1990年代,因为小说中这样一句:“17年前已经没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里无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11)(12)(13)(16)(28)李锐:《万里无云》,第50、53、63、150、193~194页。 (14)《万里无云》和李锐的其他小说一样充满了虚无主义思想。除了上面的细节,小说还写到五人坪的村民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悲剧命运的原因,全部陷入宿命论、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村里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赵荞麦的父亲赵万觉得老师没有用,党员也没有用,“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共产党员,革了一辈子命,革得自己也快进坟地了还能有他妈的什么用呀,啊?不管你有多大的学问,要是叫你狗日的也住上八年的大狱,你能不能活着出来都难说,你照样也得像他一样,变成个人影子晃过来晃过去的啥事也没有干的。”“种庄稼的白了头,第一个共产党员白了头,最有学问的白了头,当老师的也白了头,全他X的白了头。”(《万里无云》,第17页)而这种虚无主义的根源之一,在于作者把“文革”式革命的悲剧混同于启蒙的悲剧,把知青的悲剧混同于启蒙者的悲剧,把对中国式现代性的反思混同于一般现代性反思,从而表现出对整个启蒙和现代性规划的悲观绝望。这点本文最后一部分还有更为详细的分析。 (15)《北京有个金太阳》,第120页。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个注脚:张弦短篇小说《记忆》(《人民文学》1979年第3期)主人公秦慕平感叹:“革命发展到今天,怎么会出现‘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以致一张刊登领袖照片的报纸,也要视为圣物、顶礼膜拜的这种只有封建社会才有的怪事呢?” (17)“文革”时期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叫《创伤》,塑造了一个孤独无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诗人形象,他不能融入劳动大众,一天到晚只会吟诵“快乐的小松树啊,大雪染白了你的睫毛”此类文绉绉的诗句,影片对他极尽讽刺挖苦。 (19)这种隔阂和孤独在崇尚启蒙的八十年代被表述为“文明和野蛮的冲突”,古华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 (20)(21)(22)(24)王德威:《吕梁山色有无间》,《北京有个金太阳》,第222、222、224、226页。 (23)方之的获奖短篇小说《内奸》(《北京文艺》1979年第3期)就是表现这个主题的。 (27)李锐1969年1月到山西的吕梁山插队,一共在那里待了6年。 (29)王德威早就看到了这点:“他的造型在让我们想起《无风之树》中的苦根儿,他们是亢奋的理想主义者,不自觉的‘少年法西斯’。但李锐对张仲银怀有深情,想必在这个角色里,看出他同代人(以及他自己?)的虚荣与挫折、天真与毁灭。”参见王德威《吕梁山色有无间》,《北京有个金太阳》,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