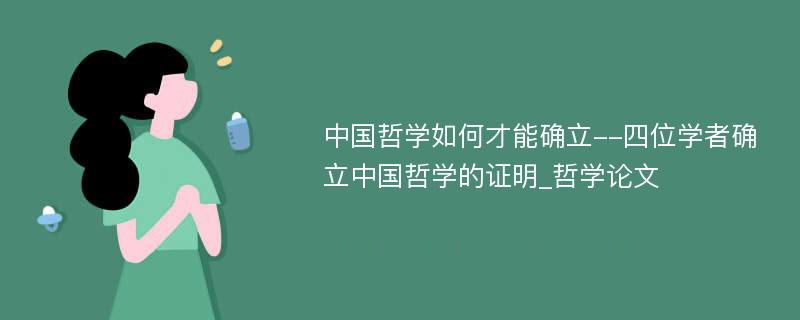
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四位学者对中国哲学成立的证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四位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Science), 科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这已成为国内学界所公认的一个定论,尽管为了挽回中国人在这方面的一点面子,梁启超曾言之凿凿地论证《墨子》中也体现着西方科学的原则(注: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的《墨子学案》中。);黄遵宪更是煞有介事地说西方科学(格致)源于《墨子》,其传入中国无非是“回娘家”(注:他说:“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经下篇。当孟子时天下之言半归于墨而其教衍而为七,门人邓陵,禽滑之徒,且蔓延于天下,其人于泰西源流虽不可考,而泰西之贤智推衍其说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教者十居其七。距之辟之于二千余岁之前,逮今而骎骎有东来之意。呜呼,何其奇也。”参见黄遵宪《日本国志》三十二卷,光绪十六年羊城富文斋刊刻版(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而胡适则打圆场说,中国没有科学内容是真的,但中国却有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发端于由孔子创导的“自由问答,自由讨论,独立思想,怀疑,热心而冷静的求知”的儒家学风,并绵延流布,到明清的考据学遂发扬光大(注:参见胡适 The Right to Doubt
i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载第三届“东西哲学家会议”论文集Philosophy and Culture——East and West,夏威夷大学1962年版。 )。然而,诸如此类的明显带有“爱族主义”倾向的言论充其量也只能给国人带来虚幻的满足感,这种虚幻的满足感毕竟无法迷住我们的心窍而睁眼不看铁板钉钉的事实,于是,我们便转而讨论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文明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李约瑟问题”(注:李约瑟问题的精确表述是:“中国古代科技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近代科学却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八十年代以来,有如此之多的人热衷于探讨这个问题以致于约定俗成地形成了一门可以称之为“李约瑟问题学”的新学科。
中国文明没有发展出科学,那么中国文明有没有发展出哲学呢?或者说,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有没有哲学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也许一些人会觉得可笑而不屑一顾,因为“中国哲学”(或称“中国哲学史”)早已成了我国大学课程表中的“常客”,而且这门学科也早就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了。就是国外的大学,有的也早就开有“中国哲学”课,更不用说众多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论著了。然而,这一切只能说明中国哲学在学科上的成立,而不能说明中国哲学在学理上的成立。而我们所要关心的却是中国哲学在学理上能否成立。
“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本是个西方术语,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有“哲”字也有“学”字(注:“哲”字如:《尚书·皋陶谟》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至于“学”字,那就俯拾皆是了,此不赘举。),却没有连起来的“哲学”一词。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Nishiamane)(注:西周,1829—1897,日本近代哲学的渊源,他在移植西方哲学于日本方面贡献很大,特别是在汉译西方哲学术语上有开创性的贡献。他除了首先将Philosophy译成“哲学”外,像主观、客观、理性、悟性、现象、实在、演译、归纳等术语也都是他苦心精译的。)首先将Philosophy译成汉语“哲学”,后来黄遵宪将“哲学”一词介绍到了中国”(注:黄遵宪曾出任驻日使馆参赞。任间他除外交公务外,还属意考察和研究日本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撰成我国第一部综合介绍日本的巨著,名曰《日本国志》。《日本国志》是以史志体裁写成的,分十二志: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共四十卷,五十万字。在其中的《学术志》中,黄遵宪介绍了东京大学的学科设置情况,其中谈到了哲学。“有东京大学,分法学、理学、文学三学部。法学专习法律,并及公法;理学分为五科:一化学科,二数学、物理学及星学科,三生物学科,四工学科,五地质学科及采矿学科;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中国学界才渐渐地接受并使用上了“哲学”一词。
西方人把他们中一些人的思想,比如柏拉图的思想或海德格尔的思想,称为“哲学”,这在他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就像给人起名字,他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哲学”也可以,叫别的什么也无妨。第一次命名总是有完全的主动权的。然而,当我们把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人的思想比如孔子的思想或朱熹的思想等,也称为“哲学”的时候,那就有个是否“名正言顺”的问题了,那就有个“中国哲学”这四个字的意义能否成立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现在所指称的“中国哲学”,不管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与西方哲学的差别都非常大,两者甚至完全相反。两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的事物怎么可以统一在一个名称下呢?这表面上看来是个简单的“名分”问题,但它所暴露出来的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文化中到底有没有哲学?
发此一问既不是杞人忧天,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西方学界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眼障下,一直有人在嘟嘟嚷嚷,认为中国是没有什么哲学的。比如,已故美国汉学家莱特(A.F.Wright)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没有哲学。 所谓的‘中国哲学’, 只是一种思想(或思潮)thought,介于古俗因袭惯例与严谨逻辑分析之间”(注:莱特, 1912—1989,原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他的这一论点参见H.G.Creel,ed.,Chinese Civilization in LiberaI Educ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141.David S.Nivison 也有类似的看法,同上书,P144,135,154,159。)。另有一些人,比如黑格尔,则认为中国哲学是肤浅的、不合格的(注: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依次以孔子、《易经》、《尚书》、老子、孟子为例,把中国哲学贬了一通,认为中国哲学是粗糙而肤浅的,在整个哲学史中不值一提。比如他谈到孔子时说:孔子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这并没有错),但却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因为中国哲学缺少抽象和逻辑。
对于国内学界而言,“中国有没有哲学”是一个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如鲠在喉的问题。本世纪初(甚至可推到上世纪末),随着西方哲学思潮的大量涌入,国内学者便纷纷以“哲学”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中国古已有之的思想学说,参照西方哲学的范式来重新整理传统思想,或者说得形象点,就用哲学之“新瓶”来装传统思想之“旧酒”。这就是所谓的“国故新知”。这些前辈们或者专门写文章讨论“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的问题,或者在写作中国哲学史时,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就讨论哲学是什么,中国传统思想中哪些东西可以当得“哲学”之名,或者证明哲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只是没这个名称而已。总之在“正传”之前都要先为中国哲学正名,先使“中国哲学”这四个字能成立,这样做显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毕竟中国是从来没有过什么“哲学”的,现在突然冒出个“中国哲学”,读者就会感到奇怪,就会向你质询,哪来个“半路程咬金”,因此先作个交待,埋个伏笔,先让人相信中国确有哲学,然后再让你看中国哲学的具体内容,这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力图论证中国哲学成立,力图“扶正”中国哲学的小心谨慎的学术习惯,今天的学界已不多见,但我们切不可忘记,我们的前辈们在这方面是费了不少心思的。本论文试举四个著名学者对中国哲学成立的论证。
二、胡适的“哲学问题”论证
这种论证的大致思路是:先阐明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再看看中国传统学术中是否也是在致力于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果中国传统学术中有那么一些人或一些学派确是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哲学就是确切无疑的了。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一篇“导言”中就用这种方法,非常巧妙地论证了中国哲学之成立。我之所以说他巧妙,是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地阐述哲学在中国古已有之,而是通过分析一个具体的例子——“善恶问题”——来让读者自己从中去得出中国古代确有哲学的结论,这是一种文学的说理方法(体现了胡适的文学家风采),亲切易懂,读者很容易接受并能自行地将具体结论普遍化。我们不妨来具体看一下胡适的做法。
胡适首先开门见山地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曰:
“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3 月版,第1页)。
这就是说,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生切要问题”,那么什么是“人生切要问题”呢?胡适马上接着说:
例如行为的善恶,乃是人生一个切要问题。平常人对着这问题,或劝人行善去恶,或实行赏善罚恶,这都算不得根本的解决。哲学家遇着这问题,便去研究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人的善恶还是天生的呢,还是学得来的呢;我们何以能知道善恶的分别,还是生来有这种观念,还是从阅历经验上学得来的呢;善何以当为,恶何以不当为;还是因为善事有利所以当为,恶事有害所以不当为呢;还是只论善恶,不论利害呢;这些都是善恶问题的根本方面。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想,方可希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同上)
在胡适看来,善恶问题就是一个“人生切要问题”,因此对善恶问题的解决就是哲学。那么中国传统学术中有没有解决过善恶问题呢?稍有中国古典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显然是有的,胡适及时地替大家作了回答:
例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荀子说性是恶的。到了后世,又有人说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说性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同上书,第2页)
这段引文中提到的孟子告子等人都曾致力于回答善恶这个“人生切要问题”,根据胡适的哲学定义,他们不消说都是在作哲学工作的。另外,胡适在行文中间还有意列举了六个“人生切要问题”及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所形成的相应的哲学门类:
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同上书,第1—2页)
这张清单中的这六个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显然都是十分突出的,既然如此,中国哲学之成立乃是毫无疑问的事。
香港中文大学的劳思光教授在其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台湾三民书局,1981年出版)中虽然一方面批评了胡适所著的哲学史不能算是一部合格的哲学史,只能算是“诸子杂考一类的考证之作”而已,但另一方面他又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胡适对中国哲学的“问题论证”法。他在这部哲学史的序言中明确地指出必须以“哲学问题”为线索来建构一部中国哲学史。他认为对每一个哲学问题的解决都会产生一个哲学观念。他的这部哲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哲学的“问题——观念”史。他的哲学史与胡适哲学史的差别在于,胡适着重于探讨中国哲学中的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也就是某个哲学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或者说,胡适所关心的是得出哲学结论的过程,而不太关心结论本身(注:这里体现了胡适对学术方法的重视。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说:“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胡适所谓的方法乃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的承袭。胡适自己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的了解,[这些传统的治学方法]我把它们英译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证据的探讨),也就是根据证据的探讨,[无证不信]。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参见《胡适自传》)可见胡适在写中国哲学史时重视中国哲学家得出结论的过程乃是他重视方法的一个反映,他的博士论文所探讨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的方法,它的原题为“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胡适自己将其译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现在我们习惯于将其译作《先秦名学史》,这是不太符合胡适原意的。这篇博士论文乃是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一个方法上的准备,两书具有极大的亲缘性。);而劳思光则正好相反,他不关心过程而只关心结论,即关心哲学问题被解决后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他在书中所论述的各种各样的观念。胡适因为要弄清楚得出结论的过程,所以不厌其烦地去考证。劳思光没有看出胡适考证的真正用意,而将其等同于明清小学考据,是为谬矣。
三、冯友兰“内容相似”论证
这种论证是把西方哲学的内容立为参照,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寻找与西方哲学内容相似的内容,如果寻找到了这些内容,那么中国传统学问中也就有了哲学,中国哲学从而也就成立了。冯友兰在其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第一章结论中开宗明义地说: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4月版,第1页)
这种论证着重一个“选”字,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挑选出与西方哲学相似的内容,将这些内容组织起来,遂成中国哲学史。这种挑选工作看上去十分简单,却是一项精工细活,冯友兰整个一生的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做这种挑选工作,刘小枫曾以冯友兰的下面这段话为例来说明冯友兰在做这种挑选工作时的思维结构是“有似”:“理之观念有似于希腊哲学(如柏拉图,亚力士多德的哲学)中及近代哲学(如黑格尔的哲学)中底‘有’之观念。气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无’之观念。道体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变’之观念。大全之观念,有似于其中底‘绝对’之观念。”(冯友兰《新原道》,重庆商务版,1945年,第119页)
刘小枫指出,冯友兰的“有似论”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现代性焦虑;冯友兰构筑“有似论”的用心所在乃是要通过中西哲学的民族性比较来为中国哲学作现代性的辩护(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月出版,第161—162页)。很显然, 这种“辩护”实际上就是为中国哲学能够在现代性境域中得以成立作论证。冯友兰在作为他早期研究成果的《中国哲学史》中虽没有直接谈到“有似”的问题,但这本书以西方哲学内容为标准为中国哲学划定了一个内容范围,可以说此书中的“有似”是未形诸文字的隐性的“有似”,而且他以后进行“有似”建构时所用的素材并没有突破这个范围。
四、韦政通“哲学起源”论证
这种论证的基本思路是:所谓中国哲学,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不是从外族传进来的哲学。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哲学,那么这种哲学一定有自己的中国本土源头,如果能找到这种源头,那么中国哲学就自然成立了。韦政通认为任何哲学都有自己的文化源头的,中国哲学亦不例外。他说: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如果不确定其源头为何,那它就是一本“断头的中国哲学史”(韦政通《中国历代哲学思想简编》,载《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台湾水牛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71页)。他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来探寻中国哲学的源头(注:另外,他还从神话、周易、阴阳五行角度探寻过中国哲学的起源问题,并且都已成文。不过,他从宗教角度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最为用力、最为成功的。),他认为宗教中总是孕育着哲学,凡是宗教,它最终都要在人类理性的催生下分娩出哲学,他说:
我们几乎可以直接断定,宗教和哲学是出于一个来源:宗教开始的时候,哲学的种子就已孕育于其中;后来由于人类在罪恶的累积中逼使理性抬头,哲学种子在理性的光照耀下,逐渐脱离母胎,开始了它的独立活动。(韦政通《从宗教看中国哲学的起源》,载《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台湾水牛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1页)
按照这一断定,中国哲学的成立问题便等价地转换成了中国宗教的成立问题,而中国古已有宗教,有原始宗教,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既然中国宗教是个事实。那么,中国哲学当然也就是个事实了。在这样一种论证语境中,韦政通对中国上古的原始宗教进行了分析,判明其中孕育着后来的哪些哲学概念,比如他说,中国哲学中的“天命”这一概念便是从中国原始宗教中的“帝”这一概念演变而来的,这种演变方向是“向人身接近,然后爆发了哲学的智慧”(同上书,第14页)。
另外,韦政通还特别指出了从哲学起源角度来论证中国哲学之成立的学者在台湾学界不止他一人,也不止他一派观点,他以不指名的方式说,当他正在从事起源论方面的研究时,“经友人的引介,得至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看书,在广泛的阅读中,始悉近人对这方面的问题,也已有了一些成绩。尤其是民族学研究所的几位先生,他们应用考古人类学等方法,对中国上古史中的神话、宗教诸问题的研究,都有很丰盛的创获……我想对研究中国上古哲学的人,总会有些参考价值的。”(韦政通,《中国哲学思想批判》,台湾水牛出版社,1988年10月版,自序第2页。 )韦政通曾在他编著的《中国哲学辞典》中专门备了一个条目,叫“中国哲学起源的问题”,把学界在中国哲学起源问题上的研究观点作了综述,共列举了六条研究线索(注:这六条线索是:(一)以图腾为线索;(二)以天神的演变为线索;(三)以周易为线索,(四)以人文思想的兴起为线索;(五)以羲和之官为线索;(六)以礼、刑为线索。参见韦政通《中国哲学辞典》,台湾大林出版社,1982年3 月版第223—226页。),这些内容虽然各异,但其目的是相同的,即都是想通过确立中国哲学的源头来论证中国哲学之成立。
五、牟宗三“文化要素”论证
这是一种从文化体系角度来俯视哲学的高屋建瓴的论证方法,它把哲学看成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其基本定律是:不管是哪个文化体系,其中必定有哲学因子。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就用这种方法论证了中国哲学的成立(注:该书在台湾和大陆多次重版,最新版本可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的《牟宗三学术论著集·讲座系列·中国哲学的特质》。这本小册子是牟宗三根据自己1961年在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的讲座讲稿整理而成的。鉴于来参加听讲座的人都是些信奉西方文化的青年学生,他们对中国哲学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牟宗三在讲座一开始就浓彩重墨地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自己的哲学,只是这种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该书第一讲“引论”在“中国有没有哲学?”的标题下针对“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所以人们也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样一种普遍性的认识立场坚定地阐述了如下的观点:哲学是“构成一个文化的重要成分、基本成分”,“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因此,如果承认中国的文化体系,自然也承认了中国哲学……说中国没有‘希腊传统’的哲学,没有某种内容形态的哲学,是可以的,说中国没有哲学,便是荒唐了。”(注:同上书,第4页。)牟宗三认为, 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人性活动,而人类对自己的人性活动必然要进行反省,这种反省,不管其形式如何,都是一种哲学活动。他说:“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活动所及,以智慧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久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注:同上书,第4页。 )在牟宗三看来,哲学是一个文化中自我反省的因素,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会衍生出自我反身的因素,即哲学。同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也离不开这个反省因素。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反省方式,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反省方式;西方文化有西方文化的哲学,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哲学,中西文化的不同决定了中西哲学的不同。他告诫道,绝不能以西方哲学的眼光把中国哲学看没了。“说中国以往没有开发出科学与民主政治,那是事实,说宗教与哲学等一起皆没有,那根本是霸道和无知。”(注:同上书,第1—2页。)“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是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注:同上书,第3页。 )牟宗三把哲学界定为文化的自身反省,从而使哲学成为文化中一个必然要素,然后从文化要素的角度来判定中国文化中有哲学,这条思路是言顺意畅的,比较有说服力。
** * *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氛围下,从内容到形式与西方哲学都截然不同的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这是一个围绕了中国学者近一个世纪的问题,以上四位学者对中国哲学成立的论证不但给了我们学理上的启迪,更给了我们信心上的鼓舞:中国文化中有自己独特的哲学,这种哲学虽然不同于西方哲学,但却一点也不逊于西方哲学。今天,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已无人能怀疑,但中国哲学在学理上能否成立依然还是一个经常会被“西方中心主义”者提起的问题,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就有双重任务,除了要研究中国哲学中的思想和方法,还要研究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
标签: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冯友兰论文; 胡适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哲学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