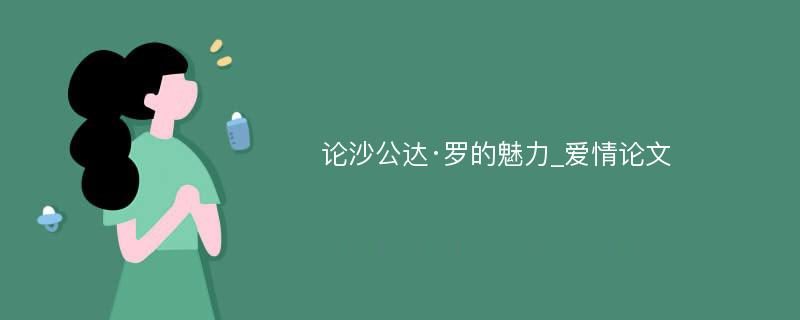
论《沙恭达罗》的魅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魅力论文,沙恭达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印度戏剧家迦梨陀娑的剧作《沙恭达罗》究竟美在哪里?有人说美在人物,因为他刻画了纯真善良、无与伦比的沙恭达罗。这一说法,笔者以为未能充分地、整体地揭示《沙恭达罗》的魅力,也未能达到作者“尽象”“尽意”之境。《沙恭达罗》的美应该是其各种因素综合的体现。不是某一方面造就《沙恭达罗》之美,而是多个方面铸成它的魅力。《沙恭达罗》这一系统中的情节、人物、环境和主题等功能,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这些功能产生合力时,它的整体美的效应就凸显出来。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笔者认为《沙》剧的魅力就是:美在情节、美在爱情、美在人物、美在自然。
一、一波三折的情节之美
古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曾对戏剧六要素作过精当的分析,他认为情节就是一系列连续性动作的安排〔1〕。 亚氏讲的动作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戏剧冲突。一部戏剧要想打动读者,折服观众,就必须精心设计情节,构筑矛盾冲突。没有矛盾冲突,戏剧就无法展开。一般说来,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主题的重要凭借。戏剧的矛盾冲突,其开端、发展、高潮乃至结局,如何安排,如何针针密线,不露破绽,恰恰成了戏剧家思考的重要之点。
《沙》是一部爱情喜剧。它的情节具有山回路转、柳暗花明、跌宕起伏、婀娜多姿的特征。首先,作者在安排矛盾冲突时,往往采用喜中有悲,悲中有喜,悲喜交织,以喜剧气氛笼罩全篇的方法,使平凡的爱情故事显得摇曳多姿,扣人心弦。
该剧剧情是这样的:国王豆扇陀外出打猎,在林中与净修女沙恭达罗邂逅,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一开场,便使戏剧陡增明快的喜之色彩。)尔后,豆扇陀用干闼婆的方式与沙恭达罗秘密结婚。(喜之情力透纸背,悦耳动听的乐曲不绝于耳,爱情喜剧达于第一次高潮。)国王回宫理政,与沙恭达罗告别。(喜剧色调为之一转,进入难舍难分的凄凉之境。哀莫大于生死,悲莫大于别离,这一别,谁料会是什么结局?浓浓的离恨别绪生发剧中。)等到沙恭达罗去见豆扇陀时,他已经记不起她了,于是她被国王遗弃。(此时此刻,观众也为之动容,内心充满恐惧与怜悯之情,与沙恭达罗一起痛斥国王的无耻和不义。刚刚升起的高昂之调,立即降下来,换上了悲怆抑郁的情调。)正当沙恭达罗进退两难之际,女神出于怜惜之情,救她去了幸福乐园。(快要消失的那一丝喜情立刻又随剧情陡变而恢复,昂扬之乐再次升起。)国王恢复记忆,日夜思念被拒的沙恭达罗。他嗟夫长叹,痛悔不已。(作家运用深沉的调子,表现真情之美。外现之象是悲,但内在之情是甜蜜。“悲”不是绝望的痛感,而是思念的快感。真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不久,天帝令豆扇陀去助神灭敌,豆扇陀战胜了天神的敌人,受到天帝的嘉奖:让他去与被遗弃的沙恭达罗团聚。(喜剧大团圆,喜之情达到顶峰,处处洋溢欢快之乐、明亮之色,爱情的颂歌回荡在金顶山——幸福乐园。)
从上面的剧情简介中,可以看出作家对情节安排的不同凡响:完全排除了单一情调对读者感情的控制,剧情张弛相间,颇有动态之美学的讲究和辩证的考虑,以悲喜交错,以悲衬喜,使喜情更浓厚,回味更悠长。假若情节全用喜调,那么戏剧只能演到沙恭达罗上京城寻夫,与夫相见便告结束。果真如此,则剧本描写的仅仅是一曲平淡无奇的爱情游戏。
《沙》剧情节的第二个特点是矛盾冲突“险象环生”,采用伏笔照应、环环相扣的方法,让观众在捧腹中获得美的享受。全剧分七幕。第一幕叫做“狩猎”,为故事的开端。国王豆扇陀率随从来林中打猎,惊喜地看到赛过后宫佳丽的沙恭达罗,顿生爱幕之情。他忙向沙恭达罗的女友打探,得知她是一名净修女,但义父想给她择一门亲结婚。这一伏笔为后来豆扇陀与她恋爱以及义父让她上京城寻夫的情节作了铺垫。如果没有净修,就没有国王与她林中相遇。如果没有义父恩准,就不会有她上京寻夫的事实发生。因而,后面的情节发展都依赖于这一小小的伏笔,矛盾冲突也得以展开。第二幕至第四幕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分别叫做“故事的隐藏”、“爱情的享受”、“沙恭达罗的别离”。这一部分集中笔墨描写豆扇陀与沙恭达罗闪电式的爱情。他们恋爱结婚进展顺利,但情节却有波澜起伏。国王回宫不能带走心上人,无疑增加了恋人们的离愁别恨和思念的痛苦。同时又引发了读者的种种猜测:国王回宫还会记得乡野女子沙恭达罗吗?他的离去是否是金蝉脱壳计?他会始乱终弃吗?假如所赠信物丢失,他会认沙恭达罗吗?正是针对这诸多的悬念,作家又设了一伏笔,安排了一矛盾冲突:沙恭达罗因沉湎于对国王的深深思念之中,而怠慢了大仙人达罗婆娑,大仙发出诅咒:定要她遭受一段磨难。这一细节安排极妙!这“扭转乾坤”的神来之笔避免了戏剧未蓄足气势便匆忙结局的尴尬处境,它为剧情的发展和进入高潮构筑了坚实的基石。第五幕、第六幕写沙恭达罗的被拒和被弃。沙恭达罗去王宫途中,由于不慎,将戒指滑落水中。见了国王,因无信物,被国王拒绝。沙恭达罗悲痛之余,怒斥国王的不义。情节至此,完全可结束全剧,只是全然改变了它的性质,成了一出典型的悲剧。而作家是表现爱情喜剧,是故,情节作了转折,让沙恭达罗从逆境走向顺境——女神救她离宫,置她于幸福乐园。这又为第七幕夫妻俩的大团圆作了埋伏。因此,读者不难发现作家的匠心独运:他有条不紊地展开他的故事,经营喜剧的结构,宛如一个经验丰富的猎手,先拿出了弓箭瞄准,然后拉开大弓,最后击中目标,一环套一环,方寸不乱,使常见不鲜的爱情故事充满生机,五彩斑斓,晶莹夺目。
二、情真意切的爱情之美
在风景如画的净修林,豆扇陀为美丽似仙的沙恭达罗所吸引。他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伪装成研究吠陀的学生,向沙恭达罗致意,向她的两个女友甜言密语地询问她的身世。当听到她本人虽想净修,她的义父却有意让她出嫁的时候,国王欣喜异常。沙恭达罗站在一旁,一言不发,可是她的内心却很不平静。她独白道:“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指国王)以后,就对他怀着一种好感?这是净修林的清规所不允许的。”〔2〕 她的表情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如国王所形容的那样:“我说话的时候,她虽然不搀言接语,我一说,她就倾耳细听。即使她不跟我面对面站着,她的眼光可也没向别的东西上转动。”一个有情,一个有意,两个人的感情相撞合流。净修林的清规戒律却被爱情的力量所冲破。国王大胆直率地向沙恭达罗表白衷情。沙恭达罗开始则百般推却,无法接受他的爱情。然而,火热的情感又使她节节败退,就连防卫的一点微薄之力也没有了。只得一再声称“我自己做不了主,或者说,这两个朋友是管我的”,“我只怨自己的命”,“我自己不自由”。她转移视线,避实就虚,悄悄地“投降”了。终于,她与国王私订了终身。这样,净修女在生意盎然、宁静详和的大自然里与国王完成了大事。爱情一帆风顺,未经曲折,如诗如画。作家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地描绘了豆扇陀与沙恭达罗的热恋。
豆扇陀与沙恭达罗爱情的第二个阶段是历经曲折的相思之苦,这是爱的深化。相思之苦的重要表现,一是别离,二是痛悔。国王走了,沙恭达罗日见不安,害上了相思病。她失魂落魄,爱得那么痴迷,那么忘我。居然大仙人的到来,她也浑然不觉。仙人给她惩罚:豆扇陀再不会记起她。爱遭到了神力的破坏。果然,她见到国王后,豆扇陀不予理睬。后来,豆扇陀见了戒指,记忆恢复,可美人已失,后悔不迭。他一会儿叹息,一会儿沉思,郁郁寡欢,茶饭不思,肤色惨淡,形容憔悴,心里充满痛苦。他不停地责骂自己:“无知的东西不知道好坏。我为什么把我爱人拒在门外?”“爱人呀!这个人毫无理由地遗弃了你,他心里悔恨得像火烧一般,什么时候再可怜他一下让他看你一眼呢?”国王的真诚痛悔,也反映了他的一腔深情。男女主人公在受挫折坎坷之时,始终对爱情坚贞不渝、执着坚定。作家细腻地展示了相思的全过程,检验了他们两者爱情的品质,从而使初恋之爱经受住了考验,使初恋之爱向更深层领域渗透。戏剧再一次彰明了爱情之美的魅力。
豆扇陀与沙恭达罗爱情生活的第三个阶段是展现人伦之美。身怀六甲的沙恭达罗被神仙救到金顶山。在那里,她平安地生下儿子,独自承担了抚养儿子的义务。豆扇陀的痛悔和深情感动了神仙。于是神仙安排他与妻、与子相逢团聚,并劝解这对夫妻握手言欢,预言他们的儿子将会成为轮转圣王,统治天下。沙恭达罗由纯情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合法的高大的母亲。她除了善待侍奉丈夫之外,还肩负培养英勇圣王婆罗多的责任。她与豆扇陀的爱情生活又加入了父子、母子之爱,这种爱已超越纯粹的男女亲昵之情的范畴,它成了沟通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天伦之爱。这是爱情的结果,也是爱情的必然趋势,人伦之爱是深化、巩固他们爱情的重要纽带。它同样是古代社会永葆爱情青春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因而,作家安排他们夫妻、父子团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它显示了爱情力量的伟大和爱情之美的魅力。
当然,豆扇陀与沙恭达罗生活在古代印度等级森严的社会,要想过上没有阶级、没有私心杂念的浪漫理想之爱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事。作家大肆渲染的环境和描写的爱情多少有些爱情至上主义的嫌疑。何况他们的爱本身就缺少深厚的基础。丑角的话倒是一种醒世的警示:万岁爷享受了后宫佳丽又打乡间野女的主意。作家的旁敲侧击只能略表“寸意”。作为宫廷诗人,他只能点到为止。他昭示国王最初的动机是令人可信的。他没能按这条思路走下去,恐怕是出于免遭杀身之祸的考虑。
三、鲜明独特的形象之美
沙恭达罗是一个纯洁自然、美丽动人、温柔多情的女性形象。作家采取正面描写、侧面衬托、内外结合的方法来完成对她的刻画。
正面描写她的纯洁自然和温柔多情是作家刻画人物性格最见力度的方法。如戏剧开头写她的天真无邪、纯洁自然就非常成功。豆扇陀对她一见钟情,向她发起猛攻。她开始有些不知所措,胆怯腼腆,脸上充满红晕。她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也从未听到过这种甜言密语,作为少女的她,焉有不慌之理?她表面上装得很平静,但内心有如大海波涛,她的“怀春”之情被引发了。她爱上豆扇陀,决不是因为她高攀上了国王,而是找到了一个少女可以依托的人,这表现了她对自由的爱情的追求。戏剧展现她的温柔多情,主要借助于“惜别”的场面。沙恭达罗为了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她不得不离开净修林。她爱豆扇陀,也热爱自己的女友、义父,爱净修林的花草树木、山山水水和各种动物。不去京城又难排解愁思,真到离去时,又难舍亲人。她脚步沉重,眼中噙满泪水。她拥抱了蔓藤,抚摸了小鹿,拉着女友依依不舍。她渴求夫君之爱,又不愿抛舍朋友情,这使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作家细致地展露了她的复杂情感世界。其情可掬,可状可憨,其言可真。把一个多情的女子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家也没有忽视从侧面衬托她的外貌之美。她是青春之美的象征,她秀色天成,自然清新。作家借豆扇陀之口对她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她的下唇像蓓蕾一样鲜艳,两臂像嫩枝一般柔软,魅人的青春洋溢在四肢上,像花朵一般。
沙恭达罗的美,不仅表现在迷人的身影和外貌,更表现在她内在品质的坚强和勇敢。她与豆扇陀自由恋爱结合,既没有尊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也没有正式的婚姻礼节,就用干闼婆的方式完成了终身大事。表面上看,这违背了当时的婚姻常规,实际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是其勇敢叛逆精神的体现。据说,用这种方式结婚生的儿子“残酷无情,口说谎言,厌恶吠陀和圣法”。沙恭达罗反其道而行之,偏偏选择了这种自由结合式,这无疑是对当时习俗的回击。
京城见夫和夫君不认的场面也有力地表现了沙恭达罗的内在品质。她没有央求和劝告,而是不卑不亢,义正辞严地谴责国王无耻,她对爱情的追求是执着的,她不允许背信弃义的行为。她要争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那怕这种力量收效甚微,但她丝毫不放弃自己的原则。沙恭达罗不愧为反抗印度夫权社会的女杰。作者歌颂具有叛逆性质的婚姻,赞美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幸福的热爱和向往。歌德读了此剧之后,挥毫赞美这一形象:“悠悠天隅,恢恢地轮,彼美一人,沙恭达纶。”〔3〕
作者把沙恭达罗作为完美无缺的理想女性来塑造,同样也把国王豆扇陀描绘成理想的贤明君主。他不仅具有高雅的情趣,而且还具有勇敢的特征。他对沙恭达罗的爱是真挚的,不是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而拈花惹草。他用干闼婆方式与沙恭达罗结婚表明了他对当时不自由的婚姻制度的叛逆。沙恭达罗被拒,完全是神力所阻,非他本人的意愿。他见信物恢复了记忆后,不断地责骂自己,是诚心诚意的悔过。他为一个社会地位无足轻重的小女子担忧,甚至赞美她的懿行,表现了他的宽厚仁爱、勇于改过的美德。他对沙恭达罗一往情深的思念,几乎使他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地步。当他接到天帝的命令,要他去平定大乱时,他又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使命,立即从个人的忧郁与苦闷中振作起来,在战斗中表现得极为勇敢。
作者从正面表现了豆扇陀的美德,也从侧面暗示了他的不良行为,隐约含蓄地表达了对他的缺点的批判,讽刺了他那喜新厌旧的态度。他追求沙恭达罗时,丑角有一句嘲弄他的台词:“啊!正如一个厌恶了枣子的人想得到罗望子一般,万岁爷享受过了后宫的美女,现在又来打她的主意。”在第五幕里,皇后恒娑婆抵也有一句对国王不满的唱词:“蜜峰呀!你贪吃新密曾吻过芒果的花苞,你愉快地呆在荷花心里,为什么把它忘掉?”正因为这样,当我们读这部佳作时,总觉得豆扇陀的所作所为有些毛病,远远不如沙恭达罗那样完美。正面描写,侧面衬托,使豆扇陀这一形象更显真实、更具特征。
沙恭达罗和豆扇陀不仅是古代印度戏剧文学中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而且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人物。他们令东西方读者惊喜,也受到了像席勒、歌德等这些伟大戏剧家的赞扬。他们的魅力将永远吸引住人们的目光。
四、陶冶情操的自然之美
《沙恭达罗》是一曲爱情颂歌,也是一首田园牧歌。作者勾画的那一幅幅如诗如画的风景图令读者陶醉。大自然中的山、水、林、日、月、草以及各种可爱的动物构成了人物活动的最佳背景。它们要么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人物情感的折射,要么是与人物一起共鸣的拟人化物象,要么是渲染气氛的烘托物,要么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向导和催化剂。总之,它们在戏剧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沙恭达罗的纯真性格,乃为大自然薰染所致。你瞧那边的净修林:清清的河水,微风吹拂,波光粼粼,有时如明镜,有时似绉缬。葱翠的树木,蓊蓊郁郁。一鸟鸣叫,百鸟共转。野兽在悠然地徘徊,无拘无束,小鹿依着人形影不离,似通人性。净修林是多么的宁静详和,又是何等的富有生机。沙恭达罗就生长在这美丽的大自然里,她汲取天之灵地之气,她的美丽宛若大自然的瑰宝一样晶莹明亮。她的纯洁与温柔,她的真挚和多情,完全在此找到其源头。
沙恭达罗别离净修林,人与物相向共鸣,互话衷肠,同道祝福,依依不舍,表现主体与客体的灵犀沟通。其情其景无不动人心魄:“小鹿吐出了满嘴的达梨薄草,孔雀不再舞蹈,蔓藤甩掉了褪了色的叶子,仿佛把自己的肢体甩掉。”这些拟人化的动植物对主人的离去,无限伤感。受过沙恭达罗恩惠的小鹿,一步也不离主人的左右,她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这里人与物、情与景,完全融为一体。
沙恭达罗的女友阿奴苏耶的一些话把别离的氛围推向高潮:“朋友呀!在我们净修林里,没有一个有情的动物今天不为了你的别离而伤心。你看呀!那野鸭不理藏在荷花丛里叫唤的母鸭,它只注视着你。”由物及人,使我们想到了沙恭达罗的温存,她的泛爱主义,她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追求,她的博爱,她的完美……景物凸现了她的性格,昭示了她的情趣。没有她与动植物的对话,没有动植物对她的回应,沙恭达罗的个性特征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丰富完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情”就是沙恭达罗之情、作者之情、动植物之情的综合体现。每读“别离”一幕,都要对女主人油然而生敬意,并伴之以博大胸怀的感觉,人格也觉得得到了升华。
景物描写既可烘托气氛,展示人物性格,又可以预示情节,推动情节发展。沙恭达罗得罪仙人之后,干闼婆的徒弟连续唱了四段描绘景物的歌词。其中有二段是这样的:“好哇,天亮了!因为在那一边,月亮正落到西山顶上,在另一边,太阳以朝霞作前驱正在露面。日月二光在同一个时候一升一降,似乎就象征着人世间的升沉变幻。/而且——月落之后,白色的夜莲不再悦目。只在回想里残留着它的光艳。爱人远在天涯,闺中的愁思,一个柔弱的女子万难承担。”这两段景物描写是对沙恭达罗日后磨难的提示与交代,它起到了勾连前后情节的作用。同时,从观众的心理角度来看,这是对观众“期待视野”的警示:以免后来的情节大起大落而使观众难以承受和倍感不真。
《沙恭达罗》这部戏剧,就它的景物描绘来讲,无疑是一首首田园风景诗;就它的情节来说,又是一首浪漫抒情曲。浪漫配合着风景,成为了古代印度人民追求理想生活的佳境。不管作者怎样调和矛盾,美化统治者,但是愿有情人终成眷属与生活和蔼美满的愿望,却是全人类共同一致的理想。这就是《沙》剧美的魅力的显示和昭告。
《沙恭达罗》这一系统工程的每一功能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但是只有当它们整体综合地配合与协调时,其独特的魅力才完全彰显。这就诚如上面所说:风景离不开浪漫(爱情故事),浪漫需要风景配合,而这两者又需要精心的构造(情节)。离开了它们中的那一部分,或者撇开那一部分不谈,都难以揭示《沙恭达罗》的独特魅力。
注释:
〔1〕参见罗念生译《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亚里斯多德的戏剧六要素是:情节、人物、思想、言词、扮相和歌曲。
〔2〕季羡林译《沙恭达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文中所引的内容,均取自季先生译本,以下不再注明。
〔3〕王忠祥、宋寅展、彭端智主编《外国文学教程》下册,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第70页。收稿日期:1997—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