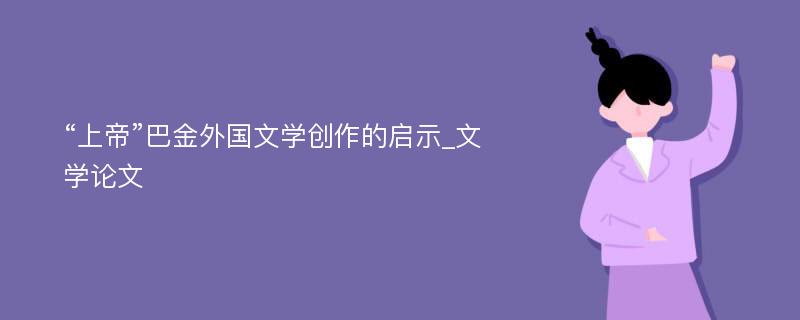
《神》的启示——巴金的异域文学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域论文,巴金论文,启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位像巴金那样的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丰富的异 域文学写作的人。这一切,当然离不开巴金的留法经历。然而,与其说留法成就了巴金 的“国际化”写作,不如说留法强化了这种写作。因为早在留法之前,巴金在西方的“ 无政府主义”乌托邦里浸染已久,并且饱读西方文学作品,确立了“为人类而奋斗”的 人生信仰(注:据巴金自述,他15岁就接触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的文章,被其“ 雄辩的论据,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问,简明的文体,带煽动的笔调”所征服,而称其 为“我的精神上的母亲”,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巴金的异域文学写作并非始于留法时代,而是回国一年半之后。一个 奇异的梦,成了这种写作的契机。巴金日后这样回忆:
在一九三○年七月的某一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来。在黑暗中我还看见一些悲惨的景 象,我的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再睡下去,就起来扭开电灯,在清净的夜里一口 气写完了那篇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 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的带睡意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中 挂着大片粉红的云霞……(注: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见《巴金写作生涯》,100 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以《洛伯尔先生》为发端,巴金一口气写出了十几篇题材相同的作品,它们以法国生 活为背景,笔下所及,有法国人、犹太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俄罗斯人,巴 金供献给中国文坛的第一个小说集子《复仇》,就是这些作品的集合。然而,巴金没有 就此罢手,源源不断地写出了《好人》、《未寄的信》、《马赛的夜》、《爱》、《在 门槛上》,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历史小说《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罗伯斯 庇尔的秘密》和取材法国报刊新闻的《罪与罚》,还有以旅居中国东北的俄侨为题材的 《将军》,后来,又根据自己的日本体验写了《神》、《鬼》、《人》。巴金以如椽之 笔,横扫了大半个地球,在写作题材的广度上,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气魄(注:巴金的这 种写作,一直待续到1949年以后,这次是配合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反映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和出访东欧、日本、印度的散文,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产 品。作品集有《保卫和平的人们》、《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华沙城的节日》、《 倾吐不尽的感情》等,进入新时期后,巴金又写下了著名的反纳粹散文《在奥斯威辛集 中营》。)。
巴金的国际题材作品可分两类:一类根据自己在异域的现实生活写成,如《复仇》里 的《房东太太》、《亚丽安娜》、《初恋》和《神》、《鬼》、《人》;另一类是在西 方文学阅读经验基础之上的二度创造,可分两种。一种是直接脱胎于某外国小说,比如 《哑了的三角琴》,就是根据一位美国新闻记者的英文原作改写而成,《爱》和《好人 》则是莫泊桑的《模特儿》的大同小异的翻版;另一种是在此基础上的自由改编,如《 洛伯尔先生》。然而,无论哪一类作品,无论哪一篇作品,都含有一个明显的“二元对 立”的主题模式:善与恶(《不幸的人》)、贫与富(《狮子》)、灵与肉(《爱的摧残》) 、自由与禁锢(《亡命》《亚丽安娜》)、正义与邪恶(《复仇》)、青春与衰朽(《老年 》)、黑暗与光明(《利娜》),神与人(《神》),甚至连父爱与情爱(《父与女》),都 纳入这种模式。
巴金的这些作品给人最大的惊异莫过于:它们几乎不像出自中国作家的手笔,且不说 那批直接(或间接)脱胎于外国小说的作品,其内涵与格调与外国翻译小说简直没有什么 区别(注:当然,这两种作品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实上,更多 的作品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比如《父与女》、《爱的摧残》、《狮子》等,由于作者未 作明确的交待,我们无法指出其出处。),就是那些根据巴金在法国的亲身经历写成的 作品,也充满着洋味,感觉不到多少本土的气息。中国学子初到异域的陌生感、惶恐感 ,由此引发的种族歧视、文化差异,这一类“留学生写作”经常触及的问题,在巴金笔 下几乎没有涉及(注:《未寄的信》写跨国恋爱,中国学子因怯于种族的障碍,最终拒 绝了法国姑娘的爱,回国以后又深深地后悔。小说完全无意探讨“种族文化”与爱情的 关系,而是将它处理成一则伤感的爱情故事。)。
毋庸讳言,从艺术的角度看,巴金的这类写作带有“率尔操弧”的性质。巴金在法国 的时间不足两年,法语尚不地道,活动范围仅限于巴黎一角和法国小城沙多—吉里两地 ,并且大部分时间耗费在书桌案头(注:这一点巴金自己也不否认,他说:“我在法国 住了不到两年,连法文也没有学好。但是我每天都得跟法国人接触,也多少看到一点外 国人的生活。我所看到的不用说只是表面。单单根据它来写小说是不够的。”在法国不 到两年的时间里,巴金创作了处女作《灭亡》,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阅读 了屠格涅夫、左拉、罗曼·罗兰、莫泊桑等人的文学作品和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大量著作 ,还积极参与援救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樊宰底和沙珂的运动。),对法国的了解程度可 想而知。巴金自己也承认,他是在缺乏艺术准备的情况下投入这种写作的:“我事先并 没有想好结构,就动笔写小说,让人物自己在那个环境里生活,通过编造的故事,倾吐 我的感情。”(注: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见《巴金写作生涯》,496页,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洛伯尔先生》的写作过程也证明,是一种非凡的道德激 情,驱使他拿起了笔。
关于《复仇》的写作动机,作者在“序”里这样表白:“这(几篇小说)是人类的痛苦 的呼吁。我虽不能苦人类之苦,而我却是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的。”“虽然只是几篇 短短的小说,但人类的悲哀却在这里面展开了。有被战争夺去了爱儿的法国老妇,有为 恋爱所苦恼的意大利的贫乐师,有为自己的爱妻和同胞复仇的犹太青年,有无力升学的 法国学生,有意大利的亡命者,有薄命的法国女子,有波兰的女革命家,有监牢中的俄 国囚徒。他们同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是同样的具有人性的生物。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 样的东西——青春,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为 他们所知道、所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注: 巴金:《复仇》,见《巴金全集》,第9集,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巴金充满感情,他说:“这些文章都是一种痛苦的回忆驱使着我写 出来的。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我底朋友,都留着我底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现在 我读着它们,还会感到一种温情,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写作生活的 回顾》))
当仁不让地以“人类”的代言人自许,巴金的自信和自负由此可见。然而,艺术的本 质并不服从道德激情,博大的“人类”情怀,没有切实的人生经验作铺垫,势必变得空 泛。文学写作面对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那种背负着独特的种族、文化风土的 人。因为缺少这样的具体可感的人,巴金的“地球村”显得单调划一,巴金笔下的“老 外”,无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还是波兰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从本质 上讲,是没有民族性与地域性差异的“平面人”——犹如那种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语 ”。在神圣的道德激情驱使下,巴金毫不费力地飞越了种族、文化的鸿沟,却不可避免 地掉入艺术的陷阱(注:在《生的忏悔》中,巴金这样叙述自己的创作过程:“我缺乏 艺术家的气质;我不能像创造一件艺术品那样,来写一本小说。当我写的时候,我忘记 了自己,简单变成了一件工具;我既没有空也没有这份客观,来选择我的题材和形式。 像我在《电》的前言里所说的,我一写作,自己的身子便不存在了。在我的眼前,出现 一团暗影,影子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一连串悲剧性的画面,我的心仿佛被一根鞭子在 抽打着;它跳动不息,而我的手也开始在纸上移动起来,完全不受控制。许多许多人抓 住了我的笔,诉说着他们的悲伤。你想我还怎么能够再注意形式、故事、观点,以及其 它种种琐碎的事情呢?我几乎是情不自己的。一种力量迫使着我,要我在大量生产的情 形下寻求满足;我无法抗拒这种力量,它已经变成我习惯的一部分了。”这种狂热的激 情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道德的。)。
巴金的“国际题材”写作有一个显见的特点:几乎所有作品都以第一人称写成。这种 写法当然不是巴金自己的发明,而是从俄国师傅屠格涅夫那里学来的。然而,屠格涅夫 的第一人称写法到了巴金手里,被大大地简便化、实用化了。对此,巴金有过诚实的交 代:“我开始写短篇的时候,从法国回来不久,还常常怀念那边的生活同少数的熟人, 也颇想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所以拿起笔来写小说,倾吐感情,我就采用了法国生活的 题材。然而又因为自己对那种生活知道得不多,就自然地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讲故事的写 法。”“屠格涅夫喜欢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 太多,不过他认为只要讲出重要的几句话就够了。……我却不然,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 小说,倒是因为我知道得实在有限。自己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这样写起来, 的确很方便。”(注: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见《巴金写作生涯》,493页,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事情确实如此,如果说,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屠格涅 夫是十八般武艺中的一种,是表现屠格涅夫式的朴素风格的有力手段的话,那么在巴金 ,第一人称是最容易操作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其功能,仅限于讲故事、倾吐感情。
然而,巴金也有超越师傅的地方。屠格涅夫的第一人称“我”,都是俄国人,不管是 作者本人,还是别的什么人,文化身份相当明确,显示了屠格涅夫严谨的现实主义写作 态度,而巴金的第一人称“我”,却可以超越种族和国家,其中不仅有中国人,更多的 是法国人。这个“我”,在《洛伯尔先生》里是一个法国少年,叫作雅克,一个不幸的 私生子;在《狮子》里叫布勒芒,一个不谙人世苦难的法国富家子弟;在《亡命》里叫 维克多,一位与外国亡命客有交往的法国大学生;在《父与女》里叫酿莱,一个在父爱 与情爱两难中徘徊的善良法国少女;在《哑了的三角琴》里,他又成了一个俄国外交官 的儿子……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创作现象。当巴金把“我”想象成一个法国人,通过这个法国人 的眼睛审视人世间的种种悲惨和不平,甚至一本正经地“替法国人惭愧”(《亡命》)的 时候,他一定不觉得这有什么困难。而在现实中,这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固然可 以超越种族、地域的差异,在纯理性的层面上理解西方人与西方文化。然而,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不同的生活环境、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决定了一个国家(民族)的人无法在 感性层面上真实地想象另一个国家(民族)的人。于是,一切只有依赖主观的想象。碰巧 ,那时的巴金正沉浸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国”中,那种主观的想象不由得越发真实, 呼之欲出。在巴金及其同志看来,国家、政府乃至种族之类,都是落后腐朽、注定消亡 的东西,一个没有国界、没有阶级、没有权力组织的伟大的大同世界将在世界上诞生( 注:正如《复仇》开场描写的那样:在一个风景优美、河流环抱的乡村,一批国籍不明 的人士生活在一起,读书、打猎、划船、游泳,空下来时闲谈各种有益的话题,探讨理 想的社会,不失为一幅融融泄泄的“无政府主义”现代乐园。)。第一人称“我”的国 际化,与巴金的这种“无政府”信仰,应当说有着内存的、合乎逻辑的联系。从这个意 义看,这个“我”无论由哪一国人担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替“人类”诉苦申冤 。
这种“人类公民”式的“老外”,无疑是外国人实像的幻化与变形,操纵这种变形的 ,却是一只看不见的历史的巨手。科学与物质生产的飞速发展使得地球一下子变小,其 结果正如马克思阐明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 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 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 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共产党宣言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阶级意识的 觉醒,使人类社会的进步有了必然的方向:无产阶级将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终将代 替资本主义;惟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才会在《共产党宣言》里充满自信地向全人类 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毛泽东才会庄严呼唤:“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 的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历史进步的巨手以摧枯拉朽的伟力指引人类告别过去,奔向未来,在新与旧、进步与 反动、光明与黑暗之间立下一道严酷的、非此即彼的界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阶级 性”扩张,扩张到足以替代“人性”的程度,“民族性”自然受到遮蔽。巴金的国际题 材写作,正体现了这种“历史的想象”。
《神》的写作过程,最能说明问题。
1934年11月,巴金化名黎德瑞,赴日本游学,抵达日本后,由朋友事先的介绍,住进 横滨一个姓武田的横滨商业学校的汉语教授家里。巴金在武田家住了三个月,后来因不 能忍受主人成天念经拜佛而搬出,移往东京。《神》就是巴金住进武田家不久,根据对 主人种种迷信活动的观察,在几天之内写成的。
小说以书简体的形式,描写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小公务员,由一名无神论者变成一个 “有神论”者以后对神的狂信,以及“我”对这种行为全知全能式的分析批判。关于这 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和主题,巴金说得很明白:“我的朋友认识武田(即小说中的长谷川) 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个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 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 ,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他想用宗教来镇压他的‘凡心’, 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 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拼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 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跃进深渊’去。”(注:巴金 :《关于神·鬼·人》,见《巴金写作生涯》,192—193、192、191页,天津:百花文 艺出版社1984年版。)
小说里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一提:主人公的藏书里,除了大量法国和俄国进步作家的 文学名著,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巴枯宁和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大杉荣、河上肇等人 的著作,这一切,都证明着长谷川过去曾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无神论者。40年以后,在巴 金的创作回忆录里,仍清楚地写着:“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 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 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注:巴金: 《关于神·鬼·人》,见《巴金写作生涯》,19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
言之凿凿,武田的“有神论”转向看来是铁的事实。然而,偏偏有人就这个细节提出 了疑问。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神》的主人公长谷川与其 原型武田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差异,现实中的武田,并不像《神》描写的那样,是一个 曾经有自由思想的人,而是一个属于“右翼”的汉语教师,当初出于“雄飞大陆”、报 效大日本帝国的念头选择了中国语专业,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部,后来追随日本汉 语界“右翼”师祖宫越健太郎,毕业后当过他的助手,日后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 国的鹰犬,先是作为一名日本军队的少佐翻译到中国,参加侵占济南的战斗,后来先后 在张家口、包头等地的日军特务机关任职,为日军侵略中国效犬马之劳(注:参见藤井 省三:《东京外语学校支那语部:在侵略与交流的狭隙之间》(日文版),168页,东京 :朝日新闻社1992年版。)。藤井就此疑惑给巴金写信请教,谜底这才解开。巴金回信 说明:那些有思想问题的书,都不是武田的,他有的只是文学书,像蒲鲁东、巴枯宁、 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都是他自己的藏书;并且这样辩解:《神》是一篇小说,而不是新 闻报道,人物与故事没有必要拘泥于生活事实(注:参见藤井省三:《东京外语学校支 那语部:在侵略与交流的狭隙之间》(日文版),129页,东京:朝日新闻社1992年版。) 。
这里涉及文学创作中现实与虚构的复杂关系,很难简单地作结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 ,巴金对武田这个人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因为巴金说得很明确:“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 是生活里的武田君。”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巴金对武田如此的误读呢?究其根源,不 能不追溯到那种不言自明的“有神”/“无神”二元对立的真理及制约其后的绝对的历 史进步观。也就是说,在既定的观念的操纵下,巴金根据一些表象,轻易地想象出一个 无神论者的武田,在此基础上,展开“人”与“神”激烈的冲突。
一切似乎都在作者的明察秋毫中,一如作品中描写的那样:“我知道关于那个自杀的 女子,一定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关于那个死在牢里的无神论者,也一定有一段悲壮的历 史。我如果仔细盘问,他一定会尽情地对我倾吐。但这有什么用呢?那女子不就是一个 生生地被拆散的多情的恋人么?那男子不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同类的一个殉道者 么?这两个人所留下的惨痛的回忆本可以产生出一个伟大、勇敢的人格来,然而如今在 长谷川君身上却作了寻求神通力的鼓舞了。他求神通力,为了要看见他们,不仅是这样 ,他求神通力为了不愿意自己也得到他们的那样的命运。崇高的鼓舞力反而产生了这懦 怯的企图。他是多么不幸的人啊!”(注:《神》,见《巴金全集》,第10集,362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这段文字读来激情洋溢,高屋建瓴,可惜那个真正 的武田,却在作者的眼皮底下悄然溜走,不能不使人感慨万千!
应当说,《神》的写作与巴金以往的国际题材写作有所不同,如果说后者是属于“写 意”的话,这回却是地道的“对景写生”。巴金的写作场所,就在武田家,用巴金的话 说:“我自己就在生活里面,小说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 经历如实地写下去。”(注:巴金:《关于神·鬼·人》,见《巴金写作生涯》,191页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然而,这种“对景写生”式的写作没有给这篇小 说带来整体意义上的“真实”。这说明:当观察生活的眼睛为某种先入之见偏引时,是 不容易看到生活的本相的。按常规讲,初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人生地疏,本应虚下 心来,以空白的感觉体验那里的一切,才能有所发现,描写才可能到位。不妨这样设想 :假如巴金对日本的文化历史、日本人的民族性有足够的了解,或者退一步说,假如巴 金不是那样的自信,不屈从急近的写作冲动,而能以客观冷静之眼观察周围的生活,情 形大约会是另一种样子。
以西方的“有神”、“无神”观念解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本来就很牵强。日本向来 是一个“人”、“神”难分的国度,求神问佛,消灾祈福,在日本原是家常便饭。所以 ,如果一定要作硬性的区分,那么只能说:日本人的绝大多数都是“有神论”者,但这 个“神”不是西方的上帝,而是“万世一系”的“活神仙”——天皇,这个“神”作为 日本的象征,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民众的心,凝聚着大和民族的精神,甚至可以成为日 本富国强兵、实现“近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巴金在日本游学的时候,正是这个“神 ”大发其威、神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包括武田在内的许多日本文化人成为侵略中国的鹰 犬,与这个“神”的激励不无关系。可惜的是,如此重要的现实竟不在巴金的视野中, 不能不叫人产生“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感慨!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就这样 轻易地消融到了“人类”的普遍性中。对于这一点日本学人看得很清楚,日本著名评论 家竹内好这样批评《神》:“在《文学》一月号上读了巴金的《神》。是篇微不足道的 东西倒也容易读下去。虽然写了一个叫长谷川的日本人由无神论转向宗教的狂态,但毫 无深度可言。”(注:参见藤井省三:《东京外语学校支那语部:在侵略与交流的狭隙 之间》(日文版),139页,东京:朝日新闻社1992年版。)
根据历史进步的“真理”改编生活的真实,是巴金一向的做法(注:比如在《家》的写 作中,为了加强对封建家族制控诉的力度,作者将现实生活中安然无恙的大嫂瑞珏与梅 表姐的命运作了大胆的改变,其下场都是毁灭性的。)。由于时代潮流的激荡,加上个 人的生活经历(指巴金对封建大家族的阴暗记忆),使巴金义无反顾地“反传统”,对西 方文化表现出一面倒的倾斜。不像鲁迅那一辈学人,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具有二重性: 既受其害,也得其惠;正因为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西方文化才能在“拿来”的 同时,迅速地“本土化”,他们才成了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开创者与奠基者。到了巴金 这一代,“反传统”已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在文化选择上,必然表现为全面的“西方 化”与“世界主义”,中国文化逐渐失去内在的根柢。巴金由于个人特殊的原因,在这 条路上走得更远。在抗战期间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中,巴金就主张:“应该保留 的倒是民族精神,而不是形式。现在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了。我们的经济组织、政治组织 、生活样式都改变了。思想的表现方式,写作的形式自然也应该改变。……我觉得,我 们在这时候正应摔掉一切过去的阴影,以一种新的力量向新的路上迈进,不要让种种旧 的形式抓住我们的灵魂。”(注:巴金:《无题》,见《巴金研究资料》,163页,海峡 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这种将“形式”与“精神”的割裂,并没有考虑艺术的“本土 性”规律,极容易导致民族文化的空虚化和“他者化”,后来的中国文学创作实况,业 已证明了这一点。
40年以后,瑞士作家马德兰·桑契曾就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问题采访巴金。 马德兰有感于“中国目前出现的西方化倾向太显著”,向巴金请教“克服”的办法。巴 金却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成立,理由是:“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 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巴金还以身说法,说明中国文学并不存在“西方 化”的危机:“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的,以后也就顺着这个条道路走去 。但我笔下的绝大多数人物始终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也是中国人的思想感情。我 多次翻看自己的旧作,我并不觉得我用的那种形式跟我所写的内容不协调,不适应。我 的作品来自中国社会生活,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它们是中国的东西,也是我自己的东西 。”(注:巴金:《一封回信》,见《巴金写作生涯》,54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这番表白作为巴金个人的选择当然无可辩驳,然而巴金究竟在何种程度上 写出了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其包含的艺术价值究竟有多少,仍是值得深思的。
著作等身、文名至巨的巴金一再否认自己是个“文学家”,是个“艺术家”,这个令 人费解的姿态中包含着复杂的意味,其中既有艺术上的自知之明,也有对“为艺术而艺 术”的藐视,更有作为“人类”代言人的自负和为了“人类”而不惜牺牲“艺术”的决 绝;在表明巴金特立独行性格的同时,也反映了他精神结构的某种缺失,这个缺失当然 也是那个时代的缺失。在近代特殊的历史处境下,中国的文化不能以更自然、更正常的 方式完成自己的变革,而一再陷于对西方文化的追逐与狂奔中,造成文化精神的深刻分 裂和内在的虚空。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
